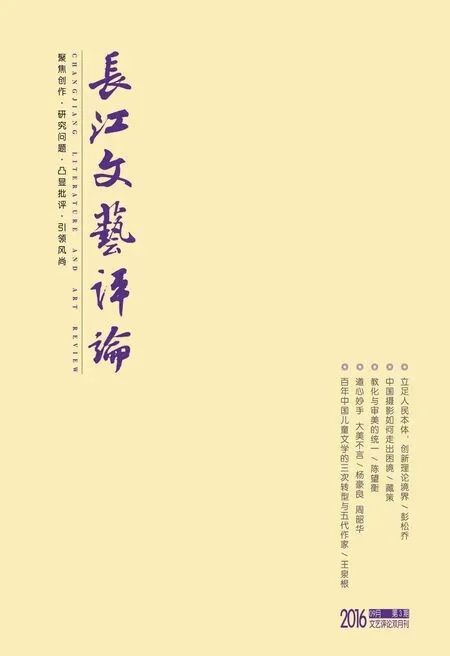写给“我们”的“生死场”
——简评周芳的《重症监护室》
2016-11-25◎叶李
◎叶 李
写给“我们”的“生死场”
——简评周芳的《重症监护室》
◎叶 李
周芳的《重症监护室》尽管未必是“理念先行”,有意地呼应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写作”热潮,在开笔之前即精准定位,可是作品被阅读者、评介者以“非虚构”写作视之不能不说与作家力图回到生命现场去做真实呈现的追求大有关联。当作者带着个人的视角和经验以行动者、亲历者的姿态去写非常态的、特定情境下的人与生活时,对于“真实”的追求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在客观上流为一种为读者的窥视欲和窥私欲提供出口的写作或为猎奇者描绘生活奇观的写作。“重症监护室”恰恰是那种容纳了非常态的人和生活,难免引发读者窥探之念与好奇心的题材,然而周芳的作品却以从容得当的处理成功地回避了前述危险,显示了创作的价值,其根本在于作者“写真实”背后对于真实的态度、立场是真正地希望“将真实的生活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表达对生活的理解和时代的困境”。作者在创作前,深入重症监护室,在这“生死场”担任义工长达一年,当她作为“行动者”去写“真实”的时候,她用强烈的情感投入、以热满之心血写就的作品,展现了这样的努力——恢复文学对自我、对生命、对时代的真相、对每个个体的困境与其生活价值进行追问的能力,文学的“在场感”和“介入性”也由此彰显。
周芳写作《重症监护室》并不着意于以虚构的方式讲述世俗故事而最终超越世俗来表达一种哲学关怀和提供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寓言,哪怕不是百分百的“非虚构”,作者毕竟是以大量重症监护室手记为基础,用偏于纪实的方式来书写“生死场”。非虚构的纪实性书写仍是这部作品的基本路向——作者选定的路子是“回到现场”,在生与死的交汇点由死而窥生,写出生命的真相、生命的尊严、生命的意义和凡常生活的价值,她要由重症监护室写出“健康地笑着闹着哭着活在这烟火人间”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重症监护室》从最接近死亡的地方来写“生”。作品虽然写了形形色色的死,写死的无奈,写死亡的尊严,但从根本上看,这是一部写“生”的作品,不是为了写“死”,而是要写“活”。整个作品的主题和基调可以用作品中两个人物的名字来概括——王美丽和高兴——生命是美丽的,活着就是值得高兴的事情。这是作者想通过带有纪实色彩的写作传达的她自己的或者说她想与读者交流的“在世”的态度。这种“贴地”式的写作,没有竭力向“形而上”的层面升华,也不试图将具体的生活抽象化,真实的生命经历着的生活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现实自有其力量,真诚地去展现这一切就能让写作的意义敞开。
周芳面对“生死场”里疾病与健康的轮转、生与死的交替,经历这变化中情感体验的跌宕,借用余秀华的句子,在《重症监护室》中写“我在摇摇晃晃的人间”。余秀华的诗也正是因为大胆地吐露灵魂深处的秘密、隐痛、灼伤、挣扎、不能止息的欲望,去书写在摇摇晃晃的人间的“活着”而动人。余秀华面对身体的特殊状况和暗淡的人生现实,要在痛苦中寻找灵魂和生命的出口,所以她选择了诗,她用诗写“活着”,显示生命的韧性。周芳恰恰是在可以享受生命的时刻,选择去接近“死亡”,由生死的交替去写生命的意义。周芳的写作是非常明亮的写作,这种明亮就在于她对于死亡和生命有一种极其严正的态度,尊重死亡,不忧生而惧死,虽然“生死哀切”,然而“因其哀,不忍弃”,投射出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可以说余、周二人从不同的路向上回到了生命的现场,在对“活着”的书写中表现出从真实的生命感受出发,“言说真实体会的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余秀华写在摇摇晃晃的人间活着的诗歌里,那些痛苦几乎是以披肝沥胆的方式对读者形成冲击,冲击不是源于诗人刻意撼人心魂,而正在于这是她写给自我的、毫不设防的心语,是诗人与自我灵魂的对话。诗人笔下的“活着”是写给“我”的。《重症监护室》里,作家窥死而悟生,带着饱满的情感写“生死场”、写“活着”,不只是写给“我”的,更是写给“我们”的——把自己所感受所领悟的,写给每一个在世的生命,通过“我”眼中的重症监护室来向不必走进、不能走进、未曾走进重症监护室的人们展现生命的意义。“非虚构写作中的‘我’都是开放的,她愿意和世界交流。——以‘我’的视角书写‘我’眼中的世界,虽然带有‘我’的认识、理解、情感,但最终的写作目的是渴望‘我’眼中的世界被更多的人所知晓……”周芳的《重症监护室》不管是不是严格的“非虚构”写作,作者那种交流式的开放的写作无疑契合上述判断。
重症监护室封闭而隔绝,周芳的写作却是开放的、愿意和世界交流的写作,她要把“生死场”写给“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方式?从作家基本的观点和立场不难找到答案。她在表达情感、判断、思考更具个人化色彩的补记里引弥尔顿的诗:
无论谁死了
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
为我,也为你
每个人并非彼此隔绝的孤岛,在生命沉湖的最深处,我们实则枝蔓相依,这是作家的体悟和观点;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的我,要为我之外的人们——我自己的一部分做担当,这是作家的立场,没有人应该超然事外,袖手旁观。《重症监护室》不单单是写给“我”,也写给“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同样,立场也决定了作者的写作姿态,她是进入重症室的观察者,却以融入者的姿态写作。整体而言,《重症监护室》是投入生活的写作,而不仅仅是观察生活的写作。怎么实现由观察向融入的切进,怎么由重症室中他者身份向融入者身份的转换,多重身份和视角的引入显示了作者的叙事智慧。作者尽量避免身份的单一和视角的固化,她有几重身份——护校教师,然后进入重症监护室当义工,成为这个特殊环境中的他者、护理人员、观察者。然而同时,她又巧妙地利用补记赋予叙述人“我”以“普通人”甚至“病人”的身份与视角。补记是作者的妙招。作品本来就是以义工手记为基础创作而成,当然不存在边写边漏,需要事后拾遗补漏的情况,实乃作者刻意为之。刻意处体现的正是作者的叙述策略:通过补记,她把重症监护室里的生活向外延伸,延伸到社会,延伸到自己的家庭,延伸到自己个人的生活与人际关系中,补记连接了重症监护室和我的世界乃至外面的世界,补记也消除了叙述人“我”和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们及其家属之间的区隔。你是“我们”、他是“我们”、叙述人也是“我们”中的一部分——补记里,作者得以从病室抽身返归到日常的生活空间中,回到更私密的个人的家庭生活中,回到凝视自己内心而获得意义的那些瞬间,用跟病人乃至跟他们家属共同的最普通的身份——妻子、女儿、母亲、一个社会人的身份来谈生论死,来描摹那些灌注了情感的最日常的生活细节、来写自己心灵的每一次波动、自己的每一点思考。于是,重症监护室的生活就不是孤岛上的生活,而是跟“我”的生活牵连起来,重症室里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我”的生活也是“我们”的生活。“我”的情绪、生命体验、困惑与思考就有了跟病室里的人们的悲喜哀痛的连通性或者说具有了一种共通感。这样“我”就不再仅仅是“他们”生活的观察者,也是“我们”生活的体验者和投入者,彼此的情感、命运、处境实则连通交融。何况,作者还有意地在作品中,于补记之外,用专章写了自己作为住院病人在医院里的万千思绪,经历的情感起伏,还有对于生、死的深切体悟,更直接地以住院亲历者的身份、视角去写“生死场”,用多重身份与视角的补充写出层次丰富的生命体验,不武断地以观察者的所得取代亲历者的实感,使“真实”真正地敞开,而非幽闭在单向度的叙述之中,让“真实”于多侧面的复杂表现中充满令人信服的力量。
周芳的《重症监护室》是她大胆尝试的转型之作,更是一部成功之作,说它成功,不仅在于“自古成功在尝试”,更在于作品有意疏离独语或私语式的写作,倾注心血,关怀远方: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无论谁死了,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远方不在别处,就在重症室,就在生死线,因为这里是离死亡最近,离生最远的地方。写给“我们”的《重症监护室》根本不指望用冷静精确的叙述当作刺向社会问题的解剖刀,它不排斥情绪的介入和情感的力量,因为它正是怀着一种“赤地意识”去书写——“我”和这个时代的每个个体一同悲喜,一同经历变化,一道在生活的跌宕起伏中心怀期待,彼此关怀,一起向着远方行走在中国这片火热的赤地之上。我身经目见的、我感怀于内的、我醒觉开悟的“都是大地、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一部分。”这样充满温度和生命力的写作值得珍视,也期待它永远“未完待续”,一直“在路上”。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学术发展计划“区域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的传承构建”学术团队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
叶李: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