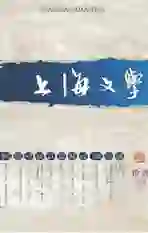他人的生活
2016-11-21张定浩
张定浩
小说写作者似乎总是在书写两种生活,自己的和他人的。詹姆斯·伍德在谈论小说人物的时候,尝试把小说家分为两类:“一边是托尔斯泰、特罗洛普、巴尔扎克、狄更斯或者莎士比亚那样的戏剧家,他们充满‘消极能力,好像是不自觉地创造出一众和自己绝不相同的人物。而另一类作家要么没有兴趣,要么在这门手艺上欠缺天赋,但不管怎样却对自我产生了极大兴趣——如詹姆斯、福楼拜、劳伦斯,伍尔夫可能也是。”这种分类法并不新奇,虽然我们看到他将福楼拜列入第二类作家可能会略有吃惊。接着,他以艾丽丝·默多克为例,他说,“默多克是第二类作家中最辛酸的,因为她把一生都用在跻身第一类人当中,在她的哲学和文学批评中,她一再强调创作出自由独立的人物是一个伟大作家的标志,然而她自己的人物从来不曾有过这种自由”。
但这并非指责,而应当视为理解。因为伍德随即又说道,“默多克对自己太苛刻了。有无数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基本上彼此雷同或者就像作家本人,然而在他们身上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很难说他们是不自由的”。
在祁媛迄今为止的小说中,这位习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书写者,也一直徘徊于自我和他人之间。《奔丧》写叔叔的故事,《我准备不发疯》写“母亲”,《爷爷》则回溯家族史。在这几部令祁媛初获声名的短篇小说里,“我”无处不在,独白俯拾皆是,但并不沉溺自身,而是时时指向他人的生活。当然,这最初的“他人”,不可避免,都是一些和自我生活密切相关的亲人,某种程度上,他们其实也构成了自我生活的一部分。她在书写这些他者的同时,也就是在很自然地书写自我。在这些小说中,我们看到一种冷峻的观察如何和肆意的独白非常自然地混融成一体,仿佛时时在提醒我们注意这位小说书写者所受过的现代绘画的训练,她写小说就像在做她所喜欢的素描,用锐利的眼睛捕捉到光影明暗间的实在世界,但落笔的每一根线条又完全是自我的,是不管不顾众多规矩限制的。
然而,小说书写与绘画又存在本质的不同。如果说,现代摄影术的发明,已经让画家摆脱了那个表象世界的束缚,可以大踏步地去追求某种所谓深层次的真与美,乃至主体的内在挖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绘画一直在趋近现代诗),那么,现代小说,不管中途有过多少昙花一现的新实验,它的主体,似乎一直坚持停留在那个表象世界之中,那个由芸芸众生构成的日常世界。诗人和画家观察世界,并倾听自我的声音;小说家同样观察世界,倾听自我的声音,但与此同时,他还要倾听他人的声音,他不光要仗恃自我的强大感官去观察、倾听他人,更要通过他人的千差万别的感官去认识和理解这个共同生活的世界。这是小说家最为独特的艰难之处。
《黄眼珠》似乎是祁媛书写他人生活的一个新的尝试。她选择一个男性视角作为叙述的主体,以此呈现几段陌生男女的情事。但这部小说似乎也最大程度地暴露出祁媛的不足。“我”虽然名义上已经换成男性视角,但一方面,“我”对世界的锐利观察依旧还是祁媛本人的眼光,类似“店铺门前搭在木凳子上的两个粉红色的旧枕头大概是主人忘收了回去,白色路灯下,变得冷红”这样的色彩观察,依旧是祁媛式的,而另一方面,作者还无力构建一个和她自己完全不同的男性心灵世界,于是,外遇、离婚、中年单身汉生活,仅仅是这些浮浅的符号构成了一个单薄的“我”。在小说中,“我”讲述和美院老同学刘悦的一夜情故事,再听刘悦讲述她和绘画才子解兆元的恋爱故事。且不谈这些故事本身的无甚新意,单就这种叙述推进的方式而言,对于单一讲述者的过分依赖,在祁媛之前的小说中已经非常明显,除了她本人之外,她似乎暂时还不能够让其他人物自行其是地生活起来。
在祁媛这里,他人的生活,暂时还只能活跃在她自己的讲述之中。这当然并非不可以,或许祁媛就是詹姆斯·伍德所谓的第二类作家,只不过,这种方式其实是对小说书写者的“自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黄眼珠》中,作者催促我们记住解兆元“那野兽般的黄眼珠”,那双眼睛,在讨厌解兆元的人看来,是“鸡屎黄”的,但我们其实并不能就此对解兆元有更深的认识和感情,在一篇以他的眼睛为名的小说中,他退化成一个愤世嫉俗的象形符号,象征才子在世间的命运,与平庸混世的“我”相对立。这种企图,无论如何,对于人世生活而言,是太过简单化了。我想起另一位画家,黄永玉,在他的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对几位潦倒艺人的描写,或许祁媛可以从中体会到一点什么不同于她现有小说中的特质,那是一个更为强大、充满活力的自我,一个可以带领我们穿透他人生活重重障壁的自我,它要求的,按照祁媛喜欢的说法,是一个网状铺开的自我的谱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