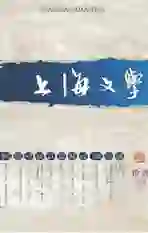美兰回家
2016-11-21范小青
范小青
站台上响起了哨子声,火车快要进站了,她朝东边张望了一下,一束耀眼的光已经出现了,她一手拐着几个沉重的包,一手抱着两岁的女儿,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这是她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的电话,不能不接,可是那几个包的包带紧紧勒在她的臂弯里,像嵌进了骨肉,根本就放不下去,只得将女儿放下来,用双腿夹住她,赶紧接电话,女儿却一下子从她的腿中间溜了出去,旁边一个候车的女人一把扯住小女孩,将她拉回到她身边,斥责说,火车来了,要不要命了。
她心里猛地一抖,真的好险,万一、万一——她不敢想下去,赶紧拉住女儿,手机滑到地上,“啪”地一声,摔成了两块,电板掉了出来。这个电话太要紧了,他到底来不来火车站,他到底能不能和她们娘俩一起走,他最后能不能出现在她的家人面前,所有的一切,都系在这个电话上,可是电话跌坏了,把唯一的希望也跌掉了,她哭了起来。火车到了,车门开了,旅客往车上涌,她不知道是该上车还是不上车,被后面的人连拥带挤上了车,她大喊我要下去,我要下去,可是没有人理睬她。
她被挤到车厢的中央,她已经无法再下车回到站台了。
找到座位后,她仍惊魂未定,赶紧把女儿安顿下来,把包塞到行李架上,又手忙脚乱地把手机的电板安装起来,两条手臂有一种脱了力的虚弱,哆嗦着勉强把电池塞进去,电板盖却怎么也盖不上。
旁边有个男人,一直沉重地皱着眉头,似乎并没有看她,却忽然“哧”了一声,装反了。
她红着脸谢了一谢,把电池重新装好,盖了电板,赶紧拨打那个要紧的电话,那边却没人接听。
再拨,仍然没人接听。
一直没人接听。
火车开动了,各自坐定或站定了的旅客,有的开始打瞌睡,有的看手机,有的茫然四顾,或者目光乱射,也有凑几个人打牌的,乘警举着喇叭过来了,口中念念有词:各位乘客,乘车请注意安全,守好你的钱财,看好你的孩子,管好你的嘴巴——
乘客哄笑。
一人说:管好嘴巴干什么?
一人答:不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吧。
乘警朝这人笑了笑,竖了一下姆指,他继续往前走,继续念叨:乘客同志请注意,上车留心看周围,小心小偷和骗子,小心拐掉你孩子——
焦美兰下意识地搂紧了女儿,又一次拨打电话。
电话仍然没有人接。
那个皱眉的男人,又“哧”了起来,打这么多遍也不接,还打,烦不烦。
其他无聊的乘客也开始说话。
可能手机没带在身边。
要不就是不想接。
人家不想接,还打还打?
不接、不想接、不肯接,她都得打,她必须得打通了,否则,她就是那个被男人抛弃了的带着私生女的母亲,她有脸回家吗?何况她要去面对的,是刚刚去世的父亲。
她继续拨打,这一次对方有了反应,但并不是接她的电话,而是掐掉了电话。那一瞬间,她的心就往下沉,眼泪涌了上来,她拚命忍住了。
皱着眉头的那个男人都懒得再“哧”了,干脆别过脸去不看她了。
她无助地看着男人的半个背脊,好像那是她可以依靠的地方。
根本不是。
在嘈杂的车厢里,手机铃声此起彼伏,每听到“嘀”一声,她就赶紧看自己的手机。
可惜不是。
车身一阵摇晃,一个包从行李架上掉了下来,“咔”的一声,差点砸到对面的乘客头上,他又惊慌又生气地跳了起来,谁的,谁的东西,要砸死人啊?
她的注意力始终在手机上,包掉下来砸人都没有察觉,直到有人大声嚷嚷,咦,咦,这是什么东西?她才惊醒过来,赶紧去看地上的包,包的拉链不知怎么拉开了,包里的东西滚了出来,摊了一地,其中就有那个人喊出来的“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是一本书,书名《表演系》。大家勾着头看地上的东西时,又有人奇怪了,咦,表演系?表演系不是那个什么吗——
另一个人说,表演系是一个系科哎,是学校的一个专业吧,怎么会是一本书?
再一个人更是奇怪到怀疑起来,他盯着她的脸看了看,说,这是你的包吗?
旁边那个老是发出“哧”声的男人替她证明说,是她的包,我看她塞上去的,一个女人,抱个孩子,还带这么多东西,哧。
她弯腰把那本书拣起来,封面上的三个字在她眼前恍恍惚惚的,坐在她膝上的女儿忽然推了推她,指了指手机,女儿先天聋哑,却十分机敏,她低头一看,短信来了。
短信来了!
短信终于来了!
原来,他去车站的路上堵了,没赶上火车,现在他签了下一趟的车,让她在前面的坞山站下车,改签和他同一趟车,然后上车会合。
终于松了一口气,正想回复短信,他的第二封短信又来了,说,因为她不停地打他的手机,电都快打没了,发了这个短信后,他得关机了,省下最后一格电,要留在会合的时候用。
他关机了。
但是至少他出现了。
她一直强忍着的眼泪,终于掉出来了。
餐车过来了,女儿饿了,她买了一份盒饭,十五块钱,打开来一看,她有些发愣。
旁边的人回过身看了一眼,又“哧”,这是米饭?
当然是米饭,只不过是一团毛毛糙糙硬生生的米饭,还有一摊黑乎乎几乎看不清是什么菜的菜,还有一个干瘪的煎鸡蛋。
有人凑过来说,这个煎鸡蛋,看起来像是出土文物了。
乘客都哄笑。
她的脸红红的,但是心情已经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的调侃,她甚至觉得很亲切很温馨。
有人生气地说,不要吃,不要吃,还给他们。
她笑了笑,女儿已经开吃了,一口咬掉了半个鸡蛋。
有人去车厢接头处打了水来,喝了一口,发现水是凉的,抱怨起来。
别人劝他说,这种火车,就这样的。
那一个人并不服气,什么叫就这样,就不应该这样。
那应该怎样呢?
应该像高铁那样吗?
是呀,听说高铁上什么都有,什么都是最好的。
高铁上确实什么都有,也挺好,可是有一样东西你没有。
什么东西?
钱。
大家又笑。
那个内行的人又说,高铁上的盒饭,便宜的四十块,贵的七八十,你吃吗?
大家乱笑。
吃不起,笑笑总可以。
列车的广播响了起来,请旅客配合,列车员要过来查票了。
列车员果然已经过来了,懒懒地向大家伸着手,既然广播里已经播了,她也不用再说了。
那个计较的人说,什么狗屁服务,还查票,我没有票。
他明明是有票的,就捏在手里,偏不给列车员看。
列车员也不着急,态度也蛮好,只是她坚持着不走开,服务好不好,跟我查票没关系。
他们在她耳边吵吵嚷嚷,她的心却安定下来了,她想起了五年前,她家乡所在的县城还没有通火车,她是搭乘一辆拉沙土的货车离开家乡的,货车把她带到另一个通了火车的县城。
她在坞山站下车,到检票的时候才知道,这两趟火车相差七个小时,她得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等着他乘坐的那趟车到达。
但是无论多长时间,她也会等的,总比独自一人带着女儿回家要强得多。
她出站的时候,被几个拉客住店的人挡住了。
起先是好几个人围着她,后来他们不知怎么商量了一下,其他人退开了,只留下一个妇女盯住她。
我不住店,她说,她有些害怕,紧紧抱着女儿。
妇女说,你住店吧。
我还要坐下一趟火车,我不住店。
你要坐哪一趟?
她报出了那一趟车的车次。
妇女十分熟悉,那还得有七个钟头,她说,这么长时间,你到哪里去呢?
我,我就在这里。
妇女立刻摇了摇头,抱着个孩子,还这么多东西,你太辛苦了。
没事的。
妇女又说,你不仅辛苦,你还很危险,你太危险了——我可是警告你哦,这地方什么人都有,你要是一打瞌睡,人贩子就会拐走你的孩子。
她浑身一哆嗦,我不打瞌睡,我会紧紧抱住她的。
妇女又摇头,你太没有经验了,你可以不打瞌睡,可是人贩子他们有迷魂药的,他们要是盯上你,你搞不过他们的,你还是住店吧,住店就安全了。
可是,可是,我不要住店,那趟车下午就到了。
那你可以开个钟点房,没多少钱的,你在外面等七个钟头,真的太辛苦、太危险,我不骗你,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经常有的哦。
她犹豫了起来,想着躺到旅店的床上,又安全,又放松,她终于点了点头。
这就对了,不该省的钱不能省,那妇女说,走吧走吧,跟我走吧。
“咔”的一声,房门开了。
焦小姐,焦小姐,你醒醒,你醒醒。
她睁开眼睛,看到助理站在她床前,正冲着她笑呢。
焦小姐,你睡过头了,你说开闹钟的,闹钟没响吗?
她赶紧把手机拿过来看看,意识还没有完全苏醒,明明是设了叫醒功能的,不知道为什么手机没响起来。
助理说,不着急,火车还有好几小时才开,但是我想你还得吃点东西,要化妆,面谈的内容也需要准备一下,这样算起来,时间也不算太宽裕了——
她已经清醒过来了,记得还需要办一些手续,填几张表,助理早已经拿在手里了,笔也替她准备好了,她提笔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其他一些情况,在填“学历”的时候,她恍惚了一下。
细心的助理注意到她的犹豫,偏过头来看了一下,说,哦,这个不用填的,还有,这个,这个,这些都可以不填,只是履行一个手续,有你的名字和银行账号就行,是他们公司入账时用的,基本信息就可以了,谁还不知道你哎——
她仍然有些恍惚,但还是听从了助理的意见,既然只要有名字就行,其他的内容也许都无所谓了。
助理说,我先去传真,回头来帮你整理东西。小心地收起表格,退了出去。
她去卫生间用冷水拍了拍脸,然后打电话订了客房送餐,点餐单上品种丰富,中式西式、大菜小点、饮料酒水齐全,她咽了一口唾沫,不敢多吃,只点了一份土豆沙拉和一份水果。
二十分钟后客房餐到了,服务员托着精致的餐盘进来,弯腰将餐盘放到茶几上,起身的时候,看了她一眼,顿时惊喜万分,差一点叫喊起来,咦咦,是您?您是、您是焦、焦……
她微微笑一下,和平常一样,没有其他特别的表示。
服务员也许会要求和她合影,或者拿一张纸请她签名,这都是可以的,她一般不会拒绝。
这位服务员暂时没有这样做,她还没有从惊喜中反应过来,她只是喃喃道,咦,咦,哦,哦,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
她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并不意外,她只是希望服务员不要打扰到自己的工作,更糟糕的场面,就是一个人又去喊来了许多人,那就麻烦了。不是她要摆什么架子,实在是没有时间,因为接下来她要赶火车到另一个城市,那里有一场十分重要的会面。
她的手机适时地响了起来,是经纪人方姐打来的,告诉她改签了前一趟的火车,因为对方希望能够尽快确认她的态度和最后的方案,提出约见的时间要提前一点。
她乘机把“提前”两字咬得重一点,又重复了一遍。
提前?
提前?
马上就得走?
服务员很知趣,赶紧说,您有事情要忙,我不打扰了。
她退了出去,随手带上了房门。
她听到轻轻的一声“咔”。
她赶上了约定的那趟火车,上车很顺利,可是在约定的车厢里,在他所说的那个座位上,并没有见到他本人。她拨打电话,他说过的,省下电来就是为了在这个时候通电话的,可是打不通,关机,一直关机。
她抱着女儿着急地四处走动张望,然后又回到这个确定的座位旁,她看了看座位上坐着的男人,不认得。
她恨不得他就是他,但确实不是。
她只能和这个陌生人说话了,你坐这个座位的时候,座位上有人吗?
有呀,他走开了,我就坐了。
是一个男的吗,个子,个子差不多这样?
没注意。
他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她急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是你男人吗?
不、不是我男人。
男朋友?
也不是。
那他是谁?
他是我、是我的同事,是我请他帮忙、陪我回家——
哦,原来。
他们的对话,被“咔”的一声打断了——
那一瞬间,有个旅客大声喊起来,哎哟,是焦美兰,是焦美兰,焦美兰哎!
车厢里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兴奋起来,纷纷过来围观,前面的呵着嘴,后面的踮起脚。
有人在车厢接头处举着打板喊:第五场第一次,开始——
摄像机就架在过道上。
焦美兰困了,趴在小桌上。
旅客纷纷加入进来。
她怎么演这么个角色?
呵呵,背着蛇皮袋、拖着小孩的邋遢妇女。
你不懂的,这是为了艺术,自毁形象。
她演的是什么?
看不出来,不过,以她的名气,肯定是女一,最差也应该是女二。
要不就反角女一。
受气的农村妇女?
不像。
假装好人的人贩子?
那她抱的这个女孩,是拐来的?
不像。
我看是一个被抛弃的女人,带着私生女回家。
这样有点像。
嘿嘿。
嘻嘻。
难怪说她是年轻的演技派,演得真赞,你看那表情,那眼神——
也可以叫实力偶像派。
呵呵。
嘻嘻。
焦美兰趴在小桌上,有人过来摇动她,喊她的名字,焦美兰,焦美兰,你睡着了?
焦美兰抬头,看看喊她的人,又茫然四顾,绿皮火车车厢里混乱、嘈杂。她有些愣怔。
你不记得我了?你同学,你高中同学呀——你真不记得我了?不过没等焦美兰解释什么,他又说,焦美兰,你父亲去世了,我听说——
“咔”。
一条过。
火车终于到达她的家乡了。
下车的时候,她发现母亲在站台上等候她,母亲看到她时,神色又惊又喜。
焦美兰却有些奇怪,妈,你怎么知道我是这趟车?
母亲笑了起来,我女婿打电话来的呀,要不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神仙,我猜不到的。
你女婿?你女婿在哪里?
母亲从她手里接过女儿,朝她看了一眼,别瞎说了,你精神很好,你病也好了——瞧我说的这废话,能一个人带着孩子回家,病怎么会没好?
她仍然奇怪地看着母亲,我有病吗?
母亲赶紧扯了开去,不说你了,不说你了,你好好的,有什么好说的——
焦美兰心里一阵疼痛,妈,爸爸他怎么会、怎么会说走就走了?
母亲愣了愣,开始躲闪她的注视,母亲说,三年是个关口,三年以后,新坟就成旧坟了,所以今年的坟,你知道是要回来上的。
我是回来上坟的?我不是回来奔丧的?焦美兰意识有些模糊了,妈,我爸什么时候走的?
三年前你不是回来奔丧的吗,你难道忘了——唉,美兰,你要是累了,就不说话,跟妈回家吧。
她们随着出站的人流往外走,焦美兰不明白母亲的意思,她只是想搞搞清楚,妈,是不我以前得过什么病,你们瞒着我的?
母亲不说话,只是急急地往前走。
妈,你得告诉我,我是什么病?
母亲停了下来,她年纪大了,抱个孩子,又走得急,她有些喘了,什、什么病,反正是说不清的。
焦美兰挠头了,难道自己得过病,自己都不知道,或者这个病很奇怪,会让人忘记自己的病?
说不清?有病都说不清?神经病啊?她生气地、赌气地说。
母亲分明是慌了,又强调说,好都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她们继续往前走,可是焦美兰的心情变得十分沮丧,一个连自己生过的病都能忘记的人,算什么人呢。
焦美兰停下了,她不肯往前走了,妈,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我不回家,我回家有什么意义?
母亲的目光,从惊喜渐渐变成了惊恐,她支支吾吾,吞吞吐吐,美兰,你别生气,是从前你们班主任说的呀,我们是没有承认,我们从来不承认的,但是大家都指指戳戳——
什么?
所以,后来你才离开的呀——不说了不说了,好在你现在身体好了。
她们到了车站出口处,检票。那个年轻的检票员问母亲,你票呢?
母亲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小纸片,检票员接过去看了看,这是什么?
站台票,母亲说,我买了站台票进去接我女儿和外孙女的。
出口处的栏杆挡了下来,她们被挡住了。
检票员笑起来,站台票?你开什么玩笑,早就没有站台票了,你哪来的站台票?
她的一个同事说,真是的,两个大人还带个孩子,只买一张票?
我真不是坐火车来的,我是来接我女儿的,我女儿什么什么什么。母亲说。
检票员中间有一个年长一点的同事朝焦美兰看了看,似乎有些奇怪,又似乎在想着什么,后来她说,算了算了。她对两个年轻的同事说,打开吧打开吧,让她们走吧。
焦美兰想,我一定要到学校去问清楚。
出口处的栏杆抬起来了。
模糊的意识中,她听到“咔”的一声。
校长办公室仍然是当年那间办公室,但是校长已经不是当年的校长,现在的校长正在和一位老师谈话,老师年纪蛮大了,她的脸侧对着焦美兰,她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认得这位老师。
老师很激动,语气呛人,我的退休工资,比一样工龄的同事,少了这么多,不公平,不公平,凭什么这样对待我?
校长年纪不算大,看起来脾气很好,她笑眯眯地说,老师,你已经来过好几次了,理由都跟你说过了呀,在你退休前的几年里,你有连续两年年终考评不合格,所以会扣工资,这是上面的政策,不是学校的规定,我们也没有办法的,就算我们帮你原样报上去,上面也不会批的。
不可能的,老师涨红了脸说,我年年都是先进,不可能有不合格。
校长说,但是你的档案里是这么记载的,我们只能认档案,任何事情口说无凭的。
是谁在我档案里乱写的,我要求你们查笔迹。
老师,你知道的,没有笔迹,都是电子的,都是从电脑里出来的,除非电脑会说话。
那你可以找我的同事去问,去了解,去调查。
老师,其实我们对你很负责的,退休工资上报前,我们就找过了,可是人家都不记得,也是的,现在谁会记得别人的事呢。
老师是固执的,不肯让步,她坚持说,这个档案是错的,知错必改,你们要帮我改过来。
校长很为难,校长说,老师,这个,你也是有知识有水平的,你应该知道的,档案是不能改的,改档案是违法的。
那,那就任由一个不真实的档案害人吗?老师愤愤地说。
校长始终是和气的,她说,老师,其实多扣的那点钱,应该不算什么大事,其实我倒是听说,当年有个班主任,给学生写评语的时候,也害了人家呢。
老师说,我也当过班主任,老师怎么会害学生呢?
校长说,可我听说那个班主任就是您呀——所以,老师,我说得不好听,您别生气,这看起来倒像是因果——她到底还是把“报应”两个字咽下去了。
老师沉默了。
校长又说,因为你毕业评语中的一句话害得人家高考落榜,人家还是考的艺术学院,若不是因为你的评语,说不定已经是大明星了。
老师仍然沉默,她似乎在想这件事,但又想不太清楚了。我写的吗,我写的什么呢?
校长说,老师,你写的什么你忘记了吗,当时我还没来,我后来听他们说的,你好像写的是“能带病坚持学习和参加体育活动”,老师,是不是你不喜欢那个女生,才这么写的?
现在老师想起来了,一想起来,她的脸都气白了,不是,绝对不是,一个班主任,要写五十几个人的评语,优点缺点还不能写得一样,后来实在写不出来,就挖空心思,想到同学有一次感冒了,或者是痛经还是别的什么不舒服,还在坚持上课,就写了她这一条,我既没有瞎说,更没有害她,我是算她优点的。
校长也沉默了一会儿,后来她说,但是,结果搞得大家都认为她有病。
老师说,不对吧,我记得后来是有人来问过我,我也跟他们说清楚了,他们也相信了,后来不是招进去了吗?
校长摇了摇头,老师,你记错了,没有招进去,大家都说是你害的,因为你说不出她是什么病,凡是说不清的病,都不是好病,最后人家都说她是精神病。
老师气得说,精神病?谁精神病?神经病啊?
校长说,是呀,大家可能认为,如果是一种说不清的病,那就是精神病了。
老师也有点疑惑了,那,后来,那个学生,她怎么样了,没被大学录取吗?生活正常吗?
校长说,有那种病的人,怎么可能正常,后来听说到大城市去治病了,反正混得不好。
焦美兰终于忍不住了,推门进去,气呼呼说,我没有出去看病,我是出去工作了。
校长和老师都十分惊讶,异口同声地说,你是谁?
问过以后,校长立刻蹙眉思索起来,她似乎对她是有印象的,可是那时候校长并不在这个学校,她怎么会对她有印象呢?这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
焦美兰气愤地说,我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精神病,老师,你是我的班主任,你的评语进了我的档案,我被你害惨了。
老师说,别开玩笑了,同学,我写你带病上课有什么错,你看看我呢,就凭从电脑里出来的一张纸,他们把我从优秀教师搞成什么不合格,被害惨的人是我呀。
校长终于认出她来了,校长喊了起来,哎呀呀,哎哟哟,我认出来了,你是你是焦美兰哎——不过校长又有些疑惑,只是,只是,你怎么会是这身打扮,会不会是在拍戏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