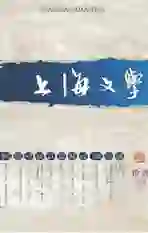父亲的老房子
2016-11-21胡宗
胡宗
我知道他又来过了。
在我刚刚做过的梦里,有老房子的影子。我能感受到他的气息,那是药水肥皂的味道,面容和衣物好像一起被漂洗过,泛白模糊,轮廓处留下了光晕的毛边,这是岁月的痕迹吗?离得那么近,抬手触摸之间又是那么远,没有言语,是父亲一贯淡漠和沉寂的样子。
那个斜墙屋顶的老房子,就这样经常出现在梦里:向外延伸的老虎天窗,油漆斑驳的木质窗,屋外的亮光把横竖条窗格挤压成的剪影,角落堆积的樟木箱,几只皮箱摞在高处,屋顶有小块粉墙脱落,漏出糊泥板条,蜘蛛网把这些连接起来,网罗了稍许尘土。父亲这时会在那里,侧坐着或是背对着我,但我能确认是他。
父亲的身影是和老房子交织在一起的。
一样的角度、一样的窗户位置,和父亲身形一起,被压扁成一幅平面的图像。醒来的时候,无论怎么用力想捉住梦里散落的碎片,脑子里的印象却更加模糊, 像见了光的显影相纸在褪去影像,只留下了大片的白。
搬过好多次家,有新公房,有带花园的老洋房。不论怎么搬家,唯独斜墙屋顶的老房子总是会出现在梦里。住了十一年,是我出生到上初中的年数,刚有记忆的能力,这岁月占据了我童年的全部,那时候父亲还健在。
从干校回来的那段时间,父亲没有了工作,赋闲在家里,显得忧心忡忡。他平时就爱干净,衣物、碗筷、水杯都要经过消毒才能用,清洁一条毛巾要反复漂水搓洗,现在有了更多的时间,竟然将拖把蘸着消毒水一遍一遍地擦地,条纹毛巾一次一次地搓洗,把它洗成一色儿的白,但还是洗不掉头上的一片阴霾。消毒水、药水肥皂的气味弥漫开来,将他的焦虑和烦躁一起飘浮在周围,久久驱散不了。我不敢跟他说话了,经常蜷缩在门后床脚,躲在不显眼的角落,免得有不适当的举动,引来父亲一顿臭骂。
余下的时间父亲就坐在那里发呆,我跟着父亲发呆,默默地看着他。父亲平时在家的时间不多,说的也是日常短语,现在更加沉默了。他不间断地吸烟,一根接一根,就这样,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看着父亲的背面,时间凝固了,吐出的烟雾飘浮起来,紧缩成一团一团,无法散去。
沿街面的天窗白天是紧闭的,几块斑驳的墙皮侵蚀了斜面的屋顶,家具简陋,大床占据了大块面积,一张老旧的单人沙发紧靠着床沿,严格意义上说是一把牛皮包面的椅子,铆钉嵌在椅背的四周,边缘的皮质已经泛白起毛,还漏出些内胆的鬃毛。这就是父亲常坐的椅子。
都说父亲长得洋气,脸部轮廓分明,眼眶略微凹陷,突出了挺括的鼻子,除了嘴形下颚的部分,外表可以算是俊朗。那些年里,父亲出门前都要换上洗干净的衣服,用湿布抚平显眼的皱褶。他烫自己的衣服,不要母亲帮忙。这些是男人干的事情,他总是这么说。长裤的折线是他的标志,旧的棉织中山装也是挺括的,领口露着小截的白衬衫衣领。他上班骑一辆二十八英寸的半链罩永久自行车,上车前他用两只衣夹子夹牢裤腿,以免裸露的车链子把它弄脏。他上身笔直,骑得不紧不慢,裤脚处却撑起一块,看起来怪怪的。
父亲是电影美术师,在离家不远的徐家汇的电影厂上班。我看过他画的电影制景图稿,各种枪炮、雕饰着花纹的房屋,完全是一幅幅精美的工笔画,在微小的局部,他勾勒得特别清晰。最让我佩服的是,那些标注的美术字体,写得像是报纸上印出来的。
父亲是从山里出来的。1950年新中国建国初期,完成了工艺美术学校四年的学业,他没有留在轻工纺织业发达的杭州城,却跑来上海——这一时期,许多公司、厂家都要成立和重组,人才需求量很大。父亲的内敛、刻板没有影响他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和好奇。于是,他直奔电影厂的招聘处而去,虽然对电影完全是陌生的,看过的电影也屈指可数,可是那些电影海报上罩着光环的明星和黑白活动影像的奇幻世界,让他充满无限的遐想,他把应聘书投出去了。
其实这都是我后来的想像,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谈起过这些事,更没有告诉我,他为什么会选择电影,也许只是一次偶然的机缘:新成立的电影厂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憨直诚实的外表和优秀的专业成绩,通过了政审的家庭出身,或许还有刻意修饰过的衣饰和干净整洁的容貌,得到了电影厂招聘人员的认可,仅此而已,但这次被选择的“机缘”,确实改变了父亲的人生道路。
我问过父亲,见过那么多演员明星,哪个演得最好,父亲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赵丹!那时候,我心目中崇拜的是李向阳、杨子荣、王心刚、唐国强,赵丹是那么陌生和神秘,而当时说起赵丹都是偷偷摸摸的事情,我知道,那时候赵丹正关在里面,而且是“有问题”的,所以父亲必须压低了嗓门说:“赵丹戏演得好,画画也好……”说话的时候,目光里充满了恭敬和凛然。后来,母亲告诉我,是赵丹带着电影厂的招聘人员,去学校挑中了父亲。难怪!
当时,见到赵丹,父亲一定眼睛发直,盯着他看——父亲感到无比的欣喜和自豪,连奔带跑出了校区,真想拉住大街上的随便哪个家伙,告诉他:要去有赵丹的那个电影厂,看赵丹演戏,跟着赵丹拍电影了。这样想来,我真是太理解父亲了,他何止是敬仰赵丹,还有一份对师长的敬畏和感激。有赵丹的身影,便成了日后美好的记忆。
父亲在填写个人履历时,每每都写上籍贯——宁海;那地方在几年前去过一次,驾车沿甬金高速拐入省道,有一段是海边的公路,气流里飘浮鱼虾水产的腥味。顺着指路牌方向进入宁海大蔡镇,两边的高山夹着山路,蜿蜒在山势的缝隙里,一眼望去是满目的绿色,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
父亲的姓氏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镇口最明显的位置是家族的祠堂,大祠堂修缮得很新,门口一块大匾,写着“尚书第”,金光铮亮,字体浑厚,炫耀着家族的历史。这样的家世可以上溯至五代的后梁后唐,寻访祖迹,三大册的宗谱有详尽的记载,太祖公官至朝廷的兵部尚书,功成名就退引到此地耕地建宅。在历史常识上,五代十国是一段大分裂的动荡时期,割据政权的争斗使得战乱不止。内乱和血腥,这是我对这段历史的全部印象。江南地区以吴国最强,当时是武夫当道的时代,掌握兵部大权的太祖公占据富庶的江南,可谓权倾一世的人物;权力的快速更替,不可能使太祖公功成引退。国力衰退、部下篡权、溃败于吴国、逃离至临海的荒蛮山林,大山的天然屏障可以躲避篡位者的追杀,太祖公从此开荒耕作、弃武从文,繁衍后代,这可能是父亲家族姓氏延续的一种合理解释。
继承了宗族的耕读文化传统,父亲在镇上的私塾背书识字,去了县城上小学中学,成绩优秀,县高中毕业后考入国立艺专——林风眠、潘天寿在那里倡导中西艺术合璧的学校。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让父亲接触到西方的现代艺术流派、传统的国画笔墨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各种艺术流派和活动让他目不暇接。父亲有种莫名的紧张,感到无所适从的局促。
父亲没有教过我绘画,我的画画兴趣是从看连环画开始的,不看文字,连续的图画已经把故事表达了。我有许多连环画,小人书里的线描人物太吸引我了,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和《敌后武工队》《奇袭白虎团》都是我的宝贝。这些书都是父亲买给我的。我还时常在作业本背面、课本的空白处和一切能画的纸上,照着小人书画。
父亲开始要我练毛笔字了,临摹颜筋柳骨的字帖,每天要写一大张,近一个小时的临帖完成后才可以去弄堂里玩,往往写到最后几个字,毛笔飘动起来,一通乱写赶紧结束。
下班回来早,父亲就会去书店买上几本新出的连环画,那会儿父亲一定心情非常好。到家在皮椅里坐定,崭新的书不是一次全部拿出来的,而是一本一本地拿给我看,炫耀他的收获。父亲脸上有着笑意和满足感:“看看这个,那个也不错,还有还有……”父亲买的书有特别好看的封面,彩色的图案展现出奇妙的世界,这是给我练字的奖赏。见到连环画的惊喜,使我对以后有了期待,要是父亲天天心情好,我就会有更多的书了。那段时候,我会很乖巧,听到父亲回家自行车的铃声,把练字的作业摊在桌面上,给他开门提鞋,眼睛却瞄着父亲的拎包,想着今天又会有什么好东西……
那是我一天最开心的时刻。
我努力回想与父亲相处的细节,更多的时候,父亲是严厉的,记得那次逃学对我的教训,大动干戈的体罚……
那是我和弄堂里阿育爷叔的故事。
阿育是有本事的人,会打拳,字也写得好,弄堂里墙壁上的大标语都是他写的。阿育练的是八卦拳,柔中带刚,腿快手快招法凶猛,一套拳法打得让人眼花缭乱。阿育一头汗水,弄湿了天蓝色的线衫,紧贴着小块隆起的肌肉,让我们这些弄堂里的小孩对他崇拜得一塌糊涂。我想着要讨好阿育,还想向他学拳。阿育人好,从不隐瞒拿手的招数,竟然教了我几招很基本的拳术,真是开心。
练功时正赶上午后放学,周围都被人围拢起来,阿育越发起劲,脚下转圈左右移步,手势变换穿掌掩肘,不时发出吼声,弄堂小孩也兴奋得叫好。阿育兴致高涨:“这招叫八反掌,半步跟……看这招,指上打下欲擒故纵,浑水摸鱼声东击西。”阿育手动脚移,声线尖厉,像一个讲兵法的教官,“看脚下,要不停地走,手快不如脚步跟,站定生跟落地花。”
太阳落山了,弄堂里安静了些,夹道的穿堂风吹来,清凉适宜。阿育端着大碗的白米饭,泡一碗紫菜酱油汤,面上滴着麻油,色泽和油的香味真是诱人。“三角头,我有办法削掉你头上的两只角。隔壁市民村浴室搓背的大块头,有一种巴哈马精油,涂在角上,热毛巾敷上两个小时,用锉刀木榔头修理,不出一个礼拜,三角头上的两只角,完全可以削脱。”阿育嚼着饭粒得意地对我说。
阿育朋友多人头熟,讲什么我都相信。
“三角头”, 这是弄堂里大家叫我的外号,因为我头大,小时候又把后脑睡扁了,两边头骨突出,脸腮瘦削下颚尖利,于是都叫我“三角头”。我都不敢吱声,有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很自卑。这个绰号让我倍感耻辱。
和阿育约好下礼拜的一个中午,我们在弄堂口碰面,去市民村浴室的大块头那里修理 “三角头”。中午去班主任那里请病假,说是头痛要去医院,病假条是阿育帮忙写的,阿育写字拿手,模仿家长的笔迹签字保证看不出来。
正午的太阳直晒,蒸发着空气里的水分,地面被照得白晃晃的,弄堂里安静,练拳空地树荫下的阴凉地里躺卧着一只猫咪在打瞌睡,却不见阿育的影子。左等右等也等不来,由于是上课时间偷跑出来的,心虚,做事也不敢张扬,几天来兴奋高涨的情绪减弱了许多,不见阿育的人影,我有点慌了,脑子里空空的,只好失望地跑回家……
没有想到一头撞见中午回家的父亲,他问:“学校下课了?”我脑子里一团糟,又慌又害怕,呆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还没缓过思绪,父亲已经一个巴掌打来,一下一下……想想自己是为了去修理“三角头”,阿育又骗了我,顿时委屈得发呆,我没有躲闪避让,硬撑着竹竿一样的身体。“小赤佬,学会撒谎了,外面轧坏道,整天和吃闲饭没工作的人混在一起,早晚也要成为弄堂野蛮小鬼。”什么“整天和吃闲饭没工作的人混在一起”,明明是人家阿育看得起我,教我“八反掌”拳法套路。父亲的话没有等来我的回应,随手又抄起一把扫帚,竹把子,一下一下打在我的屁股上,这时屈辱比疼痛来得更强烈,我的戆劲来了,憋红了脸,双眼发狠地直视着父亲……
“我就要做弄堂的野蛮小鬼。打呀,你把我打死算了!”
父亲突然停止了动作,一屁股坐在那把打满铆钉的皮椅上沉默下来,剩下的是父亲的喘气声……香烟的烟雾散开来,把室内的气息拧成了一团,当我再抬起头看父亲时,他的双眼已经噙满了泪水……
这一刻真把我吓住了。
至此之后,一个月不能去弄堂里玩耍作为惩罚。傍晚时分,下班、放学的都陆续回来了,即刻又聚拢在一起,弄堂里照常喧闹起来,打闹喧叫的声音从窗外传来,使我坐立不安,心思飘荡去了别处。每天这段时间都是最煎熬的。父亲给我的教训让我不敢再逃课了。
和父亲共处一室时,彼此的交流是空泛的,各自面对的是一个橱柜一面墙壁,总显得平淡沉闷,偏偏母亲也没有多余的话要说,交谈往往淹没在简短的盐咸茶淡的琐细之中。每天晚饭后,保姆李妈买菜算账成了说话最多的时刻。一家人围在饭桌前,不急着收拾碗筷,由李妈报出菜的价钿,父亲拿着记账小本依次记录,算出总价,结清当天的费用,言语在油盐小菜上说不完,历数小菜场新上市的品种,什么时鲜货、行销货……一屋人气氛暖暖的,结束算账,李妈收拾碗筷,接着就是洗漱上床了,也预示一天的工作任务即将完成。这时李妈总要再说一句:明朝还想吃点啥,要调调花样……
之后的一年,做医生的母亲下乡去安徽东至县巡回医疗,期限一年,保姆李妈不在我们家做了,父亲承担了家里的生活起居。每天的早饭,拿着父亲给的一两半粮票,可以到红光饮食店买上粢饭豆浆再加一根油条,晚饭吃他单位食堂带回来的饭菜,礼拜六下午还可以去厂里的澡堂洗澡。白天没有人管束的日子是自在的,吃饭没了准点,时常会饿,但是还要省下零钱去买零食。
天晚了,没有夜灯,弄堂黑沉下来,褪去傍晚时刻的热闹,听不到父亲的自行车铃声我就不回家。黑暗中弄堂空了,窗内的灯溢出昏暗的光,把人照得影影绰绰,周围有着不见底的深远。我绕着弄堂疯跑了一会儿,心里也开阔起来,感觉无比清爽畅快,好像整个弄堂都是属于我的……
那天的晚饭是电影厂单位食堂加餐的白切羊肉,蘸着陈醋和豆瓣酱料去除羊的膻味。我迫不及待地享用诱人美味的大块羊肉,几块肉下去已经撑满了,但是继续喝掉了早饭剩下的半瓶牛奶。临睡前开始腹胀,恶心难受。躺在床上开始想让自己快快睡着,用睡眠来抵御难受的感觉。在倦怠乏力中昏昏沉沉地睡去,可还是没有熬到天亮。半夜,胃里翻滚起来,已经来不及凑到床边的痰盂,在迷迷糊糊的一瞬间,直立起来蹿向父亲睡觉的大床另一侧,在父亲床沿处的毛毯上,大口地呕吐起来。吐干净了,我的神志清晰起来,身上床上地板上一片狼藉,那条白色绿花的纯羊毛毯子,沾满了黄唧唧的黏稠物,这可是家里的值钱物品,父亲花了大半个月的工资新买的。看着自己的成果,一下子惊吓起来,这下又要挨揍了,至少逃不过一顿责骂。
没想到,黑暗中,父亲迅速起身,开灯下床,看到毛毯大块的污迹,虽然呈现出惊愕的神情,却没有任何责备的表示,只是把热水瓶里的温水倒入脸盆,拿蘸湿的毛巾擦拭干净我脸上身上的污浊,替换了棉毛内衣,用没有被弄脏的被褥把我包裹紧了,再细心地擦拭那条毛毯。我看着白绒绒的羊毛擦也擦不掉的几大块黄渍,没有听到父亲的埋怨,这反倒使我更加自责,为什么要吃那么多?内疚啊……
冬天,屋里很冷,脸盆里的水是温热的,水瓶的热气冒上来时,在窗玻璃上哈了一层水汽,湿气又裹住了泛着钨丝灯昏黄光亮的房间,显得更加昏暗氤氲了。一阵忙乱后,父亲这时才想到在自己的白汗衫外披上一件绒布夹衫,父亲的背佝偻着,拿着拖把一下一下地拖地,夹衫从肩上滑落下来。昏黄的灯光把他的身影投到斜顶的墙面上,影子在斜面的交接处又分裂开来。我裹着被子,不知道是胃难受还是心里难过,慢慢地躺下,侧向一边让自己好受些,望着父亲的背影,看着看着,眼睛有些湿了。
现在我也做了父亲,儿子身上有我的影子,许多的缺陷陋习,管束训斥的同时我也在检点反省自己。发生在儿子身上的麻烦事,要我做父亲的去解决和承受,有时是难以忍受的不堪,像是我上辈子欠下的债。而每当儿子生病发烧腹泻呕吐,我都是默默陪伴,默默地收拾清理污浊,再脏再累也不怨。这时就会想到父亲的身影,对父亲的亏欠,想着怎样才能偿还……有了儿子之后才知道了“爸爸”这两个字的含义。
几年后家要搬迁了,那时父亲已经病得很重,从住了半年的一家医院出来,等待转院,要去好一些的专科医院治疗。家里的家什衣物电器大都搬走了,只剩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大床没有了,睡觉只能打地铺。那只皮椅还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因为破损严重,坐垫的鬃毛弹簧已裸露出来,是在准备丢弃的行列中。病势削弱了父亲的身体,原本敦实挺拔的体型瘦瘪下来,皮肤干枯,肩膀手臂处黑黄起皱,留下了化疗时的印记,但父亲精神很好,或许是生病的原因,上帝心软了,父亲努力争取换房的要求实现了,我们将搬进有单独卫浴的新房,完成多年以来的心愿。
那天午后,光线照例从西面天窗斜洒进来,没了家具,磨损泛白的木漆地板敞开了大面积的区域,靠墙家具移走的地板处剩下的油漆面,光亮泛到斜顶上,分裂成好几块几何图形,屋里通透敞亮,可以忽略泥板条墙面的剥落破损。心情好的父亲有了胃口,想要吃小笼馒头和咖喱牛肉汤。
我不记得严谨的父亲有要我买过吃食的经历,包括烟酒之类的东西。但这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急速拿了钢精锅,抓起自行车钥匙掉头往外冲,我知道父亲要吃哪家饮食店的点心,就是虹桥浴室边上的红光饮食店的小笼馒头。
许多个礼拜六的下午,父亲带我去公共浴室洗澡。热气蒸腾之时,在大浴池里泡上半个小时,父亲闭目享受,蒙眬之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之后帮我搓背,父亲搓得细致,我平躺在池子边,浑身通红硬撑着也不敢出声,冲洗过后待酥软乏力时再躺上一个小时,晾干身体、热量褪去后就觉得饥肠辘辘,接着就去吃那家店的点心。这时神清气爽,头上身上还散发着香皂遗留的气味,点上咖喱牛肉汤和二两小笼,倒上小碟米醋,刚出笼的小笼馒头滚烫诱人,一下子食欲大开,在口舌间的享受之时是这个礼拜最清爽适意的时刻。
赶快跑回家,趁着钢精锅里的小笼还有余热,倒上陈醋,放在父亲面前。父亲吃得很认真,他慢慢地吃着,像是在完成一幅工整的制图……父亲嵌在皮椅里,旧损的椅背遮住了他大半个身体。天色暗淡下来,空空的屋子,原本就开始萎缩的父亲,现在变得更加瘦弱单薄,即使倔强耿直的父亲,这时也显得无力无助。
看着父亲的背影,想着要搬入的新家,有单独的煤卫间,再也不用排队洗澡、抢公用厕所、用痰盂撒尿,有钢窗阳台,不用挤大床,我有自己的小床,要有一张两人坐的大沙发,软软的绒布包面的,等父亲再出院了,不用再坐那只弹簧顶着硬皮硌屁股的破椅,沙发弹簧一定要好,松软有弹性,坐久了也不会累,实在累了还可以躺一会儿,还要在沙发背和扶手边,铺上白白的镂空编织布。
父亲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病房,最终没能扛过去,他永远地离开了。
我和母亲终于搬家了,这样的告别使我追忆父亲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斜顶天窗背景的老房子里,那是父亲的老房子。
三十多年过去了,门前的马路拓宽了,切割了几幢楼的门面,露出了弄内隐秘的山墙,一眼能望见深处的弄堂底部,剩余沿街面的门洞改成了美容店、餐室、碟片店,我再也没有踏进过弄堂,几次经过也是绕路走,我确信再也回不去了,那时的一切已经物是人非了。
现在我把老房子的故事刻在记忆中,留在夜的梦呓里,它属于我的童年岁月,它属于我和父亲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