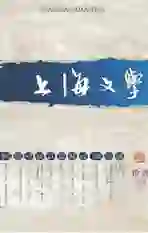聊斋?布拉格
2016-11-21陈文芬马悦然
陈文芬++马悦然
一、普实克
几年前悦然跟我到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所访问,史语所图书馆陈列展示蔡元培所长与高本汉1928年的通信手稿来欢迎高本汉弟子,悦然从老远就望见高老师的手稿,眉开眼笑。
“他写的字大,字跟字之间很宽。”悦然说。
手信确实有一种力量可以使人把无限想像推往宽广的历史之间的皱褶。
1929年是一个很奇妙的年份,蔡元培邀请高本汉担任历史语言所的外国通讯员,由于日后的战争与研究院长途的迁徙,这份通讯员的邀请可以看作是外国著名汉学大师担任外国院士以前的一份约定。史语所邀请的对象还有法国的大师伯希和、德国汉学家F.W.K·穆勒,通过这位二十四岁就成为清朝翰林的名士之手,现代民国望重四方的“天下第一所”史语所与欧洲汉学做了第一次东方遇见西方的手指点接。
1928至1929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1906—1980)负笈瑞典跟高本汉老师学习。那一年高本汉正在歌德堡大学担任校长。普实克在这儿学习《聊斋》,以后他回到布拉格将《聊斋》翻译成捷克语。
普实克1928年只有二十二岁,他曾经到德国学习汉学,在他以前捷克没有大的汉学家。普实克的学习非常专心。高本汉教他唐宋八大家、《史记》《汉书》。1928年到1930年,高本汉的精神体力处于巅峰状态,普实克的努力学习也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汉学家。
普实克1932年至1934年到中国继续学习,他与鲁迅、胡适、沈从文、徐志摩、郑振铎、冰心等中国最好的作家有来往,尤其跟鲁迅的交往很深,彼此有长时间的书信往来。普实克不只研究翻译鲁迅的作品,1949年以后普实克得到一批中国的书籍,大约二万七千册,普实克以“鲁迅图书馆”之名,在布拉格的地标铭记鲁迅的文学贡献。
“普实克是一个君子,他以鲁迅的名义做图书馆,报答鲁迅对他的欣赏。”
普实克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经过悦然的鉴定成为汉学家的座右铭。
普实克说:“你没有翻译过的书,等于没有读过。请不要讨论没有读过的书。”
普实克其人高大硕实,有一种贵族出身的自信与谨慎,他本人的思想却是较接近于安那其的无政府主义,普实克很欣赏解放区的中国“左翼”文学,对于赵树理、孙犁、浩然的文学作品,普实克很早就开始阅读。
悦然指出,汉学的巨塔浩瀚无边,当时很少有汉学家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普实克不仅很早阅读1930年代文学作品,在历史的现场跟作家本人交往,也是最早阅读中国解放区文学作品的汉学家。往后普实克的弟子都有关注现代中文文学的倾向。
普实克是一个坦诚而直率的学者,他曾经批评夏志清撰写的《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对于鲁迅的评价,是不知鲁迅为何成为鲁迅。
夏志清的西方文学修养非常好,可惜他对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传》这类口传文学的评价极苛刻,夏志清在小说史中描述鲁迅的小说审美,也是普实克不能接受的。普实克与夏志清的论战闹得很厉害,详细的文论刊载在捷克东方学院的年刊。
对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有激烈评论的欧洲汉学家不只普实克一个人,许多研究现代中文文学的专家都有意见,就鲁迅与左翼文学的评价,悦然认为作为最早研究现代中文文学的先辈,普实克说了真话。
写到这儿,我又想起普实克给汉学同行的座右铭:“你没有翻译过的书,等于没有读过。请不要讨论没有读过的书。”仔细琢磨这句话,它的哲理很深。
1975年马悦然获得斯德哥尔摩大学荣誉博士,同时马悦然也推荐普实克获得斯大的荣誉博士。
当时马悦然五十一岁,普实克七十岁。
悦然记得,宁祖在优思宏的大房子宴请普实克,庆祝两人的博士宴席,普实克却挂记着究竟要买什么礼物送给管家与司机。
现代的瑞典是没有家佣的社会,宁祖的三个儿子从住在澳洲开始就有替母亲做家事的习惯,老二佩尔是最尽职的管家,一放学回家就抓起吸尘器,整理完才去做功课。瑞典的家庭宴客时孩子们会穿上白衬衫当服务员端盘上菜。
悦然担任欧洲汉学协会会长期间,住在斯京郊外优思宏高耸山坡上的大房子,经常宴请欧洲来的汉学家,家庭酒会由老二佩尔负责吸尘、拖地,老大安德世安排桌椅座次,布置长桌摆设餐盘,老三贡纳出来跟客人们一一问好。宴会结束,家长给孩子发奖金,奖金都一样。老大问老三,我们做了那么多事,你什么都没做怎么能得一样的奖金?老三说,我给客人带来好印象。
有一次宴请波兰的汉学家斯禄普斯基(Slupski),他也是普实克的弟子,研究《儒林外史》与老舍的作品。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那批年轻的学生、马悦然的学徒们当然也属于优思宏家庭酒会的一份子,悦然的学生罗思(日后成为隆德大学中文系主任,现已退休)酒量并非海量,经历过一场汉学酒会已大约见识欧洲的汉学家,他喝得差不多了,向身旁的波兰汉学家宣布,“关于‘文革的研究,我比在场的每个人都要深厚。”
斯禄普斯基非常感兴趣,“愿闻其详。”
罗思夜里没回家,由马家的儿子们看管留宿。
与北欧汉学家的生活情况做个比较,普实克挂念着给管家买礼物是共产社会才有的甜蜜的负担,老君子也。
二、白利德
汉学家帕拉有一个汉语名字叫白利德。
悦然一直称呼他的名字奥古斯汀,私下跟我讲则称呼他的姓氏帕拉。
1950年代悦然担任瑞典驻北京大使馆的文化秘书时已经认识帕拉,帕拉担任捷克大使馆的参赞,实则深入教育文化各项业务。
当时中国跟捷克政府的关系非比寻常,中国跟捷克购买史固达的卡车,帕拉要去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去得成,卡车去哪里,像是拉萨这样的地方,帕拉就能跟着去,真是叫人羡慕,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官跟中国没有那么从容的友好关系。
帕拉在北京当参赞的时期,简直就是北京外交界的贵公子。
帕拉常常跟悦然见面,他认识所有的作家,跟文化部长茅盾交情深厚。
悦然1956年通过作协副主席老舍帮忙跟中国作家往来,一过了1956年就不行了。
帕拉却没有任何限制,他跟许多中国作家都那么友好,巴金、郑振铎、老舍、艾青。
悦然跟帕拉见面时就可以得知中国作家的近况,帕拉的讯息总是最直接又可靠。
帕拉原来是普实克的学生,专攻法律学与政治学,他是普实克以后的第二个跟中国作家关系最亲近的汉学家。帕拉的专长是宋朝的政治跟历史。
1959年悦然离开北京去澳洲教书,帕拉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前,已经回到布拉格的东方学院做学术工作。
帕拉1950年代的北京生活,至今还让人神往。
三、布拉格之春
1968年的7月底,宁祖跟悦然带着两个学生,到意大利教学。
一个是艾思仁,另一个是在中国长大曾经在北大读书的白俄学生。他们俩人中文好极了。
意大利的北方有一个岛叫Capris,从前一个瑞典有钱的名医1904年在那儿盖了许多房子,以后送给瑞典政府,学者们可以跟一个基金会申请住在那儿做研究,悦然就申请带了学生在那儿开课。
8月25日悦然跟宁祖从意大利北方开车,打算前往捷克参加一个汉学协会,当时还没有成立欧洲汉学协会。
汽车到了中途,听广播快报:苏联军队打进布拉格。
“我们在路途欣赏风景,知道没有希望,就回去瑞典。”
第二年1969年,悦然还没有当上皇家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以前,也还没选上院士呢,人文学院跟布拉格达成交换学者的协约,可当时的瑞典学者谁都不愿意去布拉格,只有悦然一个人申请,1969年得到一笔奖学金,1970年代悦然每一年都去布拉格。
1968年以后布拉格的东方学院已经关闭。图书馆还在那儿,所有的捷克学者都不能进去,不能做研究。
悦然去布拉格以前,事先声明愿意在东方学院开课,由于捷克与瑞典人文科学院的协议合约,悦然一到那儿,东方学院必须开门。
“捷克人似乎还是有一点怕外国人,换作波兰,肯定不会打开东方学院的门。”
“我一堂课都没讲过,就去摆龙门阵。”普实克、帕拉还有一群布拉格的汉学家他们都在,全部都来,哎,真好玩。
“我带了糖、烟草、咖啡、罐头,带了很多物品,大家都很高兴。我整天跟帕拉、普实克聊天。”
当年的捷克汉学家不能进自己的学院跟图书馆,情况很困窘,没有书就不能做研究,不像现在人人可以上网。当时捷克的汉学家多半在家里勤奋地做起翻译工作。
帕拉非常爱吃,他认识布拉格所有好的饭馆。
有一天帕拉带悦然去一家野肉烹调著名的大饭馆。
跑堂的领班原来是捷克驻北京大使,他回来没有工作,到饭馆当起领班。
帕拉请悦然吃一道汤,汤的味道有点像罗宋汤。
北京的苏联饭馆有罗宋汤,里头有很多胡萝卜,这道汤使悦然想起北京的往事。北京的苏联饭馆的厨子非常好,价钱又合理,悦然跟宁祖常常到苏联饭馆打牙祭。
帕拉说,什么,俄国有汤吗?这我没听说过。
领班大使说,喔,苏联有汤吗?这我没听说过。
捷克一般的老百姓深有幽默感,布拉格大城市居民比较缺乏捷克人的幽默感,但是他们十分擅长讽刺、挖苦,发挥这种城市性格时他们甚至不计较深埋自己的优点长处。
研究汉朝历史的浦古拉(Timoteus Pokora)跟悦然在街上散步,墙上有一张海报写着俄文的大字。
悦然说,你翻译给我听吧。
浦古拉以俄文流利在学界著名。
他说,我不会俄文,我不知道写的什么。
四、米列娜
每一个去过布拉格的朋友都认识米列娜,好像她是布拉格的钟塔。
我第一次听到悦然讲米列娜,却是在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博物馆跟现代美术馆船岛底下的那块坝子。
有一天,悦然跟宁祖从远东博物馆走下来,走到那块坝子,悦然的眼力好,就在六十米处,“有一个人,她好像米列娜。”
宁祖说,“要是米列娜到瑞典来,没有先告诉我们,我要生气了。”
站在六十米外的女人霎时间停住脚跟,她也看见悦然跟宁祖。
米列娜的表情很不自在,她说,我不能解释我为什么到瑞典来。原谅我吧。
悦然常常想念布拉格。
一个汉学家想念布拉格,写信给米列娜就够了。
2008年春天,查尔斯大学中文系主任给悦然安排了一堂演讲,住在离老城广场不远的教育部招待所。
出发以前悦然交代我,布拉格的汉学家不一定都讲汉语,悦然与他们总是讲英语,他们的汉语有个小特色,把“诗经”说成“诗羹”或“诗梗”,我感觉听来像粤语。
米列娜在机场相迎,一头栗色的波浪短发,薄纱丝巾,驼色西装长裤,同色船鞋,典型欧洲城市职业妇女的穿着。
米列娜一跟悦然见面就谈论研究计划,出租车来接,悦然进前座,两个女人坐后座。米列娜用英语问我:“你呢,你有什么计划(研究)?”
进招待所安顿以后,米列娜带我们走过广场,到处是旅客人潮,她的表情很不高兴,布拉格的居民总是想尽办法躲过观光客,但是不容易。
我们打算搭电车坐一两站去一家咖啡店。
老城的鹅卵石之间的小凹洞不停地抓住我的脚底板,布拉格的天空宏阔得惊人,先不说已遭观光客围观的钟楼,使人惊吓的是灰色大理石外观的大教堂,辉煌得像一个梦境里的城市,那教堂附近就是作家卡夫卡的父亲的店铺,以及他每天生活与工作的银行。卡夫卡肯定有一双好鞋子,能每天行路与思想。
米列娜好一会儿才用汉语吐出:“你还没有走惯。”
我坚持说汉语,米列娜就得用汉语回答。1970年代悦然到东方学院摆龙门阵的时代,米列娜不在。米列娜也是普实克的弟子,以后她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当汉学教授。
电车把我们带到一个安静的城区,路过画报小亭到咖啡店。
咖啡店的服务员好像是米列娜的老朋友,闲话家常。
一坐下来悦然问:“米列娜,你为什么带我们来星巴克?”
米列娜说,我就知道你要生气。
我是个咖啡鬼,已大口啜饮咖啡。“很好喝哎。”我说。“你看吧。”米列娜得意地对悦然眨眼睛。
过两天我们就懂了米列娜为什么去星巴克,而不是充满配饰图文色彩对比的新艺术咖啡屋。那里观光客太多,布拉格的居民还欣赏资本主义的咖啡店。我去化妆室回来拿相机按快门。
米列娜吼我,“你偷偷给我照相是吧。”米列娜汉语说得很流利。
晚上到老城饭馆,喝一杯金黄色的啤酒,吃一道酸菜鸭肉配土豆泥。
鸭肉好大一块,土豆泥压榨得又浓又厚,我担心吃到半夜才能吃完。
餐馆化妆室跟伦敦很像,都在地下室,穿白围裙、扎辫子的姑娘坐在门口,有张小桌,每人每次收一个铜板。布拉格是一个新旧交融的城市,城市的相貌非常华丽,宛如神仙天堂,可也随时能照见历史的鬼魂阴影。
米列娜带我们去看布拉格的玻璃艺术,瑞典的玻璃历史源自于布拉格,到一栋大楼去看玻璃精品,米列娜细数她的祖母使用的餐盘,感觉她就是一名《红楼梦》里的闺秀,只有这样的娇女配得上城市的历史。
我开始问米列娜为什么学汉学。
米列娜说到她的儿童与少女时代,生活落差很大,祖父是捷克史固达汽车的创办人之一。
“他们到瑞典学造车,学得还可以,回来就发展出来。”儿童时期米列娜见证祖父、祖母家庭宴会的辉煌,在玻璃大楼她很仔细地指给我看,祖母使用过的酒器,红酒、白酒、餐前酒,她又带我去离广场较远的小巷玻璃铺子,跟她相熟的女老板用红酒杯轻轻碰响不同音阶的演奏,布拉格的居民用耳朵选杯子。
少女时代,共产党来了。
米列娜跟她很要好的女同学,每天高高兴兴在工厂工作,她们没有唉声叹气,而是把劳动当作运动和游戏,每天有好心情去干活,就这样两人同时当选模范劳工,等于领到求学问的一张证书。
“有很多书是不准许我们读的,这个不许,那个不许,那么有资格读大学就读最遥远的中国的书好了。”
到了布拉格自然要去犹太区看教区、墓园。
坟冢林立的墓园外头的街道不远处有一个卡夫卡的雕像,我问米列娜年轻时候对卡夫卡的看法。
“看法,哈,我们年轻时不准读卡夫卡。”
五、查尔斯大学
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是东欧、中欧、北欧的第一所大学,这个说法真奇怪,总之查尔斯大学的历史太古老,古老到值得这么记载。
我对查尔斯大学的幻想由来已久。悦然每一次穿全套燕尾服必然戴上他的查尔斯大学荣誉博士金质项链。项链垂挂在他手打的白蝴蝶领结底下,显得儒雅贵气,引人注目。他得过好几个荣誉博士,唯有查尔斯大学有这么美丽的大金质项链。
进入查尔斯大学校舍确实有中世纪大学庄严肃穆的气氛,地理位置在城中心,哎,这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世界以大学为中心形成地球的运转。相比之下,斯德哥尔摩大学在城外以几栋完全相同的大楼拼装起来的著名现代化建筑,近观缺少历史纵深,鸟瞰仿佛乐高玩具。
学校的气氛当然很好,学者们都来听悦然讲课。记忆最深刻的是木质纹路深刻的两扇大门,推开门,外头满街的旅人,两旁的铺子摆的不是克林姆的金漆盒上头画着《爱人》的画像,就是布拉格上世纪的红色宝石首饰。
“我祖母戴的就是这个。”悦然指给我看。当年整个欧洲的妇女时尚潮流经过近百年以后,随着布拉格重新崛起,新艺术时期的红宝石系列首饰再度席卷欧洲的古董市集,标价很高,高得使人明白全球化这个艰涩的词语的真义。
“咖啡鬼”饥肠辘辘,需要一杯加奶的咖啡,还要鸡胸肉凯萨色拉。
米列娜手指这道门的外头对面二楼就是一家老咖啡店,超级标准的新艺术形式,黑白格子地板,木头报夹挂墙沿,天花板花叶电扇转。
女服务员年轻又害羞,她几乎不能把自己的脸对着米列娜,最后她是隔着菜单听完悦然的英语,转身离去。“模范劳工”米列娜一时气结,服务不尽人意,一想这家悠久的咖啡店很可能卡夫卡来过,话题就转开。
卡夫卡的作品以德语写作,他并不像我们阅读中文译文那么哀伤忧郁,听说他在咖啡店朗读自己的作品,经常把自己与一伙朋友逗得开怀大笑。
我买了卡夫卡的照片相册,有他童年长发卷发的样子,也有他学习游泳在泳池旁边晒肌肉的照片。
我没有错过询问米列娜关于另一个著名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机会。
“他住在巴黎啊。”布拉格人都这么说米兰昆德拉。
“你不知道他的捷克文有多么好,后来用法文写的,简直比不上。”
晚上悦然请所有他认识的布拉格汉学家在一个小酒馆吃晚饭,大概来了十二个人。
帕拉来了,带着一只“好兵帅克”的啤酒杯给悦然,还有一纸1950年悦然写给他的信。那是他们在北京时期的通信。
有一个在台湾待过三年的年轻女学者告诉我,帕拉妻子过世以后,他捐出所有图书给大学,一个人搬到老人公寓,房间很小,没有多少书,闲时帕拉常常拿出过往朋友给他的信件,沉浸在过去的时光,回忆真美丽。
悦然原来想请米列娜跟帕拉两人吃饭,又觉得很多朋友会来,不如全部请了。
帕拉是个老君子,他有一点难过,毕竟这不是1970年代的布拉格,悦然不应该请客。
布拉格学者面临另一个时代的怪象,以查尔斯大学内部的严谨沧桑,埋头案首浩瀚经典,一门之隔,屋外狂飙的物价,追逐上世纪的玻璃珠宝器物。
这天晚上大概有捷克三个世代的学者相聚:帕拉、米列娜、克劳、浦克拉,当过外交官的老汉学家何佳德、中生代女学者包捷,以及普实克的孙子,他也成为一个学者。
克劳以前在城外的博物馆工作,博物馆收藏捷克一个富商在1930年代搜购的一批齐白石的画作,大约有九十幅之多。悦然1980年代在克劳的陪同下看过那批画,当中有许多人物画,这在齐白石的作品中很罕见。布拉格可能是中国以外收藏齐白石作品最多的城市。
六、他们不在了
2012年的10月,米列娜的女儿(也叫米列娜)写信给悦然,告知母亲病重。
悦然当时很困惑,捷克人的署名非常麻烦,米列娜的母亲也叫米列娜,究竟哪一个米列娜生病。
悦然的潜意识不相信充满活力的米列娜即将远行。
第二年春天多伦多大学发布举办米列娜的纪念讨论会,我们才知道米列娜已在冬天过世。
悦然在写给朋友的纪念信中回忆了一段往事。他担任汉学协会会长时,与所有的汉学家们一起编撰四册《19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简介》,米列娜担任小说类的主编,有一回她从布拉格飞斯德哥尔摩的班机延误,到了悦然欧登街的寓所,已是晚上近十一点,所有的学者坐在客厅等她。
米列娜进屋时外套还没来得及脱掉:“给我一杯威士忌,我就可以开始工作。”
米列娜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婚姻,丈夫是捷克一个很大的文学教授,可惜婚姻维系不够长久。米列娜遭受感情打击,很快就把全副的精力专注到学术工作。当然她还是一个生活多彩多姿的女人,她在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底下的坝子,不期然遇到宁祖跟悦然,正是一段默默发展的感情插曲。
台大教授周志文曾经在查尔斯大学客座一年,他在米列娜过世后与我通信,提到米列娜对于“五四”的看法。米列娜认为“五四”带给中国的并非前进而是伤痕,周教授对这个观点惊讶而佩服。可是按照悦然的理解,米列娜专攻晚清文学,她对于晚清的新文化运动的脉络了解很深,她认为新文化运动继续往前发展,那么一个更美好的时代,更理想的中国就会到来,这会远比“五四”的情况好得多。米列娜的观点不见得能说服其他的学者,她的研究怀有很大的善意,那是毋庸置疑的。
帕拉一直很想念悦然,2015年圣诞节前夕,悦然收到帕拉的圣诞卡,写满密密两页的卡片。
悦然当即回信帕拉,春暖花开就去布拉格看他。写信给查尔斯大学中文系主任约定二月就去讲学,可惜悦然二月身体微恙,四月想去,又遇到暂时困扰的眼疾不能成行。
帕拉没有等到悦然,2016年晚春悄然远行。
那只“好兵帅克”的酒杯,我放在柜子最高处,不时仰望。
七、在巴黎
自我来到欧洲以后,跟高君唯一一次理想的谈话,是他与妻子芳芳到我们寄住巴黎的寓所楼下的饭馆午饭相聚,我跟他谈起布拉格可能是欧洲最伟大的城市。
曾经看过瑞典电视台播放的一部片子,根据公布的德国纳粹文宣部长的日记拍摄,回顾纳粹发动的“二战”历史。
文宣部长曾经到过布拉格,心迷神醉于城市河岸宏伟瑰丽的景观。
他在日记里写道:“这就是我们纳粹的理想天堂一般的美丽城市。”诸如此类写出满纸神乎堂皇的赞美之词,是以德军轰然攻进布拉格以后,德军尽其努力保护城市所有的建筑景观。
我描述这段景象时,高君露出久违的潇洒笑容。自从他得过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在台北导演一部实验意义强烈的话剧《八月雪》,因为排练太过辛苦,中途在台北的医院做过大手术,从此失去过往的健康。
好在这些年高君深居简出,慢慢在创作水墨画的意念里坚强地延续自己的意志与生命力量,举办过许多水墨画展,尽管他有好多年没有新的剧作与小说。
此时高君的答话追赶了我先前的意念。
“共产党也统治了布拉格好长的时间呢,没有拆掉一块砖一片瓦。”
高君本来就擅长简单的人物跟对话,对话总是写得像是真实生活中人们说的话,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很快就把一个信念、一种哲学说清楚讲明白。
饭馆响起一片纯洁清亮婴孩的哭声,是一对年轻的夫妇推摇篮车在饭馆露天走廊吃饭,婴儿可能只出生几天,才能有如此美丽的哭声,引得我们探头看五月春天的巴黎天色,郁蓝如新。
目送高君离去时,悦然说,他跟从前一样的年轻有劲儿,像一个新人。
马子曰:
布拉格的汉学比起别的欧洲国家的汉学相当不同。
捷克东方学院20世纪的汉学家差不多都跟他们老师普实克(Jaroslav Prusek 1906—1980)的学术兴趣相像。主要研究的领域是话本文学的源流与发展,蒲松龄的《聊斋》、晚清文学、中国解放区的文学,尤其是1930年代文学作品。
普实克先生跟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学了两年之后(1928—1930)到中国去继续学汉语与中国文学。他那时跟中国文学家与作家有了很密切的关系,他的学生因此有很好的条件在中国搞汉学研究。布拉格的汉学家也懂得翻译的重要性。Oldrich Kral据我看是布拉格汉学家里最优秀的翻译家。他翻译的著作包括《易经》《庄子》《文心雕龙》《六祖坛经》《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可惜的是西方的汉学家很少读懂捷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