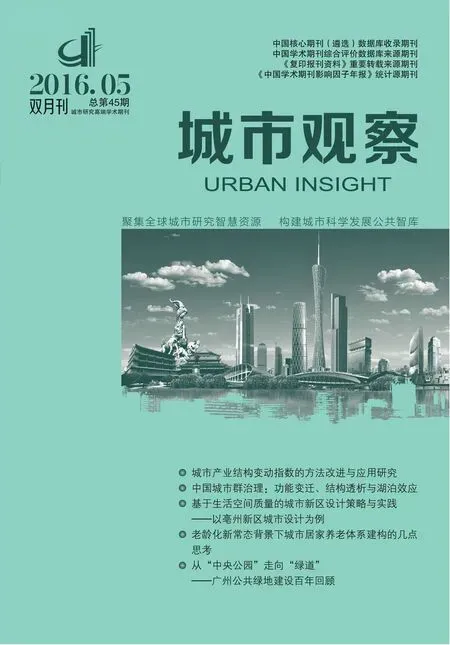广州市交通网络对居民出行碳排量的影响
——以聚德、社学、祈福与晓西社区为例
2016-11-08曹小曙
◎ 罗 依 曹小曙
广州市交通网络对居民出行碳排量的影响
——以聚德、社学、祈福与晓西社区为例
◎ 罗 依 曹小曙
低碳交通是实现交通可持续性的一种重要途径,其已成为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其中居民出行碳排量研究是其不可或缺的部分。以社区为分析单元,引发交通网络对居民出行碳排量的影响研究。选取广州市4个不同类型交通网络的城市社区作为案例,测量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并以436个样本数据库为基础,利用AMOS 17.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试图在社区层面上挖掘“交通网络-出行行为-出行碳排量”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交通网络α值越大,出行距离越近、出行时长越短、出行碳排量越低;交通网络β值越大,出行时长越短,出行碳排量越低;交通网络γ值越大,出行距离越远、出行时长越长、出行碳排量越高。
出行碳排量 交通网络 结构方程模型
低碳交通是人类低碳发展方向下体现在交通领域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以及为实现这种理念而采取的方式和执行的结果,是体现在交通运输领域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1]。研究低碳交通相关议题,是实现交通可持续性的重要途径。居民出行碳排量研究是低碳交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西方的行为主义与人本主义使得学者开始关注居民出行行为的个体差异,而社区逐渐成为城市研究的一个分析单元,由此引发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的差异研究。
国外学者通过抽样对不同个体碳排量高低进行分析,归纳出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差异分布规律,并运用SEM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个体出行碳排量的影响机制,发现居住密度、土地利用混合程度、设施可达性、社区区位等因素会对出行碳排量产生影响(Bhat CR,2007;Brownstone D,2008,2009;Handy S,2009; Valle D,2011)[2-6]。
国内关于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方面的研究,则始于中国城市居民出行行为调查。这些研究主要是以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为基础,将社区空间形态用土地混合利用程度、人口密度、道路交通设施等参数来表示,并利用相关分析、因子分析等数量手段分析其对居民出行碳排量的影响(杨磊,2011;刘沛,2012;黄经南,2013)[7-9]。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的研究大多关注社区空间形态、出行行为等因素对出行碳排量的影响,而社区空间形态大多是从土地利用程度、人口密度、道路交通设施等参数来体现,却忽略了最根本的交通网络结构。有鉴于此,本研究以广州市城市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问卷调查第一手数据为基础,通过引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交通网络、出行行为对出行碳排量的作用关系,来揭示居民出行碳排量的影响机制。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域
常用交通网络分析方法是用图论将复杂交通网络抽象为一系列基本要素,节点代表道路交叉点,节点间线段代表道路(Lowe JC,1975)[10]。抽象后一系列基本要素如点与线段通过二维系统组织起来,被称为一个平面图(Kelly ME,1998;Bowen JT,2012)[11-12]。这时,复杂交通网络的分析转化为平面图的分析。Marshall S通过对前人研究进行梳理,从交通网络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特色等因素出发归纳总结出直线型、支流型、辐射型和网格型四种交通网络类型[13]。
图论中α、β和γ系数可以用来计算网络的连通性,以便选取与理论网络具有相似特性的现实道路网。网络深度设定为3,以控制网络大小的影响,且使得不同连通度网络之间可以相互比较[13]。
本研究选取广州市城市社区作为研究场域,以广州市海珠区聚德社区、海珠区晓西社区、番禺区社学社区以及番禺区祈福新邨社区作为个案进行研究。
聚德社区位于海珠区新滘中路、江海大道、新港中路和广州大道南围成的地块中部,公交站点6个;社学社区位于番禺区钟屏岔道、市广路、Y873公路所围成的地块中部,公交站点2个;祈福社区位于番禺区禺山西路、西环路、市广路、钟屏岔道所围成的地块中部,公交站点0个;海珠区晓西社区位于东晓南路与新港西路形成平面的第三象限内,公交站点6个(图1)。
将图1的聚德社区、社学社区、祈福社区和晓西社区的现实交通网络运用图论进行抽象,并保证网络深度为3便于研究,四个社区的拓扑抽象交通网络模式如图2所示。
通过计算网络的α值、β值与γ值可以知道两个网络的连通性是否相似,而连通性对于交通网络来说十分重要,故选择聚德社区(直线型)、社学社区(辐射型)、祈福社区(网格型)和晓西社区(支流型)为个案的合理性,可以通过计算其网络α值、β值、γ值与理论网络的α值、β值、γ值进行比较得出。
如表1所示,理论网络的α值、β值和γ值与本研究选取个案交通网络的α值、β值和γ值相差不大(表1),故而认为其网络相似,可以选取聚德社区、社学社区、祈福社区和晓西社区作为本研究个案。

图1 聚德社区、社学社区、祈福社区与晓西社区交通区位图

图2 聚德社区、社学社区、祈福社区与晓西社区拓扑抽象交通网络
(二)研究方法
探讨不同交通网络下居民出行方式、出行距离、出行时长、出行成本与出行碳排量的差异,并以居民出行碳排量为因变量,出行方式、出行距离、出行时长与出行成本为中介变量,网络连通度(α值、β值与γ值)为自变量,利用SEM结构方程建立模型用以探讨影响碳排量的机制。
1.碳排量微观测算模型
城市交通碳排放量的测算方法已经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下拥有较多成果,但大多数都是宏观层面的。日本产业技术研究所LCA研究中心开发了NICE模型,研究国家行业碳排量,结果显示能源数量与类型是决定碳排量的决定性因素。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美国和瑞典的科学家开发了LEAP模型,分行业研究碳排量[14]。LEAP模型需要知道碳排放系数才能进入下一步计算,有学者利用IPCC指南中的碳排放系数数据计算碳排量[15]。
不同于利用碳排放系数计算碳排量的方法,部分学者通过计量模型直接算出各种交通方式的碳排放因子,进而计算得出碳排量[14]。MOBILE模型是利用经验公式计算各种因素对不同类型车辆排放量的影响,并用实际情况修正,最终得出实际运行状态下的排放因子[16]。COPERT模型是由欧洲委员会研究得到,同样分不同车辆类型研究碳排放因子[17-18]。MOBLE模型与COPERT模型的内在运算机理是不同的,且两者对车辆类型的分类也是基于不同基础。

表1 理论网络[13]与现实网络的α值、β值和γ值比较
以前者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需测算居民个体出行碳排量的实际情况,得到微观碳排量计算模型如下:

其中:
Eij是i类交通出行方式,j种含碳化合物的一次排放量,单位:kg;
Ej是所有类型交通出行方式j种含碳化合物的一次排放量,i、n分别为交通出行方式类型和车型总数,单位:kg;
Pi是i类交通出行方式的数量,单位:辆;
Li是i类交通出行方式行驶里程,单位:km;
Efij是i类交通出行方式,j种含碳化合物的排放因子,单位:g/km。
借鉴学者研究成果[13-17],结合本研究实际情况,得到碳排放因子(表2)。

表2 交通出行方式碳排放因子(单位:g/km)
2.SEM结构方程模型
为挖掘“交通网络-出行行为-出行碳排量”的内在机理,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研究。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处理多变量复杂关系的建模方法,相比回归分析而言,能够有效处理测量变量、潜在变量间的内生性,达到模型求解的目的。本研究只考虑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并不考虑引入潜变量,故可使用如下的结构方程[19-21]:
y=By+Γx+ζ
其中,y为内生变量的列向量,x为外生变量的列向量,B为内生变量之间的随机联系矩阵,Γ为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影响的路径系数矩阵,ζ为残差向量,反映y在方程中未能解释部分。
本研究在SPSS 20.0中建立了包含436个样本数据的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导入AMOS 17.0,利用最大似然法求解方程,进行参数估计。
(三)调研设计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居民一次交通出行中出行方式、出行距离、出行时长、出行成本等一手数据,并运用模型计算得到碳排量。调研采取随机抽样方法,在四个社区中心定点拦截过往社区居民,保证社区居民均在该交通网络中出行。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具有一定科学性,样本可以代表总体的实际情况。在问卷调查时,调研者需要将社区范围告知被访者,即是将社区的主要交通出入口告知居民,仍然是为了保证居民在该交通网络中出行。
调研共计发放48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436份,有效率为90.83%。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居委会访谈,获取关于社区的基本资料。
二、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特征
(一)社区基础数据描述
选择聚德社区、社学社区、祈福社区和晓西社区的原因是其交通网络与Marshall S总结的直线型、辐射型、网格型和支流型交通网络相似。近年来关于社区的研究逐渐兴起,以社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且四个社区在区位特点、建设年代、住宅形态及其居民属性特征上具有典型性(表3)。

表3 调查区基本情况
聚德花苑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赤岗东大塘村,是广州大型经济适用房社区之一,由聚德东社区管辖,根据访谈得知社区有居民约5576户,常住人口约9275人,外来流动人口约3522人,其交通网络总长度为2.67km。社学社区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中南部,根据访谈得知社区有居民约3475户,常住人口约5432人,外来流动人口约1081人,其交通网络总长度为3.13km。祈福新邨小区位于广州番禺区,由钟村社区管辖,由于小区面积过大,钟村社区在小区内设有祈福新邨工作站,根据访谈得知小区有居民约39820户,常住人口约572569人,小区居民经济实力较强,无外来流动人口,其交通网络总长度为10.13km。晓西社区位于广州海珠区昌岗街道,根据访谈得知社区有居民约3392户,常住人口约6345人,外来流动人口约2409人,其交通网络总长度为2.05km。
(二)不同出行方式居民出行碳排量差异
简单来讲,不同交通工具,燃料不同,在不同路况燃烧程度不同,碳排放因子不同,故而搭乘其出行所产生的碳排量可能存在差异。用人均每公里碳排量来反映该种交通工具出行碳排量特征,分析何种出行方式最低碳。碳排量由微观碳排量测算模型算出,每公里碳排量用碳排量与问卷调查数据中出行距离的比值经过单位换算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不同出行方式人均每公里碳排量
步行和自行车两种出行方式碳排量为0,在剩下的出行方式中,公交车的碳排量最低,其次是货车和电动自行车,接下来微型私家车的碳排量小于摩托车小于轿车型私家车,出租车的碳排量最高。
在只考虑碳排量的情况下,低碳出行方式最优的是步行、自行车和公交车。
(三)不同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差异
以聚德社区、社学社区、祈福社区和晓西社区分别代表直线型、辐射型、网格型和支流型交通网络。在不同交通网络行车时,由于其连通度即网络α值、β值和γ值不同,居民出行时可供选择的最佳路径存在差异,可能会影响居民出行碳排量。
由于不同出行方式对碳排量会产生影响,为了更加准确地显示不同交通网络对碳排量的影响,控制出行方式变量,以微型私家车为例,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
在出行碳排量方面,社学社区居民平均出行碳排量最低标准差最小,其次是晓西社区、聚德社区,祈福社区居民平均出行碳排量最高标准差最大。这一结果显示,不同交通网络类型的社区之间居民出行碳排量存在差异,说明不同交通网络对居民出行碳排量可能存在影响,这种具体的影响机制有待后续探讨。
三、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影响机制
(一)变量操作化赋值
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的影响机制是以建构SEM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来进行解释,在模型中以居民出行碳排量为因变量,出行方式、出行距离、出行时长与出行成本为中介变量,网络连通度为自变量。其中居民出行碳排量、出行距离、出行时长和网络连通度都是数值变量,只有出行方式不是数值变量需要进行赋值。
赋值方法依据前文(表4)关于不同交通方式出行碳排量研究的结果,由低碳到高碳依次赋值0~7等级变量(表6)。

表6 出行方式变量赋值及分布情况
(二)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结构模型建构
在AMOS 17.0软件中,导入SPSS 20.0形成的436个样本数据库,分组引入变量,逐步优化模型。在AMOS软件中选择Analysis Properties菜单,勾选Standardized estimates将原始数据正规标准化。本研究不考虑引入潜变量,所有变量均为测量变量。假设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都是单向传导;内生变量部分增加误差项检验ei(i=1,2,3,4,5),设定交通网络会影响出行行为,出行行为会影响出行碳排量,但是反之没有相关假设。故而交通网络是外生变量,出行行为与出行碳排量为内生变量。
运行模型,在AMOS软件中选择Analysis Properties菜单,勾选Modification Indices选项,便于进行模型修正,并参考输出的变量协相关矩阵和路径矩阵系数的相伴概率P值的显著性,逐渐去除与预期不符、不显著的作用路径。
综合考虑路径显著性与模型整体优度,经过多次尝试,得到最终模型的最小卡方值(CMIN)为21.324,自由度(DF)为9,最小卡方值和自由度的比值CMIN/ DF=2.369<3,数据有效性指标P=0.061<0.1,且规范拟合指数NFI=0.996>0.9,比较拟合指数CFI=0.998>0.9,拟合优度指数GFI=0.985>0.9,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0.063<0.08,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较高,数据有较高的汇聚有效性,误差项残差检验通过,最终模型接近最优模型,可以用其进行后续分析(图3)。
(三)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结构模型分析
本研究假设交通网络影响出行方式、出行时长、出行距离与出行成本中介变量,进而影响出行碳排量。构建模型过程中,出行成本整体表现不显著,误差项检验未能通过,考虑构建最优模型,故将出行成本变量删掉,用出行方式、出行时长、出行距离来表示出行行为变量。

图3 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的结果显示假设成立,整理AMOS软件输出的模型报告中标准化后的直接与间接路径系数(表7),进一步分析各变量间的关系,挖掘居民出行碳排量的微观机制。

表7 变量间的总体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1.交通网络影响居民出行行为
从结构方程中输出的标准化后直接效应系数可以看出,交通网络变量直接影响出行行为变量中的出行时长和出行距离变量。
交通网络α值对出行距离的直接影响系数达到-0.465,但未通过P检验;交通网络γ值对出行距离的直接影响系数达到0.963,在0.05水平上显著。交通网络β值对出行时长的直接影响系数达到-0.34,在0.05水平上显著。
交通网络α值和γ值对出行距离的间接效应几乎为0,忽略不计。交通网络β值对出行时长的间接效应几乎为0,忽略不计;交通网络α值对出行时长的间接效应为-0.293,在0.05水平上显著;交通网络γ值对出行时长的间接效应为0.608,在0.05水平上显著。
从总体效应系数可以看出,交通网络α值和γ值对出行距离变量存在总体影响,交通网络α值、β值和γ值对出行时长存在总体影响。
从效应系数的正负性可以看出,交通网络α值越大,居民在其中出行的出行距离越近、出行时长越短;交通网络β值越大,出行时长越短;交通网络γ值越大,出行距离越远、出行时长越长。
交通网络α值的定义是网络实际回路数与可能存在的最大回路数之比[22],α值越大说明网络中存在的实际回路数越大,即居民出行时可供选择的出行路径越多。在出行路径越多的情况下,居民容易选择到较短路径,从而使其出行距离越近、出行时长越短;可能不同居民选择了不同出行路径,但由于其出行路径较多,大多数被选择的出行路径都是较短路径,从而使其出行距离越近、出行时长越短。
交通网络β值的定义是网络内每个节点所邻接的边的平均数目[22],β值越大说明网络中每个节点所邻接的边的数目越多,即居民出行时在一个节点上可供选择的进一步路径越多。出行时可供选择的进一步路径越多越容易选到相对距离近的路径。
交通网络γ值的定义是网络实际边数与它可能存在的最大边数的比值[22],γ值越大说明网络实际边数越多。网络边数越多,即居民出行可能经过的边数越多,则出行距离越远、出行时长越长。
2.居民出行行为影响出行碳排量
从结构方程中输出的标准化后直接效应系数可以看出,出行方式、出行距离与出行时长变量均直接影响居民出行碳排量。
出行方式对出行碳排量的直接效应达到0.535,在0.05水平上显著;出行距离对出行碳排量的直接效应达到0.838,在0.05水平上显著;出行时长对出行碳排量的直接效应达到0.061,在0.05水平上显著。
出行方式对出行碳排量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125,说明出行方式直接正向影响出行碳排量,但同时通过间接负向影响出行碳排量,作用结果显示出行方式总体效应正向影响出行碳排量。出行距离对出行碳排量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038,增强其对出行碳排量的正向总体效应。出行时长对出行碳排量的间接效应几乎为0,可以忽略不计。
从总体效应系数的正负性可以看出,社区居民出行方式的选择越低碳其出行碳排量越低;社区居民出行距离越远其出行碳排量越高;社区居民出行时长越长其出行碳排量越高。
3.交通网络影响出行碳排量
现状研究中已经发现居民在不同交通网络中出行会导致其出行碳排量不同,从结构方程中输出的标准化后总体效应系数可以看出交通网络变量对出行碳排量变量存在影响。
交通网络α值、β值和γ值对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的直接效应几乎为0,即交通网络变量对出行碳排量变量不存在直接影响。交通网络变量对出行碳排量的总体效应等于间接效应。
交通网络α值对出行碳排量的间接效应与总体效应为-0.407,在0.05水平上显著;交通网络β值对出行碳排量的间接效应与总体效应为-0.021,在0.05水平上显著;交通网络γ值对出行碳排量的间接效应与总体效应为0.843,在0.05水平上显著。
交通网络连通度三个指标中,γ值对出行碳排量的影响程度最大且为正向影响,其次是α值与β值的负向影响。结合三个指标的定义可以发现,α值与β值越大体现的是可供居民选择的出行路径越多,居民越容易选择到相对距离近的路径,从而使出行碳排量较低;γ值越大体现的是居民出行可能经过的边数越多,则出行碳排量较高。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围绕交通网络对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影响的研究命题,本文利用广州市海珠区聚德社区、番禺区社学社区、番禺区祈福社区、海珠区晓西社区4个不同交通网络类型的城市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的问卷调查一手数据,测量居民个体出行碳排量均值,并基于居民个体数据建立“交通网络-出行行为-出行碳排量”的结构方程模型,以揭示居民出行碳排量的影响机制,得到结论:交通网络α值越大,出行距离越近,出行时长越短,出行碳排量越低;交通网络β值越大,出行时长越短,出行碳排量越低;交通网络γ值越大,出行距离越远、出行时长越长、出行碳排量越高。
本研究从交通网络角度切入,研究不同交通网络类型社区居民出行碳排量的差异及其影响机制。交通网络类型的划分是采用Marshall S的研究成果,而区分不同交通网络是利用图论中连通度系数α值、β值与γ值的差别,建立结构方程时,便采用α值、β值与γ值编入数据库。虽然α值、β值与γ值可以表示交通网络的特征,但并不是交通网络的全部,故而本研究存在局限性。
在现今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高能耗高污染高碳排的经济渐渐将被可持续低碳经济所取代,低碳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低碳交通是实现可持续交通的一种重要途径,是地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在低碳交通大背景研究议题下,从行为主义的角度出发,关于居民出行碳排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十分必要,而以交通网络为切入点的研究一度缺乏,从增加系统研究的角度,交通网络对出行碳排量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探讨。
[1]宿凤鸣.低碳交通的概念和实现途径[J].综合运输,2010(5):13-17.
[2]Bhat CR,Guo JY.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built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n household residential choice and auto ownership levels.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2007,41(5):506-526.
[3]Brownstone D.Key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VMT.In: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and the Division on 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 Special Report 298,Driv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e effects of compact development on motorized travel,energy use,and CO2emission.2008.
[4]Brownstone D,Golob TF.The impact of residential density on vehicle usage and energy consumption.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9,65(1): 91-98.
[5]Handy S,Krizek JK.The role of travel behavior research in reducing the carbon footprint: Form the U.S.perspective.The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ravel Behavior Research.Jaipur,India,2009,(10)
[6]Valle D,Niemeier D.CO2emissions: Are land-use changes enough for California to reduce VMT?Specification of a two-part model with instrumental variables.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2011,45(1):150-161.
[7]杨磊,李贵才,林姚宇,叶磊.城市空间形态与碳排放关系研究进展与展望[J].城市发展研究,2011(2): 12-17+81.
[8]刘沛,杜宁睿,黄经南,向澄.基于社区尺度的城市空间参数对家庭日常出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A].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多元与包容——2012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6.住房建设与社区规划)[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2:22.
[9]黄经南,杜宁睿,刘沛,韩笋生.住家周边土地混合度与家庭日常交通出行碳排放影响研究——以武汉市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13(2):25-30.
[10]Lowe,J.C.,1975.The Geography of Movement.Houghton Mifflin,Boston.
[11]Kelly,M.E.,1998.A geographer's analysis of hub-and-spoke networks.J.Transp.Geogr.6 (3),171-186.
[12]Bowen,J.T.,2012.A spatial analysis of FedEx and UPS: hubs,spokes,and network structure.J.Transp.Geogr.24,419-431.
[13]Marshall,S.,2005.Streets and Patterns.Spon Press,Oxon and New York.
[14]孙正春.基于低碳成本计算的城市交通结构优化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1.
[15]马静,柴彦威,刘志林.基于居民出行行为的北京市交通碳排放影响机理[J].地理学报,2011(8):1023-1032.
[16]任小平.基于MOBILE6.2模型的西安市机动车综合排放因子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6.
[17]谢绍东,宋翔宇,申新华.应用COPERTⅢ模型计算中国机动车排放因子[J].环境科学,2006(3):3415-3419.
[18]何春玉,王歧东.运用CMEM模型计算北京市机动车排放因子[J].环境科学研究,2006(1):109-112.
[19]吴明隆.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263-305.
[20]吴明隆.结构方程模型:AMOS实务进阶[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116-201.
[21]黄芳铭.结构方程模式:理论与应用[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5:4-26.
[22]高洁.交通运输网络连通性评价指标分析[J].交通运输工程与信息学报,2010(1):35-38.
(责任编辑:卢小文)
Impact of Road Networks on Household Travel Carbon Emissions in Guangzhou: A Case study of Jude,Shexue,Qifu and Xiaoxi Communities
Luo Yi,Cao Xiaoshu
Building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system is a key way to construct a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system,and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field of geographic research.At the same time,the study on household travel carbon emissions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low-carbon transportation system.Community is a unit of analysis on urban research to conduct the impact research among road network types and household travel carbon emissions.Four communities of different road network types in Guangzhou are selected for case study to examine the inner mechanism between road network types and travel carbon emissions in community with the help of AMOS 17.0.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greater the value of road network α is,the closer travel distance,the shorter travel time,and the lower travel carbon emissions are.The greater the value of road network β is,the shorter travel time,and the lower travel carbon emissions are.The greater the value of road network γ is,the furtherer travel distance,the longer travel time,and the higher travel carbon emissions are.
travel carbon emission; road network;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
U121
10.3969/j.issn.1674-7178.2016.05.012
罗依,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交通地理与土地利用。曹小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交通地理与土地利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全球化:过程、格局、动力与空间”(4113074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公共交通可达性对小汽车拥有及使用决策的影响研究”(41171139)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