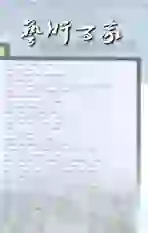加强中华美学精神与艺术实践的深度交融
2016-11-02金雅
金雅
摘要:当前中国艺术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美学精神的引领,尤其是民族美学精神的深度融入。中华美学精神的突出特质是崇尚大美。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不仅把艺术,也把整个宇宙和人生纳入创美体美的视域。中华艺术的审美价值观。不尚小艺术,而尚大艺术,重视艺术主体的情趣境格,重视艺术受众的化育涵泳,在抵御当代艺术实践欲望化、低俗化、市场化、形式化等偏畸上。具有深刻的针对性和重要的引领意义。文艺工作者应自觉加强理论修养,在艺术实践中传承宏扬践行创新民族审美精神与方法思维。
关键词: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精神;艺术实践;深度交融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中华美学和艺术源远流长,孕育了自己独特的理论精神和思想学说。但自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局面,引发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引进西学之潮。包括美学和艺术理论在内,一度大有唯西方是瞻的状貌。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引入,在中国美学与艺术的现代进程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直接作用。但是,以西方之美为美,以西方之艺为艺,悬搁中国美学与艺术生成发展的鲜活土壤和现实需求,不仅搁靴搔痒,甚或南辕北辙。美学与艺术,作为精神之果,与物质产品不同,具有内在的价值底蕴。一个民族的美学趣味和艺术情致,与这个民族的哲学品格、文化价值观密不可分,是与这个民族的意识形态相关联的。如果说,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经济、科技发展了,我们的物质生活富裕了,但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价值观,都不是自己的了,那就失去了我们民族立身之本、精神之根。当代审美和艺术实践中的种种乱象,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失本失根的苦果。
中国古典美学没有形成系统的逻辑形态的理论体系。这使得中国美学在进入现代进程后,明显缺失了融人世界美学之林,与西方美学平等对话的先机。因此,中国现代美学几乎从启幕,就离开了民族美学原有的形态轨迹,走上了与西方美学直接对接的道路。这种对接,在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上,确实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我们几乎直接引入或者说是搬用了西方美学的学科形态、概念术语、话语方式,甚至审美观念等,这使得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基本建构几乎在20世纪初不长的时间里就基本完成了,但这种揠苗助长式的速成,也留下了可怕的后果。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民族美学的全面失语,民族审美精神的某种遗落。
西方经典美学以探求美的逻辑本质为核心问题,推崇冷静、思辨、科学的认识论方法。鲍姆嘉敦、康德等西方现代美学学科的创始人,是在感性与理性分离、美与真善分离的基础上,确立美的独立地位和美学的学科体系的,他们努力探求和界定的是纯粹的美与美感。黑格尔从审美走向艺术,他把美学视为艺术哲学,主要也是以理性逻辑的方法来探讨艺术的科学美学规律。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观主要体现出以美论美、以艺论艺的科学论倾向,与整个西方现代文化的理性追求相吻合,在艺术实践中直接推动了粹情、唯美等倾向。中国古典美学无西方经典美学的显性逻辑形态和科学话语体系。其基本精神源自中国文化、哲学、艺术的多维交融,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宇宙纵横、物我交融、生命化成、人生仰俯的宏阔天地中来观照体味的。所以中华美学精神追求的是感性理性交汇、抽象具象兼具、形上形下兼容、美与真善相济的大美观大艺术观,它最终试图解决的不是美和艺术究竟是何的问题,而是美与艺术究竟何为的问胚,是把美和艺术作为精神成人的本体途径来建构的。这种美论和艺术论,不像西方现代美论和艺术论那样,对于学科自身的问题具有清晰的逻辑界定,但它的优点是突出了审美和艺术的价值向度与信仰向度,使得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存技向道,而非以技盖道,或以物非道。
如果说,西方经典美学自黑格尔始,形成了一定的艺术哲学的传统,那么我国美学与艺术,一直就有密切的关联。中国传统美学主要依靠艺术来阐释,意境、情趣、韵味、虚实、形神、道技等重要范畴,都是美学与艺术共通共用的,叉共同指向了宇宙人生这一宏大的天地。审美、艺术、人生的有机交融,使得中国美学和艺术精神崇尚大美,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以境界为高,讲美情,识美趣,崇美格,将生命的涵育与人性的升华,深深地契入了审美与艺术的鲜活实践中,不仅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质,也推动了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的理想维度和诗性向度。
1946年,宗白华先生写了《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引用了印度诗哲泰戈尔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他指出,中华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对宇宙旋律、生命节奏的创造性体验,并由形上启示形下,以艺术作为具象。因此,真正美的艺术应该是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的最高表征,也是自然规律、宇宙规律的最深写照;真正美的艺术除了“形制优美”的要求外,一定还有充盈于内的“高超趣味”。宗白华的观点阐发了文化、审美、艺术之间的内在关系,也强调了宇宙天地、个体生命、艺术创化之间的深度关联。
在中外艺术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都是时代风貌民族命运的映照,是人类心灵、人民情怀的抒写。那些只讲技巧、手法,缺乏精神、情怀的作品,或能流行一时,难以代代相承。那些流俗、媚俗,唯市场、唯刺激的作品,或能投机谋利,难成精品力作。习总书记在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就批评了当代文艺创作中“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乱编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同时,他也指出了当下文艺批评“庸俗吹捧、阿谀奉承”,“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等不良倾向。当代中国艺术实践的种种乱象,根子上还是因为我们的艺术活动缺失了内在的精神引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迷失了方向。
美学精神是艺术精神的重要引领,它对艺术理想的建构、艺术情怀的提升、艺术标准的确立。都具有关键的意义。中华美学精神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特质,其对艺术实践的深度融人,是当代艺术实践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力。
首先,中华美学精神以真善美贯通的美情观为基石。西方现代美学精神的确立以鲍姆嘉敦对知(理性认识)和情(感性认识)的逻辑区分、康德对情(区分于知意)的独立性质和中介作用的逻辑建构为基础。康德提出:“与认识相关的是知性,与欲求相关的是理性,与情感相关的是判断力”,审美判断“联系于主体和它的快感和不快感”。这种扬弃与概念和逻辑相联的认识。扬弃与实存和欲望相联的意志,切断自身以外一切关系的美感,使审美成为对对象的实际存有毫不关心的表象静观。这样的美,难免成为纯艺术的、形式的、直觉的。中华美学精神以真善为美之内质,追求真善美贯通的大美情怀,由此把审美与艺术与人生勾连在一起。中国古典美学注重美善的关联。孔子就倡导“尽善尽美”,以此为标准对音乐进行品鉴批评。中国现代美学在美善基础上强化了真的维度,以蕴真涵善立美为最高目标。朱光潜先生指出,在最高的意义上,“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宗白华则把艺术意境视为宇宙、生命、艺术三者的诗性交融。这种美论体现了宏阔的审美视野,体现了以艺术观照天地提升人生的情怀,既是执着热烈的,又是超越高逸的。对于艺术实践基本品格的确立具有关键和基础的意义。
其次,中华美学精神以涵容人生与艺术的范畴命题为血肉。实际上,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在范畴命题这个层面,很多是共通共用的。如情趣、意境、形神、道技、言意、虚实、巧拙等范畴,如出入说、无我化我说、看戏演戏说、大艺术说、美术人说、人生艺术化说等命题。但是,这些源自中华文化、哲学、审美、艺术土壤的范畴学说,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几为西方的典型、形式、语言、直觉等术语替代。少数几个尚在使用的,也大都是在理论的圈子里自娱自乐,并未能够真正与当代的艺术实践和艺术作品相结合,不能随着艺术实践和艺术作品的发展而推进,从而失去了理论应有的阐释能力和引领能力。中华美学的这些范畴命题,既重艺术自身的品鉴,又重天地、人生、艺术的关联,着意由艺术来观审和品鉴人生,是艺术实践美情至境之涵育提升的重要范导。
此外,中华美学精神以诗性超越的人文情怀为旨归。中华美学精神追求真善美的贯通,追求审美艺术人生的关联,不以小美、唯美、媚美、俗美为目标。中华美学精神既寄情于鲜活温暖的人间情怀,又神往于高远超逸的诗意情韵,在出入、有无、物我、虚实、彼岸此岸间,构筑了往还回复、自在自得的诗性张力。这种审美精神正是人间诗情的具体呈现,既非西方美学的纯粹观审,也非宗教意义的出世哲学,而是要求超越用与非用的功能限定,以无为精神来创构体味有为生活,从而追求大用大美的至美至情。它对艺术活动超越俗趣提升境界无疑有着重要的引领意义。
总之,中华美学精神与西方美学精神的重要区别。一为大美,一为纯美,论其与艺术的关系,则前者以美提领艺术,后者唯美之为艺术,前者以趣情境格等为要,后者重形言技等独立。两者虽各有特点。但在对艺术审美价值的深层范导上,在艺术活动自觉提升主体情趣境界,重视受众化育涵泳,抵御艺术实践中种种欲望化、低俗化、市场化、形式化等偏畸上,中华美学精神自有其不可忽略的深刻意义和重要作用。
当前中国艺术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优秀民族美学精神的价值引领和深度融人。如何切实推进这个目标的实现。首先就需要从文艺工作者自身做起。
文艺工作者需要加强美学理论修养。这个修养不仅指西方美学理论,更指中华民族自己的美学理论。我们无疑需要广泛吸纳与借鉴,但也需要理清自身的传统,深入发掘民族美学优秀的资源和自身的神髓。实际上,当前在实践一线的艺术家,不乏认为不需要什么理论来指导,或有意无意地唯西美为美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20世纪以来,我国美学和艺术理论界以介绍西方理论为主,还常常一知半解生吞活剥。西方美学理论是西方文化土壤和艺术实践的产物,简单套用西方理论,难免隔靴搔痒。由此,使得本土艺术家对理论更为排斥。这里还有一种对理论的错误期待,认为理论可以应对一切具体的实践问题。我认为,理论主要是解决问题的观念、方法、视野、智慧等,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20世纪初。梁启超就曾提出中国学术思想,迫切需要“除心奴”。“反依傍”。他既批评欧化派的沉醉西风,也批评保守派的夜郎自大,呼吁既“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亦“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他说,学一种思想,是要“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再根据具体需求加以创化运用,而不是亦步亦趋,全盘接纳,反致得不偿失。“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这就是不读书不可,尽信书亦不可,一切领域皆然。没有对中西美学理论的全面观照和深度把握,是难以实现民族美学精神和艺术实践的深度交融的。
文艺工作者需要加强对中华文化与民族哲学的了解学习。一个民族的美学与艺术精神,离不开这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土壤和哲学品格。而中华文化。更是一种文化、哲学、艺术、生命融为一体的大文化观、诗性哲学观、人生艺术观,是将对宇宙、自然、社会、生命、艺术等的考察交揉融汇。不懂得中华文化与中华哲学对宇宙、自然、社会、生命之规律和韵律的独特解读,就不能把握中华美学和中华艺术的要义。中华文化和中华哲学最重要的不是神性的维度,而是诗性的维度,是艺术化生命向度所凸显的物我、有无、虚实、出入的张力交融,既不漂浮,亦不沉沦,既是实存,又尚超拔。因此,中华美学和中华艺术的核心,都不是它们本身的问题,而是美之化人、艺之成人的终极问题,是以具象观照和反思创化去涵成一种独特而高逸的美情高趣至境的问题。只有探人中华文化和中华哲学之根,才能深刻理解中华美学和中华艺术的理想尺度,推动民族美学精神和艺术实践的深度交融。
文艺工作者需要在实践中积极践行民族美学精神,创化运用民族审美方法与思维。理论最终要到实践中去运用。文艺工作者只有自觉在实践中践行创化中华美学精神,民族美学精神和艺术实践的深度交融才能真正成为现实,产生积极实际的作用。深度交融,不是将理论生硬绑架到作品上。“文革”时期。观念口号先行,生产的只是“高大全”的假英雄,不可能产生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照搬西方的艺术观念和概念术语,做过一些先锋探索,也很少留下有生命力的精品。中华美学精神既有自己的内核特质,同时也在历史发展中传承创化。我们在实践中,既要秉承中华美学精神的神髓,也要具体地灵活地去化用,从而真正发挥中华美学精神引领艺术实践的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