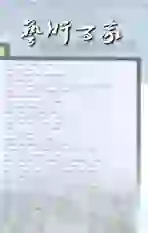浪漫诗风及其东方灵知主义
2016-11-02胡继华
胡继华
摘要:浪漫诗风(romantic for皿0fpoetry)确实不只是一种诗学形式,更是一种广义的艺术形式。一种深层的美学形式,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形式。在无限泛化的意叉上.浪漫诗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诗人和哲人共同发明的“绝对的文学”、“绝对的诗歌”、“绝对的艺术”。浪漫诗风的萌生、培壅、型构与流布。端赖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符号,建构一个象征世界。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浪漫化,其基础是魔幻观念论,其内涵是自然象征主叉赋予万物以神秘意义,其手段是语词炼金术,其目标是超验与内在合一。浪漫派建构的典范体裁是“小说”.这一文类具有深层的内省性,蕴含着一种穿透宇宙奥秘和将日用伦常神圣化的灵知。在全球化和现代性语境下,东方灵知主义的渗透和参与,共同塑造了浪漫主义文学、诗学和美学的精神品格。
关键词:艺术理论;美学形式;浪漫诗风;浪漫化;小说;东方灵知主义;精神品格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同近代启蒙关联在一起,又与古代和中古神秘主义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浪漫诗风或浪漫诗学形式(romantic form nf poetry)确实不只是一种诗学形式,更是一种广义的艺术形式,一种深层的美学形式,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形式。浪漫诗学理论自然也不局限于诗,而是同美学、艺术理论、哲学思考构成一种文化类型。本雅明将这种诗化的文化类型称为“反恩的媒介”,指出它具有指向超验之维和呈现内在之维的功能。“德国浪漫主义发明了文学”。如果让一吕克·南希和拉库一拉巴尔特所言不虚,那么我们也不妨说,它同样也发明了艺术,开启了对艺术的哲学沉思。德国浪漫主义诗学观,同时也是它的艺术观。浪漫诗风,乃是永无止境地朝着超验进化同时朝着内在渗透的“宇宙诗”。它是绝对的诗。又是绝对的艺术。它同西方神秘主义的关联相当明显,但它同东方灵知主义的关联却有待发掘。
一、何谓浪漫诗风?
对于“浪漫诗风”的系统表达,出自F.施莱格尔。其所撰写的《雅典娜神殿》不啻是浪漫派的《圣经》,其中的第116条断章则不妨称之为“浪漫主义诗学(美学)”的启示录,以及浪漫主义“艺术绝对论”的宪章。藉着这条断章,浪漫主义的精神领袖铺开了“艺术绝对性”的纲维。
主题词是“浪漫诗”,“浪漫”既是一种诗学精神,又是一种诗学体裁。第一句为总述——“浪漫诗乃是进化的宇宙诗”。“进化”,含“进化”和“进步”之意,“进化”乃是支配着现代思维的一种基本定势,而“进步”却是现代历史哲学的一种根本信念。“进化的诗”,意味着人类无限可完善。“进步的诗”.则是指诗学系统的发展以人文化成为最高境界。“宇宙”,含有“普遍”、“包罗万象”、“经天纬地”之意,表现出浪漫主义诗学的总汇意识。
第一,浪漫诗风具有整合功能。包罗万象、经天纬地的诗,乃是超越了一切对立、包容了一切差异的诗。它将分离的种类重新整合起来,让诗、哲学与修辞互相接触。它将韵文与散文、天才与批评、艺术诗与自然诗掺和融汇,赋予诗歌以生命与交流能力。在此,生命被诗化了,社会被诗化了,浪漫主义的机智被诗化了,艺术形式充满了创造物,并且获得了幽默品格。浪漫诗经天纬地,上达包括一切体系的最为广大的艺术体系,下达造物的叹息、人类的亲吻与孩童的歌谣等没有艺术形式的东西。
第二,浪漫诗风渗透于艺术类型之中,构成了艺术的基本精神。浪漫诗消逝在再现之中,诗人意在刻画个性,又无法表达个体精神,因而有写小说的渴望。这里的表述相当晦涩,自相矛盾,但是在表达个性之困境中,小说体裁脱颖而出了。浪漫诗近乎史诗,成为世界、时代的画卷。此点非常重要,浪漫诗近乎史诗,而非近乎抒情诗,故而典范的体裁是叙述主导的小说,其功能专在描写现实人生。浪漫诗充满诗意。无穷反射,再现之物和被再现之物之间的差异消融了,并超然于利害关系之上,无穷的镜像由此增殖,彼此反射。浪漫诗由内而外且由外而内地建构和谐整体,开拓了古典主义无限发展的前景。
第三,浪漫诗风具有一种哲学沉思品格。浪漫诗之于艺术体系,恰如机智之于哲学,社会、交往、友谊、爱情之于生活。在此,浪漫主义的系统诉求已经相当明确,文学不仅是一个同人类文化各个方面紧密相关的系统,更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系统。其他形式的诗歌已经发展成熟,浪漫诗可以通过解剖而传承。
第四,浪漫诗风永无止境,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而指向了人类无限可完善性。浪漫诗本质上在生成之中,永远不达至境。生成的诗歌抗拒理论的阐发.而期待一种预言的批评。浪漫诗发展,因而无限。因无限而自由——“不容忍外在任何法则”。无止境而趋于完善,不仅是浪漫诗风的品格,不仅是浪漫艺术的品格,不仅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品格,而且是人类生命无限可完善而趋向于神性的品格。…宇宙的不完善性(incomplete wndd)将人类欲望成为创世之神的倾向合法化了,就好像是说:这种永无止境也就是对决定论的消解。”““在《生命哲学》中,F.施莱格尔将世界的不完善性视为人类自由的客观对应物:“人类无拘无束,但宇宙自然、感性世界、物质造化,统统都是未完成之物,完全彻底的未竟之业。”在《哲学讲演录(1804-1806)》中,我们又读到:“惟有将在生成之中看宇宙,认为它在通过一种上行的发展而臻于完满,自由才是可能的。”宇宙未完成,这一想法同浪漫主义对于有机生命隐喻的嗜好紧密相连。有机生命这个隐喻,喻说着生命的绝对主权。
总而言之,浪漫诗风的绝对性,就是艺术的绝对性,那是一种与生命合一的绝对主权。浪漫体裁超越一切体裁的框范,“所有的诗,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或应该是浪漫诗。”在这个无限泛化的意义上,浪漫诗就是绝对的文学,绝对的诗歌,绝对的艺术。
二、“世界必须浪漫化”
浪漫诗风的萌生、培壅、型构与流布,端赖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符号,建构一个象征世界。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浪漫化,或者让世界向象征体系生成。在浪漫主义诗学和文化语境中,象征化就是一场通过魔幻观念论的运作而把人文世界以及神圣世界从自然图景之中超拔出来的救赎行为。象征化的生命体验、象征化的作品和象征化的形式,就是卡西尔“象征形式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rnen)的研究对象。因为象征形式及其所建构的象征宇宙以蕴藉的方式呈现了“灵魂的历程”(seelische ProzesseH)。以诗学的方式体现了人类使用语言的“象征意识”(sym-bolbewusstsein),以隐喻方式再现了将情感、想象、信仰融为一炉的神话体系(Mythologie)。早期浪漫派对“世界浪漫化”的基础、内涵、手段和目标首次作出了系统的描述。
象征化的基础是“魔幻观念论”(Thaumaturischeldeelismus)。这一学说缘起于18世纪的医学,其源可溯至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神秘巫术,其要义在于追求“无限微量的疗效”。诺瓦利斯将这一神秘的巫术技法转换到象征主义诗学之中,赋予诗人和艺术家以语词炼金术而追寻无限完美的使命:
追求灵魂不朽的艺术家实施更崇高的医术——追求无限微量的疗效——他永远以同时地将两个对立的因素视为同一。让两个对立因素和谐共在,依据一个原则将他们融贯一体。……无限量而不可测度的外在刺激已然恒在,其大部分已经在艺术家的掌控之中。然而,反抗外在的内在刺激力量是何等微弱!故此.追求灵魂不朽的艺术家忧患之所在,乃是渐渐增强内在刺激的力量。吾人不敢断言,艺术家有何等权力,因为诗人在此已经作出了卓越的预言.他宣称惟有诗神才能赋予灵魂不朽。一道曙光而夸已照彻了博学之才。(此乃)我的魔幻观念论。
在浪漫诗人和哲人手上,“魔幻观念论”乃是一个理性的神话,一种感性化的宗教。他们敬畏一种迷暗而且邪恶的自然力量,在完美之中发现不完美,在圆满之中感受不圆满,从而在残缺与紊乱之中奋力寻求圆满与有序。浪漫主义者崇尚观念,追求属灵性乃是它们的本能。同时,浪漫主义者迷恋魔幻,而神话升华到乌托邦的境界。魔幻观念论的重要原则之一,乃是拒绝随意事件,拒绝自然世界的偶然激励,拒绝纯粹机缘之中的“纯粹性”。“即便是机缘,亦非不可解释,它自有规律,自成章法。”拒绝偶然、随机、机缘,浪漫主义势必将整个世界理解为必然,而他们所谓的必然乃是以语言符号建构出来的自然象征主义体系。其中一切不完美都指向完美,一切不圆满都趋向圆满,一切紊乱都蕴含秩序,一切残像碎片都呈现了意义,一切邪恶势力都有可能转换为救赎恩典。而这些指向、趋势、蕴含、呈现和转换,既非自然也非文化所能完成,而必须仰赖神秘、灵知以及魔术。在诺瓦利斯看来,魔幻观念论的秘密就在于:“我们到处寻找绝对之物(das Unbedingte),却始终只找到常物(Dinge)。”然而,俗世人间那些有限的常物,却是神圣领域那一无限绝对之物的踪迹。自然为媒,常物为象,诱惑、中介、牵引人心去趋近那个无限的绝对之物。自然,因为指向神圣和传递灵性,而成为诗的“灵媒”。这就是浪漫诗学之中堪称纲维的自然象征主义。关于浪漫派艺术理论的自然象征主义,布鲁门伯格特别强调指出:
浪漫派不仅模糊了文学体裁的特殊界限.而且也模糊了为了清晰性和象征化或者为无限性灵见而设立的一般界限。他们也消融了为了一种普遍的造型性而做出的意指行为(Bedeutung)和意指对象(Bedeu—tetem)之间的区分。让它们彼此侵入、互相渗透。换一个概念来说,那就是受造的自然(natura naturata)将成为创生的自然(naturanaturans)之纯粹前景。在诺瓦利斯笔下频繁出现的这个神秘名称,却千变万化,不可琢磨。
浪漫化的内涵是以象征的自然主义将世界神秘化。“象征即神秘化。”在现代性与世俗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世界不再迷人”(disenchantment of theworld)。通过象征而再度将世界神秘化,乃是浪漫主义者为自己确立的一项志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浪漫主义者呼吁“世界必须浪漫化”,通过浪漫化而寻觅“本真的意义”。这个本真的意义,不是格物而至的知识,而是自内唤醒的灵知。所以,诺瓦利斯的“塞斯学徒”撩开伊西斯女神的面纱,所看到的不是那个沧桑的世界和愁苦的人群,而是他“自我的影像”。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对镜鉴像,让浪漫主义者忧郁成疾,自恋若狂。他们的渴望恰恰在于,通过一种“质”的强化,将潜存于内在的灵知以“指数级”推展与升华,将“低级的自我”与一种更完善、更崇高、更超越的自我同一化。诺瓦利斯写道:“给卑微物一种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物的庄重,给有限物一种无限的表象.我就将它们浪漫化了。”
浪漫化的手段是语词炼金术。对于语言之于人类解放、之于宇宙建构的巨大潜能的自觉.始于德国浪漫主义。诺瓦利斯断言:“用声音和笔画命名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抽象”,“语法乃是灵的王国的动力学”,“一个祈使语可以调动千军万马;‘自由一词可以驱策整个民族”。藉着语词炼金术,诗人便成为不朽艺术家之中最为不朽的艺术家。在诗人建构的象征体系之中,日用伦常皆为传奇与神话,爱情与忠贞把生命化为永恒的诗章。甚至战争也终归是诗的作用力之表现,两军追随一面看不见的旌旗而为了诗的事业而拼死搏杀。最为令人仰慕的是,在诗的象征体系之中,混沌的眼穿透秩序的网幕闪闪发光,启示一个新天新地,“黄金时代”将在这个新天新地再度铺展。在《施特恩巴尔德的游历》中,路德维希·蒂克假托书中人物弗洛雷斯坦赞美普罗旺斯诗人鲁代尔,追忆“黄金时代”的诗性境界:“诗和甜蜜的语言渴望把世界,把人结合在一起.骑士精神把各国结合在一起,圣战把东方同欧罗巴结合在一起。”1796年,浪漫主义者瓦肯罗德在将语词炼金术明确地界定在自然与艺术两个领域,将自然象征主义提升为浪漫的语言学纲领。浪漫的象征世界,乃是一团充满神秘欲望和神奇生命的纯粹混沌。于是。浪漫主义者找到了两种神奇的语言,来描摹他们内心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世界。一种语言是自然.便有了自然的神秘主义。一种语言是艺术,便有了语言象征主义。瓦肯罗德写道:“艺术与自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但它却同样通过隐晦而神秘的方式作用于人之心灵,具有神奇的力量。……其中一种语言,至高无上者自己在永恒地述说着它,它是生生不息、无穷无尽的自然,它牵引着我们穿过大气中广博的空间直接达到神性。艺术则通过将五彩的土和润泽的水巧妙地融合起来......向我们开启人类心中的宝藏,将我们的目光引向我们的内在,向我们展示那些无形的东西,即人的形体中所蕴含的所有那些高贵、崇高和神性的东西。”自然与艺术,殊途同归,隐含着未成文和未阐释的神圣启示,浪漫主义诗学,就是使未成文的启示成文,阐释那些未阐释隐微,不仅让宗教、而且让科学同时出现在真理和自然的光辉之中。
浪漫化的目标是内在与超验合一的境界,上溯空性而下及万有。诺瓦利斯认为,浪漫化的象征通过想象力的释放而指向了未来世界。未来世界可能被设置在三个维度上:或者被置于高处(超验),或者被置于深处(内在),或者“在灵魂的转型之中置向我们”(超验而又内在)。梦想穿越宇宙,梦想却在心中。“我们不了解我们精神的深度。这条神秘的路通向内心。”但是,在浪漫主义者那里,深入内在的路,也就是上达超验的路。深人与上达之合一,就是浪漫诗的真谛之所在,就是浪漫诗哲的无限渴望之境界。诗兴近乎神秘主义,而诗兴所至的鹄的,乃是那一超验而又内在的事体:“奇特”而又“内在”,“未知”而3L"神秘”,隐秘而需要敞开,必然与偶然合一。所以,超验的诗既是哲学又是诗,超验的诗人就是超验的人。
关于超验诗,F.施莱格尔在《雅典娜神殿》第238条断章中做出了一个经典的界定:“有一种诗,它的全部内容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所以。按照有哲学韵味的艺术语言的相似性,它似乎必须叫做超验诗。它作为讽刺,以理想和现实的截然不同而开始,作为哀歌飘浮在中间。作为田园诗以理想和现实的绝对同一而结束。超验哲学是批判哲学,在描述作品的同时也描述作者,在超验思想体系之中同时也包含对超验思维本身的刻画。现代作家的作品中不乏超验素材和准备阶段的练习,早在品达的作品、希腊抒情诗断章和古人的哀歌中,就有艺术反思和美的自我反映。在现代人中,这种反思和反映则是存在于歌德的作品里面。超验哲学若无上述特点,超验诗也就没有必要把现代作家中的超验素材和预演同艺术反思、同美的自我反映结合起来,把它们结合成创作能力的诗论,在它的每一个表现中同时也表现自己。无论何处都是诗,同时又是诗的诗。”
“超验”一语,直接源自康德,因而取了这个术语的原始意义。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用“超验性”来指称一种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的旨趣,不是达至一种对客观对象的纯粹认识,而是锋芒直指认知客观对象的方式,据此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融为一体,难解难分。费希特也使用“超验”一语,强调主客体关系之中主体的反思行为。然而.F.施莱格尔的“超验”概念废黜了诗歌与哲学的关系,大有平息“诗一哲亘古之争”的抱负。他的具体做法分为两步:第一,凸显诗一哲互动关系之中“诗的反思”;换言之,在他看来,反思不独是哲学的使命,也是诗自我发明的媒介;第二,将“反思”改造为一种“诗性反思”,从而塑造了诗学的哲学品格;换言之,超验哲学是批判哲学,因而超验诗学也是批判诗学,既描述作品又描述作者,既包含被描述者又包括被描述者,既反思超验思想体系又反思超验思维。因此不妨说,“超验诗”乃是双重反思,它既是反思的思想也是反思的诗学,反思成为浪漫主义和观念论的绝对媒介。这种双重反思呼应着“进化的宇宙诗”的节奏与命运。在一系列无休无止的镜像之中,“超验诗”展开“诗学反思”,因此无论何处都是诗,同时又是“诗的诗”。
“超验诗”之全部内容,乃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论点直接源于席勒。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是他为论衡古今诗文而设立的圭臬。理想与现实融为一体的诗文,席勒称之为“素朴诗文”;理想与现实分裂为二的诗文,他又称之为“感伤诗文”。诚如中国史家屡言诗分唐宋,席勒也将诗辨古今。唐宋、古今均与时代无关,所显示的是诗文内质,所道说的是诗文流别。所称谓的是诗文体制。是故,席勒论诗谈文不外两宗:古之诗文真朴出乎自然,是为理想与现实融合无间;今之诗文刻露见其心思,是为理想与现实的乖谬剥离;古之诗文尚其德,固有素朴韵味;今之诗文称其巧,必有伤感悲情。看得出来,F.施莱格尔描摹诗文流别,就是秉持席勒以古今为诗文体制的断制:讽刺诗文始于理想与现实的乖离,哀歌飘浮于理想与现实二极之间,而田园诗以理想与现实的完美交融而臻于至境。这个完美境界,具体描述在《雅典娜神殿》第451条断章的“宇宙性”构想之中:“宇宙性(Universality,又译“总汇性”)。就是所有形式和所有素材交替得以满足。只有藉着诗与哲学的结合,宇宙性才能得到和谐。孤立的诗和孤立的哲学之作品。无论怎样包罗万象,怎样完美无缺,似乎也缺少最终的综合。距离和谐的目标虽然只差一步之遥,这些作品却远非完美,且停滞不前。宇宙精神的生命。乃是一系列绵延不断的内在革命。所有个体,即最本质最永恒的个体就生活在其中。宇宙精神是真正的多神论。它胸怀整座奥林波斯山的全部神祗。”
这条断章的主题词是“宇宙诗”及其多神论精神。呼应116条断章,且深化了浪漫运动的“宪章”断制,重申“宇宙诗”的经天纬地与包罗万象,且将“宇宙精神”同“人类无限可完善性”直接关联起来.凸显了浪漫主义的多神教审美取向。
在“宇宙诗”层面上,“超验诗”就是形而上的“原诗”。“原诗”,是笔者斗胆从清代学者叶燮(1627—1703)那里借来的概念,意指诗文的本源之道。凡诗文之道,“当内求之察识之心,而专证之自然之理”(叶燮《已畦文集自序》),说的就是这种超验的诗学精神,及其宇宙意识。不仅如此,叶燮关于诗文的定义——“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同浪漫主义精神遥远契合。浪漫主义者心仪的“超验诗”,自成一种可以祈望却不可达至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就是“诗之至处”,就是“理”“事”“情”和“才”“胆”“识“力”的融合无问,复杂互动,心智游戏而臻于至境。于“诗之至处”,便没有文类之分,没有古今之辩,没有高雅低俗之别,没有主观客观的诗人之判。如此等等,尚在其次,“诗之至处”乃是一种闳阔而又幽深、高远而叉精微的境界:“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原诗》内篇)所以,“超验诗”是为“诗之至处”,以“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为鹄的。论诗衡文一贯鄙夷虚灵而独钟词章的钱钟书,也对“诗之至处”赞誉有加。他引用瓦雷里为法国神秘主义者白瑞蒙(Henri Bremond)《纯诗》所撰序言,断言“贵文外有独绝之旨,诗中蕴难传之妙”。神秘主义缘光烛照下的象征主义诗人,自认“祈祷”与“作诗”本为一途,活像中国古代诗论家言“作诗如参禅”,无不推重“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旨”。在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谈诗论文的话语之中,我们还隐约可以听见这点独绝之旨与难传之妙。在古典主义赫赫威权之下,理性唯清楚明白是求,而“诗之至处”那点不落言筌之宗就惨遭放逐而被遗忘了:“以为即一言半语,偶中肯絮,均由合,非出真知,须至浪漫主义大行.而诗之底蕴,始渐明于世。”
三、浪漫诗风的典范体裁
施莱格尔《雅典娜神殿》第116条断章结尾说:“一切诗……都是浪漫诗。”但“浪漫”一词同“小说”相连,赋予了这个陈述以深邃的歧义性。浪漫诗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体裁?
在一条草草写就的杂记中.小施莱格尔将诗之至境描述为“奇幻”(Fantasfisch)、“伤感”Sentimentisch)与摹仿(Mimisch)的混融。在他看来,诗歌铺展了宇宙人生的盛宴,将历史之真理与伟大同奇观幻象之自由游戏结合起来,其中却渗透着爱的忧伤。施莱格尔言下之意,便是将“小说”作为负载浪漫诗境的体裁媒介。而且他还反复暗示,希腊诗因浪漫而伟大,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因浪漫而硕果犹存。“小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为躲避枯燥的书本知识,活生生的智慧逃进了这个自由的形式里来了。”(《批评断章集》,26)小说不仅是文学媒介;祖述苏格拉底,施莱格尔将小说视为超越一切体裁局限的最高体裁,以及无拘无束独抒性灵的自由形式。“讽刺渗透了整个罗马诗文,定下了罗马诗文的基调,小说也渗透了整个现代诗。”(《雅典娜神殿》,146)这些表述无不说明,施莱格尔为浪漫主义诗学体裁所指示的方向,就是小说。在《谈诗》中,施莱格尔一篇《论小说的信》中写道:“一部小说,就是一本浪漫的书”。随后他特别强调。戏剧供人看而小说供人读,但小说要成为浪漫的书,还必须“通过整个结构.通过理念的纽带.通过一个精神的终点,与一个更高的统一体相连”。一言以蔽之,小说乃是神性式微、宇宙秩序颠转之后上帝遗落在世俗世界的史诗,小说与史诗体裁的联系更为密切。施莱格尔希望打破惯常的体裁分类,超越传统的体裁轨范,还原小说体裁以原本的品格,使这个体裁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
本雅明慧眼独到,早就看到“小说”乃是最为适合于浪漫主义反思及其文学绝对性的体裁。而最高级的反思媒介与象征形式便是小说,它无拘无束,不由正道,且独抒性灵。在论述歌德的《迈斯特学习时代》时,施莱格尔指出,小说的凝练形式和反思媒介,为观察和自我沉湎的精神提供了最佳途径,故而小说乃是最富有精神性的诗性形式。小说集浪漫诗之大成,因此成为浪漫诗文的负载者,文学绝对之基本象征物。浪漫之诗,也就是小说之诗。真正的小说,乃是不可超越的诗学体裁,位于一切体裁之外,成为一种文学理念,笼罩着古今伟大的经典。施莱格尔用儿童摘星月的比喻,来描述“小说”的超然境界:“习惯与信仰、偶然的经验和率性的要求相结合,诗学体裁概念于焉生成;按照这种体裁概念来评价《迈斯特》,它就仿佛是一个孩子要摘取月亮与星辰,把它们装进小盒子里......”
《论小说的信》关于浪漫诗体裁的逻辑可以归纳如下:(1)一本浪漫的书是一部小说,一部供人阅读的作品,一个有待接受主体参与的文本。(2)戏剧、史诗、抒情,一切一切的诗,终归必须浪漫化——向小说生成(romanticization),莎士比亚的戏剧,乃是小说的真正基础。(3)小说与史诗共血脉,与叙事、歌唱等形式混融而成。(4)小说尚奇幻,建奇观.无拘无束,独抒性灵,因而它是正在生成的浪漫诗风,一种不可缺少的诗性元素,而不仅是一种固定的体裁。(5)浪漫诗目光向后,对过去的东西隐隐顾盼,从莎士比亚身上萃取浪漫想象的精灵,而且认祖更远,在但丁、塞万提斯以致在骑士时代的爱情与童话之中去寻觅自身的起源。
“小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施莱格尔如此明嘹的断制,将小说文类确立为浪漫主义的经典,从而开启了德国思想小说、精神小说自我反思的传统。小说躲开了枯燥、机械、冷漠的知识。而以象征形式表现了自由,以及活生生的生命智慧。德国浪漫主义小说文类的传人托马斯·曼在20世纪将“心理学”与“神话”融合在一起,将浪漫诗风贯彻在自己的创作中,将叙事文学的超验性推向极致。不过,施莱格尔早就有言在先,浪漫时代的诗哲传承着荷马史诗精神和品达抒情灵韵,从古代神话中发掘出象征形式,在总体上把最美的东西融为一体,创造出“总体艺术作品”。一切都昭昭灵灵,而非苍苍莽莽,浪漫精神高瞻远瞩地展开对自己的想象。浪漫小说具有一种深沉的内省品格,且同整个中世纪基督教精神有一种剪不断的关联。所以,卢卡奇说,“小说是上帝所遗弃的世界的史诗”,“小说是内心自身价值的冒险活动形式”。外有世界,内有灵知.浪漫小说乃是无限追求的象征形式。然而,施莱格尔怀疑:“渴望追求无限的人,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所求何物。”也许,令浪漫主义者无比渴慕,而且万分憔悴,甚至忧郁成疾的对象,就是那个笼罩万物的虚无。
四、浪漫诗体裁建构之中的东方灵知原素
浪漫诗风并非一种体裁,而是异体熔材,杂语化韵,笼众多文类为一体,总汇古今于一脉。说到底.浪漫诗风是一种总汇精神,一种诗性原质,一种天人合一、神人相悦、灵肉互蕴且协调感性、理智与神性的精神。时而君临一切,时而隐身不见,却绝对不可或缺,浪漫诗风就是一种诗化的灵知,灵知的诗化。我们与其重复说“一部小说就是一部浪漫的书”,不如说一部小说乃是一部灵知的启示录。“灵知启示录”乃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关于“小说的理论”,甚至是“关于理论的理论”。在这层意义上,德意志所特有的“教化传奇”及其思辨性和神秘性传统便可以溯源至灵知主义。作为灵知的启示录,德意志小说难免染色神秘性。从歌德的《维特》到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这种神秘性对于读者总是一份灵知的礼物,一道崇高的灵符,以及一种致命的诱惑。1802年,小施莱格尔在一则笔记残篇之中明确地提出了小说与机智、史诗、神秘剧和历史剧的汇通,及其同神话性的接近性:“小说、机智和史诗式的诗,只不过是一种神话诗的原素和前奏,就像悲剧、喜剧、音乐剧之于历史剧。抒情诗也同样如此,它们应该十分接近神话诗。”然而,这种作为灵知原质的神话诗,虽然同神话审美主义的希腊传统有血脉相连的传承关系。但可能更多地来源于东方,来自印度与中国。篇幅所限,更兼实证稀少,关于浪漫主义文体建构的东方原素的探讨只能是一个初步的猜想,更需另设框架予以专门处理。
在探讨浪漫诗风的生成及其文体建构的时候,我们必须选取一个较为宏大的全球视角。因为,以一种历史长时段的眼光看,浪漫主义文化运动和诗学推进乃是发生在18世纪“中学西传”造就的“中国之欧洲”的景观下。纵观浪漫主义运动的构型因素,我们不难发现,参与这个时代建构并合力塑造德意志民族灵魂及近代欧洲精神品格的,有希腊模式、埃及模式、印度模式和中国模式。而印度模式和中国模式,对浪漫主义文化的伦理观和审美观的形成影响最为有力,也最为隐蔽。
1800年,小施莱格尔就为浪漫主义指点家园:“浪漫主义登峰造极的表现必须到东方去寻找”。不过,闪烁在他心中的东方,乃是《沙恭达罗》《阿维斯陀经》和《奥义书》的诞生地——印度。1803年,他又酝酿着对印度文化的巨大激情:“一切,绝对的一切,都有印度的源头。”在他看来,“好的东方”永远属于像昔日印度那样遥远的古代,而“坏的东方”则四处游荡在当时的亚洲。秉持“语言多元论”的断制,他相信印度语和闪米特语之间有某种深刻的同源关系,甚至还没有底线地假设埃及文化乃是印度殖民化的产物。他以语言为中心梳理世界文明的脉络,将语言区分为两类:一是高贵的有屈折变化的语言,另一类是不完美的没有曲折变化的语言,前者具有属灵性的本源,而后者却属于动物性。他坚信,只有应用以印度语言为基础的曲折变化,才有可能发展出清晰敏锐的智力,以及高等的普适的思想。在1815年首次出版、复于1822年修订再版的《古今文学史》序言中,施莱格尔表示,在他全身心地献身于古典文化的过程中,为了满足个人的求知欲而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东方语言,特别是在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印度语言。《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1808年)就是浪漫主义者施莱格尔在世界文明总体图谱上添加的浓情重彩。古代印度的建筑、墓葬、史诗、神话体系以及“灵魂轮回学说”。对于浪漫主义者都散发出上溯空性而下及万有的灵知气息。在《古今文学史》中,施莱格尔写道:
在上古时代,各种秘传教派在埃及遍地皆是,蔚然成风的许多思想与观念显然有别于流俗的信仰,没有那个国度比这里更为迷信。有时却好像是在最深厚的黑暗之中闪烁一道璀璨之光,可他确实是千差万别的不同意见。所以,毕达哥拉斯可能在埃及学得了一种当时当地并非普遍流行的学说,而这种学说之源头乃在印度。
这种学说就是“灵魂轮回学说”(doctnne of metapsychosis),他构成了毕达哥拉斯派的基本教义。而且构成了柏拉图的“灵魂学说”(psychology)原质。将这种学说称之为“最深厚黑暗之中闪烁的一道璀璨之光”,施莱格尔便认同了这种来自东方的灵知。以灵知为视角,他重新阐发古希腊文化精神,以印度模式为主导完成了一次对希腊模式和埃及模式的综合。施莱格尔用非常地道的灵知教义神话的语言重构了印度的“灵魂轮回学说”:
印度的灵魂轮回学说基于一种万物源自神并寓于神的思想;它假设人生在世悲苦而残缺,乃是罪孽的结果;所有的生灵,特别是人类,总是漫游在各种不同的形体和形式之中;他们不是罪孽俱增而堕落到造物的更低阶梯上,就是通过对他们全部本质的内在纯化而渐渐臻于完美,归向他们由之而来的神圣原乡。
施莱格尔紧接着断言,这种学说在本质上类似于柏拉图的哲学,这就将柏拉图主义灵知化了。不仅如此,东方智慧与欧洲哲学体系之间的这种类似性,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正是浪漫主义者描绘世界文明巨大网谱的起点。只有在这种振叶寻根的意义上,我们才能透彻理解《古今文学史》第一讲中的论断:“人被赋予了一个灵魂,而精神从灵魂深处、在灵魂之镜的返照下,把自己塑造成生命的创造性的语言。”也只有以灵知为视角,我们才能在究竟意义上理解浪漫主义小说的抒情性以及“感伤”的内涵。在《诗谭》之“论小说的信”一节里,施莱格尔写道:
说到头采。这种所谓的感伤到底是什么?感伤就是触动我们心灵的东西,就是情感君临一切的天地,而且不是一种感性的,而是精神性的情感.所有这些冲动的源泉和魂灵就是爱。在浪漫诗里,爱的精神必须四处飘游,无处看得到,又无处见不到。……现代人的诗作里,风流韵事从警句到悲剧无处不在……而风流韵事正是现代人的诗里最不足道的,或者比如说,这些风流韵事连精神的外在文字都算不上,在不同的情境里有时什么都不是,或者仅是某种很不可爱并没有爱的东西。不。用音乐的旋律感动我们的,是那个神圣的灵气。它是不能用强力去把握、机械地去理解的,但是人们可以友善地用尘世的美把它引诱出来,并把它裹在这种美当中。诗的咒语也能灌透灵气。也能被灵气赋以活力。然而,在一首诗里。这种灵气若不是无处不见或随时可见,那么这首诗里就肯定没有灵气。它乃是一种无限的本质。故而它的兴趣绝不仅仅粘着于单个的人、单个的事件、单个的情境及个人的爱好;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不管这些单个的人或事也许套仅仅缠绕着他的灵魂。但这一切不过是指向那个更高的、无限的及象形的东西。这就是说,有一个神圣充实的生命,她是惟一的、永恒的爱及创造着万物的自然所具有的。她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就是那个更高的、无限的及象形的东西。
这段著名论说的主题词是“灵气”。于是,一种源自印度“灵气说”.且糅合了基督教“圣灵学说”的灵知主义渗透于浪漫主义文体建构之中。灵知教义神话的二元性在此朗现无遗:感性与精神,风流韵事与神圣灵气,单个的人事情境与惟一永恒的爱及其更高的、无限的像形之物,二者形若冰炭,判若云泥。浪漫主义小说书写这种灵知,呈现那个“神圣充实的生命”,因此它像谢林的哲学、诺瓦利斯的《夜颂》和荷尔德林的《哀歌》一样,也是德意志灵魂的启示录,以及神圣生命的基本象征。小说,便是诗化的灵魂启示录,以及诗化的神圣象征物。
在《卢琴德》之“闲游牧歌”中,施莱格尔假托男性学徒之口把神圣生命的永恒本体寄寓于植物:“奇妙之树”自由萌发,自由生长,不要修剪其枝叶,要让它枝繁叶茂。植物成为闲游者理想的生命境界,闲游者亦像东方哲人一样沉浸在对永恒本体的默观冥证中,醉与梦两境相入,出神而又彻悟,忘我而又坚执,充实而叉空灵。在施莱格尔看来.唯有东方人才享受闲游之乐.而恰恰是印度人发展出如此隐微、如此甜美的思想。在这个茫然的男性学徒而言,闲游应该成为艺术、科学甚至成为宗教,而植物在所有造物之中,乃是最为神圣的生命,最有德性的生命,最是美丽的生命。普罗米修斯式的劳作,西西弗斯式的苦役,一切宗教殉道者的禁欲苦行,在男性学徒(施莱格尔)看来,都不够崇高,不够完美,遑论神圣!清净无为,道法自然,绝圣去智,施莱格尔通过男性学徒演绎出来的东方灵知,与其说是印度的智慧,不如说是中国的道家的智慧。
谈到中国与欧洲的文化关系,是史学的一场不解纠结。在宏大的全球史视角下,完全毋庸讳言,中国文化在16世纪进入西方,塑造了现代欧洲的精神品格。而中国文化涵濡欧洲的进程,同文艺复兴之后人类历史的进步与神圣的世俗化宏大叙事大体一致。通过传教士、旅行家和商人的转述而展现在欧洲人视野里的中国,在欧洲人眼里便呈现为一个“他者”的国度,一个异教的世界,一个散发着灵知气息而孕育着无限生机的世界。欧洲人对遥远东方这个灵知国度的想象,采取了神话体系建构的方式:先是因仰慕而将中国神圣化,后是因排斥而将中国妖魔化。将中国神圣化,欧洲人建构了中国之欧洲。将中国妖魔化,欧洲人便展开了“欧洲化中国”的画卷。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涵濡之叙事,经历着由崇高到滑稽的逆转。艾田蒲描述说,从1773年到1842年,中国在欧洲的形象一落千丈,“中国之欧洲”走向终结,“欧洲化之中国”随之开始。
德国浪漫主义潮流涌动的时代,恰逢“中国风”止歇.中国想象转向否定,以及神话中的东方灵知王国沉沦的时代。哈曼、赫尔德、康德、谢林和黑格尔。这些德国思想家都加人到了贬斥中国的阵容,多多少少都参与了对中国的妖魔化。带着欧洲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有色眼镜。这些思想家在想象之中扭曲了中国形象,把中国看做是一个全然的他者——一个在基督教文化圈之外的异教世界。在这种否定建构中国形象的潮流中,谢林略显例外。作为浪漫派与观念论体系源始纲领的制订者之一,谢林念兹在兹的仍然是那套充满了灵知气息的“新神话”。以新神话为视角,谢林断言中国没有神话,而转向了人类生活完全不同的“外在化与世俗化”方面。“唯有中国确是一个伟大的、独特的例外”,“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肃思索”,这是谢林以神话为视角论衡中国文化所得出的结论。与黑格尔完全将中国排斥在世界历史之外的极端傲慢不同,也和赫尔德完全将中国描述为一个野蛮愚昧的异教世界不一样,谢林从中国语言文字人手,发现了中国文化载体的形上意蕴和审美品格:“中国语言是世界上最洗炼的语言”;“中国语言中保留的.不是源始语言的质料,而是它的法则”;“中国语言中似乎还富有天的全部力量,即原初的那种统辖一切、绝对地支配、主宰万物的权力”。谢林感到奇怪。中国文化的灵知似乎解决了基督教的源始神话和教义都解决不了的谜团:精神性的天之世界为何转化为尘世的帝国?《易经》中“强大聪灵的龙”给谢林以巨大的启示。“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被早期德国汉学家以及浪漫主义哲学家臆想地解释为:“它哀叹自己的骄傲,因为骄傲使它失去方向.它本想冲入天空,却坠人大地的怀抱。”从这个灵动而强大的形象上,谢林想象到物质世界的全部力量,一切元素的强大精神。“龙”便成为中国政治哲学和审美精神的基本象征。就政治哲学而言,龙是国家的神圣象征,是国家权力和庄严的象征,类似于《圣经》之中和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就审美精神而言,龙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可见和不可见的统一,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统一。所以,中国美学讲究以一御多,杂而不越,形神不二,多样归一。这种审美精神不只是形而上层面的默观冥证,不只是在默观冥证中沉湎于迷暗的内在,而是端庄流丽地呈现在伦常日用、器物构型、政治制度等生活世界的各个层面上。
这种美学精神最为直观的呈现,就是施莱格尔在《雅典娜断章》第389则之中所提到的“中国式的花园房屋”——中国古代园林艺术。“混乱被组织得有条不紊”,“艺术混乱曾有过高度稳定性”,“比哥特式教堂的寿命还长”。用中国古典美学术语言之,这就是“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徐一篇,使杂而不越”(刘勰《文心雕龙·附会篇》)。“杂而不越”,语出《系辞(下)》:“其称名也,杂而不越。”韩康伯注:“备物极变,故其名杂也。各得其序,不相逾越。”这一美学原则当然不只是作文的章法,而是贯穿于辞章与义理之中体现出形上价值瞩望的生命美学原则,称之为灵知的智慧亦不过分。这么一种美学原则,在德国浪漫派眼里,便是作为异教世界的古代中国奉献给他们建构浪漫诗风及新型文体的典范模式。天人相调、阴阳开阉、情景互蕴、动静化生以及杂而不越、合节成韵,中国古代园林乃是政治理想、生命境界、宇宙意识的写照,直观地再现了古老民族对于世界的灵知。如果迪斯累利所言不虚,“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那么,浪漫主义者势必会认为,中国乃是一种生存样法,中国园林乃是一个心灵隐喻,中国美学精神乃是一种让他们仰慕并藉以超克现代文化危机的“灵知”。“中国形象”经过19世纪上半短暂的衰落之后,在19世纪后半到20世纪又得到了振奋人心的复兴,中国被视为拯救“没落西方”的灵丹妙药。这一点也不偶然,因为浪漫的“中国缘”以及浪漫的“中国梦”,乃是基于一种洞察生命与宇宙奥秘的“灵知”,及其对现代生活世界的世俗性与物质性的抵抗。
思想史家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的开创性研究表明,中国美学精神通过造园艺术渗透于18世纪以后的欧洲,为现代世界注入了一种生命精神、人文趣味和宇宙观念。“浪漫主义起源于中国”,这不是一个大胆的猜想和虚妄的判断。洛夫乔伊指出,18世纪欧洲人的生命情调和美学趣味发生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变化:规律性、一致性、清晰可辨的均衡和对应日渐被视为艺术作品的重大缺陷,而异于常规、对称破缺、变化多样、出人意表以及使整个构思一览无余、简单明快的整体和谐,成为更高一级的审美追求。而当时欧洲艺术实践之中四大趋势,加速了这种审美趣味的激变:风景画的兴起,自然的园林风格的传播,哥特式艺术的复兴,以及最为关键的中国园林艺术对欧洲的征服。“不规则之美”,中国造园艺术的美学圭臬,注入欧洲人的精神世界,激荡起浪漫主义的狂飙。中国园林艺术向欧洲人表明,整齐一律令人生厌,怡人景致未必令人愉悦,而残缺和阴郁却能唤起哀而不伤的感伤,昙花一现的自然美隐喻着人类荣耀的无常。感伤“就是情感君临一切的天地”,施莱格尔的这个断言,漫溢着中国美学的韵味。利用钱伯斯《东方园林概论》所转述的中国园林美学,洛夫乔伊论说了“审美的浪漫主义”与“洒落瑰奇”的风格。其基本内涵包括:拒绝规则化、对称、简朴、简洁明了的整体设计,而趋向于在艺术构思方面寻求变化、差异与多样性。
中国造国家的目标不是摹仿任何东西。而是要创作出园林抒情诗。把树木、灌木、岩石、水流和各种人造物交织在一起,构成抒情诗,区别场景的截然不同的特性。以袁现和唤起多样化基调——“寄情”(pasmons)和“浑然天成”(perfect sensation)——的精妙设计。在这一点上.钱伯斯预见到了另一种变体的浪漫主义,这种变体后来在19世纪的文学和音乐中大放异彩。
这另一种变体的浪漫主义应该同德国浪漫诗风休戚相关,这种相关性显著地表现在“浪漫主义文学三泰斗”之一的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ek.1773—1853)对中国园林艺术的评价上。在其《幻想集》中,他用否定的口吻描述了中国园林的审美风格:自然景象的崇高感,多变、没有限制和无法言传的情感,以及惊骇、惊恐、惊异的感受。可是,在早期浪漫主义者对中国园林美学的拒斥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对异教世界的神秘感,对异域情调的陌生感,以及面对神奇“灵知”的怯场感。
其实,误读,乃是内心欲望的歪曲表达,因为反讽乃是浪漫主义者最迷人的机智。而“反讽”的真谛正在于对永恒的变异和无限充溢的混沌的清楚明白的了悟。在浪漫主义者看来,眼前这个无限的世界,正是通过智性而最终证明它是由迷人的晦涩和极端的迷乱构成。所以,哲学乃是反讽的真正故乡,是超验的捕科打诨,激活它的是一种灵氛,让反讽斗士鸟瞰万象,无限地超越一切有限的事物,超越艺术、道德和天赋观念,在紊乱之中求取秩序,在混沌之中发现秘密,在黑暗之中遭遇光明。浪漫反讽,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不只是一种构思与组织的章法,而且更是一种“多元归一”、“杂而不越”的宇宙感,以及天地人神相悦相调的灵知。虽然不敢说浪漫反讽源自东方,但起码也可以说,它同寓无限于有限、藉有限达无限的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具有隐形遥契的关系。
同理,浪漫主义所迷恋的断章写作也可以做如是观。断章是被拆散的七宝楼台。或者是抽去串线的宝珠。每则断章之于体系,一如滴水之于海洋,于有限之中折射无限。所以,对话是断章之链,断章之花环。鸿雁传书,乃是大写的对话。追思怀想,便是对话构成的体系。断章、对话、通信、回忆,环环相扣,管窥锥指,探幽索赜,构成体系而指向无限。而这也是浪漫诗风的奥秘所在:刻画形形色色的诗意个体,而完整地呈现出作者的精神,展开一幅时代的画卷,因而浪漫的宇宙永无止境地生成。作为浪漫诗风的典范,小说更是史诗、戏剧、抒情的合一,是“阿拉贝斯克风格”与“艺术总体性”的辩证综合。阿拉贝斯克风格,源于伊斯兰建筑学,是指不规则、曲折多变、线条纵横交错,构成奇异瑰丽的图案。而“艺术总体性”,是指浪漫涛风要融合一切体裁、利用一切素材、使用一切艺术手段,建构“诗中之诗”、“文中之文”、“小说之小说”。在《断章》第418则,施莱格尔集中论述了浪漫小说的结构法则和美学精神,赞赏蒂克小说的断章性与整体性。确立了浪漫小说的理想境界:“《斯特恩巴德的漫游》(Franz Stembalds Wanderungen)把《洛维尔》(William Lovell)的严肃和激情同《修道院的兄弟》(Klosterbruder)的艺术家的虔诚、同一切他从古代神话中创造出来的诗的阿拉贝斯克、即总体上最美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于是产生了想象的充溢与轻盈,对于反讽的感觉、尤其是色彩的有目的的异与同。就是在这里.一切也都是透明的,浪漫精神似乎安逸地对自己展开想象。”而这便同“杂而不越”、“以一御多”的中国美学精神相通。尽管施莱格尔与蒂克对中国园林美学的“不规则之美”持一种拒斥的态度,但在骨子里似乎是将迎而拒绝、欲拒还迎。或许,中国园林美学精神已经渗透到欧洲上流社会人士的骨髓和咀脉之中,化作他们艺术实践的集体无意识。所以,浪漫主义一定以“总汇诗”(“宇宙诗”)为审美的最高境界.让所有的形式和所有的材料交替得到满足,艺术地完成一连串不间断的内在革命,让所有的个体活跃其间。“总汇精神是真正的多神论者,它胸怀整座奥林匹斯山的全部神祗。”但在浪漫的宇宙之中,诸神不复争吵,而是美美与共。和谐而又包罗万象。杂多而统一有序,这就是艺术的机智,也是人文的化成。这是浪漫诗学的全部内容,历史哲学的最后归宿,灵魂启示的终极境界。柏拉图与孔子的音乐境界,乃是中西人文的终极祈望。
经过上述粗略的考察可以证明,以园林艺术为载体西传,中国古典精神无疑参与了浪漫主义文化的建构。抒情诗体、教养传奇体、浪游传奇体、断片论说体文学模式,在中国古典文类体系之中都不乏平行对应物。除了文体催化因素之外,中国古典美学天人相调、杂而不越、抒情写意的古典规范也通过欧洲园林、游记写作、考古学体系曲折地渗透到欧洲思想之中,对浪漫主义的问题建构提供了有待细致考察的隐秘的文化资源。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是全球文化语境下多种传统杂交的产物,今天考察这段历史尤其应该清楚认识到比较文学的方法是互动认知、中西涵濡,其境界是和而不同、并存不悖。因此,“中国”是一种方法,而浪漫是一种生存样法,浪漫的中国则确然是一种谋生之道,灵知之源,绵延不朽,宁静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