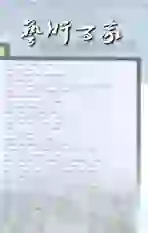自由的问道者
2016-11-02郑工
郑工
摘要:就刘海粟而言,站在中西艺术“对应”的立场上,必然导致他左右兼顾——既站在中国画的立场上反对学画必从写实入手的论调,也反对国粹派对新派画的攻击。因此.他反对临摹抄袭,注重写生,但不是“如实描写”,自然对象在他眼中只是个题目.他在借题发挥。有意思的是,刘海粟也没有进入纯粹抽象的绘画领域,也许这与传统文人画的影响有关。在买践上,他一方面在国画上使用西方表现主义的深红黪绿,另一方面在油画上又着意于中国水墨写意的横涂竖抹;在理论上,我们看到刘海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认同感——一种不排斥自我的文化认同,在认同中重新估价自身文化的价值,在自我的认知结构上不做任何改变,这就是他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美术创作;刘海粟;中西艺术;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传统;写实;抽象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读《吴湖帆日记》,翻至1938年1月7日,发现这么一段话:
海粟前几年以艺术叛徒自号。攻击古画备至,今回头从事古画,先学石涛.不免霸道,今渐改辙,处处谨慎,足见年到功深,自有一定步骤,不能强也。令购藏文中此卷。可为明证。仍回学者本色,勇于善为.不能不佩服之,且近日谈论古画亦渐投契。
因为那天,刘海粟将其所藏的吴文中《武夷九曲》卷请吴湖帆题词,故有此所言。但这绝不是一偶然事件,诚如吴湖帆所述,刘海粟与之交往,多因其喜欢古画了。吴湖帆日记中还有这么几条与刘海粟有关的记载:1.“刘海粟来,示石谷轴、枯树山水。甚好。”(1938年10月18日);2.“刘海粟携来石涛画竹,托补笔。”(1938年11月28日);3“午前同欧儿至刘定之处,遇刘海粟,同至刘海粟处,观石涛六尺大幅,设色绝古艳雄奇之致。又见仇十州绢本《回猎图》,画六马,有飞奔、打滚诸态,人亦姿态逼真,上写飞雁一行,为项子京、安仪周旧物,上书堂有项声表题字、怡亲王宝,洵绝品也。”(1939年4月7日)。然而,刘海粟就此真的“回头”了么?我不以为然。而且,我以为刘海粟热衷古画并“先学石涛”,与其提倡现代艺术息息相关,只不过他的文化立场从西方转向了中国。
刘海粟被称为“艺术叛徒”一事,缘自模特儿事件——1917年7月,上海图画美术院举办师生成绩展览,内有人体习作,引起城东女学校长杨白民的公开辱骂,称刘海粟为“艺术叛徒”。而据王震所引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档案,只说这次展览在该院。举行,“有数室陈列男人体习作,群众见之,惊诧疑异。”…”;且那时校长为张聿光,刘海粟为副校长,学校只开设西洋画科,即便是函授、夜校或师范科,均在西画范畴内教学,未及国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1923年4月聘请诸闻韵、潘天寿来校任教之前。刘海粟出任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校长是在1919年7月1日.而在1919年12月18日,《申报》刊登一文《活人模型绘画之创举》,说上海图画美术学校“重资雇得壮年肌肉丰美的数男子,使学生绘写”,亦未言及论争一事。真正有关裸体画论争乃至上诉法律者,则是在1924年.即上海美专学生饶桂举毕业后回老家江西.办刊物并筹备展览,宣传现代美术与人体美术,刊登刘海粟的文章《记雇佣人体模特儿之经过》,引起社会教育各界反应,其展览遭江西警厅查禁,随之刘海粟卷入这场风波。那时刘海粟年轻气盛,风头正健.具有叛逆精神,一再据理力争,说明艺术的人体画与色情的裸体画是不一样的。随之,就是1925年姜怀素对刘海粟的指控,1926年朱葆三对刘海粟的劝告。正是在这么一场连续几年的风波中,刘海粟由“艺术叛徒”转而为“名教叛徒”。在思想观念上,我们可以看成这是传统的伦理道德与欧美的现代文明的冲突;在艺术问题上,刘海粟是否又代表着力主推行欧美自由与民主的那股思潮?那时刘海粟年不到30岁,他以“叛逆者”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美术界,或许也是他的一种策略。
但这“艺术叛徒”的称号,并不说明刘海粟拒绝传统的艺术,他完全可能站在现代文化的立场去重新看待传统问题,特别是站在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去看待文人画这一系统。所以,1920年7月4日,上海美术学校举行西洋画及普通师范科毕业式,校长刘海粟就在他的简短致辞后,请来三位嘉宾分别演讲,一是陈少白,讲题是《西洋画亟宜提倡》;二是高剑父,讲题是《中西画之异同及变迁》;三是汪亚尘,讲题是《画学上之必要》。三者之间,高剑父的出场是一信号。不久,即是年9月6日的开学式上,刘海粟面对西洋画科与师范科的新生们发表演说,说到男女同学、研究艺术的方针与学术自由这三大问题。解放个性,推崇自由,是刘海粟思考艺术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刘海粟理解欧洲现代艺术与传统文人画的基本点。1921年,刘海粟发表了《塞尚奴的艺术》;1923年4月,他便聘吴昌硕的及门弟子诸闻韵、潘天寿来校任教,筹建中国画科。他对石涛的喜好与偏爱,也在这一时期,并南法国的塞尚联系到中国的石涛,1923年又发表了论文《石涛与后期印象派》。塞尚与后印象派画家.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颠覆了欧美传统的写实主义绘画评价体系,具有鲜明的反叛性;而石涛在中国清代画坛也独辟蹊径,形成与“四王、吴、恽”迥然不同的审美取向,强调自我,反叛精神非常突出。刘海粟之所以欣赏他们,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自己本身也在追求这么一种独立自主的艺术创造精神。他以为这才是现代艺术的精髓,而无所谓采取怎样的形式样态,无所谓采取怎样的工具材料及相应的表现技巧,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又会看到刘海粟在做着一件文化沟通工作。在理论方面,刘海粟以石涛阐发塞尚,以后印象派单纯的形体分析和自由的表达呼应中国传统的画学。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位翻译家,因为他很直接地转换了中西绘画观念上的矛盾与冲突,没有给自己制造难题。他是用“对应”的方式.在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之间建立了一条顺畅的通道。
刘海粟非常聪明,他返回中国文化的传统,就在于他能在纷乱复杂的现代现象中以最贴近自身的方式处理眼前的一切。他以精神自足为目的,只解读不设问——让中国人从自己的近代人文自觉的思想资源中解读欧洲的现代,让欧洲在现代的人文诉求中接应中国传统的诗性哲学。他不断给双方提供阅读的文本,其目的是什么?我以为他既回避了“科学”的现代精神,也回避了“写实”的造型要求,而在“表现”的旗帜下张扬自我的感觉,让明清以来的文人画传统获得现代身份。
活到21世纪的吴冠中,与刘海粟一样对石涛也怀有同样的情结。在晚年,他还在写一本书,名为《我读石涛画语录》,其前言中道:“石涛这个17世纪的中国和尚感悟到绘画诞生于个人的感受,必须根据个人独特的感受创造相适应的画法,这法,他名之为‘一画之法,强调个性抒发,珍视自己的须眉。毫不牵强附会,他提出了20世纪西方表现主义的宣言。我尊奉石涛为中国现代艺术之父,他的艺术创造比塞尚早两个世纪。”
可见,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过程中,石涛伴随我们走过了一个世纪,而且还提示我们,中国美术的现代或近代问题似乎可以从他开始谈起。而刘海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殊历史语境中,由西画及国画,由塞尚及石涛。寻其原因.我以为不能忽视日本现代艺术运动对上海画坛的影响,不能忽视汪亚尘与刘海粟之间的关系。
如,1912年11月23日,筹办图画美术院之初那“五人团”中就有刘海粟与汪亚尘。汪亚尘年长刘海粟两岁,那时才从杭卅I到上海,在乌始光家中认识刘海粟,待1913年图画美术院开学后便任函授部主任兼教员;1914年与丁悚、张聿光、刘海粟一起组织振青社;1915年7月与乌始光、刘海粟、丁悚、陈抱一、俞寄凡、沈泊尘等人去浙江普陀写生;1916年赴日本求学,次年考入东京美术学校。1919年4月,日本画家石井柏亭赴欧洲考察美术后途经上海,应邀到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参观演讲,亦到江苏省教育会美术研究会演讲,讲题为“吾人为什么要学画”,副会长刘海粟致欢迎词。是年7月,汪亚尘回沪探亲;8月23日.刘海粟即请汪亚尘到江苏省教育会美术研究会演讲,讲题是“我国美育之误”;8月26日至9月2日,刘海粟与汪亚尘、江新、王济远、张邕、陈晓江等人在上海静安寺路寰球中国学生会举办洋画展览会,刘海粟的作品《龙华春色》《农》《小贩》具有未来派风格,其《予之姐》与汪亚尘的《静物》则倾向后印象派;9月8日,刚上任的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校长刘海粟即聘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生江小鹣为教务主任;9月11日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开学典礼,安排三人演讲。一是江小鹣讲中西画学之不同及西画理法,二是丁悚讲日本美术界的革新情形,三是汪亚尘讲日本及法国美术之大概及东京美术学校教学实况。最重要的是。也就在1919年9月,汪亚尘返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就读,并邀请刘海粟、俞寄凡、陈国良、贺伯锐赴日本考察美术。这是刘海粟第一次出国考察,他们参观了当代日本美术的重要展览会,如日本帝国美术院第一回展览会(简称“帝展”)、日本美术院第六回展览会、二科会第六回展览会、草土社第七回美术展览会、日本美术协会第六十一回展览会;又参观了重要美术院校。如东京美术学校、东京女子美术学校、太平洋画会研究所、日本美术学校、日本美术研究所、京都高等工艺学校、川端画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手工科、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京都绘画专门学校和关西美术院;同时,他们还会晤了藤岛武二、石井柏亭、纪叔雄、本野精吾、石井寅冶、松本亦太郎、前田喜时等。
在日本画坛,油画家藤岛武二刚从欧洲留学回来(1905-1909年先后留学法国和意大利,1910年回日本).在白马会展览新作30件,表现出印象派的画风,导致大正前期日本画坛风靡印象派、后印象派和野兽派画风,并被称为“西洋画的东方化探索者”。接着,梅原龙三郎于1913年回国,他的画感性、热烈,色彩明快,表现性强,超越了西洋画与日本画的界限:安井曾太郎于1914年回国,在第二届“二科会”展览中展出他的欧游作品,而被称为“日本民族化的代表者”。在“二科会”,梅原龙三郎、安井曾太郎与坂本繁二郎合称“三巨头”,引领油画界一时之风尚。以日本画的民族审美情感与趣味为本原,揉和西洋绘画的有关技巧,在融合中建立新时代的审美规范。
日本在中西艺术之间传递,有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和文化过滤作用。以至到中国来的表现主义已不局限在表现的工具材料上,或者说,中国画和西洋画.不过是工具材料上的差别而已,其表现人类情感的精神性因素是一致的,无论国画还是油画,都强调绘画内在的生命意识。事后,汪亚尘与刘海粟合撰考察报告《日本之帝展》而刘海粟自己则写了《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一书(商务印书馆,1921年),他认为日本的现代美术超过中国,而中国的现实则是“艺术的精神,也永远压在物质追求的压迫之下,国民性便无从充分发挥,思想便也无从充分表现”。
这时的刘海粟开始思考了,因为在这之前,他对中国现代美术的变革路径,在认识上并不清晰。如1918年,在致江苏省教育会的一份提倡美术意见书中,其曰:“吾国美术发达虽早,而数千年来学士大夫崇尚精神之美术,而于实质之美术缺焉不讲.驯至思想日陋,百业隳敝,……拘泥如故,弁陋如故,若非亟求改进,恐数千年之文化,数百兆之华胄,将随此世界美术潮流而澌灭。”那时他期望的是什么?还是“实质之美术缺焉”,原因是士大夫崇尚精神之故。此种论调与批判文人画的时尚极为相合。1918年12月,他在上海环龙路观看英国迈克洛德(Macleod)夫人举办的美术博览会,却极为欣赏油画中那“极简略之笔”,欣赏画面颜色以“原色调合”及“用笔劲苍老”,甚而感叹:“此种画法在今日吾国一般之时髦画家见之,必有绝对不赞成,且必大骂之日:‘大红大绿不成为东西,那里如我国名家所绘之水彩画之精细美丽,用色有成法,青天、绿草、黑影,各有当然之彩色。噫!吾不欲言矣。”——这才是他的本性。
刘海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如在《画学上必要之点》一文,他依然强调破成法而提精神。无论印象派、新印象派、写实派与自然派,“其施色之自然配合,用笔之特具创造,无不各本其天性所感触自然之景象而来”,并将目光转向日本,曰:“今日岛国画学之活动发展,有甚于他国。盖彼邦研究西画者,皆知求真理而不守成法,其在今日盛唱新派画法,且‘文展与‘二科会为剧烈之竞争,可证其新[旧]与新之争,其精进靡已也。”他的思想意识自然倾向于表现,倾向新派的自由表达。他认为,画家的功夫愈深,其法愈呆。他的理论是,无拘无束无“压迫”,天机活泼,真趣盎然,才不失其美,否则,循规蹈矩,左抵右触,前桎后梏,“久而久之,已成积习,师长之一笔一点,类皆肖矣,然后再进而学其一种皮相习派.加以师之赞许,而于不知不觉中造就其一种习惯上强制的技能,自夸为有渊源有出身有派别之画家矣。”不过,刘海粟并不简单地将此视为反对定法而自由涂抹,主意笔而废工笔。他的自由。是“求理法中之自由,非理法外之自由也”什么是理法中的绘画自由?他说要先明法则,合美学之本旨;次者对对象全身贯注.洞察无余;再者知光色变化原理,免于成见。这些都是写实绘画的基本要求,刘海粟以其解释或校正其表现说,显得十分勉强,估计其无非想避免他人的攻击.如以“记号作画之讥也”。然而,到日本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他的思想一下子清晰了,有了方向感,并意识到他必须以日本作为考察世界美术的出发点。
1920年1月1日,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改名为上海美术学校,修订学则,设国画、西洋画、工艺图案、雕塑、高等师范及初级师范六科。是年6月,汪亚尘从日本回沪,7月4日参加上海美术学校的西洋画及普通师范科毕业式并演讲,题目是《画学上必要之点》;7月底介入上海美术学校暑期绘画讲习会的教学,不久便返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继续学业;1921年汪亚尘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回沪后,就在上海美术学校任教。
在中国现代美术变革的思考上,汪亚尘与刘海粟有不少接近之处。如1921年3月发行的《美术》第2卷第4期,刊有汪亚尘的《个性在绘画上的要点》。1922年。汪亚尘说得更透彻:“我们采用西洋艺术的长处,就是在材料上面,因为油画材料有永久性。至于表现方面。尽可依东方的风俗、民情和自然等努力发挥。”1924年汪亚尘在谈到新日本画的变革时还说:“一方面受西洋绘画的影响,一方面他们是要打破从来传习的信条而振救画术的沉沦。日本画家可说是对于东洋画(概括中国画和日本画等等)最先的觉悟者。近来日本人的新日本画.是优是劣,暂且别论.单从他们各作家的努力上看来,确已创出了一个新的途径。”这种创新经验对中国留学生不无启发。此时,他们已不再简单地考虑油画的民族化问题,而如汪亚尘那样.他说他“素来不赞同所谓‘折衷派绘画.拿摄影术的技巧用在材料简单的中国画上,根本是误解。国画的精髓,是在简单明了借用物体来表出内心.同时便包含许多哲理,不是粗浅的技巧主义者所能了然。”在中西画法融和问题上,汪亚尘不在意于外部形式而注重内在意涵的沟通。而刘海粟在日本看了“帝展”,就提出中西调和应坚守两项原则:第一,不能东抄西袭地改造。“既然要改造就需彻底。什么叫彻底呢?就画法论,就是不许用先人为主的方法来束缚自己,中国画旧方法的束缚固然不受,就是西洋画的新方法的束缚也不应该接受。”第二,新旧是相对的。欧洲的新派画或已过时,而中国的传统绘画也不算旧,现在欧洲“许多有思想的画家仍旧在那里研究”,考究东方艺术的究竟。“绘画不应该拿吴(道子)、李(思训)、荆(浩)、关(仝)或江左‘四王的流派当作什么金科玉律,也不应该把拉斐尔、委拉斯开兹当作神圣不可侵犯。”刘海粟有感于日本美术家对艺术的批判精神,有感于他们磨练情操,“随机应变”,发展个性。他不再逗留写实方面,不再勉为其难地努力,他可以在新派旗帜下,抱定“自由发展的主义”,施展他的才华。
刘海粟于1923年3月18日在《时事新报》副刊发表的论文《艺术是生命的表现》,可视为他的艺术宣言。在这篇文章中,刘海粟只强调一点,即“感觉”——由感觉而表现.由感觉而生情。所谓的“感觉”就是“直觉状态”。不知他是否接触过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生命哲学,是否对克罗齐(Benetm Croce.1886-1952)的“直觉说”有过详细的阅读并获得足够的理解,但他仅仅凭借个人的感觉就已经兴奋了,因为尼采的酒神“提奥尼索斯”(Dionyseseh)艺术和日神“阿波罗”(Apallonian)艺术之分类,很容易使中国画家有着重新发现自我的异样激动。刘海粟很注重自我内心的情感体验.所以。他说:“我晓得绘画就是创作的动机纯在直觉里面,表现出自己的生命来;倘使没有生命,即使大规模的铺张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们几乎未见刘海粟创作过什么大题材的绘画。,他的创作就是面对对象的直接表达——离开具体的对象,他的感觉也没有了,创作激情也没有了。他的感觉,他的激情,他那生命的表现,全在于点线之间运行。“不论是罗丹,或是八大,他们用几条线.几点墨,也能使人看出无限的趣味,这就是他们生命和灵感的表现。”这样的艺术观念,自然使他贴近了历史上的文人画,认为宋之院体派的画“有工艺的价值,而没有艺术的精神”,而元四家们将宋院体讥为“匠画”,实在不错。他也拜康有为为师,但不沿袭康有为的观点,他将视线转到了清初画僧八大、石涛及石豁。说他们的作品“超越于自然的形象,是带着一种主观抽象的表现,有一种强烈的情感跃然纸上,他们从自己的笔墨里表现出他们狂热的情感和心灵。这就是他们的生命”。在他们的画面上,一丝之隙。一分之地,极微妙的明暗间,都有精神存在,视觉的造型要素被直接还原为单纯的形迹。接着,他要“把后期印象派的要素剔抉出来,再与石涛的画论相对照考蔌其当否”,为中国明清之后的文人画进入现代获得“合法性”而论证,甚至还想证明在艺术上中国比欧洲更早地进入“现代”——“现今欧人之所谓新艺术、新思想者,吾国三百年前早有其人溶发之矣。”
一个石涛是否能应对欧洲的后印象派?后印象派画家的艺术主张并不一致,就是塞尚、凡·高和高更也难以统而论之。刘海粟会在怎样的一个理论基点上论述两者的异同?文中,刘海粟还是站在“主观情感”上谈,如“后期印象派之为画,悉本其主观情感而行”,以感受之真实、真实之形式而白解。在科学上.“真实”是可以被求证的,但用在艺术上,“真实”就成了自我印证而回避旁人追问的遁词。艺术,真的无法追问,就是理论的表述也难以清晰,一切都是相对的。有时只可意会。
刘海粟不可能十分严谨地论述这一问题,他只凭他的观念或凭他的理解阐释两者的共同意义(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即个人情感表现的审美性。如他将后印象派的特征归纳为三点:一是“表现”,“表现者,融主观人格、个性于客观。非写实主义也”;二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故重表现之画,自必重综合;重综合,则当用省略”;三是“有生命之艺术创作,期其水久而非一时也”,达一时者,未及本原,达本原者。自能永久——“若能达艺术之本原,亲艺术之真美。而不以一时好尚相间,不局限于一定系统之传承,无一定技巧之匠饰,超然脱然,著象于千百年之前,待解于千百年之后,而后方为永久之艺术。”三者的关键词即是:表现,综合,超然。这里的“表现”的含义很宽也很模糊,但“综合”与“分析”相对,与“简略”相关,其含义就有了限定,塞尚是综合的或曰是简略的么?。而“超然”一说,适合凡·高吗?适合高更吗?适合塞尚吗?无论如何,在对后印象派进行一番自我规定之后,刘海粟便开始从容地对应石涛——“观夫石涛之画,悉本其主观情感而行也,其画皆表现而非再现,纯为其个性、人格之表现也。其画亦综合而非分析也,纯由观念而趋单纯化,绝不为物象复杂之外观所窒。”一个“主观情感”就可以沟通石涛和后印象派?其实,何尝是石涛和后印象派,就是在艺术领域内的所有现象,无论古今中外,都可以“主观情感”通论之。1926年,曾仲鸣写一篇《艺术与科学》,谈到艺术的概念,就说:“凡关乎情感的表现的学问,皆可统称为艺术。”曾仲鸣的定义不一定就很严谨,但说明了一种普遍存在的观念,说明“情感”在艺术中的普遍性。我们也明白刘海粟使用“主观情感”这一概念是为了区别于客观的再现的写实的绘画,就是用与联系石涛与后印象派亦可,但未免流于宽泛。或者说,就是以此论述后印象派,也不确切,因为塞尚就不好相类而规范。前者之“表现、综合、超然”似乎也就是为石涛而设定的,作者完全站在石涛的立场(实际上是文人画的立场)看后印象派,制定一个度量的标准。所以,他谈石涛之表现,石涛之综合,石涛之超然脱然,十分顺畅,但也不能说石涛没有“一定系统之传承,又无一定技巧之匠饰”,此言过其实矣。石涛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并不是从根本上排斥“技巧主义”,石涛的画是有技巧的,否则,何谓“不可脱节,不可无理”?石涛的《画语录》锋芒毕露,但石涛的画却温和雅致,没有那许多的“否定”。不过,我们得承认石涛《画语录》所表达的个体独立的自由精神及其批判性,与20世纪欧洲绘画的表现主义有所应合,但归根结底.石涛的绘画是感性的,不是西方的非理性;石涛的理论话语是“描述”的,多隐喻,既不是陈述更不是分析,包括“一画”说。
时隔九年,1932年9月刘海粟又发表《石涛的艺术及其艺术论》,承认石涛和塞尚各有各的世界。并接过吕激关于“生”的本能及其欲求的理论(“生”之扩充论),专门谈论石涛的艺术,说石涛是将对象所有的一切通过自我的“心灵综合”而表现出来,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真实”。他认为艺术上的“求真”与科学不同,不能在“忠于自然上讲,只能在忠于自我上讲”,艺术就是自我表现,艺术的世界是自我所创造的。这里,刘海粟引用了不少近代欧洲流行的理论术语,如自我“人格”、心理“投射”、形式“自律”以及“直觉”、“象征”等,对石涛进行了现代心理学的剖析,结论是:“石涛的实在,在内而不在外,所以他底画的生命也是双层的,不单是表现个性的一回事”,而成为永恒的存在。中国画界对石涛的再认识,主要建立在“创造性”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国画的攻击是“因袭”,而中国画家要重振旗鼓。要取得现代的发展,获得现代性就要确认自身的创造性。因此,抬举石涛、八大取代“四王吴恽”,一方面说明国画家们也可以面向自然,“搜尽奇峰打草稿”;另一方面高度张扬创作主体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摆脱成规,以无法为至法。二者都非常符合现代的要求。在以主体为中心价值的现代社会,客观真正成为了对象世界。人被不断地放大,人文话语也被不断地放大,中国明清的文人画也被回头审视。
那时,上海中国画界不少人热衷石涛,上海西画界也有不少人热衷后印象派,刘海粟是站在石涛和后印象派之间阐释主观情感的表现问题。尽管石涛和后印象派还不是刘海粟自己寻找的,是时代浪潮推给他的,但他乘浪而行,将石涛的美学思想和后印象派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以一个典型的中国画家的身份阐释现代西方的表现主义美学。
四
1923年10月15日,刘海粟又写《论艺术上之主义——近代绘画发展之现象》,从思潮说到运动及之主义的形成——“从文艺复兴到现代艺术,是借印象主义为桥梁,后期印象主义是过桥后开辟的新途径。但是这种艺术思潮在距今三百年前,已有人在东方大声疾呼者,则吾国之艺杰石涛、八大是也。”这种观点,同样见之于汪亚尘。如“我国的南宗画,从南北融合以来,同现在欧洲盛倡表现派的主张,暗相吻合。国画精神骨髓的地方,都依作家胸中的丘壑来描写,在今日经过了许多变迁的西洋画,渐渐接近到国画的精髓,要晓得他们用了几十年暗中摸索的试验。不过刚才到了我国数百年前国画的出发点咧。”
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美术界出现的一股新思潮,借西方现代派大潮涌人之际,直接反拨前一阶段写实派的“科学主义”对艺术的负面影响。重新反省“五四”的文化批判,重新检点传统文化的精神。在这股思潮中,不少中国画家选择了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即以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意象创作心理迎合西方现代的抽象创作心理,以稚拙的天真对应无意的真切,以最便捷的方式扯起表现主义的现代旗帜,这是在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相撞时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而在这场运动中,中西美术的比较研究是表现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如1920年在上海成立的“天马会”。在会章中规定的赢项会务,就有两项属于中西美术方面。如第二项“宣传东西洋近代美术作品”,第三项“考查东西洋美术之沿革”。所谓西洋,即欧美诸国之美术;所谓东洋,含中国、日本之美术(印度及东南亚往往被忽略)。1922年4月15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邀请张君劢到校演讲“现代美术”;是年8月13日,又邀请梁启超到校演讲“美术与生活”。特别是梁启超,谈到创作问题时就涉及主体精神,谈“锐人观察法”。所谓“锐人”,有些“悟”的成分,近乎“智性直观”(Inteklektuelle Anschauung)。智性直观是德国哲学界较为普遍的一个概念,但在2(】世纪初的东方却产生很深的影响,如日本的西田几多郎(1870—1948),将智性直观理解为对“生命的深刻把握”。梁启超的理解呢?他说:“在未动工以前,先把那件事物的整个实在完全摄取,一攫攫住他的生命,霎时间和我的生命并合为一。这种境界,很含有神秘性,虽然可以说是在理性范围之外,然而非用锐入的观察法一直透人深处,也断断不能得这种境界。”与此同时.他亦举苏轼“胸有成竹”的那段画论相比较。如“执笔熟视,乃见其欲画者”、“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难怪倪贻德说当时的艺术界“想把我们固有的国画的价值,用新艺术的见地,再来重新估定一下了”,怎么估定?或者说如何对国画的价值再行确认?倪贻德既不在于估定写实与否或科学与否,也不在于强调使用西方绘画的材料画中国画,而是追慕一种艺术理想——“从摹仿到创造,从追慕到现实,从幻想到直感”。倪贻德也关注石涛,在《石涛及其画趣》一文中,他说:“中国画不像西洋画的拘泥于自然,他们常常望祈于自然而得其灵感.如古人所说‘行万里路和名山大川之气相同化,则山川之气自能于其笔端进出.云烟之气萦回于纸上。所以这种画并不是故意画出来的。西洋画的写实和宋院的画是从外带内,文人画是从内表现外面的。”
这种对应性的比较与解释,缓和了“五四”以来国画家和西画家的对立情绪。譬如,以维护中国画学的学统著称的广州国画研究会。,其发起人之一赵浩公曾声明:“我们不是学西洋绘画的,西洋绘画自有其思想与形式。中西文化各有其特异之处,我们应不基于狭隘思想与西洋绘画的工作者分庭抗礼”,并说“最近表现主义兴起,肇于德国,因此次战败,于无可奈何中,欲发国人于冥省,故艺术以‘体验、‘精神、‘主观三者之表现以出,表现自然内界”。诸家说法。如出一辙,可见当时这种观念流行之广,绝非刘海粟一人之见。德国表现主义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受到尼采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斯泰纳的神秘主义影响。至于东方美学影响西方世界还是有限的,或许还是中国人一厢情愿的自我发现。但这些言论却极大地鼓舞了坚守传统的中国画家们,如以“抱残”为号的广东画家潘稣与赵浩公等人就自我表白“吾人不能逆世界潮流”。张谷雏在《世界绘学之表征及时代变迁》一文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欧洲兴起的表现主义思潮,正因东方绘学的影响,西方的自由表达与中国画学“写物外形”的传统美学精神极为吻合,这就是世界潮流。其结论就是,中国画家何必舍近求远?只要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自然也就踏上了世界现代化的道路。念珠《美之民族性》、黄般若《表现主义与中国绘画》、李凤廷《世界画学之趋势》等数篇文章,与张谷雏的论调基本一致,无不从艺术的地域性和艺术的民族性关系出发,强调文化的生存环境和创造心境的差异导致自然物性和人类心性的歧异,导致世界美术形态的种种特殊性。尤其是西方现代诸流派兴起,表现之风日长,形式因素益重,使国画家们对自身绘画传统的价值重新认识。认为东方和西方各有其美,不能以西洋画与东洋画之美绳之于中国画,此犹“举吾民族性而羁勒于西方民族性之下”。黄般若对“东西方画学”的穷途之叹笑以驳之,认为西方画学由自然物象的描写到精神的表现,非穷也;中国画学本不求与外界一致,求诸心性,“表现其内界之蕴藏”,自古而今,代表着艺术的真谛,更何以言穷?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鲁迅对这一现象也有评述。如1934年5月28日,鲁迅在《大晚报》上看到一则新闻:“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喻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爱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之后,便发表一番感慨——“倘说:中国画和印象主义有一脉相通,那倒还说得下去的,现在以为‘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却未免近于梦话。半枝紫藤.一株松树,一个老虎,几旺麻雀,有些确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尝‘象征着什么呢?”那时,鲁迅提倡木刻运动,既看重艺术家的主观感受及其表现力,叉注重造型能力,对苏俄现代艺术也十分了解,他不会将常识(历史知识与基本概念)与个人的看法混为一谈。他列举了20世纪初苏俄的象征主义之后,构成主义的兴起,后又被写实主义所排去。另。“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常[尝]是象征”,所谓的“代数”应为今之“符号”概念。鲁迅没有谈象征与表现的关系,但他并不因为欧洲表现主义的盛行,而为中国文入画张目。这篇《谁在没落》的文章,鲁迅对刘海粟既无非议亦不称赞.只是纠正媒体上记者的知识性错误。
就刘海粟而言,站在中西艺术“对应”的立场上。必然导致他左右兼顾——既站在中国画的立场上反对学画必从写实人手的论调,也反对国粹派对新派画的攻击。因此,他反对临摹抄袭,注重写生,但不是“如实描写”,自然对象在他眼中只是个题目,他在借题发挥。有意思的是,刘海粟也没有进入纯粹抽象的绘画领域,也许这与传统文人画的影响有关。在实践上,他一方面在国画上使用西方表现主义的深红黪绿,另一方面在油画上又着意于中国水墨写意的横涂竖抹;在理论上,我们看到刘海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认同感——一种不排斥自我的文化认同,在认同中重新估价自身文化的价值,在自我的认知结构上不做任何改变,这就是他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