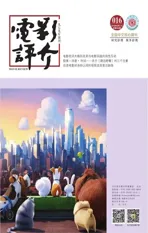台湾电影对身份认同的观照及其变迁脉络
2016-10-11杨颖达
李 洋 杨颖达
台湾电影对身份认同的观照及其变迁脉络
李洋 杨颖达
身份问题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尤其是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愈演愈烈,“我是谁”这个问题也变得愈来愈难回答。身份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不断遭遇危机,逐渐成为一个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就台湾而言,“我是谁”这个问题更是错综复杂,他们曾用“亚细亚的孤儿”来形容自己的身份,也曾用“汪洋中的一条船”作为自身处境的隐喻。可以说,自从出现了关于身份的自觉,台湾对身份的追问与挣扎便从未停止过,这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交织的深层原因。这一问题充满了纠结与挣扎,同时也引发了无数的解答、思考和追问。
在众多的追问与思考中,台湾电影是一个不容忽视且分外重要的场域。曾有学者这样评价台湾新电影,“台湾电影有一个特征,就是反复讲述目前台湾特殊局面形成的经过”。[1]对身份问题的触碰当然不只是历史题材,有台湾导演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政治议题,都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应该说(几乎)所有的台湾艺术电影都是政治电影,都是一个寻找身份的问题。”[2]
随着历史时代的更迭与变化,台湾的身份认同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关键词和“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和艺术形式,无论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还是对重要的时代问题不断进行追问和思索,其一直与身份认同问题之间保持着某种十分密切的联系,电影对身份认同问题的介入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特色。本文将考察台湾电影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脉络,不仅从历时角度进行历史阶段的划分与具体特质说明,同时也注重不同时期之间的连结,关注其间的对话与互动。
一、 1895年至1945年
自从1895年日本殖民时期开始,同化政策其实一直都是日本殖民台湾的基本政策,只是其同化的意义、目的与手段随着时代的背景,如殖民思潮、战争等因素而有所不同,无论如何变化,殖民权力总是在极力同化台湾人“成为日本人”。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电影被官方视为文明教化与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管控,以期能有效传达日本的殖民意志,努力将台湾人的身份形塑为日本人。1937年11月《台湾时报》刊载了《情报与宣传》一文,文章强调报纸、广播及电影等媒体在主导国内舆论取向与国家政策宣传方面之重要性,并特别注重电影价值,认为新闻电影“是未来最值得期待的宣传手段之一”。[3]同期刊登的另一篇文章《时局与新闻电影》更加明确地指出新闻电影在台湾的运用价值,认为“即使在尚未普及日语常用的农村地区,电影亦能透过影像的视觉传递,注入对民众思想之影响力”。[4]1941年9月,台湾总督府更设置了“台湾映画协会”作为专门的电影机构,从事电影的制作、配给到放映,以全面性地达成电影的宣传目的。[5]而台湾人民在此时由于处在被殖民的弱势边缘位置,几乎很难有机会接触或使用电影资源,自然少有机会以电影这一艺术形式和传播媒介来表达出关于身份认同的想法。因此,此时电影所扮演的角色仅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宣导者,其在介入身份认同问题时,主要是表达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权力话语,在官方权力控制下按照权力意志进行日本化典范的身份建构与形塑。
从市场的映演方面来看,在早先,台湾民众对于电影的认识与接触,主要来自台湾总督府或爱国妇人会,于庙口、广场或临时户外舞台所进行的巡回放映活动。放映的电影多半是政策宣传的教化影片或是对其殖民政策有利之战争新闻影片。进入1920年之后,大陆的电影开始进入台湾①《古井重波记》(1923)、《莲花落》(1923)、《大义灭亲》(1924)、《阎瑞生》(1921)是四部最早在台湾放映的大陆电影。[6],此后,几乎当时所有的新片都会输入到台湾,并多由台湾的巡回放映业者在全岛进行巡回放映。大陆电影的大量输入与高人气,扩大并兴盛了此时的台湾电影市场。[7]在当时最受台湾观众欢迎的电影是来自大陆的电影,以及辩士以台语解说的电影放映。这样的市场现象其实反映了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国族建构之下,仍保有对大陆文化以及地方语言的亲近性和认同倾向。

电影《台北星期天》剧照
二、 1945年至1986年
“成为日本人”是日本殖民政权对台湾身份进行塑造的终极目标,然而,这个正确权威且不容置疑的身份却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之下瞬间崩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10 月2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从当时的战败国日本手中接收台湾,长达50余年的殖民统治结束了。
伴随着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新一轮的身份解构与重建随之开启:自上而下地去除日本化,台湾人民不再需要努力“成为日本人”,恢复到“我是中国人”的认同脉络中,并由此确立大中国的身份认同典范。此时的国民党政府依然延续著日本殖民台湾时的电影态度,直接以政治力量介入台湾的电影事业,不仅全面掌握电影资源,还制定了一系列电影相关政策,主导着整个台湾的电影发展。这一系列的政策制度支配了从1949年到70年代台湾电影工业的发展,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之后,随着政治上的渐渐开放,才逐渐获得松解。[8]由于此时期的台湾电影处于政治权力的严格掌控之下,此时的台湾电影在身份认同论述方面基本上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宣导,表现出对身份的积极建构和大力宣导,将身份认同的基准点设置为国族,在历史与文化的维度建构大中国身份认同。
70年代开始,接连的外交挫折让台湾人民的身份认同遭遇危机。此时为了凝聚民心,强化认同,一系列的爱国抗日电影、寻根电影顺势而出。这时期的台湾电影,一方面,以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作为国族主体的本源或本质,也就是说,电影试图通过历史传承、文化根源、血缘和地缘,如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地域空间等符号,塑造出“一套能够渗透整个社会,为社会的成员所共享”的同质性内部文化;另一方面,将入侵的日本设置为他者,通过与他者的比照来凸显自我与他者的区别,从而加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进一步明确和确立自我。与此同时,电影也不断地把何其“混杂”的不同社会主体建构和想象成一个具有统一历史文化传统的同质的整体。最终,“塑造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形成“政治权力与同质性文化结合为一”的国族认同。[9]
一直至80年代台湾新电影时期,关于身份认同的多元思考才逐渐显影。有学者曾这样描述台湾新电影:
政治与社会的松动,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创作空间,过去视为敏感的题材,现在或许可以一试。电影创作者有机会较忠实地纪录自己的历史与成长经验;而来自文化与文学界对本土的反思,更刺激他们这样的创作欲望。在社会松动的氛围里,艺术创作开始敢于面对过去,述说过去,电影也在同样的情绪下,渐渐走出逃避主义的庇荫,成为记忆历史、发抒真实情感的工具。这样的松动,或许就是1983年台湾新电影出现的背景条件。[10]
就这样,台湾电影逐渐出现不同于以往的作品,开始传达与威权统治时期所宣导的官方意识形态有所不同的视角与声音。身份认同成为电影可以关注和探讨,并开始深入思考与表达的重要议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身份追寻其实仍然是在以国族为前提的架构下所进行的,主要是作者对于生命经验的回顾,是在不触碰政治上台湾定位问题(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前提之下所做的回望与反思。也就是说,对于认同的思考依旧是在大中国的框架下进行思考,且是战后知识分子对于自我身份的反思、生命的回望。
三、 1987年至1999年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令。“解严”之后,曾经的典范与权威身份遭到质疑和解构,“这种不确定感,形成了整个社会的认同危机”。[11]于是,关于身份认同的探索与探讨变得更加多元与激烈,并日渐成为一个备受关注与充满争论的热门问题。这一态势一直延续到90年代,甚至在学界掀起多次关于身份认同的大讨论。而学术研究的范式也逐渐由本质论过度到建构论,国族或民族不再被视为一个本质的存在,而是一种“想象共同体”。并且,随着全球化现象的不断演进,致使“民族国家”的概念不断被挑战,其重要性也逐渐减退,众多学者指出国族认同的意义在当下社会已经开始式微。亦有学者指出认为后现代社会已变成“后国家”社会;国家甚至也已经变成“携带型”身份(portable nationality)。[12]这样的身份认同讨论在政治权力的操控下延伸出统独问题的争论,并在台湾社会日益突出,然而,这样一路的争论在台湾电影中却没有看到相应的关注与呈现。而电影作为既保守又商业化的媒体,自然不会以统独问题作为题材,所以90年代的台湾电影中没有出现过相关题材。但是,讨论身份认同焦虑的却不少,“我们也能发现,90年代电影里的认同态度,出现了远比过去更多重、更复杂的形式”。[13]
这一时期的台湾电影转而开始凸显历史与文化的建构性,同时也显露出身份的建构性,解构身份的本质存在。身份认同似乎突然之间失去了某种基础,也没有了明确的认同导向,一时间陷入了游移与迷失。在大中国典范时期,台湾电影在建构身份、引导认同的过程中是有明确答案和终极目标的,即我是中国人,用肯定的口气、追根溯源的方式清楚地表明“我是谁”。而如今,台湾电影的大陆由台湾的本源变成台湾的他者,希望藉由与大陆他者的对照来证明其自身的独特性与主体性。然而,电影中的相关呈现只是通过“我”与“他”对比之后显现出的差异来勾勒出“我”的自画像,只是在竭力证明和标榜“我不是他”,而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清晰。也就是说,台湾电影中的身份认同由“我知道我是谁”变成了“我知道我不是他”,而至于“我到底是谁”,仍是一种纠结与混沌的状态。
90年代之后的台湾电影对“大陆”与“台湾”这一新一旧两个“父祖之国”同时进行解构和质疑,国族与历史本身的建构性不断被呈现,国族认同概念和意义遭到解构。然而解构和质疑只是表层行动,并不代表对身份认同主体建构的放弃与忽略,实质上这种解构和质疑更加深刻地表现出台湾在身份认同方面所面临的危机与困境,同时也更加深入地展现出由认同危机和困境而引发的一系列纠结和思考,意味着人们的精神自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对身份认同的解构其实也包含着建构的意图和冲动,即打破现在的格局和思维模式,寻找新的认同基点,建立新的认同框架。也就是说,反中心、反霸权并不是为了追求主体的解构,相反地,是希望实现主体的重构。
四、 2000年至今
2000年,台湾发生政党轮替,民主进步党的陈水扁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在政治权力的主导下,“本土化”成为时下的“政治正确”,也成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要规则。1993年提出的“闽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四大“族群”(Ethnic Groups)概念逐渐成为普遍讨论身份问题的认识论基础。2001年,九年一贯教育的施行,“母语教学”被正式规划进入义务教育中,自此闽、客、原住民(各个族群均不同)语言不再只是“地方方言”,而语言位置的提升也代表了身份有了新的认同“归依”分类。族群,成为新的身份认同语汇。
如果说90年代表现出的对身份主体的质疑与解构,那么,2000年以后则更加明显地表现出重构“主体”的倾向。“在地”逐渐成为此时社会各个领域的热门词汇,而此时的“在地化”在身份建构方面主要是在突出“地方/地域”的含义,将台湾这片土地作为台湾主体的本源,使个体或群体在其中寻求感情的归属和身份的确认。这样一来,无论历史如何断裂,个体如何混杂,台湾依然可以被想象成一个同质的整体,因为大家都是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台湾人。台湾的身份认同逐渐变成以族群和本土作为思考框架的“地方认同”。
“尤其是2008年《海角七号》票房井喷显现出在地的超强号召力之后,电影似乎更加注重围绕着台湾这片土地,从历史、文化、回忆、情感等诸多方面寻找关于它的故事,从而连结人们的共同记忆。有些电影开始回顾历史,如《一八九五》《赛德克·巴莱》和《面引子》;有些影片开始关注各类民俗文化,如《阵头》和《父后七日》;有些作品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给予关怀,如《不能没有你》;有些把记忆拉回至青葱的学生时代,如《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有些则将视线聚焦于都会,如《听说》《一页台北》和《第36个故事》;有些电影开始关注外籍劳工等新住民问题,如《台北星期天》等。可以说,只要能和台湾社会的集体意识挂钩或是引起观众共鸣都可以经得起市场考验。”[14]
这一时期的电影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在于对语言归位的推进,亦即原先是说台语的闽南人就说台语(如《海角七号》《艋胛》),原先是说客语的客家人就说客家话(如《一八九五》),是说原住民语的原住民就说原住民语(如《赛德克·巴莱》)、新移民者也是说着原先家乡的母语(如《台北星期天》)。“让角色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只要是片中人物真实的需要,任何语言都可运用在同一部影片中,这是‘新台湾电影’最大的特色。”[15]
电影似乎失去了以往对于建构国族身份的兴趣,转而将目光聚焦于脚下的这片土地,在地成为了凝聚身份归属感的关键。这类题材的电影在此时反中心、“爱台湾”的“政治正确”口号之下,在市场上大获好评。这波市场上的台湾电影热潮也带动了新一波的台湾电影荣景,一如1955年掀起风潮的台语电影时期。
结语
透过上述脉络梳理可以看出,在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政治权力、身份认同与电影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亦即在台湾这纠结矛盾的身份认同问题中,电影是如何的介入与呈现的。
而跳出台湾这个区域,从整个世界的历时与共时脉络来看,认同的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看与被看之间的辩证关系,自我总是藉由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观看,来形成自我的认同。而这样一种认同的过程,也同样发生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亦即,经由观看电影的过程,使自我在象征秩序中成为社会性的存在。观众透过电影的观看,进行多重层次的认同行为:从首要认同的自我外表认同到次要认同的电影人物认同,再到最后的电影镜头认同。透过电影的中介,想象秩序与象征秩序发生转换。[16]
从路易·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到梅兹(Metz)再到让-路易·鲍德利(Jean-Lou is Baudry)都将电影视为意识形态机器,认为电影是意识形态召唤的绝佳媒介。这个电影意识形态机器制造了观众,使观看电影的观众成了被召唤、被缝合的主体。可以说,电影指定了观众,给了观众一个想象的位置,从电影的一开始就让观众进入一场预定的旅行。[17]这种藉由电影所中介的认同,在帝国/殖民主义兴盛的年代发生在世界各国之间,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当权者无不透过电影,建构对己有利的认同意识,是为国族认同建构。然而随着战后世界经济结构的改变、资本主义的盛行,以经济为目的全球化模糊了国族的界线,形成全球化下的地球村,而一些进入后殖民社会的前殖民地内部也因为内部殖民的问题而产生了严重的国族/民族认同矛盾。这两相加成的结果便慢慢产生了以地方为思考核心的在地认同,电影逐渐扮演起反抗中央性与全球性的抵抗角色,成为再现底层意识形态并传达意识的中介媒体,是为认同意识的另一种再现。
而台湾电影与身份认同的关系脉络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同时也显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从脉络梳理中可以看出,总体可分为两大认同语境,一是以国家、民族作为思考框架的国族认同语境;另一个则是以地方族群、历史文化作为思考框架的地方认同语境。当一个新的统治政权到来时,为了安定社会的秩序以维护其自身的统治权力,当权者首先要建构的便是人民对于国族的认同。透过典范原则的建立,使人民在这样的原则之下形塑自我认同,进而达成国族认同,可以说这样的身份认同是在一个以国族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框架下所进行的思考。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族界线的模糊,这时的身份认同开始转以地方作为思考,以地方上的族群、历史、文化,作为对抗全球化的一种力量。而在台湾,因为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政治权力对本土意识的收编与操纵,使得这个地方意识结合了“去大陆”的“台湾意识”,让这样的地方认同以及随之的本土化变得些吊诡,易于成为一种狭隘的政治认同。
而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电影,一方面在当权者的管控之中,透过积极的生产或是消极的立法管制,使电影承载当局者的意识形态,宣导权力意志,召唤人民的认同主体;另一方面,也通过审美接受的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间认同的倾向与意识。这样一种既为建构又为反映的双重属性,使台湾电影成为观察身份认同问题的绝佳媒介。
[1]佐藤忠男.大陆电影百年[M].钱航,译.杨晓芬,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224.
[2]洪帆,张巍.隔岸观火——台湾电影的“后独立时代”到了?[J].电影艺术,2009(3):56.
[3]大冢正.情报与宣传[N].台湾时报,1937-11:66-73.
[4]原保夫.时局与新闻电影[N].台湾时报,1937-11:74-80.
[5]吕诉上.台湾电影戏剧史[M].台北:银华出版社,1961:14.
[6]陈飞宝.海峡两岸电影分析史之关系[J].电影欣赏,1989(41):56.
[7]三泽真美惠.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日治时期台湾电影人的交涉与跨境[M].李文倾,许时嘉,译.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121-122.
[8]刘现成.台湾电影、社会与国家[M].台北:视觉艺术传播学会,1997:46.
[9]Ernest Gellner.国族主义[M].李金梅,译.台北:联经,2001:3.
[10[11][13]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M].台北:远流,1998:259,337,338.
[12]林文淇.华语电影中的国家寓言与国族认同[M].台北: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2009:125,142,151,123.
[14]李洋.台湾电影的本土回潮现象及潜层结构[J].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14(6):11.
[15]黄仁.新台湾电影[M].台北:商务印书馆,2013:3.
[16][17]Shu-mei Shih.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与呈现[M].杨华庆,译.台北:联经,2013:37-38,38-39.
李 洋,女,山东鱼台人,厦门理工大学讲师,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厦门理工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成员,博士,主要从事电影电视史论方向研究;
杨颖达,男,台湾新竹人,硕士(MFA),台湾影像研究者与独立纪录片工作者。
本文系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台湾电影的身份认同建构及其对南台湾大学生国族意识的影响”(项目批准号:15YJC76005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