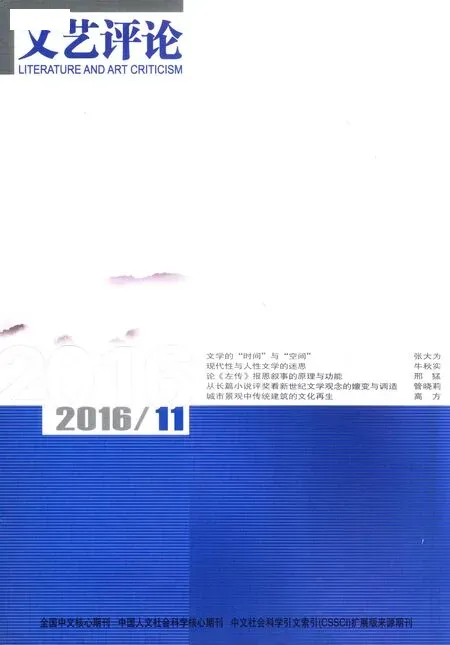“醉”:宋代蜀学之审美境界
2016-09-29谭玉龙
○谭玉龙
“醉”:宋代蜀学之审美境界
○谭玉龙
中华酒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我国先民在五千多年以前就已掌握了酿酒的技术,并且,酒还渗透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朱肱《酒经》云:“大哉,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乡射之饮,鹿鸣之歌,宾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渔夫樵妇,无可以缺也。”①个中缘由乃是酒不仅具有实用价值,它还具有精神价值。对于“诗人墨客”来说,酒的精神价值集中体现为“醉”,酒让人“醉”,“醉”让人消愁解脱、自然适意。而以“三苏”为首的宋代蜀学正注意到了这一点,引“醉”入艺术与人生,将“醉”提升为一种即工夫即本体的蜀学美学范畴,并以此区别于荆公新学和二程洛学,成为宋代美学中一个独特的美学流派。
一、醉笔得天全,宛宛天投蜺
对于艺术创作、审美鉴赏等活动来说,情感总是贯穿于始终的,所以,“美是情感变成有形”②。可见,“情”在艺术、审美活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家美学也承认并且重视“情”在人们生活和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但是,毫无节制的“情”就会导致“过”“淫”,故儒家美学倡导“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③,以对“情”进行限制而使之归于“正”。宋代荆公新学和二程洛学则沿此路径发展了儒家美学的情感理论。新学与洛学美学较为一致地认为“情”是“性”的一种状态,所以不必完全禁止和取消“情”,如“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性情》)④;“只性为本,情是性之动处”(《河南程氏遗书》)⑤。从本体论上讲,“性情一也”(《性情》)⑥。但同时,荆公新学认为:“求性于君子,求情于小人。”“动则当于理,则圣也,贤也;不当于理,则小人也。”(《性情》)⑦二程洛学也认为:“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答横渠张子后先生书》)⑧“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颜子所好何学论》)⑨。因此,虽然“情”在新学、洛学中具有存在的空间,但是他们与传统儒家一样,更多地注意到了“情”的负面影响而倡导“性其情”(《颜子所好何学论》)⑩。
三苏蜀学却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明显不同。苏轼云:“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苏氏易传》)⑪所以,“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恶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买金偿亡》)⑫“情”,在蜀学美学中,并不是“恶”,而是“性”的一种状态,它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并且“极欢极戚而不违于道”(《栾城集·上两制诸公书》)⑬。也正由于此,蜀学美学才认为,艺术创作必须要重视“情”、运用“情”,如:“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南行前集叙》)⑭所谓“不能不为”就是情感充沛到了不得不进行创作的程度。在这种状态下,艺术创作不是“勉强所为”而是纯任性灵而发,艺术作品就是情感的外化。与新学、洛学限制“情”相反,蜀学美学尊情、尚情,这就为“醉”的艺术创作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知道,“醉”是一种过度饮酒而产生的由生理到心理的一种变化和状态,它往往使人情感奋发、精神活跃。这一点正被蜀学美学所注意而将其引入了艺术创作领域。苏轼曰:“仆醉后,乘兴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跋草书后》)⑮可见,“醉”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就是一种情感的抒泄。苏轼还说:“成都人蒲永升,嗜酒放浪,性与画会,始作活水,得二孙本意。”(《书蒲永升画后》)⑯醉酒使人放浪形骸,从而在自由的状态下,自我之“性”与绘画融合为一,让艺术作品达到“活”的境界。可以说,蜀学美学因“情”而重视、倡导“醉”,因为“醉”激发“情”,让人在“不能不为”的状态中进行艺术创作。因此,苏辙云:“醉书大轴作歌诗,顷刻挥毫千万字。”(《饮饯王巩》)⑰
“醉”触发充沛的情感,从而使艺术家在亢奋的状态下瞬间地、毫不粘滞地进行艺术创作。而这种瞬间而成的艺术创作必然要超越技法。苏辙诗曰:“醉吟挥弄清潮水,谁信从前戒律人。”⑱“戒律”就是规则、技法,“戒律人”就是恪守法则、墨守成规之人。在苏辙看来,“醉”正是对“戒律”的否定,对艺术创作技法的超越。有学者认为:“洛党、蜀党是旧党豪贵内部依地域势力结合而相互倾轧的集团。”而“洛学与蜀学之争是洛蜀党争的反映”⑲,因此,蜀学自然烙上了地域文化(即巴蜀文化)的印迹。巴蜀文化,自汉代以降,就不断受到道家哲学的影响,蜀中学人大多重视吸收老庄哲学。《老子》所谓的“道法自然”⑳、《庄子》中的“庖丁解牛”㉑等等,无不蕴含着“无法之法”的美学思想。三苏蜀学美学也正是在吸收老庄“无法之法”论的基础上,倡导艺术创作应冲破技法的束缚。苏洵曾对何谓“天下之至文”的问题进行了论述:“‘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杂文·仲兄字文甫说》)㉒可见,“天下之至文”不是刻意创作而成的“文”,而是犹如风与水相接触而自然形成的“文”,这是一种“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之“文”。此“文”不待技法、规则而通向老庄之“自然”“大道”。
“醉”正满足了这种“无意相求”“不期相遭”的要求。苏轼《题醉草》曰:“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㉓日本学者平山观月曾用“蜿蜒跌宕似无意而为”来评论王羲之的草书。㉔而“蜿蜒跌宕似无意而为”正说明了草书的创作需要超越有限的技法而“无意”为之。苏轼所谓“醉”能作大草,而“醒”却不及。可见,蜀学美学之“醉”与“醒”正对应着无法与有法,“醉”就是对技法的超越,是一种无意为之的无法之法。三苏钟情于“醉笔”㉕“醉墨”㉖的原因正在于此。要言之,三苏蜀学美学不像荆公新学、二程洛学那样倡导“去情却欲”(《礼乐论》)㉗、“性其情”(《颜子所好何学论》)㉘,而是以“醉”触“情”进行超越技法的自由创作,让艺术创作真正成为解放自我、彰显个性的活动。因此,在蜀学美学中,“醉笔”可以“得天全”㉙、“醉语”可以“出天真”㉚。
二、醉中身已忘,万事随亦毁
蜀学是一种儒学,但它是融合了佛道等思想的儒学,所以我们认为,蜀学具有“融合三教、融贯博通、重经学、积极进取不因循守旧等鲜明特色”㉛。而蜀学美学同样具有“融合三教”的鲜明特色,不过在政治人生道路上,“三苏”以儒家思想为主,在艺术审美方面,佛老思想的影响则是主要的。㉜道家以出世的态度面对世间的人事,认为世间事物遮蔽人的真性、限制人的自由,所以他们欲超越当下、回复到原生性的社会中。佛教则以遁世的态度观照尘世,它认为尘世的一切皆虚幻不实、迁流变动,所以佛教在“空”万法的基础上,实现解脱、证得涅槃。佛道二教虽然有所差异,但他们较为一致地否定或超越当下的尘世而进入他们自己设想的自由之境。蜀学美学中的“醉”正是这样一种否定或超越。在艺术美学中,“醉”是对技法的超越,而在人生美学中,“醉”成为对世间忧愁烦恼的超越,如“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水调歌头》)㉝;“醉后胸中百无有,偃然啸傲倾朋曹”(《栾城集·次韵赵至节推首夏》)㉞。可见,蜀学美学之“醉”不只是一种艺术创作方法,还是一种人生的修为。
对于占据北宋思想主导地位的荆公新学来说,人生的修为主要是“思”。王安石《洪范传》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五事,以思为主……思者,事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圣也。”㉟这就是荆公新学“以思为主”的修为之法。虽然,貌言视听要以“思”为主、由“思”来统摄,但其中最为根本的乃是人的思想言行要符合“礼”。所谓“以思为主”是让人发自内心的遵从“礼”,让人自愿地按“礼”行事。而“三苏”蜀学却与此大异其趣。苏辙云:“醉中身已忘,万事随亦毀。此心不应然,外物妄使尔。”(《次韵子瞻和渊明饮酒二十首》)㊱可见,“醉”让人忘却自“身”。而“身”都已经忘却了,身之视听言貌符不符合“礼”就更加无意义了。苏轼也说:“得酒未举杯,丧我固忘尔。”(《和陶饮酒二十首》)㊲庄子美学中有“吾丧我”㊳的理论。“吾”与“我”是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我”是对待之我、欲望之我,“吾”是真我、道之我。“吾丧我”就是要消除对待分别和欲望之心。蜀学美学认为,“醉”可助“丧我”,其实是说,“醉”让人消除思想中的分别、荡去心灵中的欲望,从而实现自我的本真存在方式。苏轼《记焦山长老答问》十分形象地讲述了这种本真之“醉”:“东坡居士醉后单衫游招隐,既醒,着衫而归,问大众云:‘适来醉汉向甚处去?’众无答。明日举以问焦山。焦山叉手而立。”㊴不知向哪里去了的“醉汉”就是“我”,“醉”中的苏轼丧去了“我”,从而实现了本真之“吾”。
如果说荆公新学以“思”为主是强调修身应符合“礼”的话,那么,二程洛学以“敬”为工夫则是强调修身应主于“理”,即“涵养须用敬”㊵、“入道以敬为本”㊶。二程曰:“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一则无二三矣。”(《河南程氏遗书》)㊷“敬”就是“主一”,“一”则是“理”。所以,二程洛学以“敬”为工夫的理论其实是让人顺应、遵从天理。这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要求,是一种“自我约束的方法”㊸。而蜀学美学却以“醉”冲破这种约束与束缚。苏轼诗云:“醉中相与弃拘束,顾劝二子解带围。”㊹“弃拘束”“解带围”就是庄子美学中“真画者”之“解衣般礴”㊺,即解开了功名利禄、仁义礼智的束缚。蜀学美学之“醉”正与此相通,它让人解脱后、进入“法天贵真,不拘于俗”㊻的境界。苏轼《论淳于髠》云:“淳于髠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于州闾之间,男女杂坐,几于劝矣,何讽之有?”㊼在苏轼看来,淳于髠之“醉”超越了一切伦理道德的束缚而自由地“于州闾之间,男女杂坐”。男女之间的隔阂已被“醉”所消解,他因“醉”而进入了一种混沌未开的大道之境。
总之,荆公新学、二程洛学分别以“思”“敬”为工夫实现成圣入道的人生美学理想,而“三苏”蜀学美学却以“醉”为工夫冲破礼法、天理的束缚。所以,蜀学美学所谓的“醉时万虑一扫空,醒后纷纷如宿草”㊽“哀歌妙舞奉清觞,白日一醉万事忘”㊾等皆说明,“醉”是一种人生修为之法,它让人去除功利欲望的束缚,最终实现人生美学意义上的“旷然天真”(《与言上人》)㊿。
三、天地一醉,万物同归
人是时间性的存在,在时间之中,人的生命总是有限、暂时的。但人并不满足于此,总是在冲破有限、追求无限。这也体现在中国古典美学之中:“中国古代艺术家都在审美活动中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把个体生命投入宇宙的大生命(‘道’、‘气’、‘太和’)之中,从而超越个体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和暂时性。”而蜀学美学之“醉”正反映了这一“超越性”。蜀学美学中的“醉笔得天全”“醉中身已忘”分别代表了艺术创作和个人修为之“醉”,但蜀学美学并未就此止步,它还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超越之“醉”,即天地之醉。前两者是工夫,后者为本体。
在蜀学中,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如“道,万物之宗也。万物,道之末也”(《道德真经注·道常无名》);“盖道无所不在,其于人为性”(《道德真经注·载营魄》。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皆以“道”为宗,是“道”的一种存在方式,它们并不彼此分离。所以,苏轼云:“天人有相通之道。”(《周书·洪范》)但是,“天人相通”仅具有可然性而非必然,即并非所有人都能与天相通。那么,什么人才能与天相通呢?蜀学认为:“惟达者为能默然而心通也。”(《周书·洪范》)“夫惟达人知性之无坏而身之非实,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尽去,然后可以涉世而无累矣”(《道德真经注·宠辱》)。所以,只有“达人”才能与天相通,只有修炼到了“达”的境界才能天人合一。
东晋葛洪曰:“顺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滞者,达人也。”(《抱朴子外篇·行品》)“达人”就是不为世累、自然逍遥、淡然无为之人,“达”的境界就是庄子中的“神全”之境。《庄子·达生》曰:“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神全”乃其神“全于天”也,即人复归于“道”。而“醉”让人无欲无求、忘却生死、让人复归于天,这与“道”相通,所以“醉者”即“神全”者,他可以超越有限、进入无限,“坠车”而“不死”。申言之,“达人”即“神全”之人,“神全”之人即“醉者”,“醉”就是一种“达”、一种天人合一之境界。苏轼吸收了这种庄学思想而认为:“有如醉且坠,幸未伤即醒。”(《颖州初别子由二首》)另外,他还进一步说:“醉眠草棘间,虫虺莫予毒。”(《和王晋卿》)“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书孟德传后》)。可见,蜀学美学之“醉”不仅能让人像《庄子》中的“神全”之人那样“坠而不死”,还可让虫蛇虎豹不能来加害。
“醉”可让人“神全”而“达”,防止肉体生命受到伤害,此外,它还可以让人的精神超越有限进入无限,在精神境界上获得自由。《老子》曰:“我愚人之心,纯纯。”“愚”相对于聪明、知识,“纯纯”即“沌沌”,象征着道之混沌状态。所以,“愚”就是对知识、聪明的超越而获得那“大制不割”的混全之道。苏辙曰:“颓然一醉,终日如愚。”(《自写真赞》)“醉”即“愚”,它超越了功名利禄、善恶美丑的无分别状态。苏轼曰:“醉中不以鼻饮,梦中不以趾捉,天机之所合,不强而自记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吾尝见居士作华严相,皆以意造,而与佛合。”(《书李伯时山庄图后》)“醉”是一种无区分的心境,既然没有了区分,那么万物齐一、贵贱不存,自然不会“留于一物”。在这种状态下,人才能见出自我与万物之本真,达到“神与万物交”“智与百工通”“与佛合”的境界,让人的精神进入了永恒。
“醉”让人身心皆“全”,使“人之天”复归“天之天”,在“成己”与“成物”之间消除物我间的隔阂、彰显生命的本真,正如苏轼在《醉白棠记》中云:“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此时,万物不是与我分离、对待的客体,不是为认识、功利而存在的对象,而是与我生命息息相关的另一“主体”,物我之间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苏洵曰:“开樽自献酬,竟日成野醉。青莎可为席,白石可为几。”(《藤樽》)苏轼亦云:“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登云龙山》)在“醉”之中,天地成为人的屋宇、万物成为人的衣裳。这也就是庄子美学所追求的那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要言之,蜀学美学中的“醉”不只是工夫,它本身还是一种境界,是一种“神全”“通达”的本体之境。苏轼引《祭曼卿文》曰:“天地一醉,万物同归。”(《书石曼卿诗笔后》)“醉”让万物归于“道”,这种天地之“醉”就是人与万物融合为一的天地境界。
结语
有学者认为,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相对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中唐以后,中国文化正出现了一个由唐型文化转向宋型文化的大流转。此说大体正确。以美学观之,荆公新学、二程洛学美学的以“性”为重的性情论以及以“思”“敬”为主的工夫论等都能说明一种宋型文化的相对“封闭”“内倾”特色。但当我们将宋代蜀学美学纳入其中加以考察时,却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一方面,蜀学美学以“醉”为艺术创作方法,倡导艺术创作应该冲破技法、自然而然、任性而发,从而彰显出“天全”“天真”的审美风格;另一方面,蜀学美学以“醉”为人生的修为方法,强调它能使人“忘”的功效,在忘却烦恼、焦虑之中,使人达到“旷然天真”的审美境界。虽然,前者属于艺术创作论,后者属于人生修为论,但两者都是工夫论。而蜀学美学之“醉”不仅是工夫,它还是本体,通向了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大道之境、存在之域。这种即工夫即本体的蜀学美学之“醉”并非是在礼教束缚下的创作、修为,它指向的也不是去人欲而穷天理的道德形而上学,而是在否定、超越现实中种种束缚的真正自由的天人合一境界。它彰显出了狂放、浓烈、自由的特色。所以,虽然“三苏”蜀学不像荆公新学、二程洛学(或理学)先后成为两宋思想界的主流,但在美学领域中,“三苏”蜀学则发挥着更为重要和独特的作用与影响,如后世逐步兴起的文人画及其审美旨趣和明代以“醉”作草书的理论与实践都不能说没有受到“三苏”蜀学美学的影响、启发与刺激。总之,自由、狂放、浓烈而非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蜀学美学不仅是巴蜀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还是宋代美学乃至整个中国美学中的一个独特流派。
(作者单位: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
①朱肱《酒经》[A],载《中国古代酒文献辑录》(第三册)[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版,第1-2页。
②鲍山葵《美学三讲》[M],周煦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③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A],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2页。
④⑥⑦㉗㉟《王安石文集》[A],载《王安石全集》(上册)[M],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版,第134页,第134页,第134页,第123页,第110页。
⑤㊵㊷《二程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页,第188页,第169页。
⑧⑨⑩㉘《二程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0页,第577页,第577页,第577页。
⑪《苏氏易传》[A],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一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143页。
⑫⑮《东坡志林》[M],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五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208页,第237页。
⑬《苏辙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87页。
⑭苏轼《南行前集序》[A],《苏轼全集》(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57页。
⑯《苏东坡全集》(上册)[M],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303页。
⑰⑱㉖㉞㊾《苏辙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4页,第207页,第47页,第94页,第127页。
⑲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史纲》(上册)[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第294-295页。
㉔平山观月《书法艺术学》[M],喻建十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㉙㊲㊹《苏轼诗集》(四)[A],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九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第48页,第468-469页。
㉛蔡方鹿《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㉜王世德《儒道佛美学的融合——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8页。
㉝《苏轼词集》[A],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十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㊴《苏轼文集》(五)[M],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十五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㊶《二程集》(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3页。
㊸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5页。
㊻郭庆藩《庄子集释》(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32页。
㊼苏轼《仇池笔记》[A],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五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页。
2016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规划项目“宋代蜀学与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