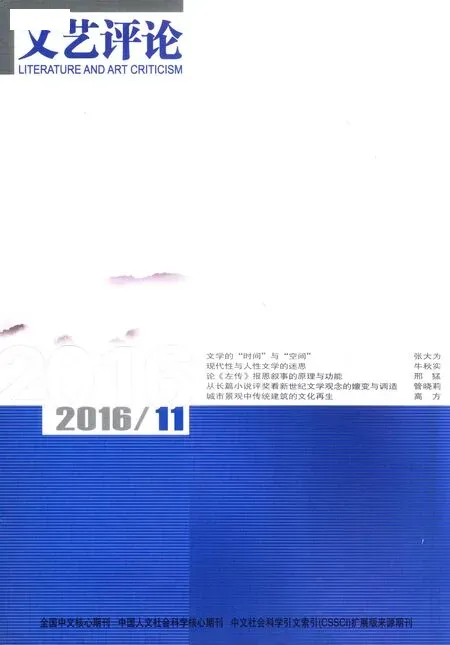返归传统的现代传奇——论新世纪中国文化探险小说
2016-09-29高媛
○高媛
返归传统的现代传奇——论新世纪中国文化探险小说
○高媛
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小说勃兴,大量新异的小说类型,诸如穿越、玄幻、宫斗等,进入大众阅读视野。在林林总总的作品中,《藏地密码》以对西藏神秘的地域和文化探求,开地域探秘类小说先河;《鬼吹灯》和《盗墓笔记》则在幽深的古墓空间中谈鬼论神,通过诡奇的内容书写,奠定盗墓寻宝类小说的基础;《古董局中局》从文玩珍宝鉴赏入手,借宝物流传的起伏跌宕,写世态人情的变迁纠葛,成为古董鉴别类小说鼻祖;《鲁班的诅咒》展现诸多器物机巧,将人物的探索活动与传统风水知识结合,使机关破解类小说风靡一时。受这些小说影响,同类作品大量涌现,形成“藏地热”“盗墓热”等小说畅销热潮,继而催生大批讲述后人创造性发展运用传统技术的小说创作。考察这些作品及其代表的不同类型小说文本,剥除其表层看似五花八门、各辟蹊径的书写内容,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品都以追寻动机和探险情节统摄全文,叙事脉络清晰且基本一致。同时,小说通过大量想象性书写,建构出多个遵从现实逻辑但异于现实世界的虚幻空间,从真实与梦幻双重维度叙述文本内容。更重要的是,小说在叙写人物的探险历程之余,糅合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知识,试图反拨技术理性主导的“祛魅”风潮,从而完成对原始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复归。这种以表面探险叙事隐喻深层传统文化内涵的作品可被归纳为“文化探险小说”,具备传奇作品的特质。
“传奇”一词在中西方文学背景中具有不同的历史语义。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传奇的早期含义近乎“志怪”,因为“传”意指记录、传述,而“奇”则代表着奇事、异闻,“传奇”即是记录并传述奇事异闻的叙事文体。随着时代发展,“传奇”一词的指代范围由最早的唐人传奇逐渐扩充至一种小说文体,进而成为诸宫调乃至戏曲杂剧的类别概念。作为文学范畴中的叙事文体,传奇具备三个基本的叙事模式:即“尽设幻语”“作意好奇”的虚构色彩、“无奇不传,无传不奇”的情节中心结构模式以及“游戏成文聊寓言”的寓言意蕴。①而在西方,传奇(romance)是中世纪欧洲流传较广的文学形式,以骑士传奇为主,“大都采用情节离奇、荒诞不经的冒险故事形式,赞美忠于国王,锄强扶弱,为捍卫宗教、荣誉或爱情而献身的骑士精神”②。注重情节的奇异性以及文本故事的虚构性,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传奇”文体的共同特点。本文探讨的文化探险小说,以人物奇幻的冒险经历贯穿全文,虚构出人物活动的想象空间,直接沿用传奇叙事模式,可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传奇文本。
一、延续探险与追寻的传奇叙事结构
探索未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禀赋与渴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现实世界进行地域拓荒,代表着人类对陌生地理空间的开掘,而弗洛伊德阐释梦境,从个人范畴发展内心透视,则激发了人类对未知精神世界的追寻。在文学作品中,冒险书写无疑是基于探索未知目标进行的直接行动,也是传奇情节的主要部分。加拿大学者弗莱将传奇叙事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危险的旅行及开头的几次无关大局的险遇;生死攸关的搏斗,通常在这场战斗中,主人公与其仇敌必有一死或二人同时丧生;主人公欢庆凯旋”③。新世纪的文化探险小说延续了同样的叙事结构。以《藏地密码》为例,主人公卓木强巴,因一张偶得的藏獒照片,与同伴涉足可可西里无人区、穿越亚马逊热带雨林、攀爬斯必杰莫雪山、漂流地下暗河,九死一生,却都是探险之初“几次无关大局的险遇”。在抵达香巴拉地区以及梦想中的香巴拉神庙后,人物面对着苯教先人遗留的重重考验,又与莫金、唐涛等十三圆桌骑士代表进行“生死攸关的搏斗”,直至最终取得胜利,获知藏地苯教失传千年的秘密。《鬼吹灯》《盗墓笔记》中胡八一及吴邪等人的盗墓经历、《古董局中局》中许愿的鉴宝打假过程以及《鲁班的诅咒》中鲁一弃的定宝路途,虽然形式有所差异,但都依循同样的事件发生逻辑,使文本叙事结构趋于一致。
在小说中,人物“探险”的“探”之行为,是在其“追寻”的目的驱使下进行的。“追寻”行为依据对象不同,又可分为几种不同情况。对某物,特别是对象征物质财富的宝藏的渴求,是该类小说中最常见的追寻动机。在盗墓作品中,人物进行的古墓宝物发现与“盗取”活动,即是受获得金钱、宝藏等物质欲望驱动。卓木强巴在探险初始的寻找目标——顶级藏獒紫麒麟,也只是个人的兴趣所在。而追寻先人嘱托,以继承家族使命,是主人公进行探险活动的又一重动机。于鲁家后代鲁一弃而言,将八宝各归其位,从而破凶穴,定凡疆,造福世人,正是家族世代传承并追寻完成的目标。而许愿坚守家族对古董“真”的追求,与制假售假的老朝奉团伙多次交手并将其击败,也为许家与对手间数千年的斗争画上圆满的句号。值得注意的是,人物的探寻动机在探险过程中可能发生变化,进而产生第三类目标,即追寻生命奥秘以及人生的神圣信仰。无独有偶,《鬼吹灯》和《盗墓笔记》故事中段,个人生命受到某种不知名力量影响,迫使主人公进行新的冒险,人物的基本生存需求压倒物质需求,攫取财宝的行为终演变成维护个体生命以及探寻命运奥秘、生命真谛的深入探索行为。而卓木强巴则在获得大量资料后,将寻找香巴拉神庙这一重要宗教和历史遗迹的目的与紫麒麟结合在一起,主人公内心中对神圣信仰和神物的追求成为探险的重要动力,与西方传奇中“寻找圣杯”的主题不谋而合。虽然上述不同人物的追寻动机相异,但却具有共同的精神性追求,富有郑重其事的严肃意味。同时,追寻信念内化于人物个体心灵,随人物探险过程发展变化,也有助于主人公的成长经验增长和人生体悟丰富。
而探险历程的“险”则遍布全文,首先即是自然环境的恶劣严峻,人物经历了亚马逊热带雨林的雷暴和洪水、藏地雪山死亡西风带的狂风以及极寒、云南虫谷的瘴气迷雾、南海海域的洋流漩涡……种种艰险地理空间和极端气候对人的生理机能产生较大威胁。在这些极端环境中生存的奇异生物无疑是人物面临的另一重危险:翼展长达三米的大金鹏鸟、体长超过一米的飞蚊、腰粗超过三个水缸直径的青鳞巨蟒等,以数倍于常人的体态产生压倒性优势。除此之外,还有人触之即自燃的达普飞虫、体含剧毒的高原雪蛛、凶神恶煞的嗜血鲛人、能学人说话并会为死去同伴复仇的鸡冠蛇……身体具备特定性能,随时可给人致命一击。较之上述自然界生物,各种环境中的机关暗器,设计毒辣,目的也在杀人于无形。湘西古墓瓮城中的机关,待人动棺椁后,即会牵动床子弩,导致万箭齐发,因箭上带火,不仅能击伤人物,还会引发火势。而大量木人站在机弩后,受水银流动所驱,不断运箭装弩、挂弦击射,直至弓尽矢绝或机括崩坏才会停止,保证攻击的持续度。除此之外,对手的全力追杀也为险境“锦上添花”,现代化的枪支弹药,已是人的血肉之躯难以抗衡的杀伤性武器,而对手在人物前进路上留下的陷阱圈套,更足以致人死地。文本中的种种险境总以递进的方式发生,从无关紧要到生死攸关,先导的困境亦预示着后发的艰难险阻来势汹汹。人物在不断升级的难关面前屡屡化险为夷,不仅是对其智力和体力的确证,亦是人物成长的重要体现。
与许多小说在结尾处宣告终结的形式不同,这些文化探险小说始终处在发展之中:每次人物探险的结束,仅意味着叙事的短暂停顿,而前方总有新的探险行动等待着人物。基于上述行为的延续性和重发性,文化探险小说成为一种“未完成的文本”,可被不断接续与填补。《盗墓笔记》的吴邪,考察告一段落后,自塔木陀的西王母墓归来,收到三叔来信。三叔希望事情“到了这里就结束了”,“你的生活可以继续下去,不要再陷入其中了”,因为“那些已经和你无关了”④,但他还是踏上前往云南的路途。《古董局中局》中的许愿,成功洗雪爷爷的耻辱并查出古董造假首领老朝奉,一切看似圆满,但结尾处“忽有敲门声传来”,意味着仍有未解决的事件即将发生。这种永无穷尽的叙述方式,使文本的叙述变成一种螺旋式的开放循环,结局呈现为“由主人公之追寻所转化和更新了的开端”⑤,孕育着新一轮的冒险传奇故事。循环式的探险发生过程使文本表面呈现出一种充满未知又得以不断填补的结构,在种种“后来怎么样”的读者疑问中,推进小说叙事生生不息地发展。
文化探险小说着意叙述险象环生的人物传奇经历,借助为现实生活所匮乏的“奇景”以及“险遇”书写,以层出不穷又出人意料的情节高潮,不断满足读者渴望通过文本实现的冒险刺激感受。同时,作品的探险情节主线隐喻着主人公自生涩至成熟的心智以及体能成长过程,使读者在阅读故事的同时,受“代入感”心理机制影响,将自我想象为英雄般的主人公,参与到文本的探险叙事以及成长叙事中。于读者而言,这类文本为他们提供了悬置于世俗经验之上的特殊阅读体验,有效规避平淡日常生活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和模糊性,故而在现代大众文学类型中具有特殊吸引力。
二、建构神秘与奇诡的传奇想象世界
弗莱曾将传奇中的世界归纳为“田园世界”和“夜的世界”,前者幸福、安全、祥和,是超越普通体验的世界,而后者充满刺激的冒险,涉及分离、孤独、丢脸、痛苦等悲剧性情感体验。⑥传奇往往带领读者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开头处“先是沉入到夜的世界,然后又回归到田园的世界,或者通向田园世界的某种象征”⑦。在这其中,“夜的世界”作为文化探险小说的主要情节空间,是创作者所建构的充满想象的梦幻世界。
在“夜的世界”中,创作者们构筑了大量充满想象力的人物活动空间以及兼具美感和不可思议力量的神奇之物。《鬼吹灯》中的湘西瓶山,整座山为一块完整青石,在天地造化的鬼斧神工下,形如天瓶坠地,“底座陷入大地,整个瓶身状的山体向北倾斜欲倒,后山断崖就这么欲倒未倒地凌空倾斜了几千万年,千分的绝险之中带着万分的离奇”,在“半空云雨起于方寸咫尺之间,幽壑林泉现于弹指一挥之际”,宛若“烟云变幻奇景掩映的神仙洞府”⑧。三峡地区地下的悬崖绝壁处,金丝雨燕群在强劲气流中以身体搭筑起一座“无影仙桥”,帮助胡八一等人安然通过,成为“银河鹊桥”的现实版展示。《藏地密码》中的帕巴拉神庙,人物穿行的古老隧道,原本一片漆黑,但在两声击掌之后,“就像装了无数声控灯一般,沿着隧道,仿佛有许多环形的霓虹灯……一团一团的如一簇簇火星,蔓延开去”,“玫瑰红,荧光绿,宝石蓝,如烟火噬灰般绚烂浸染,一圈圈火线蔓延之后,此起彼伏,如夜空中群星闪烁,又似波光粼粼而泛”⑨,以古人的智慧为现代人展现了一幕媲美现代科技的神奇画面。而卓木强巴等人在地下所目睹的人造千米巨佛,在山崖上伸出18条臂膀,每条臂膀上都担负着7至12层楼高不等的倒悬佛教寺庙,呈现出倒三角形态,仿佛一座座漂浮在空中的山,配着不同臂膀上闪烁不定的火炬,大小倒悬空寺如漂浮在空中的孔明灯,令人生出误闯天庭、如在幻境之感。种种奇观式的景物基于创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在日常世界之外构筑了一个看似超脱现实却又立足现实的虚幻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包括上文阐述的危险重重,也具备常人难以亲眼目睹的绝美与壮阔,成功融合了惊险与绝美两个极端,使主人公在“痛并快乐着”的历程中前进。
与此同时,文本中的奇珍异宝也在无形中满足了读者的宝物幻想。部分宝物集天地灵气,属于自然环境的先天馈赠,如《鬼吹灯》中的海底珠母,体内鲜活珍珠多达一百五六十余枚,“蚌甲分合之际,珠光闪现。借着水波的折射,化出瑞彩虹气,令人目为之夺,神为之慑”,映照得水下“精气璀璨,月光如昼”⑩。而中国古人用先进技艺制造出的物品,历经时间洗练,在现世也具有重要功用和美学价值。《藏地密码》中的千辐金法叉轮,每幅末端固定着时辰珠,在相应的时间发出夜明荧光,报时千年无误。象牙雕凿成的古印度都城以及黄金铸造出的唐代宫殿,不仅还原了景物的历史风貌,更巧夺天工的是,城中的车马门窗、宫中的人物器具,皆可在机关的操纵下行动自如,栩栩如生。《古董局中局》中的柴瓷,素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称,有着传说中“雨过天晴云破处”的美誉,却因世所罕见而弥足珍贵。更有宝物,在体现古代先进技艺的基础上,被传统秘术赋予超自然的功能,体现出神奇魔力。如《鲁班的诅咒》中的风水学“意形盘”,“用一盘珍奇的宝贝,按宅子的主点要穴摆置,并将这些宝贝和实际的构筑都注入意形符咒,这样可以从意形盘上看出实际构筑的状态,也可以在意形盘上对实际构筑进行控制和调整”⑪。《盗墓笔记》中的金缕玉衣,穿之可打破生死界限。作者在想象世界中虚构的诸多宝物,本身即是美与术的统一,而这些宝物的珍奇性,也唤醒了潜藏于读者意识深处的财富和权势渴望。
与奇幻小说构筑的魔法世界、灵异幻境不同,这类作品中的梦幻时空具备日常生活的现实逻辑,人物一如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并未因意外事件或命运遭际突获异能或穿越时空。小说的故事起源,往往开端于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能经历的日常事件,日常得不易被人记忆,却在一系列行动后带领人物进入幻想世界,在读者眼皮下散发出神奇幻想之光。一定意义上,这种处理方法混淆了真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使读者在不知不觉间步入幻想世界。而作品中的种种想象,看似神秘莫测,颇有鬼神色彩,但多源自可解的传统秘术或先人智慧,并非凭空虚构的魔幻法术,从而淡化了文本的“怪力乱神”之名。以《鬼吹灯》为例,胡八一在巫峡地底,仿照神笔马良,以笔画地,打开通向地仙古墓的大门,将民间传说变为现实生活。究其原因,即在于墨中物质,可吸引野蜂群在“门”顶端之树结群筑巢,而这种物质受到成群野蜂摩擦后,逐渐发光,制造出烈火燃烧的假象。受此蛊惑,野蜂纷纷遗溺以淋湿蜂巢,蜂溺从蜂巢滴落后,腐蚀地上青石,随即产生较深的地下坑洞。现实性和真实性被赋予幻想以及架空的世界,这些描写为终日沉浸于平淡且重复生活的都市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刺激,以多样的想象途径开掘出一个平行且独立于日常的传奇时空,较之平板的现实世界更容易进入。
但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结尾处往往伴随着人物探险空间的毁灭,爆炸、焚烧、坍塌……种种阴差阳错或有意为之的人为行动,导致幻想中的世界被轻易毁于一旦,而破碎、遗失以及被迫消耗,终不能重见天日,也是文中许多珍宝的必然结局。这些在小说中具备神奇瑰丽色彩,或惊险恐怖气息的景物,看似热闹非凡,最终却化为乌有,难为世人所见,某种程度上正是创作者对其塑造的幻想世界的一种解构处理,明确了文本中“夜的世界”的虚幻性,强化了横亘在现实真实与虚幻想象之间的固有界限,也使读者在完成遨游想象世界的行动后,找到返回现实世界的路径。
三、返归原始与传统的传奇文本内蕴
传奇的探险经历形成小说独特的叙事脉络,神奇的想象世界则建构文本斑斓的叙事空间,在这些表层叙事特征之下,文化探险小说更注重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和颇富原始色彩的地域文化知识。不同于英国现代传奇冒险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扩张探索梦想,这些中国当代的冒险作品反而带有返回古代祖先智慧的叙事冲动,与吉利恩·比尔所强调的“传奇唤起往昔和社会意义上遥远的时代”⑫观点相合。各小说中时时处处渗透的密宗源流、风水秘术、机关绝学以及古董鉴别方法,皆是传统文化遗留下的瑰宝。而多部作品不约而同设置的故事背景地——西北边地、云南峡谷、内蒙草原、东北林区以及南海海域等,具备独特的地理景观以及神秘的地域文化,并因发展相对滞后,留存着原始文明的印记。
小说以或隐或现的方式强调探险中心人物的家学渊源,既确立了人物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又为人物以传统知识进行的相应行动奠定了基础。卓木强巴、胡八一、吴邪、鲁一弃以及许愿等人皆是从事相关行业的家族后人,分别得到了《宁玛古经》、残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祖父日记、《班经》以及《素鼎录》等记载全面专业知识的家族典籍。在传统专业知识引导下,胡八一以罗盘对照天空中星宿,推断出吉星笼罩之地恰是古城中水井处。众人下井后旋即发现姑墨王子之墓,印证了他的分金定穴能力,体现了对风水知识的应用。卓木强巴等人见识的血池,作为苯教的独特密码装置,需要将人体相应器官摆放在血池的固定位置,使人体血液流通至此并对其进行洗刷,随后传导给某种藤蔓类植物,通过其强大的拉力打开人力难及的巨门。而道家的种种密符,能够催云生雾,能够使草人自行运动,成为活人替身,也能隐去活人身上的生命气息,帮助鲁一弃等人逃过敌人追杀,从宗教秘术方面为文本内容提供相关支持。许愿用的“悬丝诊脉,隔空鉴金”一法,得自家传,以丝线垂直悬挂金印,利用传统灌铸工艺气泡繁多的事实,推断出真印重心不稳的真相,印证了古董鉴赏知识的多样和全面。在机关破解方面,鲁一弃在对家布置的南徐水银画“逍遥一叶舟”前,借助“血红滞银流”的色彩组合原理以及“单眼不叠视”的视物方式,发现了画中隐藏得几不可见的穴点,以嘴抽吸出画中丝线,使水银不断下降,从而破解画中险势。基于此,传统文化知识在人物探险历程中扮演着指向标的重要角色,同时也是他们解决问题的重要工具。
与此同时,人物探险中面对的机关暗器,正是古人为了捍卫自身利益所设,是其智慧的物化表现。香巴拉神庙中历经千年仍在不断运行的机关动力,来自雪山积雪融水与火山内在高温产生的蒸汽,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体现出古人对自然环境的因势利导、合理利用。而机关陷阱的设计也体现出多重传统文化知识。有的机关中包含着宗教的哲理寓意,如卓木强巴难以走出的白象神木迷宫,仅需《华严经》中一句“象王行处落花红”提点,便可令人茅塞顿开;有的机关依循《周易》卦象推演,典型的即是“嵌套九宫变”,共有一万余个小房间组成类似魔方的结构,根据特定时间变换房间位置以及上下左右方位;有的机关利用中医传统理论,像《鲁班的诅咒》中的“冰晶吐寒”阵,需要将阵型想象成人类五官,按照天灵、眉心、人中、双颊、双贯太阳穴等依次砍断铁链;有些机关借鉴更前代先辈的智慧经验,诸如古希腊点灯术、古埃及转轮术、中国传统的敲砖术以及华容道考验;同时先人也会结合地理环境特点,利用人的视觉盲点,并循法自然,构造出相应的机关,如鲁家在“铺石”和“固梁”技法中,利用砖石的变换和梁椽的交错,使人产生平面与立体间杂、动态与静止混合的错觉,被困于机关之中。古人的传统智慧凝聚于物象,以有形之态打破时空阻隔,与当下的探险者以及他们应用的现代科技知识发生碰撞,上演了数场发生在二者之间的关于隐藏与发掘、护尸与盗墓、伪造与鉴真、制造机关与破解机关之间的智力斗争。
而与这些先人智慧相对应的,还有在不同作品中屡次出现的藏地、湘西、新疆、云南、东北以及南海海域等空间地点,它们本身具备现代都市空间丧失的原始自然韵味和神秘文化气息。这些地点本非小说叙述的中心内容,仅作为故事背景地侧面烘托情节内容,但在作者不经意的笔触下显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如藏地密宗的神奇修炼方式,新疆地区对胡大即“真主”的信仰,湘西地区的送尸、落洞、放蛊习俗,长江三峡的悬棺墓葬形式,南海采珠的独特水下操作流程,都成为作品中难以被人忽略的独特民俗内容。上述因社会发展而渐趋失落的民俗内容,带有原始文明的古朴特质,以其难以为现代科技所解释的神秘性,为人物的探险活动营造出神秘氛围,也为探险故事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弗莱看来,“传奇的那种永葆童真的品格,表现为对往昔的非常强烈的留恋,对时空中某种充满想象的黄金时代的执着追求”⑬,文化探险小说恰在探险的表层叙述之余,进行了一种发现原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写作尝试。随着启蒙运动进入中国,现代性“祛魅”发展曾导致民族的“文化失忆”与“集体遗忘”⑭,而文化探险作品的种种传统文化“再现”与地域文化“摹写”则试图对此进行反拨,以此融入当下的本土文化自觉潮流。除此以外,在西方强势文化以探险家的角色对东方文化进行探索之时,东方传统文明曾被西方人误读,或被美化、理想化为诗意且乌托邦化的“高贵的野蛮人”想象,或被现实接触以及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影响,呈现出“丑陋”“原始”“怪异”的一面。⑮面对这一窘境,国内精英创作者曾试图借助“寻根小说”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表现,但他们的创作意图并非出于呈现传统文化这种历史性的经验以及知识,而是从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场对传统文化进行想象与重构,文本最终的传统文化展现,经历了现代性的认知过滤,被赋予了更多的思想和文化意味。新世纪的文化探险小说采用与其不同的书写路径,回归传统文化知识的本源,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运用相应内容,虽有夸张成分,但剥离了附加在传统文化之上的重重思想意旨,更贴近大众读者的阅读期待。
传奇作为一种具有“无产阶级”成分的文学形式,在研究者的预言中,会在新的时代东山再起,⑯文化探险小说无疑就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传奇叙事复归。这类作品以探险情节推动文本发展,以奇异想象构筑梦幻空间,并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原始文明的巧妙化用中,满足读者的冒险欲望与远离现实忧虑诉求,是新世纪大众文学的重要组成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王东《传奇叙事与中国现代小说》[D],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页。
②尹建民《比较文学术语汇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③⑬⑯[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页,第269页,第268-269页。
④南派三叔《盗墓笔记·五》[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页。
⑤⑥⑦[加]诺思洛普·弗莱《世俗的经典:传奇故事结构研究》[M],孟祥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第57页,第59页。
⑧天下霸唱《鬼吹灯之七·怒晴湘西》[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5页。
⑨何马《藏地密码10·神圣大结局》[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
⑩天下霸唱《鬼吹灯之六·南海归墟》[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5页,第286页。
⑪圆太极《鲁班的诅咒2》[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页。
⑫[英]吉利恩·比尔《传奇》[M],肖遥、邹孜彦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⑭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
⑮叶舒宪《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史”(项目号:105591GK)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