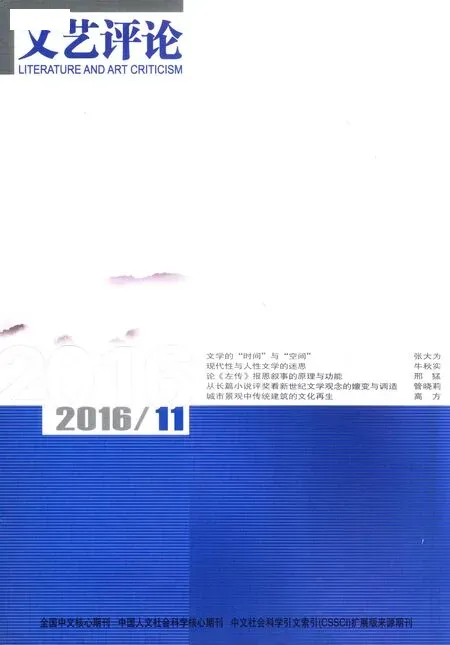二元结构的设置与个人立场的悬搁——对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的一种解读
2016-09-29杨有楠
○杨有楠
二元结构的设置与个人立场的悬搁——对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的一种解读
○杨有楠
贾平凹的《极花》甫一发表就招致驳杂的批评之声,一些读者指出它隐含着为拐卖妇女辩护的倾向,一些读者认为它显示出作者对乡村的固执情怀已是一种荒诞的行为,甚或更有女权主义者直陈它暴露了作者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立场,其功用是“用对过时悲剧假装深情的铺陈,刺激读者,以求关注和治疗作者长期抱有的男性失败的焦虑”①……针对种种争议,贾平凹试图给出自己的解释,然而他所提供的一些“辩词”似乎反而成为批评者可据其作进一步声讨的“证词”。比如,贾平凹认为:“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②如果断章取义地仅从这一句出发,我们似乎可以从容地站在道德的高地为《极花》的批评者们摇旗呐喊。然而如果我们耐心地进入文本就会发现,《极花》所引起的争议或许恰好来自作者所作的一种可贵努力,即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竭力“写这生活的黑白之间,人心里极难说出来的东西”③。小说中的“极花”是一种冬天是虫夏天开花的奇特生物,除了所被赋予的象征意义外,笔者认为它还以非此却不即彼的身份特性隐喻了作者所追求的悬搁立场。
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
作为与新时期及其转型一起拓路的作家,贾平凹对介入现实抱持着极大的热忱,他的作品几乎都或多或少地与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相关联:《怀念狼》反思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秦腔》哀悼传统文化的隳败,《高兴》关注城市拾荒人的命运,《带灯》审视乡镇基层的政治伦理困境……而在《极花》中,贾平凹则试图对拐卖妇女这一社会议题作更深层次的探讨。这一问题自然不是新近出现的,而以其为表现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已经不在少数,小说《喊山》(2004年),电影《盲山》(2007年)、《嫁给大山的女人》(2009年)等都是据此铺展而成的。如果对它们作比较阅读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主要人物的设置上,还是在细小情节的营构上,《极花》实际上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之前的叙述模式。在《盲山》中,导演李杨对白雪梅遭强暴,以及村民阻挡警察带走白雪梅等场面做了粗糙的、甚至不加节制的光影表现。而在《极花》中,村民帮助黑亮强暴胡蝶,暴力野蛮地破坏解救行动的场景在贾平凹不吝笔墨的“絮叨”中同样得以再现。然而,《极花》当然不同于《盲山》,其最大的区别在于贾平凹试图突破施害者形象的扁形塑造方式,并尽力挖掘施害行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应该说,尽管李杨也试图在紧张的叙事间隙对乡村人情、人性作更饱满的展现(比如拐卖者黄德贵的母亲就是一个相对矛盾、立体的形象),但或许是受电影时长所限,又或许是出于明确传达主旨的需要,《盲山》里的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界限基本是分明的,而结尾处白雪梅用菜刀砍向黄德贵的情节设置不仅更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尖锐对立,而且意味着矛盾缓和的不可能性。④与之相比,《极花》则力图在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搭建出更具复杂性、流动性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黑亮们施害者与受害者双重身份的着力凸显(尤其是后者)。几十年来,即使社会文明已明显提高,打击力度已逐年增强,拐卖妇女为何频仍发生?这或许是贾平凹让发生在十年前的真实故事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的重要动因之一。因之,他竭力规避了“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的中介因素和表层逻辑,而集中于对直接原因的寻找和分析。作为拐卖妇女的直接需求方,农村男性就成为作者审视的主要对象,继而他们的婚姻难题以及性苦闷现状就被挖掘出来。在此之前,梁鸿的纪实文本《中国在梁庄》、韩少功的散文《山南水北》、曹乃谦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以及郝杰的电影《光棍儿》等都对农村男性的性苦闷做过酷烈、赤裸的呈现。而《极花》的特别之处在于不只是呈现,而是力图将这一问题向前、后两个方向推演开去,即向前寻索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向后思考其带来的连锁问题和可预见的走向。《极花》开头,在进城打工的顺子的媳妇跟着收购极花的村外人私奔后,顺子爹因痛恨自己不能为儿子留住媳妇而自杀,同村的男人也因女人不愿留下备感羞辱和愤恨。接着,作者便通过美女像上的深刻刀痕表现了黑亮们的性苦闷。可以看到,作者指出症结的欲望如此急切,以致不惜直接借黑亮之口传达出来:“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尽管贾平凹旋即就站在胡蝶的立场上对拐卖行为提出质疑,但这很快便湮没甚至消解在欲言又止的语气和对农村男性性苦闷的渲染中。与其他作家相似,贾平凹走的也是“往狠里写”的路子,于是我们看到,丧妻后疯癫的金锁的哭坟声贯穿全篇,女人訾米像财物般在立春、腊八两兄弟间完成转手,光棍们只能从石头女人,甚至动物那里获得慰藉……除此之外,借助家家户户前立着的像石祖一般的门窗,以及血葱的繁盛和极花的日渐稀少之对比,作者不但暗示了性苦闷在农村的普泛性、焦虑感,更牵涉出女性缺席给农村男性带来的传宗接代的压力,以及由此造成的更大焦虑。“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荒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⑤可以说,在贾平凹看来,这是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加诸于传统农村(尤其是农村男性)的伤痛,这伤痛不仅剧烈而且很难通过正常的方式获得疗愈,久而久之它更是熬成无奈的苦衷,继而为本是受害者的黑亮们叠加上施害者的身份。这两种对立身份的纠缠无疑使得黑亮们成为一个矛盾的主体,作者一方面想给予他们同情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无法也不能轻易原谅他们的暴力行为,因而只能延宕审判的到来。但不得不说,必要的批判性的缺席也是一种写作遗憾。
其次,是一种类似于“斯德哥尔摩效应”的情节设置。一般而言,“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指的是一种反常的心理学现象,即受害者在与施害者共同生活期间,对其产生一定的认同感或正面情感。表面看来,被拐卖者胡蝶对拐卖者黑亮及其“帮凶”(几乎是整个圪梁村)所表现出的情感变化与此效应十分相似。一开始,被囚禁的胡蝶对黑亮、黑亮爹甚或整个圪梁村村民都只有满腔的仇恨。她以每天在窑洞壁上刻道儿的方式计划逃离,勾勒活下去的希望。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经历了被强暴、被迫生子等厄运的胡蝶反而能以平和的心境与黑亮们相处了。她开始视自己为家庭中的一员,主动承担家务,称呼黑亮的父亲“爹”,甚至最终接受黑亮做自己的丈夫(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灵上)……不能否认,这种情感上的转换或许出于无奈地认命,但是细究文本就会发现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胡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作出的主动情感选择。与《盲山》中粗鲁、凶悍、暴躁的丈夫黄德贵不同,《极花》中的黑亮在拐卖、囚禁、强暴胡蝶之外,不仅竭力为胡蝶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小心翼翼地给她一定的尊重和包容。贾平凹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分寸的细节将黑亮塑造为一个虽有污点,却也老实孝顺、好求上进,甚至不乏温柔,有些胆怯的农村男人。除此之外,以黑亮爹为代表的圪梁村村民其实都是掺杂着善恶因子的传统农民,他们虽蒙昧、野蛮、暴力、贪婪,却也不乏朴素的人情温暖,比如,他们自发地帮外出打工的顺子料理爹的后事,也尽量在立春、腊八兄弟丧生之后伸出援手等等。由于《极花》是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而成的,因而以上图景基本是经胡蝶掺杂着仇恨的眼睛过滤后的结果。因此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病态扭曲不同,胡蝶的情感转向在贾平凹不急不缓的铺垫下折射出的或许正是真实的人性,它如此复杂而莫测,以致黑白分明的价值判断在它面前显得无力甚至几近失效。
可以说,尽管同样是关注人口拐卖问题,相较于《盲山》等更着重于展现人道主义悲悯和现实批判精神,《极花》则意在借其勾勒出如恶之花般、异化了的人性的复杂图景。为此,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悬搁了个人的价值判断,而只是呈现了两难现状的事实存在。
城市和农村之间
虽然《极花》是从胡蝶被拐卖说起的,但贾平凹却直言:“我实在是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着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⑥可以说,关注乡村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境遇已成为贾平凹挥之不去的书写情结。而在《极花》中,作者则希冀借助主人公胡蝶的空间流浪探讨当下时代语境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进而考察个人在中国大转型年代的生存境况。
纵观全篇,胡蝶先后完成了农村-城市-农村-城市-农村的空间流浪,而乡村的全面衰败不仅激发了她最初的流浪冲动,而且还使其在很长时间内延续着对城市的美好憧憬。与《古炉》不同,《极花》中的乡村不再被描绘成“文化乌托邦式”的存在,而逐渐裸露出其真实面相。首先,物质的贫乏仍是难以摆脱的生存焦虑。借助胡蝶的喋喋不休,贾平凹呈现了连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无法保障的农村现状:饮食单调乏味且只够温饱,学费难以筹集,衣着、住所破旧不堪,医疗技术古老落后,村庄偏远封闭,环境破败险恶……不只黑亮的家乡圪梁村如此,胡蝶的家乡营盘村也是如此,借此,《极花》试图表明这样与主流意识形态描绘的新农村蓝图相去甚远的图景绝不会只是个案。其次,乡村传统伦理趋于崩塌。作为圪梁村的主要经济来源,极花和血葱在商品市场的风行所借助的是过度包装、炒作等商业手段,而那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民间营销理念则慢慢被淘汰了。与此同时,经济利润刺激了欲望的膨胀和贪婪的滋长,遂而极花在疯狂的采挖中几近消失,血葱则日益稀释、离间着村民之间,甚至兄弟之间的感情。即是说,没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农村非但不是独立于商品经济大潮之外的桃花源,反而还在逐浪的过程中或主动或被动地丢失了传统乡村文明的精神内核。小说尾声,作为德孝仁爱等传统道德象征的葫芦的枯死更是显示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忧虑和悲观思考。最后,乡村权力结构的暗疮再次被披露出来。《极花》中的村长长期霸占着村里的多个寡妇,主观把控着村里的资源分配,参与人口拐卖并从中谋取高额抽成……不要说为农民谋福祉,村长甚至成为借权力之刀残忍屠宰农民利益的刽子手。应该说,在当代乡土小说中,这类村长的形象已基本构成了乡土中国权力网上的符号化存在,比如《耙耧山脉》(阎连科)、《蛙》(莫言)中的村干部即属于这一类型。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作家塑造人物的类型化倾向,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类村干部不只出现在圪梁村,也在耙耧山区、高密东北乡等农村事实存在着。综而观之,胡蝶所要逃离的农村即是如上所述的面目,它的土地上生长着的已非希望,而满是凄苦。因之,在被拐回农村之后,胡蝶仍不能放下对城市身份象征——高跟鞋的迷恋,她所心心念念的是“我要回去……我要回城市去”,而不是“我要回营盘村去”。
然而,被寄予无限希望的城市真的可以成为胡蝶们理想中的栖息地吗?贾平凹对此持明显的怀疑态度。于是我们看到,初到城市的胡蝶与妈妈不仅仍生活在局促破陋的出租房里,小心翼翼地省吃俭用,还要额外承受着城里人的鄙夷、俯瞰甚至侮辱……但胡蝶们坚信如是现状主要导源于农村身份与城市空间的格格不入,一旦取得了城市人的身份标签,她们也能顺理成章地分享城市的馨香与甘甜。为此,以各式各样的都市符号(普通话、小西装、染发、高跟鞋等)包装自己,继而遵循城市生存法则(努力挣钱)就成为她们自以为的获取城市身份的重要路径。然而,当胡蝶们怀揣期待地搭上通往美好幻梦的客运车时,她们却被以一种狡黠又讽刺的方式遣返回农村。就此,裹挟着商品经济属性和暴力色彩的“拐卖”成了作者透视城乡关系的重要管道。可以说,农村的事实寙败已基本成为一种显证: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农村无疑是掉队者,是被牺牲者,它们甚至以自己的衰败喂养了城市的肥大。在这里,城市与农村呈现出不可调和的对立矛盾,而“拐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一矛盾激化的产物之一。胡蝶们被物化作一种可供贩卖和争夺的资源,先是城市以异于农村的表相吸引她们主动地完成空间转移,随后又将她们包装成可供出售的商品,最后农村以购买的方式将她们抢夺回来。于农村而言,这既出于实际需要,也近乎于一种绝望且无效的反抗。当黑亮们愤恨又无奈地将全部积蓄作为跟城市争夺女性资源的筹码时,城市实际上又一次完成了对农村的剥夺。而在拐卖因其非法性受到严厉打击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或许还有某种遮蔽。即是说,当解救者(警察等)以正义、合法之名重新把胡蝶们带回城市,并将审判的矛头导向罪恶的人贩子,农村男性甚至整个农村的苦闷与焦虑复又很快地淡化出公众的视野。不惜以流血的方式野蛮地阻挡解救行动,这或许是农村所能做出的最无奈、最原始的反抗,也是它在这场社会悲剧中最后的、苍凉的退场姿势。它的儿子继续如荒花般等待着命运的终结,而它的女儿——胡蝶们即使在重新回到梦寐以求的城市后也终究寻不到一朵可供栖居的花,最终只能如梦似幻地飘荡于城乡之间。
有评论者指出,在《秦腔》中,贾平凹“建构起一种新的叙事伦理”,即在面对乡村急剧现代化的现状和未来趋向时,作者以“我不知道”的含混态度替换了早前相对明晰的价值判断。⑦在《极花》的后记中,贾平凹讲述了自己到一些偏远村庄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历,面对光棍的哭诉: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消亡了,他无言以对。笔者认为,贾平凹的“无言以对”不但是因为他深知在如此巨大的悲怆面前言语安慰将是多么苍白无力,或许更基于对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向的理性认知:现代化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农村以及农民的彻底消失。于是,《极花》里,尽管哀伤的挽歌情调无处不在,尽管控诉的欲念甚至有些急不可耐,但是纠葛于现代理性与个人感性之间的贾平凹显然不是要在热情拥抱城市化和退回传统乡村之间作出简单明了的选择,他更关心的是人,尤其是饱经风霜的农村人,如何在处于转型阵痛期的中国安身立命的问题。透过胡蝶于城乡之间或主动或被动的辗转流离,贾平凹将一个田园将芜、都市未臻成熟的当代中国推至前景,其中游荡着的是不知何处是吾乡的苦命人,抑或无论是何处,都无甚差别?于是,当自认已是城里人的胡蝶喊叫着农村不是自己该呆的地方,黑亮回答道,“待在哪儿还不都是中国”;当胡蝶认为自己的星星只有在城市里才能看到,老老爷反问道,“在哪里还不都是在星下啊”;而于城乡之间完成数度空间流转的胡蝶最终也意识到“在中国哪儿都一样”……在这里,中国已然是一个混沌一体的生存场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无法成为胡蝶们、黑亮们栖身的安全地带。故事结尾,贾平凹驾轻就熟地以亦虚亦实的写作技法安排了胡蝶的归宿——在似梦非梦中回到了都市,又如剪纸般地粘在了农村的窑壁上,其所传达的不只是许多中国人的迷惘心境,还有同样“不知道”的作者的悬搁立场。
实与虚之间
承上所述,一个恍兮惚兮的情节被用来为《极花》作结,除承担着传达主旨意蕴的功能外,它还彰显了贾平凹一直以来的审美追求,即突破严格的写实框架,竭力将清明与神秘熔于一炉。这不单是受西方文学创作思潮影响的结果,更是因为“贾平凹在古老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长久修炼已经‘得道成仙’,因此构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感知世界的方式”⑧。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太白山记》《烟》,到上世纪90年代《废都》《白夜》《高老庄》,再到新世纪以来的《怀念狼》《秦腔》《古炉》等,虚实相生、亦幻亦真可谓是这些作品共有的审美面相之一。不得不指出的是,随着创作时间的推演,贾平凹处理虚与实的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太白山记》基本可看作中国传统志怪小说的当代延伸,《废都》《白夜》在借“哲学牛”、再生人的钥匙等局部意象传达神秘感的同时,也透过“废都”“白夜”这样的核心意象生发多义性,《怀念狼》意在“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⑨,《秦腔》之后的作品不仅以密实的流年式叙述呈现生活“混沌又鲜活”的自我流程,还大多择取了颇富神秘色彩的叙述人(如,引生、狗尿苔、唱师等)……而《极花》则试图一面极尽写实之能事,一面借有意构建的意象群营造虚幻的意境,进而在实与虚之间觅得一种风格上的平衡。
可以说,贾平凹摹写日常经验,雕刻生活细节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比如,《白夜》中,纠葛于欲望与理性之间的市井细民的百态生活就得到了如同影像般的呈现,《秦腔》更是事无巨细地将乡土世界中的鸡零狗碎都转化成文字。而《极花》尽管被作者称为“最短的一个长篇”,但它反而以更密实的文字构筑起愈显实在,甚至可触的日常空间。言称小说是不需要技巧的“说话”的贾平凹以一个被拐卖女人的“唠叨”结构起《极花》的故事,于是胡蝶的说话,包括控诉、对话、自言自语、所思所感所想等,无一不是《极花》铺展开去的重要凭借。与此同时,作者试图赋予胡蝶充分的话语权,即将部分掌控小说走向的权力让渡给叙述者,进而让讲述以近乎原生态的方式流淌出来。因而,日子不再被一笔带过或服膺于理念的拆分重组,而是还原成无数随时间自然流淌的琐屑细事:三时三餐中一蔬一饭的滋味,村民之间狡黠也温情的交际日常,总是披着大衣的村长在村里的来来回回……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胡蝶以“我学会了……”的句式开启的多段自陈自述,在这里,贾平凹不吝笔墨地将饲弄鸡、做搅团、做荞面饸饹、做土豆、骑毛驴、采茵陈、做草鞋等农村生存技能细致地刻写出来,这不但部分地返还了日常生活所内含的文学审美意义,也在对细节的铺排中折射了胡蝶不无矛盾的情感态度,而如此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自然是以作者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作为支撑的。即使在入城多年之后,贾平凹也没有完全褪去农村的烙印,甚至依旧以农民自居,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身份认同,其提供给作者的也不单是上述写作素材,还有一种部分疏离于现代理性的原始思维方式。因而,《极花》还将一些被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排除在外的质素呈现出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其自足的存在意义。例如,鬼魅精怪的幻影,预示风水、吉凶的白皮松和乌鸦,麻子婶的离奇经历(在槐树下怀孕、“死”而复生等),带有神秘色彩的民间禁忌、传说和习俗等等。对此,贾平凹曾指出自己并不是像马尔克斯那样硬在作品中来些魔幻,出现在他作品中的神秘现象都是他“现实生活中接触过,都是社会中存在的东西”⑩。应该说,当贾平凹以一种“确信其有”的心态记录“鲜活又混沌”的日常生活时,其已为读者带来了一种虚实难辨的阅读感受。
当然,《极花》之虚更多地来自于那些作者有意遴选、创造的意象,例如红狐狸、极花、血葱、星野、老老爷、离魂和梦境等,它们并不是散金碎玉般的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基本都暗合于作者想要传达的隐含意蕴,进而被组织进一个系统的意象群。如果说包括红狐狸在内的诸多已然消失的野物在文本中的复又出现、极花与血葱的功能与消长显示了乡土中国原始性、神秘性的一面,那么对老老爷和星野的浓墨涂抹则象征着古老化中国的当代遗存。即是说,虽然现代文明已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对乡土世界的渗透,但是农村以及农村传统仍未彻底走入历史。《极花》中的老老爷无疑是类似于傅山(《怀念狼》)和宽哥(《白夜》)那样的人物意象,其象征着的是一种将逝未逝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他承续传统,斥责“忘八谈”现象,每年的二月二都坚持给村民拴彩花绳儿;他相信宿命,认为分星和分野的对照关系决定了人生活的地域,坟里呼出的气则决定了人最终的归宿;他惧鬼敬神,当村子里连连发生怪事时,他主张通过搭台唱戏祈求神的保佑……应该说,自五四以来,现代理性就一直将改变上述情状视作启蒙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在将近百年之后,它们仍脆弱又顽强地遗存在中国的大地上。因之,现代文明的驶入与其说是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不如说是撕裂了当下的中国:中国俨然成为一个对立物的遭遇之地,极落后与极先进、极古老与极现代生长在同一块土地上。遂而,离魂和梦境两个意象的设置就更多地出于审视撕裂之中国的需要,作者不仅借此获得了更恰切便利的叙述视角,也能更有效地抵达虚实相生的美学境界。《极花》多次叙述了胡蝶的魂魄离开身体的经历,通过细读可以发现,这基本都发生在胡蝶罹难之际:逃跑被抓、被强暴、难产……每当暴力靠近,胡蝶就会分裂成两个人——处于暴力中心的胡蝶(身体)旋即失去话语权,处于暴力外围的“我”(魂魄)随之承担起叙事的职责。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引生(《秦腔》)式的叙述人,讲述由此不再受限于第一人称的限制性视角。比如,在胡蝶难产之际,作者就借离魂的“眼睛”呈现了依然流行于民间的古老落后的接生方法。而当村民们极其粗暴地抓回逃跑的胡蝶,野蛮甚至亢奋地扯掉胡蝶的衣服并将其捆绑在条凳上以帮助黑亮完成强暴,作为叙述者的离魂不只看到了女性受难的身体和毫无尊严可言的存在境遇,更披露了乡村世界粗鄙、非理性的一面。不论这是人性中蛰伏已久的恶魔性的迸发,还是矛盾激化的恶果,其在当下中国的事实存在才是作者所要着重凸显的方面。与之类似,梦境意象的设置同样带来了更加自由的叙述视阈,借此,被囚禁的胡蝶讲述了更驳杂、开阔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故事结尾处,那个以亦幻亦真的方式呈现而出的解救与阻挡解救的暴力场面同样是撕裂之中国的重要表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不管设置了怎样虚幻的意象,作者都竭力以实笔,以丰满的细节描写之,其意图在于以实写虚,而如此虚虚实实的笔法或许也可视作当下暧昧、混沌之中国的一种隐喻。
综而观之,《极花》可谓较为鲜明地显示了贾平凹的悬搁立场:在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他在一定程度上延宕了道德审判的到来,着力剖析人性的动荡与驳杂;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他既不遗余力地披露前者的恶,又毫不避讳地撕下后者的画皮,进而凸显出无处安身立命的人的苦痛;在实与虚之间,他一方面以密实、丰满的细节铺述生活固有的自我流程,另一方面借相对系统的意象群营造虚幻的意境,以求通过两者之间的平衡互动,生发深层意蕴。笔者认为,正是这一立场的择取使《极花》在很大程度上跳脱出相关题材的既有叙事框架,并拓展出相对新鲜、深度的表现空间。当然,《极花》并不完美,必要的批判性、反思性的阙如,以及过于絮叨、不加节制的语言等都是其不能被忽视的写作遗憾。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①吕频《贾平凹为拐卖媳妇辩护,何其荒唐》[N],《新京报》,2016年5月9日。
②张知依《贾平凹:我想写最偏远的农村与最隐秘的心态》[N],《北京青年报》,2016年4月16日。
③毛亚楠《贾平凹:〈极花〉不仅仅是拐卖与解救的故事》[J],《方圆》,2016年第6期。
④这是《盲山》海外版本的结局。而在内地公映版中,这一情节被删掉了,故事以警察对白雪梅的成功解救画上句点。
⑤⑥贾平凹《〈极花〉后记》[J],《东吴学术》,2016年第1期。
⑦谢有顺《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J],《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
⑧旷新年《从〈废都〉到〈白夜〉》[J],《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
⑨贾平凹《怀念狼·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⑩贾平凹、张英《地域文化与创作:继承与创新——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谈话》[J],《作家》,199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