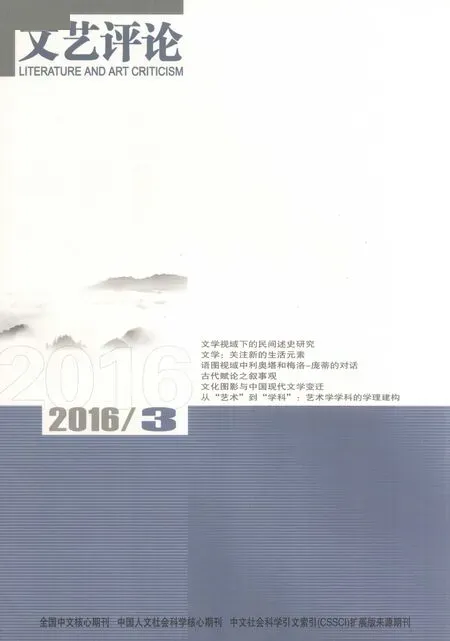语图视域中利奥塔和梅洛-庞蒂的对话
2016-09-28吴天天
○吴天天
语图视域中利奥塔和梅洛-庞蒂的对话
○吴天天
虽然利奥塔在《话语,图形》(1971)一书中的语图(语言和绘画)观与梅洛-庞蒂有冲突,但该书发表15年后利奥塔仍强调自己在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方面是“梅洛-庞蒂的追随者”①。大卫·卡罗尔指出:“自梅洛-庞蒂以来,可能没有哲学家像利奥塔那样用艺术提供对一般话语的批判性视角的方式关注绘画和批判性话语的联系和或非-联系问题。”②利奥塔和梅洛-庞蒂都把对反思哲学(意识哲学、主体哲学)的批判和对语言的批判及对绘画的借鉴相结合,但梅洛-庞蒂作为现象学家试图在现象学之内超越反思哲学,利奥塔作为后结构主义者则试图在现象学之外超越反思哲学。
梅洛-庞蒂中后期致力于在结构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将索绪尔语言学吸收进身体现象学中,而到了利奥塔写作《话语,图形》的年代,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融合被证明困难重重,且解构主义开始对现象学和结构主义形成冲击。比尔·瑞丁斯就利奥塔和解构主义的关系指出,利奥塔意义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比德里达的要宽泛——至少就后者的早期著作来说是如此,“对德里达来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问题内在于语言表象考虑自身和世界的方式中,这是一种通过类比作用于其他领域的在场形而上学,正如我们会说到‘可见者的语言’。对利奥塔来说,伴随着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梦想,语言类比的规则本身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③。德里达在语言内部区分了语音和文字,但并未对语言以类比的方式作用于非语言领域这种思维方式进行质疑,利奥塔则指出语言向其他领域的扩张本身就可能成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温床,在此意义上“写下来的言语和说出来的言语的情况差不多”④。利奥塔试图抵制结构主义以来符号学被吞并到语言学之中的倾向,而正是“在语言之外审视语言”这一梅洛-庞蒂式的思考方式使利奥塔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解构主义者。
虽然被称为“绘画哲学家”,梅洛-庞蒂却经常将文学和绘画并举。他并非用绘画反对文学,也并不认为所有的绘画都对语言理性主义有批判作用。对利奥塔来说同样如此。为对抗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的语言理性主义,利奥塔在《话语,图形》一书中提出了“图形(figure)”理论,对图形以及与图形相对的“话语(discourse)”的定义依据的并不是艺术种类(绘画、文学等)而是艺术特征和思想特征。图形理论的提出虽然得益于绘画,却并非所有绘画都具有图形性;话语的特征虽然从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归纳而来,但并非所有语言都具有话语性。
一、笛卡尔和话语
在《话语,图形》中,话语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虽然结构主义的兴起动摇了笛卡尔以来的反思哲学,二者在思维方式上却具有同源性,即都具有话语特征。利奥塔和梅洛-庞蒂都试图超越结构主义和反思哲学,但他们的思想路径不尽一致。
结构主义将语言视为按照区分原则组织起来的分节语系统,并将差异转化为了系统中的对立。差异意味着a不是b,无论二者在多大程度上不同;当a和b被纳入语言系统中后,受到关注的只是二者在比较中产生表意能力的那部分区分性,差异因而变成对立。在将差异转变为对立的过程中,结构主义压抑了不可被纳入语言系统的被指称者或者说参照对象。本维尼斯特就索绪尔语言学指出,语言活动涉及两种关系: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的关系,以及语言符号整体与言说对象(言说者所针对的现实或非现实的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第一种关系是符号固有的,第二种则超越符号。⑤利奥塔对此分析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⑥,本维尼斯特则将指称关系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中分离出来,以便“证明只有它才称得上是任意的或无理据的,而意思(signification,取决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引者)却如此不具有任意性或无理据性,以至于我们无法在没有它的‘说法’的情况下构想概念,在没有‘它想说的内容’的情况下构想词语”⑦。能指和所指的区分是理性的抽象化作用的结果,话语混淆所指和被指称者并将后者作为所指纳入语言系统中,这种将他者的差异纳入语言内部的对立系统的作法正是笛卡尔以来的反思哲学的特征。
笛卡尔的《屈光学》一书认为,语言之于参照对象的任意性也是绘画所应具有的特征。他以铜版画为例解释说,铜版画让我们联想到事物的大量不同属性,但这些属性不与铜版画相似,即使有形状上的相似,也必须根据在平面上表现立体事物的需要使事物按照透视规律在平面上发生变形。⑧对他来说,绘画的目的不是与事物相似而是刺激思想去构想,而只有“以物作词”才能使绘画像语言那样成为思想的轻便工具。
梅洛-庞蒂后期在《眼与心》一书中就笛卡尔的绘画观指出,“对于一种不再想栖居于可见者中,而是按照思想模式来重构可见者的思想来说,《屈光学》是‘必备书’”⑨。早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梅洛-庞蒂就试图通过将语言视为一种身体动作(gesture)来避免对知觉世界(可见者)的忽视。语言动作所表明的是说话的主体在言说时无需对所要表达的思想进行专题性把握,而只需诉诸于自己的意指意向(身体意向性的一种)。笛卡尔的我思需要借助语言,而他将语言视为思想的表象的作法导致“表达在被表达的东西面前消失”⑩。梅洛-庞蒂将笛卡尔意义上的语言视为“被表达的言语”,即已形成的、我们可以像支配已获得的财富那样对其进行支配的言语,思想和表达在其中是分离的。与此相反,“表达的言语”作为语言动作是意指意向处于初始状态的言语,思想和表达在其中是合一的。将被表达的言语还原到表达的言语表明,梅洛-庞蒂用“我能”的主体代替了“我思”的主体。在他中期的言语现象学中,能指被认为具有“拟躯体性”,语言学区分原则被认为可以证明意义产生于语言自身的区分化动作中,而非产生于语言对思想的表象。在他后期的肉身(Flesh)现象学中,语言动作所表明的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联被视为一种交错(Chiasm)或者说可逆性。
很多学者对梅洛-庞蒂融合现象学与结构主义的作法表示怀疑。例如福柯指出,现象学主体无法像结构主义那样解释意义的产生方式。保罗·利科认为,在梅洛-庞蒂的言语现象学中,“作为自主系统的语言之观念未曾被考虑”。利科将符号系统和意指意向视为两个需要被分开的层次,并借助了本维尼斯特对主体在语言系统中的在场方式的说明。本维尼斯特认为“主体性的基础正在于语言的运用”,他用人称代词“我”为例解释说:“语言就是这样组织的,它能使每个说话者都能在自称为我的同时将全部语言占为己有。”
在利奥塔看来,语言动作被赋予的重要性使梅洛-庞蒂忽视了语言系统不仅区别于意识主体,也区别于身体主体,因此将语言视为动作的作法是将语言视为语言所不是者。和利科相似,利奥塔将语言系统和意指意向视为语言活动的两个不同维度:言说者的能动性使语言系统的不变间隔发生改变,但言说需要以系统的不变间隔为前提。利奥塔不认为无主体、无意识的语言系统本身可以被视为语言动作:“系统永远是已然存在,而被假设创造出意思的言语动作永远不可能在它的进行构造的功能(constituting function)上被把握,它总是并只可能以解构的形式被把握。”语言动作和语言系统的结合方式不是前者构造后者,而是前者解构后者。前一种结合方式走向二者的同一,后一种结合方式见证二者的差异。
比尔·瑞丁斯指出:“利奥塔和德里达之间虽然有分歧,但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即维护差异的根本独特性而反对形而上学的同一逻辑,这种同一逻辑将差异仅仅视为对立。”对德里达来说,解构只能在结构内部进行,正如对利奥塔来说,图形不是话语的对立面而是对话语的违犯。解构主义式的思考方式使利奥塔不仅像梅洛-庞蒂那样注意到笛卡尔的视觉是“几何之眼”意义上的清晰视觉,还注意到“在笛卡尔那里同样也存在着相反的思想过程”。利奥塔结合笛卡尔的《方法论》一书指出,笛卡尔很清楚“变形图像是视场的构成要素,并且一个‘正确’视点的理性只有以在原则上忽略这一边缘的扭曲、这一儿童时代、这一事件为代价才可能被构成”。笛卡尔并非没有意识到变形图像的存在,而是试图通过方法论上的约定压抑变形图像。笛卡尔意义上的绘画是种话语,而变形图像是作为话语之他者的图形。因此,“恰恰是在关于知性活动的理论本身之中,可见者所特有的性质即差异,得以重现。图形虽然被话语所压抑,但图形就在话语之中。
二、塞尚和被动性
话语在将差异归为对立的过程中将他者归为同一,图形则因为捍卫差异和事件而向他者敞开。图形真理观用尼采的话说是“真理随鸽子悄然而至”,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是“真理从不出现于它被期待的地方”。在利奥塔看来,为得到这种真理,需要将意识的构成作用代之以弗洛伊德所说的“自由联想”(被解析者)和“均匀流动的注意力”(解析者)。利奥塔重视梅洛-庞蒂用被动性抵抗意向性的原因正在于此。但在围绕“现代绘画之父”塞尚对被动性进行的阐释中,再次显示出他们二人目标的相通和方法的分歧。
塞尚的被动性体现在他所说的“风景通过我思考,我是风景的意识”中。梅洛-庞蒂前期在《塞尚的疑惑》一文中指出:“塞尚所画的人物很奇特,如同是另一种生物所看到的样子。自然本身被剥去了为万物有灵论所准备的那些特征:风景无风,阿奈西湖不动;被冻僵之物栖居于创世之初的世界中。”在梅洛-庞蒂看来,这是由于塞尚的绘画“悬置了思想的惯习,揭示出人们寄居其中的非人类自然的底蕴”。对于塞尚像“画物体一样”画人脸,梅洛-庞蒂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塞尚将脸和脸的“思想”剥离开来,而是说思想不能和视觉行为相分离。根据梅洛-庞蒂的解释,塞尚的疑惑源于人类在将沉默的知觉世界引向表达时所感到的困难,只有用对自然的倾心聆听取代意识的构成作用才能体会到这种困难,而这种困难启发人们寻求语言动作所表明的那种思想和表达的统一。
在梅洛-庞蒂后期的肉身理论中,塞尚的被动性具有了本体论意义。“肉身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不是实体”,而是“存在的‘元素’”。人在自我触摸的过程中既是触摸者又是被触摸者,主客体的这种交错或者说可逆性是肉身所具有的特征。通过指出世界和身体一样是由肉身构成的,梅洛-庞蒂将知觉现象学中的己身(proper body)扩展到了世界的肉身。在他看来,正是肉身可以解释塞尚所说的“自然在我们内部”和克利等人所感到的被树木注视。利奥塔将梅洛-庞蒂在《眼与心》中指出的这种思想所具有的“被动性的神秘”归结为“身体与物体的某种默契”。
然而在利奥塔看来,梅洛-庞蒂所理解的被动性是知觉综合的被动性,这一在胡塞尔那里就已有所描述的被动性“仍然只有在现象学所建立的领域中才行得通——作为意向性活动的对立面或相关方,作为其支托层”,“这一被动性因而还是被设想为进行瞄向的主体所作的假设,被设想为一种被预设于主体与对象的超越关系之中的固有性,主体从某种意义上在其中被废黜、被剥夺权力,但他同样也在其中被确立”。对利奥塔来说,从意识哲学的“我”过渡到知觉意义上匿名的“人们(One)”并不能实现对意识哲学的真正超越。
德贡布也认为,把从主体到匿名主体的转换视为对主体的超越是匆忙和错误的。但德贡布并未过多提及梅洛-庞蒂后期的作品。事实上,梅洛-庞蒂后期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书中也承认《知觉现象学》停留在意识哲学中。但何以利奥塔认为梅洛-庞蒂后期的肉身理论没能从根本上超越知觉现象学呢?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利奥塔从梅洛-庞蒂的肉身理论中看到了对身体和世界之间的原始和谐的假设,而这种假设在知觉现象学中就已存在。在利奥塔看来,梅洛-庞蒂所说的交错和杜夫海纳所说的共本性(connaturality)一样,都追求身体与世界关系上的连续性,以及表达和世界关系上的连续性,而连续性是主体将他者作为他者所不是者纳入自身时的思维特征。
利奥塔对被动性的论述主要围绕塞尚后期以圣维克多山为主题创作的绘画作品展开。塞尚后期创作中用“调节(modulate)”法取代“塑形(model)”法,罗杰·弗莱对此指出,“调节”意味着“追随着自然物象在深度空间中的色调变化的暗示”。就该时期塞尚整体的创作风格,罗杰·弗莱评论说:“我们在这个最后阶段发现了一种想要打破体积,几乎想要拒绝接受每个对象的统一性,以及想要让各个平面在绘画空间中更为自由地运动的倾向。”利奥塔从塞尚后期作品中看到的是对几何光学的违犯。在他看来,塞尚的圣维克多山绘画所达到的效果需要靠“不动的能动性”对理性化的排斥才能得到。这里的“不动的能动性”不是透视法所要求的不动性,而是塞尚在绘画中使物体“变形”这一现象中所蕴含的不动性。根据巴尔和弗罗贡在《曲线透视法》一书中的研究,“长方形只有在我们正对它表面中心的纵轴并离开无穷远来看它时,才可能不产生扭曲”,而教育和习惯促使“我们的眼睛和大脑矫正扭曲”。利奥塔据此指出,在注意力的识别目的作用下,视线在各处游走以构造熟悉的画面,“通过这番由对视场的扫视和视觉器官的调节所同时构成的行程,每个组成部分都轮流被置于焦点,被认同为中央视觉,并与其他组成部分一起被排列在一个彻头彻尾的知性构造中,这一构造是欧几里得式的”。笛卡尔所主张的将绘画元素的任意性与此相似,都使视觉对象被建构为话语。
其实,梅洛-庞蒂在对塞尚作品的分析中已经将“变形”现象视为主体的被动性的产物了。利奥塔不同于梅洛-庞蒂之处不在于是否主张被动性,而在于对被动性的来源的解释。
利奥塔承认,梅洛-庞蒂并未通过对立将“此处”和“别处”并列于一个平面化的空间中,因为对于“活的眼(living eye)”来说,“此处”和“别处”的关系主要被设想为格式塔中的图-底结构,“别处、事物的背面、它的不在场,在其正面、在其在场中被给出”。但利奥塔认为图-底结构形成的深度是符合规则的,“视觉的格式塔本身是某种二次理性化的成果;在事物根据‘好的形式’被秩序化之前,被给予者呈现于光晕、叠印和扭曲效果之中,眼的运动将以消除它们为结果”。在利奥塔看来,图形性空间的差异“比格式塔主义构造中‘提供’事物另一面的不可见性的那种间隔更矛盾,同时也更原始,它是介于视场边缘及其焦点之间的无法把握的距离”。在停止眼睛的识别作用后,图形出现于视网膜中央凹区形成的清晰视觉边缘的弯曲空间中。图形所包含的差异不是系统中的对立,也不是在场不在场的对立,而是不对等不可逆的事物以解构的方式在同一空间中并置。
三、克利和超反思
梅洛-庞蒂和利奥塔共同关注的另一位画家是克利,他们都将克利视为继塞尚之后致力于超越摹仿论的现代画家之一。克利认为,绘画的职责不是摹仿可见者,而是让不可见者变得可见。这里所说的不可见者不同于笛卡尔绘画观中由意识的构成作用带来的不可见者,相反恰恰是对这种构成作用的超越。梅洛-庞蒂和利奥塔从克利的绘画观中看到了超越反思哲学的可能,并对“超反思(hyper-reflection)”作出了各自的解释。
“超反思”这一概念出现于梅洛-庞蒂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书中。与反思不同,超反思“同时会考虑它自身和它给场景带来的那些变化,它因而不会无视原始之物和原始知觉并最终消除它们”。超反思需要语言“将世界的超越性作为超越性来思考,不是根据已给定语言固有的词语意思的法则来说出这一超越性,而是当事物尚未被说出的时候,通过一种或许艰难的努力来使词语表达超越它们自身的,我们与事物之间的沉默接触。”超反思努力让反思说出自身所不是者——身体和世界,这种言说方式在语言动作理论中已有所体现,并被梅洛-庞蒂吸收进肉身理论中。
在梅洛-庞蒂对超反思的理解中,绘画不再像摹仿论中那样被视为与实物近似的物体或与实物不同的幻象,而是被视为在交错中实现的对“普遍存在(universal Being)的无概念式表达”。他引用克罗岱尔的话说“海的某种蓝色是那样的蓝,以至于只有血才是更红的”,并指出这表明颜色是“同时性和连续性网状结构中的某种交叉点”。唐纳德·兰德斯指出:“这种关于某个特定颜色的感知的描述包含了梅洛-庞蒂从索绪尔那里获得的结构洞见。”颜色的意义出现于颜色与颜色的区分中,并通过这种区分与颜色的整体相联系。这个意义上的区分即是交错。
梅洛-庞蒂从克利借颜色和线条对不可见者的表现中看到了个别与普遍的结合方式,这种结合方式不同于形而上学。笛卡尔认为素描优于颜色并将颜色仅仅作为装饰,而克利则将颜色视为“我们的心灵和宇宙的交汇地”。只有不再将颜色仅仅视为颜色-表壳,我们才能接近克利所说的“事物的心脏”。梅洛-庞蒂举例说,塞尚的《瓦利埃肖像》“在颜色之间安置了一些空白空间,这些空白空间具有使一种比黄色-存在,绿色-存在或蓝色-存在更一般的存在成形和显现的功能”。这些空白空间作为颜色的交错之地是对不可见的普遍存在的表达。约翰·塞里斯将梅洛-庞蒂对不可见者的理解和海德格尔对真理的理解联系起来:“人们可能会说,不可见者是赋予可见物以真理的东西,是赋予可见物从去蔽中涌现的可能性的东西。克利不仅使颜色通向真理,还解放了线条。对他来说,绘画的线条不是自在物体的实际属性,例如代表苹果的轮廓或田地与牧场之间的界限,而是既不属于事物又被事物所暗示:“线条不再摹仿可见者,它‘导致可见’,它是描绘事物之诞生的蓝图。”在此意义上,绘画仿佛不是被创作出来,而是自己形成的。克利“让线条自己言说自己”,正如他的颜色“有时似乎是缓缓诞生于画布上”。无论人们是注视线条还是颜色,它们都要么不及要么超出人们的注视点,因为它们同时驻留于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
利奥塔从梅洛-庞蒂的超反思中得到的最大启示,是在语言之中实现对语言的超越,而这正是图形的特征。现象学的身体能动性将可变性引入语言系统的不变性,利奥塔将此视为将“见”引入“说”(这一过程使语言的二维平面具有了造型深度),并把“见”和语言的参照对象联系起来。参照对象是言说者在言说时必然指向的东西,它被结构主义者所忽视,但在话语的地平线处影影绰绰地显现着,既是话语排斥的对象又是话语依赖的对象。参照对象成为图形的一种,即图形-图像。
然而,利奥塔在对超反思的理解方面最终偏离了梅洛-庞蒂,这主要是因为他看到了现象学身体的“人们(One)”和力比多身体的“本我”之间的差距。在利奥塔看来,现象学身体掩盖的是力比多身体,后者不遵从共本性原则以及知觉空间的方向,真正可以超越反思的不是现象学身体而是力比多身体:“解构的能量不仅仅处于不到逻各斯的程度,而且处于不到现实世界或知觉世界的程度。”力比多身体遵从快乐原则,属于原发过程;现象学身体遵从现实原则,属于继发过程。利奥塔进一步认为,话语和图形-图像(参照对象)的关系是欲望和欲望对象的关系(欲望对欲望对象的否定恰恰证实了欲望对象的存在),身体对语言系统的解构是无意识在梦的工作(凝缩、移置等)中的显现以及快乐原则对现实原则的违犯,解构在结构中的操作意味着欲望不以话语的方式言说,而是扰乱话语的秩序。
利奥塔认为超反思的真正基础是力比多身体或者说欲望,他对图形的分类正是依据欲望和图形的结合方式进行的。这种结合按照可见性标准可以分三种:被看见(图形-图像),不被看见的可见(图形-形式),不可见(图形-母型)。在图形-图像层面,欲望解构被感知事物的外形轮廓;在图形-形式层面,欲望违犯“好的形式”(格式塔);在图形-母型层面,欲望既解构图像又解构形式。母型孕育图像和形式,但母型作为“差异本身”既不可被纳入“说”也不可被纳入“见”,我们从母型中发现的不是“起源”而是“起源的缺失”。
虽然利奥塔对图形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借助了绘画,但图形并不与绘画同广延,因为绘画也可能因为对几何光学的遵守等原因而成为话语。图形也可能出现在语言中,例如本维尼斯特曾指出“无意识使用一种如同文体一样拥有‘辞格’的真正的‘修辞’”,而瑞丁斯在其《介绍利奥塔:艺术和政治》一书中也直接将图形和修辞相联系。此外,利奥塔强调,图形和话语的衔接不可能仅仅围绕图像(image)展开,因为在图形艺术观中,作品的价值不是通过形象制造的梦幻世界来让人们“实现欲望”,而是让人们如同在清醒时看梦那样“不实现欲望”,亦即见证欲望如何既被现实原则所拦截又成为暴露原发过程的作坊。作品不是梦想(梦想可能意味着昏睡),而是以解构的方式让欲望和无意识变得可见。
克利的绘画创作和绘画理论让利奥塔看到的,不仅是无意识、能量、性别隐喻等弗洛伊德式主题,更是“既超越现实世界又超越想象世界”的“间世界。克利曾说:“我称之为间世界,因为我感觉到它出现于那些能够被我们的感官从外部觉察到的世界之间,因为我能够将它吸收于内部,直到足以将它以象征的形式投射于我之外。”他提到了间世界的一种创造方式:(1)严格按照自然来画,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借助望远镜;(2)上下颠倒这幅素描,按照感受突出主要线条;(3)将纸重新放到原位,并使(1)中的画(自然)和(2)中第一次被颠倒的画相协调。利奥塔认为,(1)提供可见者,(2)提供“满足欲望”意义上的不可见者,而(3)提供真正的艺术创作所追求的不可见者。利奥塔就此指出,作品中存在一种“摇摆不定”:“在作品本身之中存在着一种介于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之间,更确切些说介于‘话语’(普遍地说,可辨认的文字)世界和图形世界之间的来与往。”间世界不仅体现出超反思的特征——图形对话语的解构,还揭示出超反思意义上的艺术功能,即不是让人略掉玻璃窗去看窗外的景物,而是让人清醒地看到玻璃窗本身。借助超反思,利奥塔回应了阿多诺对奥斯维辛之后的艺术的疑虑,并抑制了马尔库塞所批判的“文化的肯定性质”。
对利奥塔来说,超反思和被动性一样都是对话语的超越。正如他从塞尚所画的圣维克多山看到了被动性,他也从中看到了超反思。面对塞尚绘画中带有变形、侵越、模棱两可的圣维克多山,利奥塔觉得就好像画家将观者“置于眼睛的入口并使我们看见被假定发生于观看着圣维克多山的视网膜上所发生的东西,因而使我们看见什么是‘见’”。不可见者正是“见”本身,而见到“见”本身要以被动性为前提:“既然在这一假设中观众被置于对象的位置上,那么情况就好像是山通过一个瞳孔看着它自己的视网膜成像。”在利奥塔看来,“正是当克利追求绘画中的复调或者说追求不同视点的同时性,当他追求间世界的时候,他离塞尚最近”。
在利奥塔这里,被动性是力比多身体相对于意识的主动性而言所处的状态,超反思体现出的是与欲望具有默契的图形对话语的解构。但本宁顿指出:“《话语,图形》的论点似乎比它所寻求的精神分析基础更为有力。”如果我们考虑到利奥塔与梅洛-庞蒂的对话以及他们二人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史的批判的话,本宁顿的这一观点就较易理解了。
四、余论:对话以及错位的对话
图形理论作为利奥塔的后现代思想重要的策源地,体现出重视他者、差异、事件、感性以及创新等价值诉求。当利奥塔从后结构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与梅洛-庞蒂现象学进行对话时,既可能产生洞见,也可能产生偏见。
狄龙(M.C.Dillon)的《梅洛-庞蒂的本体论》一书在谈到利科对梅洛-庞蒂语言观的批判时指出,利科忽视了梅洛-庞蒂后期的语言观。盖伦(Galen A.Johnson)同样指出,利奥塔误解了梅洛-庞蒂后期对差异的理解。利奥塔在对梅洛-庞蒂的理解方面确实对后者不同时期之间的“断裂”重视不够。例如,他忽视了梅洛-庞蒂的肉身理论在吸收语言动作理论的同时,又通过指出沉默的知觉世界不是语言的“原文”、语言不与知觉世界“重合”而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语言动作理论。又如,梅洛-庞蒂后期从肉身的交错性出发对深度的理解不同于利奥塔所看到的格式塔理论中图-底结构形成的深度。
利奥塔与梅洛-庞蒂在对话时产生的龃龉和学术界在梅洛-庞蒂研究上所面临的难题也有关系。梅洛-庞蒂不同时期的思想之间是否发生过根本断裂?若没有,那么他后期的肉身理论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前期的意识哲学倾向?这些问题之所以难以解答,不仅和梅洛-庞蒂思想在各时期的变化有关,也和他同一时期的思想所具有的张力有关。梅洛-庞蒂遗稿的编者勒弗尔就曾指出,肉身的可逆性和他者的不可还原性处于紧张状态。鹫田清一的《梅洛-庞蒂:可逆性》一书和詹姆斯·施密特的《梅洛-庞蒂:现象学与结构主义之间》一书也指出了类似的紧张状态。对近年梅洛-庞蒂研究在法国的复兴起到关键作用的巴尔巴拉更是认为,在从身体本身(proper body)向世界的肉身的过渡中,梅洛-庞蒂“禁止考察进行感知的、主动的这个极点,并最终重新承认了我的肉身相对于世界之肉身的特殊性”。巴尔巴拉和利奥塔一样也得出了梅洛-庞蒂并未真正超越意识哲学这一结论。总之,对梅洛-庞蒂研究来说,利奥塔的图形理论展现出的道路既以其经验又以其教训给人们以启示。
②David Carroll,Paraesthetics:Foucault,Lyotard,Derrida[M],New York and London:Methuen,1987.p.30.
⑥[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2页。
⑩[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02-503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