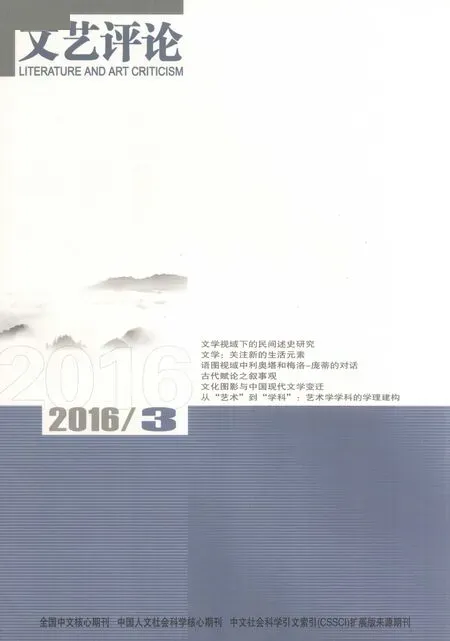童年经验与“60年代出生作家”小说中的叙述策略
2016-09-28○宋雯
○宋 雯
童年经验与“60年代出生作家”小说中的叙述策略
○宋雯
童年经验作为先在意向结构的奠基物,不但影响了作家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的形成,还影响了作家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追求及题材选择,作家的叙述策略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尤其对于那些在童年时期有过深刻情绪体验,精神兴奋点总是停留在人生早期所处的那个狂热喧嚣、混乱无序的时代,喜欢从童年经验中寻找创作资源的“60年代出生作家”来说,叙述策略的选择更是和他们的童年经验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儿童视角的运用
关于儿童视角的定义不止一个,不过虽然这些定义在表述上有所差别,但内容大致相同,即都认为“儿童视角”是指作家以儿童的眼睛和心灵去观察、体味人世百态。通常来说,成人作者选择了儿童视角,“借助儿童的思维方式进入叙事的话语系统时,并不以对儿童世界的描摹和建构作为自己的审美追求,而是要将儿童感觉中别致的成人世界挖掘和呈现出来”①。
儿童视角是“60年代出生作家”格外偏爱的一个叙述视角,如在苏童的创作生涯中,从早期的《桑园留念》,中期的《我的帝王生涯》,再到近期的《河岸》,我们都能看到贯穿其中的儿童视角,只不过有的是整篇应用,有的是局部应用。尤其在苏童的全部小说中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的“香椿树街”系列,大部分都采用了儿童视角的叙述视点。在这些作品中,苏童以自己苏州城北故乡的某条街为主轴,以少年儿童为叙述人,讲述了发生在这条街上的少年故事或成人故事,讲述了他眼中这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些故事都是苏童所珍爱的,因为它们隐含了苏童的真实童年记忆,是最具自传色彩的。在这些作品中充当叙述人的,总是一个身体孱弱,不太合群,总在一条街区上游荡并东张西望的少年,而这正是苏童童年的真实影像。苏童也坦承他小说中那条多次出现的“香椿树街”正是他从小生长的街道:“街上的人和事物常常被收录在我的笔下,童年的记忆非常遥远又非常清晰。”他在创作的时候,习惯从自己童年记忆的一个场景、一个片段出发来铺排故事,结构情节。除了苏童,艾伟、余华、荆歌、王彪、毕飞宇、东西、韩东等作家也都热衷于在作品中运用儿童视角,他们的成名作或代表作也有很多是用儿童视角来进行叙述的,如像艾伟的《回故乡之路》《乡村电影》,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兄弟》(上),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苏童的《刺青时代》《河岸》,王彪的《哀歌》《隐秘》《在屋顶飞翔》《身体里的声音》,叶弥的《美哉少年》,韩东的《扎根》,荆歌的《枪毙》,以及刘庆的《长势喜人》,陈昌平的《国家机密》等等,都是以儿童视角为叙述视点,以作家的童年记忆作为叙事依托来进行书写的。
为什么“60年代出生作家”会集体表现出对儿童视角的偏爱呢?这与他们的共时性童年经验,或者说,与他们的童年时代的集体记忆有关。他们在人生的早期共同经历了一个极左思潮和英雄主义价值观泛滥、混乱无序、狂热喧嚣的时代,这个时代是独特的,政治生活极其丰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却极其贫瘠,对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铁箍一样严密沉重然而又像真空一样虚无和自由的时代,一个最缺少生机却又最充满着浪漫故事的年代,一个密布着意识形态的神话然而又最亲和着大自然的时代——那是孩子们的天堂”②。因此,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为作家后,他们的童年时代以及生活经历就成了他们宝贵的创作资源,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经历的童年时代比起成年后的时代具有更多的故事性和可说性。的确,从“60年代出生作家”的整体创作情况来看,比起对现实的关注,他们更喜欢回望自己的童年,回望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个特殊年代。这一点和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作家都有所不同,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比起回望童年,更喜欢沉浸在他们充满激情和苦难的青春年代,或者带着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入思考;而对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由于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经历过像“文革”这类的重大公共事件,因此他们身上的历史包袱比前人要少得多,所以他们更愿意面对当下,或者在虚构的世界里天马行空。但是,虽然“60年代出生作家”的童年时代对他们构成了潜移默化而刻骨铭心的影响,可他们毕竟不是那个时代的参与者,他们对于时代所给予的苦难,并没有像“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那样有着深刻而切身的体会,因此以“旁观者”和“边缘人”的身份诉说“文革”或者他们的童年时代,诉说他们个人眼中的历史,是他们的最好选择,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复原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情绪体验,才会给读者真实可信的感觉,这就是“60年代出生作家”如此偏爱童年视角的重要原因。
但是,很多“60年代出生作家”的儿童视角小说,和之前的儿童视角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儿童视角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在现代文学初期就已出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作家群的“童年回忆体”小说中,儿童视角更是得到广泛的运用,如萧红的《呼兰河传》、骆宾基的《幼年》《少年》,端木蕻良的《初吻》《早春》等,它们多以儿童的视角追忆故土和已经逝去的岁月,形成了文学史上儿童视角小说的第一次高潮。这些现代文学时期中的儿童视角小说中的叙述人形象,往往年纪较小,都是单纯稚嫩天真活泼的,都是以简单美好的少儿世界映衬复杂丑恶的成人世界,而在“60年代出生作家”的儿童视角小说中,叙述人以叛逆的儿童、青少年居多,少儿世界并不是一味的单纯美好,而是充斥着反叛和暴力,这些叙述人往往缺乏管束,享受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自由,因此他们漫无目的的游荡,喜欢通过偷窥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这样,他们眼中的成人世界,更加以一种赤裸裸的、不堪的面貌呈现出来。在苏童的《乘滑轮车远去》中,那个孤独的少年无意中偷窥的景象令他惊讶:猫头在卧室里手淫,校长和老师在仓库里偷情;在《怪客》中,在青春性意识和性萌动驱使下的“我”,习惯性在夜晚躲在水果店楼下,偷窥二楼的那个漂亮的水果店女孩,呈现在他眼中的,是水果店女孩和街头混混三霸纠缠在一起的身体,是“怪客”将匕首刺入女孩眼睛的可怖景观;在艾伟的《少年杨淇佩着刀》中,内向、孤独、受到同学排挤的杨淇,通过偷窥发现了班主任不为人知的一面:因性苦闷而用刀自虐,和肥胖的女老师在小树林偷情。有时候,“少年偷窥”的叙述视点还是主导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在东西的《后悔录》中,少年曾广贤的偷窥贯穿小说始终,是结构故事、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王彪的《致命的模仿》中,是刘丽的窥视加剧了姜临与沈红艳之间的悲剧化进程。
“60年代出生作家”对儿童视角的偏好,显然出自于他们特有的童年启蒙记忆和认知经验,这使得他们的儿童视角小说具有了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儿童视角和童年记忆的紧密联系使得作家能够很好地复原他们童年时代的真实感受和情绪体验,使得小说真实可信。第二,儿童视角的采用巧妙地回避了那些沉重而尖锐的历史本身,并使得作品闪耀着诗性的气息,具备了卡尔维诺所说的“以轻取重”的审美品质。第三,儿童视角下的世界以更加客观、原生态的面貌呈现出来,揭示了被成人视角所遮蔽的世界和历史,丰富了历史本身。
二、荒诞化叙述
从“60年代出生作家”的整体创作情况来看,他们的作品普遍显示出了对虚构和想象的重视,隐喻、象征、变形、夸张等艺术手段屡见不鲜,使得这些作品都体现出荒诞性的审美特征,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有了显著的区别。
从“60年代出生作家”那些与自己童年时代,或者说“文革”有密切关系的作品中,我们发现荒诞化叙述策略是他们共同偏爱的叙述手段。这点和他们的前辈作家——“知青”作家和“右派”作家有着显著不同,在“知青”作家和“右派”作家的笔下,“文革”是作为政治事件以写实性的状态存在,通常被纳入伦理道德层面来进行评判,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特征,而很多“60年代出生作家”的相关作品体现出来的却是一种现代主义荒诞风格,他们采用的叙述策略有:
第一,戏谑化叙述。反映在作品中,主要体现为这样几个叙述手段。一、他们经常将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神圣的革命口号移用到日常甚至低俗的场景,在毕飞宇的《玉米》中,村支书王连方的嘴里经常蹦出一连串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快过年了,他对着麦克风厉声说:“我们的春节要过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老婆怀孕,他把老婆孕吐干呕的声音说成是“那样的空洞”“没有观点”“有了八股腔”,并被王连方批评为“又来作报告了”。特定时代流行的庄严用语被运用到极度生活化的场景,让人忍俊不禁。二、他们还喜欢用戏仿的手段来达到讽刺、戏谑化的效果,如《耳光响亮》中东西大量化用名人诗句,上大学后意图抛弃发妻的杨春光对夏明翰的《就义诗》进行改写:“离婚不要紧,只要有决心,离了她一个,还有后来人。”在毕飞宇的《平原》里,被下放的“右派”顾先生处境悲惨,可在对顾先生的描写中,叙述者用了这样的语言:“顾先生失眠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念党。”这种戏谑的语言和语调在带来讽刺意味的同时,还消解了故事本身的沉重和严肃。三、“狂欢化”也是“60年代出生作家”惯用的一个叙述手段,如在艾伟的《水上的声音》里,民兵把瞎子扔到河里让其和四类分子友灿呆一块儿居然是因为值了一夜班感到无聊,找点乐子,而这样的惩罚成全了孩子们的一场游戏,他们嬉闹着用泥巴击打水里的瞎子和友灿,狂欢的色彩冲淡了苦难带来的沉重压抑感。余华《兄弟》中刘镇人民的游行更是一场盛大的狂欢,铁匠、小贩、牙医等人物纷纷登场,从着装到语言到动作上都令人捧腹,给本应严肃的政治活动造成了一种滑稽夸张的漫画式的效果。
第二,设置荒诞情境和情节,将整体的荒诞和细节的真实相结合,将周围世界的丑恶面和人性的阴暗面夸张、放大、扭曲,使其更加荒诞不经。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合情理、不合逻辑、不可思议的行为与事件以及畸形病态的人物形象,如东西的《后悔录》,以夸张、荒诞的形式反映了“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泛滥、意识形态的专制以及严苛无比的性禁锢,作品以主人公曾广贤的回忆开篇,回忆的开端即是一件充满黑色幽默的荒唐事件,饱受“文革”性禁锢的众人通过围观狗交配来释放自己的压抑,却受到“革命派”赵万年的严厉批评,并被要求对此事写一份深刻的检查或者揭批材料,而这个赵万年自己也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对曾广贤美丽的母亲早已垂涎已久;接下来发生的事一件比一件荒唐,而这些事件的起因都与“性”有关:曾广贤在屋顶偷窥到了父亲和邻居赵山河的私情,而他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使得父亲一次次惨遭批斗和侮辱,母亲因此更加厌恶父亲,搬到单位宿舍去住,结果被领导骚扰,羞愤难当舍身喂虎,妹妹也在此时莫名其妙地失踪,居住多年的房屋也被没收,曾广贤转眼就成了个无家可归的孤家寡人。一系列灾难都由曾广贤的多嘴引起,曾广贤自己对此也无比后悔,可是在之后的日子里,曾广贤依然控制不了自己的“多嘴”,当他看到好友赵敬东因迷恋表姐闹闹而给饲养的狗取了个和表姐相同的名字,并偷偷和狗交媾,他虽然极力地控制,还是忍不住把真相公告了天下,导致赵敬东的自杀。一系列的事件使得曾广贤对性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但最后他还是在身体本能的驱使下闯入了女人的房间,强奸未遂却入狱10年……里面的人物也都是病态的,除了性压抑到和狗交媾的赵敬东,还有视性为脏东西、不停地清洁自己身体,并拒绝过夫妻生活的曾广贤母亲,以及虽然对性充满了渴望、却在有生之年没能过上一次真正的性生活的曾广贤等等,“文革”时期性禁锢和性禁忌的历史现实以漫画般夸张的形式呈现出来,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却是对历史及人性的深刻反思。对于同一主题的书写,余华的《兄弟》更加显得荒唐和怪诞,刘镇的人们从表面上看,充满了道德感和正义感,可严苛的性禁锢导致的性压抑使得他们的心理发生扭曲,所以,他们愿意付出一碗三鲜面的代价来换取小孩李光头对所偷窥到的女性屁股的描述,李光头因此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得以吃得油光满面,而李光头的爸爸为了在厕所里偷看女人屁股竟然在粪坑溺死,在《兄弟》中,许多细节的描写并不是刻意造成的荒诞,但在客观叙述时,人物的具体行动中就带出了荒诞。荆歌的《画皮》里所讲述的故事涉及到荆歌最刻骨铭心的一件童年往事:专制的父亲因为荆歌的原因被工纠队抓走,被释放后就成了一个“彻底仇恨子女”的人。《画皮》在这件童年往事的基础上运用了虚构、夸张、变形等手段,使得整篇作品变得荒诞离奇,令人毛骨悚然。在《画皮》中,“父亲”整天沉迷于他的事业:画毛主席像。为了在一幢七层楼的墙面上画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光辉照全球》,他制作了一根长达几十米的布绳子,为的是从高耸入云的脚手架上把家人送的饭菜吊上去,以便他可以持续作画。“父亲”在脚手架顶端的时候,显得只有麻雀大小。“父亲”因为我给女孩写情书的事情受到牵连,被抓进工纠队,被释放后愈加古怪,整天在家刻毛主席像,接下来的事情更加怪诞可怖:母亲莫名其妙自杀,父亲用暴力和威胁的手段强制在我的后背刻了一大副毛主席像,并刻上一行字:“向毛主席请罪,我出卖了自己的父亲!”更为可怖的还在后面:我无意中发现了父亲的秘密——藏在柜子里散发着腐尸气息的一幅毛主席画像是用母亲的整块后背皮肤做的,而在父亲死后,“我”整理遗物时又发现了好几张用人皮做的画像!这些残酷、可怖、荒诞的事件发生在亲人之间,让人更加觉得毛骨悚然。这篇作品看似荒诞不经,可是却真实地反映和表现了那段历史的某些方面,将埋藏作家心底的极为深刻的童年创伤记忆以夸张、扭曲的方式显现出来的同时,也揭露了“文革”对人性的极度扭曲。
第三,寓言化叙述。很多“60年代出生作家”在写到“文革”的时候,比起“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惯用的现实主义手法,更喜欢用夸张、隐喻、象征、意象等艺术手段将历史的现实世界寓言化。但在这种寓言化和哲理性的审视中以及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叙述中,我们还是能窥到种种历史真相。这样的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看得出明确时代背景的,如艾伟的《越野赛跑》。在《越野赛跑》中,艾伟设计了“我们村”和“天柱”——现实与乌托邦这两个世界的对照,同时以一匹具有象征意味的神马结构情节,推动叙事。在现实世界里,我们能看到“文革”、改革开放等真实的历史事件,以及人们在这些历史事实影响下真实的生存状态,而“天柱”这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乌托邦世界则是小荷花、步年等人与“四类分子”的伊甸园。作品中多次出现人马赛跑的场景,在疯狂而盛大的越野赛跑中,艾伟让满天飞舞的虫子、鸟、动物和人一起狂欢,“作品大量运用充满象征意味的描述和意象结构,深刻揭示了‘文革’社会苦海无边般的丑恶和堕落,展示了人妖颠倒的荒诞与可怕”③。《越野赛跑》用寓言化的叙述方式再现那个动荡、荒诞年代的心灵躁动,为我们观察人性、透视那个年代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还有一类作品是将时间做虚无化的处理,使得我们看不出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但透过怪诞的情节和情境却能感受到“文革”的浓重阴影。这一类作品比前一类作品更为常见,如格非的《追忆乌攸先生》《敌人》,荆歌的《革命家庭》《口供》,余华的《往事与刑罚》《古典爱情》等等,这些作品通常构筑一个具有整体象征性的叙事结构,如在《追忆乌攸先生》中,善良老实的读书人乌攸先生一直安分守己,并且热心地向村民们普及和传播医学知识。但是,他的藏书却莫名其妙地被“头领”烧掉,和他关系亲密的村姑杏也被“头领”强奸致死,而这个强奸杀人的罪名到最后竟莫名其妙落到了清白无辜的乌攸先生身上。虽然我们在小说中看不出具体的时代背景,“但是乌攸先生的荒诞的生存语境和悲剧性遭遇却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伤痕’、‘反思’文学中‘知识者被迫害’的叙事原型”④。荆歌在《口供》里也讲述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在故事的开篇,毛男、老奎和杏皮三个人去东鹤荡看录像,可半路上遇见的一位妇女却让他们被警察以轮奸罪逮捕,遇到妇女后发生的事情被叙述者完全省略,我们只能从三个当事人的各自陈述中来还原事件真相,可是听完他们的陈述后我们悲哀地发现,我们还是没能得知在遇见妇女后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的陈述都天马行空,让人难辨真假,好像是在吃了迷幻药之后说出的胡话,最后他们都承认了罪行被正式逮捕,可是更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警车在押送他们去看守所的途中无意将轮奸案的受害者撞死,而尸体解剖显示该受害者居然是一位处女!当三人得知这个情况的时候是在刑场,在还没想明白的情况下就被枪毙。在笔者看来,《追忆乌攸先生》和《口供》与作家潜意识里的文革创伤记忆有着密切关系,里面充斥着的诬陷、暴力、人性的扭曲在文革时代是真实的现实存在。在“文革”的极权体制和政治狂热之下,冤假错案屡屡发生,荆歌自己就曾因为十岁时的一个无意举动被抓入工纠队并连累父亲入狱,作品中的怪诞情节所隐喻的“真相”与作家的童年创伤记忆有着很大关系。
第四,“零度写作”的叙述策略。这是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叙述策略,反对从人的主观感情出发来描绘客观世界。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或叙述人在叙述事件(通常是悲剧)的时候回避自己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以冷静甚至冷漠的语调让事件以完全客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在“60年代出生作家”那些与“文革”有关的小说中,“零度写作”是个极为常见的叙述策略,它常常伴随着儿童视角或其他荒诞化叙述策略一起出现。如在苏童的《怪客》中,儿童叙述人在冬夜看到街头混混三霸欺负、侮辱毛头的场景,三霸不仅将毛头头上戴着的棉帽抢了过来,还点火将毛头的帽子烧了,儿童叙述人在叙述着这一切的时候语调极为平静,甚至还觉得有趣:“帽子烧起来后像一个花环,火红火红的,很好看。”⑤在荆歌的《卫川与林老师》中,少年卫川因纵火烧稻草堆而无意烧死了稻草堆里的两个人,被判了死刑。在执行枪决那天,大家纷纷过来围观,而围观的目的只是为了听听卫川死前说什么,好将此作为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而卫川因为咬断了舌头不能说话,所以“人们的希望只剩下了最后的一点点,那就是,但愿卫川在枪响之前嚎啕大哭一番”⑥。看客的冷静与欢乐与所看的悲剧与残忍形成了鲜明对比,构成了极大的叙事张力,使我们想到鲁迅及“五四”作家笔下常出现的那些麻木的围观者,这一点在余华的很多作品中也有鲜明表现,如在《往事与刑罚》中,艺术化的杀人培养了“刑罚专家”,也培养了观赏杀人的看客,看客把杀人当作奇观和奇闻来谈论,“他们觉得这种事是多么有趣”,惊讶复叹息,叹息复惊讶,但“叹息里没有半点怜悯之意”,在《一九八六年》中,因“文革”迫害而发疯的历史老师将古代宫刑施加在自己身上,用石头砸自己的生殖器、用菜刀一块块地割自己的肉,满篇都充满了血腥场景的描写,可是他周围的人都对此无动于衷,听之任之,极度的麻木冷漠,包括他的妻子和女儿,在他最终自虐而死后也“蓦然在心里感到一阵轻松”。此外,由于余华从小在医院长大,自己也有做医生的经历,因此他在叙述暴力场景的时候,除了极为冷静的叙述态度和语调,还有细致入微地刻画,如“镰刀像是砍穿一张纸一样砍穿了我的皮肤,然后就砍断了我的盲肠。接着镰刀拔了出去,镰刀拔出去时不仅又划断了我的直肠。而且还在我腹部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于是里面的肠子一涌而出”⑦。如此细致逼真的血腥场景以极度冷静的语调叙述出来,让人更加觉得阴森可怖,毛骨悚然。
除了与“文革”有关的小说,上面提到的这些荒诞化叙述策略也常常运用在“60年代出生作家”的都市题材小说中,如在毕飞宇的《男人还剩下什么》中,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移用现象:“主任的意思我懂,他怕我在办公室里乱‘搞’,影响了年终的文明评比,我很郑重地向主任点点头,伸出双手,握了握,保证说,两个文明我会两手一起抓的。”⑧设置荒诞情境、戏谑化、狂欢化的叙述策略更是随处可见,如在荆歌的《牙齿的尊严》中,“我”因在一次拔牙手术中怀疑被医生把牙根弄到下颌骨里面去了,使得亲友卷入了是打官司还是立即锯开下巴骨的讨论之中,最终亲友决定分成两组,“一组分管我那可怖的手术;另一组则由叔父牵头,要尽快将苏林医生推上被告席。第一组下设公关处、内勤处、护理处(兼接待处)、餐饮处和指挥中心;第二组下设文书处、资金筹集处和一个由叔父与三名律师组成的决策核心。各处都推举出正副处长,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要毫不留情地对责任人进行追究,并且提请该处主要领导引咎辞职”⑨。荒诞不经、引人发笑的情节背后是作者对现实秩序及现实生活的严肃而深入思考。用荒诞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无奈,是“60年代出生作家”的都市题材小说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审美意蕴,体现了他们对都市社会的怀疑和消解态度。
荒诞化叙述策略在“60年代出生作家”的广泛运用,除了与“文革”结束后的日渐宽松的政治环境、各种文化禁锢的解除、西方思潮和西方作品的大量涌入以及文学观念的转变有关,也和“60年代出生作家”的童年经验以及他们所经历的那个童年时代有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60年代出生作家”所经历的童年时代本来就是一个荒诞而疯狂的时代。在极左思潮和极权思想的影响下,革命领袖的一言一语都被视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文攻武卫”等口号的煽动下,各类充满野蛮和暴力色彩的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冤假错案数不胜数,血腥惨烈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很多在今天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文革”时期见怪不怪,这为“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中的荒诞提供了现实基础,就像东西所说的:“生活本身就比较荒谬。这种荒谬在蜜缸里泡大的人的眼里可能会显得很虚假,但是在本身经历过荒谬又比较清醒的人眼里,它显得很贴切。”⑩
第二,“文革”作为“60年代出生作家”人生经历中经历过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自然成为了他们宝贵的叙述资源,可是他们在“文革”时期只是一个幼小的“旁观者”,所以他们对于“文革”的体验较之“文革”亲历者和参与者更加具有被动性。体验的被动性意味着不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体验的理性因素偏低而情绪内涵偏高,这样留给文学创作和精神创造的余地就很大。这也使得他们比“文革”的亲历者在审视“文革”的时候,多了一份距离,而正是这种历史的“距离感”使他们可以从容地对“文革”进行重新编码和变形组合,突破了“知青”和“右派”作家惯用的现实主义笔法。
第三,“文革”时期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频繁更替的基层权力,不断更换的“打倒”对象,普遍缺席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给“60年代出生作家”的心灵埋下了怀疑的种子,再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到来,时代的价值观总是处于不停变动的状态,使得“60年代出生作家”普遍对世界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因此在面对现实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们习惯于怀疑和反叛,这样的心理结构使得他们对西方现代派、荒诞派等文学流派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因为这些文学流派的创作主体跟“60年代出生作家”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庄严与浪漫、革命与戏谑、激情与荒诞、信仰与乌托邦交织在一起的年代,他们对于现实历史的荒诞感受是他们创作出荒诞小说的主观动因和现实基础。因此他们对荒诞性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把握,很自然会引起中国“60年代出生作家”的强烈共鸣。
三、结语
总之,儿童视角和荒诞化叙述策略在“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中的广泛运用与作家的童年经验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叙述策略充分调动了作家的想象力,大大拓展了作品的叙事空间,使得那些沉重的故事也充满了轻盈的诗意,在沉重的苦难与轻盈的诗意之间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张力,实现了卡尔维诺的“以轻取重”的美学理想。此外,他们以儿童视角或荒诞化叙述策略完成的“文革”叙述也成为了“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笔下“大历史”的一个回响,一个尾声,一个和鸣。
①王黎君《儿童视角的叙事学意义》[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②张清华《天堂的哀歌》[J],《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2期。
③李运抟《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六十年》[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页。
④苏鹏《突围与僭妄——论先锋小说中的“文革叙述”》[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版。
⑤苏童《怪客》[A],《桑园留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⑥荆歌《卫川与林老师》[A],《口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⑦余华《死亡叙述》[A],《余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页。
⑧毕飞宇《男人还剩下什么》[A],《毕飞宇作品集·第6卷》,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⑨荆歌《牙齿的尊严》[A],《口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页。
⑩洪治纲、东西《伤痛的另一种书写》[J],《青年文学》,2000年第11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