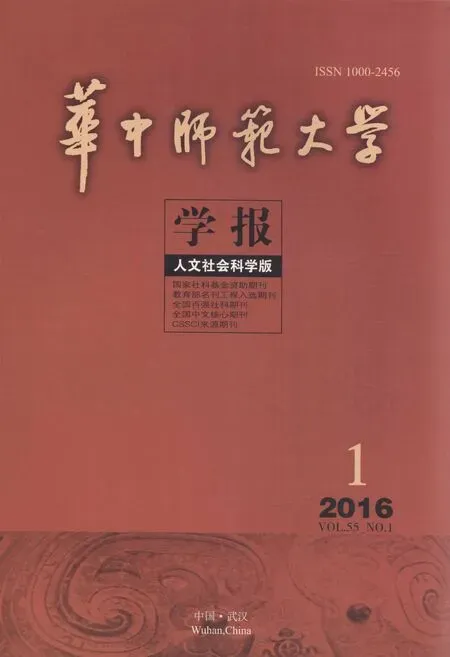文明的概念与文明史研究
2016-09-08李剑鸣
李剑鸣
(复旦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433)
文明的概念与文明史研究
李剑鸣
(复旦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433)
文明史目前主要是一个通史编纂和教学的框架,若要把它发展成历史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历史学家需要就文明的概念达成基本共识,并且发掘出特有的题材,促成自成体系的方法论。但是,文明的概念不仅复杂多变,而且具有鲜明的道德和意识形态意涵。在题材上,文明史不仅容易同其他相对成熟的专门史发生重合,而且因其概念的限制而具有突出的选择性和排斥性;在方法论方面,文明史也面临许多的困难和陷阱。种种不利情形使得文明史尚未发展出一套自足而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因此,文明史能否成为历史研究一个专门领域,还是一个很不确定的问题。
文明; 文明史; 文明史范式; 历史学
在考古学和远古历史的研究中,“文明”是一个具有组织性功能的概念,它有助于把关于人类早期生产、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林林总总的研究,整合成一个边界相对清晰、题材相对具体、方法相对鲜明的领域。不过,一旦出了人类早期文明研究这个范围,所谓“文明史”大抵还只是一种通史或教科书的编纂体系,或者是一个综合性的历史写作和教学的平台,而不能视作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以“文明”为框架来编写通史或教科书,确实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包含特定的思想取向。相较于那些以政治、社会或政治经济为中心的通史和教科书写法,文明史写法的突出优势在于扩大视野,增添容量。而且,只要把人类的过去经验视为文明的发展和变化,就必定会提升技术、思想和精神的历史意义,对各种“传统”的史观(如绝对的经济决定论或机械的社会形态史观)起到挑战或纠偏的作用①。在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历史教学中,文明史还被当成一种教学改革的路径,是对旧的教科书体系的补充或替代②。诚然,这样的文明史写法难免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意蕴。
另外,文明史还被作为一个整合多种资源与路径的研究和教学平台。在美国一些大学,基于英文系和历史系的合作而组建的“美国研究”项目,有的径直称作“美国文明”,便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生培养平台。在中国某些大学里,诸如“世界文明史”或“世界文明研究”这样的设置,大体与“世界史”类似,也是一个把地域、民族、文化和专题等要素结合起来的学术平台,目的是争取或整合学术资源,更好地组织和协调世界史的研究与教学活动。这类平台在功能和作用上与学科近似,也不具备专门研究领域的特征。
文明史是否有可能成为一个研究领域,这取决于它能不能拥有专门的研究题材,形成独到的方法论,与其他史学领域之间形成明确的边界,同时又能对它们产生辐射性的影响。这样就需要重新界定“文明”,并以某种具有操作性的“文明”概念为核心,来构建一种或若干种文明史的研究范式。
一、“文明”概念的不确定性
不论是就用法的复杂多样而言,还是从含义的驳杂混乱来看,“文明”都可以在“麻烦词排行榜”上居前几位。不仅学术界使用这个词,而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提到它。不过,无论就何种含义而言,“文明”在中文世界都是一个“舶来品”,因为当今人们使用的“文明”一词,同见于中国古代文献的“文明”(如《周易》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并无语义学的关联。“文明”是“civilization”的汉译③。“civilization”这个词出现于18世纪中期的欧洲,其产生的语境十分复杂,最初其含义就呈多样的态势④。而且,在后世的使用中,这个词的内涵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其边界也因不断扩展而显得愈益模糊。于是,“文明”的概念就具备突出的不确定性,使得对文明史的界定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⑤。
对于这样一个含义多样、用法混乱的词,要就其各式各样的语义做出细致的考辨,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即便是仅做一点粗略的类型学分析,也能看到文明概念在含义上罕见的复杂性。大致说来,学术界使用的“文明”一词,在不同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的学科方面的侧重或偏向。有哲学意义上的文明概念,例如在黑格尔的理论中,文明不啻是“绝对理念”的展现;而一般的哲学著作或许倾向于把文明看成人类的精神特质或禀赋,它把个体的人相互连接起来⑥。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文明概念,把文明理解为人类作为群体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和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⑦。有心理学意义上的文明概念,认为人类的行为习惯及其相应的观念经历了改善性的变化,从粗野、肮脏走向文雅、礼貌、卫生⑧。有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明,指的是人类奠基于长期积累的知识和技术之上的行为方式;有的学者还用文明对文化做类属的划分,也就是以某种文化或族群为中心区分不同的文化复合体,如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犹太文明等⑨。还有一种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文明概念,侧重的是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人类社会形态,如早期文明研究中的陶泥文明、农耕文明,现代文明研究中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当然,还有从意识形态着眼使用的“文明”,诸如西方文明、东方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都大体类此。
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说,对(实际存在的各种)文明的含义和边界的界定,主要是一个历史的问题⑩。可是,历史学家通常不太擅长从理论上讨论概念,他们习惯于用题材、路径和方法来体现他们对某一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从已有的各种文明史著述来看,历史学家在使用“文明”一词时,很难说有什么共识。他们笔下的文明在含义上五花八门,在边界上同样难以确定。

更大的困扰也许在于,“文明”概念还天然包含着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意涵,这使得历史学家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随处都可能遇到陷阱。
按照一般的用法,“文明”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在现代术语中,“发展”意味着向前或向上的变化,因之往往成为“进步”的代名词。于是,文明的概念便直接指向线性的进步观。




从他的这段话不妨做几点推论。第一,文明是现代西方人对于自身特性的想象,是一个文化认同的标志,用以区分“人”、“我”(或者是“主体”、“他者”)。第二,文明表达了后人相对于前人、西方相对于非西方的优越性,它既是历史的,也是超历史的:一方面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现代的结果,是“现代性”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它又只是西方人所达到的历史高度,因而与种族优越论、文化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等观念有着密切的关联。第三,文明的概念既是民族意识的展现,也是对人类同质性的追求,因而可视为全球化运动的一种潜在推力,也就是促使非西方“西方化”,最终使全人类都达到“文明”的新高度。




我们知道,文化史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也曾受到“文化”定义繁杂多变的困扰。但是,文化史家最终克服了定义的难题,他们用自己的研究实践对文化做出了相对明确的界定。经典文化史家倾向于把文化理解为“高级文化”,也就是人类在文学、艺术、思想、学术等方面的活动及成果;新文化史家通常把文化看成人类借助符号和象征物寻求意义的过程和方式。就“文化”达成共识性的定义,乃是文化史变成一个自主的研究领域的前提。然而,历史学家笔下的“文明”却迟迟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定义,这就给文明史走向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二、文明史题材的选择性
同“文明”的定义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乃是如何看待文明史的题材。文明史要成为一个边界明晰、特征显著的研究领域,首先要有自己的题材资源。可是,“文明”在概念上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势必给对文明史题材的界定带来许多的困难。




在远古历史的研究中,“文明”通常被看成是标志着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于是,技术进步(主要是农耕、制陶和冶金技术的出现)、文字的形成、城市的出现和早期国家就成了文明史的主要题材。而且,远古史研究者对文明的理解相对确定,又以探求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形态为研究旨趣,因之习惯于把地域、人口、技术、制度等要素整合起来,建构若干边界清晰、起止明确的历史叙事单位。诸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米诺斯文明、伊特鲁里亚文明、中美洲文明等,都属此类。这就是说,以古代为对象的文明史研究拥有相对具体而稳定的题材来源。


就“过程”而言,文明史强调的是发展;从“结果”来说,文明史关注的是成就。于是,人类经历中的黑暗与苦难就被“文明”的光芒所掩盖了。例如,一般的世界史或文明史书籍都把金字塔视为古埃及“文明”的象征,却没有意识到其中包含着巨大的悖论。就技术和工艺上的成就而言,金字塔固然是令人惊叹的“文明”奇迹;然而修建它们的本意却是基于偶像崇拜和来世观念,它们的建造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财富,而且使劳动者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在这个意义上,金字塔周身都带有奢靡、野蛮和暴政的鲜明印记。
此外,在现代史上,许多代表“文明”成就的技术发明和革新,也经常被用于压迫、控制、摧残和杀戮,竟至使人类陷入自我毁灭的危险当中。这似乎也可以说是一种“文明”和“野蛮”的悖论。
谁也不能否认,人类过去的经验中确实充满了“不文明”和“非文明”的成分,诸如奴役、压迫、剥夺、杀戮、歧视、战争、灾荒、瘟疫、不平等、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等,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并且一直延伸到当今的世界。

毋庸置疑,任何历史研究的方式都无法回避对题材和史料的选择;但是,如果选择导致对历史的刻意遮蔽和歪曲,那就违背了历史研究的旨趣。前文谈到,“文明”概念天然包含着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意涵,这必然导致文明史在研究题材上具有异乎寻常的选择性。换句话说,文明史本来只能涵盖人类经历的一部分,可是文明史的撰写者却总是宣称他们所写的是“人类的历史”或“世界的历史”,这实际上迫使他们不得不刻意删减、掩盖或扭曲人类经历中的“不文明”或“非文明”成分。这种选择性不仅直接损害历史研究的宗旨,而且同当今史学的价值和思想取向也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知道,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都具有平民主义取向,它们挑战精英主义史观,倡导“从下向上看历史”,关注普通人的经历,甚至采取“精英-民众”二元对立的观点解释历史。这样的研究路径和视角,固然也有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局限,其选择性同样妨害了对历史的“同情式理解”,但是它们把人类经历中的黑暗和苦难、特别是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所遭遇的压迫和苦难以及他们的抗争带入了史家的视野,挑战以至改变了以往进步史观支配下的“英雄史诗式”或“胜利凯歌式”的历史叙事。可是,文明史叙事则难于包容人类经历中的黑暗和苦难,因而必然自囚于理性和进步的神话的牢笼之中。
三、文明史方法论的局限性
通过专门的研究领域来规划和组织历史研究,或者借助题材、路径和方法对历史学做领域的划分,这是19世纪下半叶专业史学形成以后的事。在这种学术格局中,任何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不仅要有专门的题材资源,而且要有自成系统的方法论。对文明史研究来说,文明概念的不确定性也难免妨害系统的方法论的形成。
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欧美史学中,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是先后引领潮流的两种研究范式。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研究范式,并对其他史学领域产生改造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们有自成系统的新的方法论。新社会史在方法论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倡导“从下向上看历史”的视角,把过去长期被边缘化或被删除的历史角色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央;改变了以往史学关注重大事件和精英人物的趋向,把普通人的经历和日常生活作为研究的主要题材;自觉地引入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以此构建新颖的解释框架;借重统计学的分析,甚至采用计量研究的技术,基于大量数据进行量化分析;重视理论化,以提出超出一般事实判断之上的理论性结论为研究的最高指向。
新文化史在方法论上与新社会史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很大的不同。它和新社会史一样重视普通人的经历,但它重视的主要不是作为群体的普通人,而是那些留下了历史记录的普通个体;较之于新社会史,它更关注人的内在经验,也就是那些以往没有进入史家视野的心理和精神层面的经验,如梦境、记忆、情感、感觉、态度、价值、习惯等等;而这些题材一旦进入历史研究的主流,等于是重新界定了历史:内在经验对于人的类属认同的变化具有核心意义。新文化史还放弃了对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热情,转向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和文学寻求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启示,倚重文本解读、语境分析和阐释性叙事等方面的技巧,致力于对过去经验的阐释和理解,并力图揭示其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
那么,文明史到目前为止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呢?如果它有独特的方法论,其特征和支柱又是什么呢?

通论性文明史编纂方法的另一个特点,是打破自然时间的限制,不一定采取编年史的路径,而可以按照文明的内涵构想出若干专题,以此构建叙事的框架。这种专题性叙事在涉及现代文明阶段时更加常见。但是,文明的任何专题在内容上不是偏向于文化,就是接近于社会,于是专题叙事法就总是难免显出文化史或社会史的痕迹。
通论性文明史自然不能回避文明的传播和扩张,这样它就有可能采用国际史的视野,借助国际史的方法,也就是基于多国材料对国际文明的趋势和互动进行历史分析。另一方面,跨文明的接触和交流也是文明史编纂的题中之意,这样跨国史的路径对于文明史也有借鉴的价值。
尤有进者,现在还出现了单数的“全球文明”(global civilization)的概念;如果要探讨文明的全球化过程,文明史可能又要同全球史发生重叠。不过,在文明史编纂中如果大量引入国际史、跨国史和全球史的元素,可能会对文明史的边界和特征产生不利的影响,就像当年历史学大量引入社会科学的元素而导致学科特性的危机一样。
在专题研究的层面,方法同题材和问题意识有着共生性,因为方法不过是用来处理题材和阐述问题的。如上文所论,作为专题研究的文明史缺乏独特的题材资源,因而也就难于形成相应的独特方法。如果把文明史当作一个包罗一切的领域,那么历史研究的一般方法就都成了文明史的方法。如果按照经典文化史的模式看待文明史研究,那么它在方法上与经典史学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遵循埃利亚斯的思路来理解文明史,那么新文化史的方法也就是它的方法。从文明史的编纂史来看,多数学者确实倾向于把文明史看成文化史的一种类型;那么,文化研究、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和图像学等就可以作为它的方法来源。可是,历史学界毕竟倾向于把这一类方法归入文化史的范畴。
这样一来,就方法论而言,唯有通论性文明史有自己的特色,而专题性文明史研究还没有形成独特的方法。换句话说,文明史作为一种历史编纂方式,目前还只是停留于宏观(至多是中观)的层次,还没有落实到微观研究。可是,如果没有细致深入的微观研究作为支撑,宏观或中观层面的文明史著述在学术上就难免具有某种“寄生性”,完全依靠其他研究领域输送学术资源。用一个制造业方面的比方说,通论性的文明史至多是一个组装产品,它的零部件都是在其他地方生产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文明史著述又像是“贴牌产品”,“文明史”的标签被轻易地贴在某些专门史的题材和成果之上。



四、结语
在中外史学史上,有些研究领域主要是依据题材来界定的,如经典经济史、经典政治史和经典文化史等;有些领域主要是依据方法来界定的,如新经济史、新政治史等;有些领域则既可依据题材来界定,也可依据方法来界定,并且主要是依据方法来界定的,如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等。只有在主要依据方法来界定的领域,才有可能产生某种具有辐射力的研究范式。
现在看来,文明史研究面临着三重难题:历史学家尚未就文明的概念取得稳定的共识,文明史尚无确定而丰富的题材来源,而且还缺乏系统而自足的方法论。这说明,文明史要成为一个自主的研究领域,形成某种有影响的研究范式,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诚然,这是偏于乐观的看法。对于那些持论悲观的人来说,也许文明史本来就只适合做通论性历史编纂的框架,根本不具备成为一个专题研究领域的可能性。
注释
①启良在其《中国文明史》的序言中说,他之所以采取文明史的写法,主要是要打破社会形态史观、简单的经济或意识决定论以及朝代史模式。启良:《中国文明史》,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上册,第1-17页。
②王世光:《“文明史写法”与中学历史教科书改革》,《教育学报》2009年第2期。
③“civilization”是“civilize”的名词形式,若按照汉译对“zation”后缀的处理方式,应以“文化”(“以文化之”或“因文而化”)对译更贴切一些。然则习惯上“文化”一词已是“culture”的对译,我们就只能接受“文明”这个与中文原意相去甚远的译法了。
④Mazlish, Bruce.CivilizationandItsContent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9.
⑤由于“文明”一词的含义复杂多样,因而许多以文明为主题的学术讨论,往往都从界定文明的概念开始。例如,布罗代尔在其《文明史》一书的开头就用一定的篇幅考辨了“文明”一词的起源、传播和语义是流变。见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5-40页。另参见马克垚:《世界文明史导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5期;Jacobson, N. P. “The Problem of Civilization.”Ethics63, no. 1 (Oct., 1952): 14-15; 彼得·N·斯特恩斯:《世界历史上的西方文明》,李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⑥Jacobson, N. P. “The Problem of Civilization.” 15.
⑦美国学者卡罗尔·奎格利按人的组合体的不同性质区分出“集体”、“人群”、“社会”等形式,又把社会划分为“寄生性社会”(狩猎和采集等)和“生产性社会”两类,并把拥有书写方式和城市生活的生产性社会称作“文明”,以区别于简单的生产性社会。他认为,人类历史上以寄生性社会数目最多,其次是一般的生产性社会,而能称作“文明”的生产性社会则为数不多。See Quigley, Carroll.TheEvolutionofCivilizations:AnIntroductiontoHistoricalAnalysi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1, 25-32.

⑨实际上,人类学家对于什么是“文明”也没有一致的看法。See Wolf, Eric R. “Understanding Civilizations: A Review Article.”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9, no. 4 (Jul., 1967): 447-452.
⑩Kroeber, A. L. “The Delimitation of Civilizations.”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14, no. 2 (Apr., 1953): 265.


























责任编辑梅莉
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Li Jianm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at present is fundamentally a frame for writing and teaching general history,and a lot of work is needed to make it a special field of historical studies. A basic consensus pertain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civilization,the abundant sources of particular subject matter,and a systematic methodology are indispensable in this respect. However,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is not only complicated and ever-changing, but also imbued with moral and ideological implications; in terms of subject matter, the history civilization not only overlaps with other relatively matured sub-fields,but also i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selectiveness and exclusiveness that derive from limitations of the connotation of civilization; there are also difficulties and trap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ology. Given such unfavorable conditions, it is no wonder tha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still does not boast of an influential paradigm. Therefore, it is quite uncertain as to whether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shall grow into a specific field of historical inquiry.
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paradigms of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2015-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