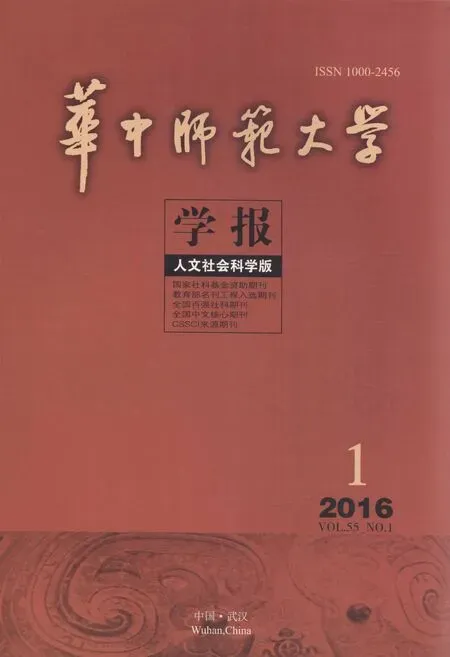文化间性: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跨文化之思
2016-09-08刘学蔚
刘学蔚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文化间性: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跨文化之思
刘学蔚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来华留学生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以稳定的发展和高度开放的姿态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尊重。以辩证的视角统一“差异”和“融合”的文化间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特质,强调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指向一种相互理解、相互适应、相互联结和依存的跨文化关系的建构。在文化间性的视角下反思教学中的跨文化难题、教学者的跨文化能力和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从文化和跨文化的本质内涵思考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呈现出来的文化危机,有助于我们看到不同文化主体之间通过对话和协商达成意义重组及分享的动态生成过程,为来华留学生教育提供一种超越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路径。
文化间性; 来华留学生教育; 高等教育国际化
以孤立呈现自我文化价值的方式进行单向的文化传播会导致文化身份的认知焦虑,这是文化的主体性带来的认同危机。如果说文化的主体性是自我文化价值的呈现和表达,那么文化的主体间性则是自我文化价值和他者文化价值在对话和交际过程中的双重呈现以及在该过程中发生的意义重组。倘若不看向文化间性,不转换“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我们就无法在跨文化的情境中进一步探讨实践的有效性。
“主体-客体”问题一直被视为西方传统哲学之根本问题,如今却处于危机之中。由于客体一直被视为依附于主体的派生之物,饱受争议的主客分离主张遭遇了各个学术阵营的猛烈抨击。在对主体性的各种消解之中,受到最多关注的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哈贝马斯认为主体形成的社会化实际上是以语言为核心的交往行为,那么“主体-客体”模式必然能被进行言说与行动的主体和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的范式所取代,即强调言说和行动着的“主体间关系”①。
文化间性问题是“当今西方哲学中的主体间性问题在文化学领域的一个具体体现”②。我们不能将它简单理解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或关联,因为它远比这种静态的关系或关联复杂。它并非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种动态的生成和演绎,是一种多维度的跨文化关系的建构,是“一种文化与特定其他文化交遇时显出的意义关联”,并“作为该文化的一种隐性特质而客观存在”③。它所看向的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通过对话和协商达成意义重组与分享的动态过程,而非意义的单向输出。因此,文化间性也可以被理解为“提高每一个交流个体在超越自身文化的基础上与其他文化形成互动的能力”④。
有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内涵上发生的深刻变化体现为对其“政治的、文化的考量”超过了对其“学术的考量”⑤。在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危机。本文从文化和跨文化的本质内涵去寻思问题所在,在文化间性视域的引领下从教学中的跨文化难题、教学者的跨文化能力和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这三个方面来探讨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跨文化发展路径,以期拓展该领域的研究视野。
一、理解文化间性
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是“所有跨文化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理论问题”⑥。要想理解文化间性的本质,我们需要从“延异”、“关联”和“融合”这三个要点入手。首先,承认“非静态性和非绝对性的差异”(延异)是文化间性之基础;继而,在不拒斥差异的前提下实现文化间的互动式契合(融合),是我们在跨文化情境中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完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则是在文化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时刻看向其关联。
其一,延异。颠覆了二元对立的“延异”比“差异”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间性。德里达用“延异”(differance)解构了贯穿于20世纪人类思想史的“差异”(difference),德里达认为延异包含时间维度上的“延宕化”(temporalization)、空间维度上的“间距化”(spacing)和差异之“散播”(disseminations)。“延宕”意味着时间上的暂时存在并不断延迟,“间距”意味着空间上的非同一性和他者性,是他人与自我之间所存在的不可通约的文化历史地平线⑦。德里达用“延异”来铭刻“大写的差异”,它是差异的无限生成,“不断地确立界限又不断地逾越界限,由此无限越界,无限接近他者和倾听他者的语言”,它“将一切静态结构的文本转化为动态生成的文本,从而决裂了自我接近和自我封闭的系统”⑧。延异所强调的是差异的非静态性,是更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处于运动中的差异的产物,而文化间性所指向的是互为主体的不同文化之间意义生成和重组的动态过程;由此看来,承认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所具有的非静态性和非绝对性,可以被认为是理解文化间性之基础。
其二,关联。归其本质,文化间性可以被视为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关联。它并非简单地指向两种文化之异同,无论同也好,异也好,其关键在于这部分文化需要引起彼此间的关注并建立起对话关系。如果说文化间性本身就是一种特质的话,那么“关联”,即是文化间性特质最主要的表现,所有的讨论都应该围绕“关联”展开。王才勇认为,对两种文化的任何言说都应该从其间的关联出发。那些参与到交互作用之中的、成为彼此真正实际的文化部分,正是由于“进入了他者的特定关联才显出其意义,离开这个关联就无从进入它真正发生作用的世界”,所以将这部分文化“作为独立的整体去论说所揭示的只是它本来的意义,而不是它在这种关联中重新生成的意义,从而也就触及不到处于交互作用中之文化的真正实际”⑨。


总的来说,“二元对立”过分看重差异的不可调和性,而“多元文化主义”则在过度强调差异性的同时忽视了对话的重要性。“文化间性”的重要价值在这里便体现出来:首先,和多元文化主义所提倡的一样,文化间性不仅承认差异,鼓励差异,而且主张维持差异和差异的共存。其二,文化间性提倡在文化间的对话和交往中、在差异共存的基础上寻找并建立关联,这恰好指向了多元文化主义之症结所在。因此,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以辩证的视角统一了“差异”和“融合”的“文化间性”,是基于多元文化主义、同时又能够超越多元文化主义的路径之一。
二、文化间性之于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文化间性得以呈现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存在文化上的他者;二,与他者相遇和交往。首先,一种孤立的文化自身是难言其间性的,文化间性得以呈现须通过他者的眼睛,或是在他者的帮助和参照之下得以呈现。因而“他者”,是文化间性得以呈现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其二,虽说文化间性是客观存在的,却是文化的一种隐性特质,这种特质只有在该文化与其他文化相遇和交往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呈现。因而“两种或多种文化的相遇和交往”是文化间性得以呈现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在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考虑到文化间性的存在了。那么具体到来华留学生教育,这些国际留学生之于我们来说是“文化上的他者”,我们的教育管理工作及教学活动本身也是我们和他者相遇和交往的过程。我们和他者共同存在,且互为主体,正因为如此,文化间性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开展和发展而言便不再是一种隐性特质了,而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到的客观存在。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开始全面走向国际化发展进程,并将培养国际化高水平人才视为重要目标。在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是一项与国际社会高度接轨的教育事业,理应被视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持续行走在教育界的边缘。要想全面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无论哪个层面都离不开一种跨文化的路径;而文化间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于来华留学生教育中的重要特质——无论这些国际学生是学历生还是语言进修生,也无论他们处于哪一个学习阶段,选择了哪一门专业——都在其在华的学习和旅居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重要体现。在间性视域的引导下对来华留学生教育进行跨文化的思考,其关注点并未局限于国际留学生在华的跨文化适应状况以及他们和中国人之间的跨文化交际问题,也绝非盲目倡导西方发达国家所推崇的多元文化主义策略并在权力的博弈中寻找出路,而是尝试着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下结合我国国情对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问题提出一条超越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路径。
那么为什么文化间性之于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呢?
首先,国际留学生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跨文化交际实践,无论他们使用汉语还是其他语言与他者进行交流,也无论他们的交流对象是中国人还是其他外国人,这种在多元文化情境中进行的交际实践从各个角度来看都充满了跨文化的意味。自霍尔提出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之后,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研究便不再停留在分析产生文化差异及误解之原因的层面上,而是开始寻找使之成功的可能性。“cross-cultural”和“intercultural”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cross-”和“inter-”这两个前缀,前者的重心在于异文化主体的某一方如何去跨越差异,而后者所追求的是建立在互惠性理解基础上的差异之共存(而非消解)。对“inter-”的重视让跨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间文化研究”,也让人们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主体的关系和关联上面。既然我们将这些国际留学生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及其旅居生活本身视为一个典型的跨文化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就一定是通过动态的对话和协商来完成的;这些学生的目的不仅是完成自己特定的学习目标,更是在这宝贵的留学经历中尽可能多地去了解他者,增进彼此之间的有效交流,积极地建构自己和他者之间的跨文化关系,并期待在留学生活结束后能保持这种跨文化关系。因此,单向的知识、文化或语言的输出显然不是帮助国际留学生达到该目标的最佳方案,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平等的、多维的、富于创造力和伦理意味的方式去全面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让中国在国际留学生教育市场中以一种高度开放的、融合的姿态去邀请和吸引更多外国学习者的到来。

三、在文化间性视域中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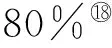
(一)在文化间性视域中反思教学中的跨文化难题
教学是留学生教育的核心组成。克服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语言与文化障碍,是国际留学生需要面对的首要难题,只有帮助学生跨越了这道屏障,教与学的质量才有不断得以提高的可能性。面对语言障碍我们已拿出了多种方案,其基本方向是在不断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有效性的同时,也加大力度开设高质量的纯英文讲授的专业课程;然而在文化问题上,尤其是面对留学生在文化背景上所具有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我们却并未找到有效的突破口和解决方法,此外,人们跨文化意识的普遍缺失也导致了教育者和教学者对文化差异的制约性并未产生足够的重视。文化无所不在,且无处不在,文化影响着人们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认知方式、信息编码和解码方式等。由于母文化所具有的稳定性特征,无论来自哪个国家的留学生都无法完全摆脱母文化对其在方方面面的影响,这一点在语言进修生和人文社科领域的学历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倘若不触及文化之间的间性特质,我们的教学活动恐将难以收获理想的效果。


(二)在文化间性视域中反思教学者的跨文化能力
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和实施者,承担留学生教学任务的高校教师(包括对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素养与能力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重要因素。教师的教学行为首先是一种跨文化教学实践,然而无论他们使用汉语授课还是使用其他语言授课,很多教师都不易摆脱自身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的深刻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全面顾及国际学生思维方式及接受习惯的多样性,这在本质上来说也是教师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的缺失所造成的。
也有教师认为,倘若能熟谙中外文化差异,也就掌握了跨文化能力。但很残酷的一个事实是,仅仅具有基本的跨文化知识储备并不足以让跨文化教学有效进行。虽然“cross-cultural”和“intercultural”在国内学界被统一译为“跨文化”,但两者的侧重点却各有不同。前者停留在静态的认知层面对文化差异进行对比,后者则是在差异的基础上看其关联,并进一步建构文化主体间的跨文化关系。显然,我们所说的跨文化能力指的是在“间性”的指引下所形成的一种更加全面的跨文化综合能力,即intercultural competence。这种跨文化能力的基础是“认知层面”的跨文化知识储备,在知识储备充足的条件下,无论是授课教师还是外国学习者,都需要拥有能够驾驭我们手中的文化符号及资源的自由的意志与心智(比如移情能力),以及掌握如何正确操作文化工具箱和各种文化开关的方法,后两者便涉及跨文化能力的“情感层面”和“行为层面”。承担留学生教学任务的中国高校教师,作为留学生教育的重要中介人和教学任务的直接实施者,必须对文化间性以及存在于文化之间的这种关联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体现在教学实践上,这样,才能让自己的课堂展现出真正的跨文化活力并收获理想的教学效果。更具体地来说,一个跨文化能力较高的教师,需要拥有丰富的跨文化知识储备,具有较高的移情能力和情感调控能力,并在教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国际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还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以间性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因为国际留学生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敏觉力的缺失也会影响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
虽然能承担留学生教学任务的中国高校教师大多具有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外语能力,但超越了纯粹语言能力的异文化之间的“对话能力”以及达成互惠性理解之关键的“跨文化能力”却容易令人忽视。语言能力也许可以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提高,但文化间的对话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却无法在教师独白式的知识阐述中获得。在高等教育快速走向国际化的今天,单向的知识灌输和独白式的文化解读显然是一种闭塞且不合时宜的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无论是专业教学还是对外汉语教学,无论是教学研究者还是教学实施者,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对外国留学生进行单向的知识、文化或语言的输出是无法建构其关联的,若想让中国高等教育真正向国际化迈进,其思路还须不断向文化间性打开。教学者和学习者,应构成一种平等的互为主体的关系,这种关系看似削弱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权威,实质上却是看向文化间性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无论这种互为主体的关系在教学实践中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体现,削弱一方主体的权威性即增加了双方平等对话的可能性,中国教师和外国留学生之间的主客关系由此变成了主体和主体之间通过教学活动所构建的跨文化关系,而主体双方获得认知、达成理解或共识、甚至是创造出新的意义的过程,亦是在对话和协商中完成的。
(三)在文化间性视域中反思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

尽管学界针对我国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服务模式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议,诸如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混住模式,效仿西方国家的寄宿家庭(homestay)模式,以趋同化管理模式代替差别化管理模式等等,但无论是哪一种方案,具体实施起来都有一定的难度,不仅难以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将国际上流行的做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运用,还需要国家层面制度法规上的支持甚至是做出相应的调整。学界普遍认为,中外学生并轨的趋同式管理方法是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改革的大方向,其最直接的好处是能为留学生创造更多接触中国社会的机会,笔者也认同这一看法。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仅缩短留学生与中国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并不是为他们创造良好跨文化教育环境的关键,真正需要缩短的是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心理距离,真正需要打破的是他们和中国人之间的文化藩篱;这里的中国人首先包括和他们接触频繁的授课教师以及时刻为他们排忧解难的院系管理人员,然后还包括校园里的中国学生和社会上的中国老百姓。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国际留学生都能在中国交到当地的朋友,即便是那些拥有中国朋友的留学生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融入中国人的圈子,诸多实证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外国留学生和中国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体验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不及他们和本国人或其他国家留学生之间的社会交往体验。虽然开放且融合的间性思维方式和较高的跨文化能力与素养,对于每一个留学生教育领域的从业人员来说都是极其重要且必要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者之中,很少有人系统进行过跨文化培训,有些管理工作者甚至都不具备基本的外语沟通能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去探讨留学生教育服务和管理模式的改善措施显然缺乏进一步实施和落实的基础。
无论是国际留学生和中国社会之间,还是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彼此之间,大到国家层面,小到院系或班级,都可以开展平等、开放、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文交流。因此,融合的间性观要求留学生教育工作的管理者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具有敢于创新的能力,以及敢于尝试和行动的魄力。既然我们邀请这些国际学生来中国接受高等教育,体验中国的人文魅力和优秀文化传统,那么这些与留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直接发生接触和交流的管理工作者应是最具国际化视野的优秀中国人代表。他们需要管理、服务和协调的不仅是与留学生在华学习生活有关的大小事务,也有义务为他们创造一个最理想、最开放的国际教育环境以促进文化间的交融互通。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仅靠中方管理工作者的努力,也需要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进来并进行充分的自我表达,但前者的不懈努力和自我提升不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因素,亦是来华留学生教育改革的必经之路。
四、结语
最后,让我们回到文化间性的三个要点上来。要想通过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来加速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首先要求我们接受和承认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在文化上所持有的差异,并考虑到这些差异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得以和谐共处的政治文化条件,这既是理解文化间性之基础,也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内涵。然后,为了克服多元文化主义的症结,并走向一种超越多元文化主义的道路,我们绝不能停留在接受和承认文化差异的层面上,而应集聚和利用中国社会文化的种种资源去创造出多姿多彩的跨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机会,其目的并不仅是达成不同文化间的理解——比单纯的跨文化理解更具魅力的是跨文化情境中的文化创造,并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去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式契合。而完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则需要我们在不同文化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时刻看向其关联,并将静态的知识传授过程转化为一种动态跨文化关系的建构与创造。
科学是无国界的,然而语言和文化的巴别塔却横亘在不同肤色、种族的人们之间,在他们对探索知识的方式和途径进行自由的选择的时候形成阻碍。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正逐步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优秀新生力量的出现,语言教师和专业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或许能整体上一个台阶,但文化呢?文化,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而言是一把最隐蔽的双刃剑,倘若处理得当,则蕴藏着无穷大的力量,不仅有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积极建构,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及其在国际留学生教育市场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倘若处理得不好,则有可能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甚至有进一步演变为偏见的可能性。因此,来华留学生教育,作为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内容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能被视为我国高等教育之边缘,而应以稳定的发展和高度开放的姿态来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尊重。它不光肩负着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大任,其跨文化性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它首先表现为最具国际化视野的中国高等教育从业者和来华留学生群体之间开展的与知识、语言和文化有关的教学活动及学术交流活动,当然还包括双方共同参与和创造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而当这些外来学习者回归故国或进一步走向国际社会的时候,他们又变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逐步迈入新时代的见证人和潜在的言说者及推广者。在这个层面上,留学生教育不仅仅是教学双方对普遍性知识的追求,更是和国家关系、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全面结合起来。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它首先是一个主体的重构过程,即强调不同文化主体的平等地位,在承认并保留差异的前提下达成教育方和被教育方之间互为主体的和谐共处。它以“和”为逻辑,在差异的基础上建立相互间的关联和互动交往模式,并以此建构一种多元和谐的跨文化关系。在这些互为主体的文化群体之间,其对话与交流的方式(如行为方式、共同行动的方式、意义阐释方式、跨文化理解方式及跨文化态度等)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客居地社会与文化的理解,后者在他们那里以何种方式发生意义的变迁与重组也取决于他们之间对话的方式和交流的内容。因此,这个过程应是通过主体和主体之间共同的协商与合作来完成的;它并非一场权力的博弈,而是强调多元文化主体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共享的意义和互惠性的理解。

在文化间性的引领下去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要意义便在于此。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特质,文化间性呈现于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体现在教学、管理、服务、战略制定等方方面面;持有文化间性的视角,研究者、教学者和管理者方能看到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多元的、动态的“生成观”,而非静态的“存在观”,在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并权衡自身利益需求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和国际留学生教育市场的激烈竞争现状,以此去规划一种自由的、开放的、融合的、创新的留学生教育发展战略。文化间性在这里,便从一种隐性特质走向了一种关系的建构,这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通过对话和交流建构起来的相互理解、相互适应、相互联结和依存的跨文化关系。当然,要想在文化间性的视域下去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加以支撑。但笔者相信,它绝不是一个理论空想,而会在相关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引起共鸣。
注释
①凌海衡:《主体/客体》,见汪民安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02页。


⑤刘江南:《美国高等教育与国际化动向及其战略意图》,《中国高等教育》2011年第9期。
⑦胡继华:《延异》,见赵一凡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758-759页。
⑧胡继华:《延异》,见汪民安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24-425页。








责任编辑曾新
Interculturality: An Inter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ducation in China
Liu Xuew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4)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stands in need of a stable development and a high degree of openness to earn the respect and trust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culturality, as an attribute that objectively exists in al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ducation, dialectically unifies the “difference” and the “integration”. It addresses the equal status of people from diverse cultures and point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that establish mutual understanding, mutual adaptation, and mutual connection and depen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ity,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of intercultural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learning process, teacher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education management model, examines the cultural crisis presented i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ducation in China through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cultur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helps to draw more attentions to the dynamic generating process of meaning recoding and sharing through discourse and negotiations among people from diverse cultures, and it provides an inter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ducation in China that lies beyond the limits of multiculturalism.
interculturalit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duc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2015-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