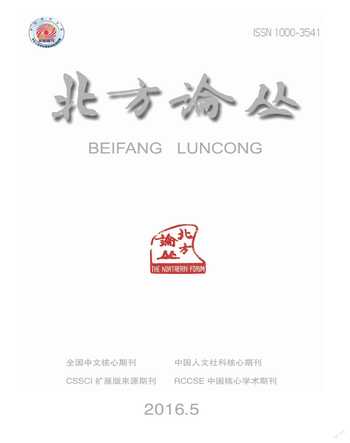“三千里步行”与穆旦的“转变”
2016-06-09段从学
段从学
[摘 要]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步行”,并没有让穆旦看到中国社会的“现实”,改变他的主体性生存立场。在抗战初期“时代感情”等因素的作用下,穆旦事实上只看到“风景”。其早期诗歌中的个人与世界之对抗性关系,经由“风景”这个特殊的现代性认同装置被保存下来。内地中国社会生活的“落后”景观,也只是一种特殊的“风景”,让诗人进一步卷入现代性生存论装置深处,埋下后来的认同危机之种子。
[关键词]穆旦;现代性;国家认同;生存论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5-0037-06
随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到昆明,横过中国西南腹地的“三千里步行”,一直被认为是促成穆旦从学徒期的幼稚走向成熟,从浪漫派的单纯,走向现代主义之复杂的关键。“转变”的前提是同一性,没有这种先在的同一性,就不可能有浪漫派和现代派的差异,更谈不上浪漫派向现代派的“转变”。为此,我们就只有先行一步,从浪漫派与现代派之间的同一性出发,才能搞清楚诗人在“三千里步行”途中看到的“现实”,究竟如何促成诗人的“转变”?这种“转变”又以怎样的形态,反过来遮蔽它得以发生的同一性?
一
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相继生成的文学潮流,的确是采取激进断裂的方式,把自己强行植入历史的。而我们也早已经习惯于循着它们的话语逻辑,把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描述为进化论时间链条上的差异性存在,以至于忘记这个基本的常识:“思想正犹如对于人一样,真实的情况乃是除非他们都站在同一块大地之上,否则他们就不可能进行战斗;在不同的理解层次之上的思想彼此交锋,是不会发生冲突或互相伤害的,因为它们永远不会发生接触,永远不会冲撞。”[1](p96)论战和冲突越激烈,把双方聚集在一起的同一性,也就越强大。
为此,在讨论穆旦的“转变”之前,我们有必要针对长久以来的错误,廓清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同一性。
事实上,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是以从个人主体性中生发出来的现代性现象,而且有着相同的历史结构。其共同之处,都是一方面把个人奉为良知和道德正当性的终极源泉;另一方面,把现实中的丑恶和不幸归咎于社会制度或文化秩序。前者坚信个人的纯洁和无辜,后者理直气壮地把批判和攻击现存话语秩序,当作不言而喻的正义行动。在这种情形之下,自觉乃至自豪地以“叛逆者”自居[2](p4),将自己“表现为一股对统治秩序的强烈愤恨” [3](p170),总是“不停地向社会结构发动进攻” [4](p92),也就成为浪漫派和现代派共同的历史形态。而且这种反叛和攻击,从一开始就不是文学艺术领域的美学事件,而是一种总体性文化运动,带有明确的历史诉求,与卢梭、马克思等人对资产阶级的攻击一切,演化成一种绵延两百余年的世界性“审美—革命”现代性现象。
海德格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现代世界的本质就隐含在世界成为被主体所支配的“图像”和人成为支配作为“图像”的世界之主体的进程中:
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同时也照亮了初看起来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这也就是说,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现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变成人类学。[5](pp94-95)
回到浪漫派和现代派身上,可以说:对现存话语秩序的批判和攻击越强烈,主体也就越是具有不言自明的纯真性;而主体的纯真性越强烈,现存话语秩序也就越是显现为亟待批判和清除的腐败之物。二者交互作用,在一轮比一轮更猛烈的愤怒批判和猛烈攻击行动中,把主体性牢牢地揳入现代文学与文化精神的核心。
一个成长中的鲜活生命,绝不可能把他热爱的作品当作无功利的审美对象,在“旁观者”的位置上来冷静地“细读”,分析其中的写作技术,再结合所谓中西文化的差异,根据表达自我和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需要,乃至“辩证地”吸收所谓的“艺术养分”。对穆旦来说,阅读行为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经验,塑造和养成其生命意识的精神养分。这种影响尽管最终通过诗人的写作活动而体现出来,但我们却不能断言它只是单纯的美学事件。按照浪漫主义的说法,有了诗人才有诗,而不是写诗的行为反过来造就诗人。
在这个意义上,就只有站在生存论立场上,才能真正理解浪漫派对穆旦的影响。我们看到,在早年作品中,穆旦一方面以“夜”和“黑暗”意象为核心,露出对外部世界的不安和恐惧感;另一方面,以《神秘》等诗为立足点,表达了返回自身,把“我”当作面对世界的基石和立足点的意向。浪漫派的影响,既以这种隐约而模糊的生存意识为根基,反过来,又将其塑造成一种明确的生命立场,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持续生长的社会文化基础。模糊的不安和恐惧感,被转化成批判现存话语秩序的自觉行动。因世界的不可信赖而被发明出来的“我”,则相应地变成不言而喻的最高价值源泉。唐湜发现的那种与社会和历史进行殊死搏斗的“肉搏者的刚勇的生命力”[6](p91)和 “向一切自然的欲望与社会的存在战斗”[7](p22)的生命意识,在笔者看来,指向的都是穆旦在浪漫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强烈而旺盛的个人主体性精神。
从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步行”,不是压抑或改变,而是进一步激活浪漫主义者激情,让穆旦更深地卷入现代性个人主体性精神的奠基性结构。
二
身处历史进程中的个体生命,不可能根据“历史真相”之类的后设叙事,而只能根据其当时遭遇的现实经验来面对未来,选择并确定自己的生活道路。至于這些现实经验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是否“真实”“正确”,与当时的选择是否“正确”,感受是否“真实”,丝毫没有关系。今天的我们,因为有了时间距离产生的“后见之明”,在知识学层面上看见战争的血腥和残暴,也就容易在“救亡压倒启蒙”论的蛊惑下,把高扬主体性精神的启蒙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救亡当作水火不容的历史存在,想当然地认定穆旦必然带着痛苦和精神分裂的现代主义体验来体验和书写抗战。
但事实正如艾青所说:“卢沟桥的反抗的枪声叫出了全中国人民的复仇的欢快。”[8](p120)抗战首先带来的,是举国上下一致的欢呼和激动。穆旦也和当时的爱国志士一样,长久的忍耐和等待之后,在终于到来的战争中,看见用自己的鲜血来洗刷耻辱和尘垢,重建华夏神州“庄严的圣殿”(《合唱二章》)的历史机缘。年轻的诗人带着兴奋和激动踏上“三千里步行”的长途,“三千里步行”又反过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这种兴奋和激动。时任“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指导教师的闻一多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举国上下都在抗日的紧张情绪中”。一路上,“同学们的情绪很好,仿佛大家都觉得上面有个英明的领袖,下面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战,反正是没有问题的”[9](pp428-430)。在这种特殊而具体的“时代感情”的激荡和鼓动下,旅行团一路“高高兴兴地唱歌,步行时唱,晚上也唱”[10](p541),满怀着兴奋不已的激情,从长沙到了昆明。从江西、广西一路西迁昆明的冯至,也从侧面证实这种“时代感情”的普遍性。冯至先生说,尽管先后遭遇到南京失守、武汉撤退等重大挫折,报纸上没有多少好消息,几乎天天都要因为日军的空袭而跑警报,但人人都“好像很年轻”,对未来充满信心[11](p67)。
置身于这种“时代感情”的裹挟和激荡之中,“三千里步行”途中的穆旦,其实并没有看见通常所说的“现实”,而只是看见“风景”。通过沿途所见的“风景”,诗人的个人激情、普遍性的“时代感情”,最终在“新生的中国”里得到有机的统一,完成从拒绝和批判现存话语秩序,到拥抱“现实”的“转变”。《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和《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两首诗,完整地讲述诗人如何从“失去了一切”的茫然开始,沿着“明亮的道路”,在“自由阔大的原野”上,找到“自由而辽远”的“中国的道路”,最终完成自己的“转变”的过程。
“三千里步行之一”的《出发》一开篇,就将湖南中西部丘陵地带的“风景”和“祖国的心脏”紧扣在一起,把“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变成“祖国”的形象化表征。紧接着,在一段略显忧郁的“自我”独白后,诗人再一次呼应着“祖国”,开始对“中国”景象的细腻描绘:
在军山铺,孩子们坐在阴暗的高门槛上,
晒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
在太子庙,枯瘦的黄牛翻起泥土和粪香,
背上飞过双蝴蝶躲进了开花的菜田……
在石门桥,在桃源,在郑家驿,在毛家溪……
我们宿营地里住着广大的中国的人民,
在一个节日里,他们流着汗挣扎,繁殖!
我们有不同的梦,浓雾似地覆盖在沅江上,
而每日每夜,沅江是一条明亮的道路,
不尽的淘淘的感情,伸在土里扎根!
哟!痛苦的黎明!让我们起来,让我们走过
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
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的两旁。
在二者交互作用中,马尾松、梧桐、沅江、开花的菜田等现实之物,“祖国”的统摄下,从生存论领域的真实存在,变成镜像中的“风景”;作为想象之物的“中国”,则附着在“风景”之上,获得它鲜明生动的美好形象,反过来召唤着诗人全身心地投入。
《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则在“渔网似的城市”、“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和“自由阔大的原野”的强烈对比中,直接把作为“风景”的道路、个体生命的内在激情、中国/祖国的自由三者,熔铸成一个有机的诗性世界,一个眼前现实的“风景”、个人内在感受和作为图像的“中国”交融在一起的圆融的化境。春天的南方“自由阔大的原野”的绿色,包围着诗人,拥抱着诗人,让诗人觉得不是走在绿色的原野,而是浮游在一望无际的“浓郁的绿海上”。沿着“浓郁的绿海”这个意象,其他 “风景”的颜色,也被诗人感受成不同的“海”,“蓝色的海,橙黄的海,棕赤的海……”,进而与地图学意义上的包围着中国的大海联系起来,有如“在浓郁的绿海上浮游”一般行走在原野上的“我们”,反过来成为地图透视学镜像中的蚂蚁,与中国的原野融为亲密的生存整体:
欧!我们看见透明的大海拥抱着中国,
一面玻璃圆镜对着鲜艳的水果;
一个半弧形的甘美的皮肤上憩息着村庄,
转动在阳光里,转动在一对蚂蚁的腳下,
到处他们走着,倾听着春天激动的歌唱!
听!他们的血液在和原野的心胸交谈,
(这从未有过的清新的声音说些什么呢?)
欧!我们说不出是为什么(我们这样年青)
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泻着不尽的欢畅。
借助于地图学透视镜像,将行走在原野上的年青的“我们”,与“原野”一起,凝聚为“血液在和原野的心胸交谈”着的亲密整体之后,穆旦返回到个人与“风景”之间的关系环节上,从“我”的视角出发,重新展开对“风景”的透视。由于有了地图学透视镜像视角建立起来的“我们”“原野”“祖国”等三者之间的亲密关联为先在基础,眼前的“原野”,也就相应地从作为现物的“风景”,转化成“祖国”和“中国”的具体形象。南方的“原野”成为“中国的土地”,道路变成“中国的道路”。饱满而浓烈的激情,把抽象的“中国”和眼前的“风景”熔铸成一个透明的有机整体:
我们起伏在波动又波动的绿油的田野,
一条柔软的红色带子投进了另外一条
系着另外一片祖国土地的宽长道路,
圈圈风景把我们缓慢地簸进又簸出,
而我们总是以同一的进行的节奏,
用脚掌拍打着松软赤红的泥土。
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
多少年来都是一样无际的原野,
(欧!蓝色的海,橙色的海,棕赤的海……)
多少年来都澎湃着丰盛收获的原野啊,
如今是你,展开了同样的诱惑的图案
等待着我们的野力来翻滚。所以我们走着
我们怎能抗拒呢?欧!我们不能抗拒
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
联系穆旦早年的相关作品来看,“渔网似的城市”这个一闪而过的意象,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换:诗人的生存世界,已经从切身而压抑的城市背景里的“周围”,变成阔大而自由的“中国的原野”。这就意味着:通过“三千里步行”途中的“风景”,诗人暗中将自己从切身性的生活世界里“提取”出来,置入“风景/中国”这个崭新的生存世界。质言之,诗人在这里,不是进入“现实”,而是从相对而言比较“现实”的“周围”,进入想象性的生存世界。
正如柄谷行人所说,“风景”并非存在于外部的客观之物,“为了风景的出现,必须改变所谓知觉的形态”,需要观察者自己从外部世界中抽身出来,成为纯粹的观看者,才能把一直就“在那里”的客观之物看作“风景”,发现“风景”之存在。“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无所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12](pp14-15)。而“风景”一旦被“内在的人”发现为“风景”,就以自然存在的“客观之物”的形态,把自身的起源掩盖起来,与“内在的人”互为主客体的两极,构成奠基性的现代性认识论装置。
现代文学中的“风景”与“看风景的人”——借用卞之琳《断章》语——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现代性认识论装置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即海德格尔所说的,人成为主体和世界成为图像两个互相交叉的现代性进程。人通过支配世界而把自己设定为主体,因而对世界的支配和控制越深入,人的主体性根基也就越加牢固和深入,越加成为支配和控制世界的主体,成为执着于其内在“自我”的“现代人”。
回到穆旦身上,南方自由而阔大的原野越是显现为“风景/中国”,则诗人也就更加隐蔽而深入地固定到作为“看风景的人”的主体性地位上,亦即越强烈地深入到浪漫主义的核心,深入到他任性而专横的“自我”意识内部。而越是如此,他也就越加无视真实的外部世界,越加把“风景”看作“风景”。二者互为因果,交互作用,把行走在南方原野上的诗人,牢牢地锁进现代性生存论装置。
皮相的说法是:浪漫主义者喜爱大自然,喜欢描写各种各样新奇的“风景”。但事实上,正是通过“风景”,浪漫主义者才成为浪漫主义者。既不是在时间序列上先凭空产生浪漫主义者,才有了浪漫主义者对“风景”的描写,也不是“风景”一直就“在那里”等待着浪漫主义者去“看”。而是“看”的行为,纯粹认识论意义上的“看”这个功能,让浪漫主义者成为浪漫主义者,让“风景”成为“风景”。在这个以“看”为纽带的现代性认识论装置中,“风景”成为“风景”和浪漫主义者成为浪漫主义者,乃是一个交叉并存、互为主客体的整体进程。 “风景”越是显现为“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就越是成为专注于内在“自我”的浪漫主义者;而“看风景的人”越是深入“自我”,则“风景”也就越是显现为纯粹的“风景”。
事实很明显:“三千里步行”,不仅没有让穆旦从浪漫主义的影响中解脱出来,而是让他在“看风景”的过程中,“转变”成更彻底的浪漫主义者。不同的是,早年的穆旦是以拒绝和反抗的姿态面对世界,而在“三千里步行之后”,则变成一个拥有无穷的“野力”,并且能够凭借这种“野力”推动“新时代”来临的行动者,一个能够有能力征服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动主体。这种“转变”,与另一种特殊的“风景”密切相关。
三
不错。穆旦确实看见“内地农民的艰辛”,看见广大的中国的人民“流着汗挣扎,繁殖”(《出发》),看见西南腹地小镇落后而愚昧的生存现状。但正如《小镇一日》指出的那样,这一切并非诗人的生活世界,而只是一幅画,旅人眼里的一片“风景”:
一个旅人从远方而来,
又走向远方而去了,
这儿,他只是站站脚,
看一看蔚蓝的天空
和天空中升起的炊烟,
他知道,这不过是时间的浪费,
仿佛是在办公室,他抬头
看一看壁上油画的远景,
值不得说起,也没有名字……
这里的关键,不是“现实”是什么,而在于它以怎样的形态进入诗人的体验结构。正如“风景”并非因其“自然之美”,而是因“内面的人”之“看”才成为风景一样,西南腹地“落后”之所以“落后”,乃是因为“看风景的人”预先站在“先进”的位置所致。同样的“落后”之物,同样是“聚集着黑暗的茅屋”,之所以会成为厌倦现代“先进”文明旅行者眼中的“风景”,根源就在這里。
内地中国“落后”景观,不仅没有改变诗人的主体性精神结构,反而强化“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唯其“落后”,才激发出居于“先进”位置上的穆旦按照自身意愿改造“落后”现状的激情。而个人也因这种改造“落后”的行动,反过来把自己更为隐秘地置入“先进/落后”的现代性认同机制。
这个“先进/落后”的线性时间装置,实际上和“风景/中国”的空间认同装置交织在一起,互为补充,把复杂多样的战时内地中国景观,吸纳进诗人的主体性精神结构。我们看到,“三千里步行”途中遭遇的内地中国景观,在以优美的“风景”召唤着穆旦,召唤着旅行团成员,在让人深感“中国之伟大”的同时,又以其“落后”的一面,引诱着年青的穆旦,促使他自觉地站在“先进”位置上,涌动着以自己的“野力”来开发中国的“落后”地带的豪情和决心。
这一点,也不是穆旦个人独有,而是“湘黔滇旅行团”成员共同的“时代感情”。当他们踏上湘滇公路之后,钱能欣曾如此描绘这种“时代感情”说:“沿着这条公路,到尽头便是我们的目的地——昆明,可是我们的兴趣的指针并不是正向昆明的;在公路两旁,深深地隐藏着而期待我们的两条腿去开发的,才是我们的希望。”[13](p148)在“看风景的穆旦”这里,千百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同样也袒露出它全部的秘密,展开“同样的诱惑的图案/等待着我们的野力来翻滚”(《原野上走路》)。充满无穷的“野力”,挣脱“旧世界”束缚的穆旦,就这样在从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步行”中诞生了。
从谱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穆旦,同样属于我们熟悉的“不但善于打破旧世界,更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现代性激进主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脉络中,此一“发展”,不过是处变不惊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现象中,稍显复杂的个案而已。
从以后的具体表现来看,可以把“三千里步行”对穆旦的影响,概括为相互交叉的层面。它进一步强化穆旦以本能的童年经验和英语浪漫主义诗歌文化为养料的现代性个人主体意识,将其从个人与异己性世界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发展成更为积极的创造新世界,推动新时代之来临的行动者。脱离北方逼仄而压抑的城市生活空间的“解放感”,以及作为“看风景的人”的旅行者身份,为穆旦提供向着未知的世界挺进并支配和征服之的现代性可能。这种发展,不是通常认为的后者取代或者彻底涵蓋前者,而是在保留前者的同时,增补上后者。
以“风景”,——准确说,是以南方开阔而自由的“原野”为契机,诗人为自己《哀国难》等早期作品中的“古国”、抗战初期全国上下一致的爱国主义激情、想象中的“新时代”三者,找到一个整体性意象:“新生的中国。”这个意象,首先其亘古不变的自然属性,接纳穆旦对历史上的辉煌“古国”之想象,让诗人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的自豪感,让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经由原野上的道路,流淌进诗人心中,建立穆旦个人与“古国”祖先之间的情感共同体。进而又以“自由而阔大”的“蓝色的海,橙色的海,棕赤的海……”和“丰盛的收获”,把地理位置上的前方道路和象征意义上的中国未来联系在一起,呈现为充满诱惑的希望,让诗人渴求着拥抱它,用“我们的野力”来征服它,改造它,使之变成一个理想而又现实的“新时代”。
而诗人则反过来在这种征服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位置上,进一步变成更有力量、更具“野力”的行动者。拥抱“新生的中国”,汇入“新生的中国”生机勃勃的“洪大的合唱”,因此而从澎湃汹涌的“时代感情”,转化成诗人内在的生命冲动。
作为想象性宏大之物的“中国”,就这样与穆旦最为珍视的现代性个人,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一如母亲与孩子通过血缘——“血液”是穆旦最爱使用的意象——纽带,“自然地”联结在一起。诗人以孩子和母亲的自然血缘关系为喻,把个人塑造成“必须扶助母亲的生长”的能动主体(《中国在哪里》)。而站在“先进”的立场上,反过来“扶助母亲的生长”的责任意识,实际上反过来,暗中颠覆个人与作为“母亲”的祖国之间的自然关系,把“母亲”变成一个可以,而且有待于通过个人的努力来生成的“人工制品”。穆旦个人,则在这种颠倒中,再一次回到“先进”位置上,成为改造和征服包括“祖国”在内的一切存在的现代性主体。
在通常误以为诗人已经完全放弃自我的地方,穆旦仍然是从现代个人主体性的立场理解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把现代民族国家理解为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建构和塑造的“人工制品”。众所周知,这种把民族国家当作人为建构的“人工制品”的现代性立场,以及诗“不再被理解为一种有灵感的模仿或者再生,而是被理解为创造”的浪漫主义诗学观,乃是同一种现代性原则在不同领域的体现。这一原则就是:根据个人设定的“应在”理想状态,来强行要求和规范“实在”状态,不断掀起凭借人类自身力量改造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现实世界的激进革命[德]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刘小枫编、彭磊等译:《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2页。。
这就是说,穆旦在“三千里步行”中建构起来的中国,实际上并非一直就“在那里”的自然之物,而是在“风景”的作用下,被置换成现代性时间轴线上的“未来”,一个有待通过现代性主体的推动而形成的“新生的中国”。现代性个人与既存社会秩序之间的空间性对立,由此被穆旦解读成战前“灰色的中国”和抗战爆发之后的“新生的中国”在线时间轴上,因而是可以消除的对立。而个人,则因其不言而喻的纯真性,成为消除这种对立,制造“新生的中国”的能动主体。共时性的结构性对立,被置换为历时性的对立,但世界的不可信赖和个人的天生正义这个奠基性的生存结构,却依然如故。一个是强烈的否定,一个是同样强烈的肯定,二者一正一反,牢牢地锚定诗人的生存空间,激荡着穆旦“年青的血液”,让他沿着现代线性时间轴,在参与“群众的洪大的欢唱”[14]的行动中,彻底卷入现代性生存论装置深处。
诗人早年在对周围世界隐约不安的恐惧中生成的拒绝现存社会秩序,转而诉诸个人自明性的主体性精神结构,并没有因为“三千里步行”而发生变化,反而以“风景”为契机,从现代性时间轴线上的“过去”和“未来”两端同时受到强化。满怀激情投身于“新生的中国”,渴望着在新时代洪流中获得新生的穆旦,很快发现自己“永远走上了错误的一站”(《幻想的乘客》),不得不返回最初的“原点”,再次开始打破丑恶与黑暗的“突围”,——以及这种“突围”必然失败的根源,就在这里。
[参 考 文 献]
[1][美]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M]何兆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英]马里琳·巴特勒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M]黄梅,陆建德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袁可嘉编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资料:上[M]刘长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5][德]马丁·海德格尔世界的图像时代[C]//林中路:修订本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唐湜搏求者穆旦[C]//新意度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7]唐湜诗的新生代[C]//新意度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8]艾青为了胜利——三年来创作的一个报告[C]//艾青全集:第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
[9]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C]//闻一多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0]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1]冯至忆平乐[C]//冯至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12][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3]张寄谦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4]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N]大公报,1940-04-28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