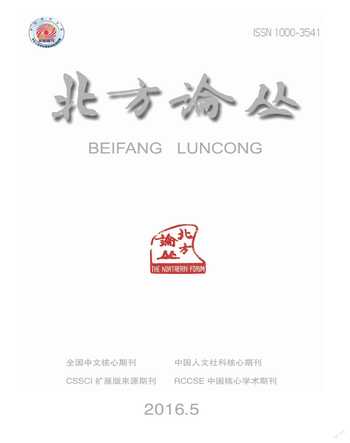异境想象与现世感知
2016-06-09王允亮
王允亮
[摘 要]神游赋是先唐时期颇为兴盛的一种文体,自《离骚》开始,一直到南北朝绵延不绝。在先唐神游赋的发展过程中,经历巫文化、黄老之学、儒家思想、玄学思潮、新自然主义相继为主导的变化。受此影响,其体现出来的空间观念也不断发生变化,在最为核心的异境漫游上,经历由偏重西北昆仑一隅至四方天地均衡分配的变迁,在最终归向上则有求神境而不得,游神境而自得,舍神境而归现世的不同转变。在神游赋发展过程中,异境想象的地位渐渐低落,与此相反对现世的认同却逐渐增加,二者间存在相反的升降过程,体现出人文主义精神在六朝的变化。
[关键词]神游赋;先唐 ; 异境想象;现世感知;文化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5-0009-07
Abstract: Spirit wanders fu that starts from Lisao until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as a prosperous style of writing before Tang Dynasty.This style of writing experienced Several different thoughts,such as sorcery, Laozi and Zhuangzi, confucianism, metaphysics and new naturalism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It also experienced the decription of the travel from notable about Kunlun to priority about all bearings.In different time,there existed different interaction between imagine space and reality space in spirit wanders writings. On the all,in the development of spirit wanders fu Before Tang Dynasty embodies the effcetion of the social culture change exert to literature creation.
Key words:Spirit Wanders Fu;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Imagine of Fantasy World;Idea of Present World; Cultural Spirit
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得意的时候,总会有背世越俗、轻举远游的念头。春秋时期的孔子曾经说过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便是这种心理的典型反映。战国晚期以来,随着神仙思想的兴起,为这种浪漫的远游想象又添上一抹瑰丽的色彩。在文学上,也产生很多以漫游为题材,表达摆脱尘世束缚,与仙灵为友,餐云气,御飞龙,游观于四海八荒,自由而无羁绊的高蹈远引愿望的作品。先唐以《离骚》为起点的神游赋系列,便是这类作品的典型,它们源远流长,作品繁富,形成独特的流派与风格。由以“游”为主线的写作模式所决定,空间是神游赋作品构成的基本要素,因文化风尚所致,不同时期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空间观念,异境想象与现世感知间也存在微妙的互动关系。对这些神游赋单篇作品的研究虽有不少,但以先唐神游赋为一个系列,从想象空间与现实世界互动关系视角进行研究尚未见有人尝试。因此,本文拟从文学空间认知的维度出发,对先唐神游赋系列中的空间关系做一考察。
一、从巫觋天地到神仙世界
神游赋的发端作品是楚三闾大夫屈原的《离骚》,先秦时期的楚国属于南方偏远地区,相对来说文化比较落后,巫风盛行,加之山川萦纡,林木茂密,很能激發楚人的想象,故与中原偏重理性的文学风格相比,荆楚文学大多想象奇特,呈现出浪漫瑰丽的特色,比较典型的体现便是《离骚》和《庄子》这两部文学作品。《离骚》对后世神游赋基调的奠定,起到关键作用,继之而起的《远游》同样是神游赋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这两篇作品中,想象空间作为作者逃避现实的乐土,被加以浓墨重彩地讴歌描摹,现世空间则处于被厌弃与拒绝的地位。接下来对这两篇作品做一探讨。
(一)巫觋背景下的神话天地
《离骚》最让人关注的是其变生天外、想象奇特的漫游过程。就对漫游经历的描述来看,屈原的重点在于西方,其“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诸语所论虽及四方,然多点到为止,没有更深入地进行阐述。至于天上漫游的渴望,由“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可以看出也没有得以实现。其自“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以下22句所着力描写者,则为昆仑西北一隅。而在中间短暂的进行历史问题思辨之后的第二次漫游,亦以西方为漫游的唯一目的地,自“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以下,花费约12句笔墨进行描述。
《离骚》的空间观念中,天地四方的位置感不是很严格,行文也不讲究篇幅的均匀,主要着墨于西北一隅。这是由先秦神话中昆仑山的特殊地位而决定的,《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而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 [1](p.294) 又《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1](p.407)又《史记·大宛列传》:“《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 [2](p. 3830)这些材料均说明昆仑为神圣之所,是西王母及诸神仙所居之处,藏有各种奇珍异宝,其重要地位甚至要超过天庭,所以,《离骚》对其进行浓墨重彩的描述。
其次,《离骚》中巫文化特征明显,这从为屈原占卜的巫咸和灵氛之身份便可知道。巫咸其人,顾名思义,为上古神巫之一。灵氛,王逸注谓古之善占者,然亦和巫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说文解字》玉部云:“灵,巫也。以玉事神,从王,霝声。靈或从巫。”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灵”字下注云:“《周礼》,司巫,凡祭祀守。注云:谓若祭地祗有埋牲玉者也。”“楚屈巫,晋申公巫臣并字子灵。《大荒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并从此升降。”[3](p.43)《九歌》:“灵偃蹇兮皎服。”王逸注云:“灵,巫也。楚人名巫为灵。”可见从字源学上来说,“灵”字即起源于巫文化,灵氛亦当为上古巫者之一。文中所出现人物除灵氛、巫咸外,尚有望舒、丰隆、飞廉、羲和等,多为日、月、风、雷之神,均为自然现象的人格化。结合《楚辞·九歌》诸章可知,楚地巫文化发达,屈原构想出来的异境空间有着浓郁的巫觋色彩。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离骚》中的现实世界,屈原文中的现实世界对他来说是个压抑窒息的存在,即使他曾做过不屈不挠的抗争,但却全部归于失败。浪漫瑰丽的天外之游,并没有使他与现世的关系缓和,反而使他对人生趋于绝望,其刚直人格使他与现世始终无法调和,故而只有以死殉志一条路。作者最后说:“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对现实世界的彻底绝望,没有任何的妥协与折中,故而在神游失败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亡。
(二)五行架构下的神仙世界
《远游》历来被认为是屈原所作,但怀疑者亦不乏其人,宋洪兴祖就发现了《远游》和屈原其他作品的不同,他在《遠游》注中说:“《骚经》、《九章》皆托游天地之间,以泄愤懑,卒从彭咸之所居,以毕其志。至此章独不然,初曰:‘长太息而掩涕,思故国也。终曰:‘与泰初而为邻,则世莫知其所如矣。”[4](pp.174-175)这种怀疑到了近世更加明显,虽然《远游》的作者迄今仍无定论,但很多学者将其视为汉代人的作品 刘永济《屈赋通笺》,游国恩《楚辞概论》,陆侃如《中国诗史》,胡小石《远游疏证》(载《胡小石论文集》)等均否定《远游》为屈原所作,认为当产生于汉代。。
要讨论《远游》的年代,其中“奇傅说之托星辰兮,羡韩众之得一”一句尤其值得我们注意。韩众是谁?对于韩众的身份,王逸在《楚辞章句》里没有解释,只是说了一句:“众,一作终。” [4](p.164)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引《列仙传》云:“齐人韩终,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也。”[4](pp.164-165)然而,《列仙传》虽旧题为刘向所撰,但《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所撰书目不言有《列仙传》,《四库全书总目》撰者疑其乃魏晋间方士所为 [5](p.1248)。因此,它关于韩终的记载可信度并不高。其实,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名为韩众的人,是为秦始皇身边的方士,《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二年载:“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2](p.319)至三十五年又载:始皇闻(卢生等)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2] (p.325)
《史记正义》云众“音终”[2](p.326),则两处所言韩众、韩终实乃一人。顾颉刚认为,韩众乃秦始皇身边为他求药的燕齐方士,后来畏罪逃亡,不知所踪,后人因附会出仙去的传说,他就是《远游》中提到的“韩众” [6]。顾氏的这种推测是合理的,梁刘孝胜在具有神仙色彩的《升天行》诗中,曾写道“少翁俱仕汉,韩终苦入秦”[7](p.920),足证仙人传说中的韩终与秦始皇身边的方士韩终实为一人。因此,《远游》一文的写作年代当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以后。
再进一步说,如果将《远游》“舒并节以驰骛兮,逴绝垠乎寒门”“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倏忽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与《大人赋》“遗屯骑于玄阙兮,轶先驱于寒门。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乘虚无而上遐兮,超无有而独存”进行比较,就不会否认两篇文章之间存在关联,从对想象世界的构建来说,《远游》远较《大人赋》规整有序,依观念意识发展的常理来说,它的创作时间应较《大人赋》为后。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再结合《远游》被刘向编入《楚辞》的事实,可知其为楚地士人所作,其文中鲜明的老庄及神仙思想,则与刘安时期淮南王国重神仙道家思想的学风相一致,所以,我们认为它很可能出自刘安周围的淮南宾客之手徐复观在《〈淮南子〉与刘安的时代》一文中,曾经精辟地指出刘安及其身边的宾客,都是时代氛围下的受压抑者,这种情况与《远游》中“悲时俗之迫阸兮”的思想一致,见《两汉思想史》(二),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267页。。无论如何,将其作为《离骚》,以及《幽通赋》《思玄赋》等作品的过渡篇章来看是比较合理的。
就《远游》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特色来看,与《离骚》中浓厚的巫术气息相比,有比较明显的老子和神仙家思想。前者如“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视倏忽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诸语;后者如“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奇傅说之托星辰兮,羡韩众之得一”等语。诚如作者所云,他所向往境界的是“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
就漫游的经历来说,《远游》也有一定的特点,其有次序之漫游,从入天庭以后开始,所游之次序为上天、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地下,空间方位感极其清晰。与漫游空间的方位相应,则有各方位与神祇之配合,如文中出现的东方句芒、太昊,西方蓐收,南方祝融,北方玄冥、颛顼,这些信息透露出五行学说的构架特色,与《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所述一致,说明作者的空间认知中有着明确的五行观念。综而言之,《远游》的空间观念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以阴阳五行为框架,以神仙思想为内容的想象空间。这是汉代前期黄老道家、阴阳五行、神仙方技之学兴盛在文学中的反映。
就现世空间来说,仅在《远游》发端被一笔带过,后来再也没有提及。作者的全部心力都关注在异境漫游上,现实世界对他来说仿佛并不存在,体现出他对现世的憎恶。就漫游历程来说,与《离骚》不同,《远游》并没有回归到现实世界,主人公的漫游似乎取得成功,并最终以老庄避世隐逸之道为依归,这充分显示出现实世界在作者心目中的无足轻重。所谓神仙之境的恣意遨游,只不过是他隐遁避世思想的一种形式化表现而已,士人通过羽翼飞升、长生久视的想象,以对抗现实世界的微妙心态,在《远游》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当然,在这两篇以异境漫游为主的神游赋中,也透露出中国文化演进的关键信息。就传统思想的发展来说,先秦时曾有由重巫至重道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以道代神,用心能体道代巫能降神,这一转变至战国时期已基本完成。《庄子·应帝王》中,道家大师壶子战胜神巫季咸的斗法,便是这种思想转变的体现[8](pp.9-10)。然而,与思想转换的大传统相较,巫术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退而作为小传统的一支在民间或边远地区存在。楚国远离中原文化圈,还保留有巫术文化的影响,这一点被《离骚》所吸收。屈原结合巫觋传统与楚人的空间观、神话知识而虚摹出来的漫游,为以后的神游赋奠定格局。由《离骚》巫文化为主导,至《远游》以老庄为外壳的神仙五行思想兴起,体现出由巫觋之学至诸子之学的转变,而《离骚》和《远游》中对于想象空间的不同描绘,也是这种两种文化性格的彰显。但现实世界,在文本中的缺失,则是它们的共同特色,体现出想象空间与现实世界,在这个长时段内的紧张对立。
二、儒家伦理世界的发现
东汉时期的神游赋创作也不乏其人,陆机在《遂志赋序》中曾有略述:
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简而有情,《显志》壮而泛滥,《哀系》俗而时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练而和惠,欲丽前人,而优游清典,陋《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虚温敏,雅人之属也。衍抑扬顿挫,怨之徒也。岂亦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余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9](pp.473-474)
在这些作品中,《显志赋》与神游赋性质有别,《玄表》与《哀系》没有保存下来,保存较完整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则为班固的《幽通赋》和张衡的《思玄赋》,接下来我们对这两篇作品做一探讨。
(一)异境想象的舍弃
班固的《幽通赋》是先唐神游赋系列中,比较特殊的一篇,文中虽然有对梦境的描述,但通篇并无神游赋作品常有的漫游过程,然而,即使如此,古今论者却也一致把他归到神游赋系列中进行考量。如孙梅《四六丛话》卷三:“若夫《幽通》、《思玄》,宗经述圣,《离骚》之本义也。”[10](p.45)刘师培《论文杂记》:“忧深虑远,《幽通》《思玄》,出于《骚经》者也。”[11](p.111)
而《幽通赋》之所以有此特点,和班固的思想有很大关系。班固服膺于儒学,对神话秉持《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对于《离骚》中的神话传说,也持批判的态度,这一点在他的《离骚章句序》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4](p.50)他既认为这些文字“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在《幽通赋》创作中略去相关环节自属正常。
除了对《离骚》撷取怪诞神话多有不满,班固还对屈原的行为提出了批评: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4](p.49)
又云:
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 [4] (p.49)
和《离骚》中遭受不公后的刚直抗争相比,《幽通赋》中多守道任命之语,如“所贵圣人之至论兮,顺天性而断谊”,“浑元运物,流不处兮”等。当然,班固的安身任命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中“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恶而不避。守孔约而不贰兮,乃车酋德而无累”,“谟先圣之大猷兮,亦邻德而助信”等语足可说明。同时,他也对老庄思想提出了批判:“周、贾荡而贡愤兮,齐死生与祸福。抗爽言以矫情兮,信畏牺而忌鵩。”
班固是第一个将儒家思想引进神游赋系列的人,这在神游赋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后世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清张甄陶云:
通篇立义正大,俱同曹大家《东征赋》。庄老狂流,悉力截断,引绳据墨,俨然儒者典型。[12]
浓厚的儒家意识使班固在神游赋中舍弃光怪陆离的异域境象,与《离骚》和《远游》相反,《幽通赋》对异境着墨甚少,它从儒学立场出发,将价值取向全部指向现实社会,异境空间的价值则被否决。这是先唐神游赋发展历程中的根本转折,稍后于班固的张衡即以儒家伦理为指归,构建神游赋中的伦理世界。
(二)儒家伦理世界的发现
《思玄赋》之漫游经历描述是先唐神游赋中最长的,其漫游次序也与以前不同,由东方开始,依次为南方、西方、中区、北方、地下、昆仑,至上天结束。昆仑游被安排在天地游之间,这大概是由于秦汉时期,昆仑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沟通地底与天界之通道有关。《淮南子·墬形训》云:“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13] (p.322)又:“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13] (p.323)高诱注云:“太帝,天帝。”[13] (p.328)故昆仑游被安排在天地之游中间。
除了对四方的描述之外,《思玄赋》在天庭漫游上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叙述作者受到天帝的款待,射猎赏乐,泛舟天汉,想象奇特,文字华美,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清何逢僖云:“唯末段天外一游,不特班所无,亦《骚》所无。视之《二京》角抵、大傩,尤为奇特,远思出宏域,真令人一读一击节也。”[12]这段描写将张衡丰富的天文知识展示得淋漓尽致:
出紫宫之肃肃兮,集太微之阆阆。命王良掌策驷兮,逾高阁之将将。建罔车之幕幕兮,猎青林之芒芒。弯威弧之拔剌兮,射嶓頉之封狼。观壁垒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泛泛兮,浮云汉之汤汤。倚招摇摄提以低徊戮流兮,察二纪五纬之绸缪遹皇。 [14] (p.761)
几乎每一句都包含有相应的星座,紫宫、太微、王良、高阁、罔车、青林、威弧、封狼、壁垒、河鼓、天潢、云汉、招摇等依次出现,整个文意融而为一。这种情況和张衡曾任太史令之职,熟悉天象知识有很大的关系。相对于《远游》对星象的泛泛带过而言,张衡将它集中在天庭部分描写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浪漫的想象和雅致的词汇,将前人不甚留意的天庭空间,构建成异境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通过与《远游》前拙后工的对比,体现出文学同题共作中后来居上的竞争意义。
当然,更重要的是《思玄赋》继承了《幽通赋》儒家思想主导的特色,重新发现了儒家伦理世界的存在意义,赋末云:
收畴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长余佩之参参。文章奂以粲烂兮,美纷纭以从风。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驱儒墨以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嘉曾氏之归耕兮,慕历阪之嵚崟。恭夙夜而不贰兮,固终始之所服。夕惕若厉以省諐兮,惧余身之未敕。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逍遥。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 [14] (p.761)
与异境空间的荒怪陆离相较,儒家道德秩序主导的尘世空间反而更为可亲,赋予人存在的价值意义。张衡虽然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对想象世界进行描绘,但从理智上来说,他对于这一切并不十分热衷,反而经常从儒家立场出发对仙境中的淫荒之处进行批评,对神仙世界的周游,更坚定了他遵循人间道德秩序的信心,徜恍迷离的神界旅行,只是他对现实儒家道德伦理世界重新发现前的一段曲折历程而已美国学者康达维《道德之旅——论张衡的〈思玄赋〉》一文,对张衡《思玄赋》中的儒家伦理道德进行探讨。参见康达维著,苏瑞隆译:《康达维自选集: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219页。。
从思想基调上看,张衡对于神仙谬悠之说并不崇信,他营造出来的迷离幻境,在儒家思想的映照下也并不质实。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论是对天地四方,还是昆仑中区,还要不遗余力地进行描写呢?这首先决定于神游赋创作的格套效应,漫游的模式自《离骚》开端,已经被认为是神游赋组成的基本要素,除非如班固那样对神怪风格进行彻底批判,否则便很难不受其影响;其次,文中异境想象还来自张衡对之前神游赋意象的有意整合,这种做法则出自同题创作时的文学竞争心理徐复观在《扬雄论究》中,曾经评价扬雄为知识型文人,他以模仿为特色的创作习惯,实有与前人一较短长的求胜心理,其实,张衡文学创作上模仿《两都赋》写《二京赋》,模仿《蜀都赋》写《南都赋》,模仿《答客难》写《应间》的做法,也具有这方面的因素。参见《两汉思想史》(二),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400—512页。。因此,虽然张衡描绘了令人目眩神迷的异域境象,但对儒家伦理空间的彰显,才是他神游思想的基调。张衡的这一做法也对后来的神游赋创作产生影响,之后神游赋虽然仍延续对异境的华丽描摹,却基本都放弃对异世空间的追求,将关注点更多放到现实世界中来。
总之,《思玄赋》篇幅宏大,文笔瑰丽,其仙境构想来自《离骚》《远游》,主导思想来自儒家伦理,可谓之前神游赋系列的集大成者,清洪若皋评曰:
立意祖《离骚》,布局拟《招魂》……则仿《幽通》,收束道德仁义,则又仿《上林》、《长杨》,是善集众长者。至文情艳发,音韵清殊,真所谓绝唱高踪,无复嗣响者矣。 [15] (p.772)
三、玄学观照下的现世胜境和新自然主义的诗意空间
魏晋以后,也有不少作者进行神游赋创作,除了前面所述陆机《遂志赋》之外,据《晋书》卷五十四载陆喜“读《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娱宾》《九思》”,可见陆喜曾模仿《幽通》《思玄》创作神游赋作品。此外,属于同一类型的还有西晋挚虞的《思游赋》和南北朝阳固的《演赜赋》,分别被收入《晋书》卷五十一和《魏书》卷七十二,故而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两篇文章的空间认知也体现了不同的文化风格,接下来对这两篇作品做一考察。
(一)玄学观照下的现世胜境
其实,挚虞作为一个有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曾对神游赋系列作品做过评价,迄今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下》中,还有评语:“挚虞论邕《玄表赋》曰:‘《幽通》精以整,《思玄》博而瞻,《玄表》拟之而不及。” [16] (p.925)在评价神游赋作的同时,挚虞也进行实际的创作,写有《思游赋》一文。对于《思游赋》的创作缘起,《晋书·挚虞传》中说:
虞尝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祐者义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顺,所以延福,违此而行,所以速祸。然道长世短,祸福舛错,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荡而积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陈处世不遇之难,遂弃彝伦,轻举远游,以极常人罔惑之情,而后引之以正,反之以义,推神明之应于视听之表,崇否泰之运于智力之外,以明信天任命之不可违,故作《思游赋》。 [17] (p.1419)
可见挚虞的创作意图是宣扬“履信思顺”的处世信条,从对信、义等伦理道德的强调来说,《思游赋》是以儒家教义为基调的,但其信天任命的人生态度,也透露出老庄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这正体现出魏晋玄学调和儒、道的特点。
因神游赋的写作模式所限,《思游赋》中天外世界的漫游自是必不可少。就漫游次序而言,该赋次序为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继之以至天庭解惑,得到圆满之解答而辞归,与《思玄赋》大致相同。其描述之重点在于天庭,在叙述天上漫游的段落中,继承了《思玄赋》以星象入文的做法。另外,相对于《离骚》中负责占卜的巫咸和灵氛,本文中的相应角色已变为伏羲和周文王,巫师被圣王取代,这说明巫文化对神游赋的影响至此已经消弭殆尽。
挚虞虽然对神异世界进行精彩的描写,却并没有迷失在光怪陆离的异境想象中,如上引《晋书》本传所言,《思游赋》对异境漫游穷形尽相的描写,只是作者说理方式的艺术化体现,其主旨所在仍在于文末揭橥的现世空间,这种曲终奏雅的模式是汉大赋的惯用套路,在张衡的《思玄赋》中也已经运用。通过对异境的舍弃,《思游赋》延续《幽通赋》以对现世的认同,从调和儒道的玄学风尚出发,对《思玄赋》发现的儒学伦理空间进行重新阐释,文章在结尾写道:
蹈烟煴兮辞天衢,心闣兮识故居。路遂遒兮情欣欣,奄忽归兮反常闾。修中和兮崇彝伦,大道繇兮味琴书。乐自然兮识穷达,澹无思兮心恒娱。[17] (p.1422)
作者辞别天衢返回现世的心情是轻松愉悦的,归来后的生活雖恬淡却也隽永有味。在这里,异境与现世间的严峻对立被消弭了,这种矛盾双方的对立调和,是当时玄学中名教与自然融合在另一种形态上的体现。《思游赋》基调虽为宣扬儒家教义,文中老庄思想痕迹却也甚为明显,从“运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为。求之者劳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承明训以发蒙兮,审性命之靡求。将澄神而守一兮,奚飘飘而遐游”等句子都可以看出,与《思玄赋》中对现世空间伦理道德性质的强调明显不同余敦康认为,自王弼、何晏提倡玄学以后,魏晋玄学的发展经历正反合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王弼为代表的自然、名教并重,第二阶段则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重自然而轻名教,第三阶段是以裴頠《崇有论》为代表的重名教而轻自然,第四阶段则是以郭象“独化”论为代表的自然、名教兼顾。相较来说,挚虞“推神明之应于视听之表,崇否泰之运于智力之外”的方式,与郭象的理论较接近,是玄学的高级阶段。参见《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思游赋》儒、道合流的倾向,与西晋盛行的谈玄贵无风气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宋晁补之已言及此点,他在《变离骚序上》中云:
《思游》有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益远矣。然晋人喜清谈,而摰虞此作,庶几有为而言,致足嘉者也。 [18]
(二)新自然主义主导下的诗意空间
南北朝时期,神游赋系列仍有人创作,代表作品有北魏阳固的《演赜赋》,该赋从自己的家世说起,由于个人与世不谐,故而有玄思冥想的漫游,最后归结于顺天委命,延续此前神游赋的套路与风格。
同挚虞的《思游赋》一样,《演赜赋》的漫游按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天、下界的秩序进行,不过最后多出世上漫游之一节。与之前的神游赋相比,《演赜赋》的最大特点在于,现实空间也成为漫游的对象,这说明异境与现世间的对立已经消失,二者的区别已经泯灭,这与《思游赋》的空间观又有明显不同。这种变化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实际上是魏晋新自然主义哲学观念的体现。我们先来看看其现世漫游临近尾声时的一段文字: 忆慈亲于故乡兮,恋先君于丘墓。回游驾而改辕兮,纵归辔而缓御。仆眷眷于短衔兮,马依依于跬步。还故园而解羁兮,入茅宇而返素。耕东皋之沃壤兮,钓北湖之深潭。养慈颜于妇子兮,竞献寿而荐甘。朝乐酣于浊酒兮,夕寄忻于素琴。 [19] (p.1609)
与神游所历的绚丽异境相比,作者归家之后的生活更为诗意自然,现实世界的不公虽然让他萌发远游的冲动,但他的不平最终在现世空间里得到了慰藉。
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演赜赋》对归家过程和家居生活的诗意描摹,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几无二致,足证阳固在文学风格和美学趣味上受过陶氏的影响。阳固之子阳休之是陶渊明文集在北朝传播的关键人物,他曾在萧统整理的八卷陶渊明集基础上,整合成十卷本的陶渊明文集,其陶集序录云:
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其集先有两本行于世,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编比颠乱,兼复阙少。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传诔,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然编次有体,次第可寻。余颇赏潜文,以为三本不同,恐终致忘失。今录统所阙,并序目等,合为一帙十卷,以遗好事君子。 [20] (p.470)
据此序文字可知,陶集在当时流传并不稀少,阳休之至少见过其中的三个版本,阳固作为阳休之的父亲读过陶集自不足为奇,他在文学创作中受陶氏影响更是正常。
除了文字上的影响之外,陶渊明儒道兼修,顺天委命的思想,也对阳固产生影响,故他在《演赜赋》中一方面很重视儒家的伦理纲常,说“诵风雅以导志兮,蕴六籍于胸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远心。播仁声于终古兮,流不朽之徽音”;另一方面,又体现出鲜明的老庄色彩:“进不求于闻达兮,退不营于荣利。泛若不系之舟兮,湛若不用之器”,其儒道兼蓄的思想正如结语所云:“反我游驾,养慈亲兮。躬耕练艺,齐至人兮。”
陈寅恪以陶渊明的思想为新自然主义,并论云:“盖主张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虽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有所触碍。”[21](pp.228-229)新自然主义主张泯灭彼此界限,从精神上追求物我合一,是一种艺术化的生存方式。阳固对现世空间的诗意体悟,泯灭异境与现世分际的艺术化精神,与它是完全一致的。
就先唐神游赋发展历程来说,其思想基调经历先秦巫觋之学,西汉神仙之说,东汉儒学伦理,西晋玄学风尚,南北朝新自然主义各个时期的转变;而就其对漫游历程之描述而言,则经历由偏重西北昆仑至天地四方并重,再由天上、东、西、南、北至东、南、西、北、天上等次序的变化,体现出昆仑神话由先秦时影响甚大,到两汉至南北朝期间渐渐衰落的历史变化日本学者富永一登在《摯虞の“思游賦”について》中,曾对《离骚》《大人赋》《远游》《思玄赋》《思游赋》等作品中的漫游次序做过统计,可做参考,文载《中国中世文学研究》,1991年,第20号。。在异境空间与现世空间的互动上,《离骚》为求异境而不得,以生命向黑暗的现世抗争;《远游》则与神仙相游息,通过游仙而厌弃现世;班固《幽通赋》通过否决异境,强调伦理道德作为现世纲常的价值意义;《思玄赋》则舍异境而归现世,实现神游赋对儒家伦理世界的再发现;挚虞《思游赋》则以异境为媒介,从儒道调和的玄学角度阐发现世生活的可贵;阳固《演赜赋》则秉持新自然主义观点,将想象与实在打成一片,《离骚》中冰冷黑暗的现世存在,至此以诗意空间的面目出现于文中。在先唐神游赋的发展过程中,前期虚构世界占据优势地位,作者通过对它的热诚赞颂,以反映现世存在的压抑无趣,但随着东汉以后对现世空间价值的发现,异境渐渐由逃避现世的理想圣地,变为衬托现世价值的媒介,现实世界的地位逐渐上升田晓菲通过对中国中古旅游文学的考察,认为其中存在一种失乐园的模式。其实,这种模式用之于汉代以来的神游赋也亦无不可,这说明对于理想乐园与现实世界间的辩证关系,在不同的文体中展现出的是相同的思想观念。田说参见《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02—109页。。在异境空间与现世存在的价值判断上,有着此降彼升的互动关系,这种变化也是先唐不同时代文化精神迭互兴衰的体现。
[参 考 文 献]
[1]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桂馥.说文解字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与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J].中华文史论丛,1979(2).
[7]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9]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0]孙梅.四六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11]刘师培.论文杂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2]于光华.评注昭明文选[M].上海:扫叶山房,1919.
[13]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5]洪若皋.文选越裁[C]//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16]许逸民.金楼子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晁补之.鸡肋集[M].四部丛刊本.
[19]魏收.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0]龚斌.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作者系郑州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连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