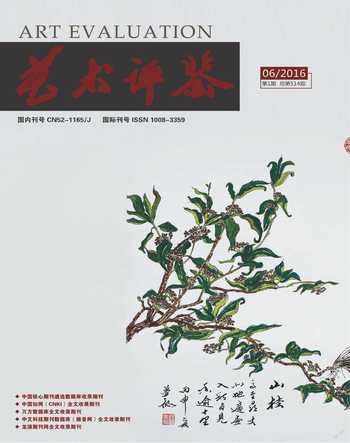“唱法”与民族认同感
2016-05-30王如意
王如意
摘要:音乐是国家文化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声乐演唱的方法与风格同样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的一种彰显。声乐演唱的方法与风格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在民族文化共同体中最大限度地获得民族认同感取决于其是否构筑在民族文化传统之上,并具有鲜明的民族亲和力和历史感,同时还能够在民族文化共同体中最大限度地产生音乐文化共鸣。
关键词:唱法 原生态唱法 民族唱法 民族认同感
音乐是国家文化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声乐演唱的方法与风格同样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的一种彰显。由于音乐与音乐文化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的族群内是人们产生民族自觉的认同意识并获得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内容。在国际间,则又是国家软实力(Soft-Power)必不可少的核心要素。因此,声乐演唱的方法与风格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在民族文化共同体中最大限度地获得民族认同感取决于其是否构筑在民族文化传统之上,并具有鲜明的民族亲和力和历史感,同时还能够在民族文化共同体中最大限度地产生音乐文化共鸣。
一、各种“唱法”的历史语境
本文所指“唱法”即近三十年来,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CCTV电视歌手大奖赛”上屡屡出现的“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原生态唱法”,以及之后用以替换“通俗唱法”的“流行音乐唱法”。毫不夸张地说,随着中央电视台强大的覆盖率和广大音乐爱好者对大赛的关注与收视率,迄今为止,“四种唱法”可谓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甚至大部分普通民众也都能对各种“唱法”的代表作品和代表性歌唱家、歌手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以致每当歌唱演员出现在电视屏幕或音乐会舞台上时,观众便能迅速地将其划归为某种唱法。无疑,如此深入人心的各种“唱法”及其新人新作的不断问世,一方面繁荣了国家的音乐生活,丰富和增加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音乐常识。但另一方面,却也对广大音乐爱好者的音乐审美产生了严重的误导,甚至让音乐院校的声乐教学也受到了一定的局限。言必称某种“唱法”的同时,似乎歌唱方法除了“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等之外,再无它法。但情况果真如此吗?
(一)“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
按理,“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一西一中,本不该并列而语。但回顾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却又不难看出,源于意大利的“BeI canto”歌唱方法,自20世纪20年代末引入中国并译为“美声唱法”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一直与中国本土以汉族民歌演唱方法为主的“民族唱法”的争论和冲突中相互揶揄、诋毁(亦即旷日持久的“土洋之争”)。但值得思考的是,当时争论和冲突的核心并非简单、单纯的歌唱发声、气息、位置等声乐本体的方法问题和风格问题,而是隐藏在“土洋之争”表象背后与国家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政治问题。
所幸,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在经过了“土洋之争”之后的中国声乐显然成熟了许多。一方面,“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的歌唱原理和歌唱方法不仅都得到了极大的普及和推广,而且彼此也都在人才培养、艺术成就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另一方面,“民族唱法”这个本应以中国各民族民歌、戏曲、说唱等艺术形式和丰富多彩的歌唱方法为代表的“方法”,却被“规范”成了“千人一嗓,万人一腔”的现状。而真正具有声音个性和艺术魅力尤其是具有独特音乐文化感染力的唱法则不属“民族唱法”,而是被归为“通俗唱法”或“原生态唱法”。
(二)“通俗唱法”“流行音乐唱法”与“原生态唱法”
如果说“通俗唱法”泛指与艺术歌曲演唱方法(如美声唱法)相对的流行歌曲演唱方法的话,那么,其近现代史上有据可查的代表性歌唱家则可追溯到“国统区”上海滩的“金嗓子”周旋,以及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以来许许多多的“非主流”歌手及其歌唱方法。尽管所谓“非主流”的演唱方法事实上恰是被社会大多数民众喜闻乐见的“主流”演唱方法(注:以“青歌赛”为例,“通俗唱法”一词从2008年举办的第13届“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开始,将已经使用了长达24年的“通俗唱法”正式改为了“流行音乐唱法”)。
“原生态唱法”一词始见于十年前中央电视台第十二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2006年),并作为一种新增的“唱法”正式纳入比赛,直至2013年第十五届比赛时才取消。根据《第十二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比赛细则》可知,新增原因是:
随着我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全面开展,全国各地挖掘出了大量的“原生态”歌曲,发现了众多的“原生态”演唱人才,这为大赛提供了丰富的参赛资源。把“原生态”从民族唱法中单列出来参加比赛,这对弘扬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生态”(ECO)一词借鉴于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亨利希·菲利普·奥古斯特·海克尔(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1834-1919)创始的“生态学”(Ecology)学科术语。其原意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的相互关系。诚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无论是学术概念还是学术术语的相互借鉴本无可厚非。然而,“原生态唱法”的出现,不仅让绝大多数人感到陌生,而且也引起了社会各界众说纷纭的热议。直到人们通过电视听到和看到了来自云南的彝族姐弟李怀秀、李怀福演唱的海菜腔,来自贵州侗族的“蝉之歌组合”,来自延边的卞英花,来自内蒙古的“安达组合”,来自四川的“羌族多声部组合”,以及来自内蒙古的阿拉腾乌拉天籁、惊艳、震撼、感人的歌声时似乎才理解了《比赛细则》中使用动词“挖掘”和“发现”修饰主语“原生态唱法”的真实含义。
毋庸置疑,假如“原生态唱法”一说能够成立,并且它确实是“随着我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全面开展”才被“挖掘出”和“发现了”的话,那么从逻辑上讲,更加证明了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与“洋嗓子”相争的“民族唱法”及其“民族”的自身含义何其偏颇,何其狭隘!
二、“民族唱法”的能指与所指
“民族唱法”中的“民族”即中国版图上现有的56个民族。正如民族学研究迄今为止引用率最高的斯大林(Joseph Vissarrionovich Stalin,1878-1953)论述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一样,因而我们可以肯定:一方面,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文化均由56个民族共同创造。另一方面,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文化又让56个民族产生了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觉的认同意识。此外,根据现代语言学大师索绪尔(Ferc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提出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理论再看“民族唱法”,可知其“能指”即“民族唱法”的语言声音形象,而“所指”即“民族唱法”特有的民族音乐、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风格,乃至民族情趣。然而,却为何几十年来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民族唱法”仅只是以汉族为主要代表的音色音质同质化,音乐风格和表演风格雷同化的演唱(甚至包括作品)?十年前,第十二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原生态唱法组”的精彩表演和富于个性的歌声之所以能成为最受社会欢迎的“亮点”并让广大民众由衷地为之震撼,绝非偶然。如若不然,著名音乐学家田青评委也不会在为其点评时激动不已地说“终于又听到老祖宗的声音了”。
如前所述,“原生态唱法”以及其的演唱方法乃至作品的出现,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全面开展”和“全国各地挖掘出了大量的‘原生态歌曲,发现了众多的‘原生态演唱人才”为前提。可是,相似的前提,甚至相似的表述,我们却也可以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文献中看到。比如:“1943年在延安开展起来的秧歌运动,把一向矫揉造作的声乐风尚拉回到自然的基础上,从而掀起了向民间唱法学习的热潮,培养起音乐工作者热爱人民艺术传统的思想感情,这是有很大的功绩的。”此外,新中国成立后至60年代中期中国音乐界关于“民族唱法”重要的四次讨论及其文献更是言之凿凿。
(一)1950年全国性关于“唱法问题”讨论
1949年12月,由全国音协与中央音乐学院合办的“音乐问题通讯部”首次制定了《新中国唱法提纲》。
(二)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前后的讨论
吕骥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工作报告中指出:“在这次音乐周听到许多出色的表演,许多知名的声乐家像喻宜萱、周小燕、黄友葵、郎毓秀、李志曙、温可铮、满谦子等不论在技巧上、对人民生活的理解上、学习民族声乐传统上.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获得了新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结束后,一向关心中国文艺问题的毛泽东主席也在接见全国文艺工作者时更加明确地指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
(三)1957年的全国声乐教学会议
《全国声乐教学会议》是在中共八大向全国文艺工作者提出创造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的任务的背景下,旨在解决建国以来唱法讨论中关于“土洋之争”的片面性、明确声乐教学方针、统一声乐思想认识的前提下召开的,并最终形成了纲领性文件《声乐教学大纲》,同时在《总则》中指出:“(中国声乐)教学要在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的传统声乐唱法上吸取民族声乐艺术的优秀传统……同时学习苏联和西欧声乐艺术和声乐教学的优秀成果和经验,使西欧传统的唱法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以逐步建立中国民族的声乐教学体系。”时任文化部副部的长刘芝明也在会议结束时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为了响应中共八大提出的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号召,声乐工作者必须继续深入学习欧洲传统唱法并不断使之与中国民族艺术传统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声乐艺术的‘民族化”。
《四)1962年在京举办的《独唱独奏音乐座谈会》
虽然说,该座谈会涉及的内容并不只是声乐独唱。但事实上,“民族唱法”和“民族声乐学派”等提法却成为了该座谈会的关键词和核心内容。与会者认为,“民族唱法”也应该“百花齐放”,不可仅仅拘泥于民间的某种唱法。皆因民间的很多唱法和发声也同样是强调科学性的,只不过是我们的研究并不深入。
综上引述,不难发现我们实际上为“民族唱法”的属性和定义,方式和方法,以及特色与风格等早已殚精竭虑,强调再三。因而称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全面开展”,我们才在“全国各地挖掘出了大量的‘原生态歌曲.发现了众多的‘原生态演唱人才”的说法既否定了建国以来我们在探讨“民族唱法”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同时又再度混淆了“民族唱法”和“原生态唱法”的关系。那么,名副其实的“民族唱法”应该是什么呢?
三、“唱法”与民族认同感
顾名思义,“民族唱法”中的“民族”当指中国版图上的56个民族。而“民族唱法”则又特指56个民族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中所形成并能代表和象征民族精神特质、性格特征、文化特色,以及审美追求的歌唱习惯和歌唱方法。但尽管如此,我们切莫忘了,真正能代表中国并冠以“民族唱法”的“唱法”也必然是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特色的“唱法”。从哲学意义上说,“和”即和谐与统一。“同”则是相同和一致;“和”是抽象的,内在的:“同”是具体的,外在的。因此“和而不同”的真正内涵应该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
有关于此,笔者认为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十年前发表的《“美美与共”与人类文明》一文尽管是一篇着眼于世界文明的高论,但其针对“文明”所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理论不仅同样适用于我们对于“民族唱法”所含56个民族不同音乐文化与演唱方法的学习和研究。而且费老后来又提出的“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就是各种文明教化的人,不仅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断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所谓“民族唱法”其实是一种以汉族歌唱习惯和歌唱方法为基质,以专业音乐院校民族声乐教学为代表的“学院派唱法”。汉族以外诸多民族真正的音乐文化、审美意趣、歌唱习惯、歌唱方法我们不仅知之甚少,而且也缺乏真正的研究。因而“原生态唱法”一词及其演唱在第十二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出现后,才被专家评委理所当然地解释为“没学过演唱方法,也没经过专业学院和老师培养过的自然唱法”。但事实上,正是这些“没经过专业学院和老师培养过的自然唱法”清新自然,美如天籁的演唱才成为了大赛最大的亮点,并获得了海内外众多华人高度的民族认同感。
在笔者看来,上述现象至少说明了我们的某些音乐院校长期固守的所谓“科学发声”有偏离民族传统之嫌,以致我们对待历史悠久并经祖祖辈辈传承至今的民歌、说唱、戏曲及其演唱方法中同样存在的“科学发声”视而不见。更重要的是,我们完全忽略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浅显道理——任何一种根植于文化传统土壤的方法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无论是西欧的“BeI canto”,还是北欧的“Yodeling”,抑或是根植于中国音乐文化传统沃土的民歌、说唱、戏曲,丰富的演唱方法也都同样如此,概莫能外!因而当我们把最能获得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族认同感的歌唱方法视为“没学过演口昌方法,也没经过专业学院和老师培养过的自然唱法”时,我们所谓的文化优越感必然导致我们缺乏“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的文化胸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清楚地看到,“唱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和单纯涉及歌唱方法和歌唱技巧的术语,它更高的哲学意义在于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传统,并且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充分体现着民族共同的精神特质、性格特征、审美意趣,同时在民族文化共同体中最大程度地获得民族自觉的共同意识和民族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