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运行特点
2016-05-28李良品廖佳玲
李良品++廖佳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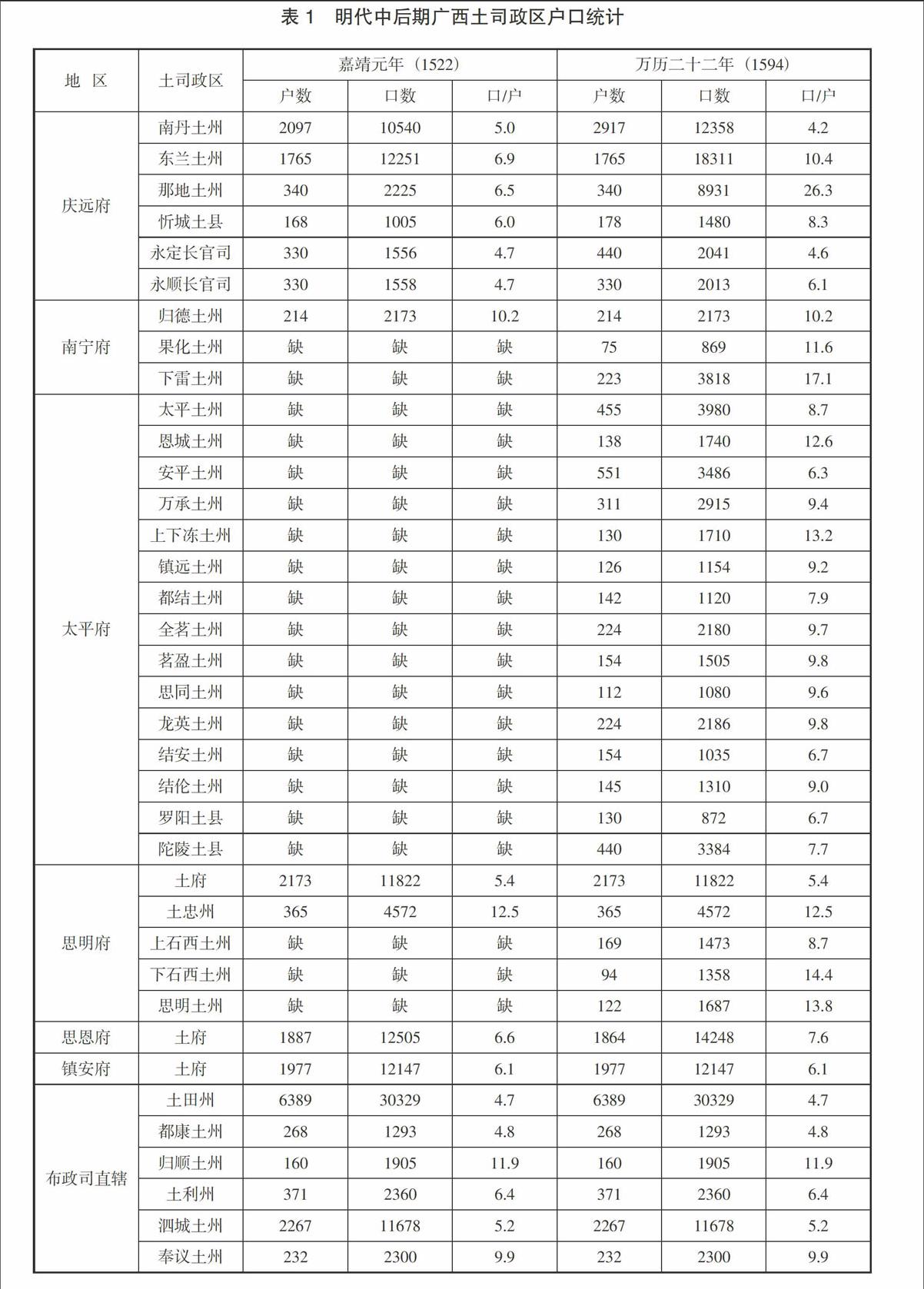


【摘 要】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运行特点十分复杂,主要体现在“家国同构”的一致性、“因俗而治”的差异性和合作共赢的依存性三个方面。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没有一个个家庭的富裕,没有乡村社会的支持,就没有国家的强盛;没有强大的国家对家庭和乡村社会强有力的保护,乡村社会就不会有安宁的生活。因此,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上下互动、有效合作的关系。
【关键词】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国家;特点
【作 者】李良品,长江师范学院教授,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重庆涪陵,408100;廖佳玲,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重庆北碚,400715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2 - 0134 - 007
古往今来的社会架构皆表现为家庭、社会、国家三种主要形态。[1 ]这三者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以不同方式存在。本文拟就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运行特点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家国同构”的一致性
在传统中国,一个家庭、一个大家族与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在政权结构和组织结构方面有其共同性,这个共同性集中体现了“家国同构”的一致性。它是以宗法关系为统领,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家”作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细胞,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她既是扎根于社会中的一种历史的实体,也是一个包括了传统思想、经济结构等因素的社会单位。在明清时期的传统中国,“家”作为社会细胞,除了具有维持家庭成员物质和感情生活的基本功能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成为维护国家专制统治的基层政治组织。“家族”是指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组成的许多个体家庭,按照封建传统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将最多的家庭,按照一定社会秩序结合成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2 ]8它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广义的家。“国家”是一个成长于社会之中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合法性为基础的、带有一定抽象性的权力机构,在其管理的领土内,“国家”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这三者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是家庭的延伸,国家则是家族的扩大。因此,在“家国同构”的明清时期,家长或族长在家庭或家族内的地位至尊,权力最大;君王或帝王在国家体系内地位至尊,权力最大。换句话说,家长或族长是家庭或家族内的一把手,是最大的管理者,而国君则是国家内的一把手,是全国子民的严父。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思想也正是来源与此。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不仅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且掩盖了阶级关系和等级关系。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在本质上反映了“家”与“国”之间这种同质联系。《保靖彭氏宗谱》的《彭氏家训》共分为修身、齐家和治国三篇,其中《修身篇》之下有“崇孝道”“正礼义”“务为学”“谨言行”“明德性”“慎交友”等六条,《齐家篇》包括“重教养”“齐家政”“尚友爱”“睦宗族”“励勤俭”等五条;《治国篇》涵盖“处世事”“和乡里”“论为政”“清吏治”等四条。[3 ]可以说,这些内容均是国家在场下的封建族权与国家政权高度统一的范例,湖广土司家族如此,其他家族可想而知。在“家国同构”的一致性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血缘关系是“家国同构”的基本依托点
众所周知,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土司的承袭,十分重视血缘关系,也就是说,血缘关系在明清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央王朝的承袭是父子传承,土司的承袭同样是以血缘关系为主。如在土司的承袭中,明朝廷制定了一些办法,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死子继,嫡子继承。其次是兄终弟及,叔侄相立,族属袭替,妻妾继袭,女媳继职,最后是子死母袭。由此可见,土司承袭的次序是先嫡后庶,先亲后疏。这体现的是一种血缘关系和亲疏关系。特别是对土司承袭必须具备宗支图本,那更是对血缘关系的硬性规定。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以无数个“亲亲”组织的家庭成为国家的基点,再以无数个具有血缘纽带的家族组成国家的基本依托点。由此可见,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血缘关系无形之中成了“家国同构”的基本依托点。
(二)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忠孝是“家国同构”在伦理层面的结合点
忠孝一体,历来是儒家学说的一贯主张。在儒家提倡的“五伦”中,将父子、君臣列于最前面,这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在父权制存在的传统社会,父子关系不仅居于家庭血缘关系之首,而且成为维系家庭关系的基础;与此相应的,在政治等级制存在的封建国家,君臣关系不仅居于政治关系的第一位,而且也成为维系封建国家伦常的基础。二是在传统封建社会的明清时期,不仅家国是同构关系,而且父子、君臣同样是一种同构关系。正是基于此,在孟子提出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父子有亲”之后接着强调“君臣有义”,这是“家国同构”关系的最集中体现。《保靖彭氏宗谱》之《彭氏家训》的第一篇《修身篇》,开宗明义第一条便是“崇孝道”:“孝始于事亲,忠始于报国。移孝以作忠,即显亲以全孝,人孝也。人子事亲,无穷富当以奉养为先,奉养之道再遂其力,富者可以甘旨奉养,贫者可以菽水承欢。务须承顺亲志,悦以颜色,婉以言语,不可貌奉心违,以贻父母之优。子之孝,不如率妇以孝。盖妇之居家时多,奉供饮食起居,自较周到。俗语云:“得一孝妇,胜于孝子”。[3 ]1由此可见,保靖彭氏土司家族对“孝”有着深刻的理解。我国自古有“忠孝一体”、“移忠于孝”的思想,这是有着实实在在的伦理基础的。[2 ]12可以说,“忠孝一体”作为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家国同构”在伦理层面的高度结合,确有其内在逻辑的合理性。
(三)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理原则是“家国同构”在内容层面的共同点
在传统中国,家礼是修身治家之具,国法是治国定天下之具。“家国同构”体现在家礼与国法的相通上,即将管理家庭关系的原则上升为治理国家的原则。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提倡读书人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治家是治国的前提,治国是治家的放大。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与人的“差序格局”及“五伦”关系中,都十分注重“礼”,并视其为顺应“差序格局”规范的行为准则。在明清时期,“家”“国”的组织系统和权利配置都是严格的父系家长制。国家组织结构与家族组织结构的一致,是属于有形的可见的“家国同构”,而“家国同构”的核心是君权与父权的相互为用,君权乃是父权的延伸,父权专制的家庭模式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专制奠定了基础。在现在还能见到的一些族谱中,对家族礼制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如《保靖彭氏宗谱》之《彭氏家训》的第二篇《齐家篇》之“齐家政”有这样一段文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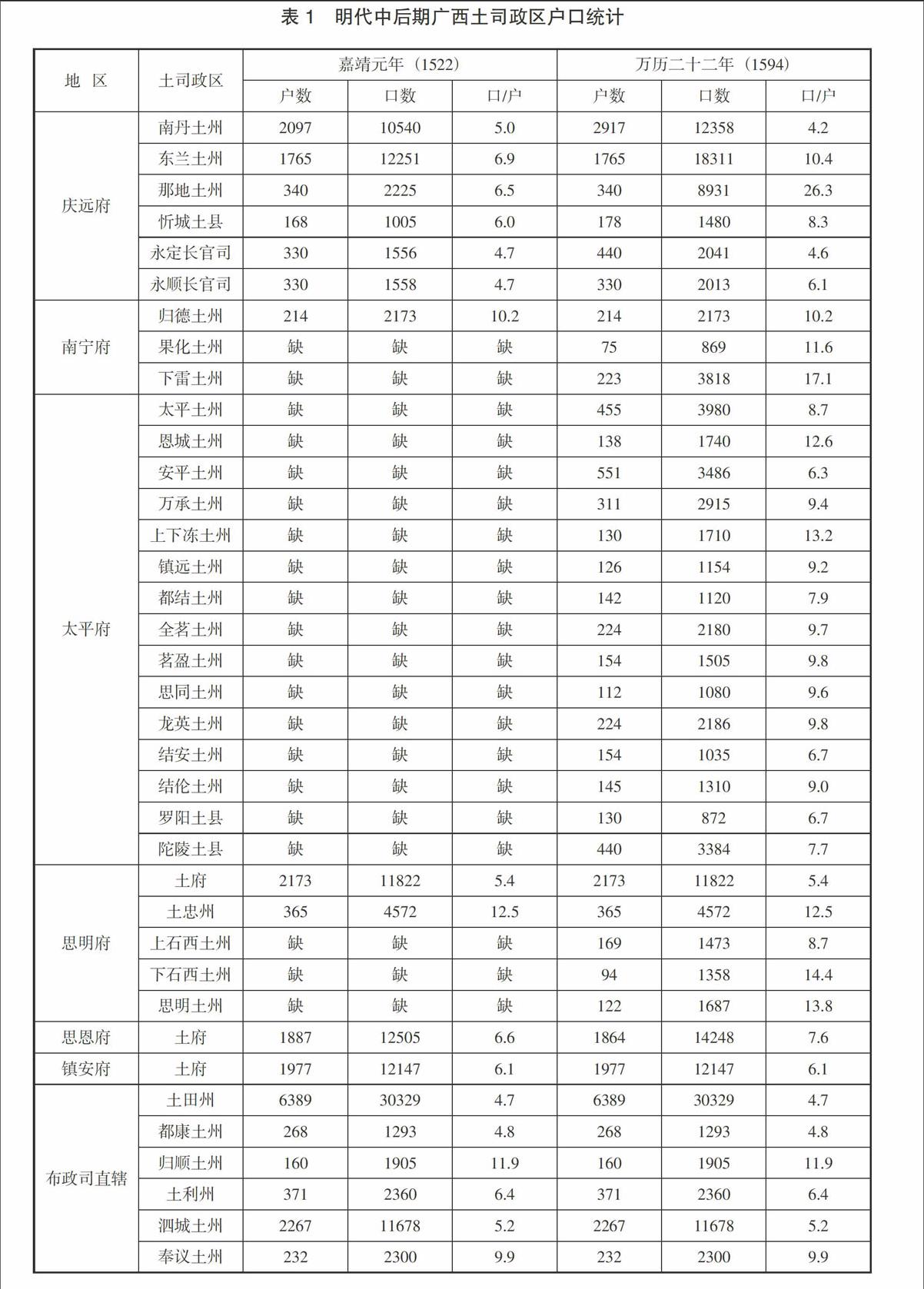
治家之道以正人伦为本,正伦以尊祖睦族、孝父母友兄弟为先,以敦亲堂和乡里为要务。近正人如父兄,远恶人如虎狼。守之以勤俭,行之以兹镶,约己而济人,习礼而好德,如此可以兴家,可以安身而立命。[3 ]2-3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各族民众,无论对家还是对国,均注重君权与父权的相互为用。因为乡村社会以血缘关系建构的宗法,推而广之就是国家的宗法。正是由于“家国同构”的一致性,决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始终未能独立于宗法关系而存在。因此,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也遵循“家国天下”是一体的规律行事。“家”是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无数个社会细胞能够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实现“家”“国”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这既有利于保持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稳定和活力,又能加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4 ]
二、“因俗而治”的差异性
国家治理理论告诉我们,国家治理应该是国家和社会(包括乡村社会)协同共治,就当今社会而言,二者的协同共治仍是现代社会国家治理的根本要求。当然,明清时期的封建统治者没有这样的认识高度,他们对西南民族地区往往采取“因俗而治”的措施。“因俗而治”是包括明清统治者在内的历代统治阶级根据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等制定的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边政策。按照学界的看法,“因俗而治”就是因袭、保留少数民族原有的政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基本不变。如果“因俗”是根据和条件,那么,“治”就是目标与归宿。如果根据和条件一旦发生变化,治理方式与目标也会随之发生变化。[5 ]在一定程度上讲,明清中央王朝实行的“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也就是在承认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各民族在历史、地理、生产、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上存在的差异性,并根据不同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这种政策体现了国家试图通过“齐政修教”来达到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有效统治,从而实现明清统治者“大一统”的目标。
(一)政治制度
明代以降至清代前期,“因俗而治”的民族地区治理模式是把“齐政修教”提高到治边政策的高度。因此,在这个治边政策的指导下,明清中央政府根据西南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如同样是实施土司制度,在川西藏族地区实行“军政教合一”的土司制度;而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广等少数民族地区则实行“军政合一”的土司制度。这种“因俗而治”的政策在明代及清前期对维护西南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清雍正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这不仅密切了西南民族地区与内地、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而且也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当时,雍正皇帝在西南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南明小朝廷负隅西南,顽强抵抗;二是吴三桂的叛乱肇始于西南,且都对清廷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为了强化对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理,实现全国“大一统”的目标,清王朝必然要在西南民族地区强力推行改土归流。事实上,即便雍正皇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够彻底,但这种加强对西南民族地区治理力度的方式,仍然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和领土完整,仍然有利于实现边疆与内地一体化以及固国安邦的愿望。[6 ]
(二)朝贡制度
明清中央王朝在对西南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的过程中,朝贡制度为其主要内容之一。当一个土司归附新的中央王朝后,须向中央王朝纳贡。朝贡包括贡和赐两个方面的内容,贡表现为各地土官的一种自觉行为,赐则是朝廷对朝贡土司的回赐。对各土司而言,赐甚至可以说是贡的目的。[7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朝贡十分踊跃,而其差异性也十分明显:一是朝贡物品的差异性。从历史文献看,西南民族地区各地土司向中央王朝所贡物品多为方物。据《明会典》卷一百八载:当时西南地区“土官贡物”,除了金银器皿、各色绒绵、各色布手巾、花藤席、降香、黄蜡、槟榔、马、象、犀角、孔雀尾、象牙、象钩、象鞍、象脚盘等物品之外,还有各色铁力麻、各色氆氇、左髻、明盔、刀、毛缨,甚至还贡有胡黄连、木香、茜草、海螺、毛衣等方物。[8 ]582-585各地土司贡物情况不尽一致,如川滇黔交界地区土司主要是贡马。可见,西南民族地区土司进献何种贡品给皇帝,主要根据当地出产情况而定。在明代,四川播州和酉阳土司除了贡马之外,就是献大木。二是朝贡时间的差异性。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各地土司的朝贡或一年一贡,或三年一贡,或五年一贡。这种形成惯例的朝贡,称为例贡。《明史》卷三百一十一载:“洪武六年,天全六番招讨使高英遣子敬严等来朝,贡方物。……每三岁入贡。”[9 ]8031这种例贡针对不同的土司,其朝贡时间也不完全相同。清朝时,西南民族地区各地土司依然是“三年一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六十五“土司贡赋”条载:康熙五十一年覆准,四川化林协属各土司,三年一次贡马,照例折价交收。[10 ]卷265除例贡之外,土司朝贡还有不定期朝贡,这类朝贡具有谢恩和谢罪性质。据《明会典》卷一百八《朝贡四》“土官”条有“谢恩无常期。贡物不等”[8 ]583之说。从这些史料记载看,中央政府除了规定各地土司“三年一贡”之外,还经常利用皇帝大寿、朝廷庆典、土司承袭、土司子弟入学等时机,要求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朝贡,并利用朝贡的机会,中央王朝与土司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不定期朝贡,没有具体时间规定。至于庆贺性质的朝贡,明王朝规定,只要各地土司不错过庆贺日子即可。如弘治六年(1493)正月,播州宣慰司派遣头目、把事等京城谢恩庆贺,进贡马匹,赐彩段、钞锭有差。[11 ]868此外,还有赎罪性朝贡。这些均体现出西南民族地区土司朝贡的差异性。
(三)文教政策
明清时期“因俗而治”的民族文化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央政府对宗教文化具有比较宽容的态度。以藏传佛教为例:在川西藏区“政教合一”的制度下,中央政府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创办官学教育以儒化学子的方式,而是借助佛教文化,依靠“多封众建,以教固政”的方式以达到对川西藏区的有效治理,从而实现了“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的目的。[5 ]同时,中央政府还在川西藏区设置“指挥使司、宣慰使司、元帅府、招讨使司、万户府等,各级官吏僧俗并用,军民兼摄。”[12 ]10明清中央政府宽容的治藏政策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藏传佛教不仅能在川西藏区迅速发展,还逐步向青海等地传播。第二,明清中央政府“因俗而治”的政策保留和维持了西南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结构,有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如清代云南很多乡规民约的碑刻里无不体现少数民族自觉接受国家主流文化、促进乡村社会与国家间的文化互动的意识。试以《宜良县万户庄乡规碑(一)》为例。
公立乡规
欲厚风俗,先正人心。然必礼教明,信义立,而后能砥节励行,以正气维正理于不替,使不垂训于先。恐人心渐灭,寡廉鲜耻,不能争自濯磨,以进于淳庞。今议立乡规,愿我父老子弟凛遵,各以痛改前非,共登仁里。
——崇礼让。辩上下,定民志,莫要于理教不明,则各分倒置,争竞成风,而和气不能翔洽。惟愿吾乡,长者正己率物,少者守分修身,斯游尧舜之世,为尧舜之民矣。
——敦信义。出入相友,有无相恤,虽异姓不啻一家。若相欺相诈,不惟亲逊之风无闻,亦必孝慈友恭之道绝矣。道道率物,公平互施,当共勉之。
——禁斫伐。树竹、花果各有其主,非其有而取之,俱属不义。斫伐朝阳寺树竹及人坟茔树木者,罚猪壹口,重七十斤,酒伍拾元;斫伐人山场、园墅树竹花果者,罚猪壹口,重陆拾斤,酒肆拾元。松树各家畜种,亦宜加竞培植。有着松毛与树,必与管事说明。如私自取用,不与言明者,罚钱壹千文。
——禁践踏。坟茔系人先灵凭依,如不分时牧放之人,纵放牲畜肆行践踏者,罚猪壹口,重捌拾斤,酒陆拾元。践踏田园、五谷、庄稼,致国赋无资,衣食无出者,罚猪壹口,重伍拾斤,酒肆拾元。
——禁偷窃。树竹、茶果、粪草之类,各有其主。私行偷砍树竹一株,罚银伍钱,贰株罚银壹两,照数升罚。偷取豆麦、谷菜者,罚谷伍斗;偷取茶果、瓜姜等物者,罚谷伍斗;偷取粪草者,罚钱伍佰文;偷取竹笋壹支者,罚钱壹佰文,照数升罚。
以上条例,俱系公议乡规,各宜遵守,互相觉查。见人斫伐、践踏、偷窃,即向管事言明议罚。如互相容隐,知见不举者,与本人同罚;亦须见查的确,不得挟仇诬人;虚诬捏报者,罚银壹两。
呜呼!细行不谨,终累大德;严取于一介,谨嫌疑于瓜李。人生立身之大节,勿谓欺人于不见,而自败其行。不惟孝悌友恭之无闻,而遗臭万年,至孝子慈孙之莫改也!凡我父老子弟,各宜劝戒遵行,敢有故违,公罚毋悔。
大清乾隆十四年(1749)六月二十五吉旦 镌立[13 ]18-19
从这则《宜良县万户庄乡规碑》可见,即便是全乡在公议禁止斫伐、践踏、偷窃之事,在前面也没有忘记“崇礼让”“敦信义”等内容,这是将国家主流文化变成了民族地区民众的自觉行为,充分体现了文化互动与文化自觉。
三、合作共赢的依存性
从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动可以看出,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二者之间只有审时度势、互动合作,才能实现共赢的目标。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频繁的良性互动,其实就是一种合作。无论什么时代,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赢的目标,这是双方的共同需要。如明清时期湖广永顺的彭氏土司,就在与明清中央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精诚合作中产生共赢的效果。据《清史稿》卷五百十二《土司一·湖广》载:永顺彭氏土司于清顺治四年(1647),“率三知州、六长官、三百八十峒苗蛮归附。十四年,颁给宣慰使印,并设流官经历一员。……雍正六年,宣慰使彭肇槐纳土,请归江西祖籍,有旨嘉奖,授参将,并世袭拖沙喇哈番之职,赐银一万两,听其在江西祖籍立产安插,改永顺司为府,附郭为永顺县,分永顺白崖峒地为龙山县。”[14 ]卷512从这些引文可见,永顺彭氏土司与中央政府确实保持了一种有效的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执行国家制度
永顺彭氏土司在执行土司制度的过程中,认真践行国家管理制度“地方化”的要求。经过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较为良好的互动,该地区乡村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国家需要朝着实现“大一统”的目标向前迈进时,永顺土司能够审时度势,积极配合,主动献土改流,并请求“归江西祖籍”。由此可见,在自上而下地推进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永顺彭氏土司在不断地接受或执行“国家”制度,这是乡村社会与国家有效合作的结果。
(二)积极纳税朝贡
作为地方土司,能够按照国家分配的数额积极缴纳“皇粮国税”,这不仅是对国家赋税制度执行过程中的有力支持,而且也是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合作的具体表现。永顺彭氏土司积极向中央王朝进贡,而中央王朝赐给永顺土司一定的赏赐,这是有效合作的最好例证。如“贡马及方物,赐衣币有差”[9 ]7991;又如正德“十年,致仕宣慰彭世麒献大木三十,次者二百,亲督运至京,子明辅所进如之。赐敕褒谕,赏进奏人钞千贯。十三年,世麒献大楠木四百七十,子明辅亦进大木备营建。诏世麒升都指挥使,赏蟒衣三袭,仍致仕;明辅授正三品散官,赏飞鱼服三袭,赐敕奖励,仍令镇巡官宴劳之。”[9 ]7993尤其是彭氏土司主动改土归流,朝廷“赐银一万两”,这在清代的土司中,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可见,土司纳税朝贡等经济方面的合作、互动,有利于加强土司首领与中央王朝的交流,减少彼此间的隔阂,增加乡村社会对国家、对中央王朝的认同,增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
(三)服从中央征调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在军事上的互动、合作主要表现为土司率领乡村社会土兵参与征调。从历史文献上看,明清时期永顺彭氏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一直处于和缓、彼此相安无事的状态,具体表现为“征调”不断。据张凯研究,永顺土兵在明朝的征调主要分为“征蛮”“征贼”和“御边”。永顺土司土兵仅在明朝就被中央王朝征调进行大大小小战役达54次之多,因此,中央王朝“赏赐”不绝。[15 ]正是因为永顺彭氏土司与明清中央王朝保持了互动、合作的关系,所以,在改土归流之后,湖广巡道王柔见永顺土司坟墓惨遭破坏,便要求当地官员及地方民众保护土司文化,他在雍正十三年(1735)撰写的《保护土司坟墓檄》文中表达了对永顺彭氏土司“祖先坟墓,倘有棍徒侵削盗葬,甚至乡僻处所有刨挖偷盗”[16 ]卷11的强烈担忧。王柔面对这种情况,出示晓谕,要求地方官“查明三土司(永顺、保靖、桑植)历代土官坟墓共有几处?坐落某保某甲某处山,逐细造册,开报到道备案”[16 ]卷11。还提出对“不法棍徒侵剥树木,恃强盗葬及刨挖偷盗等”情况以及地方官“失察”的处理。这不仅充分体现了清代朝廷命官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而且是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合作共赢的典范。
总之,只有家庭、社会、国家这三者之间的利益都得到保障,家庭、社会、国家才能稳定。无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没有一个个家庭的富裕,没有乡村社会的支持,就没有国家的强盛;没有强大的国家对家庭和乡村社会强有力的保护,乡村社会就不会有安宁的生活。由此可见,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上下互动、有效合作的关系。针对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明清时期的国家不是生母,便是严父;针对明清时期的国家,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不是亲子,便是爱女,这或许从另一个视角反映出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王集权,等.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家国一体伦理传统的价值对勘[J].江海学刊,2011(1).
[2]杨金花.论“家”及其对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D].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9.
[3]彭司礼.保靖彭氏宗谱(序)[Z].保靖彭氏宗谱编委会,2008.
[4]舒敏华.“家国同构”观念的形成、实质及其影响[J].北华大学学报,2003(2).
[5]刘淑红.以夏变夷和因俗而治:明代民族文教政策的一体两面[J].广西民族研究,2012(3).
[6]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2).
[7]李伟.乌江下游土司时期贡赋制度考略[J].贵州社会科学,2005(6).
[8]〔明〕申时行.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
[9]〔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清〕昆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
[11]李国祥,杨昶.明实录类纂:四川史料卷[Z].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
[12]张学强.明清多元文化教育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13]黄珺.云南乡规民约大观:上[M].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2012.
[14]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5]张凯,伍磊.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1(6).
[16]〔清〕张天如.同治永顺府志[Z].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CHARACTERISTICS IN THE OPERATION OF RURAL SOCIETY AND STATE RELATIONS IN SOUTHWEST MINORITY AREA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Liangpin, Liao Jialing
Abstract:The operation of rural society and state relations in southwest minority area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s very complicated. Its characteristic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isostructuralism of family and state, the diversity of "ruling by customs" and the dependencyof win-win cooperation. There is no national prosperity without getting rich of individual family and the support of rural society in anyageand any society. Correspondingly, there is no peaceful lifein the rural society without the powerful protectionof the state for the family and rural society. Thus, the rural society and the state relationsshould bemutual dependency, interactionand effective cooperation.
Key Words:Ming and Qingdynasties; southwest minority area;ruralsociety;nation;characteristic
﹝责任编辑:袁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