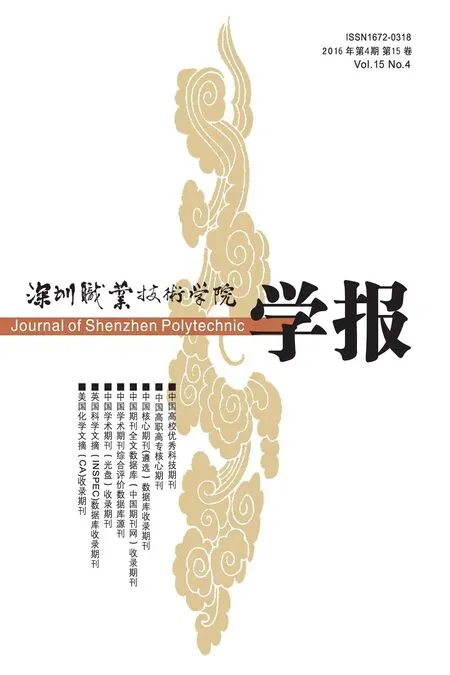对环境侵权中的免责事由—不可抗力的反思
2016-04-13姜平
姜 平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7)
对环境侵权中的免责事由—不可抗力的反思
姜 平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7)
环境侵权责任因其特殊的无过错归责原则和因果关系的认定,“不可抗力”一直以来都是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但是,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和高新科技的广泛性运用,“不可抗力”是否应该作为免责事由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从全球环境伦理的价值背景看,重新审视和考量这一法律制度,不可抗力作为环境侵权中的免责事由是不适宜的。本文结合对“不可抗力”这一免责事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进而为其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环境侵权;不可抗力;免责事由
近年来,随着全球污染问题的加重,环境污染折射出的问题很多,有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但从法律层面讲,主要是环境侵权损害的问题。从现行国内法的角度来分析,环境侵权的制度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其次,是一些单行法规,例如:《水污染防治法》第42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37条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3条的规定;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关于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责任的规定,以及第70条的民用核设施致人损害责任的规定都是与此问题相关的制度。这些相关的制度不仅规定了环境污染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且也明确规定了可以免除责任的理由。
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就有“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受害人过错、第三人的过错和战争行为。”[1]231-232还有的学者主张免责事由有“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第三人过错、受害人同意、受害人故意、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依法执行公务”[2]549-580。民用核设施致人损害责任的免责事由只有两种,即战争和受害人故意,并没有把不可抗力作为免责条款。可见,民用核设施的免责事由是非常严苛的,作为一种高科技和高度危险的能源,“不可抗力”不能免责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法律上的正义,更为重要的是表达了对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为什么有如此的不同呢?是因为环境侵权比民用核设施的损害更小,还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本身存在问题呢?毫无疑问,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丝毫不亚于一次大的核事件所造成的损害。所以,环境损害与民用核设施在免责事由上的不同,不是因为二者的损害后果不同,而是因为制度本身有缺陷。
鉴于本文主要问题在于解决环境侵权中的“不可抗力”所存在的制度瑕疵,再加上民用核设施的侵权问题相对来说规定的比较明确和完善。所以关于民用核实施的问题,在这里就不在做过多的论述,我们主要围绕环境侵权中的“不可抗力”可否作为免责事由展开。
1 “不可抗力”作为一般民事侵权责任免责事由的理由
作为一种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不可抗力”制度的设计主要基于这样的考量,即侵权损害的发生,远远超过了人类所能认识和控制的范围。更加准确地讲,致害源何时何地出现,出现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在人类现有的技术能力范围内是不可预见和避免的;或者说,虽然事前预见到了将要出现损害后果,但是人类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是无法改变和避免其后果发生的。对于这样的事件,如果还要行为人承担损害后果责任,则会失去法律正义,所以免除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这就是不可抗力作为一般民事侵权责任免责事由的理由。为了深入的分析环境侵权中“不可抗力”的制度问题,在法律逻辑之下,有必要对“不可抗力”作为一般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进行探讨。
关于“不可抗力”的经典规定,主要是体现于《民法通则》第153条:“不可抗力指的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现象。”当然这样的规定,是相当抽象和模糊的。这个范畴仅仅从性质上规定了“不可抗力”的法律内涵,并没有指出具体的内容和类型。有些学者则补充认为:“不可抗力是指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力量,包括某些自然现象(如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和某些社会现象(如战争等)”[3]135。此中补充一定程度上具体化和明确化了不可抗力的内容和类型,但还不是很完善。
从上面可以看出,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的免责事由主要分为正当理由和外来原因两大类。正当理由是从行为的规范根据上所进行的分类,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损害行为,但该行为如果是合法的、正当的,行为人可以免除侵权责任。换句话说,行为人虽承认其行为造成了损害的原因,但主张实施该行为时具有合法的根据。正当理由一般包括“依法执行公务、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受害人同意”[4]658。而外来原因则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其一般是指因行为人之外的原因而造成的损害,行为人据此可以免除或减轻侵权责任,即行为人否认损害是其行为造成的。外来原因包括“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受害人过错、第三人过错”[4]662。这是目前我国法学理论中对一般侵权行为的免责事由比较完整的论述。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不可抗力”作为一种免责事由,仅仅是侵权行为免责事由体系中的一种而已。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新的免责事由会不断出现,免责事由体系也会逐渐完善和多元化。然而,很多时候人们在使用这个范畴的时候,往往忽视其中因素变化所带来的差异,撇开具体的法律关系来适用免责事由,使其适用泛滥化,严重脱离了法律思维的轨道。
2 “不可抗力”作为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的不合理性
环境侵权及其构成要件、归责原则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免责事由的特殊性。目前,学界有的学者对“不可抗力”作为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持支持意见,但也有些学者认为环境侵权中,“不可抗力”不应该作为一种免责事由。实践层面,全世界的许多案例,如“切尔诺贝利事件”,“印度的毒气泄漏事件”,以及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都将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予以排除,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不可抗力作为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免责事由应与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具有相同基本价值取向,“即这一原则应立足于公平地保护受害人权益,并最大可能地弥补受害人遭受的损失。”[5]总之,不可抗力作为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面临挑战,其制度的不合理性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环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和因果关系。环境侵权中的归责原则和因果关系是环境侵权中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归责就是确定责任的归属,是“负担行为之结果,对受害人而言,即填补其所受之损害。”[6]272归责原则“指在行为人因其行为和物件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之后,应以何种根据使之负责,即法律应以行为人的过错还是应以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亦或以公平等作为价值判断标准,而使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7]173归责原则解决的是确定责任的根据,为责任的成立寻找依据。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也是贯穿于侵权行为法中对各个侵权的归责立法指导方针,体现了侵权行为法的立法价值取向和价值功能,在侵权行为法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我国环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现行立法明确为无过错原则。在环境侵权责任中,“在不可抗力存在的情况下,致害人无过错或只有部分过错且致害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必然存在因果关系或相当因果关系,不可抗力本身才是损害的发生的主要原因”[8]171。在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也有特殊性,一般认为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即因果关系的认定不是抽象的,主观臆断的,而是符合自然的社会的经验法则[8]172。因此,因为不可抗力,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而免责,在理论和实践中都会说不通的。
第二、工业革命以来,工具理性主义和科技革命推动所带来的现代文明,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巨大的推动了全球的工业化浪潮。欧美主要国家的生产力获得飞速发展,经济的繁荣伴随着对自然地征服和对环境的极端破坏,文明陷入了可怕的“二律背反”。经济的发展应该具有的样态是人类生活环境的美好,但是,工业化的带来的却是人类环境的巨大损害。现代文明应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人类赖与存在的环境一旦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人类灭亡也就不远了,毕竟,目前为止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最终会招来自然地报复。于是各国权衡利弊,一方面在承认环境损害的事实的基础上,另一方面采取相应的机制来增加自己的社会责任,以求效率与公平。在此背景下,各国在环境侵权责任中,大多规定了无过错归责原则,让企业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因果关系上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但是,由工具理性的主导下的经济行为,很多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可见,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凌驾于全球环境利益之上,严重阻碍了全球环境利益的维护。
第三、环境侵权行为人本身的行为是一种经济上获利行为,而且政府也是利益相关方,政府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的发展来树立的。政府不仅是一种政治组织,还是社会组织,承担着应有的社会责任。环境侵权者主要是企业组织,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伴随着对他人和社会环境的损害,所以,让其承担与其相应的无过错的社会责任也是非常公平的。企业的经营行为威胁到公共利益的时候,其承担的“公法责任”也不可避免。政府是公权力的代表,主要承担的主要是过错责任,本质上是一种监管责任。但是,当损害是在合法的情况下,或者无法追查侵权人的情况下,政府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种责任由政府的公共性质决定的。而且在侵权中,企业的经营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具有功利主义的目的,这种目标的实现与他人生存的环境利益紧紧相关。企业强势的地位决定了,在无过错的侵权中,本着正义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让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是理所当然的。王利明教授就认为:“如果某些高度危险责任属于无过失责任,就不应以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不可抗力虽然表明被告没有过错,但损害在事实上又确与被告的行为和物件有关,若完全免除被告的责任,将使无辜的受害人得不到任何补偿,从而不能达到对损害进行合理分配的无过失责任的目的”[7]317-318。
第四、要求“不可抗力”下,环境侵权行为人不免责,有利于增强其注意和谨慎义务,也有利于引导社会行为,充分发挥制度的指引作用。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在微观层面上的企业,企业的物质生产维持着人类社会的延续。大规模的企业行为,本身具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是一对矛盾,我们既不能只要发展,不要环境,也不能只要环境,停止发展,关键的是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环境侵权实行无过错原则本身的立法精神是值得赞许的,但规定“不可抗力”使其免责事由无疑使这个制度失去了本身立法价值。要求“不可抗力”下环境侵权行为人不能免责,可能有的企业认为很不公平,但其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层面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可以在更宽广的领域使行为人甚至更多企业树立环境意识,倡导环境伦理,引导良性环境行为。
第五、我国的相关立法也规定并不是所有的环境侵权中的“不可抗力”都是免责的,而只是将不可抗力的范围限定在某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6条,《环境保护法》第41条,《水污染防治法》第56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3条都将不可抗力规定为免责条款,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噪声污染环境防治法》则未将“不可抗力”规定为免责事由。从上述有关规定看,我国在环境污染损害中,就自然现象引起的损害仅限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作为法定的免责事由,而且该法定免责事由在作为引起损害时,被告必须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及时采取救济措施,以免造成环境污染。2008年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85条第2款规定:“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水污染损害的,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新《水污染防治法》把“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的范围进行了扩大。这说明立法者的在特定情况下,已经将“不可抗力”排除在免责事由之外。
第六、当今世界,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性的“全球问题”,实行无过错为基础的环境侵权领域,不可抗力成为免责事由可能会违背全球环境伦理的价值目标,也与环境哲学的理念相去甚远。全球化使地球成为一个“地球村”,使各国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一员。每个国家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单个的行为,而是与我们整个人类的行为密切相关。当我们将民主视为全球的普世价值时,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与环境和谐相处。发展是各国普遍追求的现实目标,但发展不是以技术理性无情的征服环境为代价,而是与环境相平衡、适应的发展。功利主义哲学所倡导的工具理性破坏了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关系,恩格斯早就指出,人类对环境的征服,早晚会得到环境的惩罚。现在,这个惩罚终于来临了,“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极端恶劣天气”,“生物多样性缺失”等等问题,已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存在。“全球问题”终究要靠全球治理结构的完善来解决,一个国家不能解决所谓的“全球问题”。况且,很多环境问题已经超出了一国控制的范围,如果将“不可抗力”视为免责事由,会导致各国在环境问题上相互推诿,消极不为,最终受害的将是整个人类。
综上所述,在环境侵权中,“不可抗力”不适宜作为免责事由。但现行制度还是将不可抗力作为有限制条件的免责事由,为行为人的免责留有余地。这样的规定也有其相对合理的一面。如果丝毫不考虑侵权后行为人的积极作为,一概认为“不可抗力”不免责,其后果是什么呢?行为人选择就很明确,只会消极不作为。因为积极作为防止损害扩大和消极不作为,法律后果都是不免责,那行为人当然会袖手旁观,受害的只能是受害人的环境利益。
可见,目前的制度有进行相应的完善的必要性,使其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更具有可操作性,更符合法律正义。
3 环境侵权中“不可抗力”免责事由制度的完善
综上所述“不可抗力”作为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在理论和实践中面临质疑和挑战。其根本原因归结于环境侵权中特殊的归责原则和因果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思考可行的解决方法。一方面,改变其特殊的归责原则,即把无过错责任原则改为其他的归责原则,以求与相应的侵权责任构成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将“不可抗力”从免责事由中剔除出去,实行“不可抗力”不免责的责任原则。
这两个思路,前一种做法,很明显是不可能达到的。首先,立法层面是不可能得到支持,会遭到立法机关的“冻结”。法律制度出了问题,只能通过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来解决,但这种解释不会违背其立法精神。现行制度总体上还是比较合理的,为了个别条款而废除整个制度不太可能。其次,在理论层面,无法站得住脚。环境侵权中,选择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是立法机构和法学家们经过大量的思考和总结实践经验得出的,有其社会和理论基础。利益权衡选择的无过错原则比较好的保护了受害者的环境利益,而其他的归责原则是制度设计中摒弃的 “次品”。最后,在实践层面,无过错原则有现实可操作性,有利于弥补因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赔偿,而不至于使普通民众因侵权而无法得到赔偿的制度尴尬。现实生活中,很多的环境侵权合法进行,另外,许多侵权无法找到行为人,或者说行为人是一个不确定的群体,这些都为受害人寻求救济和维权造成困难。而实行无过错归责原则,可以避免这样的局面出现,最大程度上维护受害人的利益。
第二种思路,我们可以尝试将“不可抗力”适当地清除出免责事由的体系。也就是说,在“不可抗力”的背景下,尽管行为人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仍没有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不可以免责。此制度的变化与现行制度的最大区别在于,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上的积极努力的因素,只要出现了“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行为人都应当承担责任。这样设计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行为人将承担更加严苛的责任,其间接的效果在于可以增强行为人的注意和谨慎义务,在生产中积极地采取相应措施,将“不可抗力”的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同时也有助于培养行为人的社会责任感和环境伦理意识。但是这种制度设计的缺点也是很大的,例如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来说,当不可抗力来临时,其无法预测灾害的何时到来,也无力采取完备的措施来预防。假如在此次事件中,东京电力公司没有丝毫的过错,也无法阻止灾害的发生,但却要承担巨额的赔偿费,这也是法律正义所不允许的。这样的后果就会使行为人负担巨额的赔偿金,大大阻止人们开发和从事经济活动的欲望和动力。另外,将“不可抗力”排除其“免责事由”体系,也会使行为人消极不作为,其法律和社会效果更加有害。相比较而言,第二种思路可能会更加合理,因为该制度的价值在于保护受害方的利益,但我们不能完全接受第二种思路。我们应结合现行制度,对第二种思路进行反思,使“不可抗力”制度趋向于完善,实现“修正的正义”。
首先,在法律的范围内,应当严格界定“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一个相当模糊,没有明确界定的范畴,适用到具体案件中,产生争议不可避免。法律不明确会使人们陷入可怕的奴役状态。“不可抗力”指“不可避免,不能预见,不能克服”的自然和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主要指地震、海啸、暴雪、泥石流、火山爆发等自然力,这些涉及到自然知识的范畴;社会现象包括战争、暴动、罢工等社会现象。并不是所有的自然和社会现象都可以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需要我们的技术支持和社会理性标准。也就是说,需要专业的权威的技术部门来认定不可抗力的内容,例如:不可抗力的程度、不可抗力构成法律意义的临界点、不可抗力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影响等等,这些因素对行为人是否应承担无过错责任,承担多大的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据此,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专业的“不可抗力鉴定机构”,司法机构可以建立,民间有资质的也可以建立,并在财政上和制度上保障其运行。此种机构的建立,可以更好的鉴定“不可抗力”的诸种具体因素,具有更公正的法律效果。
另外,在不可抗力发生以后,行为人“及时采取合理措施”的“及时”和“合理措施”如何认定?目前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对此缺陷,在制度设计时,最好能有法律或法规、规章对此作出较明确的规定,但一定要鼓励行为人的积极作为和利益平衡为宗旨,这样才能在司法实践层面具有可操作性。即使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司法人员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判断标准。
其次,对“不可抗力”的界定,还应以现存的科学技术水平为依据。任何法律范畴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受到具体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可抗力”的法律价值和意义不能脱离现存的条件抽象地去谈,而要以当下的技术水平为支撑。此外,“不可抗力”要以一般大众的认识水平来判断,而不能以专业技术人员的立场或行为人的立场来界定,专业技术领域的人员有很丰富的自然技术水准,以他们的眼光来界定“不可抗力”,对行为人太过于苛刻,不利于公正;而以行为人的立场来界定,他们会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也会失去公正。
最后,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进行价值分析。价值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主体自身需要和满足,二是客体固有的某种属性。价值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主客体之间一种价值评判关系,价值关系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价值的核心问题是主客体之间的实践基础上的关系,体现了主体与自然的关系,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和自身的关系。价值关系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作为价值属性,既取决于客体又取决于主体的需要和主体的实践活动,即主体的对象化和客体的人化。
近代世界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和理性是现代性最主要的特征。科学合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种价值体系下,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充斥着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人类运用技术征服自然,但是却忽视了人类终极价值。人类的终极价值在于“有家”,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告诉我们,在进行制度反思时,必须以环境伦理思想为指导,将环境价值与人的价值统一起来,将“不可抗力”的免责事由放在人与环境的价值关系中来考量。
“不可抗力”一直是环境侵权中的免责事由,这与现代的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相违背。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来考虑,环境侵权领域不可抗力不宜作为免责事由。但是,结合我国的现行的法律制度,将不可抗力完全排除在免责事由的体系之外,也违背法律的正义。只有结合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对现行制度进行修正,严格规定“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适用的相关制度,才可能实现“修正的正义”。
总之,环境侵权由于特殊的构成要件、归责原则,决定了其免责事由的特殊性。而不可抗力究竟能否作为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还值得进一步的探究。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必须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明确“不可抗力”和免责事由,严格限制“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适用范围。这样才能发挥这一制度的法律价值,最大程度上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1] 周珂.环境与资源保护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王利民.侵权行为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4] 郭明瑞.民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 陈太红.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免责事由探析[J].矿业安全与环保,2002.
[6]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五)[M].台北(自版),1987.
[7] 王利民.侵权行为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8] 李伟涛.不可抗力作为环境侵权责任免责条件的探析[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3,23(6).
Force Majeure—the Excuse for Immunity from Liability in Environmental Tort
JIANG Ping
(GuangDong AIB Polytechnic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07,China)
Due to the special principle of “no-fault liability” in environment tort, “force majeure” has always been an excuse for immunity from liability in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the extensive use of high-technology, “Force Majeure” caused academic debate as whether it is appropriate to be used to plead for immunity from liabil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ed issues of “force majeure” in immunity from liability, and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system.
environmental tort; force majeure; immunity from liability
D923
A
1672-0318(2016)04-0032-06
10.13899/j.cnki.szptxb.2016.04.006
2016-03-02
姜平(1979-),女,山东平度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