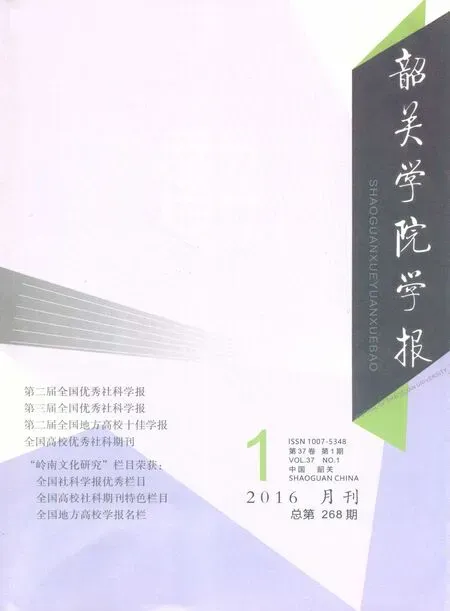重评戴望舒的《论诗零札》
2016-04-12张丽华
张丽华
(广州工商学院 基础教学部, 广东 广州 510850)
重评戴望舒的《论诗零札》
张丽华
(广州工商学院 基础教学部, 广东 广州 510850)
摘要:戴望舒对象征主义诗学理论作了批判性接受与继承,并在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论诗零札》反映出他一以贯之的理论风格,并具有现代性品格。戴望舒追求的是诗歌的永久性价值、永存性理念,他的诗论不为一般人所理解。
关键词:戴望舒;象征主义;传统诗学;《论诗零札》
从白话文兴盛以来,中国诗坛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白话文写就的新诗应运而生。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诗坛,新诗从惶惶草创期逐渐走向自觉开拓期。在这个过程中,戴望舒顺应潮流,不断地摸索诗歌前进道路。作为新事物的兴起阶段,新诗理论几乎一片空白,戴望舒的《论诗零札》虽然只有十七条,但对于当时的诗坛来说,却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可以说,《论诗零札》是戴望舒在充分接受传统诗学教育之后,再糅合国外诗学而浓缩出的诗论精华,它对戴望舒的创作和翻译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象征主义诗学的现代性影响
世界上最轰轰烈烈的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的法国。它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欧美各国,影响广泛而深远,但它从未在中国得到系统、全面的介绍。“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除了表现新的内容外,另一个特点就是“诗体大解放”。那时胡适等人正忙于为新诗呐喊,尝试创作,打破旧诗歌的格律束缚。但打破旧诗的形式之后,新诗该怎么建立、建立成什么样的形态,却难以统一意见。这期间在诗歌理论建树上比较有影响的是新月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提出了“三美”理论。但新诗自身发展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直到30年代前后,戴望舒等诗人感应这一历史要求,经过精益求精的艺术探索,终于把新诗创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更高层次上的追求,是另辟蹊径的攀登。
从法国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的“美的现代性”到活跃在19世纪末(中国的现代性社会刚刚展开的时期)的马拉美、魏尔伦、兰波,他们不仅发展了波德莱尔的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追求朦胧美和音乐感,还重新建立了全新的诗学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超越了波德莱尔,把诗引入了更高的主观层次,而且将象征主义带入了欧美,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戴望舒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到法国留学,深受象征主义诗论的熏陶。
二、对象征主义诗论的接受与发展
戴望舒的诗作,很少因过于朦胧而阻碍了完全的理解、感悟。他的诗作有一种清晰的朦胧,这种朦胧是积极的,是更神秘地促进了理解的。比如他的《烦忧》[1]:
说是寂默的秋的悒郁,
说是遥远的海的怀念,
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因,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因,
说是遥远的海的怀念,
说是寂默的秋的悒郁。
虽然我们不能明确的指出戴望舒在这首诗作中所要具体指向的对象,但这首诗却能引起我们许多共同性的情感体验,将“烦忧”的无由无理性展现得很优美,同时又将这种抽象性表现得可感可触。戴望舒始终立足于自己的真情实感,表现的是他自己整个隐秘的灵魂,弹唱的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乐音,把心灵丰富的色彩表现出来。他的诗歌到处充溢着象征主义色彩,如《印象》、《白蝴蝶》等,但他并没有出现过象征主义颓废、抱怨的一面,他的诗歌有一种明净的忧郁。苏珊娜·贝尔纳曾说:“和象征派相反,戴对现实既不抹煞也不扬弃,超越而不否认。他总是在梦幻与现实间往返,绝不顾此失彼。”[2]85
如果说波德莱尔认为忧郁是现代诗美的伴侣,那么戴望舒一直延续不变地热衷“忧郁”,则可看出他们之间的“诗心会通”。一个诗人接受一个派别的影响绝不是空穴来风的,其中有两者非常相契的理解与融通。
在《论诗零札》的第八条里,戴望舒说:“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1]波德莱尔在《交感》中提出“味、色、音感应相通”的见解,此论对戴望舒有明显影响。戴望舒在其诗作《独自的时候》:“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是流过眼泪,而从外边,寂静是悄悄的进来。”听觉与视觉沟通;《小病》:“从竹帘里漏进来的泥土的香,在浅春的风里几乎凝注了。”嗅觉转移为视觉;《款步(一)》:“如果你再说:我已闻到你的愿望的气味。”五官感觉之外的精神感觉同嗅觉联为一体。通感的手法其实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也有涉及,只是不似象征主义诗歌这样明确提出,对此戴望舒并不陌生。在《论诗零札》的第九条中,戴望舒说:“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1]从这条诗论中我们看到戴望舒诗歌的偏向性,他指向的是诗歌表现人的情绪。这是象征主义诗歌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人物兰波曾写到:“想成为诗人的人,首要的课题是认识自我,完全的认识自我,他探索自己的灵魂,观察它,体验它,研究它。”[3]这种体验要求带来自然的情绪,在第十五条里,戴望舒更进一步的提出:“诗应当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而使人感到一种东西,诗本身就像是一个生物,而不是无生物”[1],高度肯定了诗存在的生命性。而第十六条,对怎样表现情绪又做了进一步论述,戴望舒说:“(情绪)它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出来。这种笔触又须是活的,千变万化的。”[1]这里戴望舒看到了情绪化为诗之过程的活跃性、生动性、暂时性,他强调的是诗的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发展性、延伸性。表现情绪的诗歌在戴望舒的创作中比比皆是,如《雨巷》、《忧郁》等都是情绪的笼罩,感情的沉积。
通观戴望舒生前遗存的大部分诗歌,包括译诗,戴望舒的诗作与象征主义的关系很大。首先从内容的关联性来看,戴望舒的诗作触及较多的主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寂寞、怀乡病、少女、夜、等待……其次从诗歌的艺术手法方面来看,他把象征主义的作家所运用的意象大量地移植进他的诗歌中,如木叶(死叶)、青色;有些句子是完全的挪用、套用,不加变更。在关于“夜”的译诗中,有四首:《夜深》(比也尔·核佛尔第)、《等那夜》(苏佩维艾尔)、《夜之光》(沙里纳思)、《夜》(普希金)。而戴望舒有5首以夜为题的诗作,《静夜》、《夜》、《秋夜思》、《前夜》、《夜行者》。这正如他在《论诗零札》第四条里写的:“象征派的人们说‘大自然是被淫过一千次的娼妇。’但是新的娼妇安知不会被淫过一万次,被淫的次数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要有新的淫具,新的淫法。”[1]
《少女》是耶麦的一首自由体诗歌,诗歌不押韵并且不整齐,但节奏随情绪的波动而流荡,畅达而自然,淳朴而清新,充分体现出自由体诗歌洒脱自如的散文美。正如戴望舒在《论诗零札》的第六条里写的:“新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nuance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法文:变异)。”在这首诗歌中,耶麦通过通感、暗示等手法,在语言的重新组合中创造出整体象征,以造成陌生化的新奇效果,如“她有温存的手臂”。而在戴望舒的《我的恋人》中,他也以自由体的形式来构造,使用“桃色”、“天青色”、“黑色”等颜色词来暗示恋人之美,心灵之纯洁,性情之温柔,从而激发读者全方位地感受到恋人之美。这同样很符合他在《论诗零札》第八条的内容:“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随着他所受的影响而不断地发展,他开始受到魏尔伦诗论的影响,创作出了《雨巷》,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激赏,他也由此得到了“雨巷诗人”的封号。但随后戴望舒就否定了《雨巷》,他要抛弃音乐的外壳,他从果尔蒙、保尔·福尔、耶麦的主张里,认可了诗歌主要表现的是“诗情的变异”的内在节奏。紧接着,他又在诗论中不断地更正。施蛰存曾说:“望舒译诗的过程,正是他创作诗作的过程。译道生、魏尔伦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译果尔蒙、耶麦的时候,正是他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体的时候。”[4]戴望舒的诗歌写作一直处于形成发展过程,在翻译诗歌的过程中,他确实几度改变作诗的理论,这从他断续写就的十七条诗论中就可看出。
三、对传统诗学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诗歌一直有赋比兴的传统,而且主张“正变说”,从文以载道的传统一直到后来的悦情悦性,都可以看出各个时代对诗歌的主张是发生了变化的,后来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就彻底肯定了诗歌个人的情感因素对诗歌的极大作用,而中国诗歌的意象说,很有力地说明了诗歌写作中造境的重要性,就有了情景交融的探索。景是经过感情浸润过的,是带有想象性质的;情是笼罩于景色之中的,显现于眼前的,是真实的。中国诗歌的语言从先前的四六言,到固定的七言、五言,以及到现在的较为自由的诗歌体式,都同样地出现了具有历史价值的优秀诗作。无论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不影响诗歌穿越时空给与人的美妙影响,所以文字对诗歌的限制是极为细微的,甚至可以说真正好的诗歌是能够透过文字直接达到完美的精神境地的。
《论诗零札》第十条中说:“不必一定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我不反对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1]这句话可以读出戴望舒传统修养的一方面。在融新知与旧知的能力方面,闻一多、戴望舒都是达到了化而为一的境界。戴望舒的诗作在运用古典意象方面,可谓无处不有。比如:《老之将至》:“而那每一个迟迟寂寂的时间,是将重重地载着无量的怅惜的。”它使人们想到李清照的《武陵春》:“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王实甫《西厢记》中的散曲:“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又如《雨巷》中:“丁香一样结着愁怨”,它令人想起李商隐的《代赠》:“巴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南唐李璟的《摊破浣溪沙》:“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就如戴望舒在《论诗零札》第十一条里所说:“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1]《论诗零札》第十四条,戴望舒写道:“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1]这句话实质上道出了写作的要诀。写作要求作品在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达到某种超越,从而实现高于生活本身的目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而非生活的照搬,想象是超越的真实,艺术就是真实与想象的结合体。戴望舒在翻译诗作上的贡献非常大,他翻译的诗作,也一直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作为一个资深译者,他看到了诗歌超越地域性的特质,而这绝非文字所能影响。戴望舒对诗作强调更多的是诗歌的诗心,诗歌的骨骼,而非文字之类的形式所限。这也再次印证了他前面几条摒弃作为诗歌形式存在的音乐、绘画等的依托。所以他在第十三条里说:“诗应该有自己的originalite,但你须使它有cosmopolite性,两者不能缺一。”[1]这里更多的强调了诗歌本身的性质,它必须集特殊性和普遍性为一体,方能成为真正的诗作。
四、结语
作为一个既接受了传统诗学教育,同时又到法国留学的戴望舒,他的诗论不可避免地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译作,都跟他在《论诗零札》里所反映的思想是非常一致的。如《论诗零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十一条内容相关,主要是论述诗的形式,如下为基本内容:
一、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
二、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
三、单是美的字眼的组合不是诗的特点。
四、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
五、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nuance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
六、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了别人的鞋子一样。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
十一、不应该有只是炫奇的装饰癖,那是不永存的。
有人认为这是冲着当时的新月格律派而来的,我们固然不排除这个因素,但我们更应看到戴望舒其实一直强调的是不是作为“诗”的成分存在的形式。他曾说:“古诗和新诗也有着共同之一点的。那就是永远不会变价值的‘诗的精髓’。那维护着古人之诗使其不为岁月斫伤的,那支撑着今人之诗使生长起来的,便是它。”[2]73从这个角度审视,就知道戴望舒的诗论实际上是站在更高的角度,他说的是永存的诗该怎么写的问题,遵循着什么原则的问题。他的诗论比新月派更深刻的地方就在于他探索的是现代的诗歌,永久性存在的诗歌的理论方向。这是一种对诗的见解的超越性理解。象征主义与传统诗学,戴望舒都兼收并蓄,并不排斥,他以一种严谨的态度选择着他的走向,写着他的诗歌。所以我们读他的诗作常常闻到了现代人的气息,古代人的韵味,西方人的理智。当然鉴于戴望舒个人的气质,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诗作中有着太过于单薄的情感。
参考文献:
[1]戴望舒.雨巷·我用残损的手掌[M]//吴福辉,陈子善.现代作家精选本.上海:复旦大出版社,2006.
[3]张英伦.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概[J].诗探索,1981(1):164-187.
[4]戴望舒.戴望舒译诗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
(责任编辑:宁 原)
Reviews on Dai Wangshu’s Notes on Casual Poetics
ZHANG Li-hua
(Department of Comprehensive Teaching, Guangzhou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Guangzhou 510850,Guangdong,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focuses on Dai Wangshu’s symbolism poetics theory with critical inheritance,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his cre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his poetics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oetics, there is a consistent to reveal his poetics theory of style, and has the character of modernity. Dai Wangshu emphasizes the permanent value of poetry, permanent concept, therefore his poetry is not commonly understood.
Key words:Dai Wangshu; symbolism; traditional poetics; Notes on Casual Poetics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16)01-0034-04
[收稿日期]2015-12-29
[作者简介]张丽华(1983-),女,江西余江人,广州工商学院基础教学部教师,硕士;研究方向:大学语文和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