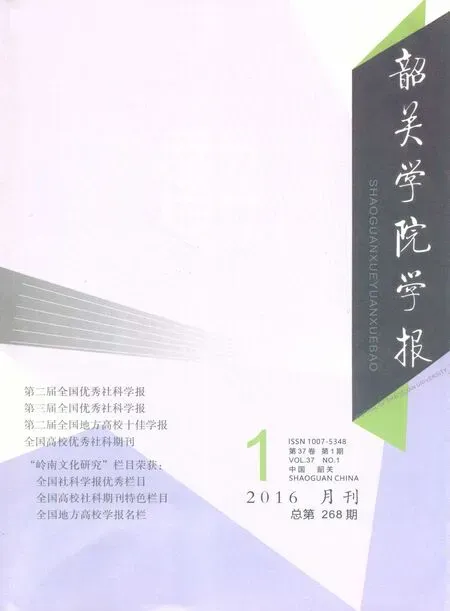论《伤心咖啡馆之歌》的时间美学
2016-04-12甘细梅
甘细梅
(韶关学院 外语学院, 广东 韶关 512005)
论《伤心咖啡馆之歌》的时间美学
甘细梅
(韶关学院 外语学院, 广东 韶关 512005)
摘要:《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叙事时间呈现回环往复的形式,对应于反复再现的小镇的社会空间,暗示作用于小镇的重复运作的社会等级化机制;景观时间作用下,现代人失去了生命时间,身体被肢解,灵魂被扭曲,孤独具有宿命性,疾病不可治愈。
关键词:《伤心咖啡馆之歌》;景观时间;主体
《伤心咖啡馆之歌》(The Ballad of Sad Café)(以下简称《伤》)是美国南方女性作家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1917-1967)言说孤独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叙述的是一个传统的三角恋故事:帅气的恶棍马文糟蹋淑女,却死心塌地的爱上了身材魁梧、性格古怪的爱密利亚小姐,但爱密利亚在结婚十天后赶走了马文,而对前来投靠她的表兄罗锅李蒙倍加呵护。罗锅李蒙又迷恋马文,抛弃爱密利亚给他的所有优厚待遇,追随马文而去,却被马文卖给杂耍团。作品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的回忆叙事模式。叙述者对叙事进程的干预以及倒叙和插叙的使用使得叙事时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跳跃,人物性格发展、叙事因果以及故事逻辑等历时性因素并非呈线性发展,而是以折扇式的层次铺开。时间的回环与空间的反复呈现更显示出现代人孤独的宿命性与疾病的不可治愈性。
一、回环往复的叙事时间
福柯认为19世纪是沉湎于历史的时代。在小说作品中,时间较之于空间具有优先性。小说家们更关注情节结构、悬念、高潮和结局等因果逻辑关系。空间因为其在场与共时的特质而“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1],是“一种现在的空无,只被赋予了形式上的特征……是一个等待着填充内容的容器”[2]170。空间只作为人物行为活动展开的背景。“人物在根本上是在空间或‘场景’中展开的时间建构,一旦被建构起来,似乎就会长久保持下去”[3]。然而,20世纪以来,空间形式的小说背离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性格刻画对情节的替代,缓慢的速率,事件结局的欠缺,甚至是重复”[4]。空间形式的小说打破时间的顺序,试图通过场景的切换实现知觉上的共时性。在此意义上,《伤》是成功运用空间叙事的小说。
然而,虽然时间与空间的表现形式相互区别,小说家对它们也各有偏好,但时间与空间相互暗示、相互作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巴赫金 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了时空体(chronotope)的概念[5]274。他认为时间是空间的第四维。“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5]275。时间虽无法建构,且被消费殆尽,但它却在空间留下痕迹。时间“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5]275,在空间中表达自己。时间的空间化使其获得了视觉感和物质性。在本质上,我们通过空间感知时间。通过空间的形式,我们意识到时间的流动[6],也获得了对时间的认知。时间与空间之间不同系列的交叉和融合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5]256。空间政治学先驱亨利·列斐伏尔也认为诸如生老病死等“时间性”现象无法与空间性分离[2]175。爱德华·苏贾认为“历史与地理具有交互作用……历史与地理是存在的‘纵向’与‘横向’关系”[7]。《伤》并没有完全抛弃时间在叙事中的作用,更多的是将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融为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体。
小说开篇,叙述者以故事的结局作为叙事时间的起点,以哥特式的手法描写小镇的偏僻、畸形、扭曲的全貌,随后跳回十年前李蒙到小镇来的那个温暖、安静的夜晚,接着又以咖啡馆的诞生为视点,时间向前飞驰到四年后咖啡馆的鼎盛时期,随后又回溯到爱密利亚为期十天的婚姻,紧接着时间又闪回到李蒙来到小镇6年后马文重回小镇的场景,最后回到开篇的八月闷热难耐的场景,即咖啡馆被毁的三年后的八月。作者在强调时间的冷漠飞速流逝,无视痛苦存在的同时弱化了时间的连续性、顺序性和因果关系性。“时间/这个无边无界的傻瓜,尖叫着环绕世界奔跑。”[8]叙事时间向前向后,循环往复,环环相扣。“时间之循环对应于一种具有对称性的循环的空间形式”[9]。时间不断闪回,相似的空间场景反复出现。八月的耀眼发烫和冬天的寒冷砭骨年复一年循环上演,毫无例外。它们袭击小镇,留下的痕迹沉淀、累积在建筑物的外墙上,使其变得更暗、更脏、更接近坍塌。小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因为爱密利亚的婚礼、李蒙的到来、咖啡馆的诞生、爱密利亚和马文的格斗等滑稽怪异的事件而被标记,界限明晰。陌生元素的移入虽然暂时给小镇输入了新的能量,李蒙作为“陌生人”的到来使得店铺改为咖啡馆,给了小镇居民一个乌托邦的去处,但李蒙最终觉得小镇的生活无聊无趣,与马文一起毁了咖啡馆,也毁掉了小镇最后一丝温情和希望。咖啡馆的变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人追逐金钱的欲望,也未打破小镇固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反而恶化了小镇衰败的状况。线性的时间机械重复的特性与空间轴的结构相关。与此相伴随的是重复的运作机制[2]175。时间与空间的重复模式揭示了反复作用于小镇的形成、发展的南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小镇是南方社会等级分化和特权政治统治的结果。时空的分离以及时空分离的社会现实是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分离的必然结果。小镇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是特权阶级使用空间技术隔离并统治边缘人群的结果。物质生活的贫乏与精神的颓废是边缘人群被扭曲了的形象再现,也是被“他者化”的人群的现实生活状态。
时间流的断裂使时间失去了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动力。“场景的空间化使得一个纯环境担任起叙述情节的任务。”[10]镇上的建筑物“有一种古怪的、疯疯癫癫的气氛”[11]1,“看上去很脏,七歪八斜”[11]57,“倾斜的那么厉害,仿佛每一分钟都会坍塌。”[11]1路边几株矮矮的桃树是细小扭曲的。李蒙离开后,“那些桃树似乎每年夏天变得更加扭曲了,叶子灰得发暗,细软得有些病态。”[11]71与过去相比,小镇沉闷、忧郁、丑陋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而且变得越发毫无生气。异常的事件因麻木、机械的生活而落入陈规,寻常化为一成不变的日子。现在和未来只不过是过去的重现。过去、现在和未来糅合成一团肮脏、破败、病态的物体表面。时间给人以一成不变的呆滞、刻板体验,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动力和生命力。
由此,叙事时间被视觉化为荒诞、破败的场景,回环的时间流获得了可见性和物质性,感官化为循环再现的天气,视觉化为南方小镇破旧、肮脏、怪诞、乖僻、畸形和扭曲并且充满空荡荡孤独感的地理空间。时间里浸透着的痛苦、疯狂、悲观、无望、无奈因此变得可视、可感、可触,震慑人的心灵。回环的时间以及与世隔绝的封闭空间成为小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空间,无法躲避,不能抗拒,不可抛弃。
二、景观时间与现代性主体
“景观时间”是居伊·德波基于“分离”(separation)概念而提出的观点。他把“人类非发展的一般时间”视为“虚假时间”,被工业改造过的时间[12]69。“可消费的虚假循环时间就是景观时间。”[12]70景观时间是异化的时间。它以商品生产为基础,重新组合了包括私人生活、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在内的一切事物,同时也作为商品被消费。“在商品时间的社会统治下……人什么也不是,至多只是时间的残壳”[12]69。商品迫使人与真实的日常生活分离,体验被消费化、机械化和重复化,人成为异化的平面人。随着现代性的到来,“时间已经在现代性的社会空间消失了。”[13]54在工业社会,个体的生命时间贬值了。除了工作时间,个体的生命时间已经失去了其形式和社会利益。“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价格,你不花钱就买不来,这就是眼下的世道。”[11]54生命时间作为商品被消费,人之为人的价值被舍弃或忽略。作为人的尊严被剥夺。贫穷让人在心灵深处感觉生命低贱、毫无意义。他们自觉生命值不了几个钱,甚至是一文不值。主体失去自我认同的价值。
现代工业分工方法肢解了人的身体,进一步将人性以及人的尊严推到崩溃的边缘。现代工业的分工方法“把作为整体的身体简化为服从于许多严格的线性控制的细小动作”,“把身体肢解为仅仅是一堆由互不相关的部分构成的堆积”[13]37。专业化的极端分工下,人不再是完整的个体,他们的身体简化为流水线上某一个重复的动作。人不再是具有情感的动物,而是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重复单调无聊的动作,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性。“我们改变了衡量人性的方式,从依靠大地的节律,变为依靠都市的机械装置。在那种机械的背后,隐藏着为了金钱而征服自然的破坏性的欲望。”[14]金钱成为衡量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的标准。以金钱作为衡量生命时间的标准扭曲了人的灵魂。以爱密利亚为代表的富人除了从别人身上榨取钱财之外,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与以往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并未让工人摆脱贫穷获得更多的福利。工人反而承受着更多的社会鄙视。工人是廉价的劳动力,工资只可以养活个人,而无法支撑家庭生活。工业不断发展,工人却更加贫困,精神空虚,情感麻木。小镇的纺织工人每天“只想到纺纱机、饭盒、床,然后又是纺纱机”[11]9,机械地重复每日的生活。他们“动作迟缓”,“有点神经质”[11]4,“眼神呆滞的、梦幻似的”[11]14。他们依靠本能行事,丧失了主体性、判断能力和批判性,成为异化的整体。他们集会,参加邪恶的庆祝活动,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也不管行动的后果是洗劫、暴行还是犯罪。“在看到某人为一种邪恶、可怕的力量摧毁时”[11]32,常常会感到特别满意。他们失去了判断力,却以主流意识形态的目光审视爱密利亚的不符合“标准”。他们受一个意志的操控,成为无意识的整体,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对“他者”实行惩罚的工具。对于“李蒙事件”,他们不仅相信说话没有分量的梅里·芮恩的谣言,并集体将谣言编缀成一个阴森、可怕的故事,“过节似地欢庆这桩想象出来的犯罪行为”[11]13,准备对爱密利亚进行审判。人物行为荒谬到让人发笑。
三、小结
卡森·麦卡勒斯以时空交叉相连的网状结构勾勒出美国南方的地理图景。时间物质化为空间,获得了荒诞、病态的特质,强化了小镇社会空间的荒凉、孤独和怪异。时间消失于现代的景观社会之中,八月下午的闷热场景反复呈现,人成为疯狂、怪诞、失去主体意识的无意识集体。异化的个人和群体又画地为牢,自我封闭,成为孤立的中心。他人成为自我孤独的根源,自我也成为他人的地狱。孤独是从百叶窗探出的鬼魅的脸,即便在燃烧的八月也让人感觉背脊凉飕飕的。荒诞中带着刺骨的哀伤。“恐惧/空间的,还是来自时间?/抑或两个概念合谋的诡计?”[8]时间和空间的角力生成了孤独的悲歌。
参考文献:
[1]Foucault M.“Questions on Geography”[M]//C.Gordon (ed.).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1980:70.
[2]Lefebvre,Henri.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 Donald Nicholson-Smith, 1991.
[3]热拉尔·热奈特,琳达·哈宁,拉尔夫·科恩,等.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M]//阎嘉.文理论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出版社,2006:136.
[4]戴维·米切尔森.叙述中的空间结构类型[M]//秦林芳,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北京大出版社, 1991:143.
[5]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6]Mitchell W J T. Spatial Form in Literature: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M].Critical Inquiry Chicago:Universtiry of Chicago Press,1980: 542.
[7]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7.
[8]卡尔.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M].冯晓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306.
[9]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建筑[M]//周宪.文化研究.北京:社会科文献出版社,2010:9.
[10]杰罗姆·科林柯维支.作为人造物的小说:当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秦林芳,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北京大出版社,1991:60.
[11]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13]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M]//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47-58.
(责任编辑:廖筱萍)
Reflections on Aesthetics of the Time in the Novelette of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e
GAN Xi-mei
Abstract:The narrative time of the novelette of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e runs in circles, corresponding to the broken social space of the small town, which indicates the repeated action of the social mechanism on the town. Under the influence ofthe spectacle time, people in the modern society lose their life time, and with their bodies dismembered and their minds tortured, they are doom to be lonely and the social diseases can never be removed.
Key words: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e; spectacle time; subject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16)01-0038-04
[收稿日期]2015-10-19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二十世纪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的空间叙事策略研究”(GD13XWW22);2013年韶关学院科研项目“《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叙事空间研究”(韶关学院[2013]205-21)
[作者简介]甘细梅(1980-),女,广东韶关人,韶关学院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叙事学、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