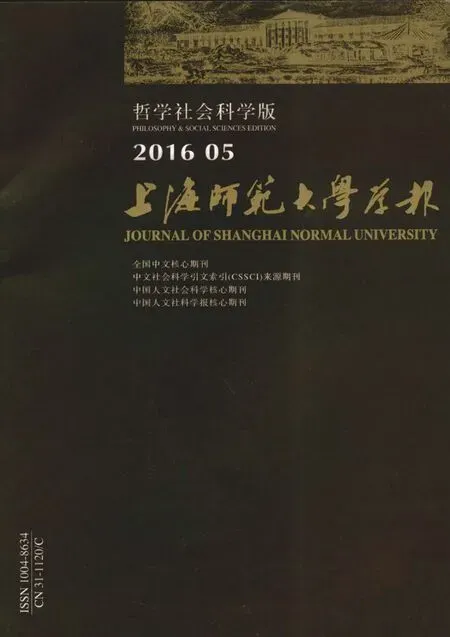自然书写作为政治表达:论兰斯顿·休斯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
2016-04-12罗良功
罗良功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被誉为美国黑人民族代言人的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 1902—1967)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激进的政治书写之后,又回到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黑人生活书写,甚至转向了他此前鲜有涉及的自然书写。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休斯创作了《哈莱姆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inHarlem, 1942)、《自由之犁》(Freedom’sPlow, 1943)、《神奇的原野》(FieldsofWonder, 1947)、《单程车票》(One-WayTicket, 1949)等诗集,其中不乏关于黑人生活的观察和记录,也有前期作品中少有的关于自然的描写与感悟;尤其是诗集《神奇的原野》不仅在主题上远离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表达,而且在形式和题材上也淡化了20世纪20年代作品中鲜明的种族特征,许多诗歌运用了大量的自然题材,展现了休斯不同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布鲁斯诗歌和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诗歌的抒情风格。不少学者从中看到了一个艺术上更加成熟的休斯,例如,黑人学者瑞丁(J. Sanders Redding)声称,休斯在《神奇的原野》中“重新发现了自我”,展示了他的作品“对探索情感的重视”和“朴素通俗表达的力量”。[1](P130)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诗歌不过是肤浅的朴素,就连先前大力支持休斯的左翼或亲共产主义的期刊也大加指责,认为这些作品的“空洞的抒情性”反映了“作者背离了早期的立场、远离了诗歌力量的源泉”,甚至认为那些关于自然的诗歌销蚀了诗人“深刻的现实感”,阻碍了诗人创造出更富有激情的“神奇的原野”。[1](P131)在很大程度上,休斯的自然书写成为争议的引爆点;但事实上,学界至今没有就休斯的书写自然及其动机与意义进行深入研究,而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动机所在。
一、负能量的自然
自然是休斯20世纪40年代诗歌中不容忽视的存在。休斯在这一时期一反早期诗歌创作风格,将艺术视线投向了自然。在20世纪20年代,休斯更关注美国城市的黑人生活,其艺术视角和题材选择常常聚焦在社会化生活场景和人物的内心世界;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休斯由于其激进的政治意图和政治立场而强调诗歌的阶级与族群表达,关注群体生活和精神世界,因而极少将目光投向社会之外的自然。休斯在20世纪40年代不只是将自然纳入自己的艺术视野,而且大量运用自然题材和自然意象,较为密集地将自然编织进自己的诗歌中。虽然鲜有全篇书写自然的诗作,但是加州的山脉、大海的波涛、街头的玉兰、风雨雷电、日月星辰、花草虫蛇等自然意象都进入休斯的诗歌文本之中,成为其诗歌文本所建构世界的重要内容。
在休斯诗歌中,自然题材并非用于建构关于自然的客观描写,而是用于表现主观世界,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休斯诗歌艺术的进一步拓展。休斯的早期诗歌深受美国非裔民族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注重透过物质世界的狭小缝隙探索广阔的精神世界,因而常常忽略物质本身的物象,在表现形式上则借鉴非裔口头表达传统,以声音建构精神世界,强调运用人声或具有浓郁黑人音乐或方言色彩的声音形态作为诗歌表现手段。在休斯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中,声音仍然是精神表达的重要载体,但现实世界的物质形象也成为重要的艺术符号,展现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交融的形态。自然因而成为休斯诗歌中的重要意象,同时联通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情感,形成具有明显现实色彩的抒情性。
在休斯诗歌的抒情机制中,自然从来不是以喻体形式存在于文本之中的,而是与人的精神世界进行互动和相互映照,从而折射出人的精神体验和生命感受。例如,在《生活多美好》(“Life Is Fine”)一诗中,自然与人的关系是通过人的切身体验来建立的。该诗前三节如下:
我来到河边,
我坐在河岸,
我想清醒却又不能,
就跳下去,管它水深浅。
第一次我爬起来大喊,
第二次我爬起来狂叫,
要不是那水太冰冷,
我已经沉尸河底死翘翘。
可是那
河水太冰冷!
太冰冷!①[2](P358)
言说者在这里并没有说明想要跳河自尽的原因,但是他(她)对河水的感受无疑揭示了其中的原因:言说者欲投河自尽,却又因为河水冰凉刺骨一次次从水中爬起来,直至最终放弃;他(她)对冰冷河水的逃离恰恰反映了他(她)投河自尽的动机,即对生活苦难的逃离。这也揭示了言说者最初选择投河的原因也在于逃离现实苦难,而他(她)通过对河水的切身体验使自己认识到当初的逃离是幻想,河水并不是能够使他(她)逃离现实苦难的灵魂栖息之所,因而深化了其悲苦的人生体验,表现出言说者深陷苦难无法摆脱的无奈,也暗示出他(她)在进退不得的困境之中不得不面对现实的人生态度转变。在这一意义上,该诗结尾多次重复的“生活多美好”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同时又表现出面对现实的乐观态度。在这首诗中,自然作为现实世界的物质存在,通过人的体验而与人建立关联,成为人投注自己人生体验和精神情感的对象,因而也成为人的主观世界的一部分。这一模式成为休斯在诗歌中运用自然意象和题材的典型模式,又如《哈莱姆之夜》(“Harlem Night”)[2](P314)即是如此。
在上面引用的诗歌中,河水与人之间并没有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们所推崇的和谐,对于希望投身其中的言说者而言河水无疑是拒斥的、冷酷的。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甚至充满敌意的关系,成为休斯诗歌自然书写的一个共性。在他的诗歌中,自然常常承载着负能量,如残阳常常带着血色、玉兰树常常与被吊死的黑人身影相联,因而凸显了自然对人的敌意和对抗。例如,在《逃难者》(“Refugee”)一诗中,常见的天气现象与人之间全然是敌对的关系:
巨大的孤独敲击着我的心,
折断了的枝条凄凉、痛苦地耷拉。
承受着撕裂天庭的狂轰乱炸,
我站着,光着头,任凭暴雨倾下。[2](P235)
在诗中,“撕裂天空”的“雨”猛烈地袭击着言说者“我”,两者之间的敌对关系显露无遗。“雨”对于言说者而言,无疑充满了负能量,不断袭击着头顶上毫无防护的“我”;但是处于弱势的“我”并不是被动承受负能量的消解,而是以弱者之身承受着大雨袭击的视觉形象,揭示了一种激烈的精神对抗:言说者作为物质意义上的弱者以精神正能量消解或战胜强者施加的负能量。因而,休斯诗歌中的充满负能量的自然与人形成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对抗;这种对立或充满敌意的人与自然关系使得休斯的自然书写远离了浪漫主义自然书写的抒情性或自省性,也远离了休斯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相反,更具有现实性和批判性。
二、反自然书写?
休斯诗歌中的自然呈现出强烈的负能量和对抗性,无疑具有现实性和批判性,但是其批判的锋芒到底指向什么?他是否试图以此建构一种反自然书写?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关注一个事实,即在休斯的诗歌中,承载负能量的自然意象常常与社会现实书写交织,《生活多美好》、《哈莱姆之夜》、《逃难者》等诗歌莫不如此,但是在休斯这一时期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几首表达理想的诗歌中,自然却都是积极、正面的形象。例如,在《诞生》(“Birth” )[2](P323)中,诗人呼唤着“神奇的原野”,那里将重新赋予星星、太阳、月亮和诗中的言说者“我”以新的生命。这四者获得新生命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新的秩序:“我”与日月星辰的平等关系。在这一意义上,这首诗全然不同于《逃难者》中通过大雨对我的头顶的袭击所表现出来的自然与人的对抗性,而表现出了自然之于人的友善平等。这一观念也在休斯的《天堂》(“Heaven”)[2](P232)等诗歌中得到呼应。《天堂》呈现了一幅世界和谐、万类友爱的理想图景:飞鸟和走禽歌唱,与每一块岩石互致问候。休斯通过将语境设置于“天堂”或充满爱的“国度”,使诗的情感和世界超脱了现实的羁绊,呈现出最为本真、自由的自然。虽然这类诗歌不多,但足以充当一面镜子,以其充满爱的理想环境之中和平等友善的自然,反衬出现实环境中的充满敌意和负能量的自然对自然本质的悖逆和扭曲。因而,休斯大量诗歌所呈现的负能量自然,实质上是在现实中被扭曲和异化的自然,是反自然;其批判锋芒不是指向自然,而是指向反自然,指向导致自然异化的社会现实。
在休斯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中,美国非裔民族无疑是自然异化的直接受害者。如前所述,休斯诗歌中自然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正是自然异化的后果,生活在美国南方乡村或北方城市以及游荡于两者之间的美国非裔民众成为被异化了的自然操弄的对象。在《生活多美好》一诗中,以布鲁斯形式自我表达的言说者无疑是纽约哈莱姆区的黑人代表;而《逃难者》所表现的也正是美国非裔漂泊生活的写照。在这些诗歌中,现实中的自然作为一种异化的存在已经成为非裔民众的巨大生存压力和精神桎梏。
然而,现实中的自然强加于非裔民族的负能量,其源头并非来自自然本身,而是来自使自然异化的力量。在休斯的诗歌中,自然的异化在本质上表现为自然的客体化和工具化,即自然在被操纵、改造的过程中走向非自然化;其目的在于将自然客体化,使之丧失自然本性而沦为工具,而客体化和工具化的自然只能臣服于强权,成为强权的奴隶和帮凶。休斯的诗歌通过展现自然的客体化和工具化,抽丝剥茧,揭示出自然异化背后的强权。
休斯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自然题材诗歌勾画了一个二战期间及其结束之初美国非裔民族从南方乡村到北方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展现了自然作为一种体制化的社会存在。就美国社会而言,二战时期非裔向城市移民有着诸多现实原因;但就休斯而言,非裔民众向城市流动是一种逃离,是一种源于他们对南方自然心怀恐惧的精神逃离。在休斯的诗歌中,美国南方的自然对于非裔而言是苦难与不幸,是南方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操纵和扭曲的异化自然。在《蓝色的牛轭湖》(“Blue Bayou”)[2](P292)中,黑人被迫长时间劳作,到头来经济上几无所获,生活中妻子被白人夺走,他自己也被处以私刑:
蓝色的牛轭湖
火一样通红。
把那个黑人用绳子
捆起来
吊起来吊到半空。[2](P292)
诗中没有明言的树被用作处以私刑的工具,而蓝色的牛轭湖成为一片灼烧的血红。自然被种族主义操纵,成为种族压迫的工具,自然本真的清纯也成为民族的苦难记忆。在《西德克萨斯》(“West Texas”)[2](P252)中,一个在棉花地里孤独地劳作的黑人头顶的太阳就像魔鬼,这是他身体体验和心理体验的双重投射:炎热的太阳灼烤着劳而无获的黑人,体现出自然对黑人的敌对性;同时,也暗示黑人身心受到密切监视——他的妻子曾对他悄悄说出逃离的想法就被处死。经济上的剥削与种族主义压迫将自然变成从身体到精神上对黑人进行摧残、桎梏的存在,这已经成为美国非裔民族的心理定势思维模式,是民族创伤的必然结果。正如在《苦涩的河流》(“The Bitter River”)[2](P242~244)一诗中,贯穿美国南北的密西西比河的河水将民族苦难历史地联系在一起:
有一条苦涩的河流
从南方流过
那河水的味道在口中
久久无法摆脱
那是一条苦涩的河流
乌黑污秽浑浊[2](P242~243)
南方的树木花草、山川日月都在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同作用下被工具化、私有化了,成为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种族奴役和压迫的工具。
来自异化自然的压力正是南方非裔民众向城市流动的心理动因。对于他们而言,城市化是逃离非自然的自然,也是逃离操纵南方自然的力量与体制。然而,现实中的城市并不是美国非裔民众能够拥抱自然的空间。休斯基于现实主义的立场对城市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观察,认为城市中的自然不过是被囚禁的私家花园,而美国非裔不过是陌路人、漂泊者。在《城市陌路人》(“Stranger in Town”)中,黑人言说者“转遍了动物园和公园,找一块石头坐下”,憧憬着自己的拥有和归属,到头来发现一无所有,自己不过是陌路人。在这首诗中,黑人言说者十分清楚“没有谁眷顾他”,“在这个陌生的古城/我只是个陌路人”,[2](P359)因而他在属于白人的公园和动物园里找不到让自己静心休憩之所。诗人将批评的锋芒直指美国社会的种族隔离制度。美国白人主流社会通过将自然私有化,剥夺了黑人享用自然的权利,私有化的自然深深地打上了种族主义的烙印。然而,在休斯的诗中,城市中的自然不仅仅拒斥非裔民众,而且成为压制他们的力量。例如,在《哈莱姆的灯火管制》(“Dimout in Harlem”)一诗中:
顺着街道,年轻的哈莱姆
在黄昏中行走
在街灯没亮的黄昏时分
在街上行走
阴影遮蔽了他的黑影
阴影遮蔽了阴影
像黄昏一样柔和
黑影遮蔽了阴影
[……]
沉默
没有说话
年轻的哈莱姆
在黑暗的街上[2](P270)
黄昏时分的哈莱姆的城市阴影投射在黑皮肤上,与夜色一起将黑人吞噬。这与休斯早期充满浪漫色彩的诗歌形成鲜明对比。他早期的诗歌深情想象遥远的非洲,黑夜是白人主宰世界的终结、黑人世界的开启,黑夜充满了非洲鼓乐的活力与激情。例如,他在早期的《诗(1)》(“Poem 1”)中写道:“那丛林里咚咚的鼓声敲进我的血液,/那丛林里野性的炙热的月亮照耀我的灵魂。”[2](P32)在《我的人民》(“My People”)等诗中,他也反复表达出非裔民族与夜色在本质上的高度契合:“夜色真美,/我的人民的脸庞一样美。”[2](P36)然而,在《哈莱姆的灯火管制》中,哈莱姆城区的夜色不仅没有给黑皮肤的美国非裔带来生气和活力,反而与城市阴影一起成为压抑他们的力量,使黑人陷入沉默和无声之中。哈莱姆城区正是种族主义空间生产的产物。这片原本由白人居住的城区在20世纪之初随着黑人涌入而逐渐被白人放弃。白人撤离这里只是不愿意与黑人混居,但他们仍然保留着大部分房产的所有权,通过不断提高房租对黑人移民进行经济上的盘剥。生活在这片年轻的黑人区的南方黑人移民们,同时遭受着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导致了黑人与自然的疏离。他们已经无法分清城市的阴影和黑夜的影子,黑夜的影子已成为黑人心中的阴影,黄昏的来临无法带给他们如黑夜中的非洲丛林所焕发的活力,而城市的街道却没有为他们点亮街灯,他们只能在城区的黑暗和自我的沉默中行走:“沉默/没有说话/年轻的哈莱姆/在黑暗的街上。”
由此可见,休斯的诗歌通过南方非裔民众向北方城市流动的空间呈现,不仅展现了自然被私有化和工具化的过程,揭示了从南方到北方自然遭到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操纵的实质,而且展现了自然异化的后果:异化的自然成为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种族压迫的工具和同谋,美国非裔无法在自然中找到归宿和自我,成为在白人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操纵的世界的流浪灵魂。休斯在20世纪40年代总结自己作为社会诗人的曲折历程时曾说:“我相信,假如我的作品写的都是玫瑰和月光之类的题材,就不会有那些不幸的经历了。”可是,他不能全都去写玫瑰和月色,因为最美的玫瑰开在有钱的白人的花园里,月光下他的兄弟们看得到成群的三K党和私刑树上吊着的黑色尸体。[3](P198~199)这段话表明休斯清楚地看到了自然被工具化、私有化的实质及其对于美国非裔民族的意义。因而,休斯诗歌中的“反自然”实质上是反“反自然”,是对美国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与意识形态的批判。
三、自然书写作为政治表达
休斯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表现自然的工具化和私有化及其后果,反映了他从20世纪30年代对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的公开、激进批判转向了修辞性的政治表达。这是他20世纪30年代在从阶级视角对资本主义、种族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社会视野和艺术视野的进一步扩展,为他自己的社会批判建构了一个新的平台,也展现了休斯的文学创造力。
休斯在这一时期的自然书写可以说是一场列斐伏尔所称的“空间生产”的文学实践。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因而也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础。空间的社会生产是由霸权阶级操控的,是他们用以复制其主导性的工具。他说:“(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生产,这种空间同时也充当了思想和行动的工具。除了作为生产方式之外,它还是控制的方式,因而也是主宰方式、权力方式。”[4](P26)休斯的诗歌所展现的自然私有化与工具化实质上是自然的空间重置。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通过将自然进行改造与操纵,实现空间上的囚禁,使之私有化,并将美国非裔排斥在外,使之工具化,成为向非裔传导并实施其思想行动的工具;其直接结果就是美国非裔在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和他者化。由此,诗人不仅表现了自然的异化,而且反映了人的异化(如非裔民众的他者化,种族主义者和资本家的非人性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自然书写虽然并不是直接进行社会批判,却揭示了种族主义、资本主义更深远、更广泛的破坏力。也正因为这一视角的含蓄性,才使得它在二战即将结束、冷战之初日趋严酷的政治语境中的意义更加丰富。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日趋保守、排斥苏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逐渐抬头,使得很多左翼作家在意识形态上转向温和,避免政治麻烦,休斯也是如此;而且1939年苏联入侵捷克和波兰令休斯对苏联充满失望。但是,他采用自然视角对美国社会进行尖锐批评时,只不过是批评策略更加含蓄,但批评锋芒不仅未减,反而更为深刻,延续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和社会主义革命理想。
在休斯的诗歌中,南方乡村的自然和北方城市的自然都已经被私有化和工具化,非裔民众从南方的自然中逃向城市,却又遭受北方城市的自然的敌对与拒斥,他们身处无所归依的境地,要求得生存,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从狭小的物质空间遁入想象世界,一是通过反叛来打破这种自然的桎梏。前者对于美国非裔民族并不陌生,南方奴隶制时期黑人奴隶在物质世界备受限制,逃无可逃,只能进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依靠想象拓展生存空间,布鲁斯、灵歌等都反映了这种生存策略,生存问题也是非裔文学长期以来的重要主题。但这一策略虽为美国非裔赢得了生存,却并没有改变他们生存的方式,故而这也不是休斯所肯定的。后者在现实中有苏联作为榜样,而且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号召在国外为自由民主而战的政治姿态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因而,休斯在这一语境下将美国非裔进退维谷的生存窘境呈现出来,有着强烈的暗示性和引导性。例如,在《自由人》(“Free Man”)一诗中,诗人写到:
你能抓住风,
你能擒住海,
可是,亲爱的妈妈,你
不能抓住我。[2](P247)
诗中的言说者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然已经被强权控制,但人的精神不能再沦陷。这首诗无疑表现了美国非裔民族面对逆境的英雄主义精神或以精神胜利法抵制强权的生存策略。但就整体而言,休斯这一时期的诗歌,在高度肯定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并没有突出精神胜利法的生存策略,而是极力暗示要通过精神抗争与外部行动相结合,将人和自然解放出来,实现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双重解放。这种诉诸行动的意图通过《城市陌路人》一诗中黑人言说者的心声得以表达:“我在这里呆上一会儿,/就会知道该怎么绕开。”[2](P359)在休斯《诞生》一诗中,赋予星星、太阳、月亮和言说者“我”以新生命和平等秩序的“神奇的原野”,其产生的前提是“就像一道/闪电/划破黑夜/有些印记/要留/有些话/要说”。[2](P323)在这里,闪电所具有的行动意味已经非常明显。可以说,休斯在诗歌中通过自然书写表现了一种激进的思想,即以人与自然和谐和物质与精神双重解放为目标、以革命为手段的社会理想,这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延续。
由此可见,休斯在20世纪40年代的自然书写反映出他艺术视角的拓展,也反映出他在冷战开始之初政治环境趋于严峻时坚守社会理想、表达激进思想的高明的艺术策略,体现了诗人在这一时期诗歌艺术上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的休斯的诗歌均出自休斯:TheCompletePoetryofLangstonHughes。
[1] Arnold Rampersad. The Life of Langston Hughes[M]. Vol. 2. New York: Oxford UP, 1988.
[2] Langston Hughes. The Complete Poetry of Langsotn Hughes[M]. Eds. Arnold Rampersad and David Roessel. New York: Vintage, 1994.
[3] “Writers, Words and the World.”[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angston Hughes. Vol. 9. Essays on Art, Race, Politics, and World Affairs[C]. Ed. Chritopher C. De Santis. Columbia and London: U of Missouri P., 2002.
[4]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Boston: Blackwell,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