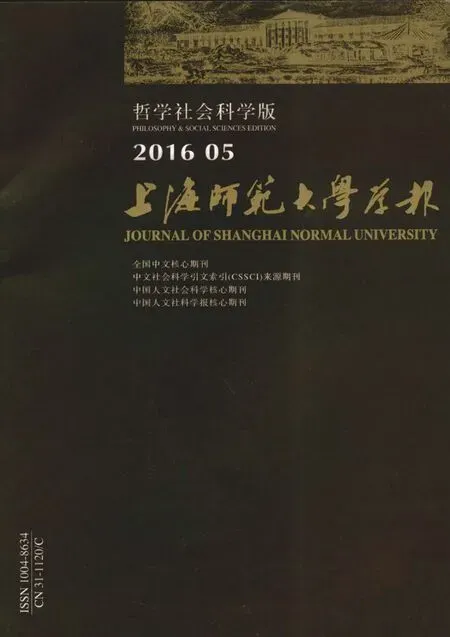钟嗣成《录鬼簿》不拘于时的戏曲审美观
2016-04-12梁晓萍
梁晓萍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钟嗣成《录鬼簿》记载了戏曲最为繁盛时期的元代的戏曲作家及其作品,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和戏曲史意义,还是戏曲理论的奠基之作和后世戏曲美学研究的源头活水。尽管它还没有成系统的美学思想,但其开创之功可谓“德业辉光”。其不拘于时的戏曲审美观不仅成为中国古代非中和美学思想中非常有力的一股力量,作为艺术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创新之力,这种审美观在今天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录鬼簿》为赵良弼作传时曰:“(良弼)总角时,与余同里闬,同发蒙,同师邓善之、曹克明、刘声之三先生,又于省府同笔砚。”①朱凯在《录鬼簿·后序》中亦指出:“(钟嗣成)善之邓祭酒、克明曹尚书之高弟。”②可见,钟嗣成青少年时曾师从邓善之、曹克明、刘声之三位大儒,是他们的高徒。又据史料知,钟嗣成与同时热爱戏曲的儒生施君美、赵君卿、陈彦实、朱经等来往甚密。这些儒生以儒为戏,游戏人生,或以名儒身份交伶伦,或优游于市井,或醉心于家务,或沉迷于卜术。钟嗣成本人亦自诩风流,传授风月。他们一方面主动接近不为正统接纳的戏曲,公开向传统的价值观挑战,展示出其迥异于传统文人的风采;另一方面却又郁郁不乐:吴本世“以贫病不得志而卒”;③陈彦实“以忧卒”;④钟嗣成本人则一生坎坷,“以明经累试于有司,数与心违”,⑤“累试于有司,命不克遇,从吏则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故其胸中耿耿”。⑥这些本自不乐却强为乐的反拨行为,无疑反证了对于儒家“兼济天下”的向往与不得已而退却的无奈。
硕儒长辈的耳濡目染、同辈儒生的相互影响,使浸染于儒学的钟嗣成自小便心怀天下。儒家入世的抱负敦促其积极奔波,然而屡试不中的现实却将其理想之梦击得粉碎,忧患意识因之滋生。退出政治权力中心而移居边缘的钟嗣成依然忧虑着社会、国家,在钟嗣成的《录鬼簿》中时时可以嗅出这样的忧患:“想天公忒□情,使英雄遗恨难平。”(吴本世吊曲)“恨苍穹不与斯人寿,未成名一土丘,叹平生壮志难酬。”(廖毅吊曲)“半生才便作三闾,些叹番成《薤露歌》,等闲间苍鬓成皤。功名事,岁月过,又待如何?”(睢景臣吊曲) “黄土应埋白骨冤,羊肠曲折云千变,料人生亦惘然。”(周文质吊曲)⑦在钟嗣成看来,《录鬼簿》所录之人皆为不死之鬼,他们尽管门第卑微,职位不高,然而他们才高识博,品高格远,可与圣贤君臣、忠孝士子相比。惺惺相惜的叹惋所体现的正是钟嗣成强烈的忧患意识;也正是这种忧虑,使其能够在不断反思中公然向儒家传统道德挑战,形成一种叛逆精神和不拘于时的审美观。
《录鬼簿》跃出世俗框架的审美观,突出体现在书之命名及其对剧作家崇高地位的肯定上。鬼指已死之人,是“人之所归”,本为人类万物有灵观念的一种显现,是人的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但因其神秘而不可知,于是人们畏惧之,继而将之妖魔化;又衍生为一种骂语,含有讽刺之意。录鬼一事,最初也无贬意,如三国时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陈述建安诸子相继亡故的事情时,便有“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史,已为鬼录”⑧的记载。姓名为鬼所录,便是人已去世之意,无贬意。然而渐渐地,此语有了讽刺之意,如“杨(炯)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⑨此“点鬼簿”在于嘲讽杨炯好以古人姓名为对,喜欢用事用典,有“掉书袋”之嫌。至元代,“点鬼”、“鬼录”之词贬义越发浓烈,后于钟嗣成的陶宗仪曰:“文章用事,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录’,又谓之‘堆垛死尸’。”由此推知,在钟嗣成生活的时代,“点鬼录”也多含贬义。而钟嗣成反其道而行之,越出常论,唱出反调,提出了充满反叛思想的录“鬼”观:“人之生斯世也,但以死者为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酒罂饭囊,或醉或梦,块然泥土者,则其人与已死之鬼何异?……予尝见未死之鬼,吊已死之鬼,未之思也,特一间耳。独不知天地开辟,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何则?……是则虽鬼而不鬼者也。”⑩
芸芸众生,只知死者为鬼,殊不知活人之中亦有混世之鬼。倘若酒罂饭囊,醉生梦死,块然泥土,活着也与鬼无异;于学问之道,甘于自弃,死后漠然无闻者,同样可谓之鬼。相反,若精于学问,勤于思考,青史留名,则虽死犹人,这是一种迥异于常规的人鬼观,它的意义在于从比较中全面凸显剧作家这群不死之鬼的才华、胆识、人格及其对于社会的贡献。首先,通过与浪荡混世“块然”之鬼和口谈道学的“漠然”之鬼的比较,衬托了“高才博识”的剧作家这些“不死”之鬼。这些人均属于没有功名利禄的下层文士,其中剧作家明显高出一筹。其次,通过与“圣贤之君臣,忠孝之士子”这些青史留名之人比较,暗示那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岁月弥久,湮没无闻”的剧作家才是真正应当“著在方册”之人,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再次,《录鬼簿》还通过与“读书万卷,作三场文,占夺巍科,首登甲第”的兼济天下者和“甘心岩壑,乐道守志”的独善其身者的比较,反衬“心机灵变,世法通疏,移宫换羽,搜奇索怪,以文章为戏玩”的剧作家是“诚绝无而仅有者”。这样,通过在不同层面上与不同人群的比较,剧作家的形象变得伟岸、脱俗而与众不同,成了“不死之鬼”。
钟嗣成“录鬼”之名是对中国文论表达的有效传承。中国古代早已有以“鬼”代指超出凡俗、拥有别具一格之灵气与才性的文人的现象。庄子曾以幽险怪妙的鬼神之说来指代和比附文学艺术上有独特造诣者——“梓庆削木为钅豦,见者惊犹鬼神”(《庄子·达生篇》)。其意思是梓庆能削刻木头做钅豦这种猛兽形的乐器,钅豦做成以后,看见的人无不惊叹,以为是鬼神的工夫。这里,《庄子》以无法想象的“鬼神”之工来显示梓庆削木时所达到的神妙境界,此后人们便常用“惊天地,泣鬼神”之语来赞美文学艺术界的新异奇绝和鬼斧神工。譬如唐代李贺,其诗想象奇特,意象幽妙,造语峭拔,境界瑰丽,北宋文学家宋祁在《朝野遗事》中称其有“鬼才”,南宋文学理论家严羽《沧浪诗话》誉之为“鬼仙”。如此说来,则钟嗣成以“鬼”喻这些戏剧作家的确有所承继,其意乃在于表示对这些敢于标新立异、绝无仅有的戏曲作家的崇敬与赞扬。
钟嗣成“叙其姓名,述其所作”的做法和他“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的期待迥异于时人,不合于流俗,必然会遭到“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的谩骂与攻击。但他全然不顾,欣然泰然,嬉戏吟玩,大胆面对高尚之士、性理之学可能的指斥,与“吾党且噉蛤蜊,别与知味者道”,“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表现出了骨鲠倔强的反传统审美立场。钟嗣成的抗争与呼吁是自觉的,他从一个明经者、省级掾吏转变为一个戏曲学人,蝉蜕了其自身的儒学之气,消解了其携带的功利之心,主观上为戏曲作家登上文学舞台摇旗呐喊,客观上也为戏曲美学的进一步成熟和戏曲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如果说《录鬼簿》一书的命名与对戏曲作家的充分肯定是钟嗣成不拘于时戏曲审美观在创作主体论方面的脱俗思考,那么,对戏曲这一艺术门类诸多功能的精确认识以及对戏曲价值的充分肯定,则是其不拘于时戏曲审美观的本体论角度的思考。
在钟嗣成之前,宋元礼法之士主张以理为道、以道统文、文以载道,故而常常以作文与道的关系为文之标准,指出“作文害道”之弊病,甚而提出否定文学审美功能的观点,并以传统的诗文观看待戏曲这一新生艺术,轻视戏曲这一艺术的存在价值。如吴澄认为“儒者托辞以明理,而非有意于文也”,“理到气昌,意精辞达”,方为好的文章;又袁桷曰:“世之为学,非止辞章而已矣,不明乎理,曷能以穷夫道德性命之蕴?”程颐视“有高才能文章”为人生之第三大不幸,其“作文害道”之说明确显示了他对于害道之文章的鄙视;他认为悦人是低贱的行为,悦人耳目之文属玩物丧志之文,这便以“害道”之标准否定了悦人之文的审美价值。元代理学大师许衡也持此观点。直到明初修元史,由元入明的儒者宋濂依然将戏曲拒之门外。
钟嗣成生活的时代,戏曲文学的处境依然艰辛。一方面,戏曲以不可遏制的勃勃生机活跃于当时的民间舞台,渐渐扎根于草野;而另一方面,戏曲却总被视为惑乱与鼓噪之物,被拒斥于已筑的文学殿堂之外。屡试而不举的钟嗣成满怀一腔不平之气,勇敢地向传统势力挑战。他以此为使命,将一种崭新的戏曲审美观念通过《录鬼簿》精心展演出来。正因为有如此坚定的立场,面对《录鬼簿》出世后必遭歧视和不满的命运,钟嗣成果敢亮剑,创造出别一种“蛤蜊”味,与坚守“性理之学”的卫道者们展开较量。
为此,钟嗣成精心发掘戏曲的各种功能。首先他通过强调戏曲作家的社会经历、心路历程与作品之间的紧密关联而探讨戏曲的社会作用。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J·刘若愚曾为文学活动描绘出一幅形似“跑道”的体系图。在跑道的四个角上分别为“宇宙”、“作家”、“作品”、“读者”,即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所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录鬼簿》在戏曲审美时即常常以作家这一创作主体为站位来审视作品,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强调元曲作家的社会遭际与元曲创作及作品之间藕断丝连的特性。如:“(宫天挺)为权豪所中,事获辩明,亦不见用。卒于常州。先君与之莫逆交,故余常得侍坐,见其吟咏文章笔力,人莫能敌……”“(吊词)先生志在乾坤外,敢嫌天地窄。更词章压倒元白。”“(曾瑞)志不屈物,故不愿仕。”“(吊词)江湖儒士慕高名,市井儿童诵瑞卿。衣冠济楚人钦敬,更心无宠辱惊。乐幽闲不解趋承。”“(范居中)以才高不见遇,卒于家。”“(黄天泽)郁郁不得志。”“(吴本世)以贫病不得志而卒。”随处可见的悲愤之语,处处可感的情感汁液,显然渗透着钟嗣成的戏曲审美观。以上诸君,若以其高致之才和文章笔力而论,为社稷之用可谓不错的人生路径。然而,他们多因不被重用或不愿屈物而游离于庙堂之外的江湖中。“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风流蕴藉,自天性中来”,正是他们的生活累积激荡出他们内在的审美气质,从而又滋养出富有魅力的戏曲作品,形成了为江湖儒士所羡慕的独特的作品风格。这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戏曲审美观:元曲不是天外来物,没有游离于社会之外,作家的经验与文本的内容、风格等息息相关;戏曲不仅关涉娱乐,它指涉的是世道人性,谈论的是乾坤天地,抒写的是人生体悟。
其次,钟嗣成还巧妙论及戏曲兼具教化的娱乐功能,从而间接提升了戏曲的存在地位。元人论曲,或忽略其教化功能而只谈娱乐;或因提升戏曲地位的心切而直接论及其教化功能。钟嗣成《录鬼簿》却巧妙地论及戏曲娱乐与教化功能的关系,体现出积极的使命感和自觉的本体论意识。《录鬼簿》称作曲为“余事”,将其与写诗文的“正事”区别开来,所谓“乐章歌曲,特余事耳”。其又曰:“(施惠)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曲为事。”钟嗣成还提出了“戏玩”说:“于学问之余,事务之暇,心机灵变,世法通疏,移宫换羽,搜奇索怪,而以文章为戏玩者,诚绝无而仅有者也。此哀诔之所以不得不作也。观者幸无诮焉。”世间不乏“读书万卷,作三场文”而“首登甲第者”,也不乏“甘心岩壑,乐道守志者”,偏偏却缺少“于学问之余,事务之暇……以文章为戏玩”的人。钟嗣成以文章为戏玩的观点,并非首创。自宋而元,文道统一渐变为文道两本。文的进一步独立,使艺术创作进一步摆脱了儒家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将艺术看成是消遣之事,这就强调了作家动笔前心志的自由——不为物役,不计丑妍,忘己无心。如宋人董卣《书李伯时县留山图》曰:“(伯时)常以笔墨为游戏,不立寸度,放情荡意,遇物则画,初不计其妍蚩得失。至其成功,则无毫发遗恨。”可见,“戏玩说”并非无目的的活动,它强调的是一种作家轻松的创作状态,核心在于拥有一颗淡泊名利之心,表现于文章中则为不刻意让文字包裹“道理”。
鉴于此,钟嗣成既看不惯“曰忠曰孝”的作品,也不屑于委婉言说政教怀抱的作品,而以极大的热情肯定“以文章为戏玩”,从事“移宫换羽,索奇搜怪”的戏曲创作,认为唯有这类“余事”的难度是最高的,这便从创作的角度肯定了戏曲的娱乐功效。不同于否定“悦人”之文的道学家,钟嗣成《录鬼簿》还从欣赏的角度肯定了戏曲之于观众的娱乐功能。如他称鲍天佑的作品“其编撰多使人感动咏叹”,这既是在强调戏曲演出的效果,也是在强调其悦人的作用。他不仅不把这种悦人之戏曲视作一种低贱的行当,而且还为从事这种行当的人树碑立传,可见是一种有针对性的自觉的审美观。
然而,我们也嗅到了其话语中的另一层含义:既为“余事”,既是“戏玩”之作,何必专门著录,反复言说?可见,醉翁之意不在酒。钟嗣成为“观者幸无诮焉”而惋惜,为戏曲无益于民心之说而证明,这便委婉地强调了此等“余事”的意识形态功能,托出了戏曲的教化功能。钟嗣成的戏曲观显然相对成熟。他一方面重视戏曲的娱乐性,强调戏曲的悦人性,关注戏曲对于观众直观的吸引力以及对于观众身心的舒缓力,极力赞扬这种其他艺术样式无法替代的愉悦功能;另一方面又强调戏曲在内容上体现出来的道德感染力。与音乐、绘画、雕塑、诗文等侧重于作家个体内心情感抒发的艺术相比,戏曲的善恶美丑观更为分明,因此更具有明确的教化功能。显然两者是相兼相得的关系:如果取消戏曲的娱乐性,则不能够使观众获得愉悦的享受,当然也就会使观众远离戏曲,其教化功能当然便也无从谈起;反过来,如果取消戏曲的教育引导功能,一味地迁就观众的感观愉悦,迎合观众的审美趣味,同样会导致戏曲滑向低俗甚至庸俗的泥淖,如他评郑光祖曰“惜乎所作,贪于俳谐,未免多于斧凿”,便是惋惜郑光祖为迎合观众,过多地插科打浑,逗人发笑,刻意造作,令人厌恶。还是吕薇芬说的好:“不论是作家和演员都不能忘记自己是缪斯的使者。”钟嗣成《录鬼簿》显然在这方面有着同样深刻的认识。
三
钟嗣成《录鬼簿》不拘于时的审美观还体现在书中关于戏曲创作与欣赏的诸多美学思考上,在此择取要者论及一二。
1.主张语辞骈丽、奇巧
曲辞乃戏曲之重要元素。关于曲辞,不少人欣赏元曲的慷慨与质朴,然而钟嗣成《录鬼簿》却主张“搜奇索古”,“翻腾古今”,反对蹈袭而缺少新意的辞句,欣赏和追求华丽、新奇与工巧的辞章。在郑光祖的悼词中,钟嗣成赞曰:“乾坤膏馥润肌肤,锦绣文章满意肺腑,笔端写出惊人句。翻腾今是古,占词场老将伏输。”他称其善于在新奇方面下功夫,故而能写出惊人之句。他还称鲍天佑肯于推敲,哪怕断肠亦在所不惜,曰:“平生词翰在宫商,两字推敲付锦囊,耸吟肩有似风魔状。苦劳心呕断肠,视荣华总是乾忙。”相反,若辞句不够新奇华丽,则会令钟嗣成叹惋,如他因金仕杰之作不够骈丽而叹惜其所述不够骈丽。关涉此主张的评语还如:“一下笔即新奇”(范康);“《潇湘八景》、《欢喜冤家》等曲,极为工巧”(沈和);“其乐章间出一二,俱有骄俪之句”(陈以仁);“一篇篇字字新”(施惠);“闲中袖手刻新词”(赵良弼);“时出一二作,皆不凡俗”(廖毅);“《哨遍》制作新奇”(睢景臣);“文笔新奇”(周文质);“有乐府,华丽自然,不在小山之下”(曹明善);“有《醉边余兴》,词语极工巧”(钱霖);“乐章华丽,不亚于小山”(屈子敬);“小曲、乐府,极为工巧”(高克礼)。
在钟嗣成的赞语中,新奇、华丽、工巧这些词汇的使用频率很高,其审美核心在于强调戏曲在词句方面要做到求新求异,超脱前人。从历时的角度看,钟嗣成这种迥异于元初美学追求的戏曲语言观不仅反映了戏曲品评观念的差异性与复杂性,更体现了钟嗣成戏曲审美的不落俗套。需要指出的是,钟嗣成强调曲辞新奇工巧,但并非主张一味求新、求奇、求巧,过分的斧凿在他眼中是没有地位的。如他在为郑光祖写的小传中指出,“惜乎所作,贪于俳谐,未免多于斧凿,此又虽论焉”,惋惜与不满之意可以见出。
2.强调表达委婉含蓄
钟嗣成多次提到曲作者善隐语或嗜隐语,视之为可以著于时、彪于史的特长。《文心雕龙·谐隐》释义曰:“隠者,隐也;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隐语”即隐去本事而假以他辞来暗示,也即不直说本意而借别的词语说明含义,类似今之谜语。清赵翼《陔余丛考·谜》曰:“谜即古人之隐语…… 刘歆《七略》有《隐书》十八篇,则并有辑为书者,然皆不传,惟‘卯金刀’、‘千里草’之类,出于风谣者,略存一二。至东汉末乃盛行,谓之‘离合体’。”此种表达方式约滥觞于春秋之前,源自人类早期的原始思维(动作思维、表象思维和神话思维),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战国以后出现多元转化。“隐语”一词最早出现于班固《汉书·东方朔传》:“臣(郭舍人)愿复问朔隐语,不知,亦当榜。”善用隐语是思维敏捷、表达含蓄的一种表现,而欣赏这种才华则折射出欣赏委婉表达的审美追求。如《录鬼簿》称曾瑞“善丹青,能隐语”;赵良弼“经史问难,诗文酬唱,及乐章、小曲,隐语传奇,无不究竟”;陈无妄“于乐府隐语,无不用心”;吴本世“天资明敏,好为词章,隐语,乐府”;李显卿“酷嗜隐语”。
强调表达委婉亦可看作钟嗣成为戏曲进入以诗歌为正统的文学殿堂而做的努力。中国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流,无论“诗言志”还是“诗缘情”的主张,都是对抒情文学而非史传文学的理性思考。自先秦、汉魏之诗,至唐诗、宋词,这些诗歌所处时代与所抒之情尽管各有差异,但在抒情方法上却多因其展转腾挪而令人掩卷忘怀。钟嗣成推崇元曲的含蓄表达,体现了其浓郁的文人情怀,也体现了他为戏曲进入主流文学而做的主观努力。与百般打击戏曲或视之为末道小技的正统做法相比,其这一努力恰又成为钟嗣成不拘于时戏曲审美观的一个重要表现。
3.崇尚激越风格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以诗文理论为主,诗文品评常常追求中和之美,崇尚哀乐有度、不伤不淫,讲究发喜怒之末、发而中节。如前人概括诗文之风,尚用温柔敦厚、平易正人、纤徐雍容、涵淳茹和等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抑李扬杜的文学现象,也可以看出古代文人的审美喜好。钟嗣成《录鬼簿》“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部分,却将关汉卿、高文秀等高蹈激厉的剧作家置于最醒目的位置。关汉卿与高文秀两位作家向以写激越之词而闻名,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呼天抢地,指天斥地,将抨击的矛头直指最高的统治者,直呼为官者,斥其不从人愿、无心正法而导致百姓有口难言的不齿行径。在关汉卿作品中,位居显赫、势力强大的权豪势要常如落汤之鸡、泄气之皮球,而身处下层的弱者却常常凯歌高奏,斗志昂扬。其作品汪洋恣肆,慷慨淋漓,极具震撼力。高文秀写了很多水浒戏,即绿林杂剧,其中“黑旋风”戏即有8种,将勇敢、义气、粗中有细、不畏强暴的李逵刻画得栩栩如生,气调豪迈,语气奔放,形象鲜明,风格与关汉卿非常相近。钟嗣成对于关汉卿、高文秀等显然是在熟谙其创作基础上才有青睐的。这种对于激越之风格的肯定,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的审美标准,另一方面也迥异于明代评论家“褒婉丽而贬激烈”的审美趣味,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直到明代,人们还常常将关汉卿拒于文学殿堂之外。如明初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只将关汉卿评为“可上可下之才”,没有给这位开拓性的多产作家以应有的地位;明中叶何良俊《曲论》认为关曲“激厉而少蕴藉”,以传统文人的审美标准打量这位文学大师的作品,否定其溢出框外的才情;在关于《西厢记》“王作关续”的诸多讨论中,人们也更多地流露出扬王而抑关的倾向。可见,充分估量一位作家的历史贡献是多么不容易。直至王国维“一空倚傍”、“当为元人第一”的评价后,关汉卿才真正被人们认识,回到他应有的宝座。由此亦可见出钟嗣成的远见卓识及其慧眼识才的审美能力。
骈丽新奇是钟嗣成《录鬼簿》在语言上的审美追求,含蓄婉转是其在表达方法上的审美崇尚,而这两点均迥异于元初的审美时俗,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情趣。激越风格是《录鬼簿》在作品风格上的审美取向,它使该作品甚至跳出传统审美的框框,以秦腔式的穿透力直接地气。含蓄婉转与激越风格看似有所相悖,实则相辅相成,并不矛盾,正是钟嗣成《录鬼簿》不落俗套戏曲审美观的多重表现。
注释:
①钟嗣成:《录鬼簿》,见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24-125页。
②朱凯:《录鬼簿·后序》,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第138页。
③同上,第127页。
④同上,第125页。
⑤《录鬼簿续编》,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第281页。
⑥朱凯:《录鬼簿·后序》,第138页。
⑦同上,第128、126页。
⑧曹丕:《与吴质书》,见萧统:《文选》(中)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91页。
⑨张鷟:《朝野佥载》卷六,载《四库全书》子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1035-281页。
⑩钟嗣成:《录鬼簿自序》,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