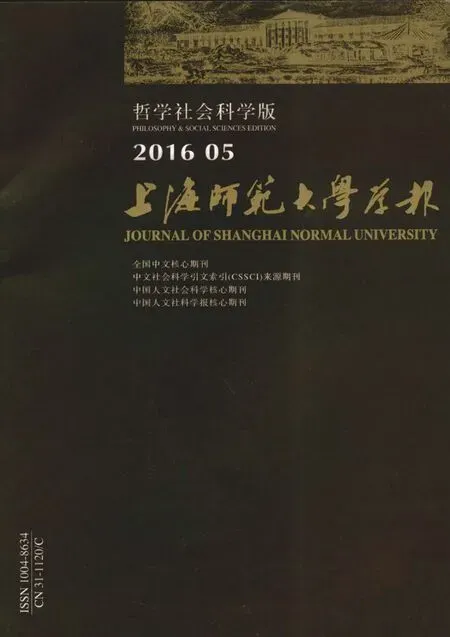从仁宗朝台谏弹劾看北宋的官场舆论
2016-04-12徐红
徐 红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舆论,史籍一般多记为“公议”。官场舆论可以理解为中国古代官僚阶层集体公认的一种意识或价值观,它常常通过某些官员之口表达出来,其方式一般是奏议、政论文章等公开性的文本。就北宋而言,由于台谏特殊的地位,使得台谏官员的奏议,尤其是弹劾奏议成为官场舆论形成的重要催化剂。欧阳修有言:“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1](卷六七《上范司谏书》,P973)宋仁宗朝又是北宋台谏制度逐渐完善并运行良好的时期,和平时期相对正常的政治状态有利于准确地分析台谏弹劾的作用及其对官场舆论的影响。因此,笔者选取仁宗朝台谏的弹劾奏议及弹劾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勾画出北宋官场舆论形成与影响的大致情况。
一、仁宗朝台谏弹劾分析
笔者依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朝诸臣奏议》、部分宋人文集等史籍中的记载,按照包含弹劾时间、弹劾者、弹劾对象、弹劾事由等内容的标准,搜集到记录北宋仁宗朝台谏的弹劾奏议及弹劾行为的资料140余条。虽然仁宗在位40年间发生的台谏弹劾事件肯定不止140多件,但这140余条资料涉及的时间范围从仁宗即位的天圣元年(1023)开始,直至仁宗驾崩的嘉祐八年(1063)为止,资料中记载的弹劾者、弹劾对象几乎包括了欧阳修、张方平、吕夷简、范仲淹、包拯、文彦博等仁宗朝所有的重要政治人物。因此这些资料基本能反映仁宗朝台谏弹劾的情况。
就弹劾者而言,台谏官员是北宋行弹劾之事的主体。宋朝制度规定,御史台的职责是“掌纠绳内外百官奸慝,肃清朝廷纪纲。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2](职官一七之一)其官员的日常行政事务主要就是监察百官及百司,纠弹其过失。谏院本是谏诤君主的机构,但在宋代也有“规谏讽谕”的职能,“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3](卷一六一《职官一》,P3778)可见台谏官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弹劾,其使用最多的文体就是弹文。现以庆历年间监察御史包拯弹劾江南西路转运使王逵的弹文为例,分析此类文体的结构和格式。
臣访闻江南西路转运使王逵,行事任性,不顾条制,苛政暴敛,全无畏惮,州县稍不顺从,即时捃拾,吏民无告,实可嗟悯。王逵先任荆湖南路转运使日,非理配率人户钱物上供,以图进用,山下之民苦于诛求,逃入蛮峒,结集凶党,致此大患,于今未息。缘江西重地,幅员千余里,财赋户口尤盛,亦与蛮接连境界,若久任匪人,窃恐为国生事。且杨纮但以体量官吏过当,尚降差遣,况王逵害民蠹化,众议不容。伏望圣慈特从降黜,则天下幸甚。[4](卷一六○,庆历七年四月,P3872)
从上述引文可知,台谏官员的弹文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开篇即直截了当指明弹劾对象的官职、姓名及所弹何事;第二部分具体阐述被弹劾者行事的不合理、不合法之处,指斥其行为对朝廷产生的恶劣影响,是全篇弹文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乞求君主不可任情放纵,应严肃处理以正官场之风,有的还提出具体的处理建议。若是多次弹劾同一位官员,从第二篇弹文开始,开篇还要点明已行弹劾、未蒙施行或施行不当之情况。如包拯劾侍读学士李淑的第二章有言:“臣近者两次论列,以李淑前过至深,不可处之亲近,乞与外任,或令侍养。今闻只罢翰林学士,依旧充侍读之职。”[5](卷六《弹李淑第二章》)可见,仁宗朝的台谏弹文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实用性的公牍文字,从文本字面看,弹劾者出于为天下计的责任感,因事奏劾,论理清晰,言辞或沉稳、或激烈,语气或平和、或咄咄逼人,彰显出当时台谏官员以国事为重、代行天下公议的凛凛正气。
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拥有弹劾权,如门下给事中、中书舍人、尚书省官员等,甚至仁宗时还出现了中外臣僚多上章弹劾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部分大臣是持批评态度的。如殿中侍御史吕诲就曾上书言:“故事,台谏官许风闻言事者,盖欲广其采纳,以辅朝廷之阙失。比来中外臣僚多上章告讦人罪,既非职分,实亦侵官。甚者诋斥平素之缺,暴扬暧昧之事,刻薄之态,浸以成风。”于是仁宗下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弹劾小过或不关政体者”。[4](卷一九一,嘉祐五年六月乙丑,P4627)因此,在宋人看来,只有台谏官的弹劾是名正言顺的,当然其弹劾产生的影响也最大。
从弹劾对象看,以中央官员为主,如宰相、参知政事、枢密院官员、侍讲侍读、六部官员、三司使等,几乎涵盖了中央所有重要部门的官员。如庆历三年(1043)七月,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弹劾参知政事王举正,导致举正罢参知政事,放外任;[4](卷一四二,庆历三年七月丙子,P3398~3399)至和元年(1054)曾有台谏官先后接连不断弹劾时任宰相梁适、刘沆等朝中重臣。[4](卷一七六至卷一七七)被弹劾的地方官,主要涉及汴京附近州县官员,以及北部、西北部靠近辽、西夏边境地区的知通和军事官员等,体现出朝廷和士大夫对这些地区的重视。如天圣八年(1030)正月,殿中侍御史张存劾比部员外郎知开封县刘汀、知祥符县李宗简;[4](卷一○九,天圣八年正月,P2536)庆历元年(1041)谏官张方平弹奏管勾泾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王沿。[4](卷一三四,庆历元年十月,P3191)
弹劾事由是台谏官弹文的重要内容,包括弹劾的具体事项、原因、影响等。就现有史料看,弹劾事由大体可分为道德和吏能两个方面,而且即使是吏能,弹劾者在论述过程中也往往与道德联系在一起。140余条史料,直接述及个人道德问题的就有90余条,还有10余条史料涉及道德、吏能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弹文文本显示,有70%以上的弹劾行为与被劾官员的道德有关系。
为官者的道德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之一,有德者可成为官员,无德者则失去资格。北宋仁宗时期,由于儒学的复兴和士大夫忧心天下意识的觉醒,社会和朝廷对官员的道德要求显得尤其突出。这些道德要求包括个人私德、为官公德两个层面,具体内容比较丰富。就台谏弹文论及弹劾事由来看,有嗜酒误事、奸邪阴险、刚愎自用、不孝寡廉、性格懦弱苟且、通奸等属于违犯私德的范畴,也有阿谀奉承、苛政暴敛、联姻非类、言行失大臣体、恃权骄纵恣横、贿赂贪污乱法、戚里恩宠过厚、阴附宗室宦官等与为官公德不符的情况。在具体进行弹劾时,有的是分别批评官员私德或者为官公德,有的则是将个人私德与为官公德杂糅在一起,一并予以谴责。
从皇祐二年(1050)到皇祐三年(1051),台谏官员包拯、陈旭、吴奎、王举正等接二连三弹劾宣徽南院使张尧佐。如皇祐三年八月,知谏院包拯与其同列劾张尧佐,论及张尧佐的个人原因时弹文是这样说的:“张尧佐怙恩宠之厚,侥求觊望,不知纪极。”[6](卷三四《上仁宗论张尧佐再除宣徽使》,P335)仁宗宠爱张贵妃,张尧佐借张贵妃伯父的身份升迁迅速,尽管张尧佐“持身谨畏,颇通吏治,晓法律”,[3](卷四六三《外戚上·张尧佐》,P13558)但仍然受到来自台谏官员的猛烈弹劾。可见,这种因缘戚里、恩宠过厚所导致的为官公德阙失,使张尧佐为士大夫所不齿,也是其频繁被台谏官弹劾的重要原因。
至和元年,殿中侍御史马遵等劾礼部侍郎、平章事梁适“奸邪贪黩,任情徇私,且弗戢子弟,不宜久居重位”;御史中丞孙抃亦言梁适位为宰相,“上不能持平权衡,下不能训督子弟”。[4](卷一七六,至和元年七月,P4264~4265)弹劾梁适的理由,既有个人道德方面的问题,也有为官之德的阙失。
赵宋建立以后,由于中央收归任官权、重视文治和士人等各种原因,从中央到地方均急需政务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员任职,因此在科举制度选拔读书人为官的基础上,还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保障吏能突出的官员能够有机会得到升迁。也就是说,为官者的吏能是宋代君主及士大夫们比较重视的拔擢官员的原则。但是,在台谏官的具体弹劾行为中,我们却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现象。若台谏官仅以吏能作为弹劾的理由,往往不能得到官僚阶层的广泛认可,所以他们常常将吏能的阙失与道德有亏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将吏能的阙失最终皆归结到道德方面,才能使自己的弹劾行为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以致引起朝中大臣及君主的重视,最终达到弹劾目的。庆历六年(1046)七月,马军副都指挥使、遂州观察使许怀德为安静军留后,御史中丞张方平论奏其不可,认为许怀德在边城素无功劳,“比诸侪辈,尤无材誉”;更重要的是许怀德居然“妄援体例,侥幸陈乞,堕紊军制,干挠朝章”。监察御史包拯更是言其“累任别无显效,而不顾邦宪,冒渎圣聪,人之寡廉,一至于是”,[4](卷一五九,庆历六年七月癸卯,P3841~3842)将其无功劳又陈乞加恩与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的无德联系在一起。像这样的弹劾方式是仁宗时台谏官常用的策略。除非是非常具体的事件,台谏官才会就事论事,不与官员道德联系在一起。如皇祐三年濮州境内群盗频发,殿中侍御史张择行认为知州聂世卿未能履行知州的责任,责罚太轻,请求加重处罚,[4](卷一七○,皇祐三年七月,P4097)这样的弹奏很少涉及道德层面。不过,如此简单就事论事的弹劾并不多。
二、官场舆论的形成
来自台谏官的弹劾是仁宗时保障朝政秩序正常的事后监督方式,其对象可以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弹劾的事由虽然多种多样,但大多数可以归结到官员道德层面的问题。台谏官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与中国古代对官员的道德要求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北宋士大夫们希望借此形成“尚德”的官场舆论,并以此制约官员的言行。
舆论的产生与社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舆论是历史环境的产物。北宋仁宗即位之时,虽然北部边疆在宋辽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基本趋于安宁,但小规模的冲突仍时有发生,西北党项族也是时叛时服,致使赵宋外患不断,始终处于强大的少数民族对手的威胁之下。在思想文化方面,自唐中期开始的儒释道三家融合,到仁宗时已近尾声,儒学的转折成为当时士大夫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他们对于儒学经典的理解有分歧,但儒学所提倡的伦理道德观却是共同推崇的修身原则。如此的社会背景,使得赵宋统治者急需社会舆论的支持,作为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北宋士大夫们很自然就成为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和推动者。而社会舆论又受到官场舆论的强烈影响,官场舆论的形成则与台谏直接相关。仁宗时由于君主对台谏的重视以及一系列保护士大夫言论权措施的实行,使得台谏弹劾成为常规化的、稳定的舆论力量的来源。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将台谏弹劾形成官场舆论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发现问题,提出弹劾。
北宋时期官僚制度已较为完备,中央、地方官员人数众多,公事繁杂,在大多数情况下,处理公事往往需要随机应变,易导致官员的各种违规行为,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违规行为才能进入台谏官员的视野,乃至成为他们弹劾的事由?从前揭分析看,官员违反道德的行为更易于为台谏所弹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士大夫阶层需要伦理道德作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合理性基础。
赵宋建立以后,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渐安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相对滞后,唐中期到五代时期社会混乱导致的道德失范已不能适应大一统政权的要求,整个社会,尤其是士人阶层必须重新树立和维护共同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责任,以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就中国传统社会的具体情况看,士人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责任往往源自于儒学。他们少时即熟读经书,修养德行,一旦有相应的社会条件,他们就会以之作为参与政治事务的基础。早在宋太宗、真宗时期,就有不少士大夫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廉洁自律、淳厚坦诚、谦逊恭谨的道德准则。太宗时枢密副使钱若水“有器识,能断大事,事继母以孝闻。雅善谈论,尤轻财好施”;([3]卷二六六《钱若水传》,P9170~9171)真宗时宰相李沆居室极为简陋狭窄,“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7](卷二《李沆》,P79)当居第出现“颓垣坏壁”的现象时,他以“但念内典,以此世界为缺陷,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8](卷八《李文靖(四)》,P92)为理由,拒绝修缮房屋,表现出因忧患天下而崇尚节俭、廉洁自律的精神。同时,也有士大夫通过著文、给友人的书简、呈皇帝文等方式,赞扬有德之官员、阐述官员德行的重要。宋初名臣田锡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士大夫所贵者,树德而亲仁,博学以师古。师得古道以为己任,亲乎仁人以结至交。至交立则君子之道胜,胜则可以倡道和德。同心为谋,上翼圣君,下振逸民,使天下穆穆然复归于古道。”[9](卷四《贻青城小著书》)将士大夫“树德”置于上辅君主、下安百姓的重要地位。杨亿在给宋真宗的《奏举韩永锡状》中言永锡“检身奉上,挺夙夜匪懈之诚;守道安贫,励风雨弗渝之操。士流推慕,名迹蔼然”,[10](卷一五《奏举韩永锡状》)正因为韩永锡德行高尚,为士流所推崇,故推荐其任官。但文章、书信的传布范围非常有限,往往只是至亲好友;呈文的传布范围稍广,也只限于能看到呈文的少数大臣。而台谏官员的弹文就不一样了,因为是对官员言行的批评,易引起官员之间的口耳相传。而且有时弹劾者往往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弹奏,或者多位台谏官员接连不断地弹劾同一位官员,被弹劾者很可能还会有所回应,这样,连续的行为势必会掀起汹涌澎湃的舆论风暴,其引导作用和陡然提升的影响力自然是个别士大夫的书信、文章及呈文所不能比拟的。至和年间台谏官员弹劾宰相陈执中的事件,最能典型反映这一现象。
陈执中于皇祐五年(1053)闰七月进为昭文相,[11](卷五《皇祐五年》,P299)仅一年多之后的至和元年十二月,因家中女奴被殴打致死,即遭殿中侍御史赵抃的弹劾,言其“家不克正,而又伤害无辜”,请求罢免陈执中相位。[4](卷一七七,至和元年十二月,P4296)仁宗未能听从,于是至和二年(1055)二月至五月,赵抃与御史中丞孙抃连续不断上章弹劾陈执中,所论因由越来越多,既有道德之亏,也有处理政事之失,显现出明显的扩大化迹象。如劾陈执中“不学无术,措置颠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仇嫌隙,排斥良善,很愎任情,家声狼藉八事”;[4](卷一七八,至和二年二月庚子,P4308)“诬罔朝端,轻废诏狱,缘嬖昵之私爱,屈公平之大议,内则灭家法,外则隳国纲。又其作为,全是虚诡”;[4](卷一七九,至和二年五月,P4339)“处置大事,违越典故,先意希旨,动成乖谬……殊无廉耻,不恤人言”;[4](卷一七九,至和二年五月乙酉,P4342)等等。一位接一位台谏官的一次又一次弹劾,就像一波又一波的海浪,不断增加能量,似乎永不停歇,乃至朝中大臣、君主皆被挟裹于其中。弹文所用语词关涉道德者为多,又一再声言物议腾涌、要从天下之公议、取中外之公议,终于迫使仁宗在至和二年六月罢免陈执中。御史台官员如此锲而不舍地弹劾位高权重的宰相,最终导致弹劾对象被罢免,其影响不可谓不大;而整个过程中体现出的尚德倾向,尽管难免会有片面性和夸大渲染的地方,但其导向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个阶段是信息传播,意见互动,形成舆论。
当台谏官的弹劾行为发生后,一旦成为朝中大臣关注的议题,很快就会引起大范围的信息传播和互动,表现为台谏官以外的官员也上疏讨论相关问题,与台谏官的弹文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如上述劾陈执中之事,在台谏官不断奏劾过程中,先后有翰林学士吕溱、欧阳修等上奏疏论列陈执中。吕溱上疏论陈执中“外虽强项,内实奸邪,朝廷故事多不谙练,除改官序,常至差错,平居不接士人,惟阴阳卜祝之流,延入卧内,干预政事。又历数其过恶十余事”;[4](卷一七八,至和二年二月,P4317~4318)欧阳修言陈执中任宰相期间,“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学无识,憎爱挟情,除改差谬,取笑中外,家私秽恶,流闻道路,阿意顺旨,专事逢君,此乃谄上傲下愎戾之臣也”。[4](卷一八○,至和二年六月,P4349)他们议论陈执中之事基本皆是道德、吏能并举,但从奏疏文本看,“奸邪”、“不学无识”、“憎爱差谬”等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词,更容易让人产生对被弹劾者品行的价值判断,也更加突出了被弹劾者的道德阙失。这些奏疏与台谏官的议论搀和在一起,看似众声喧哗,实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中心点,即陈执中道德低下,无以为相。
朝堂之上的议论也包括持不同观点的大臣之间的争论,不过这种争论可看作一个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意见求同过程;它会吸引更多的臣僚参与其中,并认同抛弃差异性之后的共同观点。如陈执中事件中,当御史台官员奏劾陈执中时,谏官范镇曾有不同意见,他认为陈执中“变祖宗大乐,隳朝廷典故,缘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学士,除观察使,其余僭赏,不可悉纪”,再加之“今天下民困,正为兵多,而益兵不已,执中身为首相,义当论执,而因循苟简,曾不建言”。文本显示,虽然范镇也不认同陈执中入相之后的所作所为,但他反对御史以陈执中私事治罪的做法,并建议仁宗将自己的奏疏宣示于陈执中和御史,“然后降付学士草诏,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职事”。[4](卷一七八,至和二年二月甲辰,P4312~4316)显然范镇更趋向于以吏事评价陈执中,由此导致御史台官员与谏官之间的交相论列,这就更加引起朝堂之上的议论纷纷,最后的结果是仁宗倾向于御史台官员的看法。因此,舆论的形成过程实则也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求同存异就是一种妥协,“为官以德”这个最根本的原则问题不能退让,但是一些细节问题、局部问题可以适度妥协。
更重要的是,台谏官往往在弹文中指出官员道德阙失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以此引起君主的重视。如皇祐二年六月,谏官包拯、陈旭、吴奎等劾三司使张尧佐“凡庸之人,徒缘宠私,骤阶显列,是非倒置,职业都忘,诸路不胜其诛求,内帑亦烦于借助”,任用张尧佐是上违天意、下咈人情,“违天意,则善应差殊,虽禳祈祷祀,无以益也。咈人情,则治风颓弊,虽督率纠摄,无以拯也”,而且“若不恤人言,罔顾天戒,祸不止其人,又贻患于国家”,[4](卷一六八,皇祐二年六月丙子,P4046~4047)明白指出如果官员德行严重受损,则会影响统治基础。谏官所言虽有夸大其词之嫌疑,但也正是通过这种无限放大其危害性的方式,才能获得君主的支持;而君主的支持对于以“尚德”为中心的官场舆论的形成意义重大。
可见,朝中大臣们的意见在互动之中不断交锋、整合,求大同、存小异,变得越来越趋向于统一,同时也使“为官以德”理念认同者的规模越来越大,其中也包括君主的认同,最终形成相对稳定、有序的官场舆论。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弹劾是官员过失已经出现之后的纠偏,犹如消极的防御,所以努力建立官场舆论,促使官员增强自律性,则是一种从根本上防止官员犯错误的有效措施。从仁宗朝台谏官员的弹劾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致力于建立以“为官以德”为主的官场舆论,且其成效十分显著,以至于是否有德成为此后北宋台谏官弹劾官员的主要标准。但是,德行很难进行客观评定,只能通过言行加以考察,而对一个人的言行,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看法,所以此一标准也常常成为北宋士大夫操纵舆论的工具,阿附我者则为德行高尚之人,不同政见者则德行有阙,以此党同伐异,打击异己。
三、弹劾形成的官场舆论的影响
弹劾是一种舆论活动方式,对于官场舆论的形成和传布有着关键性作用。北宋时期由台谏官主导的弹劾,在批评官员道德阙失的过程中,制造官场舆论热点,引导官场舆论走向,并控制官场舆论动态,从而以舆论的力量制约和监督官员,不仅对被劾官员个人带来直接影响,而且对整个士大夫群体乃至社会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台谏官的弹劾往往多以道德问题为中心,形成“尚德”的官场舆论,被劾官员一般皆会遭遇降职或改官的责罚。如庆历四年(1044),监察御史包拯劾司勋郎中张可久任淮南转运使时贩私盐万余斤,于是责授张可久为保信节度副使。[4](卷一五一,庆历四年八月,P3678)正是因为张可久官德有亏,在“尚德”的官场舆论形势下形象不佳,所以才遭遇官品从从五品上降至从八品的责罚。对于某些官员来说,弹劾舆论的影响甚至及于其整个仕宦生涯。据文献记载,王逵在仁宗时期曾经先后三次被劾。第一次是庆历元年因“在湖南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羡余”,被知谏院张方平劾奏为“肆情害物”,由知虔州徙知池州。[4](卷一三三,庆历元年八月壬午,P3160~3161)第二次是庆历五年(1045)冬或庆历六年(1046)夏,时任监察御史包拯连上两疏,弹劾王逵“行事任性,不顾条制,苛政暴敛,全无畏惮”,首先用带有主观性和感情色彩的一些语词对当事者的道德下判断,然后才论事,称“王逵先任荆湖南路转运使日,非理配率人户钱物上供,以图进用,山下之民苦于诛求,逃入蛮峒,结集凶党,致此大患,于今未息”,并请求将王逵降职,皇帝未允许。[4](卷一六○,庆历七年四月,P3872)第三次是皇祐二年,朝廷将差王逵充淮南转运使,谏官包拯又多次上疏反对,理由仍然与庆历五年所言一样,用语亦相同,认为王逵“惟务掊克生灵,凌辱官吏,任性率易,不顾条制”[5](卷六《弹王逵第三章》)等,朝廷未施行。王逵屡次被劾,仔细查阅所遗弹文,发现实则皆源于一事,即允许百姓输钱免役;北宋士大夫对这一做法本来有争议,但当弹劾者将其上升到“苛政暴敛”的道德高度时,就很容易形成舆论风暴,从而使当事官员的仕途受到影响。即使由于皇帝的恩宠或位高权重者的支持,王逵暂时未能受到责罚,但亦影响到了他在官场中的声誉。所以直到嘉祐四年(1059),王逵仍然因此事被斥责“贪酷虐民”而不得起用为知州。[4](卷一九○,嘉祐四年十二月丁亥,P4603)可见,“尚德”的官场舆论已经成为北宋士大夫群体认可的一种集体意识。它能够对士大夫个体产生心理上的压力,即:顺应舆论而动,可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个人仕途上的升迁;若逆舆论而行,则有可能陷入孤立的境地,甚至遭致贬官、迁职的惩罚。因而,官场舆论表现出较为强烈的规范官员个人行为、乃至官场秩序的作用。
弹劾所形成的官场舆论也影响到了北宋整个士大夫阶层。从北宋制度层面来看,台谏官是官场舆论的中心,他们通过弹劾将偏离社会规范和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唤起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谴责,将违反道德者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从而起到舆论整合的作用,有利于形成保持士大夫阶层崇高地位、以“尚德”为中心的主导性舆论。更重要的是,这一正向舆论一旦形成便具有权威性,对整个士大夫群体产生导向、约束、警诫等心理作用。在这样的官场舆论影响下,士大夫个体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有德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以期获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和接受。如南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所载名臣的神道碑、墓志铭、行状或传等,传主和撰者绝大多数皆为北宋时期的士大夫,每一篇皆有关于传主道德方面的评价。如言范仲淹“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12](上卷二○《范文正公仲淹神道碑》)言范镇“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12](中卷一八《范忠文镇墓志铭》)等等。也有言丁谓“机敏有智谋,憸巧险诐”,[12](下卷三《丁晋公谓》)赞颂德行高尚、声誉较高之人,贬斥无德之人。尽管碑传皆为士大夫个人所写,但这些与道德有关的评价却反映了“尚德”的舆论导向对士大夫整体的影响。再如南宋人吕本中所撰《官箴》是对北宋以来官场规范的总结,包括居官格言33则,其中第一则曰:“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13]他指出当官第一要务即为“清”,既秉承了儒学的传统,也反映了北宋以来官场“尚德”舆论对士大夫整体的影响。类似的言论还出现于南宋人张镃《仕学规范》一书中,称“士君子当以德义相先,不然,则未足为士矣”,[14](卷九《行己》)将“尚德”的影响进一步推及于整个士人阶层。
不仅如此,“尚德”的官场舆论还通过士大夫影响到了社会风气。北宋时期,科举录取人数大量增加,导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基本皆由科举出身者担任,这些士大夫们自小所读的儒学经典有利于培养他们廉、正、俭、谦的官场道德,加之北宋台谏官地位逐渐上升,各级士大夫们在为官实践中常常能亲身感受到台谏官弹劾德行阙失之人所引起的官场震荡,因此“尚德”的官场舆论必然会影响到大多数士大夫的为官行为,当他们担任地方官时,很自然地也将崇尚道德的理念贯彻于其为官实践中,对于形成当地尚德的社会风气起到了引导作用。如仁宗时,蔡襄进士及第后任西京留守推官,景祐三年(1036)目睹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4人被贬事件,深感台谏官的重要性,作《四贤一不肖诗》;后他又任职中央多年,对仁宗台谏官弹劾所形成的“尚德”的官场舆论多有体会和认同,于是在知福州任上特别注重推行尚德的理念,“郡士周希孟、陈烈、陈襄、郑穆以行义著,襄备礼招延,诲诸生以经学”,[3](卷三二○《蔡襄传》,P10397~10400)通过褒奖的方式教化地方百姓,希望能养成重义的民风。同时,他还撰写《谕乡老诸生文》,认为地方官就应该“察禁邪猾,扶善沮恶,使强弱各安其分”,引导百姓向善之心,并恳请乡间诸老与他一起促成“孝慈友弟、敦厚信让之风”,以达到“行礼让而止狱讼”的目的。[15](卷三四《谕乡老诸生文》,P619)郑至道于宋哲宗元祐初年任天台令,“为政宽简,专务教化,民心悦服”,[16](卷一五四《名宦·宋·郑至道》),留有《谕俗七篇》,直言“县令之职,所以承流宣化于民为最,亲民不知教,令之罪也”,说明其作此文的目的就是因为天台县“风俗鄙陋,教道未至”,导致本地百姓“多违理逆德,不孝不悌,凌犯宗族,结怨邻里”,于是他从孝父母、爱兄弟、睦宗族、恤邻里、重婚姻、正丧服、重本业7个方面诫谕百姓,希望能够革除陋习,形成礼义孝悌之风。[17](卷三七《天台令郑至道谕俗七篇》第七册,P7574~7578)可见,北宋时期不少地方官皆将以德教化百姓看作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并在他们的为官实践中身体力行予以实施。
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于“尚德”的官场舆论与中国传统儒学的人才观非常吻合,因此进一步强化了北宋士大夫阶层重道德、轻吏能的政治理念,这自然不利于吏能突出者在仕途上的升迁。更严重的是,官场舆论的“尚德”趋向还会直接导致北宋官员整体的行政实践能力难以提高,以致极有可能无法有效地处理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朝廷的良法善政亦可能因为地方官的执行能力欠缺而不能得到充分贯彻,甚至成为扰民之法。
四、结语
仁宗朝台谏机构的逐渐完善,使得台谏官能够在比较正常的政治状态下行使弹劾之权;他们的弹劾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政治参与行为,而且是形成舆论监督、引导士风的重要方式。在台谏官一次又一次的弹劾过程中,各种意见经过讨论、对决、交流,最终形成士大夫们共同认可的、“尚德”的为官理念,并以此构成官场舆论的重要内容。虽然这种舆论并不具备物理形态,似乎是一个虚拟的观念,但却有着巨大的能量和影响力,显示出对所有士大夫的强大约束力。同时,这种官场舆论也对士大夫个人的仕途产生较大影响。为了实现仕途上的顺利升迁,他们大多数人必须与其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保持一致,由此实现士大夫阶层群体意识的整合,即通过多次以“尚德”为中心的弹劾行为及官员的互动,形成士大夫阶层相对一致的、崇尚道德的舆论意见,并通过任职地方的方式将“尚德”的理念推行于整个社会,对于促成礼义孝悌的社会风气影响深远。
[1]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 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3]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 包拯.包孝肃奏议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7] 朱熹.宋名臣言行录·五朝名臣言行录[M].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8]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 田锡.咸平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 杨亿.武夷新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 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 吕本中.官箴[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4] 张镃.仕学规范[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 蔡襄.蔡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6] 浙江通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7] 陈耆卿.赤城志[M].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