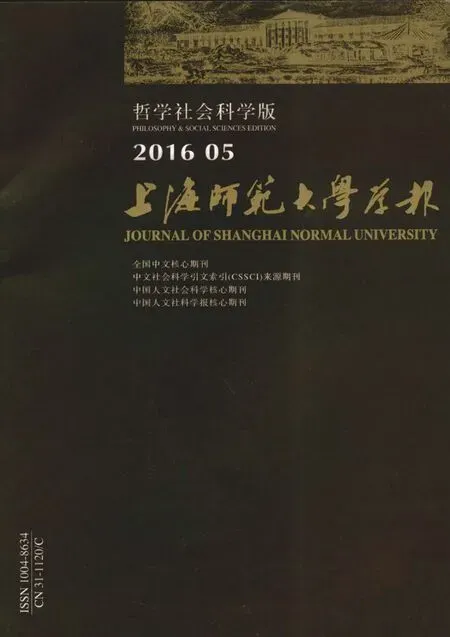劳伦斯植物诗歌的生态解读
2016-04-12祝昊
祝 昊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曾经说过,D·H·劳伦斯的作品中“激荡着悠扬的歌声,洋溢着诗歌的气息”。[1](P130)的确,劳伦斯的文学创作富含诗情灵性,这种诗情灵性不仅展露在那些充满生命力与想象力、同时又不乏思辨色彩的小说之中,更弥漫在其近千首诗歌的字里行间,生命灵气与象征性的结合使其诗作独具魅力。劳伦斯认为“诗歌的本质是它致力于唤起一种新的关注,以便在已知的世界中‘发现’一个新世界”。[2](P176)因此,无论是置身于伊斯特伍德山水的润泽之下,还是身处伦敦罹受现代工业文明的侵袭之时,抑或是在新墨西哥荒野朝圣的历程之中,劳伦斯都以一种颇为诗意的方式感知世界;不管是男女情爱、家庭生活,还是花鸟鱼虫、星辰日月,都被其融入诗中,借助于瑰丽的想象、灵动的节奏,对情与爱、生与死、文明与自然等主题进行思索和表达。特别是其中描写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的诗歌,更是倾注了诗人的深情,尤为世人所称誉。
然而,与浪漫主义诗人那些传统的自然诗不同,劳伦斯在其关涉自然的诗歌中不再仅仅将自然视为人类的审美客体,亦不再将静态的风景观感与自然的生命视同一律,而是试图以动物的视角来感知其生老病死,以植物的视角来感受其荣枯兴衰,尽可能地趋近自然的本真。20世纪晚期生态批评的兴起为劳伦斯自然诗歌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新的阐释方向,然而从近些年的研究现状来看,研究者们或是聚焦于劳伦斯的动物诗歌,或是聚焦于植物在其小说中的生态内涵,却鲜有论者对劳伦斯的植物诗歌做系统研究。因此,探究劳伦斯植物诗歌中的生态意蕴,查考其中的生态意义,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课题。
一、植物情结与植物书写
早在1905年的春季,为了向初恋女友杰西·钱伯斯表达倾羡与爱慕,劳伦斯便写出了最早的诗作《致绣球花》(“To Guelder Roses”)和《致石竹》(“To Compions”)。而在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诗作《郊野公园》(“The Common Wild”)里,劳伦斯亦在首句便以美丽的金雀花为描写对象:“金雀花丛闪耀着点点光斑/阳光流泻,似燃烧的火焰。”[3](P1)寥寥几笔将自然景致勾勒得活灵活现。在此之后,劳伦斯或是以鲜花野草入诗,或是以果实树木入诗,写就了大量诗情画意、草木葳蕤的诗篇:从早期的《啮龙花》(“Snap-Dragon”)、《水仙》(“Narcissus”),到中期的《西西里仙客来》(“Sicilian Cyclamens”)、《木槿花与鼠尾草》(“Hibiscus and Salvia Flowers”),再到晚期的《红色天竺葵和神圣的木犀草》(“Red Geranium and Godly Mignonette”)、《紫色银莲花》(“Purple Anemones”)等等,不一而足;并将之编纂于《鸟·兽·花》(Birds,BeastsandFlowers)、《三色紫罗兰》(Pansies)、《荨麻》(Nettles)等诗集当中。从这些篇名中不难看出,无论是以植物为诗歌的核心意象,还是用植物来衬托、凸显其他主题,劳伦斯对植物青睐有加都是显而易见的,无怪乎后世有论者将之誉为“植物王国的桂冠诗人”。[4](P47)
劳伦斯之所以对植物格外钟情,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这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劳伦斯“心灵的故乡”伊斯特伍德是一个地处诺丁汉郡和德比郡交界处的煤矿小镇,与传统意义上的“往昔森林和农业的古老的英格兰”只有一水之隔;劳伦斯正是在这种丑与美的鲜明对比中长大成人。根据相关传记资料记载,孩提时代的劳伦斯便尽可能地回避由黑烟和机器所构成的丑陋之地,而是亲近自然,到著名的舍伍德森林中去;并在矿工父亲的熏陶之下,对各种花草树木都分外稔熟。[5](P20)离开故乡进入诺丁汉大学学习之后,出于对野生植物的共同喜好,劳伦斯与绰号“植物学家”的史密斯成为朋友,[6](P16)他们认为除却植物学之外的课程都是在浪费光阴。[7](P41)而当劳伦斯在植物学课上看到那些肿胀的子房和突出的雄蕊之时,他更是直接地体悟到了植物在性上的坦率与直白。这一点深刻地影响到了其早期的诗歌写作,比如在那首因色情因素而饱受訾议的《啮龙花》里,劳伦斯便将两侧对称、口部唇形、裂片闭合、只有健壮的蜂类才能挤入其中的啮龙花喻为女性的生殖器,而这一隐喻亦在之后的《桃子》(“Peach”)、《石榴》(“Pomegranate”)等诗作里一再地重现。
然而,劳伦斯对植物意象的使用并不仅仅局限在表层的象喻之上,同时也富含丰富的人类学意义。这是因为劳伦斯对植物意象的偏爱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到了来自于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尤其是詹姆斯·弗雷泽及其代表作《金枝》的影响,使劳伦斯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大量地使用了人类学以及比较宗教学的材料,囊括了原始思维、原始信仰和行为习惯等不同的方面。在劳伦斯看来,植物的律动不仅揭橥了生命和创世的奥秘,同时也传达了再生、青春以及不朽的神秘性。因此他在诗歌中不仅将槲寄生、无花果、梣树等对欧洲原始先民具有神圣意义的植物反复呈现,还将植物与古代神话密切相联,诸如狄奥尼索斯、阿蒂斯、阿多尼斯等伟大的生殖之神就与葡萄、紫罗兰、银莲花等相互映射。神话寓意的注入不仅使得诗句更富张力,还凸显了诗人的原始主义旨趣。例如,在《葡萄》(“Grapes”)一诗中,劳伦斯就渴望借助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力量将人类带回到洪水之前的绿色世界,能够如葡萄那样“静寂,敏感而活跃/用藤须一般的听觉、触觉/辨向、延伸、触探、认知/依靠那天然的本能”,[3](P225)而不是如现代人那般对文明世界里“民主社会的前景、大街、电车和警察”[3](P226)念念不忘。而这一点和后世某些诗人们的生态主张亦是不谋而合的。
当然除此以外,典雅的浪漫主义自然诗歌、俚俗的英国民歌民谣,乃至约翰·罗斯金等诗人的植物书写等诸多因素,也都对劳伦斯植物诗歌的写作产生了或隐或显、浓淡不一的影响,在此就不再多加赘述。总体而言,由于生活在一个工业文明日益勃兴并渐次地滋扰和侵害自然的神圣进程的时代,当这一现实境况投射进劳伦斯的植物书写时,他总是试图通过表达独特的思想理念、采取相应的诗学策略或建构不同的宇宙范式等种种方式来恢复自然的神圣性。这种努力与尝试不仅使得其植物诗歌中形成了独特而完整的生态景观,更彰显了诗人极富前瞻性的生态意识。
二、地方意识与文化乡愁
在《作为生态一元论的“地之灵”》中,唐纳德·古铁雷斯曾指出:“劳伦斯的初衷并非要充当一位生态斗士,但其却以一位诗人预言者(poet-seer)的身份觉察到了人与大地之间的有机关联……无论是作为20世纪生态文化的先知、诗人或是小说家,劳伦斯都值得我们关注。”[8](P48)诚如其所言,尽管劳伦斯的文学创作并非以生态为原初取向,但若是从当代生态文化的角度来对其著作进行纵向重评,则会发现劳伦斯不负“预言者”之名,其许多思想极富生态价值,可谓开后世生态批评之先声,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地域之灵”的思想。劳伦斯一生羁旅天涯,先后寄迹于德意志,蛰隐于康沃尔,偃蹇于西西里,而后更是远渡重洋常年客居在美洲大陆。这种飘萍浪迹于大洋大洲的经历使得劳伦斯感受到了人类文明的绚丽多彩,体悟到了异域文明的瑰异多姿,他将自己的文化乡愁在《地之灵》(“The Spirit of Place”)一文里袒露出来:“每一个大陆都有其独特的地域之灵。每一个国度的人都被某一特定的地域所吸引,这就是家乡和祖国。地球上的不同地点放射着不同的生命力、不同的生命振幅、不同的化学气体,不同的星座放射着不同的磁力——你可以以任意方式称呼它。但是地域之灵的的确确是一种伟大的真实。”[9](P6)
尽管这种颇具神秘宿命意味的理论发轫于荣格等人提出的“人格地质学”观念,但其中所传达出的人类通过心灵与大地和种族相联、身体植根于土地之上的思想,却在某种程度上与强调环境与文化相互影响、人类与所在之地的生态和谐共生的地方意识(the sense of place)相投契。在劳伦斯的个体诗学之中,土地不仅被赋予了与文化共享的情感意义并与之形成象征性的关系,同时还成为个体、种族理解环境并与之相处的根柢。比如在小说中,劳伦斯往往将北方的冰天雪地、日耳曼人、基督教文明与南方的似火骄阳、意大利人、异教文明相对比,借以凸显个人生命力的弱与强,表征不同文明的衰与盛。劳伦斯尤为喜爱用植物来表达不同的地域之灵或是独特的地方意识,他在《花季托斯卡纳》的开篇曾说过“每个国家都有在自己土地上大放异彩的花。在英国,是雏菊、金凤花、山楂和紫金花。在美国,是秋麒麟草、星花草、六月菊、八角莲和翠菊——我们称之为紫苑。在印度,是木槿、曼陀罗和金香木……水仙、银莲花、日光兰、藏红花、长春花和欧芹,单单被地中海人赋予了独到的意义……雏菊和地黄连是英国的花儿,它们只对我们和北方人才独具妙意”。[10](P57)同样,在诗歌中,劳伦斯也是通过描写和吟味不同的植物来传达和褒贬不同的“地域之灵”,倾诉自我的文化乡愁。
劳伦斯对英格兰的情感格外复杂,既哀恸于其在工业文明的侵袭之下已入濒死之境,又厌憎它的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同时还渴望通过充满原始朝圣色彩的追寻,将之从死去的社会形式和死去的宗教中拯救出来;对之可谓既有着深厚的“地方依恋”(Topophilia),又有着难以驱散的“地方恐惧”(Topophobia)。“红白玫瑰战争”使得玫瑰成为英格兰的国花,遵循历史的传统,劳伦斯亦偏爱用盛开的玫瑰来象喻古老的英格兰。借用英格兰这朵玫瑰的凋零,他表达了机械文明的扩张和人类战争的蔓延所带来的“地域之灵”的萎缩和地方意识的失落。在《玫瑰不是甘蓝》(“A Rose is not a Cabbage”)一诗中,劳伦斯哀叹道:“烦恼的寒冬业已降临大地/英格兰的玫瑰寥寥无几/愈发无几、再也无有/徒剩甘蓝,数不胜数。”[3](P478)娇艳欲滴的玫瑰为“内心只有苍白的空洞”[3](P478)的甘蓝所取代,令诗人黯然神伤。而在《英格兰玫瑰》(“The Rose of England”)里,劳伦斯则意识到了此刻的英格兰宛若被移莳入温室的野生玫瑰一般,它那纤细的雄蕊和贫瘠的花瓣已不再具备任何繁殖能力,就像生活在其上的英格兰人一样,真正的男性特质早已云散烟消。然而,劳伦斯依然寄望于人类的改变以让英格兰的“地域之灵”重新回到生机勃勃的状态,就如同他在《玫瑰与甘蓝》(“Rose and Cabbage”)中所希望的那样:“找寻到一个敢于成为英格兰玫瑰的人/野生的英格兰玫瑰/有着金属的尖刺,当心!”[3](P527)并用这金属般的尖刺“扼杀机械”显然,地方一方面塑造了人,而另一方面又为人所改变;正是在这种互通互动的关系之中,人类才有了深厚的地方依恋,才有了家乡和故园。诚如伊迪斯·柯布所概括的那样,劳伦斯“地域之灵”的思想“意味着人与地方之间活生生的生态关系”。[11](P12)
离开英格兰后,劳伦斯开始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他将自我的灵魂附丽在异域风情之上,冀望乞灵于异域的、原始的文明来使其钟爱的英格兰挣脱濒死的命运;他在锡兰、新墨西哥、西西里岛都挥洒下了不朽的诗篇。比如在锡兰,以威尔士王储为代表的殖民者的羸弱畏葸、机械呆板与土著僧伽罗人的生机盎然、朝气蓬勃形成的强烈反差给劳伦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英格兰人地方意识的失落相比,贴近土地、熟悉土地的僧伽罗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在地生活”;他们不仅如稻谷一般与水田、耕牛、大象共同组成了一幅和谐天然的图景,还与古老的大地血脉相连:“这些长着黑面庞、棉布缠头的土著人,不计其数/密密丛丛地林立于湖畔,宛若水滨浓密的野稻谷/等待典礼之后的焰火/焰火腾空,无数被映亮的黑脸庞/宛若黑色的稻谷在生长。”[3](P320)人如稻谷一般与外在自然成为一个生态共同体,与大地保持着相同的律动和生命活力,呈现出了一种本真本然的状态。
而在写于托斯卡纳的《柏树》(“Cypresses”)一诗中,劳伦斯更是将这种地方意识和文化乡愁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以柏树为触媒,将古老的土地与古老的文明密切相联;即便是伊特鲁利亚文明早已消亡,但其原始的生命精神和生命意识却长存于柏树之中,“无法传递的秘密/已随消亡的种族、消亡的语言逝去/却如隐秘的纪念在你体内/伊特鲁利亚的柏树”。[3](P234)在诗人看来,“四处摇曳着黑暗全身的/弯曲、火焰般高大的柏树”[3](P234)就是“有着伊特鲁利亚式的黢黑、身姿摇曳的古伊特鲁利亚人”;[3](P234)它们依然植根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依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在翻腾着乳香/散发着没药芬芳的/柏木树荫深处/逝去的、人的生命是如此芳香。”[3](P236)诗人不仅将原始文明中对生命的宗教表述视为古老土地的地域之灵,认为即便是轻视自然、崇尚王权的罗马人亦无法让之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同时还将自己的文化乡愁寄寓在这片土地上,渴望柏树之中所蕴含的生命力量能够再次回到生活之中。在诗篇的末尾,诗人点出了整篇的主题:“邪恶,什么才是邪恶?/邪恶只有一种:对生命的否定。”[3](P236)在诗人看来,无论是古罗马人对伊特鲁利亚人的否定,还是机械的美国对阿兹台克之王蒙特祖玛的否定,都是邪恶的;因为他们否定了生命。劳伦斯将自己“地域之灵”的核心理念及消解文化乡愁的最终途径,都寄托在了对生命和生命力的崇拜上。他视生命为衡量善恶的唯一标准,并且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说这种主张与多年以后阿尔贝特·史怀泽那种视有益于生命为善、伤害生命为恶、敬畏生命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三、生死平衡的生态意蕴
“地域之灵”的理念消弭了自然与文化的界限,不仅为人类探索出一种健康的文化模式指引了方向,还为从自然和文化密切关系的角度解读其诗歌提供了可能性。与此同时,劳伦斯在诗歌中还赋予了植物深刻的人类学意义,将对于人类而言具有神圣意味的死亡与再生的主题放置在自然的语境之下来书写,借助于草木的春生秋谢来昭示人类的死亡与重生,将自己对死生问题的思索融入四季轮回的时空之中,使得诗歌极富张力。神话因素的介入使得社会历史的直线时间模式为仪典神话的循环时间模式所取代,死而复生的时序结构将个人的存在纳入到自然宇宙的总体循环之中。劳伦斯正是试图以此来纾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不再着重凸显人类是自然的主宰,而是将之视为“土地社区”中的一员,与自然世界中的其他成员同生共死。作为20世纪小说神话化的奠基者之一,劳伦斯对古代神话的稔熟程度已毋庸赘述,他以谙练纯熟的手法将银莲花等植物与阿多尼斯等植物性神祇相关联,杂糅进了诗篇之中,借助于“俄耳甫斯的告别”、“哈得斯劫掠珀耳塞福涅”等神话母题来表达其对“生/死”主题的思索。
劳伦斯早期诗风清丽自然,多以性爱为主题。而在其创作生涯的中晚期,经历的坎坷、身体的沉疴等因素使他更为关注死亡与再生等宏大命题,由一位“爱情的祭司”变为“死亡的歌者”。但对于劳伦斯而言,性爱和死亡在本质上是可以视同一律的,因为它们皆可被视作一种向着未知世界的跃进,都具有从一种状态跨向另一种状态的过渡仪式的意味。故而在自己的植物书写中,劳伦斯往往赋予笔下的植物意象以双重乃至多重蕴涵,如在《石榴》、《无花果》(“Figs”)等果实组诗里,诗人就通过迭现“裂缝”的特质来表征女性的私密,既展现了性的奥秘与性的美感,又暗含了生命的律动与生命的源泉。而在《欧楂与山梨》(“Medlars and Sorb-Apples”)里,劳伦斯则借果实的腐烂来呈现死亡的主题,他颇为钟爱这种腐烂,开宗明义地宣扬“我爱你,腐烂/美味的腐烂”,[3](P220)并将腐烂的过程与俄耳甫斯和狄奥尼索斯各自在冥府的情爱经历相联系,所以这种腐烂既是酒神的迷醉,又是一种“绝妙的地狱体验/似俄耳甫斯的音乐”。[3](P220)对诗人而言,腐烂的过程不仅意味着果实开始趋向死亡,同时还意味着腐坏的果肉与果核中的种子渐次剥离,故而死亡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新生的过程,就如同被酒神的狂女撕碎而最终又复活的俄耳甫斯和狄奥尼索斯一般。同样,在创作晚期的《灵船》(“The Ship of Death”)等诗作中,劳伦斯亦托物陈喻,以秋日的苹果的腐烂、种子的释放来表征人类的灵魂脱离躯体、追寻新生的历程。
较之借助果实的腐烂来表达死亡的主题,劳伦斯偏爱通过鲜花的绽放来表达新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杏花》(“Almond Blossom”)一诗。劳伦斯将杏花这一意象视为新生的象征由来已久,在稍早的《春天的早晨》(“Spring Morning”)里,杏花的灿然怒放就意味着春天的到来、万物的复苏。之所以选用杏花来表达,劳伦斯可能是受到了《金枝》的影响。据《金枝》的记载,在弗里吉亚(Phrygia)人的宇宙起源神话里,杏树被视为一切事物的始祖,因为“杏树柔嫩的淡紫色的花朵在未长叶子之前就出现在光秃秃的枝条上,它是春天最早的信使之一”。[12](P352)在《杏花》中,劳伦斯沿袭了《赤裸的杏树》(“Bare Almond Tree”)里的比喻,将数九隆冬里杏树那扭曲而又黢黑的枝干比作锈迹斑斑的钢铁,同时却又满怀期待:“让我们鼓起勇气/看钢铁绽开,萌芽/看生锈的钢铁喷放出来束束鲜花。”[3](P241)诗人并不简单地以杏花的绽放来表达新生,而是同时赋予其深刻的宗教意蕴,将自然现象与文明的兴衰更替联系起来。诗中劳伦斯视寒冬腊月里的杏树“像人类一样/在长久的世纪中遭难/流浪、放逐、长期生活在流亡之中”,[3](P241)现代的机械文明已经将人类文明带入了绝地,就像耶稣基督将要经历的“客西马尼园的漫漫长夜”;[3](P242)只有诉诸异域充满生命活力的文明,才能获得救赎,就如同杏花一样:“异国的异树/然而是鲜花的心脏 /鲜花的不可熄灭的心脏!”[3](P242)在描写杏花绽放的过程中,劳伦斯始终将代表着耶稣基督的“客西马尼园的血”的意象和代表着丰饶女神伊西斯的“天狼星吠唱的颂歌”[12](P356)的意象相比照,以之来凸显强调杏花自冬徂春、死而复生历程的方向性,暗示着人类也只有摆脱僵死的基督教文明,诉诸自然主义的、充满活力的异域文明,方能真正地获得新生。
事实上,死亡与重生之美的实质就在于人类的生死流转、文明的兴旺衰败和大自然的生灭法则之间能够完美地达成一种相谐一致、自然而然的契合。故而在著名的《巴伐利亚的龙胆》(“Bavarian Gentians”)里,劳伦斯直接地将冥后珀耳塞福涅的神话熔铸入诗篇之中,真正完整地表达了死亡与新生。在诸如《迷途的姑娘》、《瓢虫》等小说里,珀耳塞福涅的神话原型就曾被反复使用过,冥王与冥后所主宰的冥界被塑造得极富生命活力,因为在劳伦斯看来,冥域是对现实世界的翻转,是一个与濒死的文明世界迥然不同的、跃动着生命之火、活生生的世界。故而在写作这首初名《黑暗的荣耀》的诗作时,尽管疴恙缠身、濒临死亡的边缘,劳伦斯依然激情昂扬地歌颂未知的冥域。他视龙胆为火炬,指引其走向冥府:“给我一枝龙胆/赐我一支火炬/让我用喷吐蓝色火舌的花朵开路/走下愈发昏暗的阶梯。”[3](P584)因为死亡对诗人而言,不过是冥后再次奔赴冥域,“包容在普路托双臂的更深的黑暗当中/渗透了极为阴暗的情欲”;[3](P584)在与冥王的神圣婚姻中周期性地由处女的纯洁状态过渡至母性的幸福状态,在死亡之中孕育了生命的真谛。劳伦斯并不视死亡为生命的终止,而是将之视为另外一种存在的模式,而这种模式正暗含于由植物所表征的宇宙的律动之中。借由这种对于个体死亡的肯定,劳伦斯在自己的植物书写中放弃了传统意义上对于生命永恒状态的追寻,而将个体的生存与死亡、文明的兴盛与窳败都放置在自然的语境之下予以观照,将之与草木的荣枯等量齐观,在追求均衡和谐的新秩序过程中凸显出了一种生态的意蕴。
四、生命之树与宇宙玫瑰
著名的但丁研究者C·H·格兰金特在评论《神曲》时曾说过:“所有主题中最广泛的主题,即人类的罪愆和救赎的主题,与宇宙的伟大设计相谐调。”[13](P93)的确,当不得不面对人与自然日渐疏离、文明与自然背道而驰这一现实境况之时,对人类的命运与文明的前景有着深切关怀和深刻思考的劳伦斯,同样冀望于能够建构起自己独特的宇宙图式,在更为宏大的框架之下考量关于拯救的宏大命题。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宇宙作为一个“存在之链”的观念,以及支撑这种观念的充实性、连续性和等级性等原则,曾获得过颇为广泛的传播和认同。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里,诸如乔叟、斯宾塞、弥尔顿等名家亦都曾以文学性的手法对之加以描绘,并对其所展现出的秩序谨严、层序分明的状态加以颂扬。在这种传统的宇宙观中,人类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故而与处于其统辖之下的动植物或无生命体之间的有机关联始终处于割裂的状态。作为一名深受宗教思想浸润的作家,对劳伦斯而言,自然界绝非只是“自然的”,而总是洋溢着宗教的价值:天空通过自身的无限高远揭示了神性的超验性;大地直接地自我展现为万物之母;同样,宇宙也是真实的、有生命的和神圣的,它同时呈现出了神圣性的模式和生命存在的模式。因此,劳伦斯认为只有彻底地颠覆等级分明的传统宇宙模型,重新构建起生机内蕴的宇宙图式,才能够在宇宙的宏大命题之下缓解现代文明、机械文明所导致的生命力萎缩、血性意识丧失等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故而,劳伦斯在自己的植物书写中选择了树、玫瑰等有机体的意象,以之为基础构建起自己独特的宇宙图式。
劳伦斯的宇宙模型的建构经历了一个依次渐进的历程。早在《无意识幻想曲》中,他就将人类的命运和树木的枯荣紧密相关,之后在《亚伦的杖杆》等小说、在《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辩护》等散文里,“生命之树”的核心概念屡次重现。劳伦斯认为现代的人类正处在死亡的进程之中,宛若一株被连根拔起的大树,失去了生命的根柢所在。正如《连根拔起》(“The Uprooted”)一诗所声称的那样:“失去了与活生生宇宙的关联/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之流/如同切断了根脉的植株。”[3](P503)又如《宿命》(“Fatality”)一诗:“一旦树叶凋零/即便是上帝亦不能使其重返枝头/一旦人类生活与活生生的宇宙的联系被损害/人最后变得以自我为中心/无论是谁,无论是上帝还是基督/都无力挽回这种联系/只有死亡通过漫长的分解过程/能过融化分裂的生活/经过树根旁边的黑暗的冥域/再次溶进生命之树的流动的汁液。”[3](P510)之后,“生命之树”的意象多次地被劳伦斯用以表征人类的命运,通过不断的呈现与再现,逐渐地成为其个体诗学中固定的宇宙模型的称谓。劳伦斯将整个宇宙视为生机勃发的有机整体,如同树木一般定期地自我再生,宇宙无穷的生命再生能力都是借由树的生命形式来表达。故而在劳伦斯这里,一岁一枯荣的大树成为宇宙意义上的表意符号,从而将生命的永不倦歇的出现与宇宙的律动的更新紧密地联系起来。劳伦斯认为,人类亟需重新审视自身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在其极富异教色彩的“生命之树”的宇宙图式中,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消解,传统宇宙模型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鸿沟得以弥合。无论是人类还是曾被视为低等的动物,乃至更为低等的植物,在生命之树中都处于一种同等的地位,协同形成了生命力的永恒流动,超验的神性亦可寓居于万事万物当中。就如同《宇宙之流》(“The Universe Flows”)、《忠诚》(“Fidelity”)等诗篇中所赞颂的那样,“宇宙在无限的溪流之中流动”、[3](P166)“一切都在流淌,每一股生命之流都相互交融”。[3](P392)
在生命力自由流淌的生命之树上,人类与世上万物之间具有一种颇富神圣意味的平等,这不仅使得自然生灵获得了更高的生命地位,还颠覆了原先的宇宙秩序,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神话。劳伦斯在自己的植物书写中通过拟兽、拟人等不同诗学策略的采用,使得神圣的自然成为一种可堪与机械文明相抗衡的均衡性的力量。继“生命之树”的意象之后,劳伦斯最终选定了玫瑰的意象来表征生命流动的极致,象征着最终的和谐与完满。劳伦斯写就了大量以玫瑰为核心意象的诗篇,但真正意义上以玫瑰来表征宇宙的完满则是在《宇宙玫瑰》(“Rose of all the world”)里。劳伦斯在这首诗中首倡“宇宙玫瑰”的宇宙树模型。而在《葡萄》里,劳伦斯则将酒神的葡萄花喻为“玫瑰之中的玫瑰”(Rose of all the roses),认为在这朵馨香的玫瑰之中的玫瑰里,“一切都沉浸在赤裸裸的交流当中”。[3](P224)事实上,劳伦斯之所以遴选玫瑰来表征宇宙实为有的放矢,是与其一以贯之的“血性意识”的核心思想有着密切关联的。若以散文来印证劳伦斯的诗歌,不难发现早在《〈儿子与情人〉自序》中,劳伦斯就提出了“真正的玫瑰只是那颤动闪烁的血肉之血肉,永远也不会改变,它是一股恒流、永恒、无可置疑、是玫瑰的无限品质,是肉身”。[13](P257)而在《安宁的现实》里,劳伦斯则声称玫瑰是一朵完美之花、是完美的天堂;它调和了宇宙两极分化的法则,象征着一种终极的美、一种绝对的和谐。劳伦斯这种独特的宇宙观与其晚期极具泛神论色彩的宗教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正如奇塔卢克所指出的那样:“劳伦斯所寻觅的、他声称仍能在新墨西哥找到踪迹的那种宗教,并非由形式化的信仰规则所构成的一种宗教,也不仅仅是用以制约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一套伦理准则;它并不许诺通过拯救便能获得灵魂不朽。简而言之,它是对生命的一种深沉的敬畏,其唯一旨意便是让生命涌流不止。这种宗教涵盖整个宇宙,并将人视为实存宇宙的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组成部分。正是这种原理滋养了劳伦斯的本质论形而上学和他关于个性的学说。”[14](P239)
五、结语
“人与周围世界的完美关系就是生命的本质……我们的生命就存在于为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生机勃勃的世界之间建立一种纯粹关系而奋斗中”,[2](P26)劳伦斯在《道德与小说》一文中如是说道。正是这种试图使文明与自然、生存与死亡、人类与宇宙的关系臻于至善的努力,使得劳伦斯的植物书写愈发地亲近生命的本质,在那些本非以生态为原初价值导向的诗歌中展露出了诸多颇具生态意蕴的思想,如“地域之灵”的思想便是与“地方意识”相投契,视宇宙为有机生命体的思想更是开启了“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的先声。这些极富前瞻性和预见性的思想,不仅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当代生态思想的诞生,更深刻地影响了加里·斯奈德、泰德·休斯等后世的生态诗人。
[1] E. M. Foster. Aspects of The Novel[M]. ed. Oliver Stallybras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4.
[2] D·H·劳伦斯.劳伦斯读书随笔[M].陈庆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
[3] D. H. Lawrence. The Complete Poems of D.H.Lawrence[M]. London: Wordsworth Editions Ltd., 1994.
[4] M. M. Mahood. The Poet as Botanis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5] 布伦达·马多克斯.劳伦斯:有妇之夫[M].邹海仑,李传家,蔡曙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6] 迈可·斯奎尔.深情的背叛:作家劳伦斯和他妻子的一切[M].石磊,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
[7] 理查德·奥尔丁顿.一个天才的画像[M].毕冰滨,何东辉,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8] Donald Gutierrez. D.H.Lawrence’s “Spirit of Place” as Eco-monism[J]. D.H.Lawrence: The Journal of D.H.Lawrence Society (1991): 39-51.
[9] D·H·劳伦斯.劳伦斯论美国名著[M].黑马,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10] D·H·劳伦斯.劳伦斯散文[M].黑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1] Dolores LaChapelle. D. H. Lawrence: Future Primitive. [M]. Denton: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Press, 1996.
[12] J. G.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M]. New York: The McMillian Company, 1934.
[13] C. H. Grandgent. Discourses on Dant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14] G. J. Zytaruk. The Doctrine of Individuality: D.H.Lawrence’s “Metaphysics”[A]. D.H.Lawrence, A Century Consideration[C]. eds. Peter Balbert and P.L.Marcus, Ithaca,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