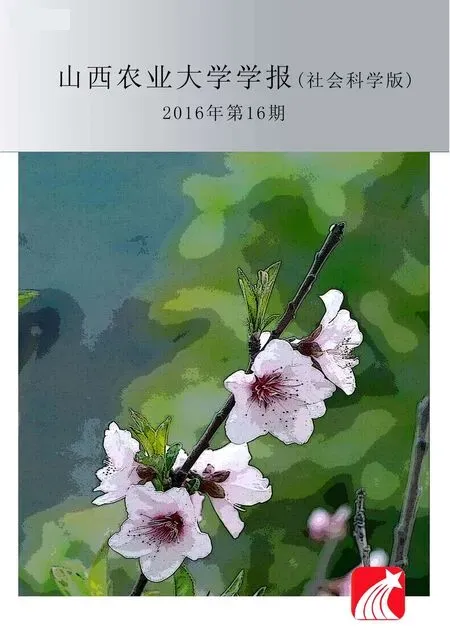思想史视域下的铭贤校园文学
——近代启蒙与救亡变奏的一个侧面
2016-04-04赫雪侠李卫朝
赫雪侠,李卫朝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思想史视域下的铭贤校园文学
——近代启蒙与救亡变奏的一个侧面
赫雪侠,李卫朝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铭贤学校作为山西近代教育的先驱之一,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生成了自己的校园文学。从20世纪20年代“自觉觉人”的呐喊与“救国图存”的呼吁并存,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启蒙运动落潮期幻灭、颓废和死亡的文学倾向,再到30年代以后救亡文学涌现,现存铭贤校园文学生动地勾勒出1924年至抗日战争这一时期铭贤学校启蒙与救亡思潮的变奏,对于我们探究铭贤学校的文化思想史、理解山西乃至中国的近代思想史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铭贤学校;校园文学;启蒙;救亡
20世纪上半叶,“启蒙”与“救亡”纠缠在一起,在北伐、内战、抗战等一系列严峻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启蒙一次次被救亡挤压,两者的关系也一直未得到合理的解决。[1]这样的近代思想历程,深刻地投射于彼时知识分子的心灵并被山西铭贤学校师生诉诸笔端,创作了大量产生于校园却具有极强社会性的文学作品。我们将铭贤师生在铭贤学校中创作的这些文学作品称之为“铭贤校园文学”。
铭贤校园文学作品主要集中收录在《铭贤校刊》《铭贤学报》《铭贤周刊》《铭贤歌集》等学校刊物中。由于历经搬迁、移交、战乱等磨难,部分文献已经散佚,但通过挖掘和审视现存铭贤校园文学作品的具体内容和丰富细节,可以梳理出1924年至抗日战争时期,铭贤学子促进国家、民族、社会的改造和进步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发展脉络。铭贤校园文学真实生动地记录了那个充满变革的时代,拂去历史的尘埃,仍能清晰呈现出山西近代启蒙与救亡的变奏。
一、山鸣谷应,同气相求:铭贤校园文学中“自觉觉人”的呐喊与“救亡图存”的呼吁
1919-1925年间, 以“启蒙”为目的、专注于文化批判的新文化运动与随之而来的以“救亡”为目的、专注于批判旧政权的五四运动相得益彰、互为臂助。与此相一致,铭贤校园文学中“自觉觉人”的启蒙呐喊与“救国图存”的呼吁也呈现出共生共存、山鸣谷应的态势。
虽然山西长期的“半独立”统治状态和两山夹峙的“半封闭”地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进步思想和社会声音的传播,但“启蒙”和“救亡”的暴风骤雨还是穿越娘子关,在三晋大地上洒下觉醒的甘霖。1924-1928年间,面对“新文化新思潮输入娘子关”的喜讯,铭贤学校的“无数健儿,整天的拿着旗帜,大扬特扬的播撒文化种子”,赵春和在《铭贤校刊出世的使命》中明确提出《铭贤校刊》有两大使命:一是作为宣传教育内容、校内新闻,师生讨论研究、交换学识的平台;二是作为宣传启蒙和救亡的阵地,要“藉着一切的著述”“与恶劣的社会宣战”,攻击“有势力的恶魔”“斩断一切魔权”。所谓的“恶魔”“魔权”指的就是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旧政府及其维护的旧权威、帝国主义势力及其控制下的军阀。铭贤校园文学就是要用“启蒙”和“救亡”的思想打破“恶魔”控制下的中国,引导铭贤学子“到光明的路上去”。[2]
(一)“自觉觉人”与“救亡图存”的思想互动
没有启蒙就没有真正的爱国运动。只有民众真正达到个人的觉醒,意识到“我是谁”,意识到并认同自己归属于“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并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关切并努力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民族意识才算真正形成,爱国救亡的思想才得以深入人心;与之相对应,若想救亡图存,必须开启民智,高喊启蒙。启蒙为救亡提供了思想基础,救亡则将启蒙思想传播得更为广泛和深入人心。
在铭贤校园文学中,首先出现了大量宣传启蒙思想的文学作品,体现了青年学生主体意识的萌芽和“人的觉醒”:学子们追求人格独立和理性精神,并显示出掌控人生的强大自信心和主观能动性。他们开始思考:我是谁?我的人生观是什么?我生存的意义何在?……他们摆脱了浑噩懵懂,开始经营个人生活、善于自我反省、有意识地培养良好习惯和高尚人格。王时信《我将来要做甚么》强调未来职业的选择是“个人对自己前途计划的一个问题,里面含着自强与进取”,[3]他们坚信自己有能力、有意志在恶劣的境遇中“创造好的境遇去积极应对”,[4]铭贤学子清晰、理性的分析和计划,清楚揭示了他们在人格独立后,把握人生的热望、超凡的自信和强烈进取心。
在精神层面上获得人格独立后,学子们开始用文学作品宣扬实践层面的个性解放,最突出的就是对传统伦理观的反叛。在校园刊物上,他们大胆地思考和谈论旧式家庭、自由婚姻恋爱、妇女解放等问题,创造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忏悔》的主人公为了摆脱父权的压抑而离家出走:“我对这个必不表示半分的忏悔,因为那是我的自由啊!我的自由是不能为任何人所捐弃的”。[5]短篇小说《林娜》借主人公之口质问“人生婚姻尚且不能自由,在世界上生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呢?”鼓励青年们“竭力的和这恶社会奋争,千万不要没了勇气,屈在这恶势力之下,低头做他们的奴隶。”[6]铭贤学子用极其激烈的笔触反叛着旧礼教旧观念,唤醒其他在封建思想禁锢下的同学。
在独立人格形成的基础上,铭贤学子必然超越单纯的“我”,将视野投向广阔的社会和国家。铭贤学子用觉醒的目光审视中国社会后,发现民众只是“可怜的群盲”,在威权下“(乳犬般地)过着迷蒙混沌的日子……一刹那一刹那地混将去……等到亡国奴的铁索套在脖颈的时候,想还茫然四顾,莫名其妙,即或死了也不晓得什么缘故。”[3]并振聋发聩地提出“若是要革命成功,必须唤醒民众,而唤醒民众的责任……除了我们赤裸裸底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来担负,别人是靠不住的。”[5]如何唤醒民众,拯救被压迫的同胞呢?“自己要做先锋,到农民、工人、士兵中间去,一面宣传自己的主义,并开导他们的知识,一面联络各界青年,组织革命的大本营,实行改造社会。……不可有一步松懈,不要怕别人毁谤,不要怕耻辱和失败,也不要怕穷,尚不要怕死!”[4]正是通过救亡运动认识到“中华存亡的重担在我们肩头上压着”,[8]铭贤学子才更加勉力地传播启蒙思想,唤醒中国民众。从“我们不要做家庭的奴隶,不当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俘虏,并且不做不道德恶习惯的降服者”的呼声中,[4]不难发现“自觉觉人”与“救亡图存”在互相激发中已经交织在一起。
(二)白话文运动与救亡思潮的彼此推动
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白话文之所以能以势如破竹风靡中国,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明白晓畅、文言合一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作为救亡思潮的得力载体,它能渗透进每一个关心民族存亡、国家权益的民众心里。可以说,白话文运动是借着救亡思潮的东风,散入中国的千家万户;与此相对应,正是因为白话文简单明白、抒情说理无往不利,大量政治改革和呼吁救亡的文章被青年学子创作出来,白话文那远远超越文言的鼓动力、号召力和战斗性,使救亡思潮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
救亡运动对白话文的传播的作用。白话文最初在铭贤学校并不受欢迎,最早使用的学生还受到他人“随波逐流”“斯文扫地”的非议和嘲讽。之后白序之、张德生、张方谷等毕业于燕京、清华等高等学府的老师们成为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推崇者和宣传者。据《铭贤中学国文教学的草案》记载,当时白序之的国文课安排给文言文和白话文几乎相等的课时量[4],并将大量白话小说推荐给学生;国文教师张德生积极推介新诗作品、指导新诗创作,在《诗之研究》中推荐大量的新诗参考书,包括王羲和《诗学原理》、胡怀琛《新诗概说》、孙良工《新诗作法讲义》、译林社编《文学论集》、冰心《春水》、焦菊隐《夜哭》、郭沫若译《雪莱诗选》、于庚虞《骷髅上的蔷薇》等,激发了青年学生学习和创作新诗的极大热情[7]……
五四救亡运动的影响,以这样的方式作用于铭贤学校,终于使白话文在铭贤学校得到了认可和欢迎。自此大量白话新诗在校园文学刊物中涌现;《山西铭贤学校出版校刊试行办法》明确表示“不论文言白话一律欢迎”,“凡白话稿件须用新式标点符号”,在此之前,许多文章都不使用标点或只用顿号断句;[2]铭贤新剧团成为铭贤学校成立最早的社团之一……可见救亡运动对于铭贤白话文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白话文对政治救亡运动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铭贤学子的心里,白话文早已与救国事业密不可分。现有的与政治救亡运动相关的铭贤校园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由白话文创作的,尤其是用白话文发表的各种救亡方案。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学子期望青年知识分子能继续用新文学进行思想启蒙达到救亡的目的,呼吁创作“直接或间接唤起革命的思想和精神,增进革命的势力的文学”;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加入共产党的学生,则提出中国国民革命是一场工人阶级领导的、反抗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9]“文学是革命中绝好的推进工具”,只有“表同情于无产阶级、将无产阶级的苦闷实实在在写出来的社会主义写实的”文学才是当下需要的革命文学。[11]
学子们更多的是用白话文创作大量的小说、诗歌、议论文、调查报告,用创作实践宣传反帝救国的思想。例如吕其哲创作的白话长诗《国魂》充分体现了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仇恨:“可恨,可恨,可恨那黄发碧眼的囚毒,我与他结成了千万世不解之冤仇!我莫名她(中华)因何惨遭此绝酷之奇刑!千刀万剐曝露白骨还予她以不容!喂!别怨上帝创造世界待我们不公!只怕我们承受者丧掉自己的魂灵”,[5]具有极强的宣传号召力和鼓动性。
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宣传工具上说,在这个时期,启蒙与救亡在铭贤校园文学中是相互呼应、彼此推动的。在这样的和谐的氛围和开放的心胸中,产生了大量充满朝气和力量、自尊和自信、热情和理想的文学作品。但随着启蒙运动的落潮,校园文学呈现出另一种风貌。
二、豪气已随红血尽,关山云雨梦难归:启蒙运动的落潮和铭贤校园文学中的幻灭、颓废和死亡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威权批判、国民革命中的暴力行为以及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10]使许多学生陷入困惑和沮丧,国民党有技巧的操控和压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政策、内忧外患使他们对国民党的统治深感失望,国民革命时期的激情、理想、自信几乎消磨殆尽,困惑茫然、空虚无聊、悲观无助、绝望沮丧等消极的集体情绪充斥校园,成为近十年校园文学创作的主旋律。铭贤校园文学作品形成了一条从理想的幻灭,到灵魂的颓废,最终到希望以死亡得到解脱的心路历程。
(一)理想的幻灭
1927年以后,当反帝反封建的火焰被大革命失败的结局浇熄,亲身经历了政治和革命过程的青年学生不得不面对革命阵营内的分裂、背叛和残杀。他们抗争过、奋斗过、激昂过,从精神到肉体都在这场变革和斗争中被折磨得疲惫不堪,蓦然回首,社会腐朽依然、国家危亡依然、民众蒙昧依然,他们因徒劳而感到沮丧和悲哀,产生强烈的无意义感和漂泊感:“当年樱花已灰飞,可怜一身无主宰”[7]“豪气已随红血尽,关山云雨梦难归”。[8]翰丞的长诗《英雄梦》从各个角度刻划了青年学子理想的全方位幻灭:“昨夜于伟大的失望里,我从英雄之梦中醒来……曾记得在梦中既呼号且跳跃好似得胜奏凯,梦醒来仍然是携带着满身创伤才为人战败。”[11]
青年们本想用革命的花朵“把全世界的尘浊染变”,最终却只能遍体鳞伤地离开花园,“无目的地跛颠前去”[12]。他们发现理想已经湮灭,“来路已不可寻”,革命的尝试后已经无法回归原来的心境和社会位置;前路亦不可知。他们被卡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尴尬而无助。因为“灵魂深处的痛伤”无法言说,只能感到无尽的孤独,哀叹“茫茫众生,谁是我的知心?”
(二)灵魂的颓废
理想幻灭后,随之而来的是灵魂的颓废。在政治上,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言论控制导致公共政治生活已无自由可言。铭贤学子看到国民党的种种虚伪嘴脸、对日妥协政策、高呼革命口号行背叛革命之实,只能在沉默中消沉颓废。《县党部》《对语》这样的讽刺剧是极微弱的反抗声音。
在经济上,家庭贫困是很多铭贤学子心头的重负,直接导致想求学的青年无法升学:“人生到底是渺茫的……平添了无数的怅惘,他那一缕热情求知欲也随着各样的声音归入与无有之乡”;[9]有的青年为了攒钱继续上学,挣扎在背井离乡困窘尴尬的生活状态下,在与家人分别的痛苦中煎熬:“人生的引诱,社会的驱逼,金钱的魔力啊!竟把孤客从天乐园(家)里驱逐出来”。[8]经济的压力使学子更加狼狈和颓废。
在伦理上,大革命的影响使得许多青年建立了新的道德标准和婚姻爱情观念,不愿再屈服于封建的家长专制,那些不得不在梦醒后回归旧式家庭的青年感到窒息,家庭矛盾一触即发。铭贤学子创作的《血痕》《林娜》《别了》《青年乞丐的自白》等大量文学作品都描写了这种旧家庭中的龃龉、分裂和死亡的悲剧。梁登高《血痕》中,17岁的赵淑媛已经接受了启蒙思想,“明了人生的意义,也感觉到人生的苦闷”,迫于长辈的压力下嫁不爱的人,于新婚之夜将纨绔的新郎用剪刀刺伤后自杀,她的恋人马蔚生家庭困难,高中毕业后就去当工厂经理,听说爱人自杀后跳江殉情而死。[7]无法摆脱的旧家庭、压抑和控制思想的旧伦理,使青年学子陷入无法回避的颓废中。
在文化上,道德沦丧、人心浇薄的负面影响伴随着战乱和死亡而来。铭贤学子深感人类的虚伪和冷漠,感慨“山无情水无情一切皆无情,人和人的心更是冷冰冰”;韩大卫《深秋的无聊》中向肃杀的秋风发出了一系列提问:“为什么吹枯萎了社会的人心,使没有一点的慈爱?为什么吹迫着万物凋谢,宇宙萧条,而却不能打破这恶社会中的种种怨恨与黑幕,吹残着他们的数病与万恶?为什么吹成了遍地荒凉风声四起,而独不能吹散人生的苦闷,使我整日愁恨?”这人生的苦闷很大程度上由于曾经期盼的民风高尚的新社会的理想破灭,呈现在眼前的只是道德堕落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许多学子或选择退隐到爱与自然的温柔乡:“妈妈!世上惟有你是纯粹的爱我,惟有你是不骗我的”;[7]“山外的云,云外的山,皎洁的明月,这些都是我精神上的安慰者”[6];或在宗教中获得安慰和寄托:随着大革命的结束而消歇的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使基督教的影响力有所回升,铭贤学校作为教会学校,本来就有比较浓重的宗教氛围,许多青年在此期间投入宗教的怀抱。除了爱、自然和宗教,能使人解脱的,还有死亡。
(三)死亡的诱惑
理想的幻灭,灵魂的颓废,使“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剧感像吹不散的阴云笼罩在铭贤学子头顶,使他们无数次地幻想用死亡得到人生的平静和解脱。铭贤校园文学中有许多短篇小说生动地刻画了走向死亡的心路历程:树真为了争取“生命的自由”“躲避旧礼教的訾议”,如壮士般“两手舞着锋利的宝剑”冲入人生的战场,希望找到理想中的光明,消除内心一切烦闷。但这种伟大的努力最终宣告完全失败,在“人生悲苦的深渊”和“沉重的黑暗”面前,只能任“失望而畏惧的利刃在我的心板上深深地刻下创痕”,最终在给初恋的绝笔信中留下“曾经的一切都是陈迹,都是梦幻”的“忏悔”后自杀。[5]在忧郁和颓废中,死亡的平静和解脱如此具有诱惑力,它可以使人“告别宇宙的一切”,“与万恶的世界作为永别,不再应酬那狡猾的人类”;学生幻想自己死后躺在充满美丽鲜花的“长方的小木房里”,“那睡眠的面孔上现出了不可思议的笑容”,[7]学生对死亡的渴望可见一斑。
如同郭守谦在《现代青年应有的分析》中总结的:在社会竞争的怒潮中,在悲惨浑浊的社会里,虽然青年“呼啸着以求他们的新生命和征服这无情的障碍的方法”,“但是事实给他们好些大的打击,青年人都从无路可走之叹……到后来不走上颓废悲观自杀的路,就只有走上反抗的一途。”[13]当日寇的铁蹄踏破东北,反抗的精神之火终于燃烧起来。
三、宁为战死鬼,不为倭奴屈:抗日救亡逐渐成为铭贤校园文学的主题
从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占东北到抗日战争结束,在严峻的国家局势和民众的生死存亡面前,思想启蒙的个人主义被充满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色彩的政治救亡需求挤压到非常次要的从属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为政治救亡的思想武器,逐渐受到青年学子们的选择和运用,“阶级斗争的觉悟”最终取代了“伦理觉悟”, 抗日救亡的怒吼掩盖了思想启蒙的呼声,逐渐成为铭贤校园文学的主题,下面就从文学主题的转变、文学理论的更新和文学作品的涌现这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文学主题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震惊了铭贤师生,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瞬间飙升。从《铭贤校刊》的第十卷第一期(1931年11月15日出版)开始,出现大量分析日本国情、中日关系、日本对华政策、日本在华利益、中国政府和民众应如何应对等文章,例如《日本对华政策》《对日本侵略我国的认识和感想》《为什么中国人要研究日本问题》《中国的危机和救国的方法》《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国际联盟的威信失坠后中国应取的步调》《东北铁道问题之研究》《东三省铁路图》等。这些研究文章旨在向青年学子普及相关知识,明确宣告抵抗日本的决定,彻底粉碎“无抵抗主义”的梦想和对国际声援的侥幸期盼,疾呼“在这样恶魔的世界中”没有公理可言,只能“趁着我们的声带未破,趁着我们的热血未干,赶快起来和我们的仇敌,决一死战”,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谋求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12]号召“凡我同胞不论农工商学兵,对于各项事业,均应特加努力,以救危亡。……要振作起精神,努力干去,‘以往譬如昨日死,未来譬如今日生’,与帝国主义者做最后的死战!”[14]在这样的危机意识和政治背景下,铭贤校园文学的主题从幻灭、颓废与死亡,转变为悲壮激昂的抗日救亡。
(二)文学理论的更新
国难当头,文学的启蒙作用、新旧文学的优劣等已经不再是关注和讨论的中心,文学如何在救亡中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成为理论核心。万桢在《多风多雨的时代里,文学应负的使命》中认为,文学是时代的表现与批评,伟大的艺术家们应当凭着丰富的学识、深刻周密的思想刻画人民大众的疾苦,发挥文学的宣传作用,引导全国人民走上救亡的道路。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要求文学反映社会政治运动、思想焦点和民众心态,有鲜明的社会功利性,注意社会宣传效果;文学的情感落脚点不再是个人小天地里的悲欢爱恨而是国家、民族、群众的集体情绪和精神诉求,文艺大众化成为文学理论关注的问题。文学理论的更新,预示着文学向民族意识、集体意识、大众文艺方向的倾斜。
(三)文学作品的涌现
1931年起,铭贤校园文学中表现爱国救亡主题的作品大量涌现,这些作品主要从三个角度表现抗日救亡的情绪:
第一个角度是通过描写祖国的美来抒发对国家的依恋和热爱:“我是一条小鱼,亦是一只小鸟,我爱我的中国,好比是我游泳的池塘,亦是我安息的树枝。假使我的中国被人侵占了,请问何处是我的归家?”[7]“文化灿烂好山河,地大物产博。我们还有四万万的人民,精诚团结共一心。无论祸福,无论荣辱,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民族。”[16]
第二个角度是用亡国灭种的危机号召同胞奋起反抗,背水一战:“不战亦危亡,战兮尚有益;宁为战死鬼,不为倭奴屈”[15];“祖国啊!……我又怎忍做那被压迫之下的亡国奴!……该是你醒的时候了,我准备得有血和泪,只等待你的最后的动员会!我准备冲向前,一直到我死!”[13]这些文学作品鼓励同胞坚毅地走向血与火的战场,立志“牺牲至崇的生命,以我们的鲜血换来我们的自由!”[14]这些富有号召力和战斗激情的文学作品,高扬救亡的旗帜,一扫此前十年颓废萎靡、羸弱彷徨的气质,为鼓舞铭贤学子的抗日精神和救国信念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个角度是将国难与乡愁紧紧结合在一起,唤起同学的救亡激情。抗战爆发,铭贤学校迁至四川省金堂县,南迁途中历尽艰辛,“离故国,别家南去,伤心无极”。国破家亡的辛酸和对侵略者的憎恨无时无刻不燃烧起铭贤师生的抗日救亡的热情:“南来万里已潸然,老母终堂心更酸。国难乡愁萦五内,挑灯怕读蓼莪篇”“三载他乡闻战急,欲随同志复燕幽”。在金堂县远离战火的日子里,乡愁和国难凝结成铭贤师生心底永志不忘的救亡誓言:“回想吾校南来,安心研读,壮志凌云,羽毛丰,万里雄飞歼敌。摹写南迁,请休成绮梦,爱怜家国。一声凯唱,千般奇耻都雪!”[17]
通过这些歌颂祖国、思念家乡、唤起民众的文学作品,铭贤校园文学中的抗日救亡文学大放异彩,救亡的怒吼逐渐淹没启蒙的声音。
四、结语
从20世纪20年代“自觉觉人”的呐喊与“救国图存”的呼吁并存,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启蒙运动落潮期幻灭、颓废和死亡的文学倾向,再到30年代以后救亡文学涌现,现存铭贤校园文学在思想史视域下生动地勾勒出1924年至抗日战争这一时期启蒙与救亡思潮的变奏,对于我们探究铭贤学校的文化思想史、理解山西乃至中国的近代思想史脉络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9.
[2]铭贤校刊编辑部.铭贤校刊[M].太谷:山西铭贤学校,1924(1):4,2.
[3]铭贤校刊编辑部.铭贤校刊[M].太谷:山西铭贤学校,1924(2):13,1,38-43.
[4]铭贤校刊编辑部.铭贤校刊[M].太谷:山西铭贤学校,1925(1):8,8,8,37.
[5]铭贤校刊编辑部.铭贤校刊[M].太谷:山西铭贤学校,1928(1):3,46-49,1,3.
[6]铭贤校刊编辑部.铭贤校刊[M].太谷:山西铭贤学校,1926(1):7,16.
[7]铭贤校刊编辑部.铭贤校刊[M].太谷:山西铭贤学校,1929(5):102,44,22,26,28-36,9-25,36-38,27.
[8]铭贤校刊编辑部.铭贤校刊[M].太谷:山西铭贤学校,1927(1):19,2,41.
[9]铭贤校刊编辑部.铭贤校刊[M].太谷:山西铭贤学校,1927(2):41,1.
[10][美]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31.
[11]铭贤校刊编辑部.铭贤校刊[M].太谷:山西铭贤学校,1930(2):8,4-5.
[12]铭贤校刊编辑部.铭贤校刊[M].太谷:山西铭贤学校,1930(1):49,6.
[13]铭贤校刊编辑部.铭贤校刊[M].太谷:山西铭贤学校,1931(1):1,3.
[14]铭贤校刊编辑部.铭贤校刊[M].太谷:山西铭贤学校,1931(4):3,3.
[15]铭贤校刊编辑部.铭贤校刊[M].太谷:山西铭贤学校,1932(1):6.
[16]信德俭,温永峰,方亮.学以事人,真知力行:山西铭贤学校办学评述[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388.
[17]吴捷三.南迁余韵[J].铭贤周刊,1941(9):6-7.
(编辑:佘小宁)
Contemporary literary of Oberlin-S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 from the horizon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n aspect of the variation of enlightenment and national salvation
He Xuexia,Li Weichao
(CollegeofMarxism,ShanxiAgriculturalUniversity,Taigu030801,China)
As one pioneer in modern education of Shanxi, Oberlin-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 generated its ow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he long term of running the school. In the 1920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enlightenment corresponded to salvation; From late 1920s to early 1930s, disillusionment, decadence and death appeared in the literature in large numbers; During 1930s, salvation literature overwhelmed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The existing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ks vividly outline the variation of enlightenment and national salvation from 1924 to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study still has positive reference value to explore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Oberlin-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 and understa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hanxi in modern times.
Oberlin-S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nlightenment; National salvation
2016-09-15
赫雪侠(1987-),女(汉),山西太原人,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
李卫朝,副教授,E-mail:sxauliweichao2013@163.com
2015年山西农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ZXSK1503);2015年山西农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ZXSK1506)
G529
A
1671-816X(2016)12-09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