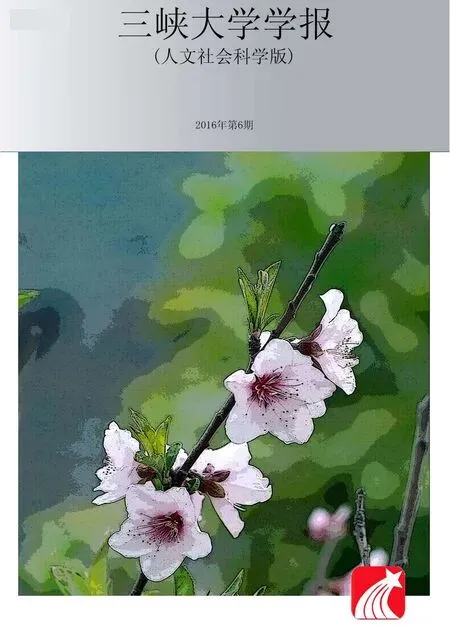论胡宏的天命观及其现代启示
2016-04-04张洪波
张洪波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论胡宏的天命观及其现代启示
张洪波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胡宏是古代少有的成体系的思想家,其心性论及天命论的理论结构前后呼应,是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命-性-心的天命流行的理路与心-性-命的尽性至命的理路统一在其理论体系中,造就了其心性论与天命观的基本特色,即确认人所受之天命即是人的本心本性,客观性的天命与主观性的性命统一在其心性论中,心以成性,当以乾道之刚健不息的性格修养心性,以成就人所受之性命,成就仁义之道,理性以至命,至于贫富穷通则可付之于外在的命运了。
胡宏; 天命观; 命性; 心诚; 中仁
胡宏,字仁仲,崇安人,生于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卒于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是宋室南渡之际理学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著名经学家胡安国的次子,因长期寓居湖南衡山五峰之下,学者称为五峰先生。五峰家学渊源,全祖望对其评价颇高:“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有过于《正蒙》,卒开湖湘学统。”[1]1366号称东南三贤的朱熹、吕祖谦、张木式都深受胡宏的影响。
胡宏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成体系的思想家,其心性论架构是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在心性论基础上成就的天命观天道观既是其组成部分,也是其自然的发展,颇具启发意义。其心性论成就了其天命观天道观,而其天命观天道观也丰富和发展了其心性论,浑然一体,构成了五峰理学思想的基本框架,也决定了他的基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对我们现代社会的人们确立什么样的世界观价值观仍有参考意义。
一、胡宏的心性论
胡宏是古代少有的成体系的思想家,其体系的理论结构是有意识的确立并被反复强调的,应该首先彰显出来,请看《知言》:
胡子曰:诚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为能尽性至命。[2]1
是故诚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动,心妙性情之德。[2]21
天下莫大于心,患在不能推之尔。莫久于性,患在不能顺之耳。莫成于命,患在不能信之耳。[2]25
人尽其心,则可以言仁矣。心穷其理,则可以言性矣。性存其诚,则可以言命矣。[2]26
诚,天命。中,天性。仁,天心。理性以立命(所立之命是个体化的),惟仁者能之。委于命者(尽心尽性以立命,个体性的命不是消极被动地实现的),失天心。失天心者,兴用废。[2]41
“命-性-心”或者“心-性-命”的概念结构非常清楚,且有两条叙述的路线:一条是自上而下的,由命至性至心;一条是自下而上的,由心至性至命。为什么这么区分呢?因为天、人之间天在上,是客观的,人在下,有主观性。“天命为性”是儒家自《中庸》《易传》而来的传统,人之性是由天赋予的,五峰自然继承了儒学、理学的这个传统。这种叙述的方式不是随意的,它当下显露出命、性、心三者的关系。
首先我们注意到《知言》开宗明义开始于自上而下的结构,“诚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2]1这很自然,因为“天命之谓性”是传统观念,大家都接受的,以“命”为开端,却没有说“天命”,这却别有深意,后当自明,不过紧随其后的一条已经透露了其基本意向:“静观万物之理,得吾心之悦也易。动处万物之会,得吾心之乐也难。是故仁智合一,然后君子之学成。”[2]1既要认识天下之理,还要在实践中安守本分,此条之“命”既是天命,也是人所受之命。既是理论的开端也是理论的终点,由始学至大成,其叙述的顺序与理念的逻辑是一贯的。
《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五峰说:“天命为性,人性为心。”[2]4为什么不是“命”而是“天命”呢?因为“命”有二义:第一,天之所命于人者;第二,人因天命所成就者(即人自己之性命或命运,即个人一生之生命活动)。开篇之大纲“诚者,命之道乎”兼有二义,故无“天”字。因为儒者都能接受“天命为性”的观念,何况“天”早已被“二程”人文化了,“天即理”是“二程”兄弟开创的,以之作为理论开端,是对儒学传统的继承。
这只是开端,只是继承了已有的理论成果。张载说:“天授于人为命(自注:亦可谓性),人受于天则为性(自注:亦可谓命)”[3]324。有趣的是,张载的这种区分在五峰这里完全一样,有两个方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由天命而人性,和由人性而至命,人既受之后就有了自己的性命。天之所命与人之所受,似无不同,其区别实则很重要。天命是实实在在的、真实无欺的,是实有,这是“诚”的首要的意义,也是北宋诸子留下来的传统。不只张载有这个观念,周敦颐早说过:“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矣。”[1]482然既受之后又如何呢?儒家没有一个类似于西方的上帝,造了人类之后还要管着人类,儒家的天只是理。五峰是如何规定或者说如何理解阐明人所受之人性的呢?
天之所授是诚实无欺的,人物之所受是既定的,既受之性有什么样的品性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规定性呢?五峰直接给出了性的规定性,即“中者,性之道乎!”中和之道也不是五峰的独创,这是《中庸》的传统,张载和“二程”也讨论中和的问题,程颐以为“中也者,寂然不动之时也”。五峰于伊川之中和说颇不赞成,他在《与曾吉甫三书》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窃谓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故伊川曰‘中者,所以状性之体段’,而不言状心之体段也。心之体段,则圣人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发之时,圣人与众生同一性,已发,则无思无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圣人之所独。夫圣人尽性,故感物而静,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众生不能尽性,故感物而动,然后朋从尔思,而不得其正矣。”[2]115五峰此段所论之意最重要者在于肯定未发之时“圣人与众生同一性”,此是性体,是大本。并且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然而众生虽具同一性,却只是潜在的,是未发,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却不能做到,常发而不中节。
可是为什么以中状性之体段呢?因为万物各足其分:“至哉!吾观天地之神道,其时无衍,赋形万物,无大无细,各足其分,太和保和,变化无穷也。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完具,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辨,不可以是非分,无过也,无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2]332所谓的中既是“在中”之中,即未发之中,也是“中和”之中,是各足其分、各得其所的理想状态。所以又说“中者,道之体,和者,道之用,中和变化,万物各正性命而纯备者,人也,性之极也。故观万物之流形,其性则异,察万物之本性,其源则一。”[2]14所谓“纯备者”,是指“人也者,天地之全也。何以知其全乎?万物有父子之亲焉,有报本反始之礼焉,……然而谓之禽兽而不与人为类,以其不得其全,不可与为类也。人虽备万物之性……”[2]14
性是万事万物的根源,所谓“性立天下之有”,万事万物皆性所有,“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性者,类指一理而言尔,未见天命之全体者也。”这是五峰存在论的基本观念,一切存有、实有皆性所为,它超越了人性论的领域,直接天道。
天地之间一切都是性中所有之事,人伦物理自然也是性中本有之事:“天命不已,故人生无穷。具耳目口鼻而成身,合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而成世,非有假于外而强成之也,是性然矣。圣人明于大伦,理于万物,畅于四肢,达于天地,一以贯之。性外无物,物外无性。是故成己成物,无可而无不可焉。”[1]6仁、义、礼、知等皆是性中本有之物,所谓道义全具焉。性本论既规定了天地万物的存在论秩序,也规定了人性论的伦理道德秩序。理学家们一般未将宇宙的存在论秩序和人生的伦理道德秩序作严格区分。
然而人虽备万物之性,却只是潜在的,要通过本心体现出来,所谓“天命为性,人性为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五峰既以未发为性,已发为心,则性之显现为心,而且性体必须通过本心显现出来:“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尧、舜、禹、汤、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后相绍,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尽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2]328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此“成性”,“是形著之成,而非本无今有之成”[4]369,本心虽可显现本性,可是却往往不得其全,这就需要“尽心”的修养功夫:“天命为性,人性为心,不行己之欲,不用己之知,所以求尽其心也”[1]4。这是孟子的理路,即“尽心则知性,知性则知天”。然而这里的确是由客观性的“天命之谓性”转向主观性的本心,既然性是未发,只能通过已发之心才可显现,那么不管如何强调其作用也不过分。因为只有通过尽心,本性才能现实化:“心无不在,本天道变化,为世俗酬酢,参天地,备万物。人之为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目闻见为己蔽,父子夫妇为己累,衣裘饮食为己欲。既失其本矣,犹皆曰我有知,论事之是非,方人之长短,终不知其陷溺者,悲夫。”[2]331宋儒大体都可以接受从孟子继承而来并加以发展了的良知良能,我们可以称之为本心,即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心体。
这就说到了五峰的修养工夫,其求尽心的思路可以称为先察识后涵养,察识的是本心仁体,即因良心之发现而涵养之:“情一流则难遏,气一动则难平。流而后遏,动而后平,是以难也。察而养之于未流,则不至于用遏矣,察而养之于未动,则不至于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则虽婴于物而不惑,养之有素,则虽激于物而不背。”[2]28牟宗三先生说此是指察养于本心仁体:“就本心仁体说,察是先识仁之体,是察识此本心,是逆觉此仁体。察识同于逆觉,养亦是存养此本心仁体。是则察养唯施于本心仁体也。”[4]367
未发已发之别,起自程颐。程颐以为所谓未发之中是在中之中,其观点是于动中求静,赞成在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是有知觉的,“自古儒者皆言静见天地之心,惟某言动见天地之心”[1]593。五峰欲察识未发之时的本心本性,并养此本心本性,与程颐的说法有别,五峰认为未发之时是没有知觉的,这关乎心性之别。
五峰与彪居正有一段对话:“彪居正问:‘心无穷者也,孟子何以言尽其心?’曰:‘唯仁者能尽其心’。居正问为仁,曰:‘欲为仁,必先识仁之体’。”[2]334又说:“齐王见牛而不忍杀,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间而见者也。一有见焉,操而存之,存而养之,养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与天地同矣。此心在人,其发见之端不同,要在识之而已。”[2]335这种所谓在仁体上下功夫的修养方法,朱熹和张式都不赞同,都持批评态度,朱子认为“初不必使先识仁体也。”[2]335对于是否先识仁体的争论,牟宗三解释为在人欲汩没之中忽有良心之发现,此良心直接显示出仁心之本体。
我们需要追问,何以心之本体是仁呢?所谓“仁者,心之道乎”,他说:“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圣人传心,教天下以仁也。”[2]336从理论上去做证明,这不是儒家学者的长处。心之本体为仁,这只能在修养过程中亲身体验,所以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由天命至本性至本心,这是自上而下的天命流行的过程。而此本性本心必将流行发用,心性之发用的过程就是道或者说天道。“道者,体用之总名。仁,其体,义,其用。合体与用,斯为道矣。”[2]10至此,五峰本体论的基本架构就清楚了,即由天命至本性至本心的天命流行的过程,知道了心性体用的理论框架,不表示就可以成为一个仁人,修养的工夫更加重要,即要有尽性至命的修养工夫,所以修养工夫的逻辑结构是尽心尽性以至于立命。一是天命流行之道,一是尽心知性以至上达天命。
二、理性以立命——胡宏的天命观
理解了五峰心性论的理论架构,就能理解天命流行的过程,或者说天命流行之道,即天道。人所受于天之心性是天命流行之结果,人之心性就是人所受之天命,它是人的现实之命运的基础。
圣人与众人同此心性,“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有害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人以术为伤德也,圣人不弃术;人以忧为非达也,圣人不忘忧;人以怨为非宏也,圣人不释怨。然则何以别于众人乎?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2]334既然众人与圣人具有同样的心性,那么通过修养也能与圣人一样,也能成圣成贤,这就是“理性以立命”的意思,通过心性的修养而成圣成贤,众人的“命”也就可以立起来,可以挺立于世间。人之立命的过程与天命流行的过程是两条路线,即自上而下的天命为性和自下而上的率性为道,一是客观的天之授予的过程,一是主观的修身养性的过程。尽性至命的过程,人之立命的过程,也就是率性为道的过程。虽如此说,天命自上而下的流行与人之心性的修养与实现的过程也不可截然分开。
众人必须修道才可与圣人看齐,这也是众人的命。“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于躯者不见其大;存乎饮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精。诸子百家亿之以意,饰之以辩,传闻袭见,蒙心之言。命之理,性之道,置诸茫昧而已矣。……然则为之奈何?曰在修吾身。”[2]3无需造作,天道本来就在每个人身上,是人人命中本有的,差别只在识与不识、为与不为而已。要理会人所受之命与道,就必须修身。所以“性存其诚,则可以言命矣。”[2]26
然则命之道即是“诚”,“诚者,命之道乎”。天赋予人以本心本性,是天之所命,是诚实无欺的,是实存实有的,这是从客观层面而言的。而人既受之后,诚于自己的心性,诚于修身修道以实现自己的命,这是从主观层面而言的。诚道是主客观统一的范畴。五峰说:“诚,天道也。人心合乎天道,则庶几于诚乎。不知天道,是冥行也。冥行者,不能处己,焉能处物?是故明理居敬,然后诚道得。天道至诚,故无息,人道主敬,所以求合乎天也。”[2]28这是在阐明天道人道之合一,天命至诚,人能至诚则可以合乎天。正因为天命之诚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所以,“道之明也,道之行也,或知之矣,变动不居,进退无常,妙道精义未尝须臾离也。”诚则无息。
理性以立命,或者说尽性以立命,先要知命。知命就要学。“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于天,拘于己,汩于事,诱于物,故无所不用学也。”[2]31如果有人不知自己的心性,也不求知道自己的心性,不修道不修身,不求合乎天道,源于心性之天道是否就不是他的命呢?当然不是,只是不诚于自己的命,不诚于道而已,是冥行而已。
正因天道人道是一体的,所以五峰得出“理性以立命”的结论就是顺理成章的:“诚,天命,中,天性,仁,天心。理性以立命(所立之命是个体化的),惟仁者能之。委于命者(尽心尽性以立命,个体性的命不是消极被动地实现的),失天心。失天心者,兴用废。”[2]41明确地提出了在“天命”之下还有个体化的命,它是修道修身所要挺立之命,要顺应本心本性以挺立此个体化的性命。正面地说,立命是积极的,否则,把万事归于命而不积极努力,不理世事,则人事都将荒废。居于这个立场,他批判佛教说:“释氏定其心而不理其事,故听其言如该通,征其行则颠沛。儒者理于事而心有止,故内不失成己,外不失成物,可以赞化育而与天地参矣。”[2]3
“理性以立命”就是尽性以立命。性处于命与心的中间层次,性成于命,通过尽心而得以实现,由性而心的现实化过程即是尽性,尽心尽性的过程就是人的道德活动过程,此过程即是个体之命的显现,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实现。因此尽性即能至命,且只有尽性才能至命。天命即存在于人性之中,只有尽性才能立命,让自己的生命挺立起来。“本诸身者有性,假诸人者有命。性可必而命不可必,性存则命立。”[2]16现实的命源于心性的客观必然性,必须通过尽性尽心才能把握、才可实现,即正命。而现实的经验层面的命则可以合于天命,也可以不合于天命,外在的命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可以掌握的是源于天命的自己的心性及使自己行为合乎天命,这是立命的真正意义,至于外在的命,则要认命,因为命之不齐:
人固有远迹江湖,念绝于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属于富贵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进。命之在人,分定于天,不可变也。是以君子贵知命,知命,然后信义,惟患积德不足于身,不患取资不足于世。[2]19
个体的经验的命是各不相同的,不可强求,也是强求不来的,是命运之命。儒者似乎也有信命者,“富贵,命也。”[2]48最后归结起来是:“命有穷达,性无加损,尽其性则全命。”[2]48本性是一定的,而人之富贵贫贱却各不相同。胡宏以这种命定论说明尽心尽性之必要性,也是儒家的老传统。从体例上看,《知言》开篇即言“诚者,命之道乎”,至其终结,则说“尽其性则全命”,证明在五峰的思想中,命、天命的观念如何之重要,这个始于命结于命的叙述结构当不是随意的。开篇言命,的确是开端,而终结之处言命,也的确是结论。这个有意识的叙述体例,也可谓是用心良苦吧!
无论如何,先验的天命与经验的天命还是有区别的。所以知命不知命也一样有这个区分。知命不知命当然也有个体化差异:“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一,物之所以万殊也。万物之性,动植、小大、高下,各有分焉,循其性而不以欲乱,则无一物不得其所。”[2]41但这不是人性的差异,而是人与物的差异,当然除了众人与圣人同此心性,其它则可有差别。请看圣人之知命而众人之不知命之别:“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圣人知天命存于身者,渊源无穷,故施于民者溥博无尽,而事功不同也。知之,则于一事功可以尽圣人之蕴。不知,则一事功而已,不足与言圣人也。”[2]9意思是说,圣人因为能知先验之天命,其经验层面的事功也与众人不同,则其经验之命不也与众人有别吗?这样,在对待先验之命与经验之命的态度上自然必须加以区分,知命与不知命也须有这种分别:“察人事之不息,则知天命之流行矣”[2]31此处所言之命显然已指涉外在事功,却也是源自天命,人之事功也是天命的表现,只在知与不知而已。
至于对待先验之命的态度,则是我们对待命的正确态度。“万物不同理,死生不同状,必穷理,然后能一贯也。知生,然后能知死也。人事之不息,天命之无息也。人身在勤,勤则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虽然,勤于道义,则刚健而日新……勤于利欲,则放肆而日殆……”[2]30这种刚健日新的生命意识是儒者所共有,易传之乾道讲君子法天而自强不息,天命或命也被赋予了这种刚健不息的性格。
三、胡宏天命观的现代启示
“本诸身者有性,假诸人者有命”,这是非常精简却历经千古而不变的真理。宋人有很强的生命意识,理学家常常思考生命本身的问题,为自身的生命所困扰,更为世间众生的生命所困扰,我们生命的本性是什么?人们该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呢?我们还能确信,千载之后,生活在越来越纷纷扰扰的世界(五峰该以纷华名之吧),我们知道自己的性命,还能知道如何安身立命吗?
若按五峰的思路反思我们今天的境遇,天赋的良知、内在的本性是否尚在呢?在名利场中摸爬滚打,是否磨灭了仅有的一点良知?也许在偶尔的一闪念中,我们还能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吧?
内与外的区分,为己与为人的理念,性分之内的事与性分之外的事,我们还有这种区分吗?还需要这种区分吗?宋明理学家(不是贬义,穷理尽性不是坏事!)包括五峰要确立的人之心性,在今天不一样了吗?不管何人,若能反躬自省,可能一时真的无法回答,我还知道,我还保有,我还能体会我的本真的性命吗?其实这些问题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反过来说,这种思考也不是西方人所独有的,在海德格尔发现人是被抛弃的存在,因之发出良心的呼唤时,我们是否知道,中国人一直在思考,我们的生命的本性是什么?只是,我们相信天性是仁道,一直在传播仁道的信念,但五峰托名王通的一番对答却发人深省:“或问王通曰:‘子有忧疑乎?’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虽然,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又曰:‘心迹之判别久矣,吾得不二言乎?’或问曰:‘通有二言,何也?’曰:‘仁则知通之言一,不仁则以通言为二。若心与迹判,则是天地万物不相管也,而将何以一天下之动乎?’”[2]25
如果知道自己的心性,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该做什么,顺应自己的心性,以至于尽性知命,那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吧?如果出现了矛盾呢?所做与所说,言行不一,又该如何呢?还是应该尽性知命吧!
所以,当我们逐渐淡忘了自己的本性,偶尔反省一下,反思一下我们作为一个人,究竟从上天那里得到了什么?我们都是上天赋予的存在,我们的心性是上天赋予的,只能在自己被赋予的心性上思考、筹划自己的命运,这是不容置疑的。以五峰等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确立的思考的起点是毫无疑义的,中国人没有走存在主义的理路,不然他们也会成为存在主义者。事实上我们被赋予了仁义的本性,只能在自己已有的本性的基础上思考、生存,我们的命运,积极地说,我们要安身立命,所立之命是我们性分中当有之命,至于偶然的世运,也只能看作是命运吧、世运吧,就不必在意了。
[1] 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66.
[2] 胡 宏.五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 张 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4]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赵秀丽]
2016-01-05
张洪波,男,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B 244
: A
: 1672-6219(2016)06-01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