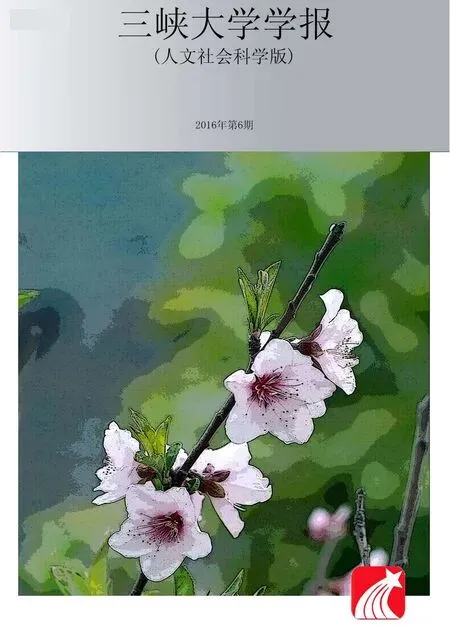刘将孙的“气”论
2016-04-04何跞
何 跞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刘将孙的“气”论
何 跞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元代文人刘将孙的文章中有关于“气”的文论,具体考察之,可以发现刘将孙有着浓厚的养“气”思想,并构成了他的气学文论。刘将孙认为“气”与“道”相生,文章关乎气运,关乎时运,而文气生于文人之气,并且,气有分类。他详细论及“清气”及其内涵,认为诗歌应有“清”气,诗人也需要养气。刘将孙以“气”论文,涉及文学理论中作家、作品、创作,以及文学的外部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因素,主于文学风格和文人人格,是较为完备的“气”学文论。
刘将孙; 气论; 文论; 文学风格; 文人人格
元代初期南方文人刘将孙以诗文称,是庐陵文派的杰出代表,为庐陵三刘(另有刘岳申、刘诜)之首。刘将孙(1257-?)字尚友,号养吾,刘辰翁之子。入元后荐授光泽主簿,曾为延平教官,临汀书院山长,有《养吾斋集》。四库馆臣将是集收入《四库全书》,云“以备文章之一格,亦欧阳修偶思螺蛤之意耳。”[1]则可见其文章风格及文论思想之不同于流俗和正统。陈水根先生说“刘将孙的文章学问对庐陵欧阳守道的文章学问有继承也有创新”[2]。而作为刘辰翁之子,刘将孙的文学思想也不免受其父影响。《养吾斋集》提要云:“辰翁已以文名于宋末,当文体冗滥之余,欲矫以清新幽隽,故所著书多标举纤巧,而所作亦多以诘屈为奇。然蹊径独开,亦遂别自成家,不可磨灭。将孙濡染家学,颇习父风,故当日有小须之目。吴澄为作集序,谓其浩瀚演迤,自成为尚友之文,如苏洵之有苏轼。”曾以立序则谓渊源所自,淹贯千古[3]卷一百六十六《养吾斋集》提要。刘将孙文章中融合苏学和朱学,这是其继承乃父而来的尚性情个性与儒家思想的融合。查洪德先生说“刘将孙哲学思想的叛逆性,其诗文主张的重自我、法自然,决定了他诗文的风格和特点”,且高度评价道:“刘将孙是元初重要的文论家,也是重要的诗文作家。”[4]另外,刘明今、杜鹃《刘辰翁父子与宋元之际江西文坛》论及刘辰翁父子所代表的宋末元初的奇崛个性文风的陆学影响,说“刘辰翁文风最为奇崛恢诡,刘将孙稍稍平畅,然亦恣肆不拘,使人动心骇目”,“刘辰翁、刘将孙等人在宋元之际确实是一有影响的具有异端倾向的诗文流派。”[5]
刘将孙是考察元代庐陵文派异端思想的重要人物,他的文论思想主要集中于其序类文章,这些序多为别人的诗文集子所作。《养吾斋集》共三十二卷,除开前七卷所收诗、词、赋、骚外,后二十五卷皆是文,共243篇,其中序类文章63篇,仅次于记之72篇。具体解读刘将孙的序类文章,可以提炼出刘将孙的文论思想,发现他以“气”论文的特点,并具体涉及到从作家作品到文学创作、文学的外部环境等多个方面,他的“气”论文论还是主于文学风格和文人人格,整个构成了刘将孙较为独特的气论文学思想。关于刘将孙的气论,可参看李璞《复古与养气——论刘将孙对刘辰翁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一文,其中将“气”联系当时社会背景,并与刘辰翁比较,认为刘将孙的“气”更尚中和(“清气,即天地中和之气”)[6]。本文则就刘将孙的“气”论再进行深入挖掘。
一、“气”的本质论:“道”与“气”
在刘将孙的文论中“心”是很重要的一个范畴,他讲求师“心”,说:“道与艺一也,未有得之于心而由师传者,非其至也。传之于人者,无非效人者也,于吾心何有哉?效人者,极于其人,则无以加矣。心不可极,艺亦不可极也。”[7]卷二十二《如心画室记》“心”就是理学讲的心,后来心学加以发展,心学一派认为心是一切的本源,当然一切都得自我心(吾心),也就是此心。心之官则思,心又是一切灵妙之源。“道与艺”一,“艺”就不是具体的“艺”,它与道为一。“道”“艺”本身不可极,而“心”也是无极的,然“艺”“道”这样最高的哲学范畴也需“得之于心”。可以说,“心”是得“道”“艺”的过程,“神”“悟”是这个过程中的具体状态,下面将要论及的“气”则是“道”的普遍赋予和体现。
在刘将孙的文论中,“道”是最高的范畴。“神”且在“道”之下。他说:“吾神遇其趣,而道揽其英”。即以我之“神”(即心灵)捕捉所描画的对象的“趣”,感知、获取并能表现它。从“道”的至高层次上把握并获取对象的真精神,也即形貌之外的英气。“趣”是领悟各种奥妙之后的快感,含有“巧”和顿悟的成分,尚且处于思维表层的快感。而“英”乃是精华,是思维的精髓。“趣”是以“神”领悟所得,“悟”的过程本身含有趣味性,刘将孙所说的“遇”其实就是神悟的过程,所以说“神遇其趣”。而个中真正的精髓英华,则必然以“道”得之,所以是“道揽其英”。“神遇其趣”是外在形式,是过程,而“道揽其英”是内容,是目的,也是宇宙中终极不变的规律,在文学中则是文章之道。
道之下是气,气是道的具体外化和实行,因是否遵循了道以及遵循了道的不同方面而不同。在由上论诸多范畴所构成的刘将孙的文论体系中,由“道”而生的是“清气”,这就是他的气本论。他说:“天地间清气,为六月风,为腊前雪。于植物为梅,于人为仙,于千载为文章,于文章为诗。冰霜非不高洁,然刻厉不足玩;花柳非不明媚,而终近妇儿。兹清气者,若不必有而必不可无。”[7]卷十一《彭宏济诗序》由道而生“气”,天地间诸“气”,“清气”是正面的代表,体现于万事万物。因为“气”大而无处不在,虽然不能直接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它对万事万物的影响却存在着,所以“若不必有而必不可无”。在刘将孙的视域观照中,“清气”赋于不同的节令、物、人、文章,赋于不同的现象中,而形成为大自然中各种不同的事物,如风、雪、梅、仙、文、诗。它们赋形不同,但都具有“清气”的特性,体现着精华和致美,具体说比如高洁、明媚等美好特质,但又不能带有刻厉、俗媚这样一些不好的特质。这些代表了刘将孙所认可的正确的文学之道,也是其所提倡的文章风格。
古代的文学理论较多使用“气”,而这个范畴的定义和内涵在不同的文论家那里又不尽相同。很多人都喜欢用“气”这个概念,其实主要是用一种具体的物事,以其充盈、阔大、无所不在、无形无迹的特征来概括某个不好描述的抽象范畴,实际上还是用有形的实物来比拟无形的理念,比如某种风格、精神、思维、趋向,这是中国古代感性形象思维和阐述方式下的典型产物。
刘将孙的诗文主张继承刘辰翁和赵文而来,更注重性情在文学中的作用,更深地走向文学感悟,在神悟中师心求道,又不断地强调性情的真实和个性。这些都体现出江西庐陵文派的整体特色,即不随波逐流,追求真实、个性和高雅不凡。
二、文章关乎“气运”
刘将孙认为文章的好坏与时代气运密切相关,且对自己所处之元初海宇混一的时代气象有着一种自豪感。《天下同文集序》举例盛世文学如汉初文章、盛唐诗歌、北宋词。在时代气运和混一的眼光考虑下,他认为盛唐苏颋、张悦的“燕、许大手笔”比中唐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更好。他说:
唐之盛时在贞观、开元间,其时称欧、虞、禇、薛,最后称燕、许大手笔,今其文可睹也。至贞元、元和来,以韩、柳著,比至德为盛,而去混一之初,则有间矣……
呜呼!文章岂独可以观气运,亦可以论人物。予每读汉初论议、盛唐词章,及东京诸老文字,三千年间,混一盛时,仅此耳。彼乍合蹔聚者,其萎弱散碎,固不得与于斯也!然此盛时,作者如浑河厚岳,不假风月为状;如偃松曲柏,不与花卉争妍。风气开而文采盛,文采极而光景消。梦得之言之也,不自知其盛者已及于极也。
方今文治,方张混一之盛,乂开辟所未尝有。唐盖不足为盛。搢绅先生,创自为家,述各为体,功德编摩,与诗书相表里,下逮衢谣,亦各有烝民立极之学问。[7]卷九《天下同文集序》
他认为时代气运对文人有很大的影响,盛世文人有着不同的心胸气象,“如浑河厚岳,不假风月为状;如偃松曲柏,不与花卉争妍”。盛世开一代之风气,也长文人之心气,使得盛世文章大盛。而随着一个朝代的逐渐衰退,文学也随之式微。也就是刘将孙所说的“风气开而文采盛,文采极而光景消”。
文章的振兴和文人的心胸气象有赖于朝代的“混一”,也即一个朝代开始的大一统、稳定、和平的社会局面,且随时代的衰退而气象渐褪和减弱。这是刘将孙文论的社会历史视角,有些独特,因为他关注于一个大一统朝代的开端和统一,这与以往人们关注于朝代的中期又不一样。他的这种视角,其实是因他自己所处元代初期,受到海宇混一的时代气象影响和感染而生,可以说是元初的社会大气象影响及于文人心态而产生的一种自信、雄大气象,或者说是元人的时代自信与自豪感的自然流露。
三、文气与文人之气
刘将孙主文气论,在《谭村西诗文序》明确地表示:“予亦于气为主之”[7]卷十《谭村西诗文序》。然而他所论的“气”与孟子的“浩然之气”,韩愈文论中的“气”又不完全相同。他不将“气”看作一种外己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个人内在有所“主”而产生的现象和效果。
刘将孙所论的“气”比以往文论家所论的“气”具有更广泛的意涵。首先,它是一种强盛的气。刘将孙强调大“气”的“浩然”、“充满”、盛大的特色,但与其说“大”,不如说“盛”,更不如说是所“主”之“强”。
另外,它也不是一味的大气,浩然气,不局限于一种、一类“气”,而是有各种各类,能大能小,能“古”能“时”。刘将孙不认为时文、才情小文,如短小的律诗、绝句,以及以骈俪工整为尚的回文骈文就无“气”。他认为写得好的律绝、骈文,其中也有浩然盛“气”。
反映在文章风格上,则是能作庙堂金石声,能体现为才情声歌,能有古风古味,也能够新鲜。所以诗文中两种看似不相融合甚至相反的风格,往往能同时并存于一种文体中。于书记序志,可以既浩荡奇伟又节制严密;于杂著诸赋,可以既古雅磅礴又优游含蓄;于诗文,则既可精整磊落,属对工巧,又可以寄兴深远。这也反映在各种文章体裁、各种不同风格的文章样式上,凡能有所“主”而文气充沛,则古文、律绝、回文、骈文皆并善不悖,而不会出现互不相容的情况。
而真正内在有所“主”的文人,往往都有大文“气”,有大才。而那些能文不能诗,只能以一种风格和一种体裁为文的人,则是内在所“主”弱而“气”衰使然,不能称为大才。这在《谭村西诗文序》中说得十分明白:
文以气为主,非主于气也,乃其中有所主,则其气浩然流动充满,而无不达遂,若气为之主耳。故文之盛也,如风雨骤至,山川草木皆为之变;如江河浩渺,波涛平骇各一其势。大之而金石制作,歌明堂而颂清庙;小之而才情婉娈,清白雪而艳阳春;古之而鼎彝幼渺,陈淳风而追泰古;时之而花柳明媚,过前川而学少年。故昌黎之古文,其小律小绝,无不精妙。东坡之大才,其回文丽句,各极体裁。或有谓能文不能诗,能诗不能文者,皆其主弱而气易衰也。
茶陵村西谭明望寄予以其文若诗。其书记序志,浩荡奇伟之中,有节制严密之意。杂著诸赋,在古雅磅礴之外,得优游含蓄之思。诗文精整,磊落属对,巧而寄兴远。凡其翩翩迈往,而截截畅达者,岂非其得所主耶。[7]卷十《谭村西诗文序》
刘将孙在《跖肋集序》中也谈到这个问题:“诸大家固有难言者,如昌黎、东坡真以文为诗者,而小律短绝,回文近体,往往精绝。后山、简斋,诗律严密,而七言古体,终似微欠。”[7]卷十《跖肋集序》其实不难理解,韩愈、苏轼为大才气强;而陈师道、陈与义则才稍逊而气稍弱,因而不能兼善。
总之,在刘将孙看来,好的诗文,不管哪种风格和体裁,必然是“气”盛之作,也就是“主”强之作。不是客体的“气”主于文章,而是作者内在本心所有的强烈的“主”心,发而为文,使其如有“气”主于文章。刘将孙的文气论,将孟子、韩愈以来的文气论推进了一步,更深入地触及到文气的实质,即作者内在本心。这已经打破了以往以气论文的神秘性和不可解,打破了文气论的客观唯心设定,而走向文气的主观生成原理,使得人们更清楚文气。
刘将孙将文气论引向个体的主观本心,强调作者的本心和才情,这更触及到了文学生成的实质,因而在当时是一种正确而先进的文学创作理论。不把文学之“气”看作高妙玄渺,难以企及的客体存在,而是个人本心的生成,这就使得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有了实际的努力方向,对指导文人创作有了实际的启迪意义。另外,由于他将文气的表现和效果推广而及于律、绝、骈文、时文等各种风格的文体,因而推进了文气论所能涵括的范围,使其具有了更普遍的定义,能更广泛地论证和理解各种风格的文体。
刘将孙这种文气理论,也跟他自己作为庐陵文人,重视个体,崇尚个性自由,而且具有个性的思想有关。刘将孙的文气论显然有别于以往的文气论,具有个性特出的新异因子,彰显了刘将孙在文论上的的个性特点。另外,这也跟刘将孙受理学影响有关。宋代程朱理学讲求心、理、气,将佛家、道家的思维方式引入儒家思想中,其特点之一就是注重人的内在本心。刘将孙生活在元初,其时理学仍是文士圈子中影响重大的学术思想,文人不可能不知理学,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理学影响,何况刘将孙及其父刘辰翁都以儒学称。理学的重个体本心,使得刘将孙将文气引入本心论,只是他在这篇《谭村西诗文序》中并没有拈出“本心”二字,而是说“其中有所主”,以“主”字代替并进行论述。但他所言的“主”,已经是在文体和作者本心意义层面上的“主”。
插言一点,刘将孙的“气”论也影响到他的诗歌风格论。虽然刘将孙的诗学观念整体上是通达的,兼融并取各种诗风。然从他评他人诗歌的眼光和他的着眼点,以及他自己的诗歌风格,还是可以看出,他更偏尚大气流丽的诗风。这也与他的文“气”论有关。他评高绀泉的诗“玄本从霶霈入,初见来贽二篇,关渉宏阔,俛仰有态。先君须溪先生即援笔,点如雨。和诗深致其意,自是从容。”[7]卷十《髙绀泉诗序》诗歌语势的磅礴充沛,内容宏阔,而又能悠游从容道来,这是刘将孙所欣赏的诗风。其内在还是有充沛的“气”作基础,才能有这样的诗风表现。
四、气的分类:“清气”及其内涵
刘将孙看到诗文和学习诗文的本末,本者为得于作者真情性的“清气”,末者为外化表现的各种风格,如“简远”“低黯”“古雅”“怪奇”“优柔”“轻盈”等。并且认为诗文的语言乃浮于外在的辞华,是末;而诗歌和诗人自己内在的神、心、意、气才是本。《彭宏济诗序》作如下论:
天地间清气,为六月风,为腊前雪,于植物为梅,于人为仙,于千载为文章,于文章为诗。冰霜非不高洁,然刻厉不足玩;花柳岂不明媚,而终近妇儿。兹清气者,若不必有,而必不可无。
自风雅来三千年于此,无日无诗,无世无诗。或得之简远,或得之低黯,或得之古雅,或得之怪奇,或得之优柔,或得之轻盈。往往无清意,则不足以名世,夫固各有当也。而后出者,顾规规然效之于其貌焉耳,而曰吾自学为某家,不亦驰骋于末流,而诗无本矣乎。清以气,气岂可揠而学,揽而蓄哉。目之于视,口之于言,耳之于听,类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有得于情性者,亦如是而已。夫言亦孰非浮辞哉。惟发之真者不冺,惟遇之神者必传,惟悠然得于人心者必传而不朽。彼求之物而不求之意,炼于辞而不炼于气,何如其远也。[7]卷十《彭宏济诗序》
在刘将孙看来,后学者总是规模前人诗文的外在风格,以自学某家而标举自己的问学途径和好尚,这是舍本逐末。学者应该锻炼自己内在的“清气”,这才是得其本。
“清气”的得来首先需要“真”情性。“气”不可学,而“清气”亦不可学,只可以“揽而蓄”之。蓄“清气”,则要养于人的情性。而文学创作中,怎样才能使文章发于情性,而赋“清气”?刘将孙认为需要发之真,遇之神,悠然得于人心。这其实就是要求书写作者内心真实情感,呈露作者本真的性情;并且不强力为诗,而是以自然的灵感意到进行创作。这种不矫揉造作和不苦心勉力为诗的创作状态,其实也指向了创作的求真要求,自然而不刻意的创作亦是对于创作过程本身的求真。总之是不求之外物,而求之作者自己之意,不炼于外在的语辞而重视内在的养气,并且在创作过程中也自始至终保持遵循自心和情性的求真态度。不模拟他者、求于自心情性、自然神遇得之于心的创作,这些都是“清气”的要求,其实都体现了一个“真”字。所以,“清”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尚真”。
作为直接抒情言志的诗歌,其重要特点之一便是“真”。所以在诗与文的区别上,刘将孙还是偏向于诗,认为诗为文章之赋“清”气者。而诗之所以较之文更有“清”的特性,是因为诗的本质便是抒情言志,是对作者真实内心的呈露,而文则还有叙事、议论的功能要求,所以在刘将孙看来,诗较文更有“清”气,诗是文章中赋清气者。
另外,“清”气实际是被赋上了人格内涵的,是一种高级的精神象征,是对高尚与美好的普遍泛称。虽然刘将孙举“六月风”“腊前雪”“梅”等物,但这些外物实际也被赋上人格内涵,而具有“清”的魅力,因而是一种精神的代表。“清”其实是对具有自我持重意义、超离凡俗、高雅人格精神的形容。
正是因为它的高雅超凡和持重自我特性,赋有清气的人或物,都显得比不赋清气者更高、更美,表现为一种高层次、高境界的审美定位和价值定位,而被众人所追求。所以刘将孙所论的“清”,对“清”气的追求,也可以说是对于更高审美的追求,以现代的评判笼统说来,就是更“好”。所以刘将孙说“往往无清意,则不足以名世”,其实就是诗歌不好不高,就难以传世,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只不过被古代的文人,像刘将孙等,以中国古代的思维范畴和话语方式,更加玄虚化了而已。
五、诗歌的“清”气和诗人的养气
气有清浊,刘将孙认为诗是负清气之物,而刘将孙所言“清”的内涵,是标举自我和个性,特立不俗。刘将孙认为诗负清气,如鹤,诗歌语言“矫矫”如鹤鸣九皋,不以媚俗听,而是以闻于天听。他将诗歌视为出尘脱俗之物,同时也透露出他自己在思想上的特立和不凡。《九皋诗集序》说:
物之负清气,出乎其类者如此。人声之精者为言,言之又精者为诗,使其翩翩也皆如鹤,其诗之矫矫也如其鸣于九皋,将人欲闻而不可得闻。诗至是始可言趣耳。夫诗者,所以自乐吾之性情也,而岂观美自鬻之技哉。欣悲感发,得之油然者有浅深,而写之适然者有浓淡,志尚高则必不可凡,世味薄则必不可俗。故渊明之冲寂,苏州之简素,昌黎之奇畅,欧之清远,苏黄之神变,彼其养于气者,落落相望,皆如嵇延祖之轩轩于鸡群。宜其超然尘埃混浊之外。非复喧啾之所可匹侪。凡学诗者,必不可以无此意也。[7]卷十《九皋诗集序》
诗歌之所以“清”,是因为它要求诗人“自乐吾之性情”,而不是“观美自鬻之技”。这里实际上是关于艺术究竟适“我”还是适“他”的问题。当然,真艺术必然深入艺术家自我的内心,艺术本是艺术家的心灵产物,艺术之真当然必须由艺术家自心所生成,而不能是有其他干扰,以取悦他人。所以,诗人当然也必须注重诗人自我,必须随自己的感发而写。这里就触及到了艺术的对艺术家的心灵要求。“养于气”,实际上是持养诗人的个性人格,这种人格里面有着深入自我个体心灵的要求,真正好的艺术都有心灵求真的要求。而在诗人深入真实的自我内心,呈现毫无杂质的纯净艺术的同时,也就决定了他对外界凡俗世界和不纯因素的排斥,而且在内向排外的心灵体悟和呈现中,他必然走向单一、专一,不免有点清高自负的感觉,并在专一和纯净的艺术追求中不免于孤独,而又在孤独中找寻着童谣纯净的艺术知音,所以是“宜其超然尘埃混浊之外”。这就如同鹤鸣九皋,以闻天听。
刘将孙认为诗有“清”气,乃因诗人之有养于“清”气。而他所言的“清”,实则是对诗人个性自我的重视,对诗人人格魅力的要求,对艺术求真和深入心灵的要求,整体而言就是对艺术求真和审美的高标准和绝对化要求。其真善美的艺术标准,也即“清”气的要求无不体现了刘将孙自己作为一个达到很高水平的文人的自我矜重(这种矜重也是许多文人所共有的人性特点),其论调中也不无庐陵文人所特有的张扬个性和崇尚真性情的色彩。
[1] 纪 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陈水根.凤林书院词人赵文刘辰翁刘将孙的交往与唱和[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03.
[3] 纪 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 查洪德.刘将孙的诗文成就[J].文学遗产,2004(2):70.
[5] 刘明今,杜 鹃.刘辰翁父子与宋元之际江西文坛[J].文学遗产,2005(4).
[6] 李 璞.复古与养气——论刘将孙对刘辰翁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M]//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六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126.
[7] 刘将孙.养吾斋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杨 勇]
2016-05-16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与理学视阈下的元代文学性情论略”(16WXB009)。
何 跞,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I 206.22
: A
: 1672-6219(2016)06-00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