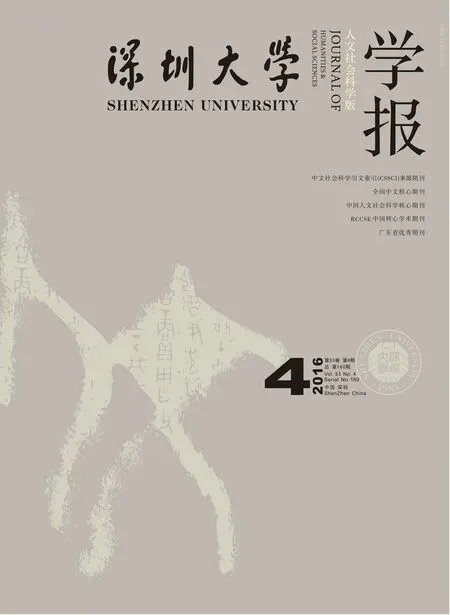五四前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西化派挑战的回应
2016-04-04朱庆跃
朱庆跃
(1.淮北师范大学信息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2.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上海 200234)
五四前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西化派挑战的回应
朱庆跃1,2
(1.淮北师范大学信息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2.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上海 200234)
应对不同时期、阶段其他社会思潮的挑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必须要破解的问题情境之一。以五四前后为例,面对西化派的挑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多方面给予了积极性回应,如在历史观上,用唯物史观回应了西化派的历史进化论和文化决定论,初步回答了当时中国问题及其产生根源是什么的问题;在自由观上,用社会主义自由观回应了西化派资产阶级自由观,初步回答了当时中国问题如何解决以及向何处去的问题;在真理观上,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回应了西化派实用主义真理观,初步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在文化观上,用中西文化融合创新的观点回应了西化派的文化整体观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初步回答了中西文化如何处理以及是否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这些回应,既向当时的民众旗帜鲜明地传递了解决中国问题(包括中西文化的处理、社会意识形态格局的构建等方面)需要马克思主义以及它具有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和品质这样的信息;也在客观上为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种间接的警醒,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帆风顺、一劳永逸的。
五四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挑战;回应
五四运动前后,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以及对西化思潮的反思,从西化派逐渐分离出一批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思想主张,不仅遭到了以东方文化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攻击,也遇到了之前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盟友”——西化派的挑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情境来看,当时西化派的挑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间接而根本性的挑战,即就中国问题及其产生根源是什么、如何解决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等方面,提出了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迥然不同的思想主张、设计方案;二是直接性的挑战,公开质疑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和实践真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格局构建中的指导性地位。面对这些挑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采取迁就避让或置之不理的态度,相反从多方面给予了积极性回应。为此,通过考察和分析五四前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回应西化派挑战这段历史,将有助于科学地把握、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实质和相关规律,也能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展开提供一些启示性思考。
一、在历史观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用唯物史观回应了西化派的历史进化论和文化决定论,初步回答了当时中国问题及其产生根源是什么的问题
历史观特别是现代历史观,除了相较于历史意识而言具有高度抽象概括性特征之外,还具有浓厚的现实政治性特征。“人们之所以要对历史进行这种宏观认识,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探求纯学术的欲望,而是为了表达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看法。”[1]从近现代中国历史来看,先进的中国人为了论证自己救国方案的科学合法性,总会以一定的历史观为依据,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西化派也不例外。在当时中国问题及其产生根源是什么的问题上,他们以历史进化论和文化决定论来论证“西化”方案替代复古方案和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的所谓合理逻辑性和现实正当性。客观地讲,西化派的这一历史观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发挥了积极作用,推进了近代先进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进程。但五四前后他们并没有以这一历史观作为思想过渡的中介而进入到唯物史观层面,相反依然固守并以其来抵制和批判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明显阻滞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将近代中国引入健康轨道的进程。考察五四前后西化派相关思想言论,他们的历史观所遵循的逻辑依然在于认为竞争推动人类社会的进化,中国的文化比西方文化落后,要免于被淘汰务,必摆脱传统的限制而学习西方的文化[2](P101);同样,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出在思想文化方面,解决中国问题根本上也有赖于思想文化问题的解决[2](P122)。如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认为,当前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受旧法律、道德和宗教的压迫摧残而致使个人毫无个性和独立的人格,指出要促进社会的健康惟有大量的 “白血轮分子”发扬 “白血轮精神”[3](P154)。傅斯年强调中国社会出现如此之多的“蚩蚩之氓”,就在于“若干恶劣习俗”,而这些恶劣习俗最集中体现于人生观上无责任心却流行“左道”的人生观念,即“都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都是拿个人的幻想,或一时压迫出来的变态,误当作人生究境”[4]。1923年丁文江在燕京大学的讲演中也明确指出,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5]。蒋梦麟则突出了人格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进化社会有三个条件,即“社会所储蓄之文明,能日日加增也”;“社会之度量,能包容新思想也”;“大多数之人民,能享文化之权利”。为此需要开展进化社会的人格教育,以促进个人负此三种责任的能力[6]。可见,五四前后西化派这一线性文化进化论的历史观,既消解了近代中国遭受屈辱就在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略这一根本原因,亦遮蔽了导致近代中国自身文化滞后的经济层面这一根本因素;更是阻碍了以唯物史观为先导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启蒙进程,间接否定了唯物史观指导下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为路径来改造中国实践的现实正当性。
针对西化派在历史观上所持的历史进化论和文化决定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武器,进行了较为理性的回应,既批判了他们相关主张的非科学性,也就当时中国问题及其产生根源是什么提出了较为正确的判断。主要体现为:一是从狭义而不是广义层面对“文化”进行了界定,凸显了文化决定论的唯心主义本质。如除之前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强调文化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7]之外,1921年陈独秀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中再次指出,文化运动的内容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8](P81)。这种从精神或观念层面对“文化”所进行的狭义式理解,有助于揭露西化派将物质、政治等混杂在文化里面以企图遮蔽文化决定论这一唯心主义本质的阴谋[9]。二是比较了历史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特点,特别是揭示了历史进化论的弊端。如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中肯定了达尔文理论在道德本质阐释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指出其在解释道德的历史变迁方面则明显处于空白,而了解这方面惟有“要用马克思一派的唯物史观了”[8](P199)。同样邓中夏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认为,“科学方法派”(即西化派)相对于东方文化派而言固然是“真新的,科学的”,而较“唯物史观派”其却在宇宙观上是单纯的自然科学的以及在人生观上又是机械论的[10](P173-174)。除上述两个方面对西化派历史观给予批判性的“破”之外,这一期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注重于“立”,即自觉地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对当时中国问题及其产生根源是什么的分析上,并获得了一些较为科学的认识。如1921年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1];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1922年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中他认为劳工的生存权和劳动权是目前中国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而瞿秋白的《饿乡纪程》(1920年)、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等文,则直接将中国当时国情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将受列强及军阀压迫的劳动人民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尽管这一期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当时中国问题产生根源的认识还不完全成熟,但较西化派相关主张而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着重经济层面的分析,至少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点,并为问题的破解提供了正确的切入点。
二、在自由观上,用社会主义自由观回应了西化派的资产阶级自由观,初步回答了当时中国问题如何解决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自由”一定程度上内蕴从某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之意。追求自由本身就是人的特性,对于自由的获取也是“人类全部活动的最高目的”[12](P1)。联系到近现代中国国情下不同阶级、阶层、群体乃至个体的自由观和他们所持的历史观一样,在具有高度抽象概括性之外也还具有浓厚的现实政治性特征,表达了他们期望从所受到的中国现实问题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去争取和追求在他们看来较为科学理性的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生存发展空间。这无论科学与否,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当时中国问题如何解决以及向何处去的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争取社会关系、社会联系、社会交往中的自觉和自由,是不同时代先进代表追求的理想。人类社会交往、社会活动中的自觉、主动、自由问题,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家、理论家探讨和论证的深层课题。”[12](P7-8)五四前后针对当时中国问题如何解决以及向何处去的问题,西化派以西方资产阶级自由观为理论武器,设计出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截然对立的方案,即主张由具体问题式的渐进性解决之道来首先实现个人思想意志和伦理道德的自由。如胡适、高一涵等人以线性文化进化论从思想文化层面对当时中国问题及其产生根源分析后指出,实现个人思想意志和伦理道德方面的自由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在 《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就强调社会要有生机活力就必须发展人的个性,即“使个人有自由意志”[3](P153);明确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就是要大力倡导一种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的 “为我主义”[3](P152)。1920年在《罗素的社会哲学》一文中,高一涵评价罗素的社会政治制度最根本特点在于 “使个个人都能自由去发展他创造的冲动”,并把这种自由看成是获得政治、经济条件的“最适用的物事”[13]。而对于如何实现这种个人思想意志和伦理道德的自由,胡适、高一涵等人受英美“内在的”现代立国路径(即“立国事业是在既有的社会秩序内进行的,是社会自己为自己立国”[14])的影响,提出了具体问题式的渐进性解决之道,并且构建了 “好政府”这一自由社会的形态轮廓。如在1922年《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胡适从消极性和积极性两个方面对“好政府”进行了描述,即一方面它能够通过设置相应的权力监督机构保障消极性自由的实现;另一方面在于通过构建群众参与权力运行平台促进积极性自由的实现[3](P671)。
针对西化派在自由观上所鼓吹的资产阶级自由理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用社会主义自由观给予了应战,毕竟这关系到当时中国问题如何解决以及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重点就社会主义自由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走实现社会主义自由这一道路,以及如何达到社会主义自由的目标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论述与探讨。具体表现为:其一,就社会主义自由的内涵是什么方面,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初步认识到它是以纯正的平民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经济自由为核心的具体而全面的自由,是民主和平等的有机统一。这点以当时的李大钊相关阐释最具代表性。如对于社会主义自由的理论基础,李大钊强调就是纯正的平民主义,因为它实现了“自由”内涵的真实性和其外延的广泛彻底性,是对过去自由主义精华的浓缩和提升,特别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消除了特权现象和行为,真正实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了人民[15]。以经济自由为核心的具体而全面的自由,李大钊明确指出“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16](P21)、“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16](P142)。坚持民主和平等的有机统一,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自由的精神就是使每个人都获得一个均等的机会,从而发展自己的个性[17]。其二,就为什么要选择走实现社会主义自由这一道路方面,除从理论层面探讨社会主义自由相较资本主义自由的优点,以及展望实现社会主义自由的美好前景之外,更多地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特别是经济状况进行了剖析。从总体来看,这一期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当时中国虽然未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但业已深受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影响,再加上原有封建剥削制度的存在,致使中国民众处于资本特权和封建特权的双重压制下,在这样情境下只能走实现社会主义自由之路。如陈独秀在《复东荪先生底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中国劳动者过着非人的生活,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8](P75)。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中,李大钊强调相较欧美资本主义的民众而言,当时中国民众所受资本剥削、压迫程度更加厉害[8](P219)。其三,就如何达到社会主义自由的目标方面,大力倡导“主义式的外在根本解决”之道,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社会革命。如陈独秀认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打碎旧的政治法律制度并建立维护劳动阶级利益的新的国家政权[8](P65);李大钊强调不以马克思派的阶级竞争说作工具,那么经济上的革命就无从谈起[8](P194)。另外,对这一期间西化派改良性方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进行了直接批判。如对于鼓吹发展实业这一温情方案,李达认为其“并不是铲除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指出要消除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两个社会万恶的根源,唯有采取“治病而复于健康的药”——社会主义运动,相反如果制造了资本主义再行社会政策则会使民众陷入水火之中并延长其痛苦[8](P716)。而对于主张走议会道路的,陈独秀批判其只能是“与虎谋皮”,因为议会制度本身就是 “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底财政而设立的”[10](P13)。
三、在真理观上,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回应了西化派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初步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
在真理观问题上,五四前后的西化派深受詹姆士、杜威等西方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影响,突出强调了真理的主观性、相对性以及注重工具价值这一真理性标准等。这一期间以胡适为代表,在真理的主观性方面,他认为“纯粹物观的真理”是不存在,只有“历史的真理论”,这种真理论就是强调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3](P303);在真理的相对性方面,指出“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真理是否能够存在与变化取决于其“发生的效果”[3](P293),要求对待主义、真理务必“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以及做到“三不可”,即“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不可用作蒙蔽聪明”[18];在检验、判断真理的真伪方面,提出了效用标准,“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3](P303)。不可否认,胡适实用主义真理观因含有崇尚实验和理性的怀疑主义精神,以及关注科技知识、工具理性等因素,从而促进了人们从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等旧思想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推进了人们对近现代科技的学习与追求[19]。但是,当五四前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希冀将救国救民之路引入健康、正确轨道时,西化派却以这一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作为攻击武器,直接掀起了质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其在中国实践的现实正当性的狂潮,其中“问题与主义之争”最为典型。依然以胡适为例,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一方面,以真理的主观性、相对性特征为依据,批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正当性。他强调真理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是“应时势而起的”,而中国的具体时势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势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传播马克思主义就是毫无用处的“汤头歌诀”[3](P172)。同时,他也指出真理包括社会主义等在内都不具有抽象绝对性,如果过分强调这点,则会具有招摇撞骗之感和体现“畏难求易”的心理。另一方面,以检验、判断真理的效用标准为根据,质疑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真理性。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胡适虽然肯定了唯物史观的功用价值,但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说则给予了指责乃至否定,认为它过多地“使历史上演出许多不须有的悲惨剧”[3](P177)。
针对西化派在真理观上所发动的直接式挑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回避,而是积极地回应。这种回应总体上表现为揭示了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局限性,阐释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以及唯物史观的真理性。具体来说:其一,揭示了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局限性。如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文中,瞿秋白批判了实用主义真理观只承认真理的主观性、相对性一面,而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一面。“实验主义首先便否认理论的真实性,而只看重实用方面,——‘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可是这一个原则,却亦没有抽象的价值。他的应用亦是因时因地而异其性质的。”[10](P408)同时,他也批判了其在判断真理的标准上只注重实际效用标准,而忽视理论内在真实性标准。通过对实用主义真理观内容的分析,瞿秋白将其本质归结为是唯心主义多元论。其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科学内容。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强调真理必须具有理论的科学指导价值和实际的变革价值的统一性。“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8](P190)依然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文中,瞿秋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不同于实用主义真理观,它注重“科学的真理,而非利益的真理”[10](P413),以及强调真理的内容本身具有客观绝对性而不会因人的主观意志的改变而改变[10](P413-414)。其三,重点从知识真理和实践真理两个方面论证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如知识真理性层面: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文中,蔡和森强调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其“完全立于客观的必然论之上”[10](P133),以及对其他理论实行了“扬弃”,“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10](P130)。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中,瞿秋白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科学性在于它把辩证唯物主义贯彻到了社会历史领域,这明显不同于旧唯物论的不彻底性。实践真理性层面:李大钊突出了阶级斗争的作用,指出它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条金线;明确唯物史观的实践价值性之一就在于重点“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并且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奋发有为的人生观”[8](P217)。另外,对包括西化派在内的其他主义质疑马克思主义有关成分的科学性论调,这一期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进行了积极而正面的回击。如对于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完全归结为阶级斗争以及将唯物史观视为“经济定命论”,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是有时间限定的,即“人类历史的前史时代”,相反它并没有否定运用互助原则来改造人类的精神层面。上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真理观上对西化派的回应,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内核”,也利于人们在这一期间迷乱的社会思想状况中充分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四、在文化观上,用中西文化融合创新的观点回应了西化派的文化整体观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初步回答了中西文化如何处理以及是否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
由于近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特别是救国救民情境的紧迫性,致使在“文化”方面的观点和看法,必然要涉及到两个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一是东西文明如何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采取何种文明的方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处理东西文明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对存在于民众头脑中的不同社会意识实行整合,即用哪一种思想意识作为社会的主导乃至主流意识形态,以在解决复杂及其迫切的社会问题过程中能达到思想意志的统一。围绕着上述两个方面,近现代中国诸多政治派别阐释着各自的文化观,西化派也不例外。在第一方面,针对东方文化派以坚持文化民族性而否认文化时代性,以及突出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来调和中西文明的文化保守主义;西化派却坚持文化时代性而不承认文化民族性,同时强调文化具有整体性特征而反对文化的调和,认为西方文明就是时代发展的方向。如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文中,胡适强调“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3](P527);指出“我们承认各民族在某一时代的文化所表现的特征,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3](P528);提出在全世界大通的背景下欧洲人的科学化和民治化将会是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3](P529)。由于反封建传统文化这一共同目标的存在,致使五四前后西化派的文化整体观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在上述第一个方面并未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关主张 (即用唯物史观指导下实行中西文化融合以再创新文明的观点)发生直接正面的冲突,然而实质上双方观点的差异性亦足已证明彼此的根本对峙性。正如著名学者刘放桐所指出的,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一传入中国就已存在对立和斗争,但它们都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目标,这就决定双方的分歧“不在是否应当、而在怎样使中国走上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并且“归根到底的意义上”体现出来了的两种不同的政治方向[20]。在第二个方面,西化派则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种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整合社会意识的思想理念进行了直接的批判和挑战,最典型就是“科玄论战”,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东西文化论战,因为涉及到了如何看待西方科学文化的作用,以及如何评判东西文化高下优劣等[21]。这场论战中,围绕科学的人生观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建立人生观等问题,科学派除反对玄学派相关思想主张外,也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建立科学的人生观这一思想进行了直接质疑。之所以将科学人生观的建立与社会意识的整合联系起来,就在于人生观虽表现为人的个性中的一种意识倾向,但是它不仅调节人的行为、活动方向和进行方式,而且决定着一个人对周围事物的态度;更重要在于社会是由个体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社会意识的统一与否取决于个体思想意识的科学与否。如胡适在《答陈独秀先生》文中就直接否定了唯物史观在人生观树立方面的指导性作用,指出其本质是一种历史观而不是人生观,即使将两者发生关系,也只能是说历史观是人生观的一部分,而不能完全解决人生观中所涉及到的其他方面[22](P106)。在文中,他还认为支配人生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经济方面的因素,还包括思想知识等非物质因素;而唯物史观更多地关注了前者却忽视了后者。
在上述文化观的第一层面,尽管因反封建传统文化这一共同目标的存在,致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思想较多地是因批判东方文化派等文化保守主义而发;但明显不同于西化派的观点理论,实质上也间接体现出对西化派挑战的一种回应。具体为:有别于西化派单纯地从精神层面的优劣高低强调文化的时代性问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从物质这一根本层面探讨了文化的时代性根源及其演变趋向问题。如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中,瞿秋白明确东西文化的差异性“都是有经济上的原因”,本身它们并“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10](P380)。杨明斋甚至关注到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之间的关系。在《评中西文化观》中,他认为产生文化时代性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养生的物质”,而不是“人类的意欲”[23](P9);同时也指出文化虽变动而其民族习惯性的东西却 “常常的经过许久时期还存在其中”[23](P189)。有别于西化派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西方文化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既肯定其优点也揭露了其弊端。如陈独秀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中指出,西方文化虽然在物质科学上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它和私有制下其他民族、地域的文化一样亦具有“虚伪、忌妒、侵夺,争杀,独占心、利己心、私有心”[8](P53)等弊端。另外,有别于西化派文化整体观下的近似于完全“西化”的方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中西文化相调和,以构建一种新文化的设想。如李大钊就主张通过融合中西文化创造第三种新文明以救世界之危机[8](P131)。而对于如何调和创新,这一期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进行了探讨。如李大钊提出了诸如“须知调和之机”、“须知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也”、“须知各势力中之各个分子,当尽备调和之德也”、“当知即以调和自任者,……乃有权威也”[8](P141-145)四条具体法则。而对于上述文化观的第二层面,针对科学派所掀起的直接式挑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积极而正面的回应,其中以陈独秀、瞿秋白的贡献最大。这一期间陈独秀虽尚未完全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实证论的界限[24],但却直接点出了科学派相关言论的实质及其危害性。如认为丁文江的存疑唯心论给玄学派留了有空可钻的地盘;指出胡适那种借口支配人生观的因素是多方面而否认唯物史观的指导性作用,则明显是心物并立的历史多元论“翻板”;明确强调唯物史观“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22](P12)。相对于陈独秀对科学派的“破”,瞿秋白则更多地是“破”之后的“立”,即具体论证了为何马克思主义能整合多元的社会意识并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如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文中,他认为这在于马克思主义能探悉支配意志行为的 “公律”即“因经济顺其客观公律而流变”[10](P407);强调人类社会人们的人生观将经历一个由利己而利他的过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与社会、利己与利他将达到统一,无产阶级在实现人类解放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解放。
可见,五四前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回应西化派的挑战在方式上明显具有“针对性”,在内容上又表现出“体系性”。“针对性”,就是在历史观上,用唯物史观回应了西化派的历史进化论和文化决定论;在自由观上,用社会主义自由观回应了西化派的资产阶级自由观;在真理观上,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回应了西化派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在文化观上,用唯物史观指导下实行中西文化融合创新的观点回应了西化派的文化整体观和西方文化中心论。“体系性”,就是在于已初步论及了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了解中国实际以及如何实现两者相结合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核心层面,向当时的民众旗帜鲜明地传递了解决中国问题(包括中西文化的处理、社会意识形态格局的构建等方面)需要马克思主义以及它具有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和品质这样的信息。
[1]黄敏兰.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17.
[2]张世保.从西化到全球化——20世纪前50年代西化思潮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3]耿云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适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4]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一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88.
[5]洪晓斌.丁文江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116.
[6]明立志,吴小龙等.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116-117.
[7]胡明.陈独秀选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108.
[8]朱维铮.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9]朱庆跃.五四前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方文化派挑战的回应[J].党的文献,2015,(1):95.
[10]李华兴.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11]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
[12]商英伟,白锡能.自由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13]郭双林,高波.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高一涵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21.
[14]秋风.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13.
[1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2.
[16]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7]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4.
[18]欧阳哲生.胡适文集(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3.
[19]李丕洋.评胡适的真理观[C].中国现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280-281.
[20]刘放桐.西学传入与“五四”前后中西文化和哲学的碰撞[J].东南学术,2001,(2):55.
[21]李白鹤,王丹桂.科玄论战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J].江汉论坛,2013,(7):11.
[22]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六册)——科学与玄学论战(上)[D].辽宁大学,1981.
[23]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M].合肥:黄山书社,2008.
[24]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49.
【责任编辑:来小乔】
Response of Early Chinese Marxists 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 to Western Challenges
ZHU Qing-yue1,2
(1.School of Information,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Anhui,235000;2.Institute of Knowledge and Value Science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
Meeting challenges from other social thoughts in different periods is one of the problem situations that need to be resolved in the practice of Marxism in China.For example,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early Chinese Marxists responded positively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westernizers from various aspects:in historical conception,they responded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historical evolutionism and cultural determinism of the westernizers,providing preliminary answers to what were China’s problems and the root causes;in view of freedom,with socialist view of freedom they responded to western bourgeoisie’s liberalism,providing preliminary answers to how to solve China’s problems and where China should go at that time;in truth view,with Marxist conception of truth they responded to pragmatic theory of truth,providing preliminary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Marxism is truth;in cultural view,with innovative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they responded to Western overall concept of culture and west-centered theory,providing preliminary answers to how to handle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whether Marxism is needed as guidance in this regard. These responses not only delivered a clear message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at resolving China’s problems(such as handl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ideological pattern)needed Marxism and that Marxism had th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solving Chinese problems,but also provided an indirect warning for the Chinese Marxists ever since that the practice of Marxism in China could not be easy or successful once and for all.
in May Fourth period;early Chinese Marxists;westernizers;challenges;response
B 0-0
A
1000-260X(2016)04-0006-07
2016-03-12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 “近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论战研究”(gxyqZD2016407);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Szzgjh2-6)
朱庆跃,淮北师范大学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