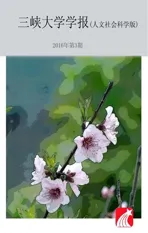致使结构中的蕴含关系研究
2016-04-04李静波
李静波
(1.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2.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言研究院,上海 200083)
致使结构中的蕴含关系研究
李静波1,2
(1.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 福建 武夷山354300; 2.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言研究院,上海200083)
摘要:从词源和类型学的角度考察了致使动词与致使结构中蕴含关系的关联。致使动词的词源从力特征上可分为强力动词、弱力动词、微力动词和无力动词。致使动词源于强力动词通常有蕴含关系;其它动词通常无蕴含关系。其原因在于致使动词承载的致使力有强弱之别,而承载能力取决于初始动词。这可以解释不同致使结构中蕴含关系对立现象。
关键词:词源;致使动词;致使结果;蕴含关系;致使力
致使结构通常表达两个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这两个事件分别是致使事件(causing event)和结果事件(caused event)。英语的make、have、cause等致使结构中致使结果具有已然性(成功性),致使事件实现则致使结果一定实现,前者蕴含后者(简称蕴含关系)。如:
(1)a.Yesterday I made him come.
b. Yesterday I made him come, but he didn’t come.
这种蕴含性也存在于日语致使结构中,如:
(2)a.太郎は次郎を走らせた。(太郎让次郎跑)
b.太郎は次郎を走らせたが、次郎が走らなかった。(太郎让次郎跑,但次郎没跑。)
但是汉语的“叫、让”致使结构并没有这种蕴含关系。如:
(3)a.上个月就让他写申请了。
b.上个月就让他写申请了,可是到现在他也没写。
以往学者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但是尚未作出充分的解释。我们拟从词源角度,通过跨语言的考察探讨该现象。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研究致使者(causer)和被使者(causee)均为人且被使者动词只表示动作的致使结构,如“张三让李四跑”;不考虑被使者动词表状态的情况,如“张三让李四很失望”。
一、以往关于蕴含关系的看法
早期的类型学研究认为致使结构必然存在蕴含关系,这从Shibatani[1]1-2对致使结构的定义即可看出。Shibatani认为致使结构包含两个事件,它们必须满足下面两个条件:(1)说话者认为致使事件要先于被致使事件发生;(2)说话者认为致使结果的发生完全依赖于致使事件;如果致使事件没有发生,那么致使结果就不会发生。他特别指出“I told John to go”之类的句子不是致使句,因为它还可后接“but he actually didn’t go”,致使结果不具有已然性。但是许多学者在实际调查和研究致使结构时也并未将蕴含关系看作必要条件。Song[2]对蕴含关系格外重视,将其作为致使结构类型的区别性特征之一。他将致使结构分为紧致型、目的型和并列型,并认为目的型和并列型最终将演变为紧致型。根据Song的分类,传统型上的迂回型致使结构可能源自于并列型,也可能源于目的型。并列型都有蕴含关系,而目的型中的蕴含关系存在与否则因语言和结构而异。
不同语言中致使结构的蕴含关系(仅限目的型致使结构)存在3种情况:(1)所有结构都有;(2)所有结构都无;(3)仅部分结构有。通过对大量语言现象的观察,Song[2]136发现所有语言的蕴含度(implicativity)形成一个从0%到100%的梯度。这表明蕴含关系不仅在致使结构中存在着对立,而且表现得很有规律,但是哪些目的型致使结构有蕴含关系,Song并没有明确说明。Jackendoff[3] 125-155通过对词汇的语义分析指出结果的已然性可标注在致使动词上,但他的研究是基于英语的,缺乏跨语言的验证。
二、致使结果实现的技术手段
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两种情况下致使结果通常都必然实现。
1.在被使者动词上有标记过去或完成的时体标记。有些语言会在被使者动词上加上明确的时体标志,如汉语“叫、让”致使结构借助完成体标志“了”表明致使结果实现。如:
(4)大家让他唱首歌,但他没唱。
(5)大家让他唱了首歌,但他没唱。
Orokaiva语在被使者动词上添加过去时标志表示致使结果实现[2]37。
(6)Embo na ami-ta meni e-n-u ji neinei humbu-to punv-n-a
Man SUB him-of son do-PST +he-SEQ wood some take-PUNT come- PST+he-IND
The man made his son fetch some firewood.
2.词汇型致使结构。词汇型致使结构中致使事件和致使结果融合在一起,两者几乎同时发生,这就导致致使事件实现则致使结果必然实现。如:
(7)John killed Mary, but Mary didn’t die.
(8)太郎が次郎を殺したが、次郎がしなかった。
(9)武松打死了老虎,但老虎没死。
上述两种表示致使结果实现的情况依靠的是一些技术手段,在此不再讨论。
另外,由于并列型致使结构都含有蕴含关系[2]135-136,所以它无论处于哪一阶段①,致使结果都具有已然性,如汉语中的“得”字致使结构。
(10)孩子气得母亲直哭。
“得”字致使结构不具有目的性。如例(10)只能理解为“孩子气母亲,母亲哭了”,不能是“母亲哭是孩子气母亲的目的”。这与“叫、让”致使结构不同,后者为目的型。如“母亲让孩子去学校”可理解为“孩子去学校”是“母亲”的目的。所以并列型(接近于紧致型)的“得”字致使结构中致使结果都具有已然性。
在形式结合松散的迂回型致使结构中,致使事件的实现和致使结果的实现在时间上会有间隔。如:“我让他明天交作业”。致使事件发生在当下,而致使结果的发生是明天。由于二者在时间上的分离,就有可能使致使结果出现两种情况——实现或不实现。英语致使结构可依靠致使动词判定致使结果是否实现,如:
(11)John made/had Mary come, but Mary didn’t come.
(12)John caused Mary to come, but Mary didn’t come.
(13)John let Mary go, but Mary didn’t go.
上面例句中的make、have、cause致使句致使结果已经实现,在let致使句中未实现。从结构上看这几句完全相同,都是Causer+Vcause+Causee+Veffect排列,不同之处仅在于致使动词的选择上。可见至少英语迂回型致使结构中的蕴含关系和句法无关,对其产生影响的是致使动词。
三、致使动词对致使结果的影响
人类语言中只有少部分动词有可能成为致使动词。根据海涅、库特夫[4]、黄成龙[5]的研究,致使动词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动词:make,do,seize,grasp,take,send,give,order,say,call,let等。我们按照这些动词所体现出的力量将其分为四类:1)强力动词:包括make,do,seize,grasp、take;2)弱力动词:包括send、give;3)微力动词:包括order、say、 call;4)无力动词:let、allow等。要完成以上四类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动作主所付出的力和对对象的影响力是不同的。正如名称所示,从施动力来讲,它们在力量的强弱上构成一个“强力动词>弱力动词>微力动词>无力动词”的等级。行为者要实现强力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必须发出直接的、较强的物理性的力;实现弱力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则相对更为间接,力也弱一些;微力动词所表示的是发话行为,对人们来讲并不费力;而对无力动词let来讲,几乎不需要力,点头就能表示许可、同意。下面考察词源动词与致使结果的关联现象。
1.英日汉语中的情况
熊学亮、梁晓波认为make的致使义依托其“制造义”[6]。这只是表面现象,还可进一步挖掘。从词源来看make源自原始印欧语的“mag”,表示“捏揉(to knead)、使用(to fashion)”等义;Have源自原始印欧语的“kap”,表示“抓(grasp)”;cause在14世纪晚期,表示“造成影响、强迫”,与现代英语的force相当;而let在原始印欧语中就表示“允许(allow)”②。 海涅、库特夫将源自动词do和make的致使动词都归为DO类致使动词,从词源角度来看是非常合理的。可以看出,除了let,英语中主要的致使动词都源于强力动词,而它们构成的致使结构都有蕴含关系。
日语中有两个致使动词su和saseru,两者构成的致使结构都有蕴含关系。前者能产性很低,在形式结合紧密度上远远高于后者。对于saseru学界普遍认为它源于古日语su。Su在古日语是动词,表“做”[7],属于强力动词。
再看汉语中的“叫、让”。太田辰夫[8]223-225指出汉语中的致使动词“叫”原先写作“教”,可能是从教唆的意义转而成为致使;“让”原来表示“劝诱”和“谦让”义,经语法化成为致使动词,可分别记作“让1”和“让2”。可以看出初始的“叫、让1”都为言说动词,这从汉语和英日语的对译也得到了体现,如“我叫/让你去,你为什么没去?”译为英日语分别是(14)和(15)。
(14)I asked you to go , why didn’t you go?
(15)行くように言つたが、なぜ行かなかつた。
汉语中还有典型的致使动词“使”③。“使”的致使义是由“使用”、“派遣”、“支使”等动作义衍生出来的[9]80,初始意义较为多样,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不表示弱力、无力。“使”字致使句中致使结果多表示状态改变,有时也表示活动,此时“使”字句中的致使结果必然要实现。如:
(16)a.已经使人打听消息了。
b.已经使人打听消息了,但(那人)没打听。
可以看出,英语的have、make、cause和日语中的saseru在词源上都是强力动词,汉语的“使”介于强力动词和弱力动词之间,它们构成的致使结构都有蕴含关系;英语let、汉语“让2”是无力动词,汉语“叫、让1”是弱力动词,它们构成的致使结构没有蕴含关系。
2.其它语言中的情况
我们按照强力动词到无力动词的顺序观察致使动词与蕴含关系的关联。
1)强力动词
芬兰语(Finnish)的pani[10]、塔拉斯堪语(Tarasacan)的úni[11]、库松达语(Kusunda)中的a[12],都能表示make义,它们所构成的致使结构都有蕴含关系。例如:
(17)芬兰语(Sakuma 2010)
Keisari pani o rjat rakentamman temppelin mutta emperor-NOM.SG.make-3.SG.P.slave-NOM.PL.build-3.INF.ILLAT.temple-GEN.SG. but temppeli ei valmistunut.temple-NOM.SG not finish-3SG
the emperor made the salves build a temple but the temple was not finished.
(18)塔拉斯堪语(Maldonado, R. & Nava L, E. F.2002)
Valeria ú-s-0-ti éski Adrianu mana-kurhi-a-ka
Valeria make-PERF-PRES-IND.3COMP Adrian shake-RFLX-FUT-SUBJ
Valeria made Adrian shake.
(19)库松达语(Watters 2006)
Me-ACCmeat roast-REAL make-3-PAST
He made me roast meat.
上面这些句子都表示致使结果已经实现,不允许后接未实现的句子。另外,据Nguyen Thi[13]越南语的致使动词lm(do)构成的致使结构也有蕴含关系。
2)弱力动词
根据Watters[12]和Nguyen Thi[13],库松达语中的 tmb和越南语中的sai作实义动词时表示send,它们构成的致使结构没有蕴含关系。如:
(20)库松达语(Watters 2006)
you him-ACC house make-CNV send-2-PAST
You got him build a house.
(21)越南语(Nguyen Thi 2014)
我已经让孩子做饭了,但他没做
3)微力动词
David[14]指出亚施宁加语(Asheninka)中由aka构成的迂回型致使结构没有蕴含关系。aka已经高度语法化,但是在词源上aka与表示say的动词密切相关。芬兰语[10]、塔拉斯堪语[11]、马赛斯语(Matses)[15]、瓜拉尼语(Guraní)[16]以及越南语中由言说类的弱力动词构成的致使结构无蕴含关系。如:
(22)芬兰语(Sakuma 2010)
opettaja käski kuoroa mutta kuoro ei laulanut
teacher-NOM.SG. order-3.SG.P choir-part.SG. but choir-NOM.SG. not sing-3.SG.P
the teacher ordered the choir sing but the choir did not sing
(23)塔拉斯堪语(Maldonado, R. & Nava L, E. F.2002)
Eratzini arhi-s-0-ti Adrianu-ni éski arhi-a-ka
Eratzin tell-PERF-PRES-IND.3 Adrian-OB COMP tell-FUT-SUBJ
Ma wantantskwa Yuyani-ni ka no wé-s-0-ti
a story Yuyani-OB but no want-PERF-PRES-IND.3
Eratzin told Adrian to tell a story to Yuyani but he did not want to.
(24)马赛斯语(Fleck 2002)
Madia-n madta-ø acte-ø ue-ø ca-o-sh.
Maria-ERG Martha-ABS water-ABS fetch-IMPER tell-PAST-3
Maria told Martha to fetch water.(Maria had/made Martha fetch water.)
Fleck(2002)指出,该句可后接结果未实现的句子。
(25)瓜拉尼语(Maura 2002)
Ha-e chupe o-ho hagua
1AC-tell to=him 3AC-go PURP
I told him to go.
Maura(2002)指出该句没有蕴含关系,致使动词e被翻译为tell表明它还处于语法化的初期阶段。
4)无力动词
无力动词基本上都没有蕴含关系,我们只以德语的lassen(英语let意义)为例简要介绍。
(26)Gestern lieβ ich ihn kommen, aber er kam nicht.
Yesterday let I-NOM he-ACC come-PAST but he come NEG.
昨天我让他来,但他没来。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对词源动词和蕴含关系的关联性作出下面预测:
初始动词:强力动词>弱力动词>微力动词>无力动词
蕴含关系:有趋于无无无。
将弱力动词定为趋于无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致使动词的词源可能并不止现有的这些。第二,强力动词和弱力动词所体现出的力量分布应该不是离散的,而是连续的。
四、初始动词制约蕴含关系的解释
语法化理论认为一个词语虚化为一个语法标记之后,其用法和使用范围还会受到它原来词汇意义的影响。迂回型致使结构中,致使动词的虚化程度不高,语义上保留了许多初始特征,它们会对致使结构产生各种影响。比如不同的致使动词会使致使结构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动词make有“强迫”义,所以make致使结构可以表示强迫致使;动词let表示许可,let致使结构就表示许可致使。Foley(1991)指出伊玛斯语(Yimas)有两个致使动词tar和tmi,初始意义分别是hold和say,它们在致使方式上表现不一样。(转引自Shibatani 2002)[17]比如:
(27)na-na-tar-kwalca-t
3SG.A-1SG.O-CAUS-rise-PERF
She woke me up
例(26)和(27)都表示唤醒对方,但在tar致使结构中表示抓住并弄醒对方,而在tmi致使结构中则是依靠呼喊叫醒对方。蕴含关系作为致使结构的一个表现,势必受到致使动词原始语义的制约。
1.致使动词承载致使力
致使力是致使情景中我们所感受到的力,致使力的传递是致使的语义核心。Shibatani[18]指出日语致使动词saseru的典型意义是X cause Y to do Z by doing something,其中doing something是saseru自身固有的意义。可见致使动词承载着致使力,但不同的致使动词承载不同的致使力,包括力量、方式等。如:John made the doctor come. John let the doctor come.尽管致使者都是John,但由于致使动词不同,前者很可能是一种强大的物理力,比如扭着“医生”进来;而后者则对医生没有施加任何的力。
英语致使动词承载的致使力大小可由相应的实义动词观察出来。但是有些致使动词已经虚化,语义特征不明显,不从词源上追溯就无法确定它所承载的致使力。王文斌、何清强[19]指出“不同对象的差异对比,越是能追溯至其初始意义,彼此的差异往往就越鲜明越本原。”致使动词都是实义动词语法化的产物。在语法化的过程中,语义可能逐步漂白,但是荷载能力不会随之同步变化,初始动词的力特征将决定致使动词的承载力。实义动词力特征越强,在致使结构中荷载能力或传递的致使力也就越强。日语中saseru源于强力动词su,所以承载强致使力;英语中致使动词make、cause、have等在词源上都是强力动词,也承载了强致使力。汉语“叫、让”源于微力动词,只能承载弱致使力。我们依照初始动词力的大小,将致使动词也分为四类:强力致使动词、弱力致使动词、微力致使动词和无力致使动词。
2.致使力与自控力决定致使结果
Talmy[20]根据力学原理建立了施力——动态模型,并运用于语言结构关系的研究之中。Wolff[21-22]在Talmy的基础上建立了动态模式(dynamics model),将致使结构中的致使动词分为三大类:致使类;能够类;阻止类。他们都认为在典型的致使结构中致使者(causer)和被使者(causee)存在着力量的对抗,致使结果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致使者的致使力和被使者的自控力(或意愿性)。致使力是致使者向被使者发出的力(设定为正值,记作Fcauser),自控力是被使者所具有的控制力(记作Fcausee)。被使者积极实现致使结果,则自控力为正值;消极对抗则自控力为负值。按照被使者的主观态度可将致使结构分为两类:①被使者积极实现Fcauser (>0)+ Fcausee(>0);②被使者消极对抗Fcauser (>0)+Fcausee(<0)。
致使力和自控力的合力为正值时致使结果才能实现。①中Fcauser和Fcausee都是正值,致使结果必然能够实现;②中只有绝对值|Fcauser|>|Fcausee|,致使结果才能实现;反之则无法实现。
强力致使动词承载的力量最大,被使者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致使力和自控力的合力都能确保为正值,即致使者对被使者有绝对的控制力,这就使得这类动词构成的致使结构中结果必然实现。源于send、give等的弱力致使动词承载的力较小,如果被使者消极抵抗,致使力很可能会小于自控力,此时致使结果就未必能够实现。言说类的微力动词,完全无法保证对象产生变化或行动。源于这类词的致使动词,由于承载的致使力太弱,没有能力保证结果实现。最后一类无力动词,几乎不承载致使力,结果是否实现与致使力无关,自然也不存在蕴含关系。
以上内容可总结如下:强力动词(make, do 等)→强力致使动词(承载强致使力)→有蕴含关系;弱力动词(send, give等)→弱力致使动词(承载弱致使力)→趋于无蕴含关系;微力动词(call, say等)→微力致使动词(承载微致使力)→无蕴含关系;无力动词(let, allow等)→无力致使动词(不承载致使力)→无蕴含关系。
五、结语
致使动词都来自于实义动词。通过跨语言的观察发现,致使结果是否实现与致使动词的初始力特征相关。作用力最强的do、make动词演变为致使动词后,所体现的致使力非常强大,导致致使结果必然出现,而微力动词和无力动词原本作用力就很小或者不存在,所以它们充当致使动词时,致使结构就没有蕴含关系。可以推测,人类语言中源于由微力动词(言说类动词)和无力动词(允让类动词)构成的致使结构,如果形式上结合得不是特别紧密都不存在蕴含关系。这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为什么日语saseru、英语make、have、cause致使结构和汉语“叫、让”、英语let致使结构会在蕴含关系上存在对立。
注释:
①致使结构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详见Song(1996):80-102。
②对词源的调查借助http://www.etymonline.com网站。
③学者们对汉语中致使动词的范围意见不一致,我们只选取公认的“使、叫、让”三个动词。
参考文献:
[1]Shibatani M. The grammar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a conspectus[M]// M.ShibataniSyntax and semantics(Vol.6):The grammar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6:1-40.
[2]Song J J. Causatives and causation: A universal-typological perspective[M].London/New York:Longman, 1996.
[3]Jackendoff R. Semantic structures (Vol. 18)[M]. Cambridge: MIT press,1992.
[4]海涅·库特夫.语法化的世界词库[M].龙海平,谷峰,肖小平,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5]黄成龙.类型学视野中的致使结构[J].民族语文,2014(5):3-21.
[6]熊学亮,梁晓波.致使结构的原型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 106-110.
[7]青木伶子.使役——自動詞·他動詞との関わりにおいて[J].成蹊国文,1977(10):108-121.
[8]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M].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张豫峰.现代汉语致使态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10] Sakuma J. The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the Finnish Language[J].Journal of the School of Letters,2010,(6):17-28.
[11] Maldonado R, Nava L E. F. Tarascan causatives and event complexity[M]// M.Shibatani. The grammar of causation and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Vol. 48).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2:157-195.
[12] Watters D. Notes on Kusunda grammar: A language isolate of Nepal[J]. Himalayan Linguistics.2006: 1-182.
[13] Nguyen Thi, AiTien.日本語とベトナム語における使役表現の対照研究―他動詞、テモラウ、ヨウニイウとの連続性[D].大阪:大阪大学博士论文,2014.
[14] David P. Causatives in Asheninka[M]//M.Shibatani.Thegrammar of causation and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Vol. 48).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ling,2002: 485-505.
[15] Fleck D W. Causation in Matses [M]// M.Shibatani(eds.).The grammar of causation and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Vol. 48).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2: 373-415.
[16] Velázquez-Castillo M. Guaraní causative constructions[M]// M.Shibatani(eds.). The grammarof causation and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Vol.48).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2: 507-534.
[17] Shibatani M. Introduction: some basic issues in the grammar of causation[M]// M.Shibatani. Thegrammar of causation and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Vol. 48).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ling,2002: 1-22.
[18] Shibatani M. Semantics of Japanese causativization[J]. Foundations of language,1973(3):327-373.
[19] 王文斌,何清强.论英语“ be”与汉语“是/有/在”[J].外国语,2014(5):2-10.
[20]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Vol.1)[M]. Cambridge:MIT Press,2000.
[21] Wolff P. Direct causation in the linguistic coding and individuation of causal events[J]. Cognition, 2003(1):1-48.
[22] Wolff P. Representing causation[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007: 82-111.
[责任编辑:赵秀丽]
中图分类号:H 3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16)03-0053-05
收稿日期:2015-10-10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50618)。
作者简介:李静波,男,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