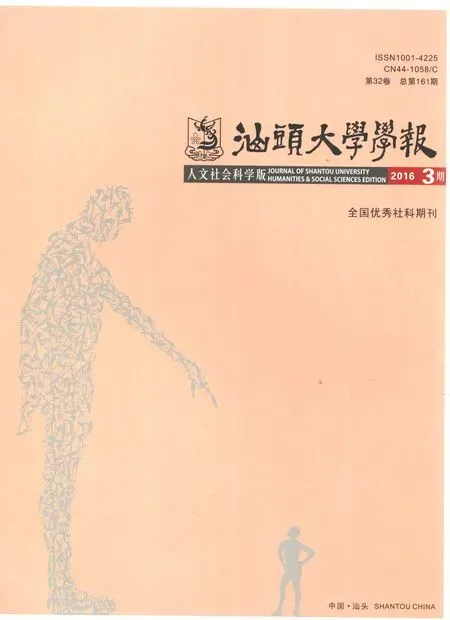《老子》之“身”辨:“有身”“无身”与“为身”
2016-04-03张艳艳
张艳艳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老子》之“身”辨:“有身”“无身”与“为身”
张艳艳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汕头515063)
摘要:在老子以气构生的有机身体观及身物关系格局中,甄别形躯之身与精神之身并非是老子论身的关键;在目、心、志与腹、骨、气的对照关系中,老子有着对身体主体构成及其价值指向的贞认。以“无身”为身,勘破现实之身在形塑过程中的失真状态,消解形塑现实之身的价值属性,以回复身体之自然原初状态为终极诉求,建构老子理想之身;以“无身”为身所实现的消解与构建揭示出老子身体观的价值旨趣。
关键词:目;腹;气;圣人;有身;无身;为身
基于《老子》文本中围绕“身”展开的话语富有含混性,自古以来注家释义便争讼不已,尤其以13章的释义最为显著,见出对老子贵身与否迥异其趣的见地。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13章》)
一说强调“无身”,以河上公本释义为始作俑者,“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有身则忧其勤劳,念其饥寒,触情纵欲,则遇祸患也。使吾无有身体,得道自然,轻举升云,出入无间,与道通神,当有何患。”[1]所要无的“身”显然是形躯之身,这倒贴合两汉之际成仙问道方式对老子的宗教式演绎。后世成玄英疏义:“执着我身,不能忘遣,为身愁毒,即是大患。只为有身,所以有患,身既无矣,患岂有焉?故我无身,患将安托?所言无者,坐忘丧我,堕体离形,即身无身,非是灭坏,而称无也。”[2]401已是援庄释老,又入庄老出玄佛,所要无的“身”是执着于一己欲念心志之身,若“无己”、“丧我”则可无身,忘身养神则得道之大清明。此论后继者众,不一一陈说。
一说强调“贵身”,司马光之论:“有身斯有患也,然则,既有此身,则当贵之,爱之,循自然之理,以应事物,不纵情欲,俾之无患可也。”[3]110李荣的注更说得直接:“身形是成道之本”,[2]672显然形躯之身不独只是生命的载器,所贵之身当亦包含对形躯之身的持守与肯定。陈鼓应在辨疑此章时说:“这一章颇遭曲解。前人多解释为‘身’是一切烦恼大患的根源,所以要忘身。一个‘贵身’的思想却被误解为‘忘身’。造成这种曲解多半是受了佛学的影响,他们用佛学的观点去附会老子。肉体和精神这两个部分是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充分而且必要的条件,也即是构成人的生命的充分而且必要的条件。有些人把‘身’视为‘肉体’的同义字,再加上道学观念和宗教思想的影响,认为肉体是可卑的,遂有‘忘身’的说法。”[3]112-113陈氏此论亦是在肯定形态之躯的前提上,在形神一体的格局中强调老子对“身体”的珍视。
然而仅就形神关系的向度言说老子之身以及由此引发的“无身”与“贵身”之争是否就得老子论身之要领?如是的思路又如何解释圣人“为腹不为目”?故此,要论说此意,恐怕要先对老子的身体观做一统和式体认,首先甄别形躯之身与精神之身是否是老子论身的关键?继而在目、心、志与腹、骨、气的对照关系中,辨析老子对身体主体构成及其价值指向的贞认,何以圣人“为腹不为目”、又何以要为天下“浑其心”?在更阔达的视域中,由老子之道来看宇宙间与人世间所开显的物身关系格局,并以此审视老子对“身”之定位与期许,老子贵身与否的争讼本身实则可以统和。虽然老子围绕“身”所展开的话语表述本身是以含混的面貌出现的,却有着清晰的方向指向性,以“无身”为身,是以损却的方式消解基于自我本位立场对一己之身的执着,同时亦勘破起于身对物(也包括他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僭越实质,在恢复物之自在本性的同时,亦恢复身之“归本复初”的状态,由此可见要损却的“身”是被对象性关系粘滞着的自我本位立场之身,当然是不应贵的,损却此身获得的身是自在而富有生机的,当然是老子珍视的。以“无身”为身所实现的消解与构建,当是老子之身的价值旨趣。
一、《老子》中涉及到“身”的关联性表述
(一)以身喻道:“母”
首要的问题是何者为老子之身的确切落实?此问初看是明知故问,但是在追问的求索之途可以见出微妙旨趣,也只有厘清这一前提之后,方可细论老子对身体主体构成及其价值指向的贞认。事实上《老子》全文与“身”关涉的关联性表述各自承载的价值属性与角色设定皆不同。母、婴儿、圣人、民,何者才是老子之身的承载者、是老子思想格局中真正的身体主体呢?
纵观《老子》全文,“母”凡5见,皆与“道”相关,取“母”的功能性隐喻义,开显“道”为万物生成之根本的生成论本体地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1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 25章》)无论是“天地母”、还是“万物母”都是对不可坐实向具象形迹的核心概念“道”的隐喻性表述,基于隐喻认知源域向目标域的投射,借助“母”这一身体意象的具象特质——蕴育生命的生殖性功能和“生”而不有的角色属性——在人的认知格局中实现格式塔式整合,目不可见、耳不可听,无法落实向形迹的“道”体,在我们这里获得异质同构的具象体认。所以“母”虽为身体意象,却不具有身体主体向度上的意义,“母”作为概念隐喻,在其它章节中,甚至直接指代“道”本身。“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20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52章》)坚守吸纳自母而来的滋养和对“母”的持守其实都是人不离道、以道为本。有鉴于老子话语生态与隐喻思维的内在亲缘,不独“母”为概念隐喻以喻道,川谷、橐龠等自然器物意象亦然,以此也可辅证“母”虽为身体意象,但是实质上与道更为关涉,并不具有身体本体意味,在身体论的视域中“贵食母”之论可暂时搁置。
(二)以身喻道及圣人:“婴儿”
与之相应“婴儿”也是身体意象,但是与老子之“身”则更多牵绊,我们可否说老子所论之身就是婴儿呢?还是老子以婴儿为用、作为言说凭介见出老子之身的真谛?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鉴,能如疵乎?爱国治民,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老子·10章》)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老子·20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老子·28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老子·55章》)
何谓婴儿?高亨说:“人性未漓为婴儿”,[3]179“含德之厚”、“常德不离”都是对于婴儿生命状态的描述,在道物关系的格局里“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51章》)诸家释义:德为道之“功”、“见”、“用”,[3]148综合王弼所述:“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4]可以说:“德是践履着的道,是道向有形之物的落实,德是生命之为生命的本质所在,生命之本性所在,也是道的显现”。[5]27如是可见,婴儿是葆有老子之道的具象身体形态,55章中我们看到老子所推崇的婴儿之身的具体状态,他“精气充足”、“元气淳和”、虽然“骨弱筋柔”却饱富有生命力,终日号哭嗓子却不黯哑,毒虫、猛兽与禽鸟都不会攻击他。何以如此?恐怕这些特性都导向同一个因由:因其“未知”所以不起欲,尚无一“己”的贞认,当然不知“牝牡”之事,也当然不会有我与物的分界,既然尚不知物我的分界,对于毒虫、禽鸟猛兽亦无所谓畏惧与不畏惧,所以两相自在。结合老子多处“朴”之为喻,“道常无名朴”(《老子·32章》)、“敦兮其若朴”(《老子·15章》),高亨说:“木质未散为朴。”[3]179-180,强调的也是本在原初的状态,可见老子是借助朴与婴儿的自然自在状态来譬喻老子之道的境界,现实境遇中的具体生命体也当以自然性为道境的终极诉求,以“复归于”婴儿与朴为修身之理想状态。于是我们看到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我“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显然“我”与婴儿有分界,所以才说“如”,句式关系清晰,婴儿是对“我”修身理想境界的具象表述,是道境的隐喻化表达,却不是老子所有语境中实际行为主体,所以老子是凭借“婴儿之身”为喻,见出“我”等身体主体养成的境界。“我”既然是老子之身的真正落实,那么“我”为何人呢?
(三)身体主体的分鉴:“圣人”与“民”
统观《老子》全文81章,在社会现实境遇中的个体生命大致呈现出圣人与民对应的两个序列,作为圣人序列的行为主体表述有:圣人(24章次)、我(吾,5章次)、侯王(2章次)、善为道者(2章次)、善摄生者(1章次)、君子(2章次)、大丈夫(1章次)、士(1章次),涉及君子、大丈夫、士各章所论皆无关要旨,另外修身工夫诸章及其他省略主语的章节,虽未明确言出其行为主体亦在圣人序列。作为民序列的行为主体表述有:民(13章次)、百姓(3章次)、众人(3章次),人(作为“众人”之人,5章次)。如果我们取圣人与民各代之,则发现两者各自代表不同的身体状态与价值取向,同时各自承载的角色定位亦不同。我们列举部分章节如下: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3章》)
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20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37章》)
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老子·49章》)
显然圣人与民的对应关系至少包含如下两个面向:其一,圣人与民分别代表不同的生命情态和价值取向,现实境遇中的民熙熙攘攘、纵情使欲,为声色、货殖、名利所蛊惑,自然的天性受到损伤,陷入与道背驰的境地。而圣人则无欲、不争,守道静定,显然圣人才是老子心目中自然道境的持守者与践履者,是其价值指向的贞认者。其二,圣人与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施动与受动关系,因为圣人处身为世的姿态,最终决定民的生存状态。圣人(侯王)若能持守自然无为之道,损却好恶、贤愚、货殖的分辨,则民自然葆有自化、自正的原初素朴状态,于圣人而言是自觉主动的行为选择,于民而言是自然被动的结果。虽然两者都是《老子》中具体的身体主体构成,但是民并不具备切实的主体性,他们的生存状态只是圣人践履自然之道的结果,所以圣人才是自省、自觉的身体主体,而民只是自然自在的生命状态。因此,我们所要谈论的老子之身及其由此带来的争辩当是以“圣人”这一身体主体为本。
二、《老子》中的身体主体构成及其价值指向
(一)礼乐建制对身体主体构成的形塑:《老子》的言说语境
中性意义上有关五官感知生理属性与功能意义的描述,是轴心时代所有论说展开的前提,正所谓:“目辨白黑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荀子·荣辱》)身体器官各有其生理功能是生就如此的自然属性,在礼乐对身体主体的形塑过程中,基于感官知觉的自然属性却生发出其价值属性,为礼乐建制提供身体论依托。
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国语·周语下》)
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五行· 45- 46简》)
目者,心之浮也。言者,事之指也。作于中,则播于外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口内味而耳内声,声味生气。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言以信名,明以时动。名以成政,动以殖生。政成生殖,乐之至也。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国语·周语下》)
诚在其中,此见于外;……初气主物,物生有声……心气华诞者,其声流散……听其声,处其气,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后,以其见占其隐,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谓“视中”也。(《大戴礼记·文王官人》)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先秦的身体观,感官感知与血气心知为一体贯通关系,两者之间呈现双向互渗、交流沟通状态。《国语》中的论说强调由表及里的显发,耳目感知是心的枢机关键所在,耳和视正、耳目聪明才能导致思虑纯固。口辨味道,耳听声音,声音和味道产生精气,精气显现于口为人的言语,渗透于目是人的观察,如果所视所听出了问题,不仅是对耳目的损害,同时也意味着损伤了人的精气,从而整个身体失去和谐。可见此时已贞认感官感知对于体气心知的塑造影响之功。在双向互渗的另一向度,也强调体气心知对于感官感知的渗透,是由里及表的显发。不同身体主体的内在“心气”不同,那么其声色自然有异,可以凭借他的“温好”之声,判断此人心气“宽柔”;也可以凭借一人“其声斯丑”,判断此人心气“鄙戾”。这便是“诚在其中,此见于外”的“视中”之法。“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目者,心之浮也”,意思非常清楚,感官感知是对于心知的执行,是其外在显现,心的绝对主导地位到孟子、荀子的文本中进一步确立,所谓心为大体、为君之论,所谓胸中正,眸子才可以正。总括来看此一体两面,感官感知与体气心知之间的双向沟通互渗关系清晰,各种文本都见出对表里内外互通关系的肯定。故此整个先秦时代的身体观是一体观而非二元论,耳目-心气是一体贯通的,同时非常重要的是,也未见将心与气对立起来表述的情况。
春秋时代的文本中时见这样的表述:视听味之正与不正、和与不和。从生理属性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几乎所有的文献中,这个问题是如影随形的。如此可见在辨析身体主体内在构成的同时,身体的价值属性一并被构建起来了,甚至可以说,对身体观的确立是为礼乐建制提供身体基础。
《左传》中,“气”首先是宇宙天地氤氲的自然之气,所谓“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是也。万物有机体尤其是人作为生命有机体,他的好、恶、喜、怒、哀、乐皆源于此,在天人感应互通的关系格局中人的六种情绪变化分别对应天地自然之气的六种状态,可见身体之内的气息流转与天地自然之气是一体互通关系,而后者为本源。“五味”、“五色”、“五声”皆为气之显发,如果它们“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所以对于气所生发之声色味必须有所整饬,才能保证“哀乐不失”、“协于天地之性”。由此“礼”的正当性、自然性、必要性呼之欲出,于是赵简子心悦诚服,“甚哉,礼之大也!”礼乐建制变成了天经地义之事,声色味便“为礼以奉之”,制定六畜、五牲、三牺是五味所要遵循的,制定九文、六采、五章是五色所要遵循的,制定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使五声有所遵循。中性意义上的声色味有了等级的分界,在该与不该的区隔中,何目视何色有了清晰的层级规定,位阶关系有了具象的感性体现,基于感官感知的身体基础,礼乐建制将新的社会秩序确立于容动声色、举手投足间,此其一。其二,中性意义上的声色味有了善恶的价值分界。何者为正、顺、善、和,何者为奸、逆、恶、淫,并不取决于声色味自身的特质,而取决于与礼乐建制的社会秩序的呼应。就个体生命而言,体气心知的塑造源于声色味的滋养,所谓“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所以视之正与不正、听之和与不和是根本所在,只有呼应礼乐建制的声色味才是正的与和的,才可以由“耳目聪明,血气和平”,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诸上两点我们已清晰可见礼乐建制对于身体主体构成的规定性与形塑轨迹,所以中性意义上的生命体仅只是潜在状态的人,要想“成人”则必是要“能自曲直以赴礼者。”
(二)老子论身体主体构成及其价值指向
在厘清老子之身的真正落实者是圣人的前提下,在《老子》文本生成的整个时代语境中,我们来看老子对身体主体构成的分辨及其蕴含的价值指向。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3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 12章》)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为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59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老子·55章》)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老子·49章》)
在诸上涉及到身体主体构成的各章中,目/腹、心/腹、志/骨、心/气,具体所示虽有差异,但是前后的对照关系明晰确定:耳目五官感知、心志在一个序列,而腹、骨、气则构成另一个序列,两个序列代表不同价值取向,前者被老子否定,后者则被老子肯定。对照之下,《老子》对于感官感知与心志的关系表述并未发生变化,但是其“气”却与“心”分离,同时骨、腹从中性意义上的躯体感知中区分出来,进入与气顺应的序列。这是表层面上术语的使用差别。更进一步,“目”、“心”与“腹”、“气”在老子视域中的价值属性又当作何解呢?
老子处身的时代语境有其双重性:一重自然是礼乐建制对于身体主体构成的形塑,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的社会秩序。但是此一重是以理想状态存在的,哪怕是以“先王”皆尚之的姿态回望其曾确实存在。另一重则是礼崩乐坏的失序现实。单穆公与伶州鸠对景王的劝谏是如此脆弱,对声色味之礼制构建在其文本语境中便显反讽意味。孔子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自候王到官宦僭越之义日显,礼乐建制对于个体感官感知的形塑在现实社会境遇中面临全然崩塌的危机。
这是老子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的双重语境。五色、五音、五味表面来看是现实状态中人人不可遏制地追求纵情声色。究其因由,老子却以为起于礼乐建制的等级分界与善恶附会。这与原始儒家的诉求无疑有着本质差异。原始儒家是做出善恶、美丑、顺逆、庄淫的分辨,贞认其一极;在忍无可忍之后,用心良苦以求礼乐文明之重建,并尝试建构礼乐建制之学理基础。而道家则勘破分辨本身,反思礼乐建制本身所弊。“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38章》)庄子将礼乐建制对于身体主体构成的形塑之弊说得更为具体:“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庄子·马蹄》)又“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庄子·骈拇》)这两段可做老子上述所论极为恰切的注脚。真正损伤耳目心知的并不是中性意义上的声色味,而是被礼乐构建了的声色味,是礼乐建制对目、心的蒙蔽与伤害。老子说“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甚至描述“小国寡民”的社会图景都是在试图消解礼乐文明让耳目心知失真的努力。既然如此,《老子》文本中的“心”、“目”便不在中性意义上使用,而是指在礼乐文明的建构与失序双重格局中,被形塑又陷溺的身体感官与心志。林语堂说:“‘目’指外在自我或感觉世界。”[3]107此解在先秦语境其实可见渊源,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五官感知与物为接,所以容易为外物蒙蔽,不免陷溺。当然孟子所论有截然不同的旨趣,因为接下来他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显然是强调心性本体的路向,而《老子》文中的心性与耳目五官一样早已被礼乐建制所形塑,并因此被挑逗起无穷尽的欲望而最终让礼乐建制失序。所以老子才说圣人之治,“不为目”,虚其“心”、弱其“志”、“浑其心”、不能“心使气”,所要损却的都是被礼乐建制所附着的“心”与“目”。“‘虚’不是去本在自然之心,而是清除附着于其中的人文化成之后滋生出的种种欲念心志,清除之后回复到自然自在的本心状态。”[5]58只有去礼乐建制对于身体的形塑之弊,心才可以复本心、目才可以复明。
老子对“腹”、“骨”、“气”的肯定态度十分显著,不同于先秦文献中“心气”并置的表述,“气”在老子文本中意义非凡。“气”凡三见,一处论气为万物之本:“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42章》)一处论修身成圣的工夫:“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老子·10章》)再就是“心使气曰强”,集合三处之义,以气为身体之本的观念已显出端倪。“治人事天”,要在于“啬”,高亨注:“天,身也。”[3]295河上公本注:“治身者当爱其精气不放逸。”[3]295两相结合,更进一步佐证老子以气为身体之本的论说。所以持守身体本在之精气,才是真正的“长生久视之道”。
圣人之治,“实其腹”、“强其骨”、“为腹”,蒋锡昌说:“‘为腹’即为无欲之生活”[3]107,林语堂则说:“‘腹’指内在自我(the inner self)”。[3]107因为“无欲”是《老子》中高频度出现的表述,并不在中性意义上使用,“为腹”与“无欲”并置有点儿同义反复,以“内在自我”与“感觉世界”相对解释“腹”与“目”又无法撇清“腹”可能与“心”发生的混淆。就其字面意思上讲,很多人将“为腹”视为对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又有生物本质主义的嫌疑。
五官感知与心志皆与物为接,试若“为目”,目之所欲为周遭情景所浸染而不易察,同时耳目感官彼此连觉、感通,很多时候感知的愉悦并不真正来自这一感官本身。举例来说,所谓“活色生香”便是在对象性关系中感官感知本身的失真状态。习语常说“口腹之欲”,其实不同,尤其在老子看来,口之愉与腹之适有着本质的不同。味觉快感与腹部舒适之间的差异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是很容易分清的,然而这一不同经常被深切的混淆,区分这一不同是理解老子深意的生物基础,腹与骨的感受不会因对象性关系而与物为接,也不会在礼乐建制中被形塑。要知老子的身体并不出离具体的社会情境,他还是谈境遇中的身体,但是身在境遇中,却“不知有之”,老子推崇的最高妙的姿态,是“太上”之境,对境遇中的物与身抱持一种两相自在的状态,为何是“为腹不为目”,恐怕有这样的寓意。承上所论,境遇中的“目”不免受制于具体情境中的“色”,而境遇中的“腹”、“骨”却似绝缘体,不为所动。以“腹”、“骨”为喻,可以更具象的引领大家体认身体主体构成本然自在的状态,而对身体主体构成本然自在状态的追求也才是老子要提领出的生命境界。
至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目/腹、心/腹、志/骨、心/气的两个身体构成序列意义不同:“这个‘腹’指的不是生理形躯,从根本上说,是指身体的自然性,这个‘目’(心)指的也不是人先在的感知意识能力,而是指身体被社会化之后滋生出的非自然性。”[5]58对自然性与非自然性的界定作为价值甄别,以自然性为其人文诉求。依然是在社会境遇中的身,但身自为身。
在理想的身体主体状态中,两个序列将统和为一,耳目、心志、骨腹、气一体贯通。那么以肉体、精神二元对分的观念分辨其贵身与否明显不恰切。同时老子的两个价值序列中杂糅肉体与精神,若依肉体与精神对分,谈老子贵此贱彼,还是贱此贵彼,实在都不得就里。
由现实格局来看,圣人“治身”皆始于自觉,是自觉自为的行为主体,民从“注其耳目”到“心不乱”的“处身”状态则得益于圣人之治,是圣人自觉自为的后果。若就整个思想氤氲渗透而言,圣王又内转为生命境界层面的内圣,于是人人皆可以此为生命境界之高标,修身以成圣。成圣之途亦见出圣人之身的微妙意趣。
三、以“无身”为身的消解与构建
(一)成圣之途的“损”与“复”
圣人的姿态首先以一系列否定式的行为显现:“去甚,去奢,去泰”(《老子·29章》);“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老子·3章》);“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老子·22章》)。河上公註:“甚谓贪淫声音,奢谓服饰饮食,泰谓宫室台榭。”[3]186已是非常具体的直陈,可见圣人对陷溺于礼乐建制鼓荡而起又无可遏制的沦丧于其中的耳目感官与心志欲念的消损与否定。老子不断告诫彼时之候王:“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老子·26章》)再看44章:“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名、货与治身对应,都可见老子对于理想生命情态的诉求:对陷溺于物的耳目五官感知之欲的消损;对陷溺于物的心志欲念的消损;对执着于一己之身,以自我为核心,充分凸显一己之欲的消损。
圣人的自我修炼表现为:“欲不欲”、“学不学”、“为无为”,“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无知”、“无欲”、“无为”,“不争”、“守道”。如何才是守道之本?“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48章》)圣人的“无为”并非指被动、放弃无所作为的行动状态,仔细留意会发现,所有否定状态的行为其实都包含主动选择的前提,于是所有的否定、弃绝都不是中性意义的,而是彰显老子明确的价值指向与观念意图。为的是“无为”,而同时“无为”带来“无不为”、“不争”带来“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极大利好后果。所以钱钟书说此为“尽人之能事以效天地之行所无事耳”[3]66。可谓一语中的。
由此我们看到圣人之治身与治世显现出卓然不群的态势。郝大维将“无欲”译为“无对象的欲望(objectless desire)”,并说“这个译法与我所解释的‘无知’和‘无为’相呼应。非原理性的认知和非强加的行为都不会造成对世界及其组成部分的对象化。同样,与‘无欲’相联系的欲望不需要通过占有、控制使我们所‘欲望的’东西对象化。”[6]218老子警告现世中的候王“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老子·29章》),所以圣人处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无执”、“无为”,王弼注:“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可通而不可执也。”[3]184可见圣人治身与治世皆“尊重那种内在于自然的方式”[6]222,任物自然。当然这个“物”不只包括外于己的物,也包括内于己的身。这是非自我-对象二元论的路向,不以自我为核心本位立场,世界是一个多元并在的有机融生体,不执着于一己本位立场,便不会抱持我与他者有根本分界与等差地位的体认,“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16章》)一己与他者都是世间万物之殊相,若可任物为物,任民(在候王与民的位阶格局中)为民,则不仅物与民得以复其本性,“万物自化”、“民自朴”。自己也从对象性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然本在的身体情态,耳目感官与心知从声色货殖之物的陷溺中回复本心、本目,成就一气贯注、筋柔骨健、自然状态中耳聪目明的生命体。
(二)从修身格局看以“无身”为身
行文至此,我们亦可以明了《老子》的文本语境中“身”至少有三种分辨:原初之身、现实之身、理想之身。原初之身作为理想之身的隐喻,以婴儿的身体意象为标示。在成就理想之身的修身工夫中常常出现:你的含德之厚能如婴儿吗?你不为物扰、不为欲惑能如婴儿吗?你的身体情态一气贯注能如婴儿吗?……现实之身用来指耳目心知被对象性关系牵绊,其占有之欲念而丧失本真状态的身体。众人“熙熙”、“察察”,“注其耳目”如此,侯王“多藏”、“甚爱”、“尚显”、“贵生”者也是。理想之身作为老子的理想生命情态,勘破现实之身在形塑过程中的失真状态,消解形塑现实之身的价值属性,以回复身体之自然原初状态为终极诉求,借助原初之身的隐喻,建构起老子理想之身的价值旨趣。
来看涉及无身与有身之辩的其他章节: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7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老子·26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44章》)
首先可以肯定老子是贵生的,所谓贵生,当然不是现实之身对于生之厚的执着,而是珍视生命的意思,“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的追问中,珍视生命之义已然显著,而现实之身在具体的社会境遇中却难免陷溺,所以老子发出这样的警告。珍视生命之义在大量的篇章中,也都可找到支撑的依据。老子反复提到“长久”之道、“长生久视之道”,如何可以“无遗身殃”、“善摄生者”怎么做等等皆是。
蒋锡昌释26章“以身轻天下”,“言人君纵欲自轻,则失治身之根”[3]173,可见此身是指现实之身,7章“后其身”之身、“外其身”之身,13章“所以有大患”之身都是指的现实之身,此时的身体主体沉浸于声色、货殖、贤愚、贵贱、高下的分辨中,其实已丧失生命原初的生机,当然是应当消解、损却的,所以老子才说要“后”之、“外”之、“无”之。消解掉现实之身对于对象性欲望的执着,则身体的原初生命状态得以复现,这是老子对于理想之身的描述。所以“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得以“先”和“存”的便是理想之身,而以此理想之身治世处天下,才放心可以把天下交给他。吕洞宾以“先天之身”与“后天之身”、“道身”与“凡身”分辨,“是存道身,外凡身”[7]。而刘笑敢则捻出“真身”与“世俗利益之身”[8]对照,诸上都是近似的意思。相形之下,我们以现实之身与理想之身对照,再辅之以原初之身为参照,旨在凸显老子对身体主体的构建之义,老子视域中的身体主体并不真正落实向原初之身,而是以原初之身为隐喻,表达其对理想之身构筑的价值旨趣而已。如是便可窥见老子以“无身”为身的内在消解与构建理路。
参考文献:
[1]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93:48- 49.
[2]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M].成都:巴蜀书社,2001.
[3]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137.
[5]张艳艳.先秦儒道身体观与其美学意义考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郝大维.从指涉到顺延:道家与自然//[C]安乐哲,等,道教与生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7]吕岩,释义.吕祖秘注道德经心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6.
[8]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80.
(责任编辑:李金龙)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4225(2016)03- 0005- 08
收稿日期:2016- 01- 13
作者简介:张艳艳(1978-),女,山东滨州人,文学博士,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先秦儒道身体观的美学意义再考察”(10CZX049);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先秦环境美学思想研究”(Yq2013075);汕头大学“基督教、生命教育与宗教文化”研究专项资助(STUCCS2013-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