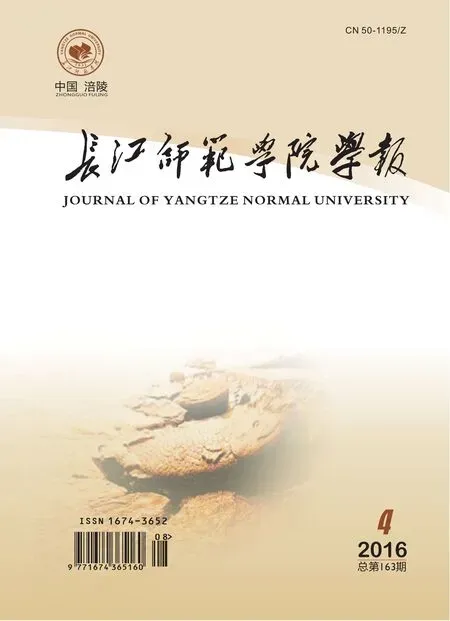乡村到城市 “人性异化”的隐喻和救赎
——木兰长篇小说 《云雀》解读及其他
2016-03-28周航
周航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重庆 408100)
□文学研究
乡村到城市 “人性异化”的隐喻和救赎
——木兰长篇小说 《云雀》解读及其他
周航
(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重庆408100)
湖南侗族青年女作家木兰因在 《花城》上发表长篇小说 《云雀》,近年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这里从小说文本的独特性、叙事特质、自杀的精神分析和生命苦难本质的探寻,以及爱的救赎和文学的治疗等几个方面以深入的解读,个案性地探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人性异化”的隐喻和救赎的深刻内涵。
《云雀》;叙事特质;异化;精神分析;救赎和治疗
《花城》2012年第2期发表了木兰的长篇小说 《云雀》,其作者是一个在外漂泊多年的湖南侗族女子,原名王建华。她的小说迅即引起人们的关注,大概缘于 《云雀》的确是一个独特的文本。
“自叙传”性质,大概是这部小说最为人所猜疑的问题。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法郎士曾言:“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其意是想说明凭空想象的东西不可信,也脱离实际。我国现代开创一代文风的郁达夫将之奉为小说创作的圭臬。在木兰的 《云雀》中,叙事人、作者和主人公 “我”3者之间常有重叠交合之处,让人难以分辨哪些是虚构的,哪些是生活的真实再现。从作者的一些自述和与“我”的交流中,小说中的人物、事件与她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的确有很多的重合之处。她在单行本出版 “后记”中说:“感谢我的父母、两个姐姐和哥哥,是他们艰难的人生,为我提供了丰沛的素材和关键性的创意,并成为我写作的动力。”凡此种种,都会让读者倾向于将小说与她本人联系起来,并产生巨大的痛惜与怜悯之情,同时与她一道感叹人生的苦难本质与虚无缥缈。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小说没有融入她“自叙传”性质的真实而深沉的人生体验,她是无法写得那么细腻而痛彻肺腑的。这种文本内外的交错性,确实让我们感受到小说所带来的戏剧性效果。其实,小说中内容的真实与否,已不再重要,因为文学的真实性已经实现。
弗洛伊德说过,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是作家精神的错乱、呓语性和性本能,这成为他这个哲学家用来解密文学的钥匙。实际上,“自叙传”性质和被人猜测的真实性问题,在作家的思想里,很多事情她也不知道是否真实。在作家的大脑里,小说中的事件是真实的,比发生过的事情还要真实。小说中与情人的爱情是否真实?她可能不知道,或许不能绝对肯定,但至少在她大脑中发生过了。只要是她写过它,对于大脑产生的影响就和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印象就是一样的。这就是暗示和想象力的作用。在作者的家庭成员中,或许确实有一个自杀了的哥哥,也会有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存在一个反复自杀的母亲和两个姐姐,连作者本人也是一直纠缠于死欲的一个人,但我们纠结于此的结果最多是知道一部作品的发生根源,而并不能估测它面世后所带来的文本价值。不过,如此有趣的争议与猜测,本身已构成了这个文本价值的有机部分。因为,这恰恰说明了,正是文本非同凡响的震撼力,才让人那么急切地想探究一切,以至于产生了文本的虚构性和文学真实性之间的交混。
作为自叙传性质的小说,其实算不上独特,关键要看叙事本身的独特性。归纳起来,《云雀》的叙事特质,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作品强烈的精神幻质和异化的生命体验。可能缘于作者本身是一位忧郁症患者,作者在与读者 “回头”时,将会发现小说的叙事总是在现实、想象和梦幻之间往来穿梭,具有强烈的精神幻质。小说一开头,便是一场告别与回归的幻想情境。接下来是关于 “真实与虚构”“死亡和苟活”的论述,旋即把读者拽进了作者关于自杀的独特感悟之中。只有深刻思考过自杀命题的人,才可能对这样可怕的事情有如此冷静的对待。从整部作品看,很像是一位忧郁症患者的一场 “谵语”。与此结合在一起的,作者大量使用议论手法。有时把议论融入叙事和描写之中,在叙事和描写的过程中发表见解;有时直接由议论带出叙事和描写;有时纯粹就某事、人、物发表看法,没有叙事和描写的夹杂。这类表现手法的充分使用,有利于向读者充分展现一位忧郁症患者不同于寻常人的内心世界。虽然精神病人在身体和行为上也表现出病症,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精神世界的异化。“我对待混乱无序的艰难生活,总是如此怡然自得,好像很无所谓的样子。我怀疑,我天生就该属于这样的环境,过这种生活。只有在这个地方,我才能意识到自己本质的存在。从根本上,我就是属于这样一个地方。”(木兰,《云雀》,花城出版社,2011年,第64页。下同,不注。)这一类独特的生命体验随处可见,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文字充分了解到主人公深刻、复杂、独特、已经变异了的内心世界,很容易激发读者的同理心,然后不知不觉地痛惜起他们的不幸遭遇来。
其次是小说采用了倾述体。叙事人把读者当成值得信赖的倾述对象,急迫地向读者倾吐她身上所发生的所有故事,以及她心中所怀有的浓烈情感。这种文体极易拉近叙事人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跟你说些什么好呢?”(第6页)从这里开始,读者就进入了叙事人所设定的情境。通篇来看,叙事人在讲述时的心境极端忧郁,甚至有点歇斯底里,话语当中总是带有非常强烈的情绪。“我已经无法呼吸了!我已经无法呼吸,我就要死了!我将为眼前的这个男人窒息而死。”(第51页)这种浓烈的感情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可能轻易见到,人们更愿意用一种心平气和的语气与人交谈。但作者是一个忧郁症患者,经常处于绝望之中,所以说话口吻夸张,并把这种极度压抑的情绪感染给了读者,让读者在阅读整个作品时有一种难以解脱的纠结和惋惜,不禁潸然泪下,感动不已。
第三,小说的语言十分独特。在东莞 《云雀》作品研讨会上,作家千夫长说:“小说语言独特,节奏感强,好像不断地造句。作者没有固定的写法,不同角度不断进行造句。造句反而像这样一个东西:词语的变化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位置。”如果反复阅读作品,就会发现其中用词经常反反复复、在同一个句子里不同组成成分的语意前后断裂、段落之间同一个意象不断循环、句子节奏感强、意境诗化,等等。
“这样的情境,让我低头自喜;这样的情境,我从未对他人言说;这样的情境,它不是突然萌发的。它就在那里。在我幼小的童年时代,在我盲目的青年时代,它已经在那里。然后,在万物显露的中年时代,在这样的夜晚,我明确了自己的意念。”(第6页)在这个小段落里,反复出现3次 “这样的情境”、3次 “时代”、3次 “它”。那么,这里的 “它”所指代的是什么呢?它代表一种想要告别城市回归家乡的美好愿望,是想象中的虚幻情境,并非实指。“那床单是柔滑的质地,湿了、凉了,我感受那悲戚。”(第23页)每个词之间的跳跃很大,断裂感强烈。“在那个夜里,这个暗影里的幽灵,从冰凉和痛苦之间走出来。每天晚上从他的车子里走下来。”这两句话之间完全是一虚一实的搭配。前面为虚,后面为实。但是就因为一个 “走”字,又很好地连在了一起。最后一章几次出现 “火车站”这个富有诗意的意象。从火车站到火车站再到火车站,这是某种情绪的不断加深,类似于诗歌的复沓。整篇小说的情绪让人感觉到非常饱满,其实跟这些手法的使用大有关联。
第四,在结构上,故事采用双重线索。主人公站在现在的时间点上,一边回忆24岁时 “我”与情人相识相爱后来又不得不挥手离别的一场凄美爱情,同时穿插了 “我”的反复自杀的家人如何走出 “死欲”的家族故事,属于回忆体。而这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之中。作者为何作出如此的安排?“我当时想人物的关系就像画画一样,从表面来讲,这个画的中心是 ‘我’和 ‘他’这两个人,是明的、亮的。从背景来讲,背景是家庭。”①张鸿《平静生活中的绝望》,《花城》,2012年2期。此外,小说所使用的这种回忆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不断变换,跳跃性强,在时空的打散与往复中,几十年的家庭故事演化为—个个片断,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将它们拼凑在一起,组成一幅幅完整的画面。这种结构很像现代绘画的拼贴手法,既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又有利于将流动的情绪充分地展现出来。
第五,其他艺术手法的运用。小说受到电影叙事的影响,具有画面感,很多画面不断重复回旋,不断加深印象,不断加强情绪的感染。此外,小说中的人称也富于变化,一会是 “我”,一会又转变为“她”,有时是 “这个年轻的女子”,仿佛将镜头转向了自己,将自己仔细打量观照,从而实现了从内视角到外视角的视线转变,并具有了镜像感。
互文性。云雀是法国的国鸟,它象征着面对死亡依然保持乐观积极的生命态度。《云雀》本是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米什莱的散文名篇。木兰的长篇小说取同样的名字,缘于两篇文章有相同的寓意。无论 “我”的一家人曾经遭遇多少次死亡考验,最后都从 “死欲”里走了出来,这是一种坚强的、积极的生命意志。关于这一点,在小说中第31页有对米什莱 《云雀》部分内容的间接引用,从而点明小说的主旨。
环境描写富有象征意义。在文中云雀多次出现,每次描写都不一样,象征着女主人公命运转折中的不同处境。这些描写反映出女主人公内心挣扎的过程。人物深含隐喻性。木兰笔下的人物总与时代密切相关,而且极具象征意味和隐喻性质。比如,母亲是传统的、保守的,两个姐姐是时代漩涡中的挣扎者,哥哥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多余人”“我”的情人确实是一个家庭、事业、爱情中的游离者,“我”无异于拯救者 (拯救他人也自我救赎),父亲怎么看都是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寄托。各个人物的关系发展形成了一种极致性的冲突和舒缓,生与死之间的距离,在这里得到了最根本的阐释,而人生最重要的过程又莫过于生死之间。当然 《云雀》的独特性并不仅限于此。
自杀是一个古老的文学话题,也经常成为文学主题分析的对象。比如歌德小说 《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维特不得不放弃爱,放弃生活,愤而自杀;《包法利夫人》是法国文学描写自杀相当经典的一部。福楼拜在他的 《年轻的事业》中说:人 “生来就追求死”,爱玛的死恰巧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利娅患上了文气的精神病,为了找到鲜花点缀花圈,竟然自沉而死。自杀也是哲学的真正起源。诺凡立斯在他的 《断篇》中指出:纯粹的哲学行为是自戕,哲学家的一切研究均从这里出发。阿·加缪在 《西西弗斯的神话》中也阐述了大同小异的观点,他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人生活在世界上究竟是否值得,将是对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回答。”近些年来,自杀也成为了现代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成为人类思想史的重要研究对象。
弗洛伊德是第一个严肃地从事自杀心理学研究并取得硕果的人物,他在晚年提出了 “死本能”学说,这让多数人难以接受。他指出:人有自我毁灭或对外攻击的本能,死成为一种欲望,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对人极富诱惑。当 “死本能”向内投射时,就会自我谴责、自我痛恨、自我惩罚和自我毁灭。
社会学家也越来越关注自杀现象,迪尔凯姆在 《自杀论》一书中,试图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解释自杀的原因,并把自杀划分为4种类型,即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他在研究中还发现,如果一个不幸的人,家里既有精神病患者又有自杀者,他之所以自杀,绝不是因为他的父母是自杀者,而是因为自杀的强烈感染力。因为他们的神经脆弱,使他们容易被吸引,同时又使他们容易接受自杀的念头。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小说中看出。“我相信自杀是一种病,想要寻死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病……那些年,前后有整整十年时间,家里的人都犯上了这个毛病。”(第9页)自杀倾向是忧郁症患者的一大症状。《局外人》对生命的冷漠、《地洞》无处不在的恐惧、《云雀》非自杀不可的 “死欲”,都是忧郁症的症状。《云雀》中病态的人物、病态的爱情、病态的家庭,甚至连语言都是那般歇斯底里,始终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死亡的阴影。
通常而言,人们对宝贵的生命倍加珍惜,即使处在绝境之中,也要想尽办法活下去。患有忧郁症的自杀者却表现出对生命的无所谓态度,对生命本身厌倦,对生与死极其冷漠。小说中的 “哥哥”,如果暂时将之拉出精神分析的世界,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作一个典型的 “多余人”形象。他是特定社会、传统家庭和自我性格共同熬制出来的病态结晶。最为典型的 “多余人”形象就是普希金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叶普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此外,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 《多余人日记》,赫尔岑 《谁的罪过》中的“别尔托夫”,还有屠格涅夫 《罗亭》中的 “罗亭”,等等,都不乏 “多余人”形象的描绘。在这类作品中,理性意义广阔面的自省力量显得苍白无力。作家的使命就是在人类广阔而深邃的精神世界里进行探险,作家本人也随时面临着精神崩溃、神经分裂和情感变异的危险。对于这一点,木兰在小说中也有所阐释。她在小说中反复提及的诗人海子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我”害怕踏上海子的人生道路,所以一直抗拒写作,正是因为 “我”看到了成为一个作家所要面临的巨大风险。
现代人所受的苦难更多地体现在精神上,这可能跟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凸显、日益增强的孤独体验有关。小说中哥哥的意志是软弱的,又常年生活在农村,他未能逃避对活着的理由和意义的追问。“他总是在本子上写着:为什么不自杀?为什么不自杀?”(第8页)女主人公对人生的看法则定格在苦难之上,并且认为人生毫无意义。“我真的想死掉,生命毫无意义,除了你必须完成的责任,你生来就要担负的一切。”(第68页)为此,女主人公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并寻找长期迷失自我的根源,这是自我追寻的一种体现。小说中的二姐也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烈的女子,潜意识代替她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选择——离开农村,到城里生活。这种人生的选择并不是为了贪图城市生活的舒适和逸乐,而是基于对世界的好奇心。但她为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反复破产、离婚、孤独、自杀、精神崩溃,必须借助服用药物才能维持仅存的理智。“我们无法接受普通人的生活,从而安于生活的平淡,世俗的规定,安于每一日的和顺。我们这样执迷,究竟在寻求什么。”(第62页)她在寻求什么,答案依然是对自我的发现,苦苦寻觅,却找不到要找的东西,这大概就是人的宿命。
苏格拉底说:人啊,认识你自己!这个命题在现代社会尤为重要。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而且其过程十分艰难,许多人穷其一生,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认为,人在实现自我潜能时,一旦遭到无法跨越的障碍,就会产生许多的不良情绪,比如自我疏离、生命无意义、虚无、孤独、恐惧、不安、焦虑,严重者甚至发展成为精神病,表现出对生命的绝望和冷漠,最后自我毁灭、自杀。
人不仅要实现自我潜能,也要得到社会认可,这是由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而且两者经常结合在一起。当人们认为自己不被社会所接受时,也会产生自戕的行为。比如小说中为封建思想所蒙蔽的母亲,她之所以要自杀,并不是因为无法实现自我价值,而是她自认为没有完成社会所要求的女人必须为夫家传宗接代的责任。文中的哥哥自杀的理由不仅体现在无法实现自我的潜能,也在于无法承担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因而得不到社会的肯定。如果说人的自杀动机有多种,那么不管是社会的、个人的、经济的、道德的,还是其他什么理由,无论哪一种,其结果都会产生各种不良的情绪,它们对人的精神和情感系统会产生巨大的冲击。相对而言,敏感、神经脆弱的人就更加容易精神受损,走上自毁的道路。
在自杀与否的过程中,要看生存和求死这两种欲望之间的力量对比与消长,最终哪一种占上风。如果生存的力量最终大于求死的力量,那么就会生存下去。如果死亡的力量最终大于生存的力量,就会求死。哥哥的人生,他的生存下去的力量要远远小于求死的力量,所以才一直求死。“我”虽然贫穷,家人的事情还有为了家里不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抗拒写作,但毕竟 “我”的学业很好,所以希望还存在,所以一直没有自杀。后来在工作中遭遇到各种精神分裂的痛苦,哥哥的境遇越来越糟,姐姐的精神病态,这些给了 “我”巨大的压力,导致 “我”夜夜噩梦,握紧拳头,没有办法活下去,几乎近于精神迷乱,甚至一度想去做风情女。但 “我”遇到了爱情,这拯救了 “我”。后来失恋,让 “我”重新回到 “死欲”之中。再后来写作又拯救了 “我”。母亲也是经常求死,两个姐姐同样地挣扎在生死之间,但最后她们重获希望,活了下来。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家庭的苦难史和心灵史发生在城市化的社会大背景之下,4个孩子的命运分别代表了一个农村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同的生存状态。哥哥留守农村,大姐和大姐夫长期在外打工,二姐和二姐夫通过从商从农村走出来,终于在城里安居,“我”通过高等教育,来到了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个人的命运,都在这个通常被称为千年之变的时代背景中演绎出来。这或许揉入了小说的另一重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尤其是农村人,曾经遭遇到精神的重创,而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重创背后的深刻的社会原因。譬如农民不再仅仅眷恋着土地,或者仅仅依靠土地求生存,或者说,土地能够提供的远远不能够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中国人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而且广泛地出现了一种迁移的现象。在小说中 “我”是通过考大学后跳出农门的,两个姐姐是外出打工挣脱农村的,唯独深受奶奶、母亲溺爱的 “哥哥”永远无法离开农村半步,离开就意味着无法生存下去。然而,于读者而言这一切都可视为社会转型期农村的某种隐喻。其中,大批农村年轻人,成为游离的一代、多余的一代,这或许是小说中痛感和忧郁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源头。
我们还可通过心理分析的途径,看到这种疾病发生的某些社会根源。罗洛·梅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人既不能与自我相疏离,也不能与社会、与大自然相疏离,不然内心就会产生不良情绪。但现代社会由于城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人的流动性也大为增强,这必然会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无力。而且现代人崇尚理性和科学,不重视感情交流和生命感性领悟,这也会增加人的孤独感。“孤独与生俱来,是一种天然存在。人与人之间总隔着某些东西,无法相通。我们每天费尽心思说话,想要表达自己,阐述自己,结果还是没有用。”(第20页)由此看出,之所以一个农村人走向城市并在城市定居之后,反而更加容易引发精神疾病,这跟他在城市里感到孤独、被遗弃,找不到安全感,长期感到焦虑、不安有关;当然也与离开大自然的怀抱有关。也因此,出生在农村、后来在城市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 “我”,反而越来越向往山村生活。在小说中一开始就描写了一个即将离开城市回归农村的想象情景;在第二章也写到我对城市生活的厌倦;在第五章,写到 “我”有一次回家过春节,跟着父母去姑父家走亲戚,看到一整片松树林,沉浸在浓雾之下,“我的心中随之涌起一种别样的情感,我发现自己整个儿属于这里。只有在这里,我才能让自己的内心感到宁静祥和,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我的人生,因为出生在这样的山村,就永远与这里不可分割了。”(第29页)
生命苦难的本质或许与生俱来,而不单纯由外界所引起。这种苦难本质上不会产生令人颤栗的效果。如果命中注定,甚至带有无法抗拒的某种神秘力量,那么这种苦难我们将更容易置于精神的最深处,也将更令人唏嘘。《云雀》中人物的病态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是家族性的、遗传性的,在人生的最初就融入到他们的人格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带有难以逃脱的命运规定。在这里,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虽然没有犯下罪行却都受到了惩罚。根据性格决定命运这个推断,因为自己无法决定自己的性格,所以自己也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小说中 “哥哥”完全没有反抗的力量,他的性格软弱是母亲和奶奶带给他的,但“我”的坚强,是理想化的父亲给予 “我”的。从他们两人身上,可以看到性格的决定因素不是来自本人的自由选择,而是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萨特在他的最初的哲学观点中,提出自由即选择。当然后期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自由的责任,这种观点与后来加缪提出的反抗意识殊途同归。实际上,人经常缺乏选择的力量,也就是缺乏获得自由的力量。小说中只有 “父亲”这个形象能够在那沉闷死寂中给人一点希望,其他的虽然在结尾时没有明确给我们带来绝望,但无一不蒙上了死亡的阴影。小说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或许深埋于此,甚至会让任何解读都显得苍白无力。
提及 “爱的救赎”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是对家人的爱。小说中虽然弥漫着自杀和死亡的气息,着力地讲述了 “我死去哥哥的故事”和亲人在死亡边缘的挣扎,但 “我”一直之所以没有最终自杀,是因为 “我”这个唯一读过大学的在外漂泊的女儿,承担着 “家族拯救”的重担,贯注了对家人深深的爱,“我”希望 “我”的努力和爱能够将这个家庭拯救出来。这又使小说在寒酷的氛围之中抽离出丝丝暖意。其二是 “我”和情人的爱。小说单行本封底可能出于商业目的,上架建议是:都市言情小说。虽然这种做法与小说真正的精神内核相距甚远,但也并非不可作如是观。“我”与家人的关系、“我”与情人的关系,确实织成了建构这部小说的两条主线。只是这两种爱的救赎都是病态的,譬如我不堪忍受家人给我带来的压力,“我”的爱常常难以得到正常的施予,或者无力施予。“我”的情人其实也是一种病态的人格,“我”与他的快乐相处,注定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他不可能走出他的家庭。然而,小说传达出来的信息是:我”虽然开始时是因为 “情人”的出现而获得了生存下去的力量,但是后来的结局反过来了,“我”的情人能够从 “我”的爱当中获取活下去的力量。“我”和情人在无形之中又相互完成了一次爱的救赎和被救赎。
文学治疗源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然而,木兰的 《云雀》无论文本内外,都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文学治疗。如此说,将会使这部小说的价值超出文本本身,溢出了文学的另类功能。中国的作家大多数爱讲故事,但故事的背后更重要的是心理逻辑的真实和读者的感受。据作者本人说,写 《云雀》时正是忧郁症急性发作时期,当时她的情绪紊乱。而恰恰就在这个不正常的状态之下,木兰写下了这个让人猜测不已的独特而复杂的文本,那么小说的最终指向必然与救赎和治疗相关。从 《云雀》通篇来看,我们在解读时不妨将其作为一个文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等交叉性的综合文本来看待,或许我们所能感悟到的东西就不仅仅是文学了。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对 《云雀》的叙事特质、自杀等其他因素进行分析之后,我们还能感受到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精神脉象,看到乡村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所遭遇到的异化过程。
[1]木兰.云雀[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
[2][奥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4.
[3][法]迪尔凯姆.自杀论[M].滕文芳,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4][美]罗洛·梅.心理学与人类困境[M].郭本禹,方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张东天,徐连明,陶建杰.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6]《南方都市报》特别报道组.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丹兴]
I206.3
A
1674-3652(2016)04-0085-06
2016-03-22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现代化进程中的进城农民文化转型研究——以‘打工文学’为切入点”(2013YBW X083)。
周航,男,湖北咸宁人。博士,博士后,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