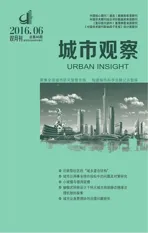论转型社区的“城乡混合结构”
2016-03-28蓝宇蕴
◎ 蓝宇蕴
论转型社区的“城乡混合结构”
◎ 蓝宇蕴
转型社区是在城市化与“城乡二元结构”松动条件下,城乡关系重构的结果。也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转型社区形成独特的社会结构,即“城乡混合结构”。该结构作为阶段性的本质特征,是转型社区深度城市化的基础和出发点,其存在和运行,虽然有助进一步拆解城乡二元结构,但也使社区关系过度纠结,结构性张力过大,并呈现出普遍的治理之困。把转型社区纳入城市运行系统、建立或健全现代社区组织结构、改革集体经济体制机制、建构具有针对性的法律制度及地方政策法规,在城乡机制或规则的互动中求得平衡,是走出治理困境的主要应对之策。实践中尽可能避免剧烈地打破原社区结构,而是通过多元渐进路径,以实现转型社区的现代转型。
转型社区 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混合结构
转型社区是与城市化相伴而生的特殊社区,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松动与趋向解体,并作用于微观社区的产物。所谓转型社区,本研究中特指为,行政村或原行政村已改为居委会社区的,正向城市社区变迁的过渡性社会单元。其中,“村改居”社区、城中村、城郊村或转制社区均是转型社区的不同称谓或不同形式。目前,我国转型社区数量庞大,仅“村改居”社区大致就占城市社区总量的四分之一,且仍在快速增长中。与普通城乡社区相比,转型社区治理的问题聚集,甚至普遍面临治理性难题(高灵芝、胡旭昌,2005;王碧红、苏保忠,2007;梁慧、王琳,2008;吴晓燕,关庆华,2015;曹姮钥、康之国,2015)。对转型社区的严峻治理状况,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但大多并未从其本质特征中探寻问题之根。有鉴于此,本研究认为,“城乡混合结构”是转型社区的阶段性本质特征,也是治理之困的核心症结所在。因而,本研究就转型社区的“城乡混合结构”进行系统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转型社区如何摆脱治理之困
目前,关于转型社区的治理之困,比较通行的解释是,村民自治或“类”村民自治(如“村改居”社区治理)的框架过于狭隘,无法承载转型社区的治理之重,致使治理问题丛生。①那么,村民自治或“类”村民自治何以变得越来越“超载”?而“村改居”也依然无法解决这种“超载”问题呢?本来,相对转型社区及其所对应的地方政府而言,“村改居”很容易成为化解问题的首选,但实际运行中的“村改居”社区,虽然获得了制度化的城市“外形”,却仍然难解社区治理之困,甚至在旧问题未解之际又平添了诸多新问题。
究竟如何破解治理之困?深入转型社区的结构中,才是问题求解之道。在我国高度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机制的作用,城乡各自形成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并且按完全不同的规则运作。与此相关,城乡关系主要局限在各自的范围之内,而不发生大范围的交集。但是,伴随城市化的推进,一些发达乡村社区越来越成为多元开放的社区,城乡关系混杂交聚。社区中如此性质各异与错综交叉的社会关系共存,如果不假以相当时日的梳理,其繁杂关系是难以理顺的。或者可以说,伴随城乡二元关系的分解和重构,转型社区的村社结构,由于自身具有的简单单一化特点,而越来越难以协调和整合日趋复杂多元化的社区关系,治理之难由此而生。
如果从结构论的角度看转型社区的治理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其“城乡混合结构”相关。处于这种结构的社区,既不能用村社型套路去解决问题,也不适合用居委型方式解决问题,而是需要根据转型社区实际,在不断寻求城乡关系的平衡中,才能获得“治病良方”。其中,既要利用或借鉴村社治理中仍在合理发挥作用的机制或方式,又要避免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缺陷,以求得社区关系的协调。即转型社区需要在各种不同关系的磨合中,才能实现社区关系的有序化。而在此完成之前,转型社区很难逃脱问题化的情境及其约束。理清“城乡混合结构”的运行逻辑,是理顺转型社区关系的基础。
二、转型社区“城乡混合结构”的形成和运行机制
“城乡混合结构”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主要用于描述和分析转型社区的体制机制及运行逻辑。所谓转型社区的“城乡混合结构”,特指存在于转型社区之中的、以村委会(简称村委)为代表的村社型体制机制及相关因素和以居委会(简称居委)为代表的城市型社区体制机制及相关因素交错并存,且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构成具有“亦城亦乡”或“似城似乡”特征的过渡性社区结构。该混合结构是目前转型社区的共性结构,且作用于社区各层面,无论在组织及权力关系领域,还是在管理服务领域,无论在心理文化领域,还是在生活和生产方式领域等等,均体现出城乡关系高度混杂交叉的结构性特点。
(一)转型社区“城乡混合结构”的生成
就渊源而言,转型社区“城乡混合结构”是在村落向城市社区的转型中,城市社会关系不断取代传统村社关系,并显示出阶段性特征的社区结构,是多因素作用下城乡关系重构的结果。城乡分立结构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建构的一种制度安排。当时,国家为便于对全社会施行垄断性管治,也为有限资源能最大限度地支持工业建设,而人为地在城乡之间竖起高度制度化与机制化的“隔离”之“墙”,使城乡成为各自封闭的结构。更具体而言,自上世纪50年代末起,国家针对城乡两种社会实体,分别进行了差异性与分离性的制度建构。在城市,除建构单位制这一主流基层体制机制外,还建构了以街道和居委会为载体的“街居制”体制,以弥补单位制管理的空隙;在农村则建构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籍此把农民整合进“巨无霸”的国家系统中。如此建构下的城市和农村,相互的差异性被空前放大,原本密切相关的城乡实体被活生生地置于严重“分割”状态。也正是国家的这种干预和推动,致使畸形城乡关系不仅得到维系,且获得相对持久的“再生产”,也致使形成相当稳固的社会结构,即学界所通称的“城乡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边界被打破,城乡关系进入了新的重构过程。由于城市化与城乡关系重构、转型社区及其“城乡混合结构”的生成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在此稍加展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的背景,既是乡村城市化的基本出发点,也是转型社区及其“城乡混合结构”得以形成的条件。在城市化与非农化的推进过程中,村社向城市社区演化,是发达乡村变迁的常态路径,而该路径恰好与转型社区及其混合结构的形成直接相关。随着城乡分立结构的松解,僵硬城乡关系进入动态化的变迁中,一些占尽天时地利的村社区,随经济结构的非农化,整个社区社会关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型。但整个社区的转型是建立在传统村社结构基础上的。随城市理念及其相关社会结构因素的不断产生或“嵌入”,且主要是依托村社结构及资源得以产生或进入的,此时的社区治理仍受村社性质的制约。②或者说,转型社区以村社结构进行的城市化,所形成的社区结构只能是城乡结构及其相关因素兼而有之的混合型社区结构。
值得关注的是,转型社区“村改居”的改革,在“城乡混合结构”的形成中也发挥重要的作用。表面上看,“村改居”是以制度化形式打破了封闭性的城乡格局,从而“架起”了村社变身城市社区的机制化“桥梁”,拓展了社区发展的社会空间。新世纪以来,发达地区的“村改居”改革进入大规模实操阶段。如在珠三角地区,深圳于2004年全面完成“村改居”,并因此而成为全国首个没有农村建制的城市。东莞于2002年启动这一改革,2014年底共完成196个村的改居任务;同年年底,中山与南海分别完成114个村和157个村的改居任务。更多地方的“村改居”改革仍在进行中。关于转型社区的这种趋同性改革,目的是要以城市社区体制机制替代村社体制机制,以化解或缓解过度密聚的社区问题。
但至少就短期而言,“村改居”的社区改革,实际效果上有事与愿违之嫌。由于“村改居”主要是政府促使下的被动、非自发、非自觉、外部因素强加的行为,且要求短时间内完成从村社向城市社区的转变,是“激进式”的变革。③与此相关,在已实行“村改居”社区的后续运作中,大多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快速转为城市社区并使治理性难题得到解决,甚至恰恰相反。由于在村社型结构不可能快速替换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居委型”的新结构,致使转型社区的社会关系更为纠结。中山市127个居委社区当中,仍有57个有施行村委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惠州市惠阳区东华村27个村民小组中,其中仍有18个居民小组以委托管理形式交由临近的司前居委托管,而被托管的“农转非”居民,其集体经济关系依由东华村管理,而并未交付托管的九个村民小组,村民的管理服务仍由东华村负责操作,由此形成“一村两制”或“一居两制”的独特机制。④在此不难发现,以居委为代表的城市型社区体制机制在进入转型社区时,所生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之高,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二)转型社区“城乡混合结构”的运行机制
转型社区混合结构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且主要体现在城乡结构及其要素的博弈中。关于此,可从两方面阐释:第一,转型社区混合结构的运行走向,主要是由村社型结构存在难以超越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传统村社型结构是村民利益关系的凝聚,如村社型组织是村民的利益工具,在人员流动稀缺的村社背景下,相对于由单一村民所构成的社区而言,其公共性是没有问题的。但在人员流动常态化,新居民越来越成为主体的社区,它对整个社区的公共代表性就会趋于丧失,社区治理的权威性及有效性就会产生问题。第二,转型社区混合结构的运行走向,还由居委型结构的适应性所决定的。在村社向城市社区的转型中,突破村社关系的约束,建构统合性强的组织结构及关系,是转型社区适应城市化变迁的基本。换言之,伴随非农化与异质性社会关系的大量涌现,只有更具公共性的体制机制,才具有新型社区关系的协调和整合能力。而居委型的组织及社会关系,主要是以居住关系为纽带建构起来的,在利益配置中遵循更具普惠性价值的原则,因而具有更强大的适应性能力。
在转型社区的不同城乡结构及其要素的博弈和替代过程中,其内在运行也有自身的逻辑。首先,城乡混合结构的运行中,所谓替代也只是部分替代而非完全替代的过程。因为村社结构诸元素本就与现代生活具有共通性,由此决定了部分传统村社元素的现代价值。其次,这种替代是相对漫长的过程,因为:第一,这与转型社区的城市化路径相关。至少在转型社区城市化的初中期阶段,主要是对外来冲击的一种自发性回应,缺乏“自主性”建构,是以村社型结构去适应或吸纳新型社会关系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获得自身结构于变异条件下的延续。但当狭隘的村社结构变得无法支撑更进一步的城市化之时,改革传统村社关系、采用现代体制机制就成为发展的必需,但改革难免遭遇村社结构的重重制约,特别是受村社型利益机制的制约。因为村社型结构建立在集体经济、尤其是集体土地关系的基础上,村社结构的延续就是相关利益机制的延续,其动力之大毋庸多论。第二,这与村社型结构的固化效应相关。如一般的村社型组织结构基本都由“标配型”的党支部、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共同组成,它们在长期运作中往往已形成相当稳定的“总体性”结构,改革中难免产生具有相当强度的惯性效应。诸如此类的缘由表明,即使是“村改居”的转型社区,其村社型的结构及机制至少相当时期内仍在发挥相应的功能。
“城乡混合结构”之独特运行机制,虽然昭示着转型社区的复杂性及其治理的艰难性,但总体路向还是具有相对的确定性。特别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并未完全瓦解,加之城乡社区各自的自然禀赋并不相同,差异性及其发展中的趋同性并存。与此相关,把握现阶段城乡社区的差异性,有助把握转型社区的城乡混合结构及运行机制,而这种差异性的主要体现是:第一,在国家法律制度规定中,城乡社区分别对应的核心公共组织是居委会和村委会,它们是性质不同的基层自治组织;第二,两者成员构成的依据不同。村民是村社人口主体,村民通常局限于有集体土地关系的成员。城市社区构成主体是居民,主要以居住关系界定成员资格;第三,两者职能关系不同。城乡社区都承担公共管理服务的职能,但村社职能更综合化,还承担集体经济及其他经济职能,居委社区则无履行经济职能的要求;第四,两者成员对各自社区的依赖度不同。村民一般对集体经济的依赖度较高,进而对村社组织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城市居民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单元,对社区的依赖主要局限在日常事务上,依赖度较低;第五,两者财源不同。村社履行公共职能时,财源主要靠集体经济。而城市社区的运作成本,主要靠地方政府下拨经费;第六,两者主管的产生方式不同。村民选举的制度及机制相对健全,体现出村民自治的特点。城市社区居委选举的相关制度及机制不完善,居委主要负责人实际多由基层政府指派、任命或招聘产生,居民自治并未得到体现,等等。这些城乡社区的差异性,对认识由“村”而“城”的转型社区及其城乡混合结构,无疑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三、转型社区“城乡混合结构”面临的主要问题
关于转型社区“城乡混合结构”所诱发的社会效应,可以从不同侧面加以认识。就正面效应看,该结构的产生及其运行,终结了长期处在“隔离性”状态的城乡关系,给城乡关系的一体化和城乡社会融合奠定了基础。但就负面效应看,由于这种混合结构是城乡分立结构松动化与城乡关系重构的结果,但这种重构是在原结构基础上的重构,很容易与原村社关系发生矛盾。诸如转型社区面临的集体产权关系紊乱、旧村拆迁改造难、就业社保问题多、债权债务纠纷多发等等问题,再如面临社区社会资本流失、信任关系难以建立、互惠规范匮乏、邻里网络趋于解体、社区认同缺失、集体合作困难、多元治理格局难以形成等等⑤,“村改居”社区还面临组织定位不明确、人员素质不高、居民参与有限、经费来源模糊、法律法规欠缺、失地农民身份认同和归属模糊、社会网络断裂等等问题。⑥虽然这些问题难以逐一列举,但都共同指向转型社区的结构及机制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
(一)转型社区混合结构易使高密度异质性关系发生碰撞
转型社区的混合结构中,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高度聚集,发生碰撞与排斥的概率高,致使社区问题集中。正如面对快速城市化带来问题多发的情形时,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区里有镇,镇里有街,街里有村,村里居民半农半城”的状态,很难在短时期内达到治理有序化。⑦此中关于镇街村社会关系极为混杂的现象,同样适用于转型社区。转型社区在由“村”向“城”演化过程中,随集体土地非农化与工商服务业的兴起,衍生出大量异质性的社会关系,如与非农产业兴起相关的各种业缘关系、与旧村拆迁改造相关的多元利益关系、与集体土地开发利用相关的各种矛盾关系等等。显然,这些多样化社会关系的涌现,使得转型社区的社会关系包括各种新旧关系异常混合纠结化。
这种杂糅状态的转型社区关系,带给社区治理以很大的挑战。如转型社区具有“总体性”结构的村社型组织,其治理主体过于单一化,社区公共事务主要就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权或“类”行政权在运作,而非真正的多元互动。现代社区生活所需的多样化组织,如志愿者组织、物业公司、业委会等等,基本处在起步发展阶段。这种组织结构在面对社区的复杂问题时,往往显得难以应对。此外,许多“村改居”社区,新居委与原村委具有高度重合性,甚至就是换了牌子的原村委,整个社区运作仍是以原组织方式进行,新居民基本排除在主要的管理服务框架之外。⑧现社区体制机制下,由于城乡社区存在不同的制度及价值取向,村社主要立足具有“村籍”及集体经济关系的居民,城市社区则主要立足居住群体。但转型社区由于“村居共存”,两者之间如果没有良好的协调,矛盾冲突很难避免。如村社型组织以本土居民利益为依归,遵循内向利益分配规则,存在严重个别利益偏向性的问题。如不少“村改居”社区的居委,在惯性力与现实利益的驱动下,仍按村社规则进行社区治理,很容易产生新老居民的“碰撞”问题,结果反而是深化了“本地人”与“新居民”之间的“隔阂”。也与此相关,通过“村改居”产生的新居委,普遍都有排斥新居民的制度化规定,如有关于本土居民才能参加所在居委会选举和居民会议的制度规定,极大影响了新老居民之间的社区融合,也直接增加了社区治理的难度。
(二)集体经济支撑下的混合型结构具有抑制现代性发育的功能
转型社区集体经济是非农化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经济形态,是以集体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土地及物业租赁为主要收益的集体经济。随着非农集体经济的扩展,社区普遍获得新的集体行动能力,但也因此而使某些现代关系的培育和发展受到制约。以广州石牌村(俗称)为代表的、撤村改制至今已走过近20年历程的城中村,虽然居民主体早已是新居民,名义上的社区公共组织也早已不是村社型组织,而是“村改居”中组建的居委型组织。但在社区治理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村社型组织,甚至主要就是集体经济的转制公司。这些转型社区的集体经济组织,由于拥有集体经济资源而仍成为社区治理的核心,也是与集体经济利益相关,有些社区才产生出要求新老居民分设不同居委,或要求本土居民和新居民分设村委和居委,致使转型社区的社会关系更加混杂,而且其复杂性还体现在,由于集体经济的原因,打破了过去只是以居住关系界定社区的惯例,反而出现按集体经济关系界定居委或村委的现象。
关于集体经济在社区治理中的效能,特别是凌驾于其他公共组织包括新公共组织之上的效能,在此稍作展开。在我国的相关制度规定中,以居委为代表的城市社区公共组织并无独立财源,运行成本来自政府且数量相当有限。转型社区即使已实行“村改居”,其主要组织的经济来源,由于传统路径依赖和居委型组织的下拨经费不多,运行经费主要仍由集体经济承担,包括日常经费开支及工作人员的补贴,基本都依托集体经济。显然,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社区治理,很难不是村社治理的一种“复制”,所谓翻牌型“村改居”,即新居委与原村委在组织结构上高度类似。虽然,这种公共组织名称上已是居委型组织,但仍是村社型的运行机制,决策上也主要是原村社人员,⑨这种“村改居”很难不陷入“换汤不换药”的尴尬改革状态。广州黄埔区2002年一次性地将辖内三个镇、15个行政村同时转为六个街道与15个居委会,五万多农民转为居民,并建立起居委型的社区组织系统。然而,这些“村改居”社区至今在人们的心理认同中也仍是行政村的概念和意识,集体改制公司仍是人们习惯中的“村委”。
集体经济支撑的转型社区,一般都很容易遭遇阶段性的治理困境。第一,由于作为社区公共经济基础的集体经济,本来自身问题就相当多,如集体所有权主体虚置、资产管理和处置不规范、用人机制近亲繁殖、高度依附行政权、经营管理者素质有限等等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或直接或间接,几乎都恶化了社区治理环境。⑩第二,源于集体经济利益机制的作用,转型社区很容易受集体经济关系的牵制。集体经济是社区非农化后的最重要资源,为争夺集体经济利益,不少转型社区产生出多形式的“反城市化”现象,如固守“村籍”或集体性要求“非转农”等,实质就是城市化利益博弈的体现。⑪“村籍”身份的固守或争取,主要是为集体经济利益,有社区以此控制外来人口与防止集体利益外流。⑫也正是集体经济起作用的原因,社区村社型结构的正当性才得到强化。第三,新老居民管理服务上存在“两张皮”的问题。因为当居委型组织的经济基础仍是集体经济时,把新居民排除在外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其实,只要“村改居”社区的经济基础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其管理服务的排外倾向就难以改变,且对新公共权威的建立和培育也不利。总之,居委型组织虽然更具包容性,但在相关经济条件的限制下,很难不受限于村社型社会关系,致使新组织的基本功能反而难以得到正常的发挥。
(三)转型社区混合结构缺乏基本的制度化规范
转型社区独特的结构性,使既有制度规范并不具有良好的适用性,治理困境亦凸现制度及政策供给的不足。⑬虽然由村社演变而来,但转型社区形成自身的结构性特点,如:在人口构成上,一般由本土村民为主演化成以外来流动人口即新居民为主,在建筑属性上,多由自住房为主演化为廉租房聚居区,在集体经济形态上,多由传统农业生产为主演化为集体土地及物业租赁为主,在本土居民的人际网络上,则由以“熟人关系”为主演化为“熟人”、“半熟人”的人际网络等等。转型社区与普通乡村社区相比,城市元素更多,而与普通城市社区相比,则农村元素更多,是具有显著过渡性特点的社区,对有如此独特结构的社区,使用既有制度规范往往都不具合理性。
相比较而言,在国家法律制度和地方政策法规中,一般性城乡社区所对应的制度规范还是比较健全的,但适用转型社区的又相当匮乏,有些方面甚至完全空白。如有关“村改居”社区的选举,究竟按居委会组织法操作,还是按村委会组织法操作,实践中就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村改居”后仍施行村民自治,并按村委会组织法运行,显然就存在法律上的合法性问题,但如果依居委会组织法进行运作,从社区基础和实际需求看,一定范围的村民自治又仍有其合理性依据,因社区中还有许多属村委职责内的事务,如集体土地开发转让等涉农事务,用村委机制处理更具合理性,因此,“村改居”社区保留部分村社制度及机制是符合现实需要。其实,“村改居”社区面对居委更具形式化选举所表现出的困惑,恰恰说明转型社区适用性的制度规范缺失。同理,这种社区中新旧关系的高度交织,基层政府、村居组织、业委会、物业公司、外来企业之间的职责关系混杂不清,除容易发生矛盾纠结之外,也制约了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⑭对转型社区而言,如果相关制度规范不能尽快完善起来,在社区治理上很难摆脱被动的状态。
四、转型社区“城乡混合结构”相关问题的对策思路
社区治理的理想目标,是能实现自主性的社区治理。转型社区则普遍出现自治弱质化与自治难度增大的情形,如自治机制和功能弱化、服务职能模糊化、组织人员理念滞后和综合素质较低等问题,⑮显然与社区理想目标有较大差距。转型社区的混合结构,虽在消解城乡分立结构及推进社区转型中有正效应,但也存在制约发展之处。如何消解这些制约是转型社区理顺治理关系的关键。由于城市化表现为“城市主义”的提升,即多元、异质、匿名社会特质不断增加⑯,因此,现代社区的深度城市化“特别需要理论和相关政策的有效指导,需要通过理论创新追寻制度创新的合理性”。⑰在转型社区的改革中,针对混合结构及其相关问题,建构更具适应性的体制机制,是摆脱治理之困与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基础。在此需要关注的是,当集体经济逐步撤离社区公共领域时,居民认同基础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完善社会服务机制,建立或增强居民新的认同性整合,⑱给居民提供福利性、公益性和互助性的社会服务,是现代社区治理的主要职责和内容,⑲也是转型社区改革创新的方向。
(一)把转型社区纳入城市系统以助推深度城市化的发展
当转型社区的城市化仍然还以“内生性”村社体制机制进行时,由于“内生性”特质具有地方性、非正式性和边缘性特征,往往无力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关系,即由于村社型体制机制的局限,转型社区若以自身路径进行城市化,就只能是粗放型、低端型城市化。当这种城市化进入较高阶段时,村社型体制机制的滞后性会越来越严重,以致陷入治理困境。事实上,转型社区的再城市化或深度城市化,是“生存型”社区向“发展型”社区的转变过程,⑳当其混合性结构面对复杂情境时,整个社区的运行机制是需要根据社区情形作必要调整的。只有及时转换社区规则和机制,才能顺应深度城市化的要求,以实现与城市体制机制的对接。
如何在城乡分立结构已破解条件下实现与城市系统的对接?在转型社区的改革中,至少需关注以下方面:第一,在转型社区建设的理念上,需调整到现代社区发展的理念上。传统乡村社区是“地方性”或“社区性”很强的社会单元,各层面都由封闭性社区结构所塑造。而现代社区是开放多元结构下的社区,是被各种“大社会”机制所建构的社区,树立开放包容理念才能顺应社会变迁,转型社区亦不例外。第二,改革“内生型”体制机制,把转型社区纳入城市系统,以实现从形式到内涵的城市化。在城乡一体化并未真正实现之时,转型社区的现代转型,只有将自身纳入城市轨道,才能按城市制度或机制进行运作。就此而言,各地已经或正在开展的撤村建居活动,就具有方向性的示范效果。“村改居”在打破村社结构制约的同时置入了现代社区关系,这对解决诸如失地农民失业率高、就业底层化及非正规化、社区边缘化等问题,都具有难以替代的功能。转型社区在体制机制上与城市接轨,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基本路径。
(二)建立或健全转型社区的现代组织结构
社区组织是社区发展的核心变量,不仅影响到居民的利益关系,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社区治理效果。转型社区由于与混合结构相关的、“村居并存”而暂时难以理顺的组织关系,建构具有适应性与针对性的组织结构,是实现混杂社区关系有序化的组织保障。在转型社区组织的建构中,需要把握好两点:首先,需要处理好大趋势与具体组织建构的关系。在现代组织结构的变迁中,虽然分化发展是大趋势,但分化程度通常受集权与分权博弈关系的限制,因而,在转型社区的组织建构中,需在权衡集权与分权利弊关系的基础上进行选择。㉑其次,由于转型社区城乡混合结构的复杂多样性以及不同结构的交叉并存,组织建构中应避免追求具有普遍性的组织模式,而是要在实践中寻求具有适用性的组织结构。
一是,改革村社型组织结构,以顺应现代社区治理的需求。村社型组织根植于传统小农经济中,与村社集体土地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具有难以克服的狭隘性特点,主要靠密集的人情关系维系,理性关系很容易被人情关系化解。加之,在转型社区成为新居民的聚居区时,村社组织已经逐渐丧失了在整个社区中的公共代表性,此时仍在主导社区治理,难免问题多多。改革这种组织结构,可考虑以下操作方式:第一,让原村社组织退出社区核心公共领域,并使其成为普通社区组织或经济组织,成为社区部分居民即本土居民所属的一个组织。这在让本土居民拥有自己的利益组织时,还为公共组织让渡新社会空间提供了帮助。而社区公共组织如何建构,后续还会论及。第二,改造村社型组织以实现组织结构的现代转型,即在职能定位、人员配备、财务来源等等方面涉及对村社型组织进行根本的改造,改变狭隘封闭的传统组织结构,使之成为超越个别人的公共社区组织,以满足现代治理的要求。
二是,建构转型社区的新公共组织,以推进社区利益关系的整合。建构居委型公共组织体制,是相对容易模仿的创新实践。在此有两个关注点值得一提:首先,核心社区公共组织的建构和运行,需解决经济来源问题。传统村社组织主要是靠集体经济提供支持的。新社区组织如果能够在抽离集体经济时,又无新经济条件的支持,其权威性是难以得到维系的。我国居委型公共组织的相关制度比较健全,借鉴既有方式以解决社区运作成本,是比较可行的路径。其次,相比之下,居委型组织的运行更具合理性,其管理服务的包容性就可消解村社型组织公共性不足的问题。“村改居”居委的组织及权力关系建构,是传统村社结构及功能机制在起作用的条件下,居民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至关重要。
三是,培育多元社区组织,以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转型社区既是农村社区发展的“前沿地带”,也是城市演化的边缘地带,城乡关系及结构混杂,社区治理难度大。而要实现社区的有效治理,不仅取决于社区公共组织的重建,还取决于多元组织的培育。第一,建构多样化的组织关系。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共同体,发展各类社区组织,既可让不同居民群体在社区中找到各自的归属,还能有效促进居民的多元参与。虽然,社区参与只是公民参与的低层次形式,但也有影响社区决策和社区发展的功能。第二,转型社区作为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根基的社区,内含传统的关系纽带,通过开发利用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就可使社区在满足居民个性化需求的同时,还可建设特色社区。如针对转型社区的村落背景,保护和发展一些传统社群组织,如舞狮会、私伙局、龙船会等等。此外,发展公益慈善类和参与促进类社团,建立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委托及被委托、授权与被赋权的互动机制,推进多元一体组织格局的形成。
(三)改革集体经济体制机制以化解治理难的核心症结
村社型集体经济是高度计划体制与人民公社制的“遗产”,也是转型社区混合结构得以形成和维系的主因。随着集体土地非农化及其价值的提升,集体经济规模获得扩展,并使社区的经济基础得到更新和强化。但与此同时,社区治理性问题也趋向严峻化。或者说,随着村社经济的非农转型,集体经济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化,治理难度大为增加。如在村社人口结构稳定的条件下,村社集体经济作为社区公共经济的基础,有着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当村社成为转型社区、居民变得流动化和多元化的条件下,若仍以集体经济作为公共经济,就意味着仅仅是部分的居民,需抽取出属于自己的利益,而用于整个社区。这无疑有失公平,也容易诱发或强化本土居民与外来新居民之间的矛盾关系。
重构集体经济体制机制,是转型社区深度城市化的标志。为此,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逐步直至根本上“切割”社区和集体经济的“一体化”关系,让社区从对集体经济的依附关系中“脱身”,这是理顺社区关系的关键。多数“村改居”社区仍在延续原村社与集体经济的依存关系,而且还使集体经济和社区都从其中获得相关的政策鼓励。㉒但随着集体经济作为社区公共经济的合理性丧失,两者的“分割”就不仅是集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消减“本地人”与“外地人”矛盾冲突的需要。落实转型社区在“后集体经济”时代的经济来源就成新议题。在此,基层政府配套制度及机制的跟进很重要,否则,“分离”性改革很可能返回原点。第二,通过改革以明晰集体经济的产权关系,为集体经济市场化奠定基础。转型社区通行的股份制改革,在产权关系上并无实质性的突破,如果能在集体股权固化与社会化上更进一步,集体经济就会因产权关系的明晰化而实现“还权赋能”目标,集体经济自主权也能得到发挥。第三,在集体经济完全市场化暂时难以实现的情形下,完善治理机制是基础。非农集体经济的运行机制复杂,健全治理体制机制是实现有序治理的必要条件。其中,建立或完善“三会制度”(如股东代表大会制度、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且使之落到实处,是解决或缓解集体经济问题的关键。
(四)建构有针对性的制度规范以缓解制度短缺问题
在主要依靠契约性制度进行治理的现代社会和社区,相关制度规范的建立或健全就凸显其重要性。在各类社区中,转型社区的混合结构尤其独特,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治理制度安排中的特殊性,包括需要具有过渡性、衔接性特点的制度安排。恰恰由于缺乏针对性强的制度依据,转型社区许多探索性的做法往往面临多重困扰。而关注制度性建构的更深层原因在于,转型社区由重血缘地缘情缘关系的传统村社变异和延伸而来,需要打破高密度人情关系的制约,建构更多正式的、契约性的制度安排。其中,由于我国城乡分立结构尚未完全打破,制度建构中应关注社区转型的连续性,立足城乡一体化高度进行制度设计,㉓以弥补衔接性制度匮乏的空缺。
一是,在相当时期内认可城乡机制及规则并存的合法性,以适应社区转型的实际。转型社区的混合结构及其治理机制和规则,对维护不同居民群体的利益有合理性。就转型社区而言,多结构并存有利于缓解不同群体的社会性不适,并让其逐步适应新环境新生活。如“村改居”社区究竟按“居民自治”规则运行,还是按“村民自治”规则运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均有不同的认识。如有研究认为,“村改居”社区在相当时限内按“村民自治”机制运行更具合理性,因为转型社区从区域范围、社会关系、利益相关度、居民参与意识看,村民自治的基础和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㉔因而,村民自治规则仍在发挥作用。但事实上,“村改居”社区按居民自治机制运行才于法有据。转型社区城乡结构并存,既有历史必然性,也有现实合理性。其合理性就在已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利益均衡中,这也预示着它的长期性和复杂性。㉕此外,在相关制度规范的建构中,需警惕居民权利萎缩的问题。正如有人发现,与居民自治相比,村民自治有更丰富的经济内容和经济资源,它比一般城市社区更具有自治理由和民主价值取向,因此,“村改居”不急于改变村民自治,可在特定范围保留村民自治并借鉴村民自治中的民主选举以实现居民自治。㉖综合上述种种,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明确“村改居”组织的职能定位和换届方式等等,是理顺转型社区关系的基础。
二是,建立或健全非农集体经济制度,让集体经济运行有章可循。转型社区的集体经济,普遍经历从“有地”的村社集体经济向“无地”的非农集体经济转型。与传统农业集体经济相比,非农集体经济更复杂,加之集体经济关系本来就存在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两者叠加,致使集体经济问题相当多,如产权关系紊乱、治理机制不健全、集体物业档次低、经济形式单一化等等问题。有的通过股权化的集体经济改革,在制度化形式上已从与社区一体化的关系中“切割”出来,并形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集体经济,但在实际运行中又与社区存在相当密切的联系,且还承担大量公共支出的经济成本。为此,建议出台高层次《集体经济法》,把集体经济纳入法律制度体系中,这样,才能保障集体经济利益关系的公平性与经营管理的高效性。
三是,建构或健全新老居民互动的多元化制度平台,以促进转型社区的社会融合。转型社区的居民结构比较特殊,主要由外来新居民和本土居民两大居民群体组成。而且,城市化的程度越高,新居民的比例越高。如城中村几乎都成为新居民聚居区,新居民人数通常是本土居民的数倍乃至十多倍。但这些社区的公共治理,仍以本土居民为主,新居民则被排除在社区治理之外,甚至排除在社区参与之外。但社区参与,实际涉及社区权力及利益关系的分配,未有参与则意味着难以共享社区权力及利益。这种治理格局,无疑给社区矛盾冲突埋下了隐患。转型社区的协调发展,不同居民群体的互动共享很重要。增大居民交往比例,搭建新关系网络等,是破解转型社区隔离和排斥的重要手段。㉗建立或完善多样化的社区制度平台,对促进居民群体的互动不可或缺。
总之,随着我国城市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变迁和松动化,一些占尽天时地利的发达村庄演化成转型社区,并形成城乡关系极其混杂的过渡性结构,即“城乡混合结构”。这一结构的存在和运行,一方面,为进一步打破城乡分立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新社会空间;另一方面,也使转型社区关系阶段性地处在相当纠结的治理状态,结构性张力增大,并普遍性地陷入治理困境。把转型社区纳入城市系统,建立或健全现代社区组织体系、创新集体经济体制机制,建构具有良好适应性的制度规范等等,是摆脱治理之困的主要策略。在此过程中,尽量避免过猛“敲碎”原社区结构,以渐进多元方式推进社区发展,是更具科学合理性的转型路径。
注释:
①顾永红,向德平,胡振光.“村改居”社区:治理困境、目标取向与对策[J].社会主义研究,2014(3).
②秦瑞英,阎小培,曹小曙.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转型社区的特征及治理模式探析——以深圳市爱联社区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3).
③姚进忠.赋权:“村改居”社区服务的路径选择[J].城市问题,2011(10).
④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城镇化进程中珠三角村改居治理体系及路径选择专题调研报告[M].内部稿,2015:131,373.
⑤吴晓燕,关庆华.“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流失与重构[J].求是,2015(8).
⑥梁慧,王琳.“村改居”社区居委会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理论月刊,2008(11).
⑦刘笑天,马丽卿.城乡统筹背景下转制社区的管理[J].经济工作,2013(9)上.
⑧徐睿.“村改居”社区组织体系的完善与问题分析——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成都市A社区为例[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6).
⑨胡旭昌,高灵芝,高功敬.济南市边缘社区管理体制研究[J].济南大学学报,2007(3).
⑩李德虎.转型社区治理中的社区干部:行动逻辑与角色困境——基于成都市LH社区的样本考察[J].领导科学,2016(6)中.
⑪李翠玲.珠三角“村改居”与反城市化现象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⑫折晓叶.村庄边界的多元化[J],中国社会科学.1996 (3).
⑬韩丹.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研究——以南京市A区村改居社区为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8).
⑭蔡新燕.论我国社会资本积累与公民政策参与的良性互动[J].理论导刊,2008(2).
⑮曹姮钥,康之国.后“村改居”时期的社区组织治理能力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2).
⑯李志刚,于涛方,魏立华,张敏.快速城市化下“转型社区”的社区转型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7(5).
⑰徐勇.为规划性的社会变迁导向——评《居委会与社区治理》[J].社会主义研究,2003(4).
⑱朱婧.城镇化视野下的“村改居”社区认同性整合研究.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15(1).
⑲王碧红,苏保忠.比较分析框架下的“村改居”社区居委会的治理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07(6).
⑳陈晓莉.村改居社区及其问题:对城中村城市化进程的反思与改革[J].兰州学刊,2014(3).
㉑徐睿.“村改居”社区组织体系的完善与问题分析——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成都市A社区为例[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6).
㉒严娜.“集团公司带社区”的现状与动因分析——W市J街“村改居”社区建设的启示[J].才智, 2014(24).
㉓杨贵华.我国城乡社区组织发展与“村改居”社区组织建设[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1(3).
㉔高灵芝,胡旭昌.“村改居”后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J].重庆社会科学,2005(9).
㉕胡旭昌,高灵芝,高功敬.济南市边缘社区管理体制研究[J].济南大学学报,2007(3).
㉖贺雪峰.自治的功能及合理性[J].社会主义研究,2002(9).
㉗王义.论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排斥与融合:以A区村改居社区为例[J].临沂大学学报,2015(1).
[1]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2(1).
[2]蓝宇蕴.“新村社共同体”:一个都市村庄的实地研究[M].三联书店,2004.
(责任编辑:卢小文)
The Urban-rural Hybrid Structure of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
Lan Yuyun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 are the results of loosen urban-rural binary structure.During this process, a unique social structure, i.e.the urban-rural hybrid structure, is formed.As a fundamental phrasal feature, it is the foundation and starting point of deepened urbanization for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 and help to deconstruct the binary structure, but its existence and function also brings extra entanglement and structural tension to community relationship and dilemma to community governance.The main strategies are including those communities into the urban operation system,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modern community structure, reforming the collective economy institution, making issue-oriented laws and rules and seeking balance of interaction of institutions or rules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spheres.It is vital not to break the structure of the original communities insensitively but to take a progressive path to modernize them.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 urban-rural binary structure; urban-rural hybrid structure
C912.81
10.3969/j.issn.1674-7178.2016.06.001
蓝宇蕴,社会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应用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ASH013)、广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GD12CSH05)、广州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ZD03)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