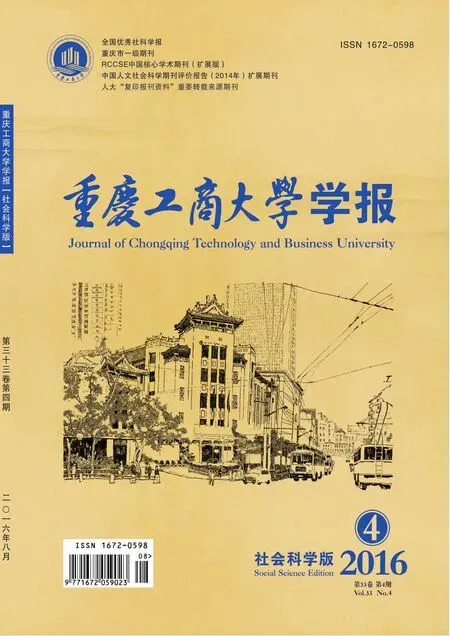从防御型治理到引导型治理
——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的治理之道*
2016-03-23江亚洲
江亚洲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从防御型治理到引导型治理
——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的治理之道*
江亚洲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挤占公共话语空间、消弭公共理性和破坏政府公信力,已经日益影响到当下网络舆论生态的正常发展。以“防”和“堵”为主要特征的防御型网络治理表现为事后的介入和适应性调整,它将网络话语视为管制和防控的对象,不能化解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也不是长期有效的网络治理机制。与此同时,以“疏”和“导”为主的引导型网络治理方式,以保护公民网络话语权合法表达为前提,通过设立信息共享平台引导网络话语主体真诚平等沟通,能够引导形成多元主体自主自觉、合作共治的网络治理综合体系,所以从理论构建到实践运行都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关键词:民间网络话语权;防御型;引导型;膨胀;治理
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媒体,其独特的“交互性”为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搭建了崭新的交流平台,极大地拓宽了公共话语空间,使其呈现立体化、多元化的态势,也促使当下网络舆论生态发生了重大变革。公共话语空间中话语秩序的变革,以民间网络话语和官方网络话语出现新的博弈状态尤为突出。民间网络话语是自发形成的,话语角色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多重性,因而与官方网络话语有着不同的话语生成机制与规则系统。由于技术的赋权特性,民间网络话语形成了区别于官方网络话语和传统现实话语的独特模式。这种话语模式冲破了现实世界的时空限制与社会角色的话语束缚,体现出一种以消除崇高、消解权威、解构传统为特色,通过自嘲、戏谑、反讽、质疑等方式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瓦解与动摇的话语模式。尽管民间网络话语权并未获得政治共同体所赋予的强制性,但由于话语权行使的主体往往是“很多人”,于是这很多人的共同意志的表达可以形成一种“场域”,不同的声音往往会被淹没,而相同的声音则会通过网络得以放大。网上网下的交互作用,将许多偶发事件升级为群体性事件而获取社会关注,对当事人特别是负有社会治理责任的公权力形成压力。在与官方网络话语权博弈过程中出现的民间网络话语权的膨胀,显然会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中弘扬的有效性。如何在保护和尊重公民网络话语权的前提下引导民间网络舆情发展,化解网络空间的潜在风险,形成轻型期网络社会的价值共识,成为当前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使命。
一、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现状
网民在中国公民群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5年6月,中国网民已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其中手机网民5.94亿,手机上网普及率88.9%。网络的普及和上网方式的便捷性让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从网络空间中接收信息或发表观点,并且这慢慢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如国外学者所言的“正在急速扩展的对网络工具的接近权开始创造公共空间,在那里,信息和建立关系的新形式能够散播”[1]。与之相伴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事件也更加容易进入到网络视野,人们围绕某一事件在网络平台上进行表达、对话、争执甚至是谩骂的行为,使得一些事件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或者产生放大了的社会效果,甚至再次影响现实主体行为逻辑,这些现象也在慢慢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为了研究中国网络公共空间发展的总体状态,笔者对自2010年以来发生在网络社会上的受到较多讨论的事件,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其做了一个大致的类别划分。(1)按发生领域分类:有政治领域,如钓鱼岛与反日游行、王立军、薄熙来案等;学术领域,如唐骏学历造假事件、中科院院士抄袭事件;经济领域,如电商价格战、多地曝出非法集资案;娱乐领域,如文章出轨事件、柯震东等明星吸毒事件;社会生活领域,如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宁波PX事件。(2)按价值指向分类:有正面宣传,如高调反腐、恒大夺冠、最美女教师;负面揭露,如毒胶囊事件、郭美美与红十字会事件;猎奇现象,如五道杠少年事件、冰桶挑战赛。(3)按关注点分类:有对制度反思的,如延迟退休的讨论、对二胎政策的讨论;对人性、道德反思的,如小悦悦事件、“扶不扶”的讨论;还有对社会现象的反思,如天价切糕事件、甘肃校车事件。(4)按发展态势分类:有舆论一边倒型,如药家鑫案、李阳“疯狂家暴”;众说纷纭型,如成都女司机被打、何炅北外“吃空饷”事件;两方对峙型,如转基因之争、方舟子韩寒之争。(5)按最终结果分类:有得到处理的,如李某某强奸案、雷政富事件、复旦投毒案;没有处理的,如央企女职工遭轮奸事件、洛阳副市长失联落网事件;无结果的,如对雾霾的讨论、马航失踪事件。(6)按问题的层次分类:有琐碎的事件,如王林涉嫌杀人事件、朗朗钢琴事件;一般影响力事件,如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重大事件,如周永康落马、长江沉船事故。
由此可见,那些进入到网络大讨论中的事件基本覆盖了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了各个层次、领域、性质的问题。在传统媒体主导时代,民众表达渠道被严格限制,他们的个性和利益诉求都受到压抑。但如今这一情况已得到根本改变,互联网的崛起和普及大大拓展了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和行为空间,为人们思想的表达、交流、协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场所。一半的国民成为网民,在网上公开参与表达、对话活动,围绕网络热点事件,民间网络话语几乎占据了新生的网络公共空间。当这成为一种社会常态,那么就意味着它已经超越新闻学、传媒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范围,进入了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视野。因为根据话语理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话语,话语总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即福柯所谓的“无所不在的权力”。费尔克拉夫也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的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话语,不仅仅是权力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权力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2]网络话语是话语的一种形态,其背后隐含权力的逻辑,也能够实现福克斯和米勒所指的“公共能量场”中的“在场”。所以,单个网民在网络公共空间上进行的观点表达、交流和对话,实际上可以解读为网民权利或权力触角的萌动,而网民群体在网络公共空间对社会事件的展开脱离了官方话语基调的大讨论,则是公民权力的扩展和张扬,我们将其称之为网络话语权膨胀。网络话语权膨胀是对网络话语现实状况的客观描述,意指网络公共空间中众人话语形成强大势能,影响社会治理格局。网络话语权膨胀表现为以下一些特点:
1.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与意见领袖的特殊作用。互联网时代人们参与网络讨论的门槛和成本都极低,很多网络事件轻易就能聚集大量网民的围观、争论。但是不同身份的人在网络公共领域产生的作用又是不一样的,表现为绝大多数普通网民的意见会受意见领袖的影响。网络意见领袖是指那些因具备专业知识或掌握信息等而能对其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在网络舆情发展、网络议题设置和网络事态演变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孙志刚事件”中提出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三位博士、“邓玉娇案件”中的网友“超级低俗屠夫”“华南虎事件”里面的对立方傅德志和关克。
2.偏离现实又与现实交割。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投射,但因为它具有虚拟性,因此不能全真地反映现实。网民参与网络公共事件的讨论也不能排除是受了只言片语的刺激或者道听途说,而真正到过现场和全面了解事件过程的是少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难以确定网络流传的就是真实情况。虽然网络言论可能偏离现实,但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又是不能分割和交互影响的,虚拟与真实的界限一旦被抽离,网络对现实就能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如反日游行前期的网络发酵,以及“药家鑫案”和“李刚案”中网络舆论的作用。正是偏离现实又与现实交割的特性,使应对网络话语权膨胀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3.从理性出发到偏激表达。什么事件受到关注、何种问题被公开讨论,可以反映一个社会的思想觉悟。有学者提出,在中国“网络话语涉及的领域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最为突出、影响力最大的,还是关乎社会体系、法律、伦理和意识形态等重大的异常的变动。”[3]近年来网络空间上讨论的热点话题,基本上都反映了当前发展阶段各领域的关键问题,这说明中国社会整体理性成分的增加,而且很多情况网民的讨论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开始展开对社会深层症结的反思。如从“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到对警察何种情况下可以开枪的讨论、从“中南大学跳楼”事件到师生关系处理的讨论、从“小悦悦事件”到对社会冷漠的反思等等。但是,中国网民又存在表达偏激化的问题,针对很多事件容易出现极端的方式和观点,仿佛如此才能提高话语的说服力。如“药家鑫事件”中“药师妹”的言论、“华南虎事件”中网民“以人头担保”的说辞。偏激的表达不符合哈贝马斯“理想话语环境”的“规范性”,因此不利于网络公共空间的构建。
二、应对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防御型网络治理的困局
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是笔者对当前民间网络话语现状的一个客观描述,这一现状对社会治理具有建构和解构的双重作用。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对社会治理的建构作用表现在:第一,它使一些隐蔽的社会问题得到关注和解决。按照韦伯官僚制理论设计的行政并不具备对社会敏感的本能,重要的社会议题无法通过正式渠道发展成为政策议程。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始于公民表达权,实际起到了群体表达和讨论以克服个体表达无力的效果。通过唤醒社会公知和对政府造成舆论压力,使不少的社会问题得到关注和解决。第二,它代表了社会力量的发展,有助于国家和社会走向平衡。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表明社会公众民主意识和表达欲望的增强,民间话语慢慢体现出对主流话语权威的强硬,是社会力量内生的过程,社会力量的慢慢壮大,有助于改变“强国家—弱社会”格局。第三,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具有公民教育的作用。网民群体既包含普通的民众也有具备专业知识的资深人士,他们之间进行的围观、表达、讨论活动,对普通网民的知识构成、思维方式能够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也是一般知识的社会传播过程。但是,尽管如此,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对社会治理的解构作用却是更需要深刻关注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挤占公共话语空间。公共话语空间这一表述来源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概念的界定。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对二者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载体的公众形成了”[4]。由此可见,正是借助于公共话语空间,社会公众基于个体自由、理性的考虑,在预先设定的规范框架内,展开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并最终达成共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得到调节因而能够协调发展,社会治理民主化有了推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在中国社会的普及,网络公共话语空间成为公共空间的重要部分,公共话语空间日益受到来自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的挤占。
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挤占公共话语空间主要是通过影响议题的导入来实现的。有学者通过分析发现能够引爆网络舆论的议题往往同时要具备公共性或利益冲突性、现实影响性、争议性或反常性三大特点,[5]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那些涉富、涉官、涉警以及司法和腐败事件特别容易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并引发持续的讨论。例如今年5月份以来庆安枪击案、何炅北外“吃空饷”、中南大学研究生跳楼成为网上热极一时的话题,而同时在5月份公示征求民意、在学界引发较多争议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这说明在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的状况下,议题是否进入网络公共讨论,与网民的偏好直接相关,那些敏感、猎奇、反权力、关乎个人隐私的话题很容易引来网民的围观,而使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对那些更为重要的事关民生、百姓长远利益以及法律制定的讨论退到了一边。
其次,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消弭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在网络话语空间中表现为不同身份背景的人都可以参与到共同讨论之中;交流过程中各主体的意思是基于个体独立和理性的思考;交流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并且相互真诚。只有在这种环境中,网络公共讨论才能够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调节,探索治理的公共价值。正如国外学者所言“只要参与者满意于让理性作为主宰,并且只要参与者不认为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形式的暴力手段达到目的,公共领域就能够作为理性交流和协商的场所”[6]。然而,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却能够消弭网络空间中的公共理性。首先,网民的偏激情绪使得他们的话语表达不是基于公民理性和独立人格的思考,脱离了政治表达的日常规范。偏激化心态使得中国网民在面对或解决社会问题时不能从现实、客观和底层开始思考。转型期我国社会矛盾多发频发,具有一定的客观现实性,而且也处于可控范围,但却被一些网民过度渲染。又如有时引发网络风波的社会现实指向是基层政府或某个公职人员很小的失职渎职,而有些网民为了吸引更大范围的关注而偏向于夸大其词地将其上升到体制和意识形态层次。这种做法无助于网络民意集中引导基层政府解决社会具体问题。其次,在话语内容方面,权力的“有罪推定”成为网络话语体系里的一种“政治正确”。[7]在网络批判现实主义中,网民往往倾向于把底层群体的悲惨遭遇跟公权力的傲慢和一些官员的贪腐结合起来。在很多与政府相关的社会公共事件中,即使是缺乏依据,公权力也被网民“有罪推定”,从而面临“网络审判”,政府话语权、政府形象都遭遇网民的“口水”围攻。
在政治学和大众传播理论中有一种现象称为“沉默的螺旋”,指的是“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8]个体如果发现他的意见和态度是少数的,就会因为害怕被孤立而趋向于不表现出来。这种现象也会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发生,当某种非理性、非客观的声音在一些事件中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气场,其他少数的代表了理性、客观的话语就会选择沉默。所以,在网民偏激情绪和公权力“有罪推定”这样一种意见主导之下,网络公共空间中的理性精神就会日渐式微。
最后,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破坏政府公信力。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破坏政府公信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针对特定事件形成的、比政府话语多得多的民间网络话语不是对政府话语的补充,反而会对其产生一种围攻和排斥效应,损害政府话语的公信力。现实社会一旦有敏感事件发生,媒体记者都会以其职业的灵敏性对其进行猎取和跟踪报道,并被其他媒体所转载和挖掘,然后,在网络空间引发其他在场或者不在场社会公众的关注,事件迎来第二轮的证实或证伪、价值评判、多角度解读等等。而随着信息的快速、任意流动和可加工性,政府对其的控制权也不断弱化,等到政府终于权衡各种考虑后作出正式回应时,网络上流行的各种观点在社会上已经先入为主了。另外,很多时候我们还看到政府只是跟公众进行着“时间消耗赛”,等公众对事件议论的热潮退了或者舆论被其他事件所替代了,政府才发布姗姗来迟的相关声明。其次,网络空间中对政府和官员真实或虚假的负面新闻大量爆料,加剧了政府话语公信力危机。我们通常能发现网络上那些揭露和批判政府和官员的言论,无论其是否真实,往往都能引来大量网民盲目的围观和转载。并随着一些官员的劣迹在网上爆料和被追查,直接催生了网络反腐的兴起,互联网成为揭露政府和官员不当行为的重要平台,同时对政府行为的讨论和批判也占据了网络空间话语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网络上盛极一时的对“庆安枪击事件”“温州动车事件”和广东“乌坎事件”中政府不当行为的评议,所有这些讨论都可能产生“群体极化”[9]*群体极化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着偏向的方向继续前进,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效应,加深公众对政府话语的“负向心理沉淀”,最终损害政府话语的公信力。
基于对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两方面影响的分析,我们将对网络话语权膨胀治理的目标分为两个层次。基本的治理目标是避免网络对社会稳定的负能量传输,防止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弘扬的有效性;更高要求的目标是形成民间网络话语权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引导和培养中国社会深层转型期的价值共识。但是,反观中国网络治理的实践,基本可以将其概括为防御型网络治理模式。防御型网络治理是指政府在感知危机后,被动采取各种临时和策略性行为来减弱威胁强度的自我保护行为。防御型网络治理发展成地方政府在网络治理中的一种反复实践,所以它已经超出了其本身的字面含义,负载了更多的政策特性,成了地方政府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一种。防御型网络治理发展成为政府网络治理的常态选择有其现实逻辑性:首先,发展型政府背景下经济发展是行政活动的第一目标,对社会秩序则采取刚性维稳措施,防御型治理即是这种思维下的惯常措施;其次,压力型体制和“一票否决”制下,地方政府出于对网络危机向现实转化的恐惧而采取防御型治理;再次,地方政府短期化官员任命机制使主要领导缺乏对长期有效网络治理机制探索的动力,当危机发生后他们只能选取临时性的、成本相对较小的防御型治理;最后,网络治理属于新出现的极其复杂的事务,政府对其尚处于探索阶段,加之经验、知识和人才的缺乏因而还没有形成成熟有效的治理模式,所以选择了操作较简单的防御型治理。虽然如此,防御型网络治理仍然无法应对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的挑战,也不能达致网络治理的基本目标,主要有如下体现:
1.防御型网络治理将网络话语视为管制和防控的对象,阻断了政府和社会的对话平台,使得更多的社会矛盾焦聚于网络空间,引发民间网络话语权的膨胀。防御型网络治理的兴起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是相伴而生的,借助于电子监控、信息过滤、网络屏蔽等技术,权威当局已经实现了对网络信息更为隐秘和强化的政治控制。但是政府却并没有将其强大的信息掌控能力运用到推进政治民主化、政务公开和政策制定的科学化、透明化过程中来,而是将其作为防控网络失序的垄断工具。当现实社会的矛盾或危机开始扩散至网络空间,地方政府“不怕通报,就怕网曝”的经验驱使他们急于封锁和屏蔽消息来源并实行网络言论审核。在“数据库的信息瞬息之间就可以流过全球范围的赛博空间,对人们实施监控。数据库无须任何狱卒的眼睛就能‘审查’我们,而且它们的审查比任何人都更加准确、更加彻底”[10]的情况下,政府和网络民众公开的沟通、协商便消失了,出现民间网络话语的堵塞。权威当局对网络话语的管控策略,实际上是在逃避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逃避新闻媒体和网络舆论对政府的监督。它阻碍了将民间网络话语表达裹携的利益诉求推向公共政策议程的努力,将民间网络话语权引入到一种更为冒进和无序的表达状态。
另外,集中的民间网络话语表达大多数时候是现实社会一些具体的利益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也说明某个事件引起了社会多数人的关注,包括对政府公务员渎职、贪污行为的指责或者对弱势群体的怜悯,是民众对社会公序良知的重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却往往本能地将网络视为“异己”的挑战力量。网络社会的风吹草动在地方政府看来都是风声鹤唳,网络社会成了地方政府的假想敌。在行政过程中地方政府无视网络在后现代公共行政中重塑公共表达和交往平台的重要作用,将网络话语表达本身而不是网络话语关涉的利益和价值考量作为政策执行的切入点而加以防控。因此,本该促进平等对话、公正裁判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行政被地方政府代之以维护网络秩序稳定的维稳行动。其结果实际上不是解决了矛盾而是制造了更多矛盾,将原本属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发展为利益相关者、社会同情者、无端发泄者等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使网络事件获得了更为广阔的二次动员基础,无法避免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政府也将自身卷入更为巨大的网络漩涡之中。
2.防御型网络治理表现为事后的介入,并伴随事态发展不断做出适应性调整,政府反应的迟钝和态度的摇摆加剧了网络话语表达的混乱。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防御型网络治理采取事后介入的方式,基层政府“体制性迟钝”造成的反应滞后不能及时化解网络话语危机。在网络事件的爆发期间,政府部门的第一反应极其关键,及时、合理的回应能有效地平息网络事态,但这对政府各部门协调统一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中国基层政府不具备这种能力,条块分割和利益部门化的组织框架下无法实现对权力与责任的清晰界定,限制了基层政府作为整体系统能力的发挥,集体行动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这对政府的网络治理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在网络事件的演化进程中关键的信息和有影响力的行动具有极强的时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大打折扣。如在“5.2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中,为澄清事实真相,网络上一开始就发出了公开车站视频的呼声,其后更是呼吁不断,但相关部门直到5月14号才公开了一些视频资料,而在这中间的12天内,网络上各种猜测、质疑、愤怒几乎充斥了与此事件相关的所有报道。
另一方面,与地方政府防御型网络治理相伴随的适应性策略调整,容易造成当局立场模糊的假象。正如国外学者所说,“在遭到公共舆论强有力的反对时,任何政府都是脆弱的。”[11]即便民间网络话语表达是非理性和极端化的,但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处在刚性维稳和一票否决制的体制环境中,为避免事态扩大可能带来的麻烦,也会采取一些带有安抚性的行动。但这样容易给社会民众造成一种地方政府态度暧昧、立场不坚定,甚至是理亏的感觉,会对他们产生一种激励效果,使他们在原来的网络话语表达框架内变得更为极端。同样以“5.2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为例,当事人徐纯合被民警击毙后,地方政府紧跟着一方面对民警的行为进行嘉奖,以彰显其执法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将被击毙者一直以来求而不得的诉求也第一时间给予满足。显然,当地政府这两种适应性的行为很难达到自洽,这也是致使该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的重要因素。
3.防御型网络治理的逻辑起点在于如何防止事态变得更差,而不是积极引导化解危机,它既不能使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的现状有所改观,又是一种拒绝学习和成长的组织模式,无助于形成长期有效的网络治理机制。当网络危机事件发生后,一些地方政府会立即采取封锁消息、堵塞言论的方法来避免危机的恶化,或者用其他辅助性行动来佐证政府行为的正确,保全政府颜面。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无效的,因为它忽略了代表民意的“公共能量场”的强大作用,其实这个时候民众只是期盼政府用坦诚、开放和公正的态度一起面对问题,找到根本原因,然后寻找解决的办法。而政府摆出这种自我防御的态度,只会增加其与社会群众的隔阂,招致更多的质疑和指责,当然也就不能引导民间网络话语向良性发展。
学习型组织理论认为,组织只有在运转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和改善,才能增强组织的能力实现共同的愿景。奥斯本等人在《再造政府》一书中也指出,“经历塑造着并不断重新塑造着我们……但许多经历与内在规则无法共鸣,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可能拒绝这种不协调而保留原有的范式……或者可能对范式进行调适(扩大、深化及重组范式以适应新经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处在学习之中的。”[12]政府作为特殊的公共组织,尤其应该在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组织更新、成长与完善,以保持和社会的适切性,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但防御型治理的政府不具有这种组织特性。因为网络危机反映的是社会深层矛盾,政府本可以在危机处理中加深对社会动态的了解,在对话中提升政府公信力,以构建更为有效的治理模式。防御型治理却是基于自我保护的策略,它缺少用真诚的态度去发现和面对深层的问题,也不会正视政府可能的过失。这种行为与学习型组织相去甚远,它没有对已有制度缺陷进行深刻反思和将新增社会因素纳入政策系统等关键环节,不能形成制度化的积累,也就不能形成长期有效的网络治理机制。
三、困局的破解:引导型网络治理的构建
网络公共空间具有后现代公共治理“公共能量场”的特征,各种能量流在这个新兴空间中涌动、交汇,防御型网络治理采取以“防”和“堵”为主的方式,没有较好地改变网络空间混乱无序的现状。与此同时,近年来一种以“疏”和“导”为主要特色的——引导型网络治理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和青睐。引导型网络治理是在开放的环境中,以承认公民网络话语表达权为前提,通过沟通对话的形式,引导公民理性、客观、自由表达,最后形成多元自觉自治的网络治理模式。引导型网络治理遵循从事实出发、循序渐进的引导原则,第一层次,引导性网络治理中政府以负责任的姿态出现,以坦诚、开放、客观、公正的立场,通过信息公开和排除噪音引导公民全面了解社会事实,化解网络社会危机;第二层次,引导型网络治理在社会日常生活中通过教育、沟通、对话的方式,引导网民群体培养独立思考和理性表达的意识,塑造具有自律自治精神的网民,确保网络空间有序发展;第三层次,网络型网络治理通过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论证和宣传主流思想的正确性、先进性、权威性,引导网民群体建立社会深层转型期的价值共识,以网络和谐推进社会和谐与发展。但是,当今中国网络空间发展还很不成熟,所以引导型网络治理主要着力于前两个层次。
1.引导型网络治理保护、尊重公民网络话语权的合法表达,同时利用技术手段排除网络噪声,以形成政府对网络社会舆情的敏感,预见网络公共空间的潜在风险并实现事前介入。行政学鼻祖威尔逊曾指出,“在行政管理活动当中,群众舆论将起什么作用?准确的答案似乎是:公共舆论将起权威性评判家的作用。”[13]借助于互联网和自媒体等网络技术的进步,公民话语表达权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极大的扩展,同时使得网络舆论也成为社会公众舆论极其重要的部分,对公共事务发挥着“权威评论家”的作用。因此有国内学者提出公众网络话语权使很多事件的结果向着公众预期的方向发展,从释放社会压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更加充分的网络话语权而不是相反。[14]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中国公民的网络话语权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甚至可能面临尴尬的境地。因为一方面,地方政府或因网络民主意识淡薄而忽略网络民意表达,或因惧怕网络舆论焦点向现实社会转嫁而对其进行过多控制;另一方面,在规则不健全的开放网络环境中公民还可能遭遇网络暴力。所以,引导型网络治理区别于防御型网络治理的关键,在于它是在“承认的政治”语境下的治理模式。它尊重并保障公民网络话语的合法表达,以此体现出对网络舆情的敏感,这增强了它及时发现问题并尽早介入的能力。
密尔曾提出“舆论自由市场”定理,认为只要保障了舆论自由,各种观点就会如同“市场交换”那样自由沟通和辩驳,在这个过程中真理就会越辩越明。但是现代网络公共舆论并没有呈现为密尔的“舆论自由市场”,而是出现了“去中心化”之后的“再中心化”,一些不良商家、极端分子和网络推手极力操纵网络舆论,普通网民在“群体极化”和“沉默的螺旋”等效应下,频频上演对立于官方话语的“群体狂欢”,因此总体表现为民间网络话语与官方话语割裂对立的局面。在网络话语表达完全不受约束的状况下,批判与攻击的声音就远远超过了理性对话、协商的声音,网络公共空间丧失了阿伦特和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交往功能。福克斯和米勒指出“由于交流失去了对话所提供的真实性的检查,公共对话衰败了,”[15]因此他们主张用“一些人的对话”来替代“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但是,在现代开放网络环境中,所有人都能以不受限制的方式参与到网络话语的讨论中来,因此治理要消除网络话语中的噪声和恶意操作就面临更大的挑战,引导型网络治理在保护和尊重公民网络话语权的前提下更注重塑造良好的网络空间,以提供平等交流平台。从技术层面上看,引导型网络治理将设计好的一整套语句和口令嵌入网络环境的代码之中,因为代码在网络信息中的隐性权力是无处不在的,它能够全程参与各大网站搜索引擎以及发帖、分享、评论过程,实现智能识别、自动屏蔽“污染源”或者生成舆情报告。
2.引导型网络治理通过设立信息共享平台,与民间网络话语主体开展真诚沟通和平等对话,以此引导民间网络舆情发展并使其规范化,达到化解网络社会危机的目的。当前民间网络话语权的膨胀以及大量非理性网络言论的出现跟政府和社会公众的信息不对称有很大关系,防御型网络治理语境下的信息是政府物化的管控对象,不具有与民分享性。但是,如果公民对某一公共事件掌握的信息越是客观和全面,其网络言论就越不易受到情绪化的感染。所以,引导型网络治理在感知危机后会及时、客观、全面地公开一些相关的资料和政务信息并主动分享一些政策动向,这样能够避免网民因信息掌握的片面性而产生从众心理与网络“群氓”现象。实际上,从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而言,政府设立信息共享平台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人们固然承担着与政府开展合作治理的责任,但是政府肩负着创造参与环境的更大义务。”[16]政府创造公民参与环境的举措之一就是要最大限度公开相关信息。另外“在确保国家安全、法人利益和公民隐私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政府实行信息公开,是对公民权利(知情权) 的一种基本尊重”[17]。
李普曼认为“当代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经济革命或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18]其实在网络治理过程中同样也需要“制造同意”的艺术。学者谢金林曾分析了控制、引导和对话在政府网络舆论管理中的作用,并指出只有对话才能促使网民达成共识,制造普遍同意。[19]这个观点是十分中肯的,因为哈贝马斯也指出“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公民的整体性不再通过一种实体的价值共识,更不能由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来维持,只能通过一种旨在实现普遍民主、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合法的方法和权力行使的程序的共识来维持。在本质上,程序不是使主体客体化的流水线,相反,程序是参加者角色互动、意见对话与整合的场所。”[20]引导型网络治理也倡导了一种网络对话的方式,政府部门通过网络沟通和对话以形成普遍的网络共识或化解舆论危机。因为政府实现对话的姿态能给网民一种参与的体验和被重视的感觉,他们也就更能够接受。更为重要的是,对话本身也是后现代公共行政意义上一种“重复性的实践”,福克斯和米勒指出,人类对 “重复性实践”的反思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由他人的期望形成的,并由能在这些期望的范围内理解、接受和实施的强大自我所共同创造。”[15]所以,共同文化框架范围内的重复性对话能够使不同的意见往相同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相反。全钟燮也指出,“通过对话,人们能够直接感受到在他们的对话之间,一个替代的选择是怎样产生的,一个由新理解结果而引发的变化是怎样出现的。”[21]
3.引导型治理的最终目标在于形成多元互构的治理模式,多主体在法律框架下持续博弈,进行选择性的伸张与妥协,能够达成共识性的规则,最后形成自主自觉、合作共治的网络治理综合体系。在复杂开放的网络环境中,政府利用行政控制治理网络之难表现为:政治控制方式必然面临权力与权利抗衡的两难;法律层面而言表达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重要权利;技术难以实现对具有极强开放性、即时性和去中心化网络的全天候覆盖。因此,引导型网络治理超越以上视域的局限,借鉴现代公共治理的前沿理论,形成一种吸纳多元主体参与互构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突破体制的界限,囊括了政府部门、网络媒体公司、网络社会组织、网络名人和普通网民等多元化主体,因而具有更强的社会动员和资源调动能力。正如国外学者所指出的,“网络空间治理需要公私部门之间的新型合作,科技的复杂性及其快速变动性使传统管理方式在许多领域都存在问题,尽管会有特例存在,如医疗信息的保护,但规制框架需要共同合作,因为自我管理、公共监督和公共惩罚相混合的模式将会更有效。”[22]其实,网络社会本来就是社会领域的延伸,所以作为网络参与者的多样化社会主体本应该承担网络治理的社会公共责任,而不是全部推脱给政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下旬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这意味着政府部门正主动寻求将“新媒体人士”纳入网络治理体系之中,他们也将承担更多的网络社会治理责任。[23]
政府引导多元参与主体治理网络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网络治理中政府和社会的互构,形成合作共治、持久有效的网络治理综合体系。这一过程是通过政府与社会在网络空间的长期博弈而完成的。在博弈的早期阶段,公民理性阙如、网络共有规则缺失和政府管制思维惯性会使整体网络秩序表现出对政府管制主义较强的依赖性。在博弈的高潮阶段,社会的理性和民主意识有了增长,政府对社会舆论的权威和垄断地位面临被解构的危机,政府与社会展开管制与反管制、规则和议程该如何设定的激烈博弈,这一时期也是网络社会的动荡期。但是到了博弈的后期阶段,反复博弈使得政府和社会对彼此的期望和底线有了大致范围的估算,他们就会努力使自己的活动不超过这个范围的界限。最后将这个范围用书面的形式确定下来,表现为政府与社会就网络舆论规则该如何设定的方式、强度形成的共识。一致同意规则的反复实践和大量积累使国家和社会的“再契约化”得以确立,也就形成了政府与社会自主自觉、合作共治的网络治理综合体系。
[参考文献]
[1] 拉克斯.尴尬的接近权——网路社会的敏感话题[M].禹建强,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00.
[2] 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61-62.
[3] 徐东.对网络话语权的担忧与思索:一个法律学的视角[D].成都:四川大学,2007.
[4]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15.
[5] 刘艳婧.网络舆论热点议题的信息架构分析[J].现代传播,2013(12):42-46.
[6] Chandhoke.Exploring Mythology of the Public Sphere[C]//Civil Society,Public Sphere and Citizenship:Dialogues and Perceptions.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5:328.
[7] 赵云泽,韩梦霖.从技术到政治:中国网络公共空间的特性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3(11):73-87.
[8] Noelle-Neumann:The Spiral of Silence: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3-5.
[9] 桑坦斯.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0] 博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98.
[11] 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52.
[12] 奥斯本,普拉斯特里克.再造政府[M].谭功荣,刘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87.
[13] 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修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7.
[14] 陶长春.非理性网络话语的舆论力量——以个体的视角[J].新闻界,2012(6):55-59.
[15] 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M].楚艳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6.
[16] Vigoda Eran.From Responsiveness to Collaboration:Government,Citizens,an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2,62(5).
[17] 陶文昭.电子政府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83.
[18] 李普曼.公共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53.
[19] 谢金林.控制、引导还是对话——政府网络舆论管理理念的新思考[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9):4-10.
[20] 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01.
[21] 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M].孙柏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9.
[22] Kobrin.Territoriality and the Governance of Cyberspa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1,32(4):687-704.
[23] 王令.新媒体时代的舆论规律及危机应对[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09):71.
(责任编校:杨睿)
From Defense-oriented Governance to Guide-oriented Govern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agement Model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Civil Network Discourse Power
JIANG Ya-zhou
(SchoolofPoliticsandPublicAdministration,SuzhouUniversity,JiangsuSuzhou215123,China)
Abstract:The expansion of the civil right of discourse in network has misused the public discourse space, made the public become irrational and undermine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which increasingly affect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network environment. The defense-type network management such as “prevention” and “block” as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network governance behaves as the post intervention and adaptive adjustment. It takes the Internet Discourse as the object of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nd its logically starting point is how to avoid making the situation worse instead of guiding solutions to the crisis actively. Therefore, it can’t solve the expansion of the right of discourse in network, nor is it a long-term effective network governance mechanism. Meanwhile, “leading” and “guide” as the guidance of the network governance mean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network discourse for citizens, and set up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to make people communicate sincerely and equally. It can build a more diversified harmonious network environment with cooperated co-management for the public. So, from the theory to the practice, it should get more attention and research.
Key words:civil network discourse power; defense-oriented governance; guide-oriented governance; expansion; governance
doi:10.3969/j.issn.1672- 0598.2016.04.011
[收稿日期]2016-01-16
[作者简介]江亚洲(1990—),男,湖南岳阳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地方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 0598(2016)04- 0076-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