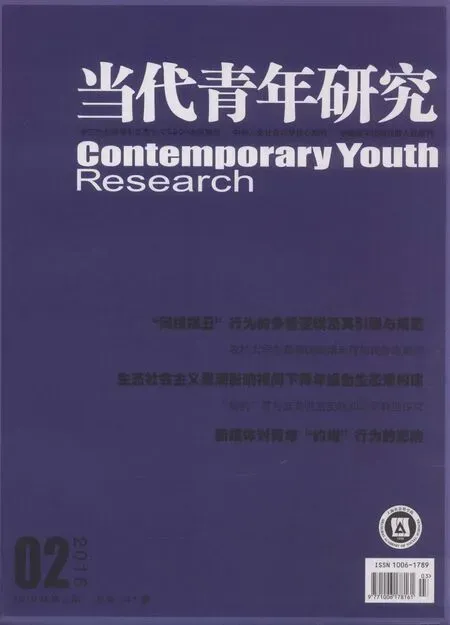“网络揭丑”行为的多重逻辑及其引导与规范
2016-03-19燕道成汪丽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燕道成 汪丽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网络揭丑”行为的多重逻辑及其引导与规范
燕道成 汪丽萍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网络揭丑”是以网民为主体,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的社会监督形式。“网络揭丑”的内在推动力是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舆论生态在其影响下有了新的变化。基于网络揭丑的多重逻辑与多重效应,只有科学引导和规制网络揭丑行为,才能形成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机制。
“网络揭丑”;多重逻辑;多重效应;引导规范
“网络揭丑”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的“扒粪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坚守社会正义和有志于社会改革的记者、编辑和作家涌现出来,针对极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时期美国社会出现的竞争无序、两极分化、官员腐败、食品安全等问题,纷纷在报纸、杂志上撰文揭露,甚至予以尖锐的抨击。[1]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把当时从事揭露性新闻写作的记者们挖苦为“扒粪男子”,记者们却把它接受下来,自称“黑幕揭发者”。当时的揭丑运动推动了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改革,给后世留下深远的影响。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托马斯·伯纳贝克·安德森(Thomas Barnebeck Andersen)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电子政务项目增加幅度从10%升到90%,腐败的出现机率也下降了10%至23%。由此不难发现,国外的反腐更加依赖于体制内渠道和媒介揭丑。[2]在我国,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反腐机构利用网络公开透明快捷的特性,顺势而为、积极引导,充分发挥网络的正面效用,力图实现反腐与网络的良性互动,“网络揭丑”由此兴起。
一、“网络揭丑”的基本要素
分析“网络揭丑”现象的逻辑起点不得不掌握它的构成要素,这是“网络揭丑”现象最表层的内容,往往也是研究中容易忽略的部分。通过与“传统揭丑”相比较,可以看出“ 网络揭丑”的五大要素。
主体层面。传统揭丑的主体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媒体工作者,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于重点事件的捕捉采集能力,工作本身也赋予他们揭丑的权利和便利;另一部分是社会中的权威人士,这部分人精通专业知识,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因此具有较强的揭丑能力。而“网络揭丑”除了为上述两类人群提供了新的平台外,更产生了一个新的揭丑主体——社会大众,具体来说是由社会大众所构成的网民群体。网民群体人数众多,涉及层面广泛,所提供的信息量非常大,而且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匿名性、及时性为这一群体提供了便捷的表达渠道,因此网民群体成为“网络揭丑”的主体,力量不容小觑。数据表明,网民对热点反腐事件和案件舆情发展的贡献率超过60%,一半左右的社会热点问题首发于网络。[3]
客体层面。虽然国外传统揭丑运动的目的在于打击贪污腐败,其抨击对象却主要是垄断资本主义者,采取的是一种从经济到政治的迂回战术,[4]很少直接明了地直指问题,因此更多地停留在对于表层经济现象的揭露上,往往无法撼动本质。但是网络揭丑却打开了一条通往根源的路径,通过“周久耕”“龚爱爱”等事件可以看出,网络揭丑越过表面现象,以反贪腐为重点,直指公权力的执行者和公权力本身,对于本质问题毫不遮掩的揭露和公开,也正是因为这种一针见血的新思路使得网络揭丑颇有成效。
平台层面。传统揭丑基本通过传统媒介平台,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通过发表稿件、接受采访、发表作品来进行揭丑行为。网络揭丑则是运用互联网平台,通过在微博、论坛、社区、微信等交互平台发表内容来进行揭丑运动。传统揭丑的平台比较窄,对于文章的内容、稿件的数量都有严格的要求,并且需要通过层层把关筛选,但网络平台对内容和数量没有太多的限制,更没有严格的把关,降低了“说话”的门槛,给民众提供了一个“说话-说真话”的平台。
形式层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揭丑运动提供了更多有效的形式,网络揭丑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相对温和的问政。通过搭建互联网问政平台,达成网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采用集中时间网上提问与作答和随时留言与回复的形式,形成对政府以及相关单位的监督和问责。二是由表及里的人肉搜索。人肉搜索开端是一些模糊和破碎的爆料性信息,然后利用各种网络渠道、各种知情人渠道获取相关内容并拼凑起来,从而全面了解整个事件并曝光出来。三是一针见血的反腐形式。这也是网络揭丑最具代表性的形式,即网民通过各种技术方式(包括文字、图片、录音、视频等)呈现具有一定说服性的信息,直接曝光事件,从而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和认同,形成强大的舆论效应,同时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以此来推动反腐事业的发展。
效果层面。效果分析在传播学体系中,特别是经验学派研究框架中处于百川归海、众星拱月的位置,其他方面的研究无不归结到效果方面,在经验学派看来,如果不是为了取得某种效果,那么传播活动就失去意义。[5]所以,“网络揭丑”作为一种传播现象,它所达成的效果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要素。从具体事件的角度来看,一部分事件在经过网络揭丑后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并处理解决,如发生在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就使“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这在当时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应,激起了舆论监督的热潮。但也有一些事件在网络揭丑后却不了了之,如“张斌受虐死亡案”的曝光就并未真正对一直遭受质疑的劳教制度产生实质影响。从社会影响的层面,“网络揭丑”在以往传统揭丑的基础上又强化了监督和制约的力量,提高了揭露和惩治的效率,更增加了对于政府及相关人员的警醒和自我约束效用。
二、“网络揭丑”兴起发展的原因
(一)网络平台的发展与网民群体的壮大
互联网已逐步发展为多媒体融合的“虚拟世界”,它搭建出诸多获取信息和互动交流的平台,如新浪、网易等综合性网站以及天涯论坛、微博、各类社区等,这些平台让人们不再受限于周围环境的人际交流,而转变成一种与所有网民的信息共享。随着传播媒介的相互渗透,互联网平台拓宽到更多的设备和场所中,如学校和公共场所的网络覆盖率在逐年上升,这使虚拟的网络世界越来越全面地覆盖于我们的真实生活中,与我们的真实生活相契合。2016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6.88亿,普及率为50.3%,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报告》同时显示,网民的上网设备正在向手机端集中,手机成为拉动网民规模增长的主要因素。截至2015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有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6]网民群体的不断扩大使共享信息更加多源化、多样化,网民参与的自由度变得更高;互联网使公民能够报道新闻、揭露恶行、表达观点、监督政府、深化参与。[7]这无疑调动了网民的积极性,也为“揭丑”创造了条件。
(二)传统渠道效果不足
我国现阶段揭露查处贪腐不公事件的传统渠道包括体制内监察、个人举报、媒体监督举报。“体制内的反腐机构组织性和纪律性比较严格,对腐败事件的上访程序也有明文规定”,[8]并且需要考虑人力物力等问题,外加整个流程并不完全公开,工作的进度和效果往往不能完全让民众满意。个人举报中,由于调查方式和调查进度不公开,举报人很难跟进和了解事件的处理情况,这会使得事件在处理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利益关系等外力的影响,而导致事件搁置,并且如果没有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做好保密处理,举报人还很容易遭到人身攻击,所以个人举报的效果相对较差。媒体监督举报具有一定的力度,但是媒体揭丑的阻力也很大,在调查走访的过程中获取有效信息难度大,想要将调查结果呈现出来需要层层把关筛选以及审查,所以最终能够真正呈现出来的揭丑内容少之又少。传统渠道的效果缺失使民众把注意力转向网络平台,网络的匿名性保证了人身安全,网民的广泛性能够产生足够的关注度从而形成舆论压力促使相关部门解决问题,这使网民逐渐感受到自身的舆论监督力量并积极投身其中。
(三)国家反贪腐“借力网络”
我国历来坚持“反腐倡廉”,特别是在飞速发展、社会转型的改革开放时期。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反腐工作成为重点,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到反对“四风”走群众路线,从“老虎”“苍蝇”一起打,到党政、高校、企业巡视全覆盖,大批贪腐官员和事件被曝光和查处。在整治专项行动过程中,我国反腐机构也充分发现并抓住了网络所带来的机遇,积极引导,发挥正面效应,促成机构反腐与网络反腐的良性互动,形成了一个新局面:“我们正在大踏步进入反腐败信息化时代”。[9]反腐机构负责人表示,要充分发挥网络对反腐工作的推动作用,借助网络的透明、公开、快捷获取更多有效信息,推进关系民生、侵害群众利益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查处。在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下,网络已成为获取贪腐信息的一条重要通道。
(四)民众民主监督意识高涨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社会大众的民主监督意识在不断增强。一方面,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更加强烈,对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件的关注度、参与度不断增高;另一方面,民众更加注重发挥自身的监督职能,民众在响应反腐号召、关注和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同时,也对政府部门和相关执法人员进行监督,一旦发现贪腐现象,民众便可通过网络平台曝光,引起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推动事件的解决。事件的解决又会相辅相成地对民众的监督职能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让民众能够感受到自身的监督力量和话语权,从而提高了民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形成舆论监督、事件查处、净化社会三者的良性循环。
三、“网络揭丑”产生的积极效应
“网络揭丑”的快速发展,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积极的“网络揭丑”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家层面:推动反腐事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反腐事业的推行自古是“自上而下”的,由国家成立相关纪检执法机构,然后对各类案件进行查处,将结果和处罚决定进行公示,民众几乎无法参与。“自上而下”的反腐流程比较复杂,进展相对缓慢,缺乏第三方的监督问责,这就使反腐事业进展比较缓慢。网络揭丑的出现代表着“自下而上”民众力量的崛起,成为了与纪检执法机构和贪腐案件(或当事人)相对应的第三方监督力量,并同时成为新的信息来源地。网络揭丑在展现自身力量的同时也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重视,国家也试图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并发挥其积极的效应,这实际上就促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反腐路线的结合,并发挥其各自的优势,推动反腐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
民众层面:自身权利得到彰显。我国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网络揭丑”的出现,为人民提供了一条彰显自身权利的新途径,网络的开放性几乎可以容纳所有人,每个人都拥有了通过网络来行使权利的机会;网络没有复杂的程序步骤,降低了民众行使权利的门槛;网络的及时性也保证了人民行使权利的效率;网络的公开性和所能形成的舆论压力让民众能够感受到自身权利拥有的强大力量,从而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提高参与的积极性。
对象层面:震慑与警醒。“网络揭丑”以贪腐现象为最主要的对象。简单地说,之所以会出现贪腐现象,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个人的贪欲性导致权力滥用,二是针对贪腐的制约监察机制不够完善导致“钻空子”。个人的贪欲不易控制,形成一个完善且强有力的监察机制才是治理贪腐的关键,利用制约监察机制来使官员“不敢腐”从而“不腐”。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重抓贪污腐败,并重用网络,网络揭丑随之成为了制约监督机制中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使制约监督机制更加完善和强力。透明度极高的网络媒介使贪腐信息更容易被发现和曝光,强大的舆论压力促使贪腐事件在公众的监督下被国家纪检执法机构严肃解决,杨达才、雷政富、周久耕等事件的曝光和最终严厉惩治就是典型实例。网络揭丑不仅仅针对公共事件,更着眼于官员们的自身行为,这也影响了纪检机构反腐的针对策略,更重视对官员自身行为素质的检查,从而对官员们产生了一种震慑和警醒作用,促使他们在正确用权的同时检点自身行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媒介层面:促进“揭丑精神”提升。网络揭丑的出现成为与传统媒介揭丑相并肩的又一股揭丑力量,而且力量更加强大,这使媒介揭丑的力量不再单一,并且两者优势互补能使揭丑案件更快更好地得到解决。网民的广泛性与传统媒介工作者的专业性相结合,能够使收集到的揭丑信息更丰富有效。网络揭丑将信息曝光后,传统媒体聚焦于该事件,进行深入的调查和报道,引起更多受众的关注,可以说传统媒体是将曝光信息由“网众”扩大为“大众”的关键,充分发挥出其大众传播和舆论监督的职能,这样的配合不但推动了反贪腐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传统媒介揭丑精神的提升,有了网民的助力,他们不再势单力薄,报道更强势、更有力度。同时,随着网络揭丑势头的不断上升,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的支持和民众的极大参与热情,都会促进媒介揭丑的信心不断提升,也会减小揭丑的阻力,进而成为媒介揭丑的动力和支持。
四、“网络揭丑”的问题与困境
当然,消极的“网络揭丑”容易引发不良社会心态、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目前,我国“网络揭丑”尚存在如下主要问题与困境。
(一)网络自身的弊端
第一,网络媒介中存在诸多虚假信息。由于网络的开放性极强,信息的真假难辨,证据也变得不一定可靠,这极大地影响了网络揭丑的真实性。一方面,揭丑者可能误选了虚假信息,对当事人造成名誉上的伤害,另一方面也可能让别有用心的人编造虚假信息来公报私仇,对当事人进行陷害和诋毁,使当事人遭受重创。
第二,网民素质参差不齐。个人素质较高的人具有一定的信息辨别能力,也能较为理性地对待揭丑事件;与此相反,个人素质较低的人信息辨别能力较差,容易成为误选虚假信息进行揭丑的人和传播虚假揭丑信息的人。个人素质较低的人自控力较差,在面对揭丑信息时,容易表现出过激态度,传播一些侮辱性、攻击性的文字,甚至引发或参与群体性事件。此外,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或是仇富仇官的人也依赖于在网络上宣泄情绪,给官员扣以“无官不贪”的帽子,这就很容易导致网络暴力。
第三,网络管理体制不健全。这主要表现在职责与权利两方面:一方面,大部分社交网站都没有对管理人员进行明确的职责划分,这就造成了网络管理的松懈以及把关的缺失,容易滞留不实揭丑信息和过激言论,从而产生误导网民、伤害当事人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网络管理者缺乏明确的制度依据,这使他们在监管过程中没有实际的权威,从而影响了监管的力度和强度。
(二)侵权及伦理道德问题
在网络揭丑现象的研究中,传媒伦理道德与新闻侵权不再局限于媒介而更多地来源于网民群体。一方面,网络揭丑者将举报信息通过文字、图片、音视频等符号公布在互联网上,如果公布的信息属实,那么这些信息确实对纪检执法机构查处贪腐案件有积极的帮助,但这些信息也可能侵犯了当事人的某些权利。所以,体现在法律诉求上,就存在一个如何准确判断隐私权、名誉权的范围,以协调好公民言论自由权与民事权利冲突的难题。[10]而如果公布的信息经调查不实,那么这就直接侵犯了当事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还可能构成诽谤罪。另一方面,一些网络揭丑者借助“人肉搜索”的方式来进行举报信息的拼接和汇总;还有一些则是在事件被曝光后对当事人进行“人肉搜索”,将当事人的详细信息曝光在网上,满足民众的“窥私欲”,这可能会引发言论攻击、骚扰等不当行为,进而严重触及伦理道德的底线。比如“重庆官员不雅视频”被曝光后,网民的关注点不仅仅在当事官员,还对视频中的女主角“赵红霞”进行了人肉搜索,而且有一张被误认为是“赵红霞”的照片也被不断挖掘,这就严重地影响了赵红霞和“照片本人”的生活,侵犯了其名誉和隐私权。并且,这种过度的“揭丑”不仅伤害了被“揭丑”对象,而且对传媒伦理也是一种“蔑视”与“践踏”。[11]
(三)“揭丑”别有用心
第一,炒作盈利。一些目的不纯的网民借揭丑者的头衔来进行炒作提高网站知名度从而盈利。比如,被称为“江湖式揭黑”的齐鲁维权网,这个网站曝光了一份医疗行业受贿的黑名单,内容非常详细,由此引发了网民的高度关注。除了公布“黑名单”引起轰动外,该网站还有一个争议颇多的地方——在网站两侧的醒目位置,赫然标注着“此广告位特价招商”的字样。[12]由于网民对于揭黑事件的高度关注,该网站点击率突破135万次,如果广告招商成功,网站开办者将获取巨大利益,这就难免让人猜疑该网站开办者的真正意图。此类别有用心的揭丑,就与最初的正义目的相违背,成为一种商业炒作的工具。
第二,敲诈勒索。网络揭丑所引发的高度关注,让一些官员都受到震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跟踪等方式,拍摄一些官员们不当行为的照片,以网上曝光要挟、换取巨额钱财。由此导致揭丑的事件不但没有被曝光,当事人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罚,还让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敲诈勒索,扭曲了“网络揭丑”的真正意义。
(四)拟态环境下的“网络狂欢”
“拟态环境”最早由美国学者李普曼提出。在李普曼看来, “拟态环境” 是由传播媒体在人与现实环境之间插入的信息环境,它并非客观现实环境镜子式的再现, 而是经过传播媒体选择、加工(如采访、编辑)后向人们提供的模拟环境。但由于人们往往忽略媒体的这种选择和加工, 把这种“拟态环境” 当成真实的客观现实环境而接受, 并据此做出行为反应;人们通过大众媒介去了解外在世界,从而形成脑海中对外在世界的认识,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自己所身处的媒介环境当成了外在世界而身陷其中。[13]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它使网民深处网络拟态环境之中,使网民根据网络所提供的信息来认识外在世界。在这种拟态环境下,网络揭丑所引发的极大关注和持续高热度,就使网民们对于揭丑越发关注和重视,从而也产生了扭曲的揭丑现象。
第一,习惯性质疑。网络揭丑的出现让很多贪腐不法事件遭到曝光,但也让一些网民产生了习惯性的质疑。例如,一位女网友在网络社区里感叹了几句为官父亲的清廉,就沦为了“人肉搜索”的对象,好事者仅仅为了证明“天下乌鸦一般黑”“洪洞县里无好人”,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嫌疑人”一一对号入座,也不管是否侵犯了个人隐私。[14]一番“揭丑”过后,真相不了了之,只给当事人带了伤害;而需要思考的是,如果仅仅是对自己父亲的清廉稍加赞扬,就会遭到质疑性的揭丑和被冠以“坑爹”的名号,那还怎么去推崇和倡导廉洁呢?
第二,娱乐化倾向。揭丑是一个严肃的过程,但是网络揭丑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焦点对准官员们的个人生活,戴着“揭丑者”的帽子来满足自身的窥私欲。这使身处其中的网民也随之将着眼点放在了这些娱乐化的信息上,而不再是关注事件本身,这使得网络揭丑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五)法律层面的缺失
网络揭丑之所以会出现各种问题与困境,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缺少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虽然我国已有针对互联网所制定的法律法规,但网络揭丑发展至今,依旧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支撑和管理,这就导致网络揭丑在进行过程中,有很多涉及法律层面的内容都是模糊不清的。例如,在网络揭丑的过程中,揭丑者举报相关信息,如涉及当事人的名誉或隐私权,这与民众的基本权利如何权衡,对于侵权行为和可能造成的诽谤、污蔑、人身攻击等行为如何处置,对于揭丑者在举报信息后所应该受到的保护,这些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再者,网络揭丑并不是由民众独立完成的,还需要借助传统媒体,最终交由政府相关部门处理,这其中的程序与步骤,以及各自的权利与责任,在法律层面也是不完善的。对网络揭丑赋予怎样的地位和职权,如何引导其发挥自身的特点和积极的效用,如何规范管理,这些也都需要法律来规定。因此,针对“网络揭丑”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是非常迫切的。
五、“网络揭丑”的引导与规范
引导和规范“网络揭丑”健康发展,应在遵循网络传播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探寻科学方法与有效途径。
(一)法律与制度保障
法律和制度是保障网络揭丑能够正确进行、积极发展的基础,网络揭丑的很多方面都需要保障和规制。当前我国反腐主要依靠制度反腐,在法律框架内,有专门机构和合理程序对腐败问题进行揭露与查处,但是公权力的自我剔除与修复能力仍需不断强化。因此,网络反腐效用的发挥首先需要制度反腐的高度协调配合,其最后结论要以制度化的形式出现,只有实现两者的有效衔接,才能发挥网络反腐防腐的功效。[15]其次,需要对网络揭丑进行一个官方的定义,明确网络揭丑在我国反腐事业中的地位,赋予它应有的职权,将其“身份”合法化,这样网络揭丑才能更加具有权威和效力。再次,对于网络揭丑的程序也需要规范化和合理化,以往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定程序,网络揭丑经常出现脱节、权责不分、事件处理遇冷等现象,严重影响揭丑的效率和质量,所以对于揭丑民众、媒体、政府机关这三大部分在揭丑过程中各自的职责和衔接的步骤应该明确规定。此外,对于网络揭丑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也需要法律法规来规定清楚。第一,举报人在举报信息时对于内容是否侵犯当事人名誉权、隐私权如何规定,如何权衡民众的民主权利(如知情权等)和当事人的名誉、隐私权。第二,对于在网络揭丑过程中可能构成的犯罪行为,比如诽谤罪,如何定罪和处罚。第三,举报人和被举报人都享有哪些权利,受到哪些保护,可以通过设立“举报法”来明确。第四,由于网络揭丑具有匿名性和广泛性,所以对于民众在互联网上的行为也应该出台或更新细化行为规范来规制,从而促进揭丑的理性化,避免发生非理性的行为。
(二)注重三方平台建设
第一,官方发言渠道。网络揭丑出现以来,更多的是民众掌握主动权,通过举报制造舆论压力来推动案件的处理和解决,政府部门相对被动,有时甚至是被倒逼应对,这不利于政府与民众的互信,也不利于舆论引导。所以政府应该积极参与进来,通过网络建立官方的发言平台,主动获取和监测网民们的揭丑信息,在揭丑案件出现的第一时间发出官方的声音,以进行正确舆论引导和管理。接手揭丑案件后,通过官方平台跟进案件的进展,采纳网民合理的建议,接受网民监督,并及时反馈相关信息。同时,网络官方平台有利于提高政务公开的透明度,这样的双向沟通渠道有助于政府部门和网民的合作互信,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更高效地处理揭丑案件,避免错误言论的产生和传播。
第二,民主监督渠道。网络揭丑的合理化,不仅仅需要法律的外在支持,更需要为民众提供一个“说话”的平台。网络揭丑之所以会出现很多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监督平台的不完善造成的。因此,可以在政府的官网上开辟专门的“揭丑区”,或是建立专门的监督型网站,供网民提供揭丑信息,发挥其监督职能。监督平台应该设专业人员管理并及时提供反馈,便于网民跟进事件核实调查的情况,一旦事件调查属实或有相关处罚决定时,应在网站进行公示,让网民能够了解事件结果,形成一个互动的监督平台,这样揭丑信息在得到有效集中的同时也更便于管理。
第三,当事人回应渠道。当事人也是有发言权的,在信息遭到举报后,应当给当事人一个平台来回应有关自己的举报信息,这一点很重要,但时常被忽略。当事人回应平台可以设立在政府网站版面上,设专人管理实名认证。这是给当事人一个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也可能是承认错误);如果揭丑信息不实,这个平台也可以给当事人一个申诉和澄清自我的机会,一定程度地帮助当事人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减少对自身产生的不利影响。
(三)提升民众网络素养
网民是网络揭丑的主体,他们的素质直接影响网络揭丑的效果。网络素养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网络技术的应用,这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培训班、网络课程等进行培训,网络技术的普及会扩大网民群体,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网络揭丑中来,同时网络技术的熟练也将提高网民获取和甄别信息的能力,有效地减少虚假信息的出现和传播。第二是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这主要是通过加大社会的普法宣传和教育以及对于提高社会责任感的宣传和教育,帮助民众了解和学习法律,树立法律意识,培养社会责任感,使网民们对自己的网络行为更加负责任,减少非理性行为的出现。第三是网络伦理道德的培养,主要是通过网民自身的学习以及社会对于伦理道德知识的普及来达成,网民伦理道德素养的提高会使网络揭丑中的言论生态更加有秩序,更加和谐。这里的和谐不是指“不敢言”,而是指在遵守伦理道德的基础上理性地发表言论,采取行动,避免过激不当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他人的伤害。网民网络素养的提高,将使网络揭丑的主体水平整体上升,从而使网络揭丑的质量和效果也随之提高。
(四)加强网络监管
加强网络监管,能有效减少网络揭丑中的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色情等现象。第一,权责分明。国家应规定信息与责任挂钩,根据网站发布信息的重要与危害程度,让网站管理者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将使网站管理者认真严格管理网站,同时明确网站管理者的相应职权,如删除或保留信息、屏蔽不当言论的发表人等,让网站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得到保障,同时也提高他们的管理积极性和管理力度。第二,建立相应标准。国家应针对一些特殊的网络行动(如网络揭丑)制定相应的执行标准,如哪些信息不能公布、哪些言论不能发表以及相应的惩治方式等,网民也需要根据标准来核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合理。第三,培养专业队伍。国家应加强对网络管理人员的培养,一方面提高他们应用网络技术的能力,培养网络管理能力;另一方面更应该培养他们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当有突发事件发生时,如何控制局面、如何尽量避免不利因素的产生、如何进行正面的舆论引导,以及如何上传下达等,这些都非常考验网络管理人员的处置能力,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事件的处理效果,过硬的管理队伍和管理能力将是网络揭丑顺利正确进行的重要保证。
[1] 黄建跃.“网络扒粪”反响论调之辨正[J]. 领导科学, 2013(03):10-12.
[2] Thomas Barnebeck Andersen. E-Government as an anti-corruption strategy [J].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009(03):201-210.
[3] 叶竹盛. 网络时代的中国式“扒粪”[J]. 南风窗, 2012(20):30-31.
[4] 陈潭、刘建义. 网络时代的“扒粪运动”—网络反腐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 理论探讨, 2013(04):11-16.
[5]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209.
[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http://www.cnnic.cn/gywm/xwzx/rdxw/2016/
201601/t20160122_53283.html.2016.
[7] Larry Diamond. The Coming Wave [J].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2(01):23-25.
[8] 度永梅. 网络反腐的传播机制及困境分析[D].重庆:重庆大学, 2013: 34-36.
[9] 周丽萍. 网络:反腐新宠[J]. 人大建设, 2008(03):26-28.
[10] 邹庆国. 网络反腐:兴起缘由、价值解读与风险防范[J]. 理论导刊, 2012(04):8-11.
[11] 杨静. “揭丑运动”对媒介生态的影响[J]. 媒体时代, 2013(10):41-43.
[12] 张庆申、孙安清.民间人士自建网站曝光受贿医生引争议——“江湖式”揭黑能走多远[N]. 法制日报, 2008-6-30(6).
[13] 陈航. 新媒体与“拟态环境”[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0(06):111-114.
[14] 施平.别让“揭丑”快感淹没向善之心[N].解放日报, 2014-7-23(5).
[15] 程曼丽. “扒粪”之后需要什么?—兼谈“中国梦”[J].新闻与写作, 2013(01):88-89.
The Multiple Logic and Guide and Specification of“ InternetRecrimination””
Yan Daocheng Wang Lip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ract: “Internetrecrimination”is the social supervision form using the internet users as the main body and internet as the platform.The inner driving force of “internet recrimination” is the growth of the awareness of citiz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has the new change under its influence. Based on the multiple logic and multiple effect of “internet recrimination”, only by scientific guiding and regulating, the orderly 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can eventually be formed.
ds: “Internet Recrimination”; Multiple Logic; Multiple Effect; Guide
D621.5
A
1006-1789(2016)02-0005-07
责任编辑 曾燕波
2016-01-23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数据时代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机制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5BXW029。
燕道成,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汪丽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