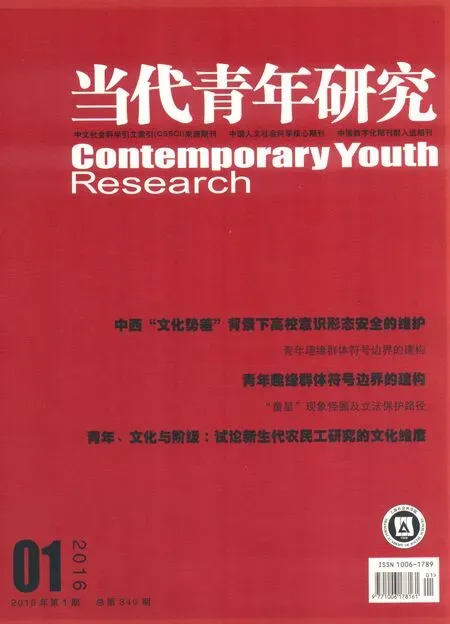“微时代”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嬗变及规制
2016-03-18张林
张 林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微时代”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嬗变及规制
张 林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微时代”的到来在改变传统青年政治社会化范式的同时,也为青年政治社会化的现代转型带来了冲击。“碎片化”、“去中心化”导致青年群体政治选择困难,“指尖决策”加剧了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非理性”,“手机依赖”导致青年群体政治角色认知失调,“把关人”角色弱化加剧了青年群体政治行为失范。要规制和应对这些不足,必须要从“外在引导”与“内在形塑”两个方面入手,要注重“微空间”中的政治治理,加强现实政治环境的优化改善,建立网上网下和谐共振的双向引导机制。同时,也要注重青年群体的“内在形塑”,提升其“微素养”,完善其“微道德”。
“微时代”;青年;政治社会化;冲突;治理
青年政治社会化是青年社会化的核心内容,是青年群体在社会主体的教化下逐渐形成符合特定社会政治要求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实践的过程。青年政治社会化是青年群体由“自然人”转变为“政治人”的必经之路,其价值目标内在地包含了青年的个体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两个层面,是一个对青年和社会发展都至关重要的过程。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微博、微信、微支付、微电影等“微产品”不断涌现,“微时代”已悄然来临。青年群体正以拍手称快的姿态迎接着“微时代”的到来,对各种新生的“微产品”表现得青睐有加。“刷微博”“聊微信”已经成为青年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不可否认,“微时代”带来的各种技术和理念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当代青年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当然,“微时代”的到来也为青年政治社会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环境空间。传统的政治社会化范式受到“微媒介”和“微产品”的强烈冲击,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方式和途径也都发生着重要改变。探究“微时代”背景下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嬗变以及存在的隐忧,对于推动当代青年政治社会化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的消解与嬗变:“微时代”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时空转向”
信息媒介塑造着人类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每一次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都会营造一种全新的信息空间,从而重塑整个人类社会的时空结构。就像曼纽尔 • 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所说 :“我们个人和集体存在的所有过程,都直接受到新技术媒介的塑造。”[1]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变革为人类社会开启了“微时代”的大门,并逐渐改变着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和实践方式,推动着人类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的信息传播、话语表达、人际交往等方式的急剧变化,对当代的青年政治社会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时间的多维”与“空间的流动”:青年政治社会化历程加快
青年政治社会化要达到预期效果,必须要经历特定的时间跨度和空间积累。传统观念认为,青年群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一般是在14岁到28岁期间能够基本完成。而之所以需要十多年的时间跨度,是因为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需要青年群体掌握大量的政治技能,而政治认知、政治判断、政治习惯的养成都需要青年群体具有一定知识量的积累。因此,受物理时空条件的局限,传统的青年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需要的时间较长,每个阶段的任务也比较明确。如果说传统网络时代因为台式电脑的笨重和信息技术的瓶颈,青年政治活动的时空环境仍然相对稳定,那么“微时代”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便捷与4G网络技术的普及,就使得青年的政治活动突破了时空的局限。“微时代”中“移动的网络”将时间技术和空间技术高度融合,形成了“多维的时间”和“流动的空间”。“永远在线”突破了青年政治参与的时空局限,青年群体可以在车站、在路上,甚至在卫生间就利用“掌媒”阅读政治资讯,谈论政治话题,参与政治互动。传统“点对点”的政治参与模式逐渐被“点对面”的全方位的政治参与所取代。“全天候的网络在场”和“日不落的网络狂欢”让青年群体可以跨越时空地接触政治信息,分享政治资源,参与政治活动,而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物理时空。可以说,在“微时代”背景下,青年群体的时间是“多维”的,空间是“流动”的,政治社会化是随时随地进行的。这使得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历时态过程缩短,而共时态坐标却是全方位的‘世界历史图景’”,[2]极大地加快了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历程。
(二)“虚拟交往”与“真实社交”融合:青年政治社会化途径多样
在传统的社会时空结构中,家庭、学校、政治组织、大众传媒等的正面教化是青年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施化主体利用自己不同的社会地位对青年群体实施不同类型的政治教化。这种政治教化的途径既可以是言传身教的政治感化,也可以是规范系统的政治教育。但不管采用何种教化形式,传统的政治社会化范式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和灌输性的特征,青年群体是在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主导模式中完成自己政治角色的转化。而在“微时代”的时空环境下,青年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变得灵活多样。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突破了传统互联网时代的时空范围。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普及和实名制趋向改变着网络交往的既定规则。青年群体的社会交往在经历了现实世界的“熟人社会”向传统互联网时代的“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后,再次有了向真实世界转变的趋向。在“微媒介”的身份交往中,匿名性和虚拟性的时空范围正在缩减,而“实名”的真实世界的范围正逐渐扩张。这为交往空间营造出了一种“真实的虚拟”,实现了青年群体“虚拟交往”与“真实社交”的高度融合。在这样的时空维度中,青年的政治社会化途径不再局限于学校或政治组织说教式的单向的政治灌输,而是开始转向青年与社会主体开放式的平等的政治互动。青年群体的政治认知既可以来自“朋友圈”的政治探讨,也可以来自与某个政治人物的“微博”互动。总之,“微媒介”实现了青年群体虚拟政治活动与现实政治活动的高度融合和自由转换,极大地拓宽了青年群体政治交往的路径形式。
(三)“微关注”与“宏视野”并存:青年政治社会化方式更新
从参与主体的维度出发,传统政治观念认为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的统一是实现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方式。社会教化主要是特定的社会组织采用多种手段向社会个体输送社会主导的政治文化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认同其政治理念,以维护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而个体内化则主要是社会化中的个人通过主观认同和自我建构等形式形成自己政治价值理念的过程。长期以来,人们都非常注重社会教化在青年政治社会化中的功用,对社会的政治教育给予了很高的期望,而对个体内在的政治体悟缺乏相应的关注。当然,这与我们长期以来推崇“大”理念和高度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紧密相关。而在“微时代”的时空环境下,这种注重宏大叙事而轻视个人体悟的社会化方式开始受到冲击并逐渐消解。微博、微信等“微媒介”打破了宏观政治教育传输的单向通道,使得青年群体开始以“微”形式关注个体存在与国家政治。个人微观的柴米油盐等生活琐事与国家宏观的民主公正等政治话题交叉并存。在“微媒介”上,青年群体可以做到刚刚还在谈论“今天吃什么”的话题,马上就切换到对“国家反腐”等政治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微时代”中,“微关注”与“宏视野”的并存,实现了青年群体“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叠加和自由转换,从而改变了青年政治社会化的社会教化方式和个体内化方式。
(四)“主体的自觉”与“个性的凸显”:青年政治社会化“自我实现”增强
无独有偶,就在本次学术研讨会召开短短数日之后,2018年9月24-25日,由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宗教学与历史教研室主办的俄罗斯宗教学中心协会第四次代表会议在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举行。俄罗斯宗教学中心协会是俄罗斯最具学术权威性的宗教学学术研究组织之一,致力于世界宗教历史与文化、宗教哲学、宗教学理论、文明的冲突与共生等研究,每两年召开一次代表会议。本次代表会议以“作为文明互动因素的宗教”为主题,汇集了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喀山、叶卡捷琳堡、伊尔库茨克、巴尔瑙尔、赤塔、雅库茨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乌苏里斯克等俄罗斯城市,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等科研单位40余名国际学者。
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完成离不开青年群体的政治实践,只有在参与政治实践的具体过程中,青年的政治认知才能得到现实的检验和升华。正如王浦劬教授所言,政治实践是“客观政治世界达之于人们主观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最重要的桥梁”。[3]而政治实践发展的最高形式就是主体政治活动的“自我实现”。青年政治社会化的“自我实现”是指随着青年群体主体性意识的增强,青年自觉学习政治知识、提升政治技能,主动参与政治实践,积极适应或改造社会政治关系的过程。“自我实现”是青年群体“寻求自我的过程,突出了新时期青年个体的自主性”。[4]而在“微时代”的时空背景下,青年群体的自主性更是得到进一步的激活和释放。青年群体不再是政治灌输的被动对象,而是追求自我呈现的能动主体。他们能够利用微博、微信等“微平台”即时地分享政治资源,表达政治诉求,参与政治互动。青年群体的政治话语空间和自我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微时空”里,青年群体可以在围观、转发和评论中尽情展现自己的政治观点,发泄自己的政治情绪,彰显自己的政治诉求。总之,“微时代”时空环境中青年群体“主体的自觉”与“个性的凸显”使得青年政治社会化“自我实现”的程度进一步增强。
二、“碎片中的冲突”:“微时代”青年政治社会化之隐忧
从宏观上看,“微时代”的到来的确为青年政治社会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政治舞台,但“双刃剑”效益又总是时刻提醒着人们除了看到乐观的景象之外,还必须要善于发现问题,心存一份“隐忧”。在“微空间”碎片式的信息世界里“呈现出来的是‘一地鸡毛’的生活本相”,[5]既包含着后现代的个性与自由,也夹杂着形形色色的喧嚣与冲突。这些“碎片中的冲突”给青年政治社会化的顺利完成带来了挑战。
(一)“碎片化”、“去中心化”导致青年群体政治选择困难
“微时代”中“微博”、“微信”等“微媒介”的普及改变了社会信息的传播方式,“碎片化”、“去中心化”传播趋势加剧。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传播的主体,每条“微博”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内容。而一条“微博”内容又仅仅局限在140个字符,可谓“惜字如金”。如此必然导致“微空间”信息的过散、过碎。人们在这种时空环境里随时随地阅读、评论和转发信息,必然会使得网络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和“裂变式”传播。这使得“微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渠道多样,却无中心;信息海量,却无权威”的显著特点。不同国家、政党和阶层的政治观念在“微空间”中同时并存,相互交流交融与交锋,这就给青年群体塑造了一个虚虚实实、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在这种碎片式的信息海洋中,主流政治价值理念的传播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传统的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心理活动开始逐渐消解,主流政治权威对青年群体的绝对主导作用也开始不断弱化。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西方国家加大了其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度,一些西方社会的政治思潮开始在“微空间”中的迅速蔓延,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西方普世价值与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的政治理念冲突加剧。青年群体长期在这种不同的政治文化中浸泡和游走,使得其政治认知越来越琐碎和多元,缺乏一种坚定有力的政治判断标准,政治选择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二)“指尖决策”加剧了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非理性”
“微时代”的来临离不开移动互联网终端的高度发达,青年群体的政治交往、政治监督等政治活动都可以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上借助手指就可轻松完成。“掌媒”的高度发达使得某些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微时代也可以被称为‘手指时代’。”[6]而在“手指时代”的网络狂欢中,“指尖决策”正日趋成为青年群体日常行为决策的常态。然而,正是这种即时、灵活的“指尖决策”使得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行为变得更加随意和自我,进一步加剧了青年群体政治参与中的“非理性”因素。在相对开放和自由的微时空环境下,青年群体的网络政治参与变得热情高涨。在手指的不断滑动和敲打中,青年群体可以即兴地转发政治言论,发表政治观点,而很少能够冷静理性地思考这些政治信息的真实与否,正确与否。在这些碎片式的政治话语空间中,青年群体传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复杂思想”正逐渐消解。他们更多的是在只言片语的政治话语中管中窥豹,倾向于情绪化地表达政治诉求。由于和传统现实的政治参与不同,青年群体不必要过多地考虑政治身份、政治地位等现实政治因素的影响,所以,他们往往表现得更加任性和自我。可以仅仅是根据个人偏好和直观感受就简单地作出政治判断,而对那些不同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则一味地采取否定和谴责的态度。然而较之于少数的网络政治精英,青年群体的信息素养和政治判断能力都相对较弱,所以在“指尖决策”的政治参与中很容易就出现盲目从众、跟风甚至极端化的非理性政治行为。
(三)“手机依赖”导致青年群体政治角色认知失调
如果说人对人的依赖,是人类社会在原始生产力条件下的自发趋势。那么,人对物的依赖就是人类物质生产水平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前,人类社会依然正处于人对物的依赖阶段,只是这个“物”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众传播社会学家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就提出了关于“媒介依赖”的相关理论,认为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越是能依赖媒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媒介对人就越重要,影响也就越大。随着移动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在智能手机上的合二为一,智能手机正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媒介中心,成为青年群体在“微时代”最重要的上网工具。眼下各种“微信控”、“低头族”随处可见,可以说,手机已经成为青年群体学习、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件“附属品”,“手机依赖”已经成为青年群体不折不扣的生活写真。从本质上看,“手机依赖”只不过是“虚拟依赖”在“微时代”的一种最新表现而已。青年群体长期依托手机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参与政治活动,会使得其政治角色认知发生改变。因为虚拟的政治实践和现实的政治活动存在很大差别,很多世俗的政治规范、政治要求在虚拟世界中都可以被最大程度地弱化,而现实的政治参与又总是存在种种不足,这种虚拟角色与现实角色之间的反差,使得青年群体总是试图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去寻找在现实社会中不能拥有的政治满足感。而长期沉浸于这种虚拟的政治角色扮演,会弱化青年群体参与现实政治实践的兴趣,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青年群体对现实政治实践发生疏离。久而久之,就会导致青年群体政治角色认知出现失调,政治人格发生分裂,从而产生众多现实世界的“沉默者”和虚拟化的“政治人”。
“把关人”一词作为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 • 卢因(Kurt Lewin)于1947年最早提出。他认为“把关人”控制着信息流通的各个关口,负责对传播的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从而引导舆论。不可否认,“把关人”的角色在传统的信息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微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已经来临。青年群体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发布者。无数的信息源头和裂变式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得传统的“把关人”角色开始弱化。在传统的政治交往中,青年群体的政治行为要严格遵守现实的政治规范和政治纪律。而在虚拟性、开放性和交互性共存的微时空环境中,一旦外在的政治把关和政治约束机制开始减弱,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就会迅速在微时空中得到蔓延。一些虚假的、非法的政治言论也会堂而皇之地混杂其中。青年群体由于政治理性不足,很容易受到这些不良政治信息的干扰而做出政治失范的行为。因为在这种监管缺位和规则缺失的网络时空中,青年群体不会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循规蹈矩的旁观者,他们“自然有胆量甚至乐意去展示私密的我、情绪化的我、夸张的我、丰富的我”。[7]有人可以仅仅是根据自己的政治偏好和直观感受就对一些政治事件发表自己过激的政治意见。或者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点赞”或更多人的关注,就在“朋友圈”转发一些道听途说的政治言论。也可能有人利用网络的隐蔽性去随意传播政治谣言,恶意攻击政治人物,挑战既有的政治权威,甚至参与一些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严重相悖的政治活动。所有这些政治失范行为都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顺利完成带来了严峻挑战。
三、“何以解忧”:“微时代”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导”与“塑”
面对“微时代”给青年政治社会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我们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除了要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以外,我们更应积极探寻相应的解忧之道。笔者认为,要规制和应对“微时空”中青年政治社会化的不足,必须要从“外在引导”与“内在形塑”两个方面入手。也就是既要注重“微空间”中的政治治理,又要加强现实政治环境的优化改善,尽量建立一种网上网下能够和谐共振的双向引导机制。同时,也要注重青年群体的“内在形塑”,要提高其媒介素养,完善其网络政治道德。争取建构一种将“外在引导”与“内在形塑”相结合的青年政治社会化模式。
(一)充分利用“微媒介”,将主流政治文化融入“微空间”,引导“微舆论”
在“微媒介”时代,传统青年政治社会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施化主体要转变施化思路,要学会充分利用“微媒介”来传播主流政治文化。政府部门、政治组织和教育机构等要充分认识到“微媒介”的重要作用,要积极运用自己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微平台”向青年传播社会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思想。当然,这种微平台的新型传播要与原来的直接灌输有所区别,不能再将政治意图、政治观念等通过枯燥乏味的文字强加给青年。实践证明,这反而会适得其反,引起青年群体的反感和抗拒。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青年群体通常不会太愿意接受意图很明显、方式很强硬的政治说教。所以,在使用“微媒介”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采用渗透式的方法,无论是内容选择还是话语表达都应该更具时代特色,要符合青年群体的社会心理特点。比如,我们可以采用视听同步、图文并茂等灵活生动的传播形式将主导政治文化像空气一样注入青年的日常生活,尽量做到将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与青年的日常生活实现无缝对接。只有让社会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融入青年群体的“微生活”,才能引领“微舆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理念的主旋律,激发青年的政治认同,从而使青年群体的政治社会化朝着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方向发展。
(二)健全制度法规和加强技术监控,完善“微空间”政治治理
从时间上看,“微媒介”属于最近几年才兴起的新兴事物。古语有云,“新生之物,其形必丑”。不可否认,“微空间”里的确充斥着很多低俗、虚假、非法的政治言论和政治信息,这对青年的政治社会化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要规制“微媒介”带来的不足,就要加大对“微空间”的政治治理。首先,要完善制度建设。“微空间”不能成为信息杂乱的垃圾场,必须要建立一套系统严格的制度规章。一方面,对于微博、微信等人们常用的社交平台,必须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实名登记制度。要让“微平台”的信息传播做到有名可查,有源头可找,从根源上减少不良政治信息的传播。另一方面,要完善对“微电影”“微小说”等“微产品”的审查制度。对那些具有错误政治导向的“微产品”进行禁播,要真正做到对“微产品”的政治内容实行严格的政治把关。其次,要健全法律法规。“微空间”的政治自由不是漫无边际的,必须要以一定的法律法规为底线。我们应该抓紧完善“微空间”中的法律法规。对那些随意传播政治谣言、恶意攻击政治人物的传播者要进行相应的法律惩处。只有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才能为“微空间”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再次,要加强技术监控。信息监管部门要加大技术投入,加强对相关互联网企业的技术合作,提升技术监管的力度和水平。对一些不良的政治信息和政治言论要及时屏蔽和删除,尽量为青年群体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活动氛围。
(三)改善现实政治环境和优化政治教育形式,塑造青年政治活动的现实空间
虽然“微媒介”极大地延展了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时空范围,但毕竟虚拟的政治实践与现实的政治活动还存在很大差别。而且不管“微技术”如何发达,都不可能完全取代现实的政治实践。当前,之所以很多青年会出现“手机依赖”,沉迷于虚拟的政治交往不可自拔,一方面是因为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确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另一面也是由于现实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教育形式还不能完全调动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热情。所以,我们应该尽量改善现实的政治环境和优化政治教育形式,积极引导青年群体投身现实政治实践。一方面,政府、学校、社区等要尽量为青年提供一个民主、宽松的政治环境。要定期开展一些形式多样的政治主题活动,鼓励青年探讨政治问题、参与政治活动。要将青年群体的目光从冰冷的手机屏幕转移到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中来。对青年应该参与的选举、投票等政治实践不能形式化、走过场。要充分借助这些直接的政治参与来调动青年的政治热情,使他们了解现有的政治准则和政治秩序,明确自己的政治使命,从而增强对现行政治制度和价值的认同。另一方面,要改变单一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努力构建一种实践型、综合型、开放型相结合的政治教育模式。青年群体的政治社会化不是单一的书本教育能够完成的,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政治实践途径,要鼓励青年参与各种志愿活动、社区活动和自组织团体。只有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青年群体才能真正地了解政治文化,开拓政治眼界,积累政治经验,从而促进自己政治社会化的顺利完成。
(四)培育“微素养”,完善“微道德”,提升青年政治参与的“内在自觉”
媒介素养作为现代公民的一项重要素质指标,是指人们“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8]在信息传播“碎片化”“去中心化”的“微时空”中,培育青年群体在“微媒介”使用中的“微素养”就显得更为重要。我们的各级学校、政治组织和主流媒体都应该积极发挥教育功能,培育青年群体在“微平台”中解读信息、甄别信息和使用信息的素质和能力。要注重培养青年群体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不能随便接受政治谣言蛊惑。要提升他们的政治信息素养和政治判断能力,使他们养成独立政治人格。在面对政治问题时,能做到理性思考,冷静客观,而不是偏信盲从、瞎起哄。只有提高了青年群体本身的媒介素养,才能从根本上产生抵抗不良政治信息的免疫力,提升青年政治社会化“自我实现”的效率。同时,还要注重完善青年群体的“微道德”,提升青年群体在“微空间”的自律能力。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每个人都是信息源,人人都有麦克风。各种虚假、非法的政治信息防不胜防,全靠外在的技术监控也不现实,最终还是要依托于青年群体的个人自觉。将外在的法律规范与内在的道德约束相结合一直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在“微时空”条件下也同样适用。青年群体除了要掌握必要的媒介技能和法律规范,还必须要遵守“微空间”的伦理道德秩序。只有具有了个人内在的道德约束,才能提升青年政治参与的“内在自觉”,从而促使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朝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发展。
[1]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64.
[2]王卫.网络时代青年社会化范式的转型[J].青年研究, 1999(12):10-14.
[3]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286.
[4]王大春、高军.网络时代青年社会化的自我实现[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4(06) :100-102.
[5]包莉秋.论微时代下社会审美诉求的冲突与调适[J].求索, 2013(07):226-228.
[6]罗迪.微时代大学生思想行为新样态透析[J].中国青年研究, 2015(04):80-84.
[7]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47.
[8]张艳秋.理解媒介素养:起源、范式与路径[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80.
“MicroAge” of Evolu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Youth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Zhang Lin
(School of Marxism,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he arrival of the “micro age” changedthe traditional youth political social paradigm.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brought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youth political socialization.“Fragment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made youth groups’ political choice difficult, “fingertips decision” exacerbated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youth groups’ “irrationality”,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led to youth groups’ political role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gatekeeper” role weakening intensified anomie of youth groups’ political behavior.To regulate and deal with these weaknesses, two aspects of “outer guidance” and “internal shape” must be put emphasis on.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micro space”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strengthen the optimization to improve the re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set up an online and offline two-way guidance mechanism for the harmonious resonance.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ner shape” of youth groups, promote the “literacy” and perfect the“moral”.
“Micro Age”; the Youth;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Conflict; Governance
C913.5
A
1006-1789(2016)01-0022-06
责任编辑 曾燕波
2015-07-17
张林,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