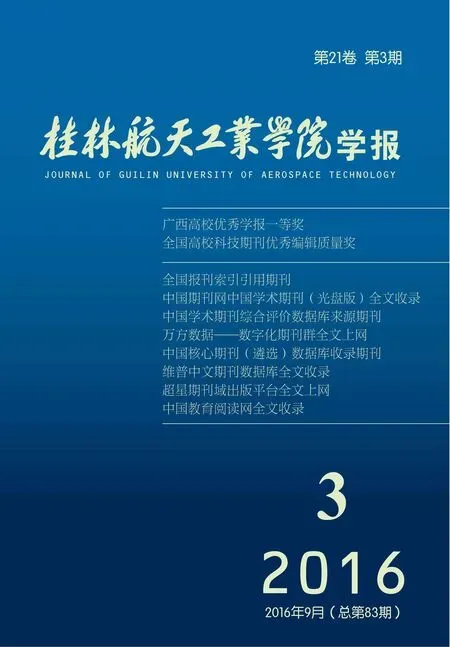民俗风情描写在《呼兰河传》叙事中的作用
2016-03-18吕海玲
吕海玲
(长沙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6)
民俗风情描写在《呼兰河传》叙事中的作用
吕海玲*
(长沙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6)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自传体小说,书中描绘了东北小镇呼兰河的民俗风情,展现出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特色。这些民俗风情自身所具备的审美价值打破了传统的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在情节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科学理性主义来袭时,人们对待书中所描写的一些民俗陋习应该秉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来观照传统文化。
民俗风情;《呼兰河传》;叙事;审美价值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成名之作,为其获得众多盛誉,且被列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必读书目。鲁迅对其评价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同时,茅盾的观感是:“‘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一些比‘像’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1]手捧书籍,俯首低吟,人们会不自觉地被其极具地方色彩的风俗画面所吸引与触动,这种淡化情节的描写方式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1 颠覆传统的叙事模式
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经过长时间的积淀与深化,在读者阅读经验中已然构建成无意识的理解框架,塑形成一种固定不变的审美情趣与思考方式。对于千篇一律的小说叙事模式——全知型视角下以情节为中心的连贯性叙事,输出给读者的是审美疲劳与钝化的视觉效果,甚至培养了民族“惯性”的文本批评与“恒性”的鉴赏能力,以至于“新小说”与“五四”时期,西方翻译名著被民众“拒之门外” ,抑或秉持着一种偏倚的态度来看待“舶来品”、观照西方的现代文明,从而产生了自我满足的文化效应。
诚然,在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结构之外,还有其他的中心可以搭建小说框架,寄托作者的深情与思想——人物与环境。在这里我们主要论述环境。“小说中独立于人物与情节以外而又与之相呼应的环境或是背景,既可以是自然风景,也可以是社会风景,乡土色彩,还可以是作品的整体氛围乃至‘情调’。颇为五四作家推崇的‘抒情式小说’,可能落在人物心理的剖析,也可能落在作品氛围的渲染。而这两者,都是以情节为中心的传统小说叙事结构的突破。”[2]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作家为了突破传统的桎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小说长河中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汪曾祺笔下那个清新高雅、温婉淡泊的苏北水乡,还有沈从文构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他们是地域灵魂的刻画者,是地方的代言人,也是民族的传唱者。
在时代横断面的铺展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呼兰河传》中,也有异曲同工之构想。萧红在前两章大篇幅描写了当地的民俗风情。第一章以呼兰河地理位置为中心,对其内部的构造:东二街道、西二街道、十字街,还有些小胡同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勾勒出了小城的整体轮廓,在观者的思维里形成了一个隐喻的布局,同时也描绘出了一幅淳朴而“卑琐平凡”的乡土生活图画。笔锋通俗却不庸俗,简单而富有韵味,使得读者细细咀嚼时颇感耐人寻味。第二章主要以民俗为视角,探索当地人精神上的“盛举”,如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等,一股乡土气息溢于言表。另外在其他章节里也添加了很多适应且推动情节发展的风俗习惯,比如围绕不让团圆媳妇“出马”为中心,老胡家的“良方”、请了大仙、看洗澡、烧“替身”等等民俗活动。这些片段化的描写方式,错落的分布于整篇小说之中,解构了以跌宕起伏的情节为中心的小说布局,自然而然对于颠覆传统的叙事结构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利于建构“抒情式的小说”,体现一种 “清新的诗趣”。
小说创作模式的转变,一方面有利于作家思想的放逐,打破成规,开辟一片更加广阔的素材天地,形成多元化的叙事时代;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影响读者的文学接受范围,培养高雅的审美体验,为适应异于自身期待视野的外国作品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正是作者如此别样的创作模式,迥然不同于当时的创作氛围,是对“五四”小说探索的延续与发展。假若说是萧红敢于同传统“叫板”,毋宁说是她忠实于自己,书写自我熟悉的情感体验与生活习惯,如此一来才会游刃有余,驾轻就熟。萧红说过,作家不是某一个时代的表征,而是属于整个人类的产物,其写作的立足点是站在人类社会之上,描绘形而下的现象,阐释其存在的形而上的意义。她将触动自己心灵深处的那一抹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或许,这也正是地域性文学作家存在的缘由。萧红对她的故乡——东北,内隐着某种深切的爱恋,一草一木都足以触动她敏感的思绪。
2 建构现代的审美体验
“对风土人情的重视,不再是为了增加小说的真实感,而是承认其具备美感价值。”[2]所谓审美价值是指审美客体的属性对审美主体需要的满足,是对象特定的属性与主体需要发生作用时显示出来的令人获得审美享受的一种价值。换句话说就是文学作品的呈现不仅使读者获得了情感的陶冶,而且在阅读的过程中,供予一片自我精神休憩的净土,进行诗意的栖息。
“五四”之前,作家对出现在文本中的民俗风情并没有投入足够的关注度,认为其只是为了区分自己所描述的地域,不至于出现南北不分的乌龙事件。然而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与对话,我们逐渐意识到了风土人情,其本身也是一首诗意的“歌谣”:能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异域风情的同时,也由于其细腻的描绘,独到的剪裁,饱含情感的书写,使读者观赏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盛宴。
《呼兰河传》以描绘淳朴的民风与极具地方色彩的风俗画面而为读者所喜爱。“呼兰河除了这些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在精神上,也还有不少的盛举,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一方面作者用平常普通的生活片段编织文本:挑着馒头的老大爷走街串巷的叫卖,染缸房里的逸闻趣事,扎彩铺子的零零碎碎,拿着麻花的“小谗嘴”追逐打闹等;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流传至今古老的风俗习惯。作者在介绍这一部分时,只是客观去描述其存在的形式与活动,而并没有添加过多的阐释与界说,将评价的权利留给读者,让读者去深思与权衡。还有小说的主体部分,是以儿童为限知叙事视角对所见所闻的记录,渗进字里行间的是一种诗意的情趣,以及儿童对世界本真的美好感受: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蜒、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
蜻蜒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简洁的词汇,口语化的描绘,轻快的节奏,优美的旋律,作者以儿童视角作为回忆的立足点,笔下的世界也是一个孩童摄入脑海中具体又鲜明的形象,为读者勾画了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天地。花园里弥漫着生气,如同一个儿童的游乐园,以花草为伴,树木为友,在这个小小伊甸园里,我们能感受到的是浓郁的幸福与放飞的自由。种种的美好,让读者在读了作品之后回想起自己所熟知的事物——那段人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不自然地感到愉快。换句话说,就是读者的情感找到了“客观对应物”,也就是那些引发情感的“一组客体、一个情境,一连串事件”,这样“一旦有了归源于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情感便立即被唤起了”。只有受到了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感情和原则的影响,才能够震动各式各样人们的心灵,才会具有情感净化的功能,尔后对于文本的个人喜好偏向,则在于审视对象时的“心境”。所以有人说萧红的小说既像散文又像诗歌,带给我们以美的享受,散发出“洛神”特有的神韵,而这也足以证明《呼兰河传》独特魅力的所在。
不管是社会民俗的呈现,还是自然风情的体察,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既可以知晓真切的生活事实,又可以激发内部潜在的真挚情感的诉求,获得审美体验的价值。
3 推动故事的情节发展
民俗文化,就类同于荣格所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在《呼兰河传》中,那些民俗风情的流传是经过悠久的历史演变而成,最终影响我们的心理性格和思维方式,导致了我们对于同一件事情会无意识地采取同样的看法与作为。
民俗风情是小说的一块幕布,扮演着无声指示的角色,引导着部分情节的发生和发展,在人物心理与情感的刻画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呼兰河传》中,萧红用细腻的笔调,简洁的语言描绘了东北土地淳朴的民间风俗画卷。从第一章民风琐事的描写,读者可以感受到当地淳朴的民风与平宁的氛围,似乎是木然,然而只是习惯成自然的行为。这与下文团圆媳妇与人们形成“看与被看” 的模式,冯歪嘴成家生子成为了茶余饭后的话茬,“西院的杨老太太听了风也来了”,“这事情一发,全院子的人给王大姑娘做论的做论,做传的做传,还有人给她做日记的”具有一定的关系;第二章的民俗描写,如会治病的大神,在施行法事的时候手舞足蹈为患者驱赶病魔;七月十五盂兰会,呼兰河上放河灯;秋收时节,河边的野台子戏也便开始了,出嫁的女儿们,姐妹们便有机会归省碰面等等。由此我们可知当地的民俗盛行,精神生活匮乏,其中必然也包含着落后,非人道主义成分在内。那么,为后文团圆媳妇被我们置于“表演”的地位进行了铺垫,其牺牲也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
民俗风情也隐含作者的情感。很多小说,由于“布局”的创新性,不再是故事的连贯性叙事,以塑造人物的饱满取胜,而是在“对淳朴的民风与古老的陋俗的描写中,体现出来的对这块土地这般乡民的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我们依然也发现在《呼兰河传》作品中,萧红体现出来的不仅有对这块黑土地的“同情心”,也不缺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派生出来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也没有。”总是回避问题的关键之处。“大家正在谈说之间,她的婆婆过来,赶快拉了一张破棉袄给她盖上了,说:‘赤身裸的羞不羞!’(小团圆媳妇怕羞不肯脱下衣裳来,她的婆婆喊着号令给她撕下来。现在她什么也不知道了,她没有感觉了,婆婆反而替她着想了。)”落后的民俗习惯,无情地吞噬着悲惨者,一个活蹦乱跳的姑娘在“集体无意识”的侵害下成为了牺牲品。这让我们不得不想起鲁迅笔锋下那一群麻木且冷漠的“看客”。因此不仅自五四狂飙突进的氛围之中,即使到了萧红生活的年代,已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中国改造国民性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而在萧红内心状态的此种外在,即是故乡中那一群落后的民众。
另外,美与丑充斥着文本,给予读者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情感的对换。美丑对照主张将两种对立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有效地突出两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从而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两个事物相反的本质特征。在《呼兰河传》中,我们熟知她在小说中描绘了一个伊鸠壁鲁式的乐园,令读者不自觉地沉醉于静美的“后花园”中,还有小孩子们烂漫的笑容,天真的话语“间或也有小孩子太不知时务,他说他妈不让他吃,说那是瘟猪肉”。通过孩子们的视角来表现未经污染的纯真的美的世界。然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被置于“前景”的,呈现在大人们眼前的“丑”——无人理会的大泥潭,验证他人即是地狱的看客,集体无意识“逼死”了团圆媳妇,违背人道主义的迷信行为等等,这些 “丑陋”的行为,与“背景”中的花园,拉开了距离,形成了莫大的反差,使得读者不至于被美好的景象所迷醉心灵,也不至于一直浸漫在透露着绝望的“死水”中压抑得透不过气,而是二者调和,美丑相结合,不做全知型的作者,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将一切最真实的情境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对文本做出属己的真切的评价,参与到文本的再创作之中,证实“作者已死”的论断。
4 观照文本的文化情怀
中国的文明源远流长,在这历史的长河之中,知识的雨露滋润着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心灵,积淀成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惰性”。从巫术——宗教——科学,时代不断地向前与进步,更加贴近生命本真的特征不断取代每一个不确定的假说。
对照乡土文学的许多作家及其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作品或多或少会掺杂有对乡土民俗的描绘与捕捉。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发挥了女性独特的情感体验与细腻的观察视角,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淳朴的民风民俗画景,而这民风民俗既有落后、无人道主义的成分,如作品中团圆媳妇在滚烫的热水中三次昏厥,三次浇醒;也有温情脉脉的人性,如趁着看戏时节,姐妹们互相送礼亲近。诚然,用现代唯科学论的视角来观照这些民风民俗时,用现代文明来对比过去的举止,我们不难定义这些是迷信且落后的“遗产”。然而,对待这些广义上的文化延续,我们应当秉持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过去的文明,给予它们以后我们同样也需要的宽容态度,怀揣着人道主义的文化情怀。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二律背反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同时,另一方面,人性的缺失,一种淳朴的民风与人情味将在这一过程逐渐被消磨,最终消失殆尽。或许,这也是作者除了外化的小说情节呈现的悲剧情怀之外,其在这纵深里更是作者难以接受却又处于矛盾的焦点。都市与乡村,通常是二元对立的两方面,现代文明的进程必定会打破乡村的那份宁静与闲适,科学也必定会取代迷信,将格局“整一化”。
[1] 茅盾.《呼兰河传》序,茅盾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348.
[2]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8.
[3] 包天亮.论萧红小说《呼兰河传》中的民俗描写[J].安徽文学:文教研究,2006(11):14-15.
(责任编辑 骆桂峰)
吕海玲,女,广西柳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7.42
A
2095-4859(2016)03-044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