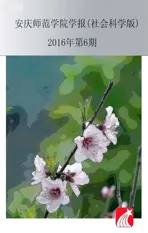从苏荫椿手稿看清季民初皖南下层士绅的社会生活
2016-03-18李永卉
李永卉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芜湖241002)
从苏荫椿手稿看清季民初皖南下层士绅的社会生活
李永卉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安徽芜湖241002)
晚清民初皖南石埭县生员、典商苏荫椿遗留了系列手稿,记载了以苏荫椿为代表的皖南下层士绅,在同治末年到民国中期近六十年的生存状况。晚清时期,皖南的下层士绅弃儒经商与科举仕进并存,但是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两种生存模式均受到冲击。旧有的知识结构为新的谋生提供了帮助,也导致他们在近代化过程中逐渐被社会淘汰。
晚清民初;皖南;下层士绅;苏荫椿手稿
关于近代士绅的研究,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备受关注,成果丰硕,主要论著有:市古宙三《鄉紳と辛亥革命》、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乡居地主の生活空间》、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李世众《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李平亮《卷入“大变局”——清末民初南昌的士绅与地方政治》等。总体来说,现有研究对上层士绅关注较多,对下层士绅的专门研究尚显不足。由于下层士绅的社会地位不高,现存史料不多,我们很难窥知这个群体的生活细节。本文讨论的下层士绅即指以苏荫椿为代表的,在清末废除科举考试前取得功名的贡生、监生、生员等皖南地区的读书人。苏荫椿手稿目前发现的主要有《文稿》《信稿》《典业杂志》《各大宪通电》《东鳞西爪》等五种,均藏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是清末民初留存的比较完整、翔实的商业及社会文书,详细记载了以苏荫椿为代表的皖南下层士绅的日常生活。
苏荫椿,字萱臣,号忏因主人、华胥老人,安徽石埭(今石台)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卒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之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23岁的苏荫椿考上生员,因“贫困不能自存”[1]致吴玉山表姪,五年后,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弃儒从贾,入同族太平苏文卿所办的安庆同春典任职,其后的二十多年,一直负责安庆、湖口、芜湖、宣城等处的具体经营管理工作。本文将通过对苏荫椿早年的乡居生活、后来的经商、交游以及他的精神世界的微观解读,以期再现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皖南下层士绅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变迁对于他们的影响。
一
皖南的太平、石埭两邑苏氏家族据说都是源于四川的眉山苏氏[2]。石埭苏氏为太平苏氏迁出一支。苏氏家族是皖南望族,太平、石埭苏氏在地方上名人辈出,太平苏氏在盐业、典业有所成就,而太平石埭苏氏更致力于家乡的文教公益事业。
苏荫椿的父亲苏吉治(字虞廷)便是一位地方文人,在乡间收徒讲学,苏荫椿的好友汪由中(字性初)即拜其为师,存世的其贡卷载:“年伯苏虞廷夫子,讳吉治。恩贡生,候选教谕,著有救病药石,已梓行世,仍有存心堂全集待梓。”[3]手稿亦曰:“性初,名由中,内乡沙塍人,博学强记,十二岁以背诵五经文宗拔入邑痒。尊公选青先生与先府君虞廷公为莫逆交,命性初从先府君读,予与同窗三年,后由优廪生贡入成均惜未五十而卒。”[1]覆汪性初·附注目前发现有三部著作存世,分别为《虞廷氏稿本三卷》(抄本,安徽省博物馆藏)、《存心堂杂著不分卷》(稿本,安徽师大图书馆藏)[4]、《流离记》。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之前,苏荫椿一直居住于家乡池州府石埭县,读书科考是他的人生目标。光绪十一年(1885),与沈素娥结婚,是年沈氏18岁[1]致沈赞臣内弟。婚后依然苦读,光绪十四年(1888),16岁的苏荫椿独往贵池大演拜邑庠生吴自修为师,一年后因父病危返家。光绪十八年(1892)苏吉治去世,苏荫椿“其时年轻,又受讼累,贫困不能自存”[1]致吴玉山表姪。光绪二十一年(1895)“取入县学”[5]寄慕东,但依然贫困如旧,“嚼字不能疗饥,境遇益形窘迫,亲族中无有肯为援手者,不料山穷水尽之时,偏有绝处逢生之妙。”[1]致吴玉山表姪
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编修家谱苏荫椿结识了宁国府太平县岭下同宗苏文卿,手稿记载:“先是,太平同宗苏文卿,家赀百万,长江一带,设典肆九所。椿以修宗谱得与往还,颇蒙青睐,谆谆劝我弃儒而贾。旋于光绪二十六年招往安庆,就同春典银房一席。”[1]致吴玉山表姪这一机缘,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
苏荫椿出身于下层士人家庭,从小立志读书取得功名,只因家庭变故,不得不放弃科考去经商。苏荫椿的母亲、妻、子常年患病,子女年幼,家庭负担沉重,弃儒从贾实为生活所迫:“椿自壬辰失怙以来,遭遇坎坷,不能自存,因勉就敝同族质库中会计一席。”[1]致曹竹溪孝廉前辈32岁时候回忆往事,亦是无奈居多:“椿书生命蹇,遭际多艰,不得已改弦易辙,藉谋生计。”[1]致陈镇寰仁丈在写给父亲的好友曹焕先生的信中亦曰:“忆自束发受书,闻先君子盛称前辈品端学粹,为吾郡一时硕彦,私心辄向往久之。”[1]致曹竹溪孝廉前辈
其实,苏荫椿弃儒从贾,除了家庭原因外,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晚清时期皖南商人纳捐之风盛行[6],这对靠科考取得功名的如苏荫椿这样的底层读书人有一定的冲击。有学者指出:“近代商人之锲入士绅阶层,多少分化和改变了这个传统权势阶层的内部构成,为之融入了某些近代因素,使长期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阶级结构终于发生了某种裂变。”[7]同时,士绅的社会流动开始多元化,经商便是之一。早在鸦片战争后,就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进行了反思,郑观应曰:“嫉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何则?”[8]薛福成亦认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率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则工由必兼士之事。”[9]卷63同时,皖南重商,明清以来徽州商帮名扬海内,太平苏氏家族也是清中后期经商成功者,因此,苏荫椿在穷困潦倒之时,随即加入了商人行列,虽然对科举念念不忘,亦很快融入了商业生活。
二
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苏荫椿正式赴安庆任同春典钱房始,其后大部分时间一直在各地的苏氏典当行任职,直到民国15年(1926)辞去南京通济公典(非苏氏家族所办)的银房职务,从事典当业时间总计有22年。这一时期,恰好是国家发生剧变的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对典当业的冲击很大,典当业也由此转衰,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苏荫椿在苏氏典当行一直是中层管理者的角色,从事近廿余年的典业经营,其中有16年任钱房之职,约7年时间任经理。在典当业经营管理方面,苏荫椿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撰有《典业杂志》一书,详细记载了其所在各当铺的经营状况。只是其进入典当行业时,典业已经过了繁荣时期,逐渐衰败。
苏荫椿入职安庆同春典时,典业经营已经困难重重。义和团事件虽然未波及东南十三省,但是受局势影响,安徽亦不太平,“时事日非,各处土匪,蠢蠢欲动,前闻宁国县境,盐枭肆劫,与浙匪联络一气,藉谋不轨,大宪檄剿,渐获安谧,和议迭受外夷挟制,旧岁闹教之处,停考五年,朝内忠义,半被惨戮,尤亘古未有之奇祸也。”[1]覆汪性初1901年入夏后安徽一直雨多晴少,导致“江水陡涨数丈,为近年所未见”,“东南隅汪洋一片”[10],人们纷纷逃往省城避难,“今夏淫雨为灾,沿江圩圮,变成泽国,逃荒到省者,络绎不绝,刻又大疫,死亡相继,诚巨劫也。”[1]致汪性初清末新政又引起通货膨胀,对工商界影响巨大,典当业也损失惨重。“光绪二十八年,铜元出世(每枚十文),制铸价值,日渐低落,典业因之渐次亏本,资力弱者,亦多收歇,或整个盘典出售,典当高涨之风,随之衰减。”[11]内忧外患下同春典不得不暂停营业。
很快,苏荫椿便于“(光绪)二十九年,调往九江湖口县同兴典内,职务仍旧”[1]致吴玉山表姪,但湖口的情况也不乐观,“敝处生意,已成强弩之末,兼乏持筹之方,每天当有八九百号,出本六七百千,较之旧年,稍有佳境。而居停因钱价过疲,嘱生意收紧,不愿长生库中。丰亨有象,争奈清闲市上,典质偏多,欲从权而不能,欲守经而不可。”[1]覆汪冕卿他已经觉察到典业开始走下坡路了,“至于典事,生意虽仍如旧,操算总是不工,岁有三百六十天,利仅一万三千数。以视昔年,计拙端居我辈,方诸同业,先声已让他人。”[1]致王芝卿吴味畊杜遐斎杜瓒如四同政从与友人的通信中随处可以感知他的悲观情绪,很是怀念以前的朋友:“自抵湖典,悉是新交,益怀旧友。暇惟浏览古书,藉可怡神。兼消永昼。”[1]覆吴味畊他在湖口同兴典工作了7年,1909年同兴典歇业后调入宣城同吉典。
苏荫椿在安庆、湖口、宣城的经历,积累了丰富的典当业经营经验。虽然1915年,苏文卿关闭了沿江苏氏九典,北上投资天津大生银行[1]致吴玉山表姪,丙寅十二月十六日,并没有继续聘请苏荫椿,但是1921年,友人在南京成立南京通济公典时,力邀其加入,“民国十年夏,适南京友人仿公司章程,招股集赀,组织通济公典,闻椿微名,特请任钱房一席。又复闻云出岫,寄趾白门,荏苒五载。综计生平,服务典业二十于年,东奔西突,依然两袖清风,毫无树立。”[1]致吴玉山表姪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动荡的社会环境对商业尤其不利。“芜湖当长江要冲,非乱世所宜,尊席又烦剧,果何所取耶?池郡自省垣被陷以来,陆续过兵,居民散而之四乡者,不知其数,而乡僻之处,土匪横掠,人心惶惶,寝不安席。”[1]致谷宝泉·附覆函苏氏的宣城同吉典、芜湖同福典都受到冲击。危机时刻,苏荫椿被委以重任,任宣城孙家埠同吉典经理,同时芜湖同福典经理汪冕卿因无法应付混乱的局面,不辞而别,“又兼任芜湖同福典经理。”[1]致吴玉山表姪他在与谷宝泉的信中说:“九月大局一变,人心惶惶,居停以孙典系我旧部,迭函敦促,仍旧管理,命与来迎,星夜前往。弟念感情,扶病就道,到典以来,事事棘手,内外交困,乱世外游,自悔孟浪,正思作乞退之谋,而居停又有调赴芜典督理之命。以该典于上月受兵士之扰,执事汪冕卿,不辞而行,致人心浮动,纷纷归去。请我来此,收拾残局。弟以病辞,迄不获允,奈何奈何。”[1]致谷宝泉
苏荫椿抱病至芜后,对同福典的境况很不乐观,内外打理都需要费用,但是“监翁”(当指苏文卿——引者)并没有系统打算,亦不想花费太多,因此让他很是为难,“往广德民军,曾否由孙埠经过?我典受扰否?接函后,甚焦灼也。监翁毫无主见,处处惜费,冕卿因其不内外安顿,知事不可为,故逸去。监翁有挽留弟接办消息,而西舫、永芝、锡年等,亦表同情。第芜典既决裂如此,苟能为力,冕卿不去,以人不能做之事,而冒昧以从,智者不为。”[1]致李逸洲典泐他一面抱病处理同福典事务,一面关心同吉典安危。为安抚人心,防止有人擅自离职,让同吉典的李逸洲效仿同福典的做法,给同事加薪,“好是监翁不久到孙,一切之事,由东宅布置,胜弟多多。再调查皖芜两典,自十月起,同事另有津贴,内缺每人龙洋三十元,柜友各二十元,中缺各十元,学生大二三各八元,四五六各六元,以下各四元,厨司待年底,再为酌给。又另给同事川资,以备不虞。(每人本洋二十元,龙洋十元)一概入册,并不收回。弟思同事受惊,彼此一样,皖芜既有成例,孙典尽可照行。乞阁下宣布此意,按人补发,以免向隅。典内各事,全仗阁下暨诸君极力维持,众惊易举,其今日之谓也。即请大安不一。”[1]致李逸洲
虽然苏荫椿力挽狂澜,同福典暂时稳定下来,但是直到1912年境况依然不佳,“孙黎交斗,青、太、石三知事均逃,近无官长,而斗大山城,尚称安谧,较之外埠,可算福地。南京兵变,子受损失否,为问。芜典事,真不易办,仆权住,徐图乞退,再不允,则效汶上之行矣。”[1]致族华存虽然苦苦支撑,到底乱世多艰,不久苏文卿便关闭了沿江九典,损失惨重,“无如光复以来,居停九典,损失不少于六十万金,以致同时歇业。椿于民国四年,善后办毕,亦回里家居矣。”[1]致吴玉山表姪
三
苏荫椿的社会活动并不广泛,因此友人也局限于早年一起读书的伙伴和经商后结交的朋友,主要有三类人:一是亲戚;二是早年读书求学时结识的朋友,大多数为池州府的读书人;三是进入商界后,结识的商场上的朋友,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皖南地区人。
苏荫椿的友人中取得科举功名者较多,这些人在清末民国动荡转型时期,从事的职业已经有了分化:一、科举出仕成功者只有苏慕东、杨积堂。苏慕东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正科中式举人,民国初曾两任陆军部军需司司长,两任财政部次长,一任审计署署长。”[12]卷49苏慕东的成功与太平苏氏家族雄厚的财力支撑不无关系,例如光绪三十年(1904),他参加在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的“万国赛会”,投入10万巨资采购景德镇瓷器和皖南茶叶参会,被赠予头等宝星一枚[13]。二、从事商业活动的有谷宝泉、杜实菴、黄皖辰等。其中杜实菴、黄皖辰都在苏典任过经理,与苏荫椿一样属于当行中的骨干人员。谷宝泉通晓医术,平时在乡间行医,也在苏典任过职。凭借个人能力,也谋得了生计。三、继续参加科考者有杨藩卿、陈焕文、徐存斋、吴复初、曹竹溪等人。曹竹溪为地方名士,科考停废后,他依然是皖南士人的中心,对其生活影响不大。其他人则不同,虽然“科举既议停减,旧日举贡生员年在三十岁以下者皆可令入学堂之简易科”[14],但是从苏荫椿和他的友人们通信中,并未看到有人继续去学堂读书,可以认为他们的年龄或许都如苏荫椿一样,已过了而立之年。这些人当中只有徐存斋、谢来宾在新式学堂谋到了教职。
苏荫椿的信札中经常流露出弃儒从贾的苦闷,非常向往传统士人的读书科考人生。由于生存的压力,他的社交范围与以往的乡村生员有所不同,已经不局限于参加科举考试的同仁们,活动范围亦突破其生活的石埭县,远及省会安庆、邻省江西的湖口以及南京等地。应该说随着时代的变迁及友人范围的扩大,他对社会、人生的认知亦在不断改变。1905年,当清廷宣布:“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停止”[15],其他士子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他已经在苏典任职5年,成功找到了谋生之路。
四
王先明认为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其中“19世纪60年代后到20世纪初年科举制度废弃前,是传统封闭性社会流动向近代开放性社会流动的过渡,出现了‘绅一商’流动局面”,“科举制度革除后,促成了绅士阶层的结构性社会流动。”[16]我们从苏荫椿为代表的下层士绅的生活来看,尽管“‘绅—商’流动尚属于非强制性的自由流动,相对于百数十万之众的绅士阶层,这种自由流动的规模十分有限”[16],但是科举考试废除前皖南下层士绅弃儒从贾的现象并不是个案,即皖南部分下层士绅向商业领域拓展与通过科举入仕,这两种人生轨迹是比较常见的。究其原因,与该地区的社会风气不无关系。皖南的徽州商人明清以来名闻遐迩,宁国府的经商风气亦有深厚传统[17],何况苏氏家族本身就是以经商闻名的大家族,受这种传统的影响,苏荫椿因生活艰难涉足商业,对他个人来说思想上的转变或许要相对容易。但是,由于社会地位不高、经济能力有限,他们一般依附于同乡或朋友,很少有人独立经营。这种职业的脆弱性显而易见,一旦依附者经营不佳时,便面临失业危险。如苏文卿的典当生意,从光绪末年便开始在走下坡路,最终关闭歇业,苏荫椿也随之失业。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于早期知识分子和已经分化了的士绅们,近代化过程改变了他们的知识结构,但还不能立时塑制他们的文化心理。”[18]而以苏荫椿为代表的皖南下层士绅,近代化既没有改变他们的知识结构,也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心理,他们只能过着朝不保夕的依附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度过余生。
[1]苏荫椿.文稿[M].民国稿本.
[2]苏雪林.苏雪林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3.
[3]汪由中,等.江南安徽贡卷[G].清末排印本.
[4]李灵年,杨忠主.清人别集总目(上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678.
[5]苏荫椿.信稿[M].民国稿本.
[6]梁仁志.明清徽州的绅商——兼谈明清绅商与近代绅商之不同[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
[7]章开沅,马敏,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74.
[8]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591.
[9]陈忠倚.清经世文三编[M].清光绪石印本.
[10]李文海,林敦奎,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167.
[11]刘炳卿.晚清安徽的典当业[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12]苏鹤孙.苏氏族谱[G].未刊本,2006.
[13]时事要闻·会场华茶畅销[N].大公报,1904-11-03.
[14]管学大臣等奏请试办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J].东方杂志,1904(1).
[15]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8:5392.
[16]王先明.中国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J].历史研究,1993(2).
[17]董家魁.明清代宁国商人新探[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
[18]王先明.近代士绅阶层的分化与基层政权的蜕化[J].浙江社会科学,1998(4).
责任编校:徐希军
K252
A
1003-4730(2016)06-0032-04
时间:2017-1-20 15:3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70120.1533.007.html
2016-08-14
李永卉,女,安徽六安人,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6.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