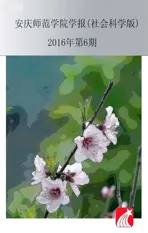善因善创:方东树诗歌“通变”论
2016-03-18郭青林
郭青林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善因善创:方东树诗歌“通变”论
郭青林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对传统诗学中的“通变”问题,方东树提出“善因善创”,要求诗家既要善于继承前人创作精神,又要以此为基础加以创新,并提出具体的继承、创新的方法或角度。这一看法继承了诗学史上通变观念,旨在实现诗文创作的个性化。它与方东树的诗体正变论一起构成《昭昧詹言》诗学批评的基本思路,体现了桐城派包容并蓄,融通开放的文学精神。
桐城派;方东树;通变;《昭昧詹言》
中国传统诗学中的“通变”问题,实质是如何处理好诗文创作中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诗文家在创作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命题。如何理解并用之指导诗文创作往往关系到个体的诗文创作水平,甚至关系到一个时代诗文发展的方向。这一点可从明代诗坛流派的更替中得到证明。作为桐城诗学的重要人物,方东树对此是有着清晰的认识的。他在《昭昧詹言》中对历代诗家特别是对明清两代诗坛主流人物均有批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基于“通变”问题的。他对传统诗文创作历史进行充分考察,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的“善因善创”(《答叶溥求论古文书》[1]卷六),是其对“通变”问题理解的基本态度。本文拟就此略作讨论,以揭示方东树“通变”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其实质。
一
一般以为,“通变”一词,源于《周易》:“生生之谓易,……通变之谓事。”[2]234“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2]224“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2]244“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2]246“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2]257“通”即通晓、通行,虽不可直释为继承,但因为“变化”总是在旧的基础上进行,须通晓其旧,才能知其新变,故也不能排除继承之意,“变”即“变化”,有“变化”即有革新,故《周易》之“通变”意在不断变化革新,却为后世“通变”理论强调继承与创新提供了哲学基础。汉人对“通变”概念的运用依旧基于《周易》之义,如崔骃在《达旨》中云:“道无常稽,与时张弛,失仁为非,得义为是。君子通变,各审其履。”[3]将“通变”直接地、系统地用于文学批评的是刘勰,《文心雕龙》专列《通变》一章,论“通变”之旨。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
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4]519
刘勰明确了“通变之术”对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指出“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通变”就是“因革”,即继承与创新之义。为此,他要求“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4]519,即继承前人之为文之方,又依据自情己才情加以创新。刘勰将《周易》的“通变”观,移入到文学批评中来,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学创作中的因革问题,纠正了当时复古派与新变派理论上的偏颇,在文学理论史上影响深远。
隋代惩前朝覆灭之训,将亡国之因归于六朝统治者娱情文艺,要求革前朝之华靡之弊,转承坟典(李谔《上隋高帝革文华书》[5]),有“通变”之意,但实为复古。唐代与隋相反,虽为复古,实为“通变”。如陈子昂《修竹篇》序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6]从表面上看他要恢复的是“汉魏风骨”、“风雅”之道,但实际上是企图通过继承“汉魏风骨”、“风雅”之道,来变革齐梁“彩丽竞繁”之风。持此倾向的还有李白、殷璠、杜甫等,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云:“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7]他选诗兼取新与古、文与质、风与骚而不偏失,与刘勰之“资于故实”,“酌于新声”相近,正是其“通变”观念之体现。此外,皎然在《诗式》提出“复变”之说,其曰:“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复变与“通变”义近,但侧重于“变”,“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他批评“陈子昂复多而变少,沈、宋复少而变多”,[8]故也有折中之倾向。宋人论诗“主变,不主正”,对“通变”的理解侧重于“变”,如黄山谷注重取前人之成规,参悟活法,但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却旨在“变古”,如云“通变”,但实为“新变”。
明人论诗重视“拟议变化”,即通过模拟古人来成就自己的“变化”,尽管在创作上“拟议”多,而“变化”不足,有剽窃之讥,但其诗论却大多符合“通变”之精神。如何景明云学古要“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9]),主张既要领会古人之“神情”,又要有“临景构结”之创造,即为“通变”之意。许学夷指出“论诗者以汉魏为至,而以李杜为未极,犹论文者以秦汉为至,而以四子者为末极,皆慕好古之名而不识通变之道者也。”[10]190李、杜五言继承汉魏而加以变之,故能另立一极,而不是“未极”,此处“通变之道”即继承创新之道。“广其资,参其变”他认为“盖诗之门户前人既已尽开,后人但七分宗古、三分自创,便可成家。”[10]416故其“通变”之说,更多倾向于复古。清代是古典诗学的“通变”理论总结阶段,较有代表性著作是叶燮的《原诗》。
古典诗学的“通变”批评,刘勰时已完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至清代叶燮始得深化和总结。“通变”批评始终伴随着诗学上“复古”和“新变”两种趋向的对立,并企图对诗歌创作和诗歌历史的演变规律作出客观的回答。“通变”批评实质对诗歌史演进过程中“正”与“变”交替运动过程的动态描述,它以批评者的“正变”观念为基础,并受其制约。方东树的“通变”观念,继承了前人的“通变”学说,尤其是韩愈古文理论中的“通变”思想的影响。在唐代古文运动中,韩愈提出为文宜师古,但要“师其意不师其辞”及“能自树立,不因循”(韩愈《答刘正夫书》[11]),“惟陈言之务去”等观点,均被方东树所吸收,并用之于诗学批评。他虽批评刘勰“身未自造”,只是“知解宗徒”,[12]31但其“善因善创”之“通变”观念却与之更为接近。
二
方东树“以为文章之道必师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答叶溥求论古文书》[1]卷六)“师古”即“通古”,继承古人之意,“不可袭”即要求“变”,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这是方东树“通变”观念的完整表述。他曾以水为喻,对其“通变”观念作进一步阐释。《答叶溥求论古文书》云:
(为文)以师乎古人若此者,何也?以为不如是则不足以为文也。此固二道也。尝观于江河之水矣,谓今之水非昔之水耶?则今之水异于昔之水安在?谓今之水犹昔之水耶?则昔之水已前逝,今之水方续流也。……古之水今之水是二非一,人皆知之。古水今水是一非二,则慧者难辨矣。……夫有孟、韩、庄、骚,而复有迁、固、向、雄……此古今之水相续流者也。顺而同之也。而由欧、苏、曾、王、逆推之,以至孟、韩道术不同,而卒其所以为文之方而弗同焉者。此今水仍古水之说也,逆而同之也。古今之水不同,同者洷性,古今之文不同,同者气脉也。[1]卷六
就古水、今水而论,要义有二,一是异同关系,古水、今水有异,异在于它们存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古水、今水有同,同在于它们有着共同的洷性。正因为有异有同,故古今之水可以先后相续成流。二是源流关系,今水是古水之流,古水是今水之源,今水必源自古水,没有古水即没有今水,正因为古水与今水相续成流,才有江河之流的存在。古文与今文有似于此,异在历史先后,同在“气脉”相通,古文今文如水之先后相续,绵绵不绝,古文发展的历史由此形成。东树此论从古文发展的历史着眼,意在强调今人作文必师古人,从古人那有所继承。他认为文章如人的面貌,各个不同,但从为文之“深妙之心”来看,即使相隔千载,也如同出自一手。因此继承古人,不是继承其面目,而是继承其“深妙之心”,否则所作之文章只是“优人之肖人歌泣悲愉,”(《姚石甫文集序》[1]卷三)只能是形似而本异,并非为文之正道。为此,他要求深入研究古人作品,参悟并继承其“深妙之心”。但是,这种“深妙之心”具体指的是什么,弄清这个才是问题的所在。方东树云:
读古人诗文,当须赏其笔势健拔雄快处,文法高古浑迈处,词气抑扬顿挫处,转换用力处,精神非常处,清真动人处,运掉简省、笔力崭绝处,章法深妙、不可测识处。又须赏其兴象逼真处……而工拙高下,又存乎其文法之妙。[12]23
读古人诗,须观其气韵。气者,气味也;韵者,态度风致也。……气韵分雅俗,意象分大小高下,笔势分强弱,而古人妙处,十得六七矣。[12]29
他从用笔、文法、词气、转换、精神、风格、章法、兴象、气韵、意象等角度,明确读古人诗文应该注意的要点。学者当于这些地方用力,方有所得。其“深妙之心”正在于此,具体言之,在古人作品中,作者对用笔、文法、词气、转换、精神、风格、章法、兴象、气韵、意象等进行处理时的艺术技巧、艺术追求,就是古人的“深妙之心”。上列要点中,最重要的是“兴象”、“文法”和“用意”,他以三个“高妙”概括之,“用意高妙;兴象高妙;文法高妙;而非深解古人则不得。”[12]30“兴象”是“情兴”与“意象”的统一,其要求是“逼真”;“文法”是字法、句法和章法的统一,其要求是“精严密邃”;“用意”指构思,要“深微含蓄”。对于“用意”,他还特地指出“读古人诗,其用意须会之于意言之表,方可云善继其志。”[12]139因为“意在言外”,故当于“会之于言之表”,同样,对于古人“文法”、“兴象”等“妙”处也要求之有道。
若夫古人所处之时,所值之事,及作诗之岁月,必合前后考之而始可见。如阮公、陶公、谢公,苟不知其世,不考其次,则于其语句之妙,反若曼羡无谓;何由得其义,知其味,会其精神之妙乎?[12]6
求通其辞,求通其意也。求通其意,必论世以知其怀抱。然后再研其语句之工拙得失所在,及其所以然,以别高下,决从违。[12]7他认为,要想领会并继承古人之“妙”必须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对古人所处时代,所历之事及作诗年月均要考证,然后才能准确理解其用辞达意之妙。古人作品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或是特定的生活情境下创作的,他的人生际遇、知识修养以及作诗时的心理活动、情感状态等对其诗歌创作都会产生影响,有的甚至是其诗歌所表现的对象,因此,采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研究古人作品,对继承古人创作之精神,当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对如何继承古人作品之“妙”,他以杜甫、韩愈为例,作进一步说明,他详细地列出学习两人诗作时应该取法的诸多要点,主要涉及创意、造言、选字、章法、起法、转接、气脉、笔力、助语、豫吞、离合、伸缩、事外曲致、顿挫、交代、参差等[12]10,并对每一要点都有指点,此举虽有重复琐碎之嫌,却把继承古人的东西具体化了,学诗者当各随才情以研寻之。
方东树以为对古人之妙处是要继承的,但也要识其可能造成的流弊。如:
古人之妙,有著议论者,则石破天惊;有不著议论,尽得风流者。在此二派皆有流病,非真有得者,不知其故。[12]63
学古人诗,须知其有短处。如子美有近质处,东坡有汗漫处,山谷有太尖巧处。[12]487“著议论者”,虽有“石破天惊”之妙,但不加控制,一味议论,不见兴象,诗歌则尽是理语,有学究陈腐之习。“不著议论”,虽能“尽得风流”,但若只是山水清音,则有空疏之病,这两种作风都不可取。在方东树看来,即便像杜甫、苏轼、黄庭坚这些诗歌史上的大家,其诗歌也有其不足,杜甫诗有“近质”之短,苏轼诗有“汗漫”之弊,黄庭坚诗则过于尖巧,这些,学者当先细辨之,而后才可取法。总言之,对古人诗既要取其长,又要避其短,这就是其所谓的“善因”。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方东树对“善因”的看法,是以“学古”为前提的,这种“学古”的主张,不同于“复古派”之“复古”,复古派的“复古”是“归古”,即诗歌创作以古人为圭臬,方东树的“学古”,只是“继古”,但并不是使诗歌创作回归古人,其旨在继承古人创作之精神,以实现新变,其“善因”是与“善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三
“善创”就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再加以变化,就是善于变化创新。方东树以为:“大约天下义理及古今载籍文字,惟变所适,无所不备,但用各有当耳。不能观其会通,而偏提一端,即为病痛。”[12]40可见,他既重视对前人的继承,又重视富有个性的创造,只继承不加以变化,或者只变化,而没有继承,都是“病痛”。正如前文所引,文章仅做到“议论既工,比兴既得格律,音响既肖”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得乎古人之精神”、“周知其变态”。“得乎古人之精神”、“周知其变态”固然难,但“创意造语”等“无一字不己出”更难。只有在继承古人的同时,又能够加以创造,才能“若与古人偕没”(《答叶溥求论古文书》[1]卷六)。方东树用“力避”、“力覆”、“力损”诸词竭力描述创作时求新求变时努力之心态。他曾归纳了学作诗时在创意、造言、选字、用典、文法、章法等方面对创新的要求:
凡学诗之法:一曰创意艰苦,避凡俗浅近习熟迂腐常谈,凡人意中所有。二曰造言,其忌避亦同创意,及常人笔下皆同者,必别造一番言语,却又非以艰深文浅陋,大约皆刻意求与古人远。三曰选字,必避旧熟,亦不可避。以谢、鲍为法,用字必典。用典又避熟典,须换生。又虚字不可随手轻用,须老而古法。四曰:隶事避陈言,须如韩公翻新用。五曰文法,以断为贵。逆摄突起,峥嵘飞动倒挽,不许一笔平顺挨接。入不言,出不辞,离合虚实,参差伸缩。六曰:章法,章法有见于起处,有见于中间,有见于末收。或以二句顿上起下,或以二句横截。……迨于杜、韩,乃以《史》、《汉》为之,几于六经同工,欧、苏、黄、王,章法尤显。此所谓复古也。[12]10
这里的避熟、避俗、避陈言、不许平顺挨接等无一不是要求新变,一言以蔽之,凡是常人所有,己必去之,如若不能,即堕凡俗。此处所列,几乎涉及诗歌创作的各个要素,从内容到形式,从主旨到风格均强调“变化”,可见方东树对创新的重视。“此所谓复古”并非是肖似古人,而是指今人诗歌创作合乎古人的为文的“气脉”,即那种穷尽变化而又不失其正的创作精神,即前云“古人深妙之心”。他以为“学诗之正轨”在于“在讲求文、理、义”,故诗歌的创新,概言之,也就是“文、理、义”上的创新:
文者辞也;其法万变,而大要在必去陈言。理者所陈事理、物理、义理也;见理未周,不赅不备,体物未亮,状之不工,道思不深,性识不超,则终于粗浅凡近而已。义者法也;古人不可及,只是文法高妙,无定而有定,不可执着,不可告语,妙运随心,随手多变,有法则体成,无法则伧荒。率尔操觚,纵有佳意佳语,而安置布施不得其所,退之所以讥六朝人为乱杂无章也。[12]8
“文”就是“辞”,创新在于“去陈言”。“理”包括“事理”、“物理”、“义理”,见“理”要周,状“物”要工,“道思”要深,“性识”要超远,能做到“周”、“工”、“深”、“超远”就能“摆脱凡近”,就是创新。“义”就是“法”,无定而有定,随手多变,只要不执泥死法,就是创新。值得注意的是,方东树对“义”的解释与方苞“义法”说有别,“义法”的“义”是指“言有物”,内涵包括方东树的“理”,“法”指“言有序”,即法度,方东树直接将“义”解释为“法”,盖是基于指导诗歌创作的需要。
江西诗派黄庭坚论诗有“夺胎换骨”和“点石成金”之说,(按:惠洪《冷斋夜话》卷一:黄庭坚语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人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见《冷斋夜话》,四库全书本。)“夺胎换骨”是指袭其意但不袭其辞,“点石成金”,则袭其辞,但不袭其意,一侧重要求在语言上创新,一侧重要求在立意上创新,方东树则语言、立意上均要求创新,显然比黄庭坚要求更为严格。他以为,诗文创新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出于自然,如:
只是一熟字不用,以避陈言,然却不是求僻,乃是博观而选用之,非可饾饤外铄也。至于兴寄用意尤忌熟,亦非外铄客气假象所能办。若中无所有,向他人借口,只开口便被者所笑。二者既得,又须实下深苦功夫,精思审辨古人行文用笔章法音响之变化同异,而真知之。须使后世读其言,服其工妙,而又考其人,论其世,皆本其平生性情行事而载之,乃能不朽。[12]17
“创意造言”,要避陈忌熟,但并不是矫揉造作,标新立异。“意”与“言”必须是身之所有,本自“平生性情行事”,也就是要有自己的个性,而要做到这点,必须深究古人作品,真正掌握其为文之精神。可见,方东树所谓的“善创”是建立在对古人创作精神的继承之上的,创新只是诗歌的“言”与“意”,而其实质并不脱离古人创作之旨。
四
方东树的“通变”思想是和其诗体“正变”论联系在一起的。他提出的“善因善创”前提就是“知正知奇”。诗歌的“奇”处就是创新之处,就是“变”。“知正知奇”实质就是“知正知变”。方东树既以为“师古”为“文章之道”,并以“通变”之策实现“师古”之目标。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古人作品,因为只有正确解读古人作品,才能“通”而“变”之,创作出具有自家精神面目的作品来。为此,方东树提出要“知正知奇”,即既要清楚古人作品之“正”,又要知其之“变”。
对于“正”,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二十一,附论诸家诗话中引戴叔伦语指出:
古人诗,譬行长安大道,不由狭邪小径,以正为趋,则通于四海,略无阻滞……夫大道乃盛唐诸公之所共由者,予但由乎中正,自能成家。[12]480
方东树以为学古人诗一要“以正为趋”,二如严羽所说,要从“最上乘”“第一义”[12]493入手,取其正宗、正体,汉、魏、盛唐之诗是诗歌之正宗体式,故应作为取法之对象。故所谓“知正”当指诗歌之正体而言。大历以还及晚唐之诗“皆非正也”,“非正”即是“变”、于诗就是“变体”,对于“变”,他引顾亭林语云: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今取古人之陈言,而一一摹仿之,可乎?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之,则失其所以为我。[12]481诗文沿袭一久,便渐趋于衰,其“变”是因为不得不变。盛唐诗一变为中唐,再变为晚唐,原因在于“沿袭”而不能新变,或者能新变却“失诗之旨”,违背诗歌之正宗属性,使得诗歌之原有的体性被改变,呈现出另一种面目。然而“变”并不是总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变”以使诗盛,也可以使诗“衰”,所谓“盛者得衰而变之,功在创始。衰者得盛而沿之,弊在趋下。”[12]483故方东树称“变”为“奇”,侧重强调“变”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他以为“夫文章小技,然必有入理之功,经世之用,开拓其心胸,遗弃乎浅俗,出入乎经子,游观于事物,深究乎古今文家之变,而后以其雄直之气,瑰杰之辞,以求中乎法律,逼肖乎古人,而不袭其貌。”(《答友人书》[1]卷六)所谓的“知奇”也就是“深究乎文家之变”,即要求学诗者善于辨别古人诗歌的创新之处。
方东树对“知正知奇”的强调,表明其具有明确的诗体正变观念。它与“通变”论一起,构成《昭昧詹言》诗学批评的基本思路。在《昭昧詹言》中,方东树是本着先明“体制”,后晓“通变”这一方式展开诗学批评的。如对七言古诗的批评,方东树先以数则概括其体制特点,然后“依体定人”,选择诗歌典范,接着以其“通变”观为指导,论其因革。在这一过程中,又以阐释诗歌因革关系为主,着重发掘诗歌典范身上的创新精神,体现了方东树以师古实现新变的心理诉求。
总之,方东树是以辩证的眼光来看“通变”的,在他看来,“善创”以“善因”为基础,如不能继承前人创作之精神,创新也就无从谈起。“善因”的方向或目的是“善创”,如不能实现创新,那么“善因”只能流于剽袭,只有“因”“创”并举,诗歌才能自成一家,这是方东树“通变”思想实质所在。方东树的“通变”观继承了姚鼐“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14]的诗学观点,体现了桐城派包容并蓄、融通开放的文学精神。
[1]方东树.考槃集文录[M].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2]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711.
[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544-1545.
[6]陈子昂.陈子昂集[M].徐鹏,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62:15.
[7]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08.
[8]李壮鹰.诗式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30.
[9]何景明.何大复集[M].李淑毅,点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575.
[10]叶燮.原诗[M]//郭绍虞.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65.
[11]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07.
[12]方东树.昭昧詹言[M].汪绍楹,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3]叶燮.原诗[M]//郭绍虞.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65.
[14]姚鼐.惜抱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85.
责任编校:汪长林
I207.22
A
:1003-4730(2016)06-0001-05
时间:2017-1-20 15:3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70120.1533.001.html
2016-10-01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方东树诗歌史论研究”(SK2015384);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文学史学视域下的《昭昧詹言》研究”(AQSK2014B013)。
郭青林,男,安徽庐江人,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