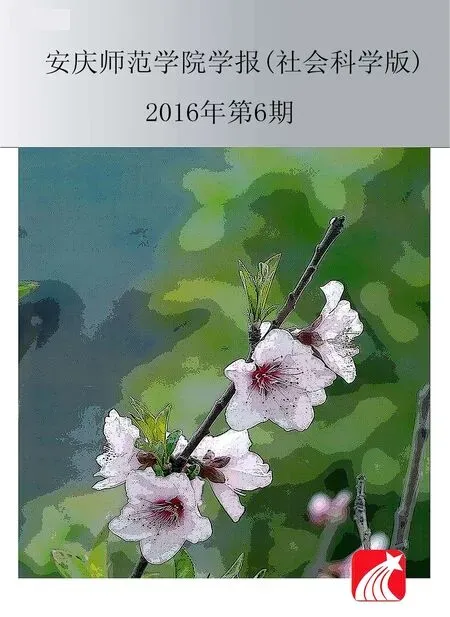爱国、爱真理、爱人道:陈独秀“三爱”笔名考辨
2016-03-18陈长松
陈长松
(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院,江苏淮阴223300)
爱国、爱真理、爱人道:陈独秀“三爱”笔名考辨
陈长松
(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院,江苏淮阴223300)
“三爱”是陈独秀主办《安徽俗话报》时期使用的笔名,现有研究倾向于认为“三爱”是指“爱科学”、“爱国家”与“爱自由”,而根据对《国民日日报》刊载的《慨论德人自戕事》与《自杀篇》两篇论说以及陈独秀这一时期思想言行及笔名变化的考察,可以认为“三爱”实指“爱国”“爱真理”与“爱人道”。厘清“三爱”的确切含义,有助于研究陈独秀早期的思想观念。
陈独秀;笔名;《安徽俗话报》
作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陈独秀一生都与报刊活动密切相关。在其报刊活动中,他曾使用过近38个笔名[1]12,这些笔名反映了陈独秀不同时期的心态与主张。作为诸多笔名中的一个,“三爱”是陈独秀主办《安徽俗话报》(以下简称《俗话报》)时期使用的笔名,反映了陈独秀当时的思想主张。然而,关于“三爱”笔名的确切含义,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这也势必影响到对陈独秀早期思想主张的深入探讨。讨论“三爱”笔名的来源及确切含义,不仅有助于澄清客观史实,也有助于进一步探究陈独秀早年的思想主张。
一、“三爱”的三种释义
当前学界关于陈独秀“三爱”笔名含义的代表性观点有三种:一是沈寂认为,“用‘三爱’署名,是在民族危机的关头,接受西方国家观后,所表达的爱国主义激情,寓爱国家、爱科学、爱自由民主之意”[2]128;二是任建树认为,“综合陈独秀《俗话报》期间的所发文章的内容,分析他所提倡和反对的,‘三爱’的含义大约是爱祖国、爱科学、爱自由”[1]9;三是如唐宝林认为,“从陈独秀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来看,‘三爱’似乎指‘爱国家、爱人民、爱家庭’”[3]17。
上述代表性观点中,沈寂与任建树对“三爱”含义的解释基本一致,差别只在于前者是由当时的国家情势以及陈独秀个人思想主张的变化所做出的推论,后者则是根据陈独秀以“三爱”署名刊于《俗话报》的文章内容所做出的论断。值得注意的是,唐宝林虽然也采用了任建树由报刊内容推论“三爱”含义的相同方法,但其结论除了在“爱国”这一点与任建树的论点相同外,“爱人民”与“爱家庭”两层含义则与沈寂、任建树两人的解释存在很大差异。尽管观点存在差异,但是上述三位学者的“论断”方法却存在一个共通之处——相关结论均是在考察《俗话报》时期陈独秀言行尤其是陈独秀以“三爱”笔名所刊文章内容这一共同的基础上得出的。不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一共同的基础并不牢靠,上述论点都忽略了对陈独秀在创办《俗话报》前编辑《国民日日报》经历的考察,尤其是忽略了对刊于《国民日日报》相关文章的考察。因此,上述三种代表性观点均带有推论的色彩。事实上,任建树与唐宝林两位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如任建树在论述时使用了“大约”一词,唐宝林在论述时不仅使用了“似乎”,还明确标注“是否如此,待考”[3]17,表明当前学界对陈独秀“三爱”笔名的含义及来源尚不确定。本文则尝试在上述三位学者合理推测的基础上,通过考察陈独秀、章士钊共同主笔的《国民日日报》所刊载的《慨论德人自戕事》、《自杀篇》等两篇“社说”的内容以及陈独秀这一时期笔名从“由己”到“三爱”的变化,进一步“确定”“三爱”笔名的来源及确切含义。
二、“三爱”笔名的考辨
本文对陈独秀“三爱”笔名的考辨分为三步:首先,从陈独秀与章士钊共同主持《国民日日报》笔政的史实,推论该报连续发表的《慨论德人自戕事》与《自杀篇》两篇社说所提出的“爱国家”“爱真理”与“爱人道”的主张反映了陈独秀的思想“印迹”。其次,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两篇社说论及的“爱国家”“爱真理”与“爱人道”的“三爱”与前述三位学者由陈独秀《俗话报》时期言行所推论出的“三爱”的含义进行比较,指出《俗话报》所阐释的“三爱”与“爱国家”“爱真理”“爱人道”的“三爱”在内容上是“相合”的。最后,从陈独秀笔名从“由己”到“三爱”的变化,以及《国民日日报》、《俗话报》等两份报刊在创办时间、内容方面的承继性等方面,进一步指出笔名“三爱”是指《慨论德人自戕事》、《自杀篇》两篇社说所论及的“爱国家”“爱真理”与“爱人道”。
1.《慨论德人自戕事》《自杀篇》与“爱国家”“爱真理”与“爱人道”的出现
《俗话报》创刊前,陈独秀曾与章士钊一起创办、总理编辑《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7日-1903年12月4日)。《国民日日报》尽管发行时间较短,但影响颇大,被时人赞评为“《苏报》第二”。该报在停刊前两日连续刊发了《慨论德人自戕事》(12月2日)与《自杀篇》(12月3日)等两篇“社说”,这两篇“社说”均明确论及了“爱国家”、“爱真理”与“爱人道”。
《慨论德人自戕事》一文在体裁上类似新闻评论,篇首交待德国人朱臻仕自戕详情,其后以“记者曰”对此事件进行评论,论述了自杀与“爱国”“爱真理”及“爱人道”的关系:“若中国为奴之贱种,即令划除净尽,犹已死有余辜,果何足以真理与人道而相衡度,故德人非爱中国也,爱真理爱人道也,盖华族不足与真理人道相支配,即不足以当德人之爱,若谓华族尚存真理人道于万一,则以德人自戕之惨断不致如木石之毫无感觉,戢戢以待死,顽然而不知所为,一至于是也,可断言也。”[4]
《自杀篇》一文虽用了大半篇幅讨论自杀问题,但在文章末段也论及了德人朱臻仕自杀一事:“近顷有德人朱臻仕,为爱中国之故而自杀,昨已著论言之。夫此德人不过中国之一教员耳,中国国事之危急,德人无可死之道也,而德人者,乃以欲表其伟大之民族,强武之名誉,并爱真理爱人道,如耶稣之有迷信之故,而出于自杀。此德人适成其为德人,若以种族之贵贱例之,则以一外人而以爱真理爱人道推以爱其国而自杀,则其国之果有一人否耶……今以德人之自杀,因推论自杀之原理著于篇。”[5]
考察上述两篇“社说”的引文,可以发现两篇“社说”都围绕德国人朱臻仕自杀事件展开立论,也都明确论及了“爱国家”“爱真理”与“爱人道”。然而,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国民日日报》的“社说”并不署名,所以很难断定两篇社说的作者究竟是谁,也很难判定陈独秀“三爱”笔名即是指“爱国家”“爱真理”与“爱人道”,但可以明确的是,这两篇社说提出并讨论了“爱国家”“爱真理”与“爱人道”。
应该看到,《国民日日报》时期,中国报坛仍处于政论时代,言论是那个时代报纸的“灵魂”与“旗帜”。言论不仅构成了一份报纸的主要内容,言论质量的高低也与“报刊影响的大小成正比”[6]。因此,主笔是报刊的台柱,而主笔的主要任务则是主持笔政,发表社说。《国民日日报》的笔政是陈独秀与章士钊共同主持的,而且相较于章士钊的“一心二用”,陈独秀则是全心全意投入报纸的编辑工作。因此,《国民日日报》必然反映陈独秀的思想印迹[7]。在这个意义上,虽不能断定陈独秀即为上述两篇社说的作者,但我们可以认为陈独秀是赞同或赏识这两篇社说所提出的“三爱”的思想主张。
2.《安徽俗话报》对“爱国家”“爱真理”“爱人道”的阐释与宣传
《国民日日报》停刊后,陈独秀回到安庆筹办《俗话报》。1904年3月,《俗话报》第1期面世。《俗话报》的创办不仅让陈独秀有机会将积累的报刊经验付诸实践,也让其获得了系统阐释思想主张的报刊阵地。陈独秀以“三爱”笔名刊发的五十余篇文章,不仅构成了《俗话报》的内容主体,也让《俗话报》“风行一时,几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埒”[8]。当前学界虽然对“三爱”的确切含义存在争议,但都认为《俗话报》的内容反映了陈独秀的“三爱”思想,那么《国民日日报》停刊前两日所刊社论提出的“爱国家”“爱真理”及“爱人道”的“三爱”与陈独秀在《俗话报》上宣传阐释的“三爱”在内容上是否“相合”呢?如果“相合”的话,则可以认为陈独秀利用《俗话报》所宣传阐释的“三爱”是指“爱国家”“爱真理”与“爱人道”。
本文并不打算从文本分析角度分析《俗话报》所宣传阐释的“三爱”的具体含义,而是采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两篇社说论及的“三爱”(“爱国家”“爱真理”“爱人道”)与前述三位学者所界定的“三爱”含义的比较,以此判定《俗话报》所宣传阐释的“三爱”是否与“爱国家”“爱真理”“爱人道”的“三爱”“相合”。从沈寂、任建树、唐宝林等人关于“三爱”含义的论述看,两者是“相合”的。如上所述,沈寂认为,“三爱”寓指“爱国家、爱科学、爱自由民主之意”;任建树认为,“三爱”的含义大约是爱祖国、爱科学、爱自由;唐宝林则认为,“三爱”似乎指“爱国家、爱人民、爱家庭”。应该看到,“爱国家”为三人共同承认,“爱真理”与沈寂、任建树归纳的“爱科学”相类,“爱人道”则与唐宝林归纳的“爱人民”“爱家庭”相通。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人道”定义的宽泛性,“爱自由”与“爱民主”也可以纳入“爱人道”的范畴。可以说,“爱国家、爱真理、爱人道”是对沈寂、任建树、唐宝林等人结论的高度概括。从这个角度看,《国民日日报》停刊前所刊两篇“社说”提出的“爱国家”“爱真理”“爱人道”的“三爱”与陈独秀以“三爱”笔名在《俗话报》所刊文章宣传阐释的内容是“相合”的。
如前所述,任建树与唐宝林对各自所作的论断并不“确定”,分别使用了“大约”与“似乎”,唐宝林还进一步认为“是否如此,待考”。为何他们无法确定呢?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根据陈独秀在《俗话报》上刊载的文字所做出的推论确实具有不确定性,不同的人对同一内容往往可以作出不同的论断,存在差异势所必然;二是当前对陈独秀早年思想主张的研究普遍忽略了对《国民日日报》的研读。事实上,如果研读了《国民日日报》末期刊登的《慨论德人自戕事》与《自杀篇》两篇社说,就很容易确定陈独秀的“三爱”笔名应该与这两篇社说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三爱”笔名即来源于这两篇社说。
3.“由己”到“三爱”笔名的变化与两份报刊的连续性
上述两部分已经指出《国民日日报》末期刊登的两篇社说所提出的“三爱”与《俗话报》阐释的“三爱”在内涵上的相合性,前者应该是陈独秀“三爱”笔名的来源,但这个结论仍然带有很强的推论色彩。本部分主要从陈独秀笔名从“由己”到“三爱”的变化,以及与此变化相伴随的《国民日日报》与《俗话报》在创办时间、内容上的承继性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三爱”笔名即是指“爱国家”“爱真理”与“爱人道”。
“由己”是陈独秀在《俗话报》前曾经使用过的笔名。1902年9月,陈独秀第二次留学日本,即为自己取名“陈由己”[1]8,该年年底加入东京留学生界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时,也署名“陈由己”[9]。1903年第二次演说会期间,陈独秀署名“由己”在《苏报》“学界风潮”栏发表了《安徽爱国会演说》(1903年5月26日)。沈寂认为,“‘由己’转语法为‘自由’,即凡事由自己抉择,也即独立思考问题”[2]128。因此,“由己”的笔名反映了陈独秀对“个人自由”的主张。应该看到,上文沈寂、任建树归纳的“爱自由”、“爱民主”主要受到了“由己”笔名的影响。
《国民日日报》停刊后,陈独秀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即回到安庆筹办《俗话报》并使用“三爱”笔名。需要注意的是,就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报刊活动来看,《国民日日报》的停刊与《俗话报》的创办在时间上是前后相继的,“由己”与“三爱”这两个笔名在时间上也是相继的①《俗话报》创刊后,陈独秀曾以“由己”笔名在《警钟日报》发表了两首哀诗,《哭何梅士》(1904年4月15日)、《夜梦忘友何梅士觉而赋此》(1904年5月7日)。这是对忘友的哀悼,主持《警钟日报》的也是蔡元培、刘师培、林白水等熟识,理应使用“由己”,而不用“三爱”。。这种相继性至少表明两点:一是陈独秀需要通过《俗话报》来完成《国民日日报》未竟的工作,传播自己的思想主张;二是笔名从“由己”到“三爱”的变化,寓意陈独秀思想主张的变化,表明陈独秀即将展开“三爱”的宣传。
应该看到,与《苏报》被封不同,《国民日日报》的停刊来自于内部纠纷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偶与卢某涉讼,经费缺乏,停刊”[10]。报纸的停刊让主笔稍稍论及的“三爱”思想失去了讨论的媒介阵地,如果要继续传播“三爱”主张,就需要新的媒介阵地,而稍后创办的《俗话报》事实上就成为陈独秀传播“三爱”思想的媒介阵地。章士钊、刘师培、林白水等《国民日日报》报刊同人停刊后的报刊实践与社会活动也印证了这一点。章士钊在报纸停刊后直至民元前再也没有创办报纸;刘师培、林白水则主持《俄事警闻》,后又创办《中国白话报》,进行激烈的“排满革命”宣传,只有陈独秀通过《俗话报》旗帜鲜明地对社会底层民众进行“爱国家、爱真理、爱人道”的“三爱”启蒙。至此,我们有理由确定“三爱”来源于《国民日日报》末期刊登的《慨论德人自戕事》与《自杀篇》等两篇社说论及的“爱国家”“爱真理”与“爱人道”,甚至可以说这两篇文章即为陈独秀所作。
三、结语
《国民日日报》停刊前两日刊登的《慨论德人自戕事》与《自杀篇》等两篇社说中论及的“爱国家”、“爱真理”与“爱人道”,应是陈独秀《俗话报》时期使用的“三爱”笔名的来源。这不仅是因为陈独秀是《国民日日报》的总理编辑之一,该报所刊言论应该反映陈独秀的思想主张,也因为《国民日日报》与《俗话报》这两份报刊在停刊与创刊时间上的承继性,以及《俗话报》对“爱国家”、“爱真理”与“爱人道”的深刻阐释与宣传,笔名由“由己”改为“三爱”不仅透露出陈独秀由“由一己之欲”转向对民众展开“三爱”的思想启蒙,更反映了德国人朱臻仕自戕一事对其深入灵魂的触动。当然,因为《国民日日报》刊发的《慨论德人自戕事》与《自杀篇》两篇社说并没有署名,所以本文的结论仍带有一定的“推论”性质。这种“推论”是必要的,既还原了史实,又有助于研究陈独秀早年的思想主张。
[1]任建树.陈独秀大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沈寂.陈独秀传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3]唐宝林.陈独秀全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慨论德人自戕事[N].国民日日报,1903-12-02(2).
[5]自杀篇[N].国民日日报,1903-12-03(2).
[6]曾建雄.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近代部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24.
[7]陈长松.论陈独秀于《国民日日报》的地位与贡献[J].编辑之友,2012(12).
[8]房秩五.回忆《俗话报》诗一首[G].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14.
[9]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M].上海:上海书店,1990:61.
[10]张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5-6.
责任编校:徐希军
“Love the Country”,“Love the Truth”and“Love Human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EN Du-xiu’s Three-love Pseudonym
CHEN Chang-s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Huaian 223300,Jiangsu,China)
The three-love pseudonym was used by CHEN Du-xiu during his period of producing Anhui Colloquialism Newspaper.The current research tends to believe that the pseudonym means“love science”,“love the country”and“love freedom”.However,in this essay,CHEN Du-xiu’s two articles,i.e.“Theory of Self-Suicide”and“Suicide”published on“National Day Daily”have been carefully studied.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his thinking,words and pseudonyms during this period,it can be concluded that“love the country”,“love the truth”and“love humanity”are the true meaning of his pseudonym.The clarification will b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thoughts of CHEN Du-xiu in the early stage.
CHEN Du-xiu;pseudonym;Anhui Colloquialism Newspaper
D231
A
:1003-4730(2016)06-0017-04
时间:2017-1-20 15:3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70120.1533.004.html
2016-04-18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陈独秀报刊实践与思想研究”(2016SJB860005)。
陈长松,男,江苏海州人,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6.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