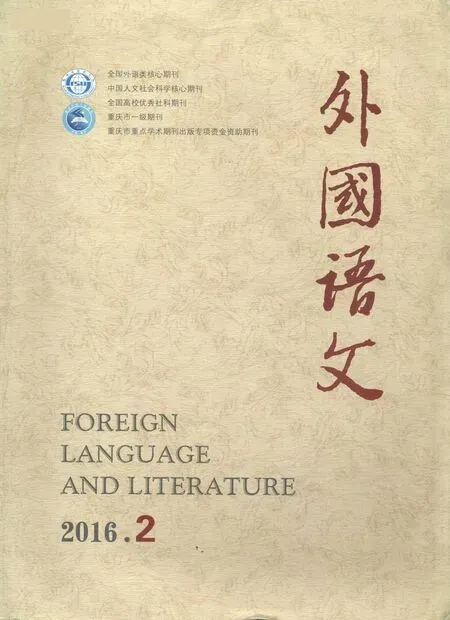沉默与言说:库切小说《福》与后殖民批判
2016-03-17姜小卫
姜小卫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沉默与言说:库切小说《福》与后殖民批判
姜小卫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重庆400031)
摘要:库切的小说《福》已成为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逆写帝国"的经典。论文通过解读库切的小说文本阐释斯皮瓦克对于后殖民理性的批判,对于西方知识权力阶层为他者代言时必然隐含的话语权力的批判。理论文本与小说文本相互佐证、相互阐释,论文力图阐明《福》的主旨在于:面对被砍掉"舌头"的礼拜五们,那些在知识-权力话语场域被褫夺了言说权力的他者,那些在现代性历史进程和现实语境中遭受伤害的沉默者,面对礼拜五们残损的身体和难以磨灭的历史创伤和心理创伤,知识分子、历史书写者和作家如何才能承担起政治和伦理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库切 《福》 他者 沉默 言说与叙事
斯皮瓦克的理论文本素以艰涩、繁难著称,她认为库切的小说《福》可以作为一种理解其理论的“启示性辅助工具”(Spivak, 1999: 174)。我在论文中首先结合斯皮瓦克对《福》等文本的阐释对《属下能说话吗?》这一著名的理论文本进行了详细读解,问题并不在于属下阶层是否能够言说,而在于西方知识-权力阶层在表征属下时所采取的绝对化他者的主体立场和代言者姿态。斯皮瓦克认为库切的小说形象地展示出“独特的、不可证实的边缘”,对于将沉默的他者全然绝对化过程是“一种折射性的屏障”(Spivak, 1999: 175)。斯皮瓦克让我们警示他者化过程中的本质主义:代言和表征沉默的他者始终存在重新抑制他者声音的危险,始终有可能将他者重新湮没在宰制性语言和知识暴力凝结而成、使他者沉默的黑暗深渊。在论文第二部分,我在斯皮瓦克理论洞见的烛照下,重点阐释《福》中最为扑朔迷离、神秘难解的第四章*对于库切小说前三章的总体阐释请参阅拙文《他者的历史:被砍掉“舌头”的礼拜五》,见《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理论文本与小说文本互释互解,旨在阐明库切小说标识出后殖民历史书写、文学表征、政治代言难以逾越的界限,即那些殖民历史中受伤害、受残损的身体,礼拜五的身体成为所有受伤害者深海一样沉默的符号,标示出后殖民和后现代历史书写的标准与尺度。
1他者的沉默与表征
斯皮瓦克在其极负盛名、屡遭误解的文章《属下能说话吗?》中,把20世纪欧洲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印度属下研究团体所宣称的——知识分子可以代表边缘化群体、为那些被褫夺话语权和发言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属下阶层代言——与19世纪统治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假装正直地宣称把当地妇女从印度教寡妇自我殉身的陋习解救出来等同起来,意在阐明西方激进的知识分子宣称为属下群体经验代言又吊诡地使其“哑言”、沉默,其路径和策略与那些自称善意地解救自我殉身、而实质上在殖民话语霸权和历史中被“哑言”、沉默的寡妇们的老派殖民主义者如出一辙。斯皮瓦克认为“知识分子总存在与持续地将他者视为自我的影子来建构形成共谋的可能性”(Spivak, 1999: 266),西方知识分子在对自主性主体(Sovereign Subjects)进行激进批判的同时,却在面对更广泛的属下阶层这样的他者时创立了西方主体,创立了作为大写主体的西方知识分子精英群体。他们在批判“知识暴力”(epistemic violence)的同时,又确立了针对女性群体,特别是第三世界底层女性群体的知识暴力。斯皮瓦克认为,这样的知识话语霸权依然是帝国和后殖民历史叙述的基质,其“后表征主义的语汇掩盖了本质主义的议程(an essentialist agenda)”(Spivak, 1999: 271)。
对处于这样的知识话语体系中却安之若素,并对自我的境遇浑然不察的知识分子而言,属下群体的声音唯有通过知识分子熟悉的话语、词汇才能被知识界所听闻、察觉和关注,因而斯皮瓦克在文中一再追问这样一个令人困扰不解的问题:“属下能说话吗?”当把知识暴力与学问和文明的进步混为一谈时,作为属下阶层的女性能有发言权吗?面对历史叙述和记忆、知识话语、学术体系中不可恢复的被殖民属下主体的异质性,有人聆听、阅读女性属下的声音吗?
斯皮瓦克坚持被殖民属下主体,特别是后殖民语境中和全球化资本经济体系中被同化的女性属下主体,这种不可恢复的异质性。其犀利的观点同样针对国际女性主义为女性代言的普遍性宣言,以及与她自己有密切联系的“属下研究团体”。前者自诩为全球所有女性的代言者自居,却忽视了全球化资本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及其自身观点和知识话语的立场,后者机械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挪用到对于印度农民属下阶级反抗殖民统治的历史撰写中,希望赋予这一属下群体一种“属下意识”。斯皮瓦克赞同后者的研究立场和观点,但是对其研究方法和策略提出质疑,她在文中指出:“这不是在描述‘事物的真实状态’,也不是给作为帝国主义的历史叙述以最佳历史叙述的殊荣。而是要说明对现实的一种解释或叙述何以被确立为规范的解释或叙述。”(罗钢、刘象愚,1999: 115)斯皮瓦克认为:古哈等人的文本实际表明把自身不可能条件重写成可能的条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在知识可能性的普遍暴力中,“属下阶级的历史撰写必须面对撰写的不可能姿态”(罗钢、刘象愚,1999: 124)。
斯皮瓦克以冷静的自我批判意识提醒人们对所有的表征保持警觉:作为“代言”的政治话语的表征和“作为重新表现”艺术领域的表征相互关联,却是无法还原地断裂。她坚持认为任何体系、知识话语,都不可避免地把某物排除在外。斯皮瓦克应该会同意伯麦兄弟的说法,排他性理性与包容性理性的对立和界限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清晰,包容性理性于是成为一厢情愿的社会实践理性,最终带有工具理性的功能,“正是因为有了他者,理性才必不可少”,理性离开他者便无法存在(哈贝马斯,2004:356)。在伯麦兄弟看来,自康德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就是一个划分界限的排他性理性逐步确立的稳定领域,而“划界的过程就是明确自身和排除他者的过程”(哈贝马斯,2004:354)。这一排他性理性逻辑在斯皮瓦克所批判的殖民理性中尤为显著。
面对属下这种“去殖民化空间纯粹的异质性”所体现的他性,斯皮瓦克呼吁人们应该像德里达所说的那样:不能让别人为自己说话,而是诉求于对“完全的他者”的“诱惑”和“号召”,把我们内心中作为他者声音的那种内在的声音如痴如狂地表现出来(罗钢、刘象愚,1999: 134)。在斯皮瓦克看来,言说正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说话总是在一系列行为关系中得以发生,聆听、回应、解释、提出异议加以限制等。巴赫金认为作者创造(authoring)就是一种对话,总是面对特异于作者自我、处于另一个特定时空(chronotope)语境的另一个他者,斯皮瓦克同样说:“所有的言说,即使看起来是最直接的,都伴随着另外一个人有一定出入的解读,这种解读最好是一种拦截。这正是言说之所以成为言说之处。”(Spivak, 1999: 309)在面对历史沉积层和文化记忆中湮没无闻的他者的声音时,斯皮瓦克一方面吁请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包括身为知识分子的女性知识分子,必须“表征”属下阶层;另一方面又告诫我们不要简单地赋予那些无言、无语的他者一种声音,告诫后殖民评论家不要像西方左翼的知识分子一样,一味地抱着善良的美好愿望,在表征属下阶层时将属下主体(the subaltern subject)浪漫化、同质化。斯皮瓦克尤其关注殖民生产语境中处于“更深层阴影之中”的女性属下阶层,关注全球化以及后殖民理论话语形成中必然遭到双重压制的第三世界的女性。女性与沉默的关系必然笼罩在种族和阶级差异的重荷之下:“属下阶级的历史编纂必须面对这种姿态的不可能性。帝国主义狭隘的知识暴力给予我们是普遍暴力不完善的讽喻,这种普遍暴力构成了认知型的可能性。”(罗钢、刘象愚,1999: 124-125)斯皮瓦克坚持一种自我批判的后殖民理论,坚持帝国主义批判的解构策略,以揭示表征赖以展示的普遍意义上的“书写”所固有的知识暴力和认知困境。
在历史的修正式重写中,对于构成认知型可能性的知识暴力的批判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思考维度。在这种思想维度中,后殖民理论与解构的后现代理论具有必然的关联性。“许多修正主义历史以及重写宰制和压迫场景的许多观点,正是试图激活那些别的力量极力想要抹除、阻止其发生效应的言说。想要恢复昔日场景的历史学家、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文化理论家,必须描画出沉默的属下残留下的‘踪迹的路线’,标识出属下被去除的场所,阐明实施这种去除的话语。”(Vincent B. Leitch, 1999:2196)
对于萨义德所开创的后殖民研究,斯皮瓦克亦颇多微词。她在《教学机器以外》中这样说道:边缘性这一语汇及其相关研究是“阿拉伯世界”的伟大文本,如弗朗兹·法农等人的论著所言说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亦成为后殖民研究学科的重要来源,“但是萨义德的著作并非是对边缘性的研究,甚至也不是对边缘化的研究。它是对于建构一种研究对象的研究,以研究和控制为鹄的。殖民话语的研究已经衍生为繁花似锦的大花园,其中边缘人可以说话、被言说,甚至由别人代言”(Robert Young, 2003: 8)。可见,斯皮瓦克这位自称为“实践的、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只牛虻式”的理论家,以坚持不懈的解构姿态审视“真理是如何建构的”,并以一种理论为契机来暴露、揭示另一种理论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的知识暴力。对于她而言,理论本身是一个不断被质疑、揭示和批判的过程,而不是建立知识权力体系或知识霸权并提供现成答案的工具。斯皮瓦克自己对于自身的理论也具有清醒的自我批判意识,她竭力提防自己的理论沦为其理论标枪投射的标靶。
斯皮瓦克在书写普瓦奈斯瓦里以及其他属下女性的故事时尝试了新的书写办法,以揭示出在形成女性属下哑言背后的话语形成过程,揭示普瓦奈斯里的声音不能被听到的原因。16岁的普瓦奈斯瓦里是一位参加印度武装独立战争的女革命者,因为无法完成一次政治谋杀任务而在月经期自杀。斯皮瓦克把普瓦奈斯里的自杀举动解读为“对sati自杀的社会文本的一种无力的属下重写”(罗钢、刘象愚,1999: 156),但是却无人聆听、阅读、记载她的声音。她去咨询一位孟加拉女性学者,对方顾左右而言他。她为这种交流的失败难以自抑,因而写下了不无愤激之辞:“属下不能说话!”*斯皮瓦克在1999年的版本中说,“这句话并非是明智的评述”。(Spivak, 1999: 308)斯皮瓦克要“女性主义文学评论家用解构为阅读服务”,以防止揭示中的抹除。“处于生产叙事模式以外的女性标识出学科史书写中的没点(the points of fadeout),即使他们使诸如踪迹——她们在揭示时擦抹的踪迹之足迹的‘书写’哑言。”(Spivak, 1999: 244-245)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斯皮瓦克坦言在关注那些伴随着生产叙事的女性的同时,无论她们是参与者、抑制者还是牺牲品,更加关注书写女性生活的生产叙事模式最基本层面的价值编码(the ground-level value-coding),因为“价值是最有效、最抽象的编码”,即经济构成了生产叙事模式之所以有效的关键。而这些价值编码却是最难察觉和理解的,是令人难以捉摸的形象(elusive figures)。
按照德里达更为激进阶段、肯定意义上的解构观念——解构即是正义,斯皮瓦克赞同正义和伦理是不可解构的术语,她在《后殖民理性批判》中提出全球化和后殖民理论新的伦理维度,后殖民研究的知识分子应该向那些“反全球化者或者另一种发展的行动主义者”(Spivak, 1999: 429)学习,学会掌握他们的语汇,而不是以他们的代言人自居,为其表征。向属下学习!学会向底层人学习,而不是由上至下“仁慈”地分派所谓的人权,以塑造底层群体的灵魂,这便是斯皮瓦克所说的“属下的教育艺术”。斯皮瓦克坚持不懈地批判、自我批判的精神与其伦理上的考量紧密地连在一起,共同指向“具有开放目的的政治学”,而解构可以充当“守卫者”的角色,以反对主流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对于“他性”(alterities)的宰制,反对不可避免的暴力语言和知识权力将人自身(民众)视为可以工具般塑造的某种物质,反对形塑主体、建构话语世界、扭曲和殖民化本真性生活世界的知识暴力。这种知识暴力与占据支配地位的世界观一道把那些“他者”,不合其知识霸权体系的人、观念和事件,任意分派、切割并达到隔除和压制的目的。
在《后殖民理性批判》的“文学”一章中,斯皮瓦克批判了萨特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对于他者,只要有足够的信息,总可以找到完全理解他们的办法,她提出仍然摆在欧洲人以及学术精英——处于新殖民语境中的美国评论家和人文学科的教授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如何在其自身中重塑对于中国人、印度人或非洲人的设计?斯皮瓦克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解构提供了双重的策略。“从你所处的位置出发;但是在寻求一种绝对的判断时,要谨记边缘者自身是一个划分完全的他者之不可能性的界限,而与完全的他者相遇与我们的伦理准则有着不可预料的关系。被命名的边缘人既是对边缘者的揭示又是对边缘者的遮蔽;在她/他揭示之处,她/他是独特的。”(Spivak, 1999: 173)斯皮瓦克从如是的解构观对库切的《福》进行了详细的互文本解读,她认为真正的解构读解模式对于后殖民评论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解构的立场”使后殖民评论者“对作为历史个案的后殖民性结构说‘不’,后殖民评论家们在批判这种结构的同时又安之若素”(Spivak, 1999: 191)。斯皮瓦克应该会同意希利斯·米勒的观点,小说首先是一种“虚拟的现实”。正是《福》小说的元小说性使库切在拒绝讲述礼拜五故事的同时,在拒绝从上而下、浪漫化地给予礼拜五这个黑人一种声音的同时,通过形象化地描写失去声音的礼拜五这个人物展现出历史中那些沉默者“不可能经历得以浮现的过程”(Sangeeta Ray, 2009: 43)。与史实相比,甚至与历史编纂中的“史实”相比,小说中的真实讲述并非要做到精确无误,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从边缘之处来阅读后殖民小说,才能理解“通过阅读文学,我们学会了从独特、不可证实中学习”(Spivak, 1999: 142)。
斯皮瓦克对于《福》的解读,旨在揭示出在西方小说中大量存在的“灵魂塑造”的书写,“《福》重新打开了18世纪早期两个试图建构边缘性的英语文本,《鲁滨逊漂流记》和《罗克珊娜》”(Spivak, 1999: 172)。在笛福笔下,礼拜五是黑人从边缘融入中心、由土著转变为正常的殖民主体的原型和成功典范。库切则拒绝这样的书写,在他的重新铭写中,失去语言的礼拜五仍处于边缘处,他那大海一样的沉默不仅象征着历史书写中被压抑、被沉默的他者的叠层和厚度,而且代表着一种姿态:即斯皮瓦克所说的拒绝向殖民主义者提供信息。与《藻海无边》中的克里斯托芬妮不同,里斯所描写的是从边缘走向中心,以中心的语言言说的女性他者,一位疯癫者的形象,是“边缘的守护者”,而礼拜五则是“位于边缘处的守护者”,他以沉默的话语来言说,以“沉默”的言说抗拒灵魂的塑造,抗拒另外的他者对自身故事的讲述。礼拜五拒绝一种他者视角下的“土著”的声音,即使这种视角来自于和他一样同处于另外一种边缘状态的“白人礼拜五”、对自己充满同情、关切和呵护的苏珊,即使这种声音是属下性的土著声音。斯皮瓦克明确指出:
面对每一个地盘性的空间(territorial space),被殖民主义以及大都市反殖民主义命令土著发出他自己“声音”所编码的价值[价值符码统辖、支配、分割的辖域化空间],都存在一个抵制的空间,由一个并非是秘密但难以解开的秘密所标识。不论“土著”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一个牺牲品,而是一个能动主体(an agent)。是拒绝提供信息的处于边缘处的令人讶异的守护者。(Spivak, 1999: 190)
正如桑吉塔·雷所论,在斯皮瓦克对于《福》的解读中,斯皮瓦克对于大都市后殖民主义评论者的批判达到顶峰,她告诫我们不要轻易地给予迁移性和杂糅性(migrancy and hybridity)以特许,也不要轻易地赋予属下一种代理人或者一种填充在“土著”声音缺口的历史书写。斯皮瓦克关注的是“土著”或历史撰写中沉默的他者“被不同类型的评论家们所赋予的声音以及伴随这种赋予其声音时政治和批判投资的过程”(Sangeeta Ray, 2009: 47)。
2沉默他者的言说与叙事
苏珊在希望赋予“被砍掉舌头”的礼拜五一种声音的时候,是否会清醒地意识到斯皮瓦克所批判的这种仁慈、自上而下的浪漫化呢?她并不认为礼拜五是她的仆人,他并非臣服于她,他只是如影随形地伴随在她左右。他不是自由人,却不是任何人的仆人。“从法律上来说,自从克鲁叟去世后,他就是他自己的主人。”(Coetzee, 1986: 150/139)*引文为笔者自己所译,曾参考王敬慧的中译本《福》(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斜杠后为中译本页码。(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无论如何,库切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斯皮瓦克不遗余力所揭示的书写他者时的两难处境,他拒绝用自己的声音来讲述礼拜五或者苏珊的故事。
苏珊应该会同意作者福先生所说的那样:写作宛若掉入“怀疑的迷宫”,要想获救、走出迷宫,就要不断地在自己停留的地方标上记号,回到起点就意味着再次迷失方向,然后只有不断地从标记的起点开始,反复地回到起点,最终才能走出迷宫。那么,起点又在何处呢?对于同样陷入迷宫的读者又该从哪里出发呢?苏珊讲述荒岛漂流记和自己与礼拜五在英伦本土的漂荡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的故事似乎充满了比我自己意欲的更多的寓意,我必须一次次折回、煞费苦心地抽取正确的寓意,为错误的[向你]致歉、并加以删除。”(Coetzee, 1986: 81/71)这或许是库切为自己煞费苦心、精心建造的这座叙事和语言密织而成的、精致繁复的迷宫作辩白,以探求为沉默的他者言说之不可能的可能性。读者唯有一次次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像采珠人一样深潜进海底,从历史的残骸和废墟中,从业已形成的历史记忆的陈迹中,探寻那宝贵的珍珠,而不是被遗弃的贝壳。
在《福》的迷宫中,礼拜五的“舌头”被砍掉这个“可怕的故事”是最大的谜团,是《福》(也是所有历史书写和小说叙述,包括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叙述中的一个谜或者一个洞。库切自始至终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究竟是谁因何原因砍掉了礼拜五的舌头(如果你相信克鲁叟所说的话,是奴隶贩子干的,请不要忘记苏珊的怀疑,克鲁叟从沉船上带上荒岛的唯一器具就是挂在他腰间的那把刀子)。关于这个谜团的模糊性,库切暗含着克鲁叟、福先生、苏珊,甚至包括他自己——身为白人殖民者后裔的《福》这本小说的真实作者,在使礼拜五“失语”的事件中都是同谋,目的在于阻止礼拜五们拥有自己的语言,阻止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或许他们想要阻止他,永远不要来讲他自己的故事。”(Coetzee, 1986: 23/19)
正如克鲁叟荒岛的真实经历只有通过克鲁叟自己来讲述一样(这难道不正是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使用的叙述策略和程式吗?由叙述者自己讲述亲身经历难道不是保证现实主义逼真性效果的一大惯例吗?小说《福》特有的后现代反讽的张力恰恰在于,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段和叙事模式也是库切自己既挪用又不断质疑、拆解的解构策略),“能够说清礼拜五秘密的舌头(语言)只能是礼拜五被砍掉的、他自己的舌头!”(Coetzee, 1986: 67/59)显然读者完全可以把这个句子中的舌头替换成语言,礼拜五没有言语能力,克鲁叟又病疫在回国的途中,唯一能够讲述荒岛奇遇的见证者、亲历者便是女性海难者苏珊·巴顿。苏珊只能尽力讲述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我会将能描述的事情以最简单的字眼来说明,不能阐明的事,我就三缄其口”(库切,2007:108)。她会预料到自己的讲述也能够成为历史吗?“生活中可以接受的事情,在历史中却是不可接受的。”(Coetzee, 1986: 67/59)生活经验与历史叙事之间始终存在语言媒介本身构成的鸿沟。有关礼拜五失去舌头这件令人恐惧的事情,真相究竟在何处呢,或许就在其不可言说的沉默中(当然我们可以说,沉默也是一种言说,沉默同时也是一种抵抗策略)。
在苏珊看来,有关礼拜五被砍掉的“舌头”的故事是无法言说,因为真实的故事只有礼拜五知道,他却失去了言说的能力。“这个真实的故事只有等我们找到一种办法给予礼拜五声音。” (Coetzee, 1986: 118/106)我们再次回到了历史叙述的原点,语言的原点,这正是库切这部令人费解的小说所要讲述的故事,一个关于讲述之不可能性的故事。一个关于语言和叙述、叙述和真实的故事,一个关于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定见如何规约着人们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故事。唯有通过语言和叙事,人们才能够了解自身,才能够获得言说的权力,表达其自身。面对历史叙述中的“谜”和“空洞”,面对人道主义者们不忍心直面的礼拜五们残损身体这一残酷的历史记忆,故事讲述人只能像采珠人一样深潜在历史叙述档案的海洋里,去揭开历史话语的叠层,去探寻历史的印迹。
小说结尾一章颇令人费解。该章由两段并列的叙述构成,不明身份的叙述者两次造访历史记忆的阁楼(第二次应该是已进入不朽的经典作家之列的丹尼尔·笛福的故居)。叙述由过去式转为一般现在时,作者的叙述把读者引到当下时空。叙述空间也由昏暗不明的阁楼一直到克鲁叟和礼拜五的小岛再到海底沉船(克鲁叟、礼拜五遭遇海难的沉船?抑或一艘贩运黑奴的沉船?)的残骸。颇有些相似却又如此迥然相异的造访和叙述有一个共同的发现,那就是蜷缩在壁橱里的礼拜五的身体,以及从前没有注意到的礼拜五脖子上项链似的疤痕、被绳索或者铁链捆绑后留下的疤痕。
礼拜五与不知名叙述者碰到的其他死者僵硬、冰冷的尸体不同,他微温的身体传出微弱的脉搏,“他的身体发出的声音十分微弱、单调乏味,宛若落叶飘落在树叶上的声音”(Coetzee, 1986: 154/143)。叙述者试图撬开礼拜五紧闭的牙关,凑近他空空如也的嘴巴,凝神静听,远处传来微弱的呼啸声:像贝壳里海浪的咆哮、风声、鸟鸣、鹤嘴锄的重击声,“他的口中回荡着小岛的声音,持续不断、绵延不绝”( Coetzee, 1986: 154/144)。克鲁叟的小岛依然存在,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历史文本中,存在于人们的文化记忆中,也存在于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但是这个曾被视为西方殖民者海外殖民的典范、开拓者的伊甸园、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乌托邦的著名岛屿,其真实的声音却是自然界各种声响与历史叙述所制造的各种“声音”的混响,这需要我们凝神谛听,包括沉默的他者发出的微弱得令人心痛、却又如此持久、没有任何间歇的“呐喊声”,亦包括库切小说本身所蕴含的独特“声音”。
在与戴维·安特威尔的访谈中,库切阐述了小说最后一章的创作构思以及对小说主题的思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一种能力:像弗洛伊德似的悲观地接受,或者像德里达一样平静地接受没有结尾的前景。”(Coetzee, 1992: 249)而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笔记》的结尾,借用编辑的话指明文本应该理解为无休止的延伸,只是“一种美学上的无奈”(Coetzee, 1992: 248)。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较,陀氏在面对信仰和怀疑的困扰、纠结时不是用忏悔的结束而是用绝对的仁慈对于世界的干预的结束来对抗无终结性(endlessness),库切自认《福》的结尾关乎表征的权力问题。这一点或许是库切与福柯如此接近又截然不同的地方,在《福》中,叙述表征的权力,作者霸权受到严重的质疑,正如前面所有的分析表明的,这一点是通过“文本化无休止的质疑过程”实现的,但是库切并不认为,在这样叙述中,即使像《福》这样一部对现实主义历史和小说坚持不懈地文本化的元小说中,经由文本以及在文本中加以表征的女性主体、殖民主体并非权力尽失。这一点库切与斯皮瓦克的观点相合,“对于苏珊·巴顿而言,这部书是她的,而不是福的,尽管采取了记述她追索一个仇敌来替她自己讲述的线索的形式”(Coetzee, 1992: 248)。无论是对福或者笛福,对苏珊·巴顿还是克鲁索而言,“礼拜五是真正的考验”,其遭受伤害的身体拥有不容否认的权力,“《福》的最后几页拥有某种权力。它们用力量来结束全书,也就是说,对抗小说怀疑主义的无终结性”(Coetzee, 1992: 248)。库切的意思已相当明了,小说结局落脚在礼拜五受到损害的身体,三百年过去,其遭受伤害的残缺身体依然拥有不容否认的权力,身体受伤害的印迹直面着美学上语言符号无休无止的漂移。
“礼拜五不能说话,但他并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礼拜五是身体。”库切自认他在小说中确立了一个“简单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身体。“无论身体是别的什么,身体并非是‘其所不是’,证据恰恰是身体所感受到的苦痛。”库切在访谈中再次重申,受伤的身体的权力不容否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原因,而是因为政治原因,因为权力的理由。“并非人们赋予受伤害的身体一种权威,而是受伤害的身体攫取了这种权力,那是它自己的权力。其权力不容否认。”(Coetzee, 1992: 248)(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无论就形式还是主题而论,第四章的元小说性已然显露无余。第二段叙述中,叙述者在昏暗的房间里,拧开黄铜铰链、打开储物箱,借着微弱的烛光读着一经触碰即散成半月形碎片的泛黄的稿纸:“亲爱的福先生:最后我再也划不动了。”(库切,2007:144)随即又接连两段以稍有不同的陈述句与文本首段回应:“叹了一声,我从船上滑进海里,勉强激起一点水花。”*见小说第155页(中译本第144、145页)上两段描写,又见小说第一段以及苏珊回忆自己在荒岛上面对面向克鲁叟讲述自己经历时结尾一段(第11页)。相似的重复还有第三、四章的首句(第113和153页)。这里库切一方面是对前文的回应式描述,引领读者回到前半部各章的叙述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暗示读者应该像采珠人一样深潜到文本的底层,去探寻历史叙述中沉默、招致伤害的他者身体的回声。叙述者摸索着抓着甲板,潜入礼拜五撒在海面的花瓣,曾被福先生称之为“故事之眼”的花瓣像雪花雨一样漂浮在海水深处,漂浮在“我”的四周。叙述者终于在横梁下方最后一个角落里找到半陷在泥沙里的礼拜五的身体,“我”“双手和膝盖都陷入在泥沙中”,触摸着礼拜五卷曲的头发、抚摸着他脖子上的铁链,想要和礼拜五对话。礼拜五依然没有回应。
但是,这儿不是词语的所在。每一个音节,一经说出口,就被海水侵蚀、消散。在这里,身体是其自身的符号。这里是礼拜五的家。(Coetzee, 1986: 157/146)
此处,身体不依赖于任何符号或者话语体系,它是“其自身的符号”,拥有正视符号无限制漂移的能力,即库切所说的正视其他符号“无终结性”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身体不依赖其他符号而赋予其自身的权力,使礼拜五的身体成为《福》这部文本唯一的尺度,也成为重写经典/历史以及“逆写帝国”之表征的标准,一种对抗斯皮瓦克所指责的把沉默的他者浪漫化和同质化的权力和标准。
小说结尾处,礼拜五终于张开了他一直紧闭着的嘴巴。“从他的身体里涌出一股舒缓的细流,没有间歇、无休无止。这股细流流经他的身体,向我直冲出来;它流过船舱,流过沉船的残骸;冲激着荒岛的峭壁和海岸,向南北两面散开,直至世界的尽头。柔软、冷冰冰、黑黝黝的,永无止歇,它拍打着我的眼帘、拍打着我的面庞。” (Coetzee, 1986: 157/147)礼拜五身体涌出的这股气息,舒缓却又如强劲有力,流经“船舱”“船体残骸”“悬崖峭壁”“荒岛沿岸”,一直到“世界的尽头”,它承载着礼拜五受到残损的身体印迹和记忆,承载着历史伤痕的记忆以及传统历史和文学叙述的缝隙,其不容否认的身体/主体权力从边缘流向同样“巨大的黑暗中心”*Peter Widdowson指出,最后一段是对康拉德《黑暗的心》的逆转暗示,表明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历史中“沉默的‘真实’故事仍有待书写”。Widdowson又指出沉默的礼拜五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只能寻求属于自己身体的声音、然后讲述自己的故事。见Peter Widdowson,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75页。该书已有中译,更名为《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敲打着每一个人的眼睛和面庞。
礼拜五的身体,这遭受到双重损害、既无法言说又丧失了生育能力的残损的身体,在历史书写中遭到压制、伤害而失语的身体,成为所有书写应该凝神倾听的“他者”形象。库切在文本结尾处发出一种诉求,让我们真正倾听历史书写中受伤害者的无语的“声音”,关注现代化和殖民化历史进程中处于社会底层、非西方的他者的苦难。正如福柯所论,历史书写的关键在于:谁在说话?礼拜五的身体成为各种宏大历史书写中了无痕迹的受伤害者的表征和符号。尽管礼拜五丧失了言说的权力和能力,尽管言说的希望仍然在于他能够学会那些加害于他的殖民者的语言,但是他受伤害的身体成为一种边缘者沉默的言说,成为历史书写的标准和尺度。礼拜五的身体在此也可视为一种吁求倾听他者的指令,倾听他者并让主体间的空间保持敞开的意愿构成了关怀他者的前提。这也是对于苏珊·巴顿面对为沉默的礼拜五表征时疑难的回应,历史的他者是如何被叙述和书写本身压制得无法呼吸。潜入历史书写档案堆积的沉默之海,接近历史的他者却不把他们置于我们叙述的特权、支配的话语中,去倾听我们或他们身上的他性,以一种倾听的心态和尺度开启、应答历史书写中对他者的责任。这样的吁求要求我们承担对于他者的“轻度关怀”,在揭示世界、叙述人类故事时承担对于他者的责任,呵护、培育他者,关注本哈碧波所说的他者“具体的历史、身份和感受——情感构成”(怀特,2004:123)。只有感受历史上这样一些个别的、特定的具体他者,接近、关切、呵护他者身体所固有的他性,我们才能意识到在拉近我们与他者之间距离时我们自身的限度,他者的身体正是人类有限性的见证,因而关注他者身上的差异性,避免把具体的他者纳入普遍化、同质化他者必然产生的宰制他者的危险,就成为抵抗的前提,抵抗为他者言说时宰制、支配他者的欲望,抵抗在接近他者时超越限度而表现出的“控制性姿态”。
库切并未表明不明身份的叙述者其实姓甚名谁,叙述者“我”显然承担着福柯所说的“作者功能”。“[作者功能]并非纯粹、简单地指向一个真实的个体,因为它同时催生多个自我(several selves),催生能够被多个个体之不同阶级占据的多个主体位置。”(Foucault, 2000: 182)福柯反对把作者视为与所有其他人不同的个体,“一开口说话,意义就开始增值并无限地泛滥”。对于他来讲:“作者是意识形态的象征,人们凭此标识出我们恐惧意义增值的姿态。”(Foucault, 2000: 186)福柯认为,所有的话语都与作者功能相关联,并拥有“自我的复指性”(plurality of self)(Foucault, 2000: 182)。他又指出,作者功能在真实作者与虚构的言说者之间的隙缝间,在这样分离和距离间实施、运作。
我们该如何称呼这里的这个“我”呢?这个“自我的复指性”,苏珊·巴顿、丹尼尔·福、丹尼尔·笛福、J. M. 库切,抑或我们自己,享受着西方殖民文化“福祉”的每一个文化的书写者和消费者,抑或不同于他们的库切小说的每一个读者,我更愿意把此处的“我”看成是作者库切对每一个读者的吁请,他吁请所有的读者能够像这个神秘、多重指意的“我”一样去沉潜在历史废墟竞相堆积的陈迹中,去发现、去聆听历史陈迹档案、历史叙述中那些沉默者无语的呐喊,那些有可能陷入永久性沉默的他者,那些不同肤色的礼拜五们;去发现沉默的他者处于被擦抹状态的踪迹,去倾听他们身体发出的如此强劲有力、一直“传到世界尽头”的“声音”。
克里斯蒂瓦(2009:265)曾经谈到文化是人类赖以存在的条件,但是人作为人之存在的前提在于我们“必须不停地破解它,就是说不停地批评和移动它……[他]不断地掀开司空见惯的事物的厚度,让沉默说话”。托妮·莫里森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里同样指出言说的语言霸权所隐含的知识暴力:“对语言系统的掠夺可以从使用它的人那里把它的细腻、复杂和助产士似的品格抛弃,而代之以威胁与压服的口气。压制性的语言不仅代表着暴力,它就是暴力;不仅代表着知识的局限,它制约了知识。”(莫里森,2006:354)所有的语言工作者,所有的言说者或代言人,知识分子、历史书写者、文学阐释者、文化批评家们,包括文学文本的读者,所要做的就是要不断地批评和移动文化以及历史话语形成的叠层,去除所有的常见(doxa)、偏见和定见,“掀开司空见惯的事物的厚度,让沉默说话”,让所有善良的礼拜五们用自己的声音,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开口言说,因为这是福柯所说的意义增值、无限泛滥的开端。最重要的,要摒弃寓含着知识暴力的“压制性语言”,因为这种语言是对语言系统本身的掠夺,阻遏了语言原本固有的繁复、多重关系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同时也制约了我们自我认知和历史认知本身。
参考文献:
B. Leitch, Vincent. 1999.NortonAnthologyofTheoryandCriticism[M]. New York : Norton.
Coetzee, J. M. 1992.DoublingthePoint:EssaysandInterviews[M]. David Attwell, e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etzee, J. M. 1986.Foe[M]. Harmondsworth: Penguin.
Foucault, Michel. 2000.“What Is An Author?”[G]∥ David Lodge and Niegel Wood.ModernCriticismandTheory:AReader. Essex: Longman.
Ray, Sangeeta. 2009.GayatriChakravortySpivak:InOtherWords[M].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Spivak, Gayatri.1999.ACritiqueofPostcolonialReason:TowardaHistoryoftheVanishingPresent[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Young, Robert.2003.Postcolonialism[M]. 南京:译林出版社.
哈贝马斯.2004.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克里斯蒂瓦.2009.反抗的意义和非意义[M]. 林晓,等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库切.2007.福[M].王敬慧,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罗钢,刘象愚.1999.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G].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斯蒂芬·怀特.2004.政治理论与后现代主义[M]. 孙曙光, 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托妮·莫里森.2006.宠儿[M]. 潘岳,雷格, 译. 海口:南海出版社.
责任编校:冯革
Silence and Speech: Coetzee’sFoeand A Critique of the Postcolonial
JIANGXiaowei
Abstract:J. M. Coetzee’s novel Foe has become a postmodern and postcolonial canon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for “writing back to the empire”. By reading Coetzee’s novel,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erpret Gayatari Chakrovorty Spivak’s critiques of postcolonial reason, of the implied discursive power used by western intelligentsia when speaking for the other. Through intertextu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Spivak’s theoretical text and Coetzee’s Fo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of self and other in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 and of narrative and speech in the western history of modernity, arguing that the intellectual elite, the historians and writers should take their social, political and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when facing the woundeed bodies, the unforgettable historical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s of the Fridays whose tongues were cut by the epistemic violence of the western knowledge-power.
Key words:J. M. Coetzee; Foe; other; silence; narrative and speech
作者简介:姜小卫,男,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现代主体的退隐与重构:德里罗研究”(14XWW006)前期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12-06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6)02-003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