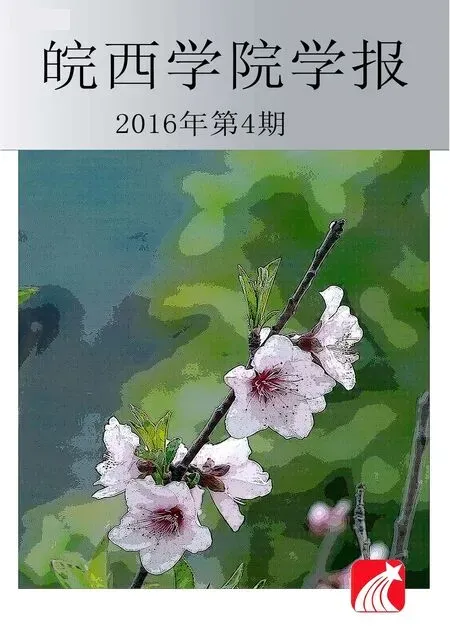从《尚书》看中国古代循吏的思想基础
2016-03-17汪千霞武建国
汪千霞,武建国
(皖西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从《尚书》看中国古代循吏的思想基础
汪千霞,武建国
(皖西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中国古代循吏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应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从《尚书》的视角看中国古代循吏的思想基础,主要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德治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以及“崇善抑恶”,爱憎分明的价值评价观。研究中国古代循吏的思想基础,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吸取思想营养,保持和发扬尧、舜、禹以来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加强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从思想深处防止腐败。
中国古代循吏;《尚书》;思想基础;德治;民本
中国古代典籍,特别是儒家经典,是中国古代循吏的思想文化基础。从汉武帝时代始,《尚书》就归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五经”之一。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献资料汇编,保存了尧、舜、禹、商、周时期的重要文献。但由于当时保管的条件差,秦始皇焚书坑儒,秦汉之间兵火浩劫等原因,其中不少文献散失或残缺不全,故此带来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他说“《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1](P19)故此他对《尚书》未作史料引证。郭沫若说:对于《尚书》,“我们早已知道有今古之别,古文是晋人的伪作,但在今文的二十八篇里面也有真伪,也是近年来才开始注意到的。例如《尧典》(包括古文的《舜典》)、《皋陶谟》(包括古文的《益稷》)、《禹贡》、《洪范》这几篇很堂皇的文字,其实都是战国时代的东西——我认为当作于子思之徒。”[2](P4)郭老把《尚书》视为迷宫,并且庆幸自己没有陷入这座“迷宫”。冯友兰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有别于胡适、郭沫若,他大胆探索了“孔子以前及同时之宗教的哲学思想”,他说:“孔子以前,无私人著作,今搜集《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说,足以代表孔子以前及其同时之宗教的、哲学的思想者,以见孔子以前及其同时人智之大概。”[3](P28)冯友兰在研究上古哲学思想时,大胆引用了《尚书》,肯定了《尚书》的思想价值。笔者认为《尚书》影响中国历史文化3000多年,长期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教科书,即使有些地方文字有变化、有出入,但我们可以把《尚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整体的视角认识《尚书》对中国古代循吏的教化作用。具体来说,《尚书》作为中国古代循吏的思想基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重视道德对人的教化作用和对国家的治理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就是一部道德教化史。《尚书》作为中国哲学的源头之一,“德”是全书重要的范畴,它对尧、舜、禹、皋陶、周公高尚的道德情操予以赞赏,为人的发展提供榜样,对中华民族国民性的培养和中国古代循吏的人格塑造,提供了廉德思想论证,充分说明了以《尚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典籍是中国古代循吏的思想文化基础。
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4](P13)。帝舜“玄德升闻,乃命以位”[4](P24)。帝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4](P47)。他们的成功都离不开一个德字。尧、舜、禹道德高尚,德泽下降于民,所以民众才相信他们,归附他们,歌颂他们。皋陶主张“允迪厥德,谟明弼谐”[4](P55)。即君主只有诚信地遵守仁德,才能谋划英明,君臣和谐。皋陶把“九德”作为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九德”就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4](P57)做人既要宽厚又要谨慎,既要柔和又要有主见,既要忠厚又要庄重,既要干练又要严肃,既要温顺又要刚毅,既要耿直又要和气,既要简朴又要廉洁,既要刚正又要求实,既要顽强又要合乎道义。“九德”是皋陶向舜帝提出的选任官吏的九条标准,其中把简朴和廉洁作为对官员的要求,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我们可以说廉政文化从皋陶时期就明确地提出来了。
“人无廉耻,百事可为。”一般的人不讲道德,就会什么坏事丑事也做得出来,这样的人必然成为害群之马。而掌握一定生杀大权的官吏如果不讲道德,其危害性更大。“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4](P116)官员不廉洁,贪污无度,不讲道德,就像大火燃烧在昆山之上,美玉美石都会被烧毁,他们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的灾难,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严格地说官员缺德甚至比猛火更惨烈,更能破坏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和影响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更能毁弃人间美好的东西。夏桀制酷刑施暴政,“灭德作威”,违背天道,祸害人间。天道是什么呢?“天道福善祸淫”[4](P136)天道是给善良的人以幸福,给作恶的人以灾难的东西。夏桀违背天道,恶贯满盈,终于为成汤所灭。成汤把夏桀的暴政概括为“三风十愆”,从思想上对夏桀的所为进行了总结和批评。“三风”指巫风、淫风、乱风。巫风是“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淫风是“殉于货色,恒于游畋”;乱风是“侮圣言,逆忠直”。“十愆”指十种错误,即恒舞、酣歌、贪财、好色、恒游玩、恒田猎、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4](P158)任何人都不可自作孽,卿大夫自作孽,他的封地就会消亡;诸侯自作孽,他的国家就会灭亡。“天佑于一德”[4](P166)只有保持纯一的德性,才能兴旺发达,才能免遭灭亡之命运。
商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斫朝涉之胫,削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4](P245)周武王针锋相对,“树德务兹,降恶务本”,打败了商纣王。武王灭殷后,声望大增,有西方国家献上巨犬,为此召公说:“玩人丧德,玩物丧志。”[4](P284)要求周武王不贵异物贱用物,不作有害无益之事。周公执政,反复强调“勤用明德”、“王惟德用”、“敬德保民”。成王成人,周公归政于成王,成王继续坚持德治方针。成王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4](P406)皇天只亲近那些有德性的人或君主,为善者治,为恶者乱。尧帝、舜帝、周公的德治思想不仅影响了成王,而且构成了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对未来中国哲学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讲仁,孟子讲仁政。《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4](P47)宋明理学家称为“十六字心诀”。理学家认为,世上人心险恶,令人难以度测,只有道心是精微、纯洁的,应信守中道,用道心主宰人心,不使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用纯正、精微的道心主宰人心,人心才能转危为安,达到“中”的状态。
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不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国古代思想家不可能明确地提出这样的观点,但有许多重民思想,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聪自我民聪,天视自我民视”等许多具有民主性因素的命题,这些具有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因素,值得我们予以总结。中国古代的循吏,为什么一直为人民传颂,其重要根源之一就是他们心中有人民,他们洁己爱民,关心民间疾苦,视贪腐为民贼。爱民、忧民、畏民、安民思想是理解中国古代循吏的一条思想红线,这一思想传统,在《尚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皋陶和夏禹讨论怎样治理国家,皋陶提出治理国家在于“知人安民”,禹表示赞同,并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4](P56)“哲”是明哲、明智、智慧,就是知人善任,会用干部,会安抚民众。皋陶进一步提出“天聪自我民聪,天畏自我民畏”的命题。上天和下民是相通的,下民的要求和愿望就是上天的意志,老百姓就是官吏头上的天。夏王朝的第三代国君太康即位后一味田猎,不理朝政,不恤民情,人民怨恨他。他的五个弟弟对他的行为表示谴责,作“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4](P107)民众可以亲近但不可轻视,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国家才会安宁。面对千千万万的民众,君主内心应充满畏惧,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驭六匹马一样,坐在车上的人稍一懈怠,就会车毁人亡。
盘庚是商代第二十位君主,盘庚为什么要把都城由山东曲阜迁往河南安阳,理由是“重我民,无尽刘”,重视人民,不让老百姓受伤害,死在原地。“施实德于民”,“视民利用迁”,迁都是顺应民意,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历史证明,盘庚迁都的决定是正确的,有利于百姓的生存和发展。盘庚迁都后,给商朝带来了生机,此后三百年商朝再未迁徙,促进了中原地区的发展。
周武王会诸侯于孟津,在誓师大会上发表了声讨纣王的誓词,他打的是替民伐罪的旗号:“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4](P233)“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4](P236)“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4](P242)小邦周本来不敢取替大殷商的统治,但又没有办法,原因是商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讨伐商纣王的战争是顺天应民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周朝将士同仇敌忾,奋勇争先;商朝战士无斗志,临阵倒戈。商朝灭亡是天的意志体现,是人民的愿望,是不能逆转的趋势。
周公旦相信“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4](P334)。即官员不要以水为镜子来察照自己,而应以民众为镜子来察照自己,想一想人民需要什么,人民答应不答应。武王死后,周公辅佐成王,平定武庚、管叔、蔡叔之乱,为周朝经济的恢复、社会的稳定作出了贡献。周公还政于成王后担心成王贪图安逸,一再提醒成王“知稼穑之艰难”,“能保惠于庶民”,“怀保小民”,“咸和万民”,即只有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上,懂得老百姓生活之艰难,让老百姓有一个安定平和的生活环境,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
历史上有作为的君主、贤臣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或多或少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总是为民做主,为民造福,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一思想资源是十分宝贵的。
三、崇善抑恶,爱憎分明
作为一名官员爱什么,恨什么;学习谁,反对谁;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实际上是一个价值评价问题。价值评价是价值主体在对价值事实认识的基础上,借助一定的评价标准,对人和事所作的肯定或否定、赞同或反对、亲近或排斥的态度。在价值评价上价值评价标准是一个关键问题,评价标准出现问题,就会使人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好坏不明。《尚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其标准是崇善抑恶、爱憎分明,歌颂为人民作出了贡献的尧、舜、禹、皋陶、周公、成王等历史人物,贬斥祸国殃民的丹朱、夏桀、商纣,有助于官员正确地认识历史人物的价值。作为一名循吏,就是要像尧、舜、禹、汤那样做人做事,力争成为圣人,而不要像丹朱、夏桀、商纣那样,成为万人唾弃的人。
尧、舜、禹是中国人民心中的英雄,他们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广泛爱戴,是历代清官良吏的楷模。帝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4](P13)帝尧治理国家政事严谨,仪态温和宽厚、诚信、恭谨。协和万邦,使各部落共同发展,为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帝尧死后,“百姓如丧考妣”,反映老百姓对他有深厚的感情。帝舜“睿哲文明,温恭允塞”[4](P24)。他深沉而又智慧,为人光明磊落,温和谦恭,诚实守信。帝舜的父亲是一个瞎子,后妈对他尖酸刻薄,弟弟象对他傲慢骄横,而舜以仁爱之心与他们和睦相处。帝舜谨慎地遵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伦理规范,把对家人的爱推广到整个社会,对国家大事管理得井井有条,故此尧帝把帝位传给了他。大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5](P17-18)禹把全国分为九州,对九条大河进行疏理,不畏劳苦,身先士卒,风餐露宿,三过家门而不入,为中华民族山川大河的治理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丹朱、夏桀、商纣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乱臣贼子,他们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历史上反面人物的典型。丹朱是帝尧之子,“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4](P70)。丹朱傲慢无礼,戏虐胡为,懒惰游乐,不管白天黑夜都作恶不止。洪水退了,他坐在船上迫使民众推舟。成群结伙在家淫乱,因此帝尧没有把帝位传给他。夏桀是夏王朝的最后一名君主,“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4](P123)夏桀昏乱败德,酷虐百姓,加重赋敛,生灵涂炭,人们对他恨之入骨,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消失,我们愿意同你一起灭亡。”商纣王“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百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4](P233)商纣王奢侈残暴,沉于酒色,宠信妲己、剖比干之心,刳孕妇之腹,将人杀死晒成肉干。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追逐,为长夜之饮。纣王无道,招致了天下人的反抗。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谁善谁恶,谁好谁坏,爱谁恨谁,其标准是十分清楚的。人们学有目标,赶有方向,恨有对象,文化导向鲜明,使读书人价值评价标准明确。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循吏如包公、海瑞嫉恶如仇、奉法循理、刚正不阿的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一脉相承的道统。中国古代形成了一个崇善抑恶、爱憎分明的历史文化传承系统,这个系统始于尧、舜、禹。
[1]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2]郭沫若.郭沫若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4]尚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5]夏松凉,李敏.史记今注[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On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Upright Offici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ngshu”, the Book of History
WANG Qianxia, WU Jianguo
(WestAnhuiUniversity,Lu’an237012,China)
The existence of ancient Chinese upright officials is not accidental but the result of profound social, historic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ngshu”,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upright officials in ancient China mainly lies in the ideology of ruling the county with virtue like “the God being just and unselfish and helping people with virtu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of “the people be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serving its people”, and values of “upholding kindness against evilness and being clear about what to love or hate”. Exploring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upright officials helps to learn ideological merits from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maintain and develop the excell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since the era of ancient emperors of Yao, Shun and Yu,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of current officials, and therefore prevent corruption from the depths of minds.
ancient Chinese upright officials; “Shangshu”; ideological foundation; ruling with virtue; people-oriented
2015-10-18
皖西学院校级项目(WXSK201628)。
汪千霞(1986-),女,安徽六安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武建国(1978-),男,湖北荆州人,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K207
A
1009-9735(2016)04-0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