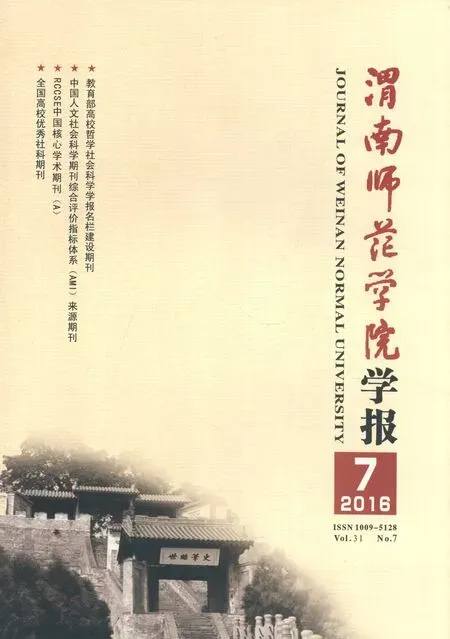非遗保护区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教育人类学研究
——以马洒壮族传统文化保护区为例
2016-03-17郑雪松
郑 雪 松
(信阳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信阳464000)
非遗保护区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教育人类学研究
——以马洒壮族传统文化保护区为例
郑 雪 松
(信阳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信阳464000)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经过价值衡量后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马洒壮族村之所以成为传统文化保护区,与马洒壮民历来比较重视教育和本民族文化传承有关。在马洒文化400多年的历史中,干栏技术、手工技能、马洒侬人古乐演奏等富有特色的壮族传统文化得以很好的保护和传承,为马洒壮族村寨成为传统文化非遗保护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教育人类学者的观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顺利开展有赖于一定自然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和规范生态环境等。在这个生态环境中,民族文化是教育的主要内容,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非遗保护区;马洒壮族;传统文化;教育人类学
随着《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下发和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在北京的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相关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起始于2004年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介绍,渐渐涉及民族宗教、祭祀文化、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等。但目前关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方面的研究还不算多。人类学学科的一大特色便是进行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教育人类学是较长时间对田野点的人、文化、教育及其相互关系等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笔者10年前为完成硕士论文第一次到云南马洒壮族村,至今仍在继续田野点的教育与文化研究工作。
一、马洒壮族传统文化非遗保护区概况
马洒村除几户汉族外,近300户皆为壮族(侬支系),当地自称“布侬”也称“侬人”。村寨建于明末清初,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但仍保留着传统的仓储、采集、渔猎等工具和传统的耕作农具等。壮族独居特色的节日文化、干栏式建筑和古代的寨老制传统仍在马洒村传承,壮族祭招性丧葬舞蹈纸马舞也仍流传在马洒壮族村,并发展成群众性娱乐舞蹈,是壮民族文化保存比较完好的形式。
马洒壮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于2009年8月被公布为云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之一,列入保护名录的马洒壮族传统文化保护区,专项保护规划范围、规划面积、规划原则及具体的保护对象等更加明确,不仅为使其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提供了强有力支撑,而且符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名录的要求。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需要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和明确的有关保护责任主体。马洒壮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该村的稻作和采集等传统农业、原始森林、神树、神山、龙潭、家神、山神庙及壮族传统文化习俗等均得到更好的保护和教育传承,老人厅和传统的干栏建筑也加以修复。
二、马洒壮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传承
马洒壮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主要靠老人口传身教流传下来,老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向晚辈传递干栏技术、手工技能、马洒侬人古乐演奏等方面的知识。
(一)干栏技术的掌握
传统的壮族民居一般以干栏建筑为主,云南壮族民居也不例外,至今一些地区民居仍保留着传统建筑和聚落格局。杨宗亮研究员认为:“近现代云南壮族民居主要存在3种建筑形式,即传统纯木结构的干栏建筑,又叫吊脚楼或麻栏;土木结构的干栏建筑;土木结构的汉式二层楼房。”[1]310传统文化保存比较完好的马洒壮族村,独具特色的干栏式和半干栏式建筑民居是其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的重要条件之一。但随着各民族的互相交往,特别是马洒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砖木和砖混结构建筑的民居也在增加。
传统文化背景下,马洒壮人都亲自建自己的房子,所以要向长辈学会怎样建房子。到了开工的吉日,青少年和自己的父亲一道燃好香烛,杯里倒好酒,摆好祭品祭祖先,对祖宗叩首三次,让他们保佑。仪式完毕后,建造房子的工作真正开始了。青少年和大家一起把房子框架所用的木头、木方全部刨光。上房梁时只选那些父母健在、妻儿齐全的人上房梁,据说这样才会家庭幸福安康、人财两旺。在上房梁之前,房主人家准备好一些糍粑。房梁上好后,房梁两端的人就把装在篮子里的糍粑吊上来,然后向下扔。很多孩子就去争抢那些糍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无偿的美味小吃,而对于大人们来说,就意味天上掉下了银圆。这寄托着马洒壮民的美好愿望。伴随着房子的建成,马洒壮族青少年对怎样建壮族民房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二)手工技能的获得
马洒刺绣盛行于民国时期,以红、黄、蓝、靛、紫、白、黑花线等为主要材料,按照自然景物色调绣出。刺绣与其他织物一样,是马洒女童必须掌握的手工技能。她们自幼就向女性长辈,母亲、同辈中的姐姐和嫂子等学习刺绣和编织,喜欢把她们绣制出来的图案佩戴在身上。马洒壮族姑娘除了喜欢在头帕、围腰、飘带、枕头套、被面或者送给心上人的礼品上绣出千姿百态的壮族民间图案,更重要的是要学会织壮锦。她们一般懂得壮锦织法大致有三:一是各种曲线型或方线型图案;二是鸟、兽、虫、鱼、花卉图案;三是金条折曲镶嵌点缀图案。姑娘到了八九岁时,由旁观和学习女性长辈或同辈刺绣及编织到开始拿针线亲身实践了,刚开始做一些简单的边角。马洒女性在编织方面以编织荷包和捞虾网较出色,六七岁的女孩会被告诉将葛藤放进沸水中煮后去皮,抽出内白皮丝撵积成长线,编成荷包和虾网,具有经久耐用、着水不腐、洁白、美观等优点。走向生活期女性对刺绣和编织的一般知识都应掌握,也就是到了十七八岁就应“出师”了,不然会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马洒壮民用的布和衣服都是自己编织和缝纫的。按马洒壮民的族规,女孩在出嫁前要学会种棉、养棉、收棉、纺棉、织布和缝纫等一套系统、完整的知识。若到出嫁了还未能掌握这些知识,特别是纺棉、织布和缝纫等方面的知识技能,母亲要送教到女儿婆家。新媳妇农闲时也可跟婆婆学,但会使自己的母亲显得没面子。
以男性为对象的手工业知识的习得,刚开始主要是以同一家族的后代为传授对象,后来高、王、田、李有互通婚姻现象,所以几大家族就有互相传授的可能了。雕刻方面有木雕和石雕两种,以浮雕和镂空较为出奇,打制花窗、橱柜非常精致,这些多为子承父业。
由此看来,马洒壮族的手工业虽有明显的性别角色分工,但都以观赏和实用相结合,做工复杂而精细。
(三)侬人古乐的熏陶
马洒儿童成长于古老悠扬的侬人古乐之中,马洒侬人古乐壮语为“恒宁曼侬马洒”,据相关人员考证已有200多年历史,乐器类有民间打击乐、击弦乐器、笛类、胡琴类等。每两年或一些特殊活动(二月求雨或六月消灾等)要诵读道教的《文昌大洞仙经》和《观音大洞经》,常伴有佛腔调,《满江红》《柳叶青》《浪淘沙》和《透碧霄》等也包含在曲目中,充分体现了马洒侬人古乐融合了儒学、佛教和道教文化传统及壮族民间巫卜信仰等。
侬人古乐和民间舞蹈纸马舞是马洒传统文化中最富有影响的,侬人古乐的传承与马洒壮民丰富的信仰及对本民族文化的信念追求是分不开的。 “早在乾隆年间,居住于此的马洒人就掌握了洞经二十四调和六个外调的演奏技艺,并于光绪九年(1883)成立了洞经古乐演奏班子。直至今日,马洒洞经会已发展成一个主要由马洒退休返乡干部和村民20多人组成的侬人古乐团,规模不断发展壮大。”[2]马洒侬人古乐团逐渐成为传承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壮族侬人文化的乐团,乐团主要传承人是高天眷、王世堂等,高天眷的儿子和儿媳妇都是乐队的成员。在高天眷、王世堂等人的带领下,马洒侬人古乐团在马洒村演奏,而且曾应邀参加过县壮学会组织的“三月三歌节”文艺演出和文山州首届民族民间器乐展比赛等。
侬人古乐是马洒村壮族侬人特有的一种传统音乐。马洒壮民自小浸润于侬人古乐之中,耳濡目染了古乐器的演奏,自然会萌发关于侬人古乐的感性认识。
(四)“追孝”教育的深化
随着儒学教育在马洒村的确立,壮民们进行续族谱、立牌位、建宗祠等文化创建活动,在伦理观念方面逐渐接受儒家道德思想,形成了“对父母孝,对叔婶尊,对兄弟仁,对妯娌爱,对邻居善”等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自觉意识和规范,但仍较偏重于进行本民族传统道德规范教育,特别是对老人和长辈的“孝”,即对生者所尽的“孝”为“生孝”。无论“生孝” 还是“追孝”都是马洒壮民历来所追崇的。
“追孝”实际上是“生孝”的延续和扩展,父母长辈去世后,走向生活期的孩子不仅仅是参与,更重要的是要负责请“卜么”“师公”等为已去世的人超度。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奠基者爱德华·泰勒认为:“宗教仪式在理论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具有重要造型的或象征的意义,是宗教思想的戏剧性表现或宗教的哑剧语言。一部分则是跟灵物交际的手段或影响它们的手段。”[3]797通过“跟灵物交际的手段或影响它们的手段”渗透人心,给在场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
据调查所知,马洒壮族办丧事有两种情况:田氏、李氏家族一般要请师公做道场,一是为死者超度亡魂;二是为死者歌功颂德,其法有献酒献食、招魂、告别、送行、追思往古。高、王两姓兴念三教济度亡经,富裕人家要念超亡大洞经。无论哪种情况,当“灵魂桥”(似桥形,里面放一个圆糍粑和灵牌位。由两长孝子抬着,“卜么”手持长刀,端一碗水,以越刀山火海之势)从场上抬送到棺前时,众孝子在棺前团团围跪,每人伸出一只手,用手指顶住筛子。筛子里排列三只酒杯,三双筷子。这就是马洒壮民传承的接灵魂下桥入棺的“郎坝局”仪式。“郎坝局”除了仪式,还有对“感恩”的诉说。“‘郎坝局’的‘感恩’部分主要诉说父母生儿育女的千辛万苦和持家的艰难,作为子女要永远牢记,并以父母为榜样养育好下一代。如‘夜洗尿数起,日洗尿数次。日累日儿长,月累月成人’等。”[4]深夜,子女要请人为死者举行“堂祭”,即丧葬的第三个仪式。第三个仪式由“卜么”主持,道师呼《哀思苦》。《哀思苦》共三章,首章借“大舜耕田”“文帝尝药”“大禹筑河”“文王寝门”“武王味饭”“周公代疾”等为父母尽孝的多种方式,引发在场子女向“父母”尽孝。在举行“灵魂桥”“郎坝局”和“堂祭”等仪式活动的过程中,全家男女老少都在场,后代在“跟灵物交际的手段或影响它们的手段”的感召下,便会萌生和增强孝顺老人之念,整个丧葬仪式使在场的后代子孙领略孝道之重要。
马洒壮族晚辈除了通过各种方式向长辈学习干栏技术、手工技能、马洒侬人古乐的演奏技巧和向长辈尽孝之外,马洒壮族先民还擅长“铜鼓舞”“牛头舞”“纸马舞”;“虎围棋”“圆围棋”“抓七子”;银器制作、泥塑、绘画(国画);刺绣、壮锦、蜡染;抛绣球、打磨秋、轱辘秋、玩陀螺等,这些传统对后代子孙影响颇深。既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发展和技能养成,也有利于民族文化传承的活动,应该进入马洒壮族校园,以利更好地促进教育和文化传承。
三、非遗保护区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教育人类学解读
按照教育人类学的逻辑:“民族是由其成员通过共同持有的文化得以维系的,文化则是通过教育得以传播的,而民族的文化和教育都产生并植根于特定的生态环境。”“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知识和文化的传授使人类能更有效地适应和利用生态环境。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通过教育来传递,就会逐渐被削弱,从而使该民族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降低,为其生存和发展带来直接或间接的损害。”[5]73民族文化传承和教育互为手段,相互联系,不可或缺,二者的顺利进行有赖于一定的生态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生态环境也不外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规范生态环境。
(一)非遗保护区马洒壮族传统文化教育传承的自然生态环境
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自然生态环境(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是指存在于该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周围的对其保护和教育传承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地质、地貌、森林、植被、地理位置和气候等天然形成的物质和能量的总体。地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之一,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们,遵循这一地域的生态变化规律,并传承和孕育着生态神话。一定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生态环境的影响,而是在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生成发展,并深深烙下相关印记。
壮族人喜爱大自然,禁止乱砍滥伐。马洒壮族村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不仅拥有悠久的壮族文化传统,而且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村庄依山而建,山中流淌着一条小河,山脚下和村子周围是纵横交错的耕地和梯田,山上仍保留原始森林。大片原始森林的留存和森林高覆盖率的拥有使马洒壮民敬树、敬山等。神树、神山、龙潭、家神、山神庙等成为马洒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的物质空间载体,此外,还在传承二月祭祀的传统,东村祭牛王庙、南村祭土地庙、西村祭龙山、北村祭龙王庙。
每个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的具体条件和环境基础上的,就某种程度而言受制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其保护和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教育生态环境。教育人类学者认为,人既是社会的产物,也是自然的产物。人是在与自然和社会环境构成的复杂系统中身心得以发展,人、文化及人与其生存的生态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互动是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出发点。
(二)非遗保护区马洒壮族传统文化教育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
文化生态环境(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是人化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人和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综合体。就民族文化传承与变异而言,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应有原生态文化环境和再生文化生态环境之别。一个民族的原生态文化环境是指较为依赖自然环境的处于萌芽期的文化环境,仍保留着自然环境的烙印。随着文化生态环境人文因素的增加,对自然环境依赖渐渐减少,原生态文化环境就走向了再生文化生态环境。正如,人的自然属性是基础,作为人的根本属性的社会属性制约着自然属性。同样,原生文化生态环境是再生文化生态环境的基础,而再生文化生态环境是影响极其深远的文化生态环境。
马洒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取决于壮族原生文化生态环境,即马洒村寨特有的壮民族地域特色,而且与其再生文化生态环境,即本村寨壮民世代注重文化教育有关。对教育的重视为马洒壮族传统文化传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使马洒壮族村寨至今仍保留着有别于其他民族村寨明显标志的老人厅。“马洒老人厅始建于清道光十一年,木质结构,内立神位碑、功德碑、遐稽碑、进士匾等,是村寨集体祭祀和聚会议事的场所。每逢正月初二、二月初二、三月三、六一花饭节,长老就到厅内聚会议事,杀鸡、杀鸭,献上刀头(猪肉),摆酒点香供奉神农氏,祈求全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随着时代变迁,如今的老人厅仍然是祭祀、安排重要事项的场所,但更大的意义是对村民行为的约束,是一种历史的承载。
从明末到清康熙年间,先后有李、高、王、田四个姓氏的先祖迁到马洒居住,形成了马洒如今的四个主要姓氏。四大姓,特别是高家和王家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在周边较有影响的文人武士。改革开放以来,他们认识到知识与经济的关系,更加重视教育,并于1995年发起兴建马洒文史宝塔, 在塔周围刻上壮民祖先定居马洒的简史、壮民功德和在外工作人员名单,以激励和教育后代。
尽管马洒壮民向来重视教育,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马洒壮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受到的冲击不仅仅来自学校传授的汉文化课程,更多是周边的信息环境。信息环境为马洒壮族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其传承带来挑战。文化传承受到冲击,人的培养和教育的发展同样受到影响。“教育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机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教育都是某种文化的教育,任何文化也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文化。因此,任何教育,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教育。”[6]5这与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关于“文化以使人格深深地改变”[7]83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政府的重视和规范化管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至关重要。
(三)非遗保护区马洒壮族传统文化教育传承的规范生态环境
规范生态环境(Criter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是人类为了满足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及其人类自身发展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的规范生态环境主要指国家、地方等行政部门制定的相关保护和传承政策法规及村规民俗等内容。
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就起草和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文件,如1982年全国人大颁布了《文物保护法》、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等,特别是2011年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开端。
为了规范和监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2013年2 月23 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指导制定并通过了《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该《条例》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
2009年8月26日,马洒壮族传统文化保护区、么所壮族传统文化保护区、以口夸村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等29个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云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从此,马洒壮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受到更加规范的管理,不仅有明确的规划期限和阶段划分,而且保护和传承的对象比较具体,整个规划体系相对完整。
从国家到云南省、文山州和马洒壮族村寨的整个社会生态系统都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马洒壮族传统文化保护区保护工作的开展。但原生“非遗”生存环境已遭受重大冲击,非遗保护区的规范生态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和加强。
马洒壮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之所以能被誉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因为其拥有悠久的历史、鲜明的地域特色、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完整的规划体系。这四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部分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整个生态系统的核心,是保证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区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传承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 杨宗亮.壮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2] 罗彩娟.马洒侬人古乐的传承与发展探析[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4-18.
[3]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4] 郑雪松.壮族丧葬习俗的教育人类学分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8):73-76.
[5] 王军.文化传承与教育选择[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6] 哈经雄,滕星.民族教育学通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7] [英]马凌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刘蓉】
Study on the Education Heritage of the Ethnic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Intangible Heritage Conservation——Tak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Zhuang Nationality in Masa as an Example
ZHENG Xue-s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ess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whose value has been evaluated and measured. The main reason of Masa Zhuang Village being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zone is that Zhuang nationality in Mas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Zhuang nationality is relatively preserved better. In 400 years, the technique of the pile dwelling, manual skills, Masa Nong people’s ancient music and so on, are well protected and inherited. These have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Masa Zhuang Village being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zone abou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nthropologists on education,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eing inherited by teaching depends on certain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riter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nder thi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national excellent culture is the main content of education, education is the important means of the inheritance of ethnic culture.
Key words:Protection Zone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Zhuang Nationality in Masa;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中图分类号:G122;I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5128(2016)07-0048-05
项目基金: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河南沈丘回族文狮舞传承的教育人类学研究(2015BJY004)
作者简介:郑雪松(1967—),女,河南固始人,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民族文化与教育、教育人类学研究。
【社会与法律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