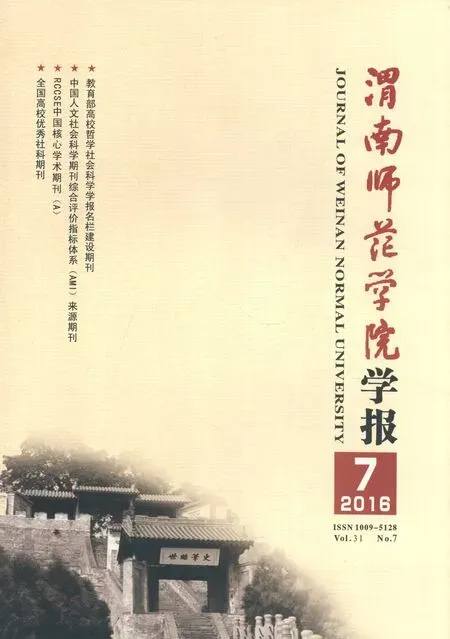管虎“狂欢三部曲”的主题和风格表达
2016-03-17尹晓利
尹 晓 利
(渭南师范学院 莫斯科艺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艺术研究】
管虎“狂欢三部曲”的主题和风格表达
尹 晓 利
(渭南师范学院 莫斯科艺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摘要:《斗牛》《杀生》《厨子戏子痞子》,因其有着相同的叙事风格被视为管虎导演的“狂欢三部曲”,三部曲除沿袭了导演一贯的风格:娱乐元素的多重拼贴、夸张荒诞的影像狂欢与隐喻离奇的意义表征外,在主题表达上形成了一种介于寻找与坚守、自省与批判、个体与群体、暴烈狂躁与悲情绝望的情绪之间的笔调,在风格表达上形成了一种介于荒诞与写实、魔幻与原生态之间的整体隐喻和寓言表达。
关键词:管虎;狂欢三部曲;主题;风格
作为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的管虎,有着很强的实践倾向和人文关怀,作品往往聚焦社会现实,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起伏。其第一部影片《头发乱了》涉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影片关注边缘人群的特征非常明显。其后,管虎导演的作品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比较深远,往往对世俗神话进行解构和批判。在《斗牛》《杀生》和《厨子痞子和戏子》,难以寻到正面权威的英雄形象,代之以逆历史潮流而上的普通人群的生存状态。三部曲中,故事背景都设置在抗日战争时期,人物塑造多选择普通人,甚至是草根人物并以一种反英雄形象示人,叙事策略都放弃了传统的线性叙事,取而代之以多线叙事展开情节,时空表达复杂、自由切换得心应手。从而使得三部曲整体变得复杂和富有回味余地,生发出一种间离化和陌生化的效果。
一、深沉悲情的主题延续
如果去掉这种狂欢荒诞的外壳,三部曲裹挟着管虎对生命、社会、生存、文化、价值、理想的深切思索,在他的影像世界中,即便是最卑微的个体也会被刻上叛逆的标签,用肆意挥洒的人生进行着含蓄内敛的寻找和坚守,以此反抗主流社会的木然和冷漠,影片巧妙地将社会、个人的价值体系糅合在一起,完成了一个民族的自省和批判,流露出作者对生命本身酣畅淋漓的至高礼赞。
(一)寻找与坚守的执着
“寻找”和“坚守”是管虎电影的两大主题元素。《斗牛》用小人物牛二的视角展现出一个另类的战争,一个彻头彻尾的浑身充满缺点的小农民,却在战争中不断挑战着自身的懦弱,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日本兵、难民、土匪等各色人物周旋,以其对八路牛苦苦守候数年的执着,守着一份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承诺,支撑他的是他心里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与坚守相关。《杀生》是一个悲情故事,设计生与死的重大命题,表面看似在寻找一个杀人的真相,内在的是在寻求一种精神之根,而村民联合起来要杀牛结实这个人,其实是有某种断根的暗示。[1]《厨子戏子痞子》故事从始至终都在寻找一种名为“虎烈拉”的病毒,而在《斗牛》《杀生》中被推到背景里的抗日抗争在这里被作为主体叙事情节显于观众面前,随着剧情的发展,一开始几个被刻意塑造为“丑”的角色摇身一变为抗战英雄,在敌我生死对峙中完成了对革命信仰的坚守。三部影片中,所谓的寻找和坚守,都是以牺牲个体价值为代价换来集体价值的实现,无论主动与被动,都流露着浓浓的悲情色彩。
(二)自省与批判的深思
《斗牛》中牛二的坚守最终等来了战争的胜利,在宏大的战争背景下,个体被怂恿去干一件特别高尚的事情,但是那个所谓的特别高尚的历史目标往往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个体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个人的价值被革命的洪流所淹没,荒诞的大历史与个体生命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对等,牛二在那座山上刻写着个人价值的时代烙印。《杀生》在一个封闭、神秘又让人敬畏的羌族小寨里,牛结实不断上演着与长寿镇的对抗,一个重生,一个重死,二者不断地发生着冲突与对抗。影片里这个封闭的集体空间是整个社会的缩影,集体与个体的对抗使观众很容易了解其中封建与反封建、传统与反传统、个体自由和集体压制的宏观隐喻,从而使电影有了国民性、民族性批判的成分。[2]影片里众村民设计杀害他们心中的异类牛结实的情节延续了自《党同伐异》到《血色清晨》的消灭异己的主题,只是《杀生》选择了远离生活、远离现实的近乎架空的历史展开了疯狂的叙事,这种疯狂跟库斯塔利卡的《地下》很像,同样触及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这是需要自省的,同时也是需要勇气的。
抗日故事汗牛充栋,为抗战叙事提供了广阔的题材,“抗日神剧”更是比比皆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抗战作为媒介事件,再现的共同信仰似乎只是出于民族利益而刻画得大快人心的复仇情结,却远远背离中国人的当下生活。《厨子戏子痞子》近乎闹剧般的戏谑,形式上似与以往的“抗日神剧”无二,但是“从小学开始,学生们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会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到那段历史的血腥,但是由于这段被侵略的历史叙事是与其他同时代课题分离的,所以,在大陆中国的思想空间里,日本的侵略历史与中国人面对的其他现实课题之间的联系是不清晰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并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进时代状况中去,它似乎游离于其他讨论和思考,也无法形成一个冲突和论争的场域。当仇恨与正义感孤立于其他思想课题的时候,它无法避免抽象化和简化,因而也就无法避免被遗忘的命运”[3]135。所以在精神内核上,尤其是面对民族创伤的态度上,影片另辟蹊径有意将抗战叙事与流行文化相结合,由此展开了别具特色的抗日叙事。影片并没如以往的抗日神剧用简单的“复仇叙事”人为掩盖了国家的自卑,掉进假想的英雄主义里难以自拔,而是从职业精英的角度来展现战争。更为难得的是予敌人以平视的角度,这种平视又不是《南京南京》里作者的刻意和观者的障碍,影片貌似有一个真实的背景环境,实则环境被推至陪体,甚至成了被架空的历史真实,加上戏谑的荒诞风格,消解了观者的障碍。影片甚至将敌人也刻画为为寻找病毒而受着迫害的一方,在特定的历史空间和精心设计的表演空间里尽量不涉及国家、民族,不讨论正义、道德。只是将敌我双方的职业军人放在一个空间进行角逐,似一场游戏,又充满平视的公平。这无疑是一种更深层面的自省,平视并非软弱,而是国族尊严和文化自信的表现。[4]影片的主要场景设置在一间日本料理店里,将彼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和在军事上强大残忍的日本双方的历史背景隔绝在外,某种意义上是双方职业军人间平等公平的决斗场,也成就了另一番平视和自省。
(三)个体与群体的对抗
管虎的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地关注普通人,在他们身上涌现出的生命力是导演对于个人价值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会被有意或无意地置于历史性、社会性的情境中,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冲突,是其影片思想同质性的另一个表现。
《斗牛》里的牛二是一个浑身污垢的小人物,与英雄形象毫无关联,而影片正是通过这个小人物去呈现个体化的真实状态和个体需要及欲望表达。影片的主题结构很复杂,在慌乱中转向一种悲剧色彩,写出了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一个小人物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荒诞人生。这种历史与个体的疏离感,使影片站在一个个体生命立场看待生活。个体生存的荒诞感与历史的无常性之间的冲突是导演特有的一种反思。
如果说《斗牛》里的反抗是一种隐性的内敛的反抗,那么《杀生》里的反抗几乎成了故事的主线。牛结实是极端符号化的,牛结实的癫狂与戏谑都是为了彰显其反制度、反权威、反主流意识形态的个体元素;而作为对立面的小镇,同样是符号化存在,小镇的“长寿”理想可被看做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隐喻,小镇也是以此建立其伦理权威与日常生活的秩序。影片从始至终都在极力揭示牛结实的死因,当牛结实被认定逾越了宗族群体的道德规范时,他面对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妥协,要么死。显然牛结实选择了后者,这个反叛的个体与代表权威的小镇之间的对抗才是他真正的死因。
(四)或悲或喜的生命礼赞
《斗牛》的苦难通过镜头语言尽收眼底:开篇牛二的大特写,风声呼吸声混合着被浓浓的恐惧和寂寥吞噬的村庄,惨遭屠戮的荒芜虚空构成了影片悲情的整体基调。但是正是在这个极端的困境里,人的至纯至美的性情并未减弱:堡垒村民众誓死保护村庄、九儿倔强而鲜活的性情、牛二情愿用生命守护承诺、企图宰牛果腹的流民最终打消了杀牛的念头,连日本兵的形象也放弃了以往惨无人道的描绘,尽可能将其还原成一群背井离乡作为人的日本兵,关注其精神世界里的乡愁和战争带给他们的伤害。影片里,镜头关注的始终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以及在极境里尚未泯灭的人性,甚至连那头牛二拼了命也要护其周全的奶牛,也从一个需要牛二施救的对象演变成一个与牛二互相支持,同为对方生命支柱的对象。在战争的悲怆里生命不论敌我、人畜,同样高贵,影片里流露出浓浓的悲情意识,同时也散发着对人性的悲悯情怀。影片充满对生命苦痛感的表述,挥之不去的荒凉和沉重让观众笑着流泪的同时感悟到生命的真实。
《杀生》延续了《斗牛》的苦难叙事,同样涉及生死的重大命题,用一种近似荒诞的方式表达出喜剧与悲剧共存的叙事主题。影片从一个外来者的视点介入,缓缓揭开了一场事先张扬的群体杀戮。影片中,当牛结实这个不羁的生命个体,被认定为逾越了宗族群体的道德规范时,他面对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妥协,要么死。牛结实触发全镇人对他的围剿,是因为他的存在打破了这个表面安详有序的小镇对长寿的理解,双方的意识形态里流露出太多的差异。小镇的村民一直守着一个长寿的理想,向往秩序井然的生活,而牛结实总是挑战这种权威与秩序:他给临终的百岁老人偷酒喝,勾搭殉葬的寡妇并与之相爱,用催情剂戏弄全镇……这个反主流反权威的个体的种种行径具有草根性和抵抗性的特征,挑战着具有宰制性的正统思想。而所谓的正统思想不过是一种犬儒态度的体现:一方面归顺、驯服,另一方面却又各怀心思。以致到了村民集体围剿牛结实时,这种自我的心思表露无遗。而只有牛结实从始至终都活得真实,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他身上的激情是原始的、真实的、肆无忌惮的,是一种源自生命本初的冲动和生命力的极力张扬。
《厨子戏子痞子》剧中人物双重身份强烈反差,轻松诙谐与严肃沉重的调子对比,以新的力量建立起崇高的英雄主义情结。面对生的希望,每个人都情愿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面对死的威胁,每个人都情愿挺身而出,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延续了抗战题材影片的英雄人物的无畏精神,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里的“断死”的精神内核。战争,无疑是一种绝境,如若人可以在绝境里选择断死,可以以一种革命的豪情包容一切,牺牲自己,便意味着可以笑看一切悲剧。对自我生命的尊重,对自由的追求并不是生命的本质,只有了解生命的等重,才可能抛开个体生命的价值,成全国家民族大义。
二、荒诞写实的影像风格
三部曲除了主题的延续外,也延续了多角色、多线索的叙事方式,不注重故事完整的叙事风格,带有一定的现代主义风格。此外,也加入了一些类型片的惯用元素:永无休止的镜头晃动、凌乱的剪接,各种风格杂糅于一体,故事场面荒诞离奇,人物叛逆疯狂,使得影片的悲喜相交的深刻主题平添了很多荒诞写实的意味。
(一)虚实时空
空间的建构,以人物带出空间,以空间衬托人物是管虎最熟悉的时空处理观念,在管虎的影片里,时空是被打乱的,并通过自己的方式重新组合在一起。同样的,在三部曲中,他将这种处理方式用到了极致。三部曲都以抗日战争的宏大历史作为背景,但其实都与抗战毫无关系,抗战的背景被完全推到了后方。影片里的世界不是一个实在的世界,而是一个虚化的世界,这个世界被虚化了之后,背景被抽空,但是逻辑并没有被抽空,它还是现实存在的,甚至多少隐喻了现实世界。“它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营造出来是有荒诞感的,其实有表现的色彩,它不允许你走到另外的颜色上去,它只能是这样。”[5]历史在影片中貌似是不在场的,但是时空更加具体可感,成了一个没有具体指向,但又无处不在的东西。
《斗牛》里作为故事重要标志的八路军或者解放军,在影片里出现的次数寥寥无几,而在牛二眼里,各类人群和他的牛是没有区别的。宏大历史和个人记忆之间的失衡带来的荒诞感无疑也表露了作者对个人与群体的思索。《杀生》的故事空间更加闭合,导演选择了不面对当下的态度,时空远离生活,远离现实,是一个完全想象和设计出来的近乎架空的历史空间。这个时空的存在是为整个寓言故事服务的。《杀生》营造了一个原始世界,那个封闭神秘的羌族寨子更像是一个高度浓缩的中国社会的缩影。《厨子戏子痞子》在一个封闭的“日本料理”店里,各种角色轮番上演着各自的闹剧,使得影片的空间具有了舞台空间的特质,与现实空间拉开了距离。
三部曲在叙事时间上都是从故事高潮点开始,然后凭借闪回,展开对事件来龙去脉的揭示。《杀生》以外来医生跟牛结实的相遇、村民对牛结实的暴打开始,以外来医生的主观视点还原一个杀人真相。《斗牛》以受到日军摧毁的满目疮痍的村落开始,闪回牛被找到之前和平年代的村庄和村民,而后顺序展开的是牛二为保护八路牛而与各路人马斗智斗勇的故事,这是主体结构。同时这一主体结构又穿插了一段一段的闪回倒叙,不断地交代前情,情节也不断被截断。
《厨子戏子痞子》同样摈弃了传统的线性叙事,大量闪回的频繁使用,使得在时间轴上,故事时间前后跳跃,错落有致,这种交叉式叙事使得人物身份能够自由地转换。影片中闪回式的叙事,“不只是一个故事事件的抽象重组。它的功能是激起我们的兴趣,去发现导致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的原因是什么”[6]119。同时,影片依靠延伸或压缩故事事件实际消耗的实践操控故事的持续时间,形成种种悬念。影片在叙事时间上极具后现代主义的杂乱、非连续性、无法预知、拼接的特点。
(二)多元视点
三部曲在视点的使用方面,最大的特点是,视点的多元化,而且叙事视点和镜头视点往往是不一样的,且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在叙事展开的过程中虽然是以角色的第一人称视点展开的,但是导演更希望以更多的视点视角去呈现这个事件,让观众各自完成立场的选择和道德的批判。通常,管虎会通过第一人称的主观视点介入影片的叙事流程之中,而后随着影片讲述又引入第三人称的客观视点对整个故事进行总体关照,并且在客观视点的讲述中又有主观视点介入叙事层面并切断客观视点的叙事进程,在主客观视点的游移与交错中既完成情节层面的叙事,又完成意蕴层面的表达。
《斗牛》用一个无奈生存、灰色调的底层农民的视角去看待战争,是一种低视角。叙事以当事人牛二的视点展开的,介绍他如何在一个险象环生的境地里与他的牛一起活下去。《杀生》叙事解开悬疑的过程,是以外来医生的视点揭秘牛结实真正死因的方式看开的。在整体叙事上二者同时都以剧中人物视点展开叙事。
《杀生》的叙事采用非线性的方式,同时故事和剧作也极具风格化,所以影片一直在找寻一种能够与之相匹配的影像风格来讲述这个非一般的故事。影片一开始,因为开场的风格直接决定影片的气质,所以开场使用了客观的纪录镜头:画面从一条河流起来,然后俯拍山峦,接着是一个旋转镜头,模拟的是一只鹰的俯瞰视点,完成了对整个神秘、封闭、诡异的羌族山寨的描摹。虽然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但是从开场镜头就给人一个先入为主的感受,引导观众相信这个虚构故事的真实性。接下来村民在拖拉机上抽打牛结实与任达华饰演的医生不期而遇的镜头,继续沿用了这种非常规拍摄,使用徒手执机拍摄,镜头角度诡异多变,画面晃动,剪辑飞快,徒手拍摄的纪实性让一个荒诞的故事可信。外来医生背牛结实回村,因为全村人都躲避和窥看,所以用了第三者的偷窥视点,给人一种危险的信号。另外,在故事发展过程中,按照导演本意,有安排过一个红头绳少女的主观镜头,虽然是一个主观视点, 但是把她作为一个客观视角来处理,只是冷静地旁观,凡是她看到的都是相对真实的画面,甚至还专门安排过牛结实与少女的几次对视和对话,她是一个牛结实愿意去相信的人。另外,用少女的视点也比较容易让观众相信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让观众客观地看到整个事件的发展全过程。正如该片摄影师宋晓飞所言:我希望摄影机所代表的叙事视点是多变的,有时引领观众,有时代表讲述者,有时审视,有时隐喻,有时参与表现,并且感性、动情。[7]
(三)隐喻寓言
隐喻性是管虎创作风格的另一大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杰姆逊指出:“在传统的观念中,任何一个故事总是和某种思想内容相联系的。所谓隐喻性,就是说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因此故事并不是它表面所呈现的那样,其真正的意义是需要解释的。”[8]90只有当我们把故事当做一个回溯个人与群体,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冲突对峙触及国民性的寓言故事来读解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影片在时空构建上的虚与实,在叙事上的跳跃错乱。《杀生》中的长寿镇虽然设置在与当下历史绝缘的民国时期的羌族小镇,但是随处可见的地震、断线的风筝、雨中的狂欢无一不彰显着这种寓言性的指涉,牛结实也成了可供精神分析的国民形象。反叛的个体无论如何张扬要在一个权威性主流型占统治地位的空间里活下去,唯一的出路便是妥协,或者躲进乌托邦似的山洞里,这才是牛二和牛结实们最终的归宿。
在《斗牛》和《杀生》里,悬念是理解影片寓言性的核心,牛二如何生?牛结实如何死?悬念不仅仅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它更接近于一个母题,一个关于生存、死亡和爱的母题。同时,表现主义光线的使用,也有力地推动了影片隐喻性的发挥。《杀生》里的光线更具有情绪化、感性、主动化的倾向。影片最后,牛结实背着棺材离开镇子,光线气氛是低角度的暖色调,牛结实把之前拿别人的东西还给大家,背景低角度的暖光打在石级上,映出牛结实的剪影,暖色调的逆光勾勒出他的轮廓,像极了耶稣受难,这时的牛结实不再是一个让所有人深恶痛绝的人,而是一个饱含导演所有正向情绪的人,以暖光背景为其送行,希望他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三、结语
《厨子戏子痞子》更像是一出影像的狂欢神话,流露着普世价值关怀下的平民意识,影片延续了《斗牛》《杀生》的黑色幽默风格,杂糅了各种类型电影的特征,混搭了黑白影像,默片字幕等其他娱乐元素,借鉴了邪典电影的相关创作手法,将历史个人化狂欢化。
纵观管虎的狂欢三部曲,不难看出导演表现的主题及风格的同质性和延续性,可以看出管虎成功地为自己打造了一种风格,一种介于荒诞与写实、魔幻与原生态的笔法之间、介于暴烈狂躁和悲情绝望的情绪之间,用整体的隐喻和象征重归宏大历史叙事。固然,在时空建置、情节设置的虚实处理,叙事闪回的频繁切换,个人与群体、个体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峙的不彻底性,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从中可以窥见管虎以后作品的整体走向。
参考文献:
[1] 管虎,赵鹏逍.从刀子到锤子——管虎访谈[J].电影艺术,2012,(4):45-48.
[2] 李存.从电影《杀生》看多主题叙事的混搭[J].电影新作,2012,(5):58-60.
[3] 孙歌.感情记忆面对相互缠绕的历史[M].台北:巨流出版社,2002.
[4] 陆嘉宁.另一种想象性解决——评《厨子戏子痞子》[J].当代电影,2014,(5):125-127.
[5] 管虎,赵鹏逍.从刀子到锤子——管虎访谈[J],电影艺术,2012,(4):45-48.
[6] [美]大卫·波德维尔.电影诗学[M].张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7] 陈刚. 心由像生——与宋晓飞谈《杀生》的摄影创作[J]. 电影艺术,2012,(4):144-149.
[8] [美]弗·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马俊】
Research on Style and Theme about Guanhu’s Carnival Trilogy
YIN Xiao-li
(Moscow Art School,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Abstract:Three films, Cow, Design of Death and The chef, the Actor, the Scoundrel are recognized as Guanhu’s carnival trilogy because of their same narrative style. The carnival trilogy inherited the director’s consistent style: multiple collage of entertainment elements, exaggerated and absurd image carnival and th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surreal representation. The carnival trilogy form a tone of the search for and persistence, introspection and criticism, individual and group and violent rage and sadness tone between despair on the theme expression which formed a kind of expression in style between myth and realism, magic and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to compose the whole expression of metaphor and allegory.
Key words:Guan Hu; carnival trilogy; theme; style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7-0092-05
收稿日期:2015-05-10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新西部片崛起与陕西电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12J025);陕西省社会科学艺术学项目:当代中国乡土儿童电影创作与传播研究(2014049);渭南师范学院研究生项目:中国八十年代以来乡土儿童电影发展研究(11YKZ044)
作者简介:尹晓利(1982—),女,陕西蒲城人,渭南师范学院莫斯科艺术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影视理论及创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