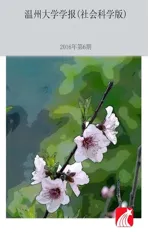婚嫁仪式与族群记忆
——关于畲瑶传统婚姻文化历史流变的再思考
2016-03-15谭静怡
谭静怡
(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湖北恩施 445000)
婚嫁仪式与族群记忆
——关于畲瑶传统婚姻文化历史流变的再思考
谭静怡
(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湖北恩施 445000)
畲瑶两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丰富多彩的传统婚姻文化,包含了较多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母权制遗俗,具有相似的历史发展脉络,呈现出了血缘婚、普那路亚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等婚姻形态。同时,两族在婚姻习俗上也表现出较大的同一性,具体表现在舅权至上、招郎入赘、从妻居和不落夫家等婚姻习俗上。因此,以畲瑶传统婚姻文化为研究对象,从溯源、发展、丰富、完善等层面,探寻畲瑶两族婚姻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既能为两族的文化亲缘关系提供有力的历史依据,又能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比较研究作出一些有益的参考。
畲瑶两族;传统婚姻文化;血缘婚;普那路亚婚;对偶婚;一夫一妻制
婚姻是人类文化与文明的起点,也是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归宿,它诠释着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底蕴。婚姻文化同其它文化一样,也有其产生、发展、丰富、完善的历史过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畲瑶两族的婚姻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改变而不断完善,走向更加文明。由于畲族与瑶族共同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都受到较为相似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民族意识、宗族组织、族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在婚姻文化领域展示出了比较相似的发展脉络。本文拟从历史学的视角,对畲瑶两族在重要时期的婚姻形态、婚姻方式、婚姻习俗等进行梳理,并尝试勾勒出两族传统婚姻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为探讨两个民族间深层的文化亲缘关系提供必要的历史佐证。
一、畲瑶传统婚姻文化的溯源
畲族与瑶族都是我国南方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早在五六千年前,他们的先民蚩尤、三苗部落便追随炎黄部落“逐鹿中原”,一起开拓了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畲瑶的族源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蛮”“南蛮”“荆蛮”“楚蛮”“蛮荆”,汉朝时被称作“盘瓠蛮”,之后在南北朝以前又称为“武陵蛮”“长沙蛮”“零陵蛮”、桂阳蛮”等,直到宋代他们才逐渐产生了较为明晰的族称。《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载:“五溪之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沅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猺、曰獠、曰獞、曰犵狫,风声习气,大略相似。”①参见∶ 李瀚章. 光绪湖南通志∶ 卷二百四十八∶ 艺文志四[M]. 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8734.可见,在历史上,畲瑶两族之间就有着深刻的种族渊源和相似的风俗习惯。畲作为专一族称,始见于南宋末年刘克庄的《漳州谕畬》,其中载:“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蛋,在漳者曰畬。”①参见∶ 刘克庄. 后村集∶ 卷九十三∶ 漳州谕畲[M]. 四部丛刊景旧钞本. 854.而瑶族族称始名于南北朝时期梁朝的“莫徭”,是免除徭役之意,最早见于唐初史学家姚思廉所撰的《梁书·张缅》,据载:“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1]至宋代,开始单独称为“瑶”,并广泛见诸于各种史籍中。从古至今,畲瑶两族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其婚姻文化也必然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逐渐演进的过程。
原始时期人类刚从猿脱离出来,过着“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②参见∶ 郑玄. 礼记∶ 卷七∶ 礼运第九[M]. 四部丛刊景宋本. 130.的群体生活。为防止野兽的攻击和抵御自然灾害,人们常常十几个或几十个人聚集成群进行生活。在繁衍过程中人们处于一种毫无规律的、不受辈分约束的血缘杂交状态,即蒙昧无知的杂婚、乱婚时期。如今这种原始的杂婚阶段,在畲瑶地区已无明显迹象,但通过解放前畲瑶某些边远山区保存的婚姻遗俗中,我们仍可窥见其残迹。解放前,畲瑶地区仍有逢年节、社节,男女成群结队聚集山岭唱歌谈情的习俗,情投意合的男女可临时性自由结合,这种遗存的乱交现象即带有原始群体乱婚色彩。如:畲族的“以歌做媒”“倚歌相和”及瑶族的“踏歌”“正月屋”“耍正月”等习俗,都是对畲瑶两族原始乱婚的生动映射。
经过几十万年的发展,随着石器工具的制造和天然火的使用,人类生产力水平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乱婚已不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人类的婚姻形态进入了血缘婚时期。血缘婚以血缘为纽带,由具有一个老祖母血统的成员组成几十人的血缘家族,生产资料归家族所共有,是人类第一个社会组织形态,也是人类婚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进步。畲瑶两族存在过血缘婚这种早期的婚姻形态,且都与盘瓠传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盘瓠传说载于《风俗通义》《山海经》《搜神记》《后汉书》等诸多史籍,是流行于畲瑶各地家喻户晓的神话,可以形象地反映出畲瑶两族早期的婚姻形态。《太平御览》引《魏略》和《搜神记》载:“高辛氏有老妇,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茧。妇人盛瓠中,覆之以盘,俄顷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2]《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亦载:盘瓠妻帝女后,“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3]从上述的记载中,我们可知盘瓠所配女子是高辛氏之女,盘瓠与高辛氏之女理应是兄妹关系,但彼此之间却结为了夫妻,而他们所生育的子女之间亦是兄妹关系,却也结成了夫妻关系,足见此时畲瑶地区盛行的婚姻形态应是兄妹婚。畲瑶两族这种兄妹为婚的神话传说,不仅可以印证畲瑶先民血缘婚的经历,还可以窥见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婚姻家庭形态的残迹。
由此可见,畲瑶两族在古代传统婚姻发展史上,都经历了杂婚与血缘婚的早期婚姻阶段。盘瓠传说不仅是畲瑶两族共有的精神信仰,也再现了两族原始的婚姻形态,而早期的婚姻遗俗则从另一个侧面又对盘瓠传说中有关畲瑶起源阶段的婚姻形态做了有力的证明。解放前,血缘婚这种早期的原始婚姻形态在畲瑶一些落后、偏远的地区仍有存在,归根到底是受两族原始社会经济残余的影响造成的。以血缘婚为代表的畲瑶起源阶段的婚姻形态是人类婚姻史上原始社会混沌时期的早期现象,也是一种原始观念的反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这种起源阶段的婚姻必定会被更进步的婚姻形态所取代。
二、畲瑶传统婚姻文化的发展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人类进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婚姻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人们渐渐认识到直系间的血缘近亲婚姻对后代的智力、身体发育都有极其不利的影响,所以对婚姻的择配范围开始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它是通过逐渐把同胞兄弟姐妹排除出婚姻关系的途径而从血缘家庭中产生出来的”[4]。这种婚姻形态被摩尔根称之为“普那路亚”婚,它标志着血缘群婚制被亚血缘群婚制所取代,形成了新的亚血缘婚家庭组织。普那路亚婚的主要特点是血统按母系计算,一定家庭范围内互相共夫共妻,实行两个氏族间男女交互的集体群婚,所生子女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作为一种婚姻形态,普那路亚婚在畲瑶社会中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其残余却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主要表现为姑舅表婚、夫兄弟婚、妻姐妹婚等遗俗之上。在畲瑶两族,舅权是非常神圣的,如:舅父之子可优先娶姑母之女,舅舅不到婚礼不成,把母亲和舅母都称作母亲、把父亲和舅父都称作父亲,这些都是母系氏族时期普那路亚婚舅权为大习俗的生动体现。由于普那路亚婚是在原始经济的土壤上滋生的,加之畲瑶地区生产资料甚不富足,所以为了防止族内财产外流,两族产生了夫兄弟婚、妻姐妹婚等婚姻形式。普那路亚婚是人类婚姻发展史上的第二个巨大进步,它对畲瑶两族的婚姻文化有着悠远的影响。
对偶婚形成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期,是与父权制一同产生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是这样描述对偶婚的:“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制度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5]41由于对偶婚时期父权制与父系社会都没有最终确立,所以依然是男子出嫁到女子氏族中,且婚后男子属于妻方氏族成员,所生子女也必须跟随母姓,这就导致出现了父子、父女不同姓的现象。对偶婚这种婚姻形态对畲瑶两族的婚姻状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该阶段产生了一种对两族后世子孙作用久远的婚姻方式,即入赘婚,此后两族长期保留着对偶婚时期男子外嫁、女子招郎的入赘习俗。民国建德县志载:“畲客则喜招女婿,可以婿为子。”[6]《渔舟续谈》亦指出:男壮则出赘,女长则招婿,皆从妇姓。此外,畲瑶在对偶婚时期还产生了服务婚与“做两头家”的婚姻方式,它们都是介于从妻居与从夫居两者之间的婚姻形态,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所有权的逐渐转移,男子在婚姻中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
通过上述对畲瑶两族舅权为大、招郎入赘为特征的表亲婚和入赘婚的叙述,可知畲瑶的普那路亚婚和对偶婚都是在生产力的进步和自然选择的推动下产生的,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但与畲族相比,瑶族在对偶婚时期呈现出的特征则更为鲜明,如我们熟知瑶族通过“爬楼”“点火把”等形式进行社交活动,来公开打“老契”、找“谷择”,建立一种临时的夫妻关系①所谓“爬楼”、“点火把”、打“老契”、找“谷择”, 是指瑶族的每个人可以通过爬楼与点火把的方式寻找自己的情人. 因此, 瑶族在正妻、正夫之外, 出现了许多副妻、副夫.。在一定程度上,瑶族这种“爬楼”“点火把”的婚姻习俗,是由于对偶婚内在的不稳定性所造成的,当然也是对偶婚阶段向一夫一妻制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普那路亚婚和对偶婚为主体的畲瑶婚姻文化发展阶段,蕴含着两族朴素的、原始的婚姻色彩,是其传统婚姻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日后畲瑶两族许多的婚姻观念、方式和礼俗都是在该阶段形成的,因此它为深入地研究畲瑶两族传统婚姻文化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三、畲瑶传统婚姻文化的丰富
畲瑶的先民三苗在部落战争中战败且遭受重挫,又加之两族受历朝统治者的挤压长期以山居生活为主,使其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处于异常落后的状态。基于上述因素的影响,畲瑶两族婚姻文化中保留了较多的传统形貌,然而由于两族对历史材料缺乏完整的保存体制,导致史料匮乏,我们已难以考证他们是何时过渡到一夫一妻制的。但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与推敲,我们可以确定在宋代畲瑶两族已经步入了“族内”的一夫一妻制时代。宋代时,北方战乱,引起大批汉人南迁,与畲民、瑶人杂居。汉人的到来,有利于畲民、瑶人学习汉族先进的婚姻观念、方式以及礼俗,这带动了畲瑶地区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发展,如从汉族地区引入了端午节;另一方面,由于汉人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民族压榨政策,致使畲瑶地区民众禁止与汉族通婚。事实上,畲瑶这种族内婚的传统,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实行的氏族外婚制与部落内婚制基础之上形成的古老婚俗。《侯官县乡土志》中提到:有盘、蓝、雷三姓,自相配偶,不与平民通婚姻。《评皇劵牒》亦载:“一准令十二姓王徭内行嫁,不许族外婚配。”[7]
宋时的畲瑶婚姻残留了原始社会多个时期的遗俗,有着鲜明的民族印迹,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首先,节日择配。《岭外代答》载:此种择偶,“各自配合,不由父母。其无配者,姑俟来岁”[8]。《文献通考》载:“十月朔日,各以聚落祭都贝大王,男女各成列,连袂相携而舞,谓之‘踏傜’。意相得,则男吚呜跃之女群,负所爱去,遂为夫妇,不由父母。”[9]可知,宋代时畲瑶延续了青年男女喜欢在节庆里选择配偶定情的习俗,且在这种择配方式中,父母仍不起太大作用;其次,夫兄弟婚。《册府元龟》记载:“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①参见∶ 王钦若. 册府元龟∶ 卷四百七十台省部[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531.《容斋随笔·渠阳蛮俗》也载:“凡昏姻,兄死弟继。”[10]畲瑶两族这种兄弟死则妻其妻的婚姻,溯其源是族外群婚制时期通婚集团之间兄弟姐妹互为夫妻遗习的一种表现形式;再次,姑舅表婚。《大诰》载:“同姓两姨,姑舅为婚。”②参见∶ 朱元璋. 大诰∶ 婚姻第二十二[M]. 明洪武内府刻本. 5.《光绪湖南通志》亦载:“姑舅之婚,他人取之,必贿男家,否则争,甚则雠杀。”③参见∶ 李瀚章. 光绪湖南通志∶ 卷四十∶ 地理志四十[M]. 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1369.此种婚姻完全属于舅权制遗俗的范畴;最后,抢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这个习俗,应当是较早的一种习俗的遗迹,那时一个部落的男子确实是用暴力到外边从别的部落为自己抢劫妻子。”[5]8而畲瑶两族的抢婚仅保存了其本来意义上的外在形式,实际上早有密约,并非真抢,只是一种佯抢的形式而已,作为部落与部落间的一种婚姻遗习,演变成了别具风格的结婚仪式。《荆川集》载:“虽其良族,亦率以抢婚为常事。”④参见∶ 唐顺之. 荆川集∶ 文集卷十四[M]. 四部丛刊景明本. 285.《奁史》也记载:“辰、沅、靖州蛮,嫁娶先密约,乃伺女于路,劫缚以归。亦忿争叫号求救,其实皆伪也。”⑤参见∶ 王初桐. 奁史∶ 卷六∶ 婚姻门二嫁娶[M]. 清嘉庆刻本. 58.抢亲是野蛮时代人类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时代一种普遍的结婚仪式,与之相对应的是女子“不落夫家”的婚俗,它是母系力量反抗以父系为中心“抢亲”婚姻仪式的一种生动体现。
除此之外,随着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两宋时期私有关系逐步渗入到畲瑶两族婚礼程序的置办中,特别是在婚礼物品的选择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不以礼金作为聘金,而是以水车、铜、盐、犁、蓑衣、斗笠、草鞋、耕牛等生活必需品当做嫁娶物品。在畲族婚礼中,主要以镰刀、斧、耙、锄等农具作为嫁妆和聘娶物。据史料记载,浙江景宁畲族“时而论婚,其聘资则定一十二金有五钱焉,其奁具则耒焉、耜焉,而镃基焉,室家于是乎成矣”[11];福建建阳畲族“嫁赀,稍充裕者予以田器,此外无他物”[12]。而瑶族婚礼中则需要少量聘礼,且生子之后要给岳父和岳母送牛、酒等物品,以示敬意。《溪峦丛笑》中“拕亲”条记载:“山猺婚娶,聘物以铜与盐,至端午约于山上,相携而归。”①参见∶ 朱辅. 溪蛮丛笑[M]. 明夷门广牍本. 5.《老学庵笔记》卷四亦载:“生子乃持牛酒拜女父母。初亦佯怒却之,邻里共劝,乃受。”[13]综上,宋时畲瑶两族婚姻仍比较自由,实行以一夫一妻制为主的族内婚,但其中却夹杂着较多的原始痕迹,呈现出血缘婚、普那路亚婚、对偶婚的综合特征,婚姻内涵较前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形成了一整套具有民族特色的婚姻文化制度。
四、畲瑶传统婚姻文化的完善
元、明、清时期,畲族与瑶族的婚姻处于一夫一妻制的完善阶段,婚仪虽简朴,但婚姻形式却呈现出多样性。元代,畲瑶两族的通婚地域范围仍很狭窄,主要盛行族内婚,亦严禁与外族通婚,但为明代以后其传统婚姻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积淀。从明代开始,畲瑶两族的婚姻逐渐步了一种全新局面,进入了其传统婚姻文化发展的完善阶段。
明代时,畲瑶两族的婚姻虽然仍存留着大量的原始气息,但与以前相比,都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其婚姻特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同姓“不婚”。《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畲族“其姓为盘、蓝、雷、钟、苟,自相婚姻,人与邻者亦不与通婚”②参见∶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 广东[M]. 稿本. 1817.。《临汀汇考》中亦提到:福建汀州畲民,“以盘、兰、雷为姓,三姓交婚。”③参见∶ 杨澜. 临汀汇考∶ 卷三∶ 畲民. 清光绪四年刻本.而浙江丽水地区畲族“竹节不分,同姓不婚”的习俗,也是对同姓不婚现象的一种形象化表达。可见,畲族婚姻实行族内自相婚配,崇尚同姓不婚。而瑶族一般同姓与异姓都可以通婚,从某种意义说来其残留了原始血缘关系下兄妹为婚的影子。《广东新语》载:曲江瑶“婚姻不辨同姓”④参见∶ 屈大均. 广东新语∶ 卷七∶ 人语[M]. 清康熙水天阁刻本. 131.,韶州府瑶史料亦载“婚姻不辨同姓”⑤参见∶ 欧樾华. 同治韶州府志∶ 卷十一∶ 舆地畧(附猺俗)[M]. 清同治刊本. 407.。然而从明代起,瑶族同姓之间通婚开始限制在三服或五服之外,这是其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根本上讲,畲瑶同姓“不婚”是原始社会族外婚的产物,是乱伦禁忌的表现形式和自然延伸。2、以歌为媒。畲瑶两族都是善歌的民族,山歌不仅是他们表达情感、交流思想的形式,也是族内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媒人”。所谓“婚姻以唱歌相谐”⑥参见∶ 阮元. 道光广东通志∶ 卷三百三十∶ 列传∶ 六十三[M]. 清道光二年刻本. 4685.,正是畲瑶“对歌求婚、自由择偶”婚姻的真实写照。《赤雅》卷上载:“十月祭多(都)贝大王,男女联袂而舞,谓之蹋摇,相悦则男腾跃跳踊,负女而去。”⑦参见∶ 邝露.赤雅∶ 卷上∶ 猺人祀典[M]. 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2.《粤述》载:“十月朔,祭都贝大王,男女连袂,相携而舞,谓之踏歌,意相得则负去。”⑧参见∶ 闵叙. 粤述[M]. 清康熙刻说铃本. 13.《广东新语》载:连山八排瑶“岁仲冬十六日,诸傜至庙为会阆。悉悬所有金帛衣饰相夸耀,傜目视其男女可婚娶者,悉遣入庙。男女分曹地坐,唱歌达旦”③。畲瑶这种以歌为媒的婚姻方式,父母一般不会过多干预,因大多在盛大的节日中举行,故简称为节日择配,实际上此种婚姻形式宋已有之,它与周去非《岭外代答·蛮俗》“踏摇”条的记载十分相似,是一种比较自由的婚姻,虽带有原始社会残习色彩,却更是畲瑶两族传统婚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媒妁订婚。明代时,一些与汉族杂居在一起的畲族和瑶族,在汉文化的长期渗透下,也开始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仪,婚姻不再完全由男女双方作主。《广东新语》卷七载:“男当意不得就女坐,女当意则就男坐。既就男坐,媒氏乃将男女衣带度量长短,相若矣,则使之挟女还家。越三日,女之父母乃送牲酒使成亲。”③《君子堂日询手镜》亦载:横州山子瑶“结婚时,男家有媒氏至女家,立门外不敢辄入,伺主人出以期告,主人不诺,即辞去,不敢言。明日复往,伺如初,主人诺,则延媒氏入饮。”[14]可知,明代畲瑶部分地区的婚姻主要由女方父母与媒氏商定,且更为看重媒妁之言。此外,明代畲瑶两族依然盛行以姑舅表婚、夫兄弟婚为代表的一些原始族外群婚制残留下的婚姻形式,它们也是其传统婚姻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清代时期,畲瑶仍实行一夫一妻制,并沿袭了明朝大部分的婚姻观念、方式和礼俗,如:有限制的同姓为婚、招郎入屋的入赘婚、舅权至上的姑舅表婚等。《广东通志》记潮州府畲瑶事说:“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三姓自为婚。”①参见∶ 阮元. 道光广东通志[M]. 清道光二年刻本. 4681.《罗浮山志会编》卷九载:“分盘、蓝、雷、钟、苟五姓,自相婚姻,土人与邻者亦不与通。”②参见∶ 宋广业. 罗浮山志会编∶ 卷九[M]. 清康熙刻本. 95.《蓝山县图志》卷十四载:瑶“昏多赘婿,权在女子”[15]。《白山司志》卷九中指出:“白山徭人……岁时祭祀,男女跳跃,歌唱相悦为婚。”③参见∶ 王言纪. 白山司志∶ 卷九∶ 风俗[M]. 清道光十年抄本.《同治溆浦县志》卷八也提到:瑶族嫁娶亦用媒妁,或郎舅结姻,男家备聘金七两,鸡六只,又(幼)鸡一只,名曰押礼。如舅氏无子,以女子他姓,则女家备银三两送外家,曰回娘礼④参见∶ 齐德五. 同治溆浦县志: 卷八: 风俗[M].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依据上述史料,我们发现清代畲瑶两族的婚姻制度,依然保留着较为浓郁的原始朴素色彩,但仍有一些习俗有所改变,如:节日里对歌择偶的婚姻方式,以前这种婚姻由男女双方自行决定,清朝时这种婚配最终演变为由父母决定。各地方志中对畲瑶两族用媒定亲的婚姻方式也有所记载。《乾隆雅州府志》载:“婚用媒妁”⑤参见∶ 曹抡彬. 乾隆雅州府志∶ 卷十一∶ 夷俗[M]. 清乾隆四年刊本. 243.。《乾隆开化府志》卷九中提到:瑶人,婚用媒。而《道光广南府志》卷二也指出:瑶人,婚用媒。在历史上,畲瑶两族是严格限制与外族通婚的,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落后封闭的自然经济存留下较为原始、传统及保守的婚姻状态;二是汉族统治者长期执行的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使少数民族产生了民族间的心理隔阂。到清朝时这种限制依旧没有改变,称畲客为“化外之民”。《过山榜》中也明确规定:“一准王徭族子孙之女,不许嫁与汉民百姓为婚。”⑥参见∶ 评王劵牒[M].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抄本.除此之外,清代史籍上对瑶族的婚姻形态又有所补充,如我们熟识的“不落夫家”,即女子结婚后即返母家居住较长一段时间,一般在怀孕或生子后才始归夫家。《同治溆浦县志》卷八指出:溆浦瑶“女子初嫁仍居母家,岁余及生育后,则于腊月二十五六日归夫家。”⑦参见∶ 齐德五. 同治溆浦县志∶ 卷八∶ 风俗[M].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同治溆浦县志》卷八指出:溆浦瑶“女子初嫁仍居母家,岁余及生育后,则于腊月二十五六日归夫家。”①参见∶ 齐德五. 同治溆浦县志: 卷八: 风俗[M].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雍正广西通志》载:河池瑶“嫁时不置衣被,其女过宿即回母家。”②参见∶ 金鉷. 雍正广西通志∶ 卷九十三[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39.从“不落夫家”的婚俗中,我们可以窥见母系氏族时期婚俗的某些残留形式,事实上此俗苗族也有之,究竟是何时产生今已无从考证,而畲族在历史文献和调查材料中均未见此俗,仅在福建惠安县新宁一个蓝姓畲族村中有一例,经调查研究是受当地汉族影响产生的。
任何一个民族的婚姻文化都是同一定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是客观实际与历史发展的产物。从民族形成与演变的角度研究畲瑶两族传统婚姻的演变,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族古老的婚姻文化中,含有较多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母权制残迹,主要表现在舅权、从妻居、抢婚、不落夫家等婚俗之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畲瑶两族人民创造了许许多多有着本民族特色的传统婚姻文化,通过对其传统婚姻历史脉络的梳理,不仅有利于理顺两族传统婚姻的源流,还有助于影射出畲瑶等南方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婚俗风情。其婚姻特点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其他民族那里也都相应地存在,这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互相影响、共同进步、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各民族间友好为邻、和谐为伴的历史明证。
[1]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502.
[2] 李昉. 太平御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3476.
[3]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833.
[4] 马克思.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20.
[5]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C]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6] 夏日璈, 王韧. 民国建德县志∶ 卷三∶ 风俗志∶ 时尚土礼[C] //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府县志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3∶ 46.
[7] 《过山榜》编辑组. 瑶族《过山榜》选编[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9.
[8] 周去非. 岭外代答校注∶ 卷十∶ 踏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423.
[9] 马端临. 文献通考∶ 卷三百二十八∶ 四裔考五[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9024.
[10] 洪迈. 容斋随笔[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821.
[11] 周杰修, 严用光, 叶笃贞. 同治景宁县志∶ 卷十二∶ 风土志∶ 风俗[C] //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3∶ 453.
[12] 姚有则, 万文衡. 民国建阳县志∶ 卷八∶ 礼俗[C] //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国地方志集成∶ 福建府县志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231.
[13] 陆游. 老学庵笔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45.
[14] 王济. 君子堂日询手镜[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
[15] 雷飞鹏. 中国方志类书∶ 蓝山县图志∶ 卷十四∶ 礼俗篇第五之四徭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0∶1042.
Wedding Ceremony and Ethnic Memory——Restudy on the Traditional Marriage Culture and Historical Changes of She and Yao Ethnic Groups
TAN Jingyi
(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stitute, Hube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Enshi, China 445000)
∶ Both She ethnic group and Yao ethnic group has formed colorful traditional marriage culture in the long history, including quite a few matriarchy relic from the primitive matriarchal clan society. The two ethnics have simila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keleton and present such marriage forms as consanguineous marriage, Punaluan marriage, couple marriage and the system of monogamy. Meanwhile, they also show a greater identity in marriage customs in the fields of avunculate first, son-in-law adoption, uxorilocal residence and uxorilocal customs. Therefore, taking the traditional marriage culture of She and Yao ethnic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he and Yao’s marriage culture is explored from the source, development, abundence, perfection and other aspects. The study provides not only a powerful historical basis for the cultural affinities of the two communities,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beneficial references to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es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cultures.
She and Yao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Marriage Culture; Consanguineous Marriage; Punaluan Marriage; Couple Marriage; Monogamy.
K892.22
A
1674-3555(2016)06-0080-08
10.3875/j.issn.1674-3555.2016.06.011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15-08-20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一般项目(2015-GM-205);湖北民族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MY2014B033)
谭静怡(1982- ),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