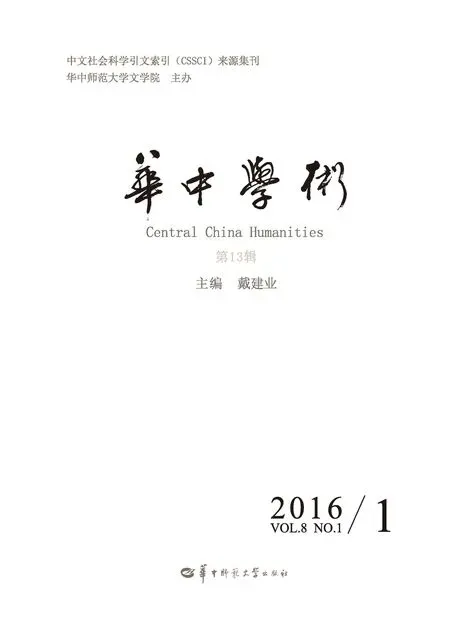鲁迅小说中“油滑”手法与戏剧的关系透视
2016-03-15孙淑芳
孙淑芳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650092)
鲁迅小说中“油滑”手法与戏剧的关系透视
孙淑芳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650092)
内容摘要:鲁迅小说的“油滑”手法,固然得益于鲁迅多方面的艺术素养,但从直接关系来说,则是鲁迅借鉴戏剧,特别是中国民间戏曲审美经验的成功尝试。“油滑”不仅具有如同“丑角”以滑稽姿态对现实进行揭露和讽刺的艺术效果,而且具有如同中西方戏剧有意制造观众与舞台生活幻景的距离,引导读者对小说整体进行理性思考和评价的间离效果。
关键词:鲁迅小说;油滑;戏剧;丑角;讽刺;间离效果
“油滑”问题在鲁迅研究中成为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比较活跃的领域”[1]。研究者不仅围绕着“油滑”的优点和缺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主要是从小说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如果我们对“油滑”的产生作审美情结溯源式的分析,就会发现鲁迅小说与戏剧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研究表明,和底层民众的精神共鸣以及和民间戏曲的血肉联系,构成了鲁迅童年故乡记忆和民间记忆的核心,它们是鲁迅生命成长的底气,是他的艺术之根,因此,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民间戏曲对鲁迅小说潜在而深刻的影响。鲁迅小说的“油滑”手法,固然得益于鲁迅多方面的艺术素养,但从直接的关系来说,则可以看作是鲁迅借鉴戏剧,特别是中国民间戏曲审美经验的成功尝试。
一、鲁迅运用“油滑”手法的初衷
在《故事新编·序言》中,鲁迅专门谈到了运用“油滑”手法的由来:开始试做古今题材结合的第一篇历史小说《补天》时,刚开始写作还是非常认真的,不想写到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碰巧看见某人对汪静之诗作《蕙的风》的批评,此人说要含泪哀求青年,不要再写诸如此类的文字。这样可怜的阴险让我感到滑稽。于是再继续写《补天》这篇小说时,就“止不住”在女娲两腿之间有意安排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形象,以示对“含泪批评”家——胡梦华假道学的厌恶与讽刺,“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2]。由此看来,“油滑”也就是不认真,显然,这并非指创作态度而言(鲁迅一向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是毋庸置疑的),而是指在进行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时,突破了“‘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3]的约束与规定,在古代的人和事中插入现代的生活内容,以达到嘲讽、讥刺时弊的目的。
鲁迅在《补天》中安排古衣冠的小丈夫的具体情节为:在女娲正要点火炼石补天时,出现了古衣冠的小丈夫,小丈夫本来是要指责女娲裸体有失道德礼法规范的“禽兽行”的,然而却偏站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等发现女娲看到自己时,就仓皇地递上写有劝谏文字的竹片,并背诵上面与女娲语言根本不通的古文字,当被置之不理后竟呜咽地哭起来。古衣冠的小丈夫这一形象明显具有喜剧性和滑稽性,他并非主要人物,只是源于现实而虚构的穿插性的喜剧人物。他以古人面貌出现,同小说整体保持着一定的情节上的关系,同时,他又可以脱离小说所规定的具体的时代环境而表现出某些现代性的言行或细节,因而不仅对现实中的人和事具有嘲讽和批判的作用,也可以使人们易于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产生理解和作出评价。我们看到,“古衣冠的小丈夫”并没有影响女娲宏伟壮美的形象,反而以其猥琐滑稽的形象反衬出女娲更为瑰丽动人的伟大创造力,将女娲写活了,使女娲的创造精神、牺牲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大大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鲁迅还专门针对胡梦华事件在写《补天》的同一年月发表了杂文《反对“含泪”的批评家》,由此可见,小丈夫这一穿插性喜剧人物的现实感是十分强烈的。而小丈夫滑稽的言行就是对现实中所谓道德家的有力讽刺。这些喜剧性穿插人物丑恶虚伪的嘴脸和卑琐破坏的行径就是对现实中破坏者的影射和讽刺。
诚如茅盾曾经所作出的十分中肯而恰切的评价:“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锐利的观察,战斗的热情和创作的艺术,非但 ‘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且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茅盾认为此种手法的精妙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面是“用现代眼光去解释古事”,而另一面更深层的用意则是: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的爱憎[4]。所以,从鲁迅所谈到的开始运用“油滑”手法的直接原因来看,“油滑”是指在鲁迅小说中设置穿插性的影射现实的喜剧人物或类似戏剧中的丑角人物,从而体现出来的喜剧性质或插科打诨的性质,具有揭批和嘲讽的艺术效果,它是鲁迅用以揭露、讽刺、批评、抨击社会现状的特殊手段,是与黑暗、丑恶战斗的一种有效力量。
关于真正开始运用“油滑”手法的直接原因,固然如鲁迅所言,是受了胡梦华“含泪批评”的刺激。但这只是偶然事件的触发,实际上鲁迅在小说创作中采用“油滑”的手法却是必然的。从1922年11月写成的《补天》,到1935年12月编成的《故事新编》这本历史小说集,鲁迅对于“油滑”手法的青睐与坚持,“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5],“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6]。这显然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所能持久影响得了的。况且,鲁迅虽然强调的是《故事新编》中的小说惯用“油滑”手法,而事实上,“油滑”已成为鲁迅小说在表现手法上的总体特点。也就是说,《呐喊》、《彷徨》这两部以现实题材创作的小说集中,同样潜移默化地渗透着“油滑”。对于“油滑”手法的利弊,鲁迅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如此看重“油滑”,所考虑的正是其所带来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中更为有利的一面。如果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鲁迅小说中的“油滑”手法与戏剧,尤其是与绍兴民间戏曲有着更为密切与本质的联系。“油滑”手法不仅是对绍兴民间戏曲美学特点的直接吸收和借鉴,而且具有与中西方戏剧艺术类似的美学效果。
二、鲁迅小说的“油滑”与中国戏曲中丑角的关系
鲁迅从《补天》开始有意识的“油滑”写作,是与其在家乡绍兴所接触到的民间戏曲审美趣味的强劲影响分不开的。在杂文《二丑艺术》中,鲁迅专门写到了浙东戏班中的一种叫作二花脸(雅称二丑)的脚色。这种脚色扮演的身份是倚靠贵公子的拳师或清客,他在剧中担有一定的演出任务,表演的是侍奉上等阶层所沾染的腐朽生活习气和被权门豢养仗势欺人的生活态度。但“二丑”的特色在于,他在表演中可以脱离剧情,可以旁若无人地直接面向台下的看客揭示出他公子的缺点,并摇头扮鬼脸加以嘲弄和戏谑。所以,鲁迅说二丑是智识阶级,知道所倚靠的不能长久,以后还要另有攀附,必须得装着和他正侍奉的公子并非一伙,因而戏里戏外两副面孔。小百姓在生活中看透了这一种人,于是通过加工提炼,制定了二花脸的脚色,使现实中的这种人物在戏台上呈现。
二丑脚色这种古今交错的审美特点,其他戏曲种类中的丑角或丑旦也都有,即有时可以脱离剧情和规定的时代环境而表现某些现代性的语言细节。丑旦,目连戏中称为花旦,鲁迅在《大观园的人才》中指出了这一角色的特点:“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7]因为丑角和丑旦常扮演滑稽风趣或奸诈阴险的人物,所以都可以油腔滑调,可以插科打诨,他们脱离剧情的穿插性的现代语言不仅没有让人感觉破坏了剧情整体的演出,造成了时代的错乱,反而是使整体演出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起到揭露和讽刺现实的作用。可以说,以“油滑”的姿态讽刺现实就是中国戏曲中丑角和丑旦的审美特征。中国戏曲中丑角和丑旦的这一独特而普遍存在的审美传统一直深为人民所喜爱。对于丑角脱离剧情插入与台下观众直接交流的现代生活语言细节,鲁迅深谙其中的美学意义,尤其强调并重视它所具有的娱乐与讽刺功能:“绍兴戏文中,一向是官员秀才用官话,堂倌狱卒用土话的,也就是生,旦,净大抵用官话,丑用土话。我想,这也并非全为了用这来区别人的上下,雅俗,好坏,还有一个大原因,是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使本地的看客们能够彻底的了解。那么,这关系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8]
丑角在对鲁迅有着深刻影响的目连戏中的出演是相当多的,成为目连戏经久不衰、备受欢迎的重要艺术手段。目连戏自东汉初形成以后就因其本身所具有的宗教化戏剧的弹性框架结构优势,在民间被大胆演义,使得情节大肆扩充,在目连救母的结构核心和主要故事情节中,穿插的小故事越来越多。这些穿插性小故事都相对独立,具有诙谐油滑的喜剧特点,由丑角表演。它们是由人民自己创作,反映社会现实的故事,平时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都借丑角的滑稽表演得到了畅快淋漓的表现。鲁迅十分赞赏和推崇民间目连戏中运用丑角艺术手段所表现出来的清新刚健的民风,幽默诙谐的情趣和嘲弄讽刺的效果,认为:“这是真的农民和手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借目连的巡行来贯串许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连救母记》是完全不同的。”“比起希腊的伊索,俄国的梭罗古勃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9]
如“跳活无常”这一折戏中,活无常“领了老婆儿子去捡一个路边的猪头吃;谁知道那不是猪头,却是狗头,当他去捡时,竟给狗咬了一口。于是,他便拍拍蒲扇骂起狗来了。他用各种各样的话语,骂了各种各样的狗。这时,台下观众中间,便不断地发出哄笑,觉得他骂得好,有意思,诙谐好笑”[10]。观众如此赞赏,是因为活无常扮演的丑角以滑稽的表演,机智地痛骂了社会现实中各种各样的“狗”,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鲁迅一直到晚年都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段《武松打虎》的戏:“甲乙两人,一强一弱,扮着戏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换,却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说怨话,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11]这里,甲乙两人的插科打诨,实际上就是对现实生活中压迫者的戏谑和讽刺。由此可见,人们喜爱目连戏,是喜爱那些穿插进去的喜剧性小故事,是丑角的插科打诨所产生的讽刺现实的艺术效果,而并非目连救母的主要故事。目连戏中丑角艺术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将丑角的审美特征归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丑角均为喜剧性人物,可以脱离剧情面向观众,插科打诨,穿插现代性的语言,其表演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第二,以滑稽的形态,引人发笑,并进行大胆地揭露和讽刺。第三,无论是正面丑角还是反面丑角,都为表达主题思想服务。在鲁迅小说中,我们发现,鲁迅同样用了很多喜剧性人物,把他们鼻子涂白,让他们像戏曲中的丑角一样尽情表演,自我揭露,显现出现实中的原形。
如果将《补天》中古衣冠的小丈夫与戏曲中的丑角放在一起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两者所使用的艺术手法及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则是类似的。它们所运用的都是古今交融的艺术手法,在历史故事的整体中穿插现代生活的言行细节,从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能够油滑机智地对“今”也即现实进行嘲讽和批评。鲁迅小说中的“油滑”与丑角的艺术效果类同,重要的是取其在诙谐滑稽的笑声中机智而深刻的讽刺效果,摒弃了中国旧剧中丑角脱离剧情的喜剧性穿插只是为了取悦台下权贵或引人捧腹的庸俗功能。鲁迅儿时深受绍兴民间戏剧的浸染,对戏剧中丑角的审美特点十分熟悉,自然也就能够把民间百姓赋予丑角辛辣而深刻的讽刺力量、艺术地表达自己爱憎情感的手法灵活恰当地移用到小说之中。正像亲自前往鲁迅故乡观看了绍兴地方戏演出的王西彦所指出的那样:从鲁迅所喜爱“游园吊打”、“女吊”和“跳活无常”这样的绍兴戏剧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老百姓的憎恨、同情和喜爱。而鲁迅,也便是以老百姓的爱憎为自己的爱憎的,他的感情正和老百姓相通”,绍兴戏“也是狼的奶汁的一部分,所以鲁迅才始终不能忘怀,要 ‘时时反顾’,直到逝世前一个月还在写象 ‘女吊’那样的回忆文章”[12]。所以,茅盾认为,鲁迅《故事新编》中所运用的古今错综交融的“油滑”手法虽然被众多人研究和学习,但是“就现在所见的成绩而言,终未免进退失据,于 ‘古’既不尽信,于 ‘今’亦失其攻刺之的”,因为鲁迅更深层的用心——以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鲜明的爱憎情感,是“我们虽能理会,能吟味,却未能学而几及”的[13]。
鲁迅小说中的“油滑”不仅表现在穿插性的喜剧人物和诙谐滑稽的故事情节(现代性语言和细节)上,也表现在叙述者风趣幽默的评论上。
在《故事新编》中,如同丑角式的穿插性的喜剧人物几乎每篇都有,他们既与故事整体保持情节和结构上的联系,又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现代性的语言和细节,这种古今交错的艺术手法往往在一种诙谐滑稽的审美之中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如《奔月》中的喜剧性穿插体现在一些现代性的语言上,如嫦娥说羿:“并不算老,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女乙说羿:“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女辛说羿:“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这些话都是有现实根据的,高长虹在《狂飙》第五期(1926年11月)《走到出版界》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攻击鲁迅以“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鲁迅曾对此做出过回应:“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思想界之权威’乎,抑 ‘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 ‘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战士’?”[14]小说中人物如同丑角插科打诨似的,突然冒出这些话来评说羿,让人觉得十分滑稽,就连羿自己也认为这些评说与自己根本不符,简直是“放屁”,因为这些语言具有现实性,也就产生了讽刺现实的艺术效果。这些插科打诨似的语言并没有损害主要人物羿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反而把羿的形象写“活”了,使羿的身上具有了现实的投影,特别是鲁迅当时孤独寂寞心情的投影,这就是运用喜剧性穿插的重要意义。
《非攻》中同样运用喜剧性人物更好地塑造了另一位“中国的脊梁”——墨子。墨子身体力行、脚踏实地、机智勇敢地为民奔波的形象,是通过穿插性喜剧人物曹公子鼓吹“民气”的表演来展现的。曹公子在宋国做了两年官之后就变了样,开始玩“气”嚷“死”,只见他夸张地将“手在空中一挥”,大叫道:“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这实际上是影射民国当时的现实情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而表面上却故意发一些慷慨激昂的空论。所以曹公子小丑式的演说是对当时国民政府“民气救国”谬论的巧妙讽刺。
可见,鲁迅历史小说中善用喜剧性穿插人物的这一“油滑”手法,与中国传统戏曲中丑角艺术诙谐滑稽和能够脱离作品规定的时代环境而自由发挥的审美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讽刺现实的艺术效果是相似的。并且,喜剧性穿插人物的运用可以使作者超出历史小说集体经验的写作方式,立足于现实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个人的价值评判,将主要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写“活”,在“油滑”的姿态中拓展了叙事空间。这与丑角以戏境为掩护,演员借用剧中人物的声口表达自己的心声,从而进行讽刺世相丑恶和不平的艺术手法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采薇》中丑角式人物小丙君对伯夷、叔齐揶揄式的评论——“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实际上就是作者立足于现实的个人价值评判。鲁迅正是通过伯夷、叔齐的“通体矛盾”才更鲜明地展示出了他们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并更有力地讽刺和批判了他们的处事态度。这与丑角可以插科打诨,不需拘泥于剧情和规定的时代环境的艺术特点显然是类似的,所以也就写出了伯夷、叔齐的现实意义。另外,《出关》中驻守函谷关的公差关官(关尹喜)对老子进行了讽刺性的嘲笑。鲁迅在《〈出关〉的“关”》一文中言明自己“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15],也就是说,作者借喜剧性人物插科打诨式的议论实际上是表达出了自己立足于现实对老子的个人价值评判。当读者在小说的结尾看到关尹喜把老子的《道德经》“放在堆着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的积满灰尘的架子上时,自然会对老子的无为哲学及其现代崇拜者投去鄙夷和讽刺的笑。所以,《出关》这一历史小说中穿插的喜剧性人物身上所具有的诙谐、幽默的现代性语言和细节不仅揭露和讽刺了现实中的人和事,而且因其体现了作者对于主要历史人物的个人价值评判而把老子写“活”了,具有深化主题的作用。
另外,《起死》中的巡士,《铸剑》中的瘪脸少年,《理水》中文化山上的官场学者、考察灾情的昏庸大员、头上被打出疙瘩的奴性十足的下民代表等,也都是喜剧性人物,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由以上所论可见,《故事新编》中所穿插的喜剧性人物大都是虚构出来的,类似于中国传统戏剧中插科打诨的丑角,鲁迅积极汲取戏曲艺术审美经验而采用的这一“油滑”手法,在历史小说个人写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喜剧性人物的穿插,产生了如同丑角艺术的魅力效应,不仅以诙谐滑稽的表演机智地讽刺了现实,而且使作者所要着重写出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更“活”了。正是这一手法的运用,使他“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16]。作者之所以这样来塑造历史人物,目的是照见现实中各色人的灵魂,由此可见鲁迅始终关注现实的一腔热情。
鲁迅小说中的“油滑”,除了表现在运用穿插性的喜剧人物之外,还表现在叙述者风趣幽默的评论上。如《出关》中当叙述者叙述到老子到达函谷关,想要爬城,但坐骑青牛却没有办法搬出城外时,叙述者插入了脱离小说情节叙述和时代背景的言论:“倘要搬,得用起重机,无奈这时鲁般和墨翟还都没有出世,老子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玩意。”这一超出老子时代环境的滑稽议论,显然是对老子哲学在现实中无用的嘲弄与讽刺,这比直接地揭批更能暴露出老子的狼狈相。在鲁迅小说中,叙述者风趣幽默的评论其实也正像中国戏曲中丑角的插科打诨一样,并且同样具有丑角机智地进行讽刺的艺术效果,我们将在第三部分对其进行重点论述。
总而言之,鲁迅小说中的“油滑”根本区别于“中国自以为的滑稽”,中国当时文学上普遍的“油滑”即“轻薄,猥亵”[17],“和真的滑稽有别”[18],真的滑稽是指“有情滑稽”[19],是善意而热情的讽刺[20]。然而“对于讽刺文学,中国人其实是不大欢迎的”[21],所以借鉴中国戏曲丑角艺术的“油滑”手法就成为鲁迅明知其“弊”但仍坚持运用的战斗法宝之一。
三、鲁迅小说的“油滑”与戏剧的间离效果
鲁迅小说中穿插性的喜剧人物和叙述者风趣幽默的评论,不仅具有中国戏曲丑角讽刺的艺术效果,还呈现出戏剧间离效果的艺术魅力,可以使读者以清醒的头脑对小说中叙述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理性的价值判断。间离效果,也被译为间情法或陌生化效果。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曾在潜心研究中国戏曲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篇相当著名的论文——《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他在文中论述了中国古典戏剧对于陌生化效果的运用,认为:中国古典戏曲十分精通并擅长运用陌生化效果[22],而运用这种手法的用意“就是要在表演的时候,防止观众与剧中人物在感情上完全融合为一。接受或拒绝剧中的观点或情节应该是在观众的意识范围内进行”[23]。布莱希特为了更明确说明陌生化效果,他就中国古典戏曲与西方戏剧中观众、演员、角色三者之间的戏剧化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中国古典戏曲中观众、演员与角色是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而在西方戏剧中是感情共鸣的关系;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演员制造了观众与角色之间的距离,西方戏剧中的演员则千方百计地拉近观众与角色之间的距离。具体来说,中国戏曲中的丑角、中西方戏剧中的旁白角色、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都是戏剧中创造间离效果的特殊艺术手段。
就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角而言,具有演员和角色的双重身份,所以,丑角行当都可以脱离所扮演的规定角色而以演员自己的身份直接面向观众,表现出某种现代性的语言和细节,然后再回到角色的扮演中去。那么丑角以演员身份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的语言和细节,就可以起到引导观众或读者(针对戏剧文学而言)对作品整体进行思考和评价的间离效果的作用。丑角这种古今交错的插科打诨,是中国戏曲独特的审美习惯和艺术传统。深谙其中意味的鲁迅,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便融入了这一戏剧因素。现代读者虽然不会相信在古远的大禹时代会有人大谈维他命、遗传学、莎士比亚、募捐计划,会有学者用英语交流,也不会相信有警察吹着警笛、拿着警棍与几千年前的庄子打交道,更不会相信商周时期的小丙君能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然而,却能在重叠的心理默契、忍俊不禁的喜剧调侃与古今“间离”中受到感染和启发,并形成明确的是非观念和鲜明的爱憎立场。
布莱希特之所以要在德国尝试建立非亚里士多德式(不是建立在感情共鸣的基础上)的戏剧,是因为他认为:一种新的戏剧要想实现其社会批判的作用以及它对社会改造的历史记录任务,在所有艺术效果中,陌生化效果将是必要的[24]。由此可见,布莱希特如此重视中国古典戏曲的陌生化效果,是看中它对社会的作用。只不过在德国的史诗戏剧中,创造陌生化效果的“目的主要是使被表现的事件历史化”[25]。而鲁迅小说正好相反,创造陌生化的效果是为了使被表现的事件现实化。穿插喜剧性人物的运用实际上正是鲁迅创造陌生化效果的一种艺术手段。喜剧性人物的设置就是为了防止读者在感情上完全与《故事新编》中所写的主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融合为一,才在读者和历史人物之间制造了距离。从《故事新编》各篇的主要人物来看,鲁迅是严格地根据历史文献来加以描写的,但是鲁迅重视的是在现实中如何正确看待古人。鲁迅在《古人并不纯厚》一文中认为,古人的面目在历史上并未得以真实地呈现,而是经过了后人的选择,“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26],“试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27],“清朝曾有钦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28]。所以,鲁迅写历史小说就是要写出古代人物真实的精神面貌。正像捷克学者普实克评价的那样:鲁迅用冷嘲热讽的幽默笔调,不仅剥去了历史人物所拥有的传统荣誉,而且扯掉了浪漫主义的历史观环绕在他们头上的光圈,从而使这些历史人物脚踏实地地回到现实世界中来[29]。鲁迅在《故事新编》写作中有意识地借鉴了民间戏曲艺术的同时,也借鉴了中国古典戏曲的间离效果,如同丑角似的喜剧性人物的穿插即在小说中起到了间离读者与所叙述的主要历史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使读者处于观察的立场,清醒而正确地认识古代人物的精神实质,明白历史发展的真谛。
鲁迅小说中除了运用穿插喜剧性人物创造间离效果以外,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戏剧化关系同样可以产生间离效果。如同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在剧中担任着叙述剧情、调节氛围、联系观众的艺术职能一样,也如同戏剧中的旁白角色,在剧中仅面向观众,具有揭示人物内心隐秘、深入认识人物形象的功用一般,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常常通过与读者的直接对话,在读者和故事情节之间制造距离而获得一种间离效果。叙述者在叙述中偶尔会风趣地和读者进行三言两语的交谈,所谈内容尽管与故事情节有某种联系,但绝无纠纷,已经暂时脱离小说的情境。而间离效果的产生有助于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冷静地去看待小说中所表现的人物和事件,并在具有间离作用的叙述者的引导下作出自己理性的判断。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主要论述采用“油滑”手法的叙述者风趣幽默的评论,并非要对所有的可以产生间离效果的叙述者的语言进行分析。
在《阿Q正传》中,当写到阿Q自从用手拧了小尼姑的面颊后就总想着女人时,叙述者插进了直接面向读者的议论:“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叙述者这一风趣幽默的评论虽然源于阿Q想女人的心理,但却是暂停了有关阿Q的故事情节的叙述,直接对读者发表的议论。这样,叙述者就创造了读者与阿Q及其故事之间的距离,使读者此时从有关阿Q的故事情节中摆脱出来,开始像个“观察者”一样通过叙述者的议论去冷静思考阿Q这一形象及其有关故事。女人是祸水,中国男人做不成圣贤,责任全在女人!如此荒谬、滑稽的逻辑和论调,是鲁迅用传统观念针对阿Q总想女人的事实所发的议论,显然具有反讽意味。鲁迅对于女人的真实看法在其杂文中可以看到:“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30]叙述者的反语,间离了读者与阿Q情感上的融合和思想上的呼应,使读者在忍俊不禁的喜剧调侃中受到感染和启发,产生了一种从旁“观察”的警惕心理,从而引导读者重新认识阿Q与女人的关系。叙述者在面向读者议论之前,描写了阿Q总想女人的心理:“他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而阿Q的这一想法正体现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思想。由此可见,阿Q为女人所困,并不在于女人本身的“可恶”,而恰恰在于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叙述者的间离,深刻地揭露了儒家学说的荒谬和反动,并使读者清醒地认识到,因为这种谬论长期流传,不免也就毒害了像阿Q这样的劳动人民。
《风波》中赵七爷一出场,叙述者就从故事中人物的眼光出发对赵七爷作了郑重而“客观”的介绍:“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方圆三十里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紧接着,叙述者插入了一段体现鲁迅主观认识的富有调侃性的评论:“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从叙述者这一幽默风趣、居高临下的评论来看,一般人眼中“出色人物兼学问家”的赵七爷变成了一个迂腐、无知、可笑的人物,赵七爷的学问简直少得可怜。叙述者此时脱离了作品中故事环境的影响,只把读者作为他的交流对象,起到了间离读者与故事中人物的作用。从运用“油滑”手法的这一喜剧性评论中,读者看到了与前面叙述的赵七爷截然相反的另一面目,从而开始重新审视故事中人物对赵七爷仰慕崇敬的看法。当读者带着辨识的立场去看待赵七爷时,就不难认清赵七爷迂腐、无知、可笑的真面目,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周围人对赵七爷仰慕崇敬之情的荒谬与滑稽,进而认识到广大农民群众落后、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由以上论述可见,鲁迅小说中叙述者风趣幽默的议论创造了戏剧般的间离效果,能够引导读者走出误区,深入认识和正确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深刻的思想意义,并形成鲜明的爱憎立场和明确的是非观念。
从以上论述可见,鲁迅小说中叙述者幽默风趣的评论不仅具有讽刺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可以创造间离效果。这种间离效果的创造所运用的艺术手段与戏剧中所采用的手段是类似的。古希腊悲剧在演出时会安排有合唱队,而且这个合唱队贯穿演出始终,它主要面向观众,一般不参与剧中的活动。歌队可以向观众解释剧情,而且歌队合唱还可以对剧中人物、事件进行评价和感叹,代表诗人发表政治见解和哲学思想,有时预示有恐怖事件的发生,具有间离效果的作用。另一方面,中西方戏剧中常用旁白作为对话的补充来表现人物隐秘的内心活动,旁白是剧中其他人物并不了解,只向观众披露的,因此观众可以从中获得艺术享受。旁白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和展示情节的进程。鲁迅小说中叙述者的功能就如同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和中西方戏剧中的旁白角色一样,在客观叙述中有时会穿插进叙述者幽默风趣的评论,从而产生间离效果,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幽默风趣的评论与小说的故事情节并无纠葛,既不负责解释剧情,也不负责展示情节的进程,它是鲁迅居高临下极具智慧的启发和引导的评论。
《高老夫子》中,当老朋友黄三看完聘书问高老夫子是不是改了名字时,作者没有同样运用人物的对话来回答,而是紧接着写了一段叙述性的语言:“但高老夫子只是高傲地一笑;他的确改了名字了。然而黄三只会打牌,到现在还没有留心新学问,新艺术。他既不知道有一个俄国大文豪高尔基,又怎么说得通这改名的深远的意义呢?”表面看来,这段叙述是采用同一视角的客观叙述,而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视角的不同。开头写高老夫子“高傲地一笑”是事实的叙述,属于现实情况。而从“他的确改了名字”到最后的叙述,则是叙述者在面向读者来揭示高老夫子此时的内心活动,是高老夫子没有说出来的想法。可以说,叙述者充当了类似戏剧中向观众披露内心隐秘的旁白角色,扮演了对小说中人物——高老夫子内心进行解说和评论且只能让读者知道的人。这一旁白式的诙谐议论,明褒实贬,形式上模拟高老夫子内心的真实想法,表现高老夫子是与黄三截然不同的“博学”、“高雅”的“维新”人士;事实上却是鲁迅俯视高老夫子的巧妙揭露,是对高老夫子的调侃和揶揄,在鲁迅眼里,高老夫子不过是不学无术,用维新装点门面,比黄三好不了多少的无耻之徒。叙述者在这里有意制造了读者和高老夫子之间的距离,防止读者为高老夫子改名的表象所迷惑而失去分析和批判能力,使读者能够在这一诙谐议论引导下冷静地透视高老夫子形象的真面目并深入理解鲁迅塑造这一形象所具有的现实意义,这就是鲁迅利用叙述者喜剧性的评论所创造出来的陌生化效果。它成功地打破了那种认为故事和人物是“生活”而非“艺术”的幼稚幻觉,帮助读者顺利地走出思维的误区,并作出正确的价值评判。
综上所述,鲁迅小说中“油滑”的产生并非源于偶然事件,它是鲁迅深受民间戏曲影响,有意或无意识地借鉴戏剧审美经验所创造的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法。“油滑”手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穿插的喜剧性人物;二是运用叙述者风趣幽默的评论。它们不仅具有与戏剧艺术相似的审美特点,而且呈现出与戏剧艺术类同的审美效果:其一是如同丑角插科打诨,以滑稽姿态对现实进行揭露和讽刺的艺术效果;其二是如同中西方戏剧有意制造观众与舞台生活幻景的距离,引导读者对作品整体进行理性思考和评价的间离效果。这两大效果无疑生动地体现了鲁迅意欲以小说服务现实,与现实抗争的杂文文艺思想。
∗本文为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小说与戏剧关系的三维透视”【15 BZW 162】和2013年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鲁迅小说的艺术个性与绍兴地方戏”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郑家建:《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故事新编〉诗学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38页。
[2]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3页。
[3]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4页。
[4]茅盾:《〈玄武门之变〉序》,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茅盾》(下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407页。
[5]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4页。
[6]鲁迅:《书信·360201致黎烈文》,《鲁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7]鲁迅:《伪自由书·大观园的人才》,《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5页。
[8]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
[9]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103页。
[10]王西彦:《论阿Q和他的悲剧》,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第214页。
[11]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12]王西彦:《论阿Q和他的悲剧》,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第215页。
[13]茅盾:《〈玄武门之变〉序》,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茅盾》(下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407页。
[14]鲁迅:《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8页。
[15]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40页。
[16]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4页。
[17]鲁迅:《准风月谈·“滑稽”例解》,《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0页。
[18]鲁迅:《准风月谈·“滑稽”例解》,《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0页。
[19]鲁迅:《准风月谈·“滑稽”例解》,《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0页。
[20]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1页。
[21]鲁迅:《书信·360201致黎烈文》,《鲁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22][德]贝·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张黎、景岱灵,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192页。
[23][德]贝·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张黎、景岱灵,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191页。
[24][德]贝·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张黎、景岱灵,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202页。
[25][德]贝·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张黎、景岱灵,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199页。
[26]鲁迅:《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3页。
[27]鲁迅:《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2页。
[28]鲁迅:《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3页。
[29][捷克]J.普实克:《鲁迅》,《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
[30]鲁迅:《且介亭杂文·阿金》,《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