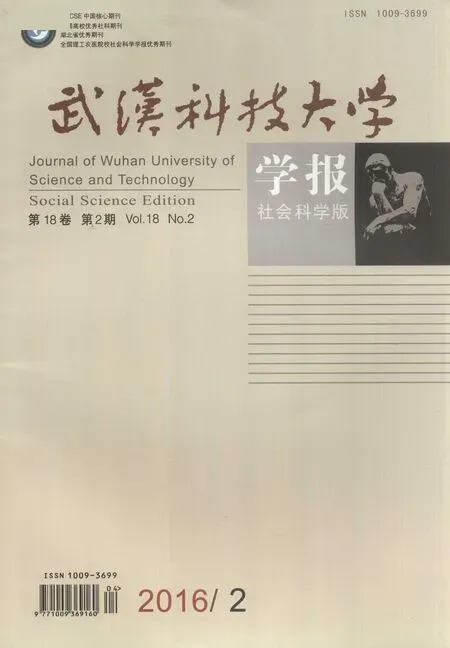从“梁启超宪草”看民初中间势力的政制抉择
2016-03-14陈浩
陈 浩
(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1)
从“梁启超宪草”看民初中间势力的政制抉择
陈浩
(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出身清末改良派-立宪派的梁启超在民初立于官僚派与革命派之间,秉持温和、稳健的政治主张,成为中间势力之代表人物。梁启超拟定的宪法草案接受有限度的内阁制,寻求立法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他一方面反对新兴革命派势力要求国会独大,主张给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固有势力保留一定的权力空间;另一方面又反对袁世凯的行政专权与独裁。“梁启超宪草”所体现的温和主张为民初政治转型提供了一条理想路径,虽然在实践中未能被贯彻,但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民初;宪法草案;中间势力;权力平衡;内阁制
辛亥革命成功后,官僚派势力、新兴革命派势力以及原立宪派势力相互间纵横捭阖,成为政坛上最为关键的三股力量。在民初政争中,官僚派势力与新兴革命派势力截然对立,而原立宪派势力则构成中间力量调和于两者之间,其政治主张多具温和、稳健色彩,梁启超即为此派势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长期流亡国外的他在1912年底回国后即被卷入政治纷争之中,他一方面积极促成中间势力之整合,推动组织进步党;另一方面又创办《庸言》杂志,发表大量政论,积极宣传中间派之政策主张,从而成为此派势力的代言人与精神领袖。
在民初,制定宪法并从根本上厘定国家体制,是政治纷争中的核心环节。正式国会以此为首要任务,民间人士也纷纷自拟宪法草案[1]。不同政治势力基于自身立场与利益的考量,在制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基本主张。作为中间势力代表的梁启超也积极投身其中,他为进步党拟定了一份宪法草案《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以下简称“梁启超宪草”),充分体现了他在这一阶段的政治主张,成为本党人士与中间势力讨论制宪问题的指南。“梁启超宪草”首先发表在1913年8月15日出版的《庸言》杂志上,共有11章、95条,在某些重要条文后还附有梁启超的相关说明。对比于民初出现的其他几份倾向性较强的宪法性文件,“梁启超宪草”则显得更为温和、稳健,从中可以看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间派势力对于民初政制模式的抉择。
一、梁启超民初论政的理论基础
梁启超在民初论政的两大理论基础为“开明专制”论和“政治对抗力”论。“开明专制”论是1906年梁启超与革命派的论战中提出的,进入民国后梁启超延续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思路,他虽然表示认可新生的共和制度,但是基于对民众政治程度之较低评估,仍然主张将“开明专制”精神融入新兴的共和体制,有效控制民众政治参与的程度①。从日本回国前,他致信已当选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指出“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2]401,将实施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在作为政治强人的袁世凯身上。但梁启超显然又不希望这种“开明专制”走向极端,为此他在民初又及时提出了所谓的“政治对抗力”理论,强调要允许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互相对抗,反对任何单一势力独占政治舞台,他指出只有“强健实在之对抗力”才能避免“政治上之力而成为绝对”,从而避免走向专制引发革命、革命重塑专制的恶性循环[3]2595-2597。在民初的政治环境下,“开明专制”论与“政治对抗力”论各有针对性的言说对象:“开明专制”论主要针对刚刚登上权力舞台的新兴革命派势力而言,反对他们在政治上提出过分的权力要求;“政治对抗力”论则主要针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既有官僚派势力,反对他们在共和旗帜下垄断政治权力。这种双重的针对性与梁启超在民初主张裁抑“莠民社会之乱暴势力”、同时矫正“官僚社会之腐败势力”是一致的,体现了以他为首的进步党中间派势力最基本的政治立场②[3]2589-2590。
在民初有关宪法的争论中,国民党与进步党分别以“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国”相号召,而“梁启超宪草”第1条即规定:中华民国永远定为统一共和国,其主权以本宪法所定之各机关行之。在相关说明中梁启超指出“无论何种国体,主权皆在国家”。他特别强调此论“久成定说”,在他看来,民初南京临时政府所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规定“主权在民”,实际上“与国家性质不相容”[3]2615。梁启超的“主权在国”主张是受到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影响,他在1903年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就表示接受伯伦知理“主权在国”的理论,认为其能驳正博丹和卢梭的“专制的君主主权”与“专制的国民主权”之谬误,“有功于国家学也最巨”[3]1075。可见梁启超对于“主权在国”的主张是相当一贯的,而此理论对于在政治上长期以中间温和派自居的梁启超来说也是非常适宜的。这一理论是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德国作为一种应对激进人民主权理论之反动而出现的,其本身“调和反革命的旧制度与新生的制度”,可以说是“一种与调和妥协的政治状况相适应的主权学说”[4]70,这非常符合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在民初的自我定位。正是借助于这一理论,多数出身原立宪派的这些中间势力可以很自然地否弃君主主权论而坦然接受新生的共和体制并顺势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专权,同时他们还能借此拒绝以部分革命派人士为代表的激进民权派所一再标榜的是为“共和国体最要之原理”[5]26的“主权在民说”。通过将主权归之于抽象无形的国家,他们否认所谓人民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主权,也就釜底抽薪式地否定了激进民权派以“主权人民”之代表自居的任何可能,这无疑为防止激进民权派“盗窃主权”进而在政治上提出过分的权力要求打了一剂预防针,正契合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间派势力在民初的基本政治立场。
二、有限度的内阁制
“梁启超宪草”对民初中间势力政治立场的彰显尤其体现在对共和体制的规划之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关制度选择的首要问题是政府究竟采取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实行的是总统制,而《临时约法》则改为内阁制,但当时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显然又不愿成为内阁制下的虚位元首,一时间论争迭起。总体而言,包括进步党与国民党在内的政党人士中主张内阁制者还是占据多数,这从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讨论宪法草案时几乎一致通过内阁制即可见一斑[6]35-37。梁启超在“梁启超宪草”中也选择了内阁制,“梁启超宪草”第66条规定:国务员赞襄总统,对于众议院担负责任。大总统所发关于国务之文书,须经国务员一人以上之副署。第36条规定:众议院认国务员施政失当时,得以不信任之意,牒达大总统。[3]2619上述国务员对于总统文书之副署权、对于众议院负责任而众议院又有不信任投票权,这些都是典型的内阁制设计。
梁启超赞成内阁制而反对总统制,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即出于对总统专制的顾虑,他认为此种制度下总统无权解散国会而国会亦不能对政府投不信任票,行政部并不对立法部负责,实为“无责任政府”。他指出总统制下欲求政府之强有力而赋予总统以大权,人民对其不满之时国会又不能借势以去之,则政府“必返于专制”而易酿成人民革命,所以他认为这种总统大权体制根本上乃是“革命之媒介”[3]2438-2439。由于在民初政坛上占据总统职位的是袁世凯,梁启超反对总统制实际上也就或多或少体现了他对于袁世凯的疑虑。他在民初政争中虽然较倾向于作为政治强人的袁世凯并寄望其能行开明专制,但他对袁世凯的信任显然不是绝对的,其中包含着对其个人专权的疑虑,在这一点上,他与激进民权派人士有着一定的共通之处。梁启超的这种态度在进步党中是具有代表性的,表明他们在与袁世凯的合作中自有其底线,正凸显了其作为中间势力的一个侧面,而这也是他们最终与袁世凯分道扬镳的根源所在。
但是另一方面,梁启超也不想以内阁制来完全架空袁世凯,推行所谓完全的政党内阁制,即以议会多数派之领袖出任政府总理、掌握行政实权而使总统处于虚位元首之地位。这也是当时不少革命派——国民党人士的主张,如宋教仁一再宣称,“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7]460,“欲完善政府,须有政党内阁”[7]446。戴季陶也强调,“欲救中国危亡,定政府之内讧,以唯一之政策,收健全之效果者,舍完全之政党内阁而外无政策”[8]436。至于梁启超,他虽然承认政党内阁制为“民权之极轨”,并且认为我国未来之政治“自当以行完全政党内阁为究竟”[3]2501-2503。但对于当下能否立即实行此种制度,他有着相当的疑虑,强调“不可不从各方面之观察而审慎出之”[9]596,尤其认为“其能见诸实事与否,则恒观政党之状态以为衡”,而民初政党发展之不成熟,梁启超是早有认知的[3]2638-2641,在他看来,在没有形成成熟的两党制前提下,所谓的政党内阁制注定将是不稳定的。
不过关于缓行政党内阁制,实际上更关键的考量还在于如何处理袁世凯的权力。梁启超很清楚权力欲极强的袁世凯显然不愿意退居虚位元首的地位,而在民初共和初立的政治环境下,企图仅以议会多数支持来架空掌握北洋军的袁世凯,显然是太不现实的。要想使初生的共和制度得以成功启动,其初必须给予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以一定的权力空间以换取其对于制度转型的支持,所以不宜对其猜忌过渡、防闲过甚,以免激起反动。梁启超实际上期望在总统与内阁权力之间维持一种可能的动态平衡,待时机成熟再逐渐向内阁制方向倾斜转化,这种设想彰显了其作为中间派的身份特征,也将他与部分革命派人士为代表的激进民权派区隔开来。
三、具体的权力规划
在民初,袁世凯掌握行政实权,而政党人士则控制着国会。原革命派改组而来的国民党身为国会第一大党③,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政治态度相对激进。在这种形势下,平衡新旧势力之关键即在于如何处理行政与立法两部门之间的关系。此时,梁启超主张平衡两部门之间的权力,他指出“政府与国会同为宪法上直接独立之机关”,“其尊相并,初不缘其所自出而判贵贱”[3]2578,两者本立于同等之地位,他尤其强调要杜绝某一机关专制的情形出现,不可“以一机关压他机关,而被压者变为隶属”[3]2564,他将此视为吾国宪法所当有的三大精神之一。梁启超处理立法与行政部门之间关系的此种立场,既不同于袁世凯极力抬高行政权力以致走向个人专权的做法,也有别于激进民权派人士所强调的“国会至上”观点。在激进民权派人士看来,议会之可否即为国民之可否,政府不得再有异议,“行政权应受立法权之指挥”,是共和制度应有之义[5]18-21。梁启超平衡行政与立法两部门权力的主张与民初的《中华民国宪法案》(以下简称“天坛宪草”)和《中华民国约法》(以下简称“袁记约法”)④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宪法修改权与解释权方面。“天坛宪草”规定议会独占宪法修正案提议权并拥有宪法解释权,加之其本已掌握的宪法制定权和修正案议决权,从而使宪法完全成为议会一手包办之物,体现了强烈的排外性。尤其宪法解释权使其能“随时任意扩充其职权之范围,而减削行政、司法他部之势力”[10]63。而“梁启超宪草”的相关规定则要公允得多,其中第95条规定大总统与国会两院都有权提议修正宪法,而行使宪法解释权的国家顾问院也由国会选举与总统任命的成员共同组成。可见梁启超反对议会独占宪法修正权与解释权,而主张同时赋予行政部门一定的发言权。出于同样的考虑,实际上梁启超也不赞成国会单独制宪的规定,而主张组织专门的宪法起草机关[3]2481-2483。
关于总统任命国务员是否需要国会同意以及总统是否有权解散国会,是民初政争中最为关键的两个问题。在当时完全政党内阁制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国务员之任命成为总统与国会角力的重要战场。以不少国民党人士为代表的激进民权派多希望借助国会的同意权来促进政党内阁之实现,他们强调,“有同意权正所以保持真正内阁制之稳固而与责任内阁由议会中多数党组成之原则方不至违背”[11]6,“天坛宪草”也规定“国务总理之任命,须经众议院同意”。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则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同意权有损行政部门之独立而“与责任内阁制之精神不能相容”[3]2623,“在政治上更有百害而无一利”。梁启超指出宪法规定了国会的弹劾权,若国会于行政用人既同意于前而又弹劾于后则不免自相矛盾,他特别强调在议会中小党林立、无稳定多数党的情况下,同意权往往成为小党要挟总统的利器[3]2577-2578。基于上述认识,“梁启超宪草”中虽然没有废弃同意权,但是却将此权给予了性质迥异于国会的国家顾问院,而梁启超设计的这个国家顾问院是一个融合了议会与行政部门势力的机构,相对于国会单独掌握同意权,这一设计对行政势力已经作出了较大的妥协。
与同意权连带的则是解散权。解散权作为内阁制下政府制衡议会不信任投票权的一种手段,可以说是平衡立法与行政部门关系的最关键工具。但在民初以不少国民党人士为代表的激进民权派却反对政府具有此种权力,在他们看来,“解散权与代议制度根本上不相容,必欲有解散权即不啻将代议制度根本推翻”[11]31。而“天坛宪草”虽然确认了总统解散众议院的权力,但同时却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条件,总统必须得到参议院出席会议人员2/3以上多数同意。梁启超对于上述主张都不赞成,在他看来,“欲政府善而且强而不使有解散权或有之而不能贯彻,是犹欲北行而南其辙”[3]2621。解散权与弹劾权相对待,议会既有权弹劾内阁则政府即当有权提请解散议会,否则即成“矛盾之法理”。梁启超强调解散权乃是政府与国会产生冲突时求解于国民的一种必要手段,否则只能国会弹劾政府或投不信任票,则政府必将屈服于国会而失去独立机关之性质[3]2577-2579。对于“天坛宪草”中总统解散众议院需要参议院同意的规定,梁启超认为这无疑会加大行使解散权的难度,尤其当两院为同一政党控制时此同意必将形同虚设,“犹之自卫者有枪而无弹”[9]678。鉴于上述认知,梁启超在自拟宪草中规定大总统有权解散议会之两院或一院,而只需得到国家顾问院的同意,其主张是十分温和的。
关于国会的弹劾权,“梁启超宪草”规定国会认为大总统有谋叛行为或者国务员有违法行为时,两院联合组成“国民特会”以总员2/3以上出席,出席者2/3以上同意即可通过弹劾案,然后交由国务裁判院审理,后者由最高法院与平政院(即行政法院)选出9名法官组成,由作为第三者的法官来审理弹劾案是比较合理的。而“天坛宪草”却规定众议院所提出的弹劾案交由同为议会之一部分的参议院来审理,对于作为被诉方的行政官员来说则显然有失公允。袁世凯一手炮制的“袁记约法”取消了立法院对于国务卿与各部总长的弹劾权,而只规定其违法时将受肃政厅(平政院下设机构)之纠弹与平政院审理。立法院虽然可以弹劾大总统,但是要求甚高:需要议员4/5以上出席、出席者3/4以上同意方可通过,即通过弹劾案需要议员总数3/5以上同意。这几乎无形中剥夺了国会对于大总统的弹劾权,可以说在“袁记约法”中国会的弹劾权几乎消失于无形。对于这种极端弱化国会行政监督权的做法,梁启超显然不能接受。如果说在同意权和解散权等问题上,梁启超主要是站在行政部门一边反对过分扩张国会权力,那么在弹劾权问题上,对比于“袁记约法”的规定,梁启超的态度则同时凸显了其预防行政专权的一面。
在其他方面“袁记约法”规定实行总统制,所以议会不能对政府投不信任票,但却又赋予总统内阁制下方有的解散议会的权力,自相矛盾之间更显袁世凯的专权企图。“梁启超宪草”采行内阁制,在规定总统解散权的同时,也规定了议会的不信任投票权。“袁记约法”还特别规定当立法院对于大总统要求复议的法案以出席者2/3以上仍坚持前议时,大总统如认为其“于内治外交有重大危害,或执行有重大障碍时,经参政院之同意,得不公布之”。而有鉴于参政院完全由大总统任命成员组成,可以说这项规定实际上使得总统对于国会所通过法案具有了绝对的否决权,严重侵犯了立法院最基本的职能。“梁启超宪草”中虽然也规定了总统要求议会复议的权力,但若是议会以出席者2/3以上通过则法案自然生效,对比于“袁记约法”,这种规定要正常、温和得多。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梁启超宪草”既反对国会独大又反对行政专权,追求国会与政府权力平衡的主旨。为了凸显这一特色,最后我们将“天坛宪草”规定设立的国会委员会以及“袁记约法”规定设立的参政院与“梁启超宪草”中设置的国家顾问院进行一下比较。“天坛宪草”规定国会闭会期间设立国会委员会,代表国会监督政府。总统任命总理、发布紧急命令,政府进行财政紧急处分都必须有其同意,而其成员由国会两院各选20人组成,可见完全是国会的附属机构。但考诸法理,既然紧急命令、财政紧急处分事后都要经过下一期国会追认,则国会委员会之设立显然多此一举,其与国会的大量雷同职权则很容易引发“双重责任”的问题,所以时人即曾指出其根本为“叠床架屋”之设计[12]。实际上“天坛宪草”的此种设计正凸显了其一贯的扩张议会权力之主旨,彰显了国会对于袁世凯的过分猜疑,其中包含着强烈的“因人立法”意味。“袁记约法”中的参政院,则是走向了另一极端,其成员完全由大总统任命,却拥有巨大职权,它有权制定正式宪法草案并初步审定之,有权解释宪法,可以同意大总统解散立法院、发布紧急命令与紧急财政处分,甚至在立法院成立以前还可以代行其职权。一个非民选机构而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袁世凯借此完成行政专权的企图一目了然。“梁启超宪草”中有关国家顾问院的设计则显得非常温和,它虽然也具有很大职权,诸如大总统任命总理、解散国会、提议修正宪法等都需要其同意,宪法亦由其解释,其人员乃由两院各选举4人、大总统任命5人组成,融合了国会与政府两部门的势力。梁启超解释之所以以国会所举占多数是出于“重民意”的考虑,而必参以总统所荐者,则旨在“谋立法部与行政部之圆融”[3]2623。梁启超不讳言此机构之设置旨在限制行政权,但也比较充分地参考了行政部门自身的意见,体现了他平衡国会与政府的一贯主张,而这也是整个“梁启超宪草”的根本宗旨所在。
四、结语
民国初年共和体制的建立是近代中国民主转型的开端,此一转型之成功与否一方面固然与各种客观因素诸如历史文化传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和转型过程中各种政治势力的策略选择与彼此互动有关。民主转型的成功离不开各方参与势力之间的相互妥协与调和,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民主国家是通过谈判、妥协和协议而产生的”,“在政治精英中进行谈判和妥协是民主化进程的核心”[13]202-203。
在民初的政治环境下,身为中间势力之代表的梁启超正秉持着上述理念,旨在调和以袁世凯官僚派为代表的既有势力和以革命党人为代表的新兴势力。在他看来,新旧势力只有避免各自走极端、相互妥协,才能形成权力分享与流动的稳定机制从而使新兴的民主制度逐渐走向正轨。一方面必须给予新兴势力参与政治的机会,另一方面又要给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既有势力保留一定的权力空间。“梁启超宪草”中具体的政制规划也正是基于上述理念,突出体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之温和、稳健的政治理念。
在民初的政治转型过程中,以原革命派势力为代表的激进民权派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既有势力偏偏是各走极端,前者要求政党内阁制,企图完全架空袁世凯;而后者则最终干脆走向了专制称帝的不归路。在这种浓厚的不妥协气氛中,近代中国初次的民主政治试验走向失败,苦心号召政治妥协的梁启超最终也没能真正发挥塑造舆情、引领社会的中坚作用。但现实的不成功不代表理论上的无价值,正如邹谠所指出的那样,广泛存在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精英权力斗争过程中的“全赢全输”模式,即赢者通吃、败者尽输,乃是中国政治不能走上正轨的根源之一[14]118,而“与全赢或全输传统的彻底绝裂是任何政治进步的必要条件”[14]160。就此而言,“梁启超宪草”所反映出的平衡新旧势力、强调调和为国的政治理念,对于反思民初政治转型的失败仍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我们推动真正的民主建设仍然不无借鉴价值。
注释:
①梁启超在1906年最初阐述“开明专制”论时,否定当时中国有立即实行共和制甚至君主立宪制的可能,也就不赞成立即召集议会,这是最纯粹意义上的“开明专制”论。而他在民初的论政是以接受共和、议会体制为前提的,只不过强调要控制政治参与的程度,一定程度上落实“开明专制”的“精神”。这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开明专制”论。
②当然对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间势力而言,应对“暴烈派”与“腐败派”也存在着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梁启超曾表示现阶段当以“暴烈派”为“第一敌”而“先注全力与抗”,对于“腐败派”则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这与进步党联合袁世凯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不过这种联合也并非是无原则的,他同时强调“党人所最宜猛省”之处,正在于“或遂为腐败派所利用”。
③除跨党者不计外,众议院596个议席中国民党占据269席,参议院274个议席中国民党占据123席,总计两院870议席,国民党392席,占45%左右。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间势力组建的进步党只拥有223席,占总席次的25.6%,远落后于国民党。参见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252页)。
④参见夏新华,胡旭晟,刘鄂,等:《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42-449页,第471-476页)。
参考文献
[1]夏新华,刘鄂. 民初私拟宪草研究[J]. 中外法学,2007(3):318-338.
[2]丁文江,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张品兴. 梁启超全集[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小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 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M].毕洪海,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5]王宠惠. 王宠惠法学文集[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6]宪法起草委员会第6次会议[C]∥宪法起草委员会. 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录:第一册,1913.
[7]陈旭麓. 宋教仁集: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8]唐文权,桑兵. 戴季陶集[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9]夏晓红.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陈茹玄. 中国宪法史[M]. 上海:世界书局,1933.
[11]宪法起草委员会第9次会议[C]∥宪法起草委员会. 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录:第一册,1913.
[12]张东荪.国会委员会之研究[J].庸言,1913(20):1-11.
[13]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8.
[14]邹谠.中国革命再解释[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周莉]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6)02-0228-05
作者简介:陈浩,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外政治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0